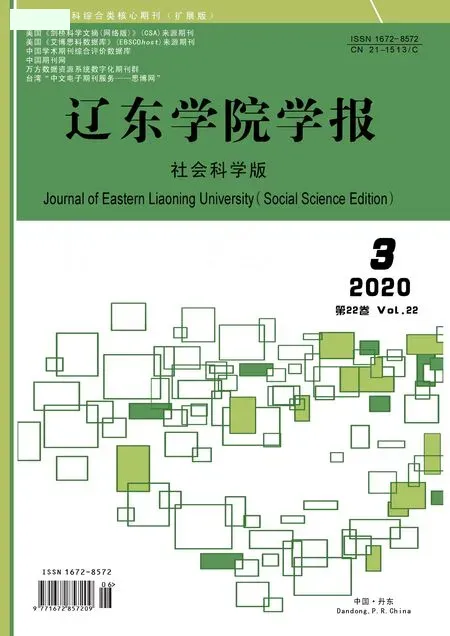爱与殇的交织
——论冯沅君小说的创作特点
李岳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主要兴起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中国。到了“五四”时期,寻求情感的自由表达和抒发,情绪全面泛滥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精神解放和个体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的桎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与革命的浪潮。“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界的传播以 “创造社”为核心,强调小说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这种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和其他主观型的叙述小说还辐射到了当时敏感多情的女作家群体。其中,以冯沅君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积极迎合了浪漫主义的浪潮,书写了受到“五四”精神启蒙的新型知识女性力求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理想爱情和个性解放,却又难以承受社会的压力,陷入生命或人生困境为主题的系列小说,将“自我表现”的主观性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
笔者将以浪漫主义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结合冯沅君的具体作品从“选取题材”“创作文体”“抒情意象”“情感基调”几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位浪漫主义女作家特殊的创作风格和情感意义。
一、选材切近自我
浪漫主义讲究主观性,“自我表现”就是主观性的体现之一。 “自我表现”的原则运用于浪漫主义小说,首先表现为题材的切近自我。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曾说过:“一切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于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1]60。”冯沅君身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亲身感受到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在那样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混乱时代的生活境遇,因而能深刻地认识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那便是如何反抗陈腐的包办婚姻制度,寻求自由的爱情。旧时代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制度实质是对女性身心的禁锢,是真正的“制度的牢笼”。只有打破这不合理的制度,勇敢地追爱,才能开启女性解放的大门。所以,冯沅君的小说选取了知识女性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追求幸福生活的题材,并且在一些人物身上还有作者自身或身边亲友的影子。比如《误点》小说中的继之“两兄一母”的家庭人物配置是根据冯沅君自身家庭成员的关系图为参照设计的。有所不同的是在生活中的兄弟母亲是开明的,支持沅君的读书和恋爱;而小说中的俨之、凝之俩兄弟和母亲是继之追求向往生活和爱情的“亲情枷锁”,束缚她的自由。在选取写作题材方面,冯沅君采用“切近自我”的方式,以作者周围的环境和亲人朋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个情感充沛、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因为是作者熟悉的题材,因而在写作时才能更好地捕捉到作品中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使人物形象更生活化、人物情感更真实化,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二、主观宣泄的创作方式
主观性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最突出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故内心活动的描写往往要多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浪漫主义作品要求人物内心情绪情感的宣泄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冯沅君在主观情感宣泄这方面,运用了直抒胸臆的方式,将人物内心的情感或情绪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同时代的女作家庐隐认为:“文学创作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2]。对于精心雕饰情感一类的文艺作品,她是不赞同的。她说:“创作者当时的情感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其本色描写出来,因感情的调节,而成一种和谐的美,这种作品,虽说是为艺术的艺术,但其价值是万不容否认的了。”[3]冯沅君也因深受“创造社”浪漫主义主张的影响,十分重视内心情感的抒发。单纯地呐喊、咆哮、悲泣只能停留在情感宣泄的表层,要想呈现出更强有力的表达,还得依托一定的媒介洞察人物的内心深处,触及最核心的情感点。也许是女性天生就懂得如何表露情感,在创作方式上,冯沅君采用了书信、日记体的形式作为内心情感最佳的宣泄方式。如此做法一方面,使得文章不再以故事情节为重心,而被人物无结构的情感描述所代替,虽然书信日记体的运用可能会令故事情节变得拖沓繁复,但如果运用恰当可以极大地增强情感的表现力度,直击读者的内心;另一方面,通过以第一视角来创作书信、日记,有利于更直白地释放人物内心的情感情绪,使得人物的情感愈发真实。同时人们阅读这类文体时,能够更好地拉近读者与作品人物间的距离,产生情感的共鸣。如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全文实际就是纗华给爱人青霭写的信。述说了自己被家人囚禁隔绝在屋内,迫使嫁人而宁死不从的决心。在这“书信体”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大胆描写两人自由恋爱时的种种美好回忆,当写到两人的亲吻和庄重纯洁的性爱时,喜悦、幸福之情便在文中弥漫开来;当写到刘家提亲、被迫出嫁时愤怒、决绝之情顿时跃然纸上;在写到设法逃脱囚禁,计划失败则以死相抗时勇敢坚毅之情又体现出来。情感和情绪随着平白叙述的自然流露使得文中虽没有对纗华的具体形象进行描写,但是从叙述的过程中却不难看出纗华俨然是具有“五四”个性解放精神、反抗封建礼教的新知识女性青年的典型代表。由此看来,日记、书信体在作品中的大量运用在主观宣泄方面确实有着独特且难以取代的作用。
三、丰富的抒情意象
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在进行“自我宣泄”的同时还带有抒情性的色彩。抒情可分为主观抒情和客观抒情。主观抒情自然就是存在于“自我宣泄”之中的情感表达,具体表现为直抒胸臆的手法;而客观抒情具体的表现是寄情于物,将人物的情感寄托在山水虫鱼等客观事物当中,假借这些客观事物的外形特征或生活习性间接地表达出人物内心的情感,此时,这些事物就由普通的客观存在转变成了文学人物的抒情意象。这些意象凝聚了主体对客体的感受,暗示性强,能够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意义。冯沅君小说中对情感世界的建造除了直露地表达内心冲动外,还利用了许多具有特定意义的外部意象作为人物心理情愫的延伸,使作品呈现出一派浓郁的抒情色调。
冯沅君的小说里有许多抒情的景物描写,各类花草、霞光、山色、烟雾、黑夜、枯木等都是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意象,但不同的景物代表着不同的情绪。明亮、壮阔的意象一般代表着欢快、热烈的情绪;而黯淡、冷寂的意象则一般象征着痛苦和悲哀。如在《旅行》中写到女主人公纗华与爱人青霭在火车上看到的景色:“可是又因为微阴的缘故,在浮云稀薄处露出的淡黄色的阳光,及空气中所含的水气把火车的烟筒中喷出的烟,作成了弹熟的棉花似的,白而且轻的气体。微风过处,由大而小的一团一团的渐渐分散,只余最后的一点儿荡漾空际。”[4]8此处的景物梦幻轻快,带有少女恋爱时的甜蜜感。“棉花似的烟雾”既显示女主人公内心充满着幸福、欢愉的情感,又体现出她对自由的向往,希望像烟雾般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荡漾,同时也隐喻出对自由恋爱的崇敬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又如《误点》中继之收到电报南归之时,写到九月北方的景色:“不耐风霜的树木,已零落得半剩枯瘦的杈枒;较耐风霜者虽依旧枝叶蓊蔚,但终似曾经践踏陵辱的人们,在努力挣扎中显出无限憔悴可怜的情调。”[4]45这时候的继之自知电报召回肯定与家庭订婚事宜相关,想到要和自己相爱的渔湘分离,嫁给不喜欢的人,过着不幸福的日子,和渔湘再也无法有重逢的一天。心中顿时涌起万千的惆怅却无力改变,就像这北方的枯木,在风霜雨雪中痛苦地挣扎,却始终逃脱不了被摧残的命运。
四、浓重的情感基调
中国的浪漫主义者效仿西方追求精神的自由,渴望超越平凡,体现为由爱、美、自由构成的单纯信仰,然而他们又不得不直面黑暗的现实。所以中国特殊的国情注定中国的浪漫主义者不会像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浪漫派一样坚守个人主义,表现出征服一切的扩张性激情。反而是受到了同时期涌入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使浪漫主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振奋民族精神相联系,形成激愤型浪漫主义;另一种,遵循非理性的方向向内心深入,体味生命本身的孤独忧愁和人生的坎坷无援,形成感伤型浪漫主义。这两种类型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五四”时期对文人影响极大,冯沅君也在其列。
冯沅君小说的情感基调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里虽然有着淡淡的感伤情调,但这种“感伤”有别于同时代行文风格相近的“庐隐式的感伤”。除去外部条件的压迫外,庐隐的感伤多是出自人物的想象和思考,是属于在极度自卑或面对挫折后自主生发的感伤;冯沅君的感伤更主要是来源于人物的牺牲或妥协,是敢于放弃年轻的生命向苦难宣战或在艰难的抉择面前无奈妥协的感伤。相比较而言,庐隐的作品感伤气息更为浓郁,而冯沅君的前期作品往往带有力度和刚性,倒把感伤气息冲淡了不少。前者的“自发性”更强;后者“被动性”更强。
其实,冯沅君一开始作品的风格趋向于郭沫若的“激愤型浪漫主义”,她曾热烈称赞郭沫若《漂流三部曲》里《十字架》的一节:“觉得作者的热情,直像正在爆发时节的火山,凡在他左近的东西,都要被熔化了。”[1]64所以她前期的小说也充满了这样炽热的情感。如像《隔绝》和《隔绝之后》,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故事,当纗华因为要自由婚恋,不愿服从家庭安排嫁给刘家,被囚禁在房间之中。情人不得相见,纗华女士就以书信的形式写给自己心爱的人青霭(《隔绝之后》的士轸),她大胆地描写男女恋爱的场景,将男女间亲密的行为全部展露在世人和读者面前,这在当时来说,无异于是对旧时代的社会和封建礼教制度宣战,这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冯沅君借女主人公之口热情讴歌了自由恋爱的美好纯洁,充满着神圣的光辉,这是女性个性解放思想的一大体现。最后纗华没能按计划逃脱囚禁,和青霭(士轸)一前一后双双殉情。这种壮烈性的结局充满“五四”鲜明的反抗精神,是作者对包办婚配制度的强烈控诉和反叛,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彻底决裂。如果说这两部作品中的感伤之处是殉情部分的不舍和缠绵,但一联想到“革命的牺牲者”,殉情马上变得崇高而壮美起来,这时候的“感伤”早已被“悲壮”所取代。冯沅君后来的作品也逐渐加重了“感伤”的情调,这种“感伤”主要来自年轻的知识女性放弃自由的爱情而选择向亲情让步。如《误点》中,阮继之与杨渔湘是一对恋人,可继之母亲假以“病重”为由将继之召回,让弟兄劝说继之与渔湘分手,撮合她与杜梅尘的结合。继之此前早就怀疑电报的目的性,经受过痛苦的挣扎,甚至为了亲情与爱情的抉择一反常态,在饭店喝得烂醉,可是回到家中看到母亲时,她终究舍不下“刻板拘泥而诚挚朴实的家庭”,抛弃了“悲恻缠绵的浪漫生活”,选择了向母爱妥协,向亲情低头。由此可见,冯沅君前期的作品差异较大,前期的作品既可以为了自由的爱情与包办婚姻制度抗争到底,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也可为了“血浓于水”的母女之情舍弃自由恋爱,在“慈母的爱”和“情人的爱”只能择其一的条件下,内心的冲突矛盾从未停息,失去哪一种爱对女主人公来说都足以痛彻心扉,所以在成全亲情的同时,爱情的凋谢为作品平添了痛苦、不甘、绝望又无可奈何,难以排遣的“感伤”气息。在冯沅君的作品中“母爱”与“自由恋爱”属于两种平等的爱。她认为“五四”女性的反抗更多的是反对父权、夫权的束缚,而同为牺牲者的母亲并未在列。她并不把母爱以及母爱的权威当作对立面进行批判,甚至在《隔绝》《隔绝之后》中女主人公的遗书里都顾及对母亲的歉意。这实际上显示了冯沅君及其笔下人物对旧封建礼教的妥协和退让。后期冯沅君的作品集《春痕》和《劫灰》在内容和手法上有了一定的扩大和转变,虽然依旧有部分作品写反抗封建制度的主题或男女之间的爱慕,但更多的是这些年轻的女性与其他青年人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五四”高潮跌落的迷茫和彷徨之中,青春之火已经燃尽,在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苦难后开始看清社会现实,以困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此时的“感伤”情绪才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
冯沅君的情感基调显示出一个动态且复杂的变化过程,从一开始高喊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决裂又受“母爱”的牵制的夹杂着“徘徊踌躇”的“悲壮激情”,过渡到后来浮沉在现实和人生中的“苦闷哀怨”,从早期的“激愤型浪漫主义”转变成了后期的“感伤型浪漫主义”,使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五四”从高潮至低落时期的青年,特别是女性青年的心境变化:由激越变得冷静、深沉,又带着淡淡的困惑和怅惘。
“五四”时期是浪漫主义之风盛行的“黄金时代”,女性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浪漫主义的浪潮之中,除了受到当时个性主义的时代风尚和创造社的影响外,还与女性独特的角色和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女性感情细腻,对爱情婚姻这类问题特别敏感,而几千年来压迫在女性身上的封建礼教枷锁又十分沉重,所以她们与男性相比,在争取个性解放方面更迫切却也更为困难,内心的悲哀往往也愈加沉重。当悲哀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之时,早已顾不得冷静的思索。故冯沅君等人写成主观色彩浓厚、感情直露的浪漫主义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她们一齐谱成了“五四”时期的“爱情悲歌”,不仅深刻反映了“五四”时期女性在个性解放和个人生命体验的境遇,还共同开创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尤其是“书信体”写作和“感伤”基调的缠绵多被后世女性作家模仿继承,同时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