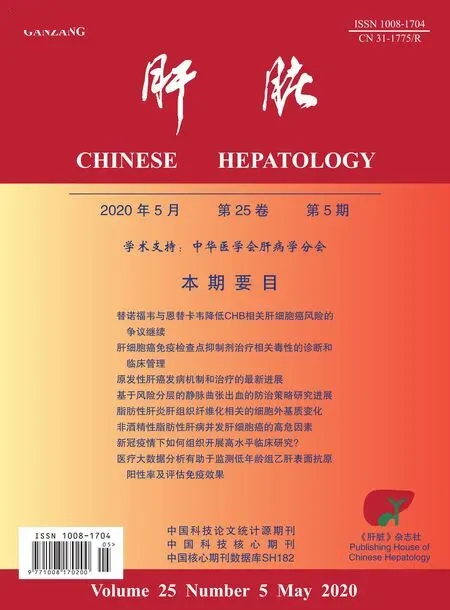原发性肝癌发病机制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张鹭 江建宁
近20年,在原发性肝癌(HCC)的发病机制、早期发现、诊断、分期、治疗等方面的认识已有显著提高。首先,HBV/HCV感染与HCC发生的直接相关性已经被认识。在预防和监测方面,已经确定普及乙肝疫苗接种、超声监测(包括/不包括甲胎蛋白检测)可为有风险的患者提供临床益处。基于无损成像的HCC的诊断标准已于2001年确立。在HCC的发病机制方面,自从P53突变首次被发现以来,伴随着近年来突变领域和分子详细类别的确定,已有重大进展。在疾病分期方面,奥田(Okuda)11分期方法已于1999年被主要用于西方国家的巴塞罗那(BCLC)分期方法取代,香港分期方法则在近年来主要在亚洲使用。就治疗方面而言,1996—2001年发生了重大进步,确定外科切除术、移植手术、局部消融术的适应征,2002—2003年则把化疗栓塞确立为标准治疗手段。对局部治疗反应的评估最初采用欧洲肝脏病学会(EASL)标准,最近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在晚期HCC的治疗方面,索拉非尼成为HCC治疗中第一个有效的系统性分子靶向药物,证实数个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乐伐替尼、瑞戈非尼、卡博替尼、雷莫芦单抗)可产生临床受益,免疫检查点分子也可以作为肿瘤免疫治疗或联合治疗的药物靶点。联合用药策略(阿特珠单抗加贝伐单抗)正成为未来几年的新金标准。与此同时,对肝内胆管癌(ICCA)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了解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首部ICCA诊治指南也已问世。一线全身化疗(吉西他滨和顺铂)和辅助化疗(卡培他滨)已建立实践标准。由于一些重要的分子驱动(FGFR2融合,IDH1突变)的发现,在Ⅱ期临床试验中有着肯定疗效的药物,目前正在进行Ⅲ期临床试验[1]。
一、HCC的发病机制
上世纪80、90年代,对HCC发病机制研究的主要进展有:(1)发现P53突变是导致肝癌的关键驱动基因,黄曲霉毒素B1(AFB1)与HCC密切相关。(2)详细解析乙型肝炎病毒的致癌作用,例如插入诱变突变。(3)转基因小鼠模型在HCC发生、发展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2-4]。
在近10多年里,新一代测序技术的突破,研究者对HCC分子发病机制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来自全外显子组和全基因组测序的数据发现肝癌发生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通路包括: P53细胞周期信号通路、WNT/β-catenin、表观遗传修饰、氧化应激信号通路、PI3K/AKT/MTOR 和RAS/RAF/MAPK通路。这些通路均为肝癌发生过程中重要的调控通路[5]。这些新数据帮助我们理解了HCC基因改变和转录改变之间的联系,以及确定HCC亚组的临床和病例特征。
最近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群在肿瘤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微生物群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与抗肿瘤免疫应答的关系,以及与包括细胞毒性化疗和免疫疗法的全身治疗反应的关系,近年来已在包括HCC在内的癌症中得到描述。Schwabe等[6]强调微生物群在H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一个潜在治疗靶点。
动物模型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在HCC发生、发展机制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临床前模型是一个了解肝癌的发病机制和测试针对免疫系统和信号通路的新药的有用工具。这些模型能再现人类HCC并识别对治疗原发性肝癌可能有用的新药[7]。
二、HCC的流行病学和监测的新动向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HCC流行病学发生了重要转变。HCC最初主要归因于慢性HBV和HCV 感染人群。但现在随着HBV疫苗的在全球各国的普遍应用,及小分子直接抗病毒药物的问世,HCV 感染治愈率明显提高, HBV、HCV相关肝癌正逐渐减少。而由于现阶段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肥胖、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和酒精性肝硬化等逐渐上升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与之相关的HCC的发病率也日益成为医学界关注的焦点[8]。
而肝癌流行病学的变化会对肿瘤的监测策略产生影响。最常用的监测是血清生物标志物、B超、瞬时弹性成像技术、CT和MRI。Singal等[9]发现AFP是诊断HCC的血清生物标志物,多年来运用广泛,但其在小HCC和早期HCC中不敏感。目前已报道数种肝癌生物标志物,但很少有新的生物标志物在临床实践中有价值。改善诊断性能的最合理策略可能是将AFP与HCC的其他生物标志物组合使用。AFP与另一种临床上使用的HCC生物标志物-γ-羧基凝血酶原(DCP)的组合可提高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原发性肝癌实验室诊断的现状,但对于早期HCC诊断的改善不显著[10]。血清GP73在肝硬化阶段存在普遍的异常升高,不推荐应用于原发性肝癌的实验室诊断[11]。
常用于监测筛查肝癌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包括B超、CT和MRI。B 超方便快捷、费用低等优势使其成为HCC诊断中最常用的检查手段。多项指南均建议,对直径<1 cm的肝脏结节,应每3~6个月复查1次B 超。超声影像联合肝癌肿瘤标记物在早期肝癌筛查监测中具有重要意义。肝癌肿瘤标记物特别是AFP能够对B超筛查HCC形成一个有效的补充,特别在早期HCC筛查方面更具优势[12]。
CT扫描可使HCC的诊断具有高度的可信度,欧美各大学会指南均把CT作为肝癌的常规检查之一。CT诊断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和87%,并且肿瘤直径>2 cm的诊断准确度明显增高。
MRI对肝癌的诊断优于CT,MRI可用于发现其他检查手段无法显示的病变。它与CT或B超相比,10%~17%的非肝硬化HCC和36%的分化良好的HCC中存在细胞内脂肪积累,在MRI更容易检测,这意味着诊断非肝硬化肝脏中的HCC具有较高可信度。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对<1 cm 的肝癌病灶显示效果不理想。
三、HCC的治疗
(一)HCC的切除术和移植术 手术切除是保留患者肝功能的主要治疗方法。肝功能储备不足导致在肝硬化情况下肝部分切除成为禁忌。然而,肝硬化被认为是肝切除术的几乎绝对禁忌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临床上常用15 min滞留率(ICG-R15)评估衡量患者所能耐受的肝切除体积,其对肝硬化患者肝切除的预后判断价值已得到证实。综合应用肝实质病变、Child-Pugh评分和ICG-R15三个参数对肝储备功能进行分级量化评估,可为定量化安全肝切除提供决策依据。对于肝硬化患者,Child-Pugh C级为肝切除手术禁忌证,Child-Pugh B级只能行肿瘤切除术,Child-Pugh A级可允许部分肝实质切除,其能耐受的肝实质切除体积可进一步依据ICG-R15结果作出精确判断[13]。
与传统的开腹切除术相比,腹腔镜肝切除术具有创伤小、术中出血量小等特点。腹腔镜肝切除术已经是原发性肝癌的常规治疗方法。
肝移植术是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方法。与腹腔镜手术相关的、较低的并发症发病率以及基于未来肝剩余体积和质量、门脉高压程度、肿瘤复发风险的个体化的预测已经改变了在HCC治疗规范中对外科手术的考量[14,15]。沿着这样的思路,尽管活体捐赠消除了获取器官的障碍,移植获益的观念是肝移植多学科团队讨论的核心[16]。
(二)HCC的局部治疗 在HCC治疗领域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在于局部治疗的作用,特别是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依据BCLC分期,中期肝细胞癌(BCLC B期)首选TACE治疗,对TACE进展的患者可采用系统治疗。然而目前并不确定,若疾病进展,哪些患者会从再次TACE获益,而哪些需要改用全身治疗。AFP升高(>400)、癌栓以及6个月内需要3次或3次以上TACE治疗似乎是接受TACE患者中位总生存期较短的独立预测因素。预后不良的患者往往具有更强的HCC侵袭性,尽早开始全身治疗可能对这些患者有益[17]。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标准治疗方式TACE并不适合所有中期HCC患者,广泛主张细化中期患者群实施个体化综合治疗。多模式治疗的初衷在于利用两种或多种现有治疗方式叠加效应,使患者获得更多的生存获益。目前,多模式治疗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包括TACE联合消融(RFA、MWA等)治疗、TACE联合放射治疗、TACE联合手术切除、TACE联合全身治疗等,对于中期HCC患者,目前多数联合治疗方式包含TACE。TACE引起的局部缺血会导致缺氧诱导因子(HIFs)及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的上调,理论上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具有显着的叠加效应[18]。目前国内外已有多个团队对此展开探索。
在评估治疗的反应方面,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mRECIST)的提出是为了使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RECIST)适应HCC的特殊性[19]。这个提案旨在克服在局部和全身治疗后测量肿瘤缩减时RECIST的一些局限性,同时也改善用传统的RECIST 1.1可能误判的疾病进展评估,因为临床事件是与慢性肝脏疾病的自然进展相关的。自mRECIST被收纳入HCC管理的临床实践指南以来,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如今,mRECIST已成为HCC早期/中期测量放射终点的标准工具。mRECIST已经被证实在分子疗法治疗的肿瘤中可获取更高的客观反应率,这些反应已经证实与更好的存活是独立相关的[2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除了络氨酸激酶抑制剂之外,第一批被批准用于HCC治疗的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被多个临床研究证实对晚期肝癌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能够有效改善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21]。近来,抗PD-L1抗体阿特朱单抗与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单抗的联合应用首次被证实可以提高索拉非尼的效果[22]。因此,毫无疑问地,无论是单独还是联合治疗,免疫疗法将成为HCC全身疗法中的一种。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耐受良好,但它们能够提高T细胞的活性,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毒性[23]。HCC患者常有晚期慢性肝脏疾病,其毒性作用的处理不同于其他肿瘤患者,更具有挑战性。
在经过近10年的与药物治疗晚期HCC的随机试验的阴性结果作斗争之后,过去3年出现的新数据改变了临床治疗HCC的局面,促进了创新药物以及联合治疗策略的发展。Faivre等综合地概述了晚期肝癌现有的已获批的靶向治疗,包括一线的索拉非尼和乐伐替尼,以及二线的瑞戈非尼、卡博替尼、雷莫芦单抗[24]。Faivre等主张探索新的治疗靶点(免疫检查点、转化生长因子-β、络氨酸蛋白激酶-MET、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采用联合疗法,以跳出固有思维模式。针对程序性细胞死亡-1(PD-1)通路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疗法,已经成为HCC联合疗法临床试验的主流[24]。
发病率日益升高的ICCA是一种高致死率的肝胆管肿瘤。ICCA预后差,随着对ICCA生物学特性和预后规律的深入认识,近年来ICCA的外科治疗策略和技术方法有了较大进步,远期疗效也有一定改善。ICCA准确的临床诊断、R0切除、术中区域性淋巴结清扫、术后有效的辅助治疗,以及复发性ICCA的再切除和多学科治疗,是目前提高该病总体疗效的主要途径[25]。使用卡培他滨6个月进行辅助性化疗被推荐用于高危的患者(多病灶、大病灶、阳性淋巴结或者R1切除)[26]。近来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对于不能采取切除术的极早期ICCA (≤2 cm),肝移植术可能是一个治疗选择,而对于局部晚期ICCA,新辅助疗法联合肝移植术也可能是一个选择。
ICCA对化疗敏感。Kelley等[27]在2010年报道一线的晚期ICCA化疗标准药物为吉西他滨和顺铂。与HCC相比,ICCA已发现有多个可靶向的基因异常,最常见的靶突变是FGFR2融合和IDH1突变[28]。目前,在药理学方面,把这些肿瘤形成因素作为靶点的临床资料正趋于成熟。FGFR2抑制剂的Ⅱ期试验阳性结果已经被报道[29],IDH1抑制剂的Ⅲ期试验报道了无进展生存期观察指标获得阳性的结果[30]。同时,免疫疗法的作用已经被认识,成为积极研究的领域。
本文介绍了原发性肝癌医学史上的重要进展,综述了关于肝癌发病机制和治疗方面的主要新进展及最前沿的信息,希望能为治疗和研究原发性肝癌的医生和研究者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