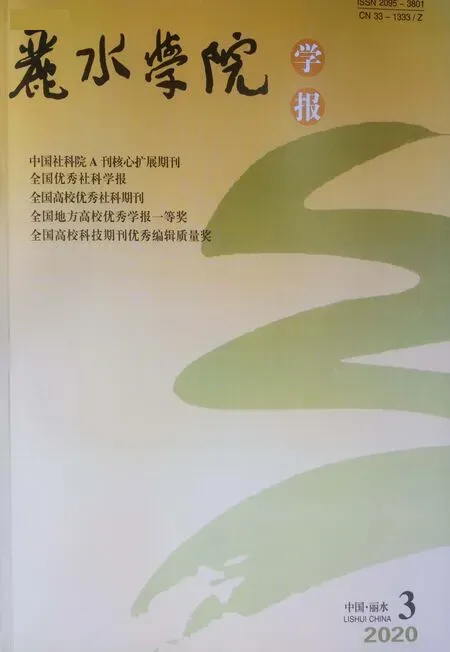从《吉尔伽美什》的三种冥界想象看人类原始思维
吴芷境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主要取材于苏美尔 -阿卡德神话故事的 《吉尔伽美什》是已发现最早的英雄史诗,其所述历史时期在公元前 2700年至 2500年间,此时是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人类自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演进的“英雄时代”①维科在《新科学》以埃及人的时代划分为基础,概括人类文化发展规律过程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
不同于其他早期的民族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主角们的历险并未 以战胜强敌告终,史诗的后半部分与死亡问题紧紧纠缠,为 作品带上了哲思的神秘色调。作品通过恩奇都和吉尔伽美什几番进出冥界,将故事的叙述空间从纷争的人神二界扩展到了天人冥三界,叙事 时间从现世延展到过往和未来。
在古巴比伦人的理解中,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甚至是人神杂处的,神可以经常介入人的生活,而人可以向神谈论世俗或发出申诉。然而人死后进入的世界 (冥界 / 阴间 / 地下世界)是与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隔绝分离的,甚至是被严密看管着的。在第六块泥板①《吉尔伽美什》最早被发现是以楔形文字载于 12 块泥板之上,经过基本复原和破译能呈 现在我们面前。中,女神伊什妲尔请求父亲——天 神阿努降下“天牛”,以惩罚拒绝自己求爱的吉尔伽美什。她对父亲威胁道:
“你如果不把‘天牛’制[作]②《吉尔伽美什》由于部分泥板残缺,诗行并不完整,本文中括号”[ ]”内为缺失或译者根据有 关部分酌加部分。,
我就把阴间的大门破开,
我就把阴间的大门敞开,
我 就 [唤 醒 死 者, 让 他 们 象 活 人 一 样 吃喝],
[使死人倒比活人多]!”[2]46
可 见 阴 间 对 于 人 和 神 来 说 都 是 不 可 测 的,隐藏着不可控制的危险因素。《吉尔伽美什》从第七块泥板开始,描摹了三种不同风格的地下世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彼岸想象体系。
虽然在故事结尾,英雄吉 尔伽美什未能摆脱死亡的阴影求得永生,但古巴比伦人对冥界的瑰丽想象和古巴比伦人的整体原始死 亡观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世死亡哲学的源头活水。从四五千年前粗线条的叙事和略显拖沓的表述中,我们能接近他们的思维世界,寻找到人类童年 时代的情感特征。
一、梦境中的庄严殿堂
《吉尔伽美什》第七块泥板 描述的是吉尔伽美什和挚友恩奇都因为杀死了“天牛”和树妖芬巴巴而受到天神们的惩罚,病倒了的恩奇都在第二个梦中被带入阴间世界:
那爪如同鹫爪
它把我压倒
[]它扑上了身,
[]它要使我下沉。
(23-30 行损坏)
在[]他将我变形,
[]于是我的手就和飞鸟仿佛[]
他见了我,就领到“黑暗之家”,伊鲁卡鲁拉(阴间女王)的住处。
领到那个家,有进无出,
领上那步行 者有去无回的路,
领进那住人的家,光亮全无。
那里,尘埃是他们的美味,粘土是他们的食物,
穿上有翼如鸟的衣服,
就在那见不到光的黑暗中居住。[2]55
在恩奇都的梦中,进入阴间的过程为:鹫爪抓住他下沉—走上有去无回之路—进入地下世界(“黑暗之家”)。其中,用爪抓住恩奇都下沉变形的是沟通人间和冥界的使者,它们引领他来到接待外界魂灵的“黑暗之家”。“黑暗之家”还是这些阴间使者居住的地方,住户们栖息在黑暗中,以尘土为食、以羽翼为衣。
阴间引魂使者的形象与某种夜行猛禽接近,原型可能来自猫头鹰:猫头鹰昼伏夜出、叫声凄厉,如人般凝视的特性,或许解 释了新石器时代的欧亚大陆上曾经普遍存在崇拜鸟女神 (Bird Goddess)的传统;同时,猫头鹰在死亡信仰中占据一席之地,它是阴间女神莉丽丝(Lilith)的象征,莉丽丝的基本造型特征就是人身鸟爪[3]。
值得注意的是,恩奇都在 进入阴间的时候经历了 骤变——人骤然变成动物 (“他将我变形 ”),动物骤然突化成人(“它”和“他”的突然转换),整体可肢解为局部(“我的手就和飞鸟仿佛[]”),局部可重新结合为整体。在古巴比伦人看来,不同生命领域没有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划分,各领域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流动的(如 恩奇都从野兽变成了人,看守马什山的沙索利人是蝎头人身),各领域可以相互联系、相互转化。这“变形的法 则”[1]103预示着古巴比伦人混沌整体的世界观,他们以“转化”的观念看待死亡:死亡是从一个形体转换为另一个形体,而生命不会终结。
随着恩奇都的行动路径,正殿堂(即“尘埃之家”)的丰富场景展开了:
在我进入的“尘埃之家”,
我看到[统治者们(?)]把冠冕摘下,
我[看到公子们]把冠冕[],他们自古以来把国家统辖。
在阿努和恩利尔的[象前(?)]捧献烤肉,
把烤[肉]捧献,把皮囊的冷 水浇洒。
在我进入的“尘埃之家”,
住着高僧和新的成员,
住着咒术师和巫觋,
住着大神们的洗碗差卞,
住着埃塔那,住着苏母堪,
住着阴间女王艾雷舒乞嘎尔,
[卑利特]·塞利那个阴间的记录员跪在她的面前,
[她手拿书板(?)]朝着她念。
她[抬起]头来瞧见了我,
[就说:“是谁],把 这个人带到此间。”[2]55
“尘埃之家”由阴间女王艾雷舒乞嘎尔掌管,有着不同于俗世的秩序:独尊 的王公贵胄成了捧肉洒水的侍从,显贵的高僧巫 师沦为洗碗打杂的差役,褴褛的乞儿流丐升为端居高位的判官。其中,“审判”的庄严 恐怖场景——记录员宣读来者信息,女王质问恩奇都来历——成为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母题,在西方发展 出但丁笔下的九层地狱,在东方变幻成阴曹地府的幽冥世界。
这段以恩奇都梦中游历的口吻描述,勾画了冥界的社会框架。睡眠或梦境同死亡的相互认同,是在史诗中普遍出现的神秘观念,如吉尔伽美什在寻找长生药的途中,向人类始祖 乌特纳庇什提牟说道:“〈睡着了的人〉 和死者是那么近似难分。他们岂不是正将死的影像描摹……”[2]73这 一 联系也频繁见诸后世诗篇,最出名 者莫过于莎士比亚在 That time of year(Sonnet 73)中宣称的睡梦是“死亡 的 第 二 自 我 ”(“Death's second self,that seals up all in rest”)。追其本源,它与原始信仰中的灵魂观念密切相关,睡眠的实质被视为灵 魂暂时性地离开躯体[4]155,正因为如此,乌特纳庇什提牟在六天后才 将 吉尔 伽美什 从 睡 梦 中 唤 醒[2]84,让 他 的 灵 魂 有充分的时间回归躯壳,从死中复活。
二、马什山里的瑰丽乐园
在挚友恩奇都病逝后,吉 尔伽美什突然认识到“我的死,也将和恩奇都一样。悲痛浸入我的内心,我怀着死的恐惧,在原野徜徉”[2]62。与自己相同的英雄死于病榻,让吉尔伽美什从对外在武功的追求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反省,他强 烈地渴望躲避死亡阴影,由此他踏上了遍寻永生的道路。
当他跋山涉水,来到通天地的马什山前:
山的名字叫 马什
他[一]到马什山,
只见它天天 瞭 望着[日]出和[日落]。
那山巅上[抵]“天边”,
那山麓下通 阴间。
把关的是沙 索利人,
那可怕的凶 相,如同死亡一般。[2]63
马什山非同 寻常:它上达碧落下至黄泉,有着沟通阴阳的作用;面相凶恶的把关人看守着它的山门。在巴比伦语中,“马什山”意思是“双生子”,这个名字暗示了它与太 阳 神舍 马 什 (Shamash)的特殊联系 (舍马什的神庙表象为日环从两座大山间升起),其中山径通往的地方令人格外好奇。
把关人沙索 利人(“蝎人”)警 告他“从未有人跨越那条山径。在那十二比尔的地方,无边的黑暗,没有光明”。 而吉尔伽美什坚持进山,并用超人的勇气和毅力打动了把关人,把关人敞开了入山的门户。
他就沿着太阳的路[向前]。
一比尔过去时,
[那里没有光],极其[深邃的]黑暗,
[他前后什么都看]不见
二比尔过去时,
[那里没有光],极其[深邃的]黑暗,
[他前后什么都看]不见
…
九比尔过去时,他感到(?)有北风,
[]他的脸[]
[那里没有光],极其[深邃的]黑暗,
他[前]后[什么 都看不见
[十比尔过]去以后,[]
靠近[]
[]比尔的[]
[十一比尔过去时]射进来 太阳的光线。
[十二比尔过去时]有了光,
在[他]前面看到了[石]的树木,他就健步向前。
红宝石是结成的熟果,
累累的葡萄,惹人爱看,
翠玉宝石是镶上的青叶(?)
那儿也结着果,望去令人心胸舒展。[2]66-67
吉尔伽美什严格地沿着太阳的方向,穿越了十二比尔①古巴比伦的长度单位。的隧道。在走过前八比尔路程的时候,一直是“没有光”,“极其深邃的黑暗”,“前后什么都看不见”;直到第九比尔的时候,他感到了有一阵北风;在十一比尔的时候,有了射进来的光线;到十二比尔过去的时候,豁然开朗,他见到了一片石 林 和 光 辉 灿 烂 的 珠 宝 果 园 ——那 里 宝 石 为 果 、翠玉为叶,确实是人间不曾有的景象。
对于先民而言,散发着热 力光芒的太阳是一切生命的保证条件。太阳的光辉能够驱逐死亡,如第十块泥板上吉尔伽美什对大力神 舍马什提出永生的祈愿:“请让我的眼睛看到太阳吧,使我浑身广 被 光泽 ;那 有 光的地 方,黑暗便 告退,让 我 沐 浴太阳神舍马什的光辉,将死亡给予 那些死者!”[2]68叶舒宪在《英雄与太阳》中解释吉尔伽美什所经过的 黑 暗中 的 摸索 仍 然 是“沿 着 太 阳 的 路 ”,认 为 黑暗隧道为太阳必经的关口,由于长 达十二比尔的隧道太过狭窄与深黑,使得太阳挤过去时身体被拉长和变得暗淡[4]145。
我们随着英 雄的脚步,不断看到日出与日落、光明与黑暗、阳世 与阴间……这些暗示着太阳的意象和英雄的生存命运联系紧密——似乎与太阳相随同行,就能加入宇宙的循环,超 越有限的死亡阴影。
吉尔伽美什终于摸索到的乐园充满浓厚的浪漫色彩,一洗之前路途的灰暗阴郁。这是怎样的华彩绚丽的景象?红玉成串,碧石舒展,令无数人间王侯将相梦寐以求的、需要耗费千万劳力辛苦开凿打磨的翠玉宝石,在此福地却无 须假于人工就能悠游自然地遍布各处,流淌在眼前……
在这里能够纵享人间少有的明媚舒畅,几乎接近神明的世界。这是“神圣的一瞥”——似乎这里的一切正是尘世间相应事物神圣的原型,而在尘世间的一切只是这原型黯淡无光的影子,一个不持久、不完美的摹本。
三、入冥后的悲惨世界
第十二块泥板对恩奇都的死亡做了另一番解释:恩奇都为了帮吉尔伽美什取回掉入阴间的鼓和鼓槌而进入地下世界,因为未遵 守吉尔伽美什教诲而被捉住。在地神埃阿的调停下,恩奇都能够暂离冥府,告诉吉尔伽美什他在阴间 的所见:
(涅嘎尔)他刚刚在地里凿 开一个洞,
这时,恩奇都的灵魂,噗地 从阴间上升。
……
[不过],假如我告诉你,我曾见到的阴间的秩序,
就会使你坐下来哭泣!
“[……]我宁肯坐下来哭泣 。”
“[我的身体……],你高兴时曾经抚摸过的,
早就被害虫吃光,[活象]一身陈旧的外衣。
[我的身体……], 你高兴时曾经抚摸过的,
[……]早就为灰尘所充斥 。”
“你看到他从桅竿上[跌落]?”“[我看到了]:
[……]好容易才把钉子拔脱。”
“你看到[他暴]死?”“[我看到了]:
他夜里躺在床榻上,并把那洁净的水喝。
“你看到他在战斗中被杀戮? ”“ 我看到了:
他的父母把他的头抬起,他的妻为他[哭泣]。”
“你看到他那被抛在草原的尸体?”“我看到了:
他的灵魂觉得在阴间不得安息。”
“你看到他的灵魂无人护理?”“我看到了:
他在吃那瓶子中的酒滓,面包的碎屑,街上的臭鱼烂肉。”[2]92-94
通过死神涅嘎尔凿的洞,恩奇都的灵魂突然从阴间升回到人间。恩奇都对吉尔伽美什讲述了他在阴间可怖的所见:肉体和灵魂阴阳两隔,阴间的 灵 魂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被 留 在 尘 世 的 肉 身 的 迁 化 。纵使吉尔伽美什将自己的尸体“像新嫁娘似地用薄布蒙罩”,“躺在荣誉的 床上…坐在左席,舒适的座 位 上”[2]60(第 八 块 泥板),但肉 身 依然 腐 坏,被 蛆虫吞食,被灰尘充斥。同时,无论是被钉死在桅杆上或暴毙床榻或战死沙场,无论是英雄与庸人,圣人或罪人,所有的灵魂都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至亲伤心悲痛、肉身被折磨消减,自身永远无法安息。
在古巴比伦人混沌不分的完整世界中,永远死去是不自然的,死亡也是 整体流转的一环,是从一个形体向另一个形体转变的过渡 。在这样不可磨灭的与生命一体的心灵中,最需要担心和最使人痛苦的是肉体的消腐和与亲人的别离,而不存在永远寂灭无存的终结事实。
第 十 二 块 泥 板 总 体 呈 现 出 低 沉 阴 郁 的 基 调,被 一 些 学 者 认 为 是 经 过 祭 司 集 团 修 改 后 的 结 果 。祭司集团借恩奇都之口来诉说阴间 森然惨切的情景,从而 宣 扬 神 力强大 、天 命难违,比 起 对 教 义 信仰的直接传述,史诗表现出的具体 生活更能贴近先民的真实世界。
在 大多数“入 冥 ”题 目 中,主 人 公 们 往 往 出 于“情感的牵挂和驱使”[5],如目连不忍看母亲在地狱受 刑 而 入 冥救母(《佛 说 盂 兰 盆 经》);奥 德 赛 为 了找 到 归 家 之 路 而 下 到 冥 界 献 祭 见 先 知 (《奥 德赛》);恩奇都为了捡回吉尔伽美什的鼓槌和鼓进入冥界,吉尔伽美什则因 为挚友离世而悲恸、继而决 定 寻 找 永 生…… 无 论 是 出 于 亲 情 或 是 友 情,还是 爱 情,英 雄 们 常常在“ 人 性”的 照拂 下 踏 上 入 冥的征途,长路漫漫而步履弥坚,艰险 重重而不改初衷。这亦是这些故事能引发共鸣、恒久流传之原因。
四、冥界想象的发生与启示
从人类主体意识诞生之初,死亡就是使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业文明使得古巴比伦人很早就目睹 了动植物的死亡和再生以及四季与昼夜的更替,或出于给以某种解答的需要,也可能为了消减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他们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并将其神化,编造出了另一个亡灵容身的世界。在先民的思维活动中,他们尚未使用抽象的推演或纯粹的理 念,而是以直接的情绪与具体的活动来呈现自身的处境,即列维 -布留尔所言“原逻辑思维(Prelogique)”[6]。
现 在 的 我 们 似 乎 停 止 了 对 死 后 世 界 的 想 象,我们不再思考眼前的物质世界是否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灵魂是怎么被引导 入另一个世界的、阴间世界将被怎么样地组织……在一切科学化了的世界里,人 是由 细 胞、神 经 元 组成 的,人 的生 老 病 死 变成细胞的衰老变异,变成了纯粹生理性的。如果把《吉尔伽美什》中对于冥界和永生的描绘仅仅视为古代人民对无法充分认识的生死做出的解释[7],那么对生死问题有了合 理并且“科 学”解释的现代人为何还需要一遍遍地回到史诗、阅读史诗呢?对于冥 界 和 永 生 的 想 象 为 何 仍 旧 能 够 拨 动 人 的 心 弦 、激荡我们的性灵呢?
史诗不是写 出来的,是先民们在旷野中、在天地间迸发出来的呼告。他们把自己对于死亡的疑问、对于永生的追求寄在了一位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是神的英雄吉尔伽美什身上,让他上天入地。《吉尔伽美什》中关于冥界的想象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合理地解释了世界,而是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感知自然、创建与自然的联系。原始的人们并不缺乏使用经验来区别事物的 能力 (他们对事物的观察和辨别的天赋甚至是惊人的),但在他们关于生命和自然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情感底色:人是 自然中的一分子,和各种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是平等的、沟通的、交感的[1]107。因此,《吉尔伽美什》的结尾也可以从这个倾向来理解:即便是历经 艰险的人间英雄,依然不处于自然等级的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依然无法摆脱生死的谱系。
史诗和科学从两个方面扩大了人类的生存视域,在今天这个仍然时常令我们感到迷茫的世界里,《吉尔伽美什》 中的冥界想象不仅不会使我们疏离这个世界,恰恰相反,它能让我们的情绪和感觉回归本位、重新流动,让深埋于理 性思维之下的感性情感得以抒发,让我们更加有激情地栖居于这个世界。
而吉尔伽美什历经千难没能找寻到永生的结局,除了让世代读者重抵 内心最本质的恐惧,并和这个 疲 惫的 英 雄一齐发出“死生有命、人生无常”的悲伤喟叹,吉尔伽美什也由此升华为了充满悲壮感的英雄。吉尔伽美什这一人们 想象中更加坚韧和强大的形象,也被放置在更宏大的背景中,他的悲恸和绝望融入了更广阔的天地之间,甚至让我们恍然觉得,在绝望和无 序背后,生命还有另一重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