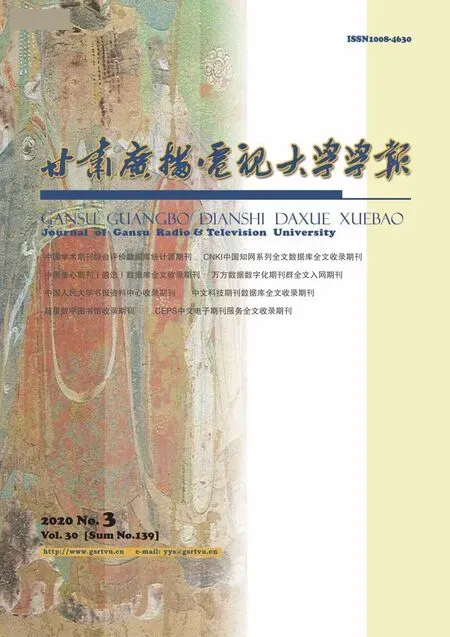刻划神灵:二郎神在安多藏区的形象变迁
闫子琪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安多藏区黄河沿岸,尤其是南岸的贵德、同仁和尖扎地区较为广泛地分布着二郎神信仰。为何此地区会出现二郎神信仰以及该地区二郎神信仰的形态、特点怎样?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数还局限在对仪式过程的分析以及对此信仰源流传播过程的追溯上。二郎神信仰来到河湟地区后,先经历了与当地土著和藏传佛教的隔离,之后又与当地藏传佛教发生接触,在接触之后变成了现在所看到的结果:二郎神被藏传佛教所接纳,成为了当地藏传佛教的保护神、地方守护神以及当地高僧、活佛的护卫。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不鲜见,如关帝也演变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之一①。故而确有必要了解、研究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及原因。杜赞奇认为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会根据自身群体的利益需求和实际情况,对神灵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释,这就形成一种对神灵形象的“刻划”。本文从杜赞奇的“刻划”神灵理论[1]出发,分析二郎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两次形象转变的过程及其原因、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晰的看待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
一、战神二郎神的塑造
二郎神初为治水之神,无论其原型是李冰还是赵昱,均是因治理水患有功而被奉祀。西北岷州的二郎神最初也是作为治水之神在护佑一方百姓,还有“没水斩蛟”[2]35之神迹。
二郎神的战神功效在明代西北战事中得以初显。甘肃岷县《重修二郎神庙碑记》[2]35载:
我圣朝龙飞抚运,及洪武十一年戊午,命指挥使淮东马烨开设卫治。次年率兵讨平乌斯藏、思窝纳邻洮源诸番寇,边境宁义。谓神有阴佑功,遂大兴祠宇。自兹厥后,水旱冰灾,有祷辙应。
成化甲午秋,西番族类,屡为边患。陕西按察司副使吴玘,奉敕镇临其地,具以其事闻。上命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马文升,都知监太监刘祥,右府都督白玘提重兵以讨之;护军则按察使佥事左钰,督饷则布政司参议张琳。至则皆修敬祠下,以祈灵贶。继而兵威所加,不旬日番酋授首,远近顺化。
碑文所述,二郎神在洪武、成化年间两次护佑了护边将士。二郎神“巡抚诸公,以神威灵昭著,庇及是方”。
是以御灾捍患,福善祸淫,虽山川辽邈,翕歘之间,厥应如响,皆神之能。有事兹土者,庙而祠之,阴阳表里,可谓知所重矣。知所重,是率斯民以诚也。
可见,至少在成化年间,还有地方官员以官方身份来祭祀二郎神并修建庙宇,而二郎神也以战神的形象保佑明朝军队在西北的战事。之后,作为战神的二郎神在这些卫所驻军中流传开来。
二、战神二郎神进入安多
民国贵德县志[3]载:
明季洪武十三年于河州发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后又发河州卫世袭百户王、周、刘三人,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又东乡康、杨、李三屯百姓原系土人,编入民籍完粮。
当王、周、刘三位百户率亲眷从河州来到河湟地区屯垦时,极有可能将二郎神信仰随队带来。毕竟洪武十三年(1380)来此屯垦距离洪武十二年(1379)二郎神保佑马烨征讨乌斯藏仅仅过去不到一年,且马烨所开设的岷州卫在前一年还属于三位百户所调出之河州卫。且河州卫确实也有二郎神信仰之流传,嘉靖《河州志》[4]记载:
二郎庙在州西北原上。以上三庙俱洪武十六年指挥徐景建。
虽然在康熙《河州志》[5]中与二郎庙同时修建的马神庙和狱神庙都尚在,二郎庙却不见于记载,但是二郎神信仰曾在河州这片土地上存在过,并且有一定的影响。
三位百户远道从河州徙来屯守,深入番人腹地,将能够保佑番寇归顺、边境宁义的二郎神带来,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至今,在贵德的刘屯,人们还认为当地的二郎庙就是刘庆屯军后在屯堡里修建的。当地2006年重建二郎神庙的碑文为:“三屯寨之‘刘屯寨’、二郎神庙,即为刘庆军户籍屯地后,相继建成。”[6]除贵德地区的二郎神外,同仁地区的二郎神来源大致于此相类似。明永乐九年(1411),自河州卫调中左千户于归德(今贵德)居住守备,分兵屯田,当时计分十屯,贵德有六屯而保安(今同仁)有其四。清《循化厅志》[7]16,95载:
贵德州元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八年正月改置贵德守御千户所(《明史·地理志》)。……按明立河州卫以右所调贵德守御共十屯而保安有其四。
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永乐四年都指挥使刘钊奏调中左千户一所贵德居住守备,仍隶河州卫,保安其所属也。贵德共十屯而保安有其四。
这些只能说明二郎神信仰已经进入这个地区,还不能说明当地藏族已经接受了二郎神,更不能说明二郎神进入了藏传佛教的保护神体系。事实上,这一过程到清初甚至清中期才完成。明代军屯稍显封闭,军屯内居民和军屯外番人的沟通还不是很通畅,这主要是由于军屯之中的人世代均为军户,而军屯之外的人则为民或番人。关于军屯中自成一体的文化单元在史料中也有所体现,这不是安多军屯所独有,边境军屯大抵如此。军屯居民是外来屯军戍边至此,为了能够在这边陲之地求得生存,加强防卫、抵御外敌侵袭自然是其第一目标。每个堡寨都修筑了比较厚实坚固的寨墙,夯土版筑,墙基很厚、很高,难以翻越,还有统一出入的寨门。堡寨对外封闭、自成单元。因而军屯居民很难与藏传佛教产生互动。
三、战神二郎神进入藏传佛教化身地方保护神
清初,屯军被改为“屯丁”,专事农业生产。康熙以后,清政府大量裁撤卫所,屯军直接划为州县编户。这些旧日屯军也“渐染夷风”。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循化厅志》[7]34就载有:
考乾隆二十九年历卷册保安番民……屯兵之初皆自内地发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为之番民矣。
《循化厅志》中记载的保安四屯“王喇夫旦事件”则反映了安多藏区屯田军户由军变民的过程。清雍正初年(1723),清政府以王喇夫旦日渐骄纵为由,令陕西总督岳钟琪发兵进剿,将王喇夫旦生擒,并将当地土兵全部革除,代之从内地另行募兵。此后,四屯之民不再是屯军,而是自耕自种的农民。这样以为,军屯居民维系群体认同的身份失去,就加快了屯军本土化的速度。自此,旧明的屯军军户与当地的番人土著在国家行政上再无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二郎神信仰跨越族群的界限成为可能。
1.藏传佛教内部的阐释
隆务四寨子即明代到贵德地区屯垦的十个军屯中地处隆务河畔的四个,今均属同仁县。明中后期隆务寺崛起并改宗格鲁派。在历代夏日仓活佛及其弟子的努力下,隆务四寨子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寺院并奉隆务寺为宗主寺。隆务四寨子皈依隆务寺也有标志可循,“城门上方的玛尼康”,这一标志也是文化压力的反映[8]。不管是文化强势的一方还是处于较弱势的一方,要想实现文化涵化,避免激烈的冲突,双方都需要做出一定的改变与妥协。这一涵化过程也体现在对二郎神的重新“刻划”上。二郎神信仰能够进入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圈离不开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阐释与祭祀。在热贡地区高僧大德赛康巴写的有关二郎神的祭词中,有一段藏文偕颂诗记述了二郎神来到藏区的原委[9]。
古时汉地中原,叫四川的地方,借助魔力前来者,为汉藏交界大战神,尤其为热贡地方神,其名为瓦宗日郎。
赛仓·洛桑扎西赤列嘉措写的有关二郎神的藏文祭祀颂词中,也有二郎神来热贡的简单描述[9]。
您作为神通广大的神灵,早在东方皇帝的宫殿里,您跪拜于皇帝跟前,许诺要前往藏地,并被特派来热贡。奉皇帝之命前来者,称其为巴宗日郎。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赛康巴·罗桑丹曾嘉措大师精通佛法、著作颇多,在安多藏区有着很大影响[10]419,他还曾为隆务寺的三世夏日仓活佛洛桑曲扎嘉措讲经[10]499。赛仓·洛桑扎西赤列嘉措即五世色仓活佛本身即为同仁隆务镇人,光绪十五年(1889)出生,五岁坐床,九岁入隆务寺闻思学院学习,二十五岁从显宗部毕业升任隆务寺法台[11]。这两位一位是名传整个安多藏区、影响颇大的佛法大师,一位是同仁隆务原屯田所在地也就是二郎神信仰所在地大寺院的法台。他们的颂词的作用就如海西斯所言:“他们从此之后就被宣布为佛法的保佑神和‘守护神’。因为他们听命于像莲花生那样的大师们并且接受皈依。”[12]207二郎神信仰虽然不像关帝信仰那样被直接列为藏传佛教护法神,但是这样的祭词与偕颂诗毫无疑问说明二郎神在藏传佛教中也有着自己的地位和位置。
2.民间的解释
在当地民间传说中有一则故事与祭文描述相吻合。文殊菩萨的化身——大明皇帝把二郎提任为将领。有一次,他未听从皇帝的调派,擅自调兵与外界交战,结果惨败。于是,皇帝罚他戴上枷锁和脚镣,到遥远的藏地安多热贡守边。他率众兵,屯垦守边,久而久之在热贡永驻下来。他年迈老去,他的幽魂游荡空中,无恶不作,给百姓带来了灾祸。后来,他被第一世赛仓活佛收服,并被指定为保安镇,尤其是尕则冬村的守护神,而且赛仓活佛还为该村信众写了对二郎神的颂词。每当村民需要二郎神守护时,就念诵祭文颂词,祈求神马上显灵[9]。这则传说前半部分基本与现在所考证出来的二郎神跟随屯军入驻屯田来到这一地区的过程相一致,后半部分则应该是藏传佛教收编二郎神进入自身神灵体系的过程在民间传说中的反映。
除此之外,据年都乎村的老人们讲,二郎神有三个兄弟,“齐卡”村的为老大,该村的为老二,保安尕队村的为老三。该村的二郎神原来是负责管理财务的,后来因发生偷盗事件,被清代的某个皇帝(当地人称为“郭麻秦始皇”)赶出皇宫,四处流浪,无以为家,堪钦活佛一世慈悲为怀,将他收留在此,所以他要听从堪钦活佛的命令[13]49。
还有一则传说是:以前该村的二郎神特别能喝酒,每天都要喝64碗酒。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躺在神庙门槛的一把刀上睡着了。一位女性进香,从他头上跨了过去(因为是神,凡人是看不见的)。堪钦活佛见了之后,十分生气,只准他每天喝8碗酒。所以,现在人们每天给二郎神只敬献8碗酒。四合吉村里的二郎神也只是夏琼活佛手下的一员武将。从这则传说中可以看出,二郎神是受寺院活佛管辖的,要听从活佛的命令[13]49。
可见,安多藏区的二郎神是从属于活佛的,二郎神的这一地位也与地方保护神从属于藏传佛教的地位相一致。在年都乎村祭祀二郎神的仪式上,也可以明显看到藏传佛教的影子。年都乎人在举行祭祀二郎神的“於菟”仪式之前和之后都要在年都乎寺中集会,或者说,祭祀二郎神的仪式是从年都乎寺这一藏传佛教寺院开始和结束的[14]。从“於菟”仪式开始时的诵经一直到仪式结束后举行的集会,地点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而不是供奉二郎神的庙宇。寺院作为仪式展演的时间及空间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郎神在藏传佛教中的从属地位。供奉二郎神的庙宇虽然在空间上与年都乎寺相分隔,但是在仪式上处于从属地位。
“但当喇嘛教甚至还允许巫教中的守护神存在下去时,它却始终都坚持把巫教的召神仪式和庆祝仪式运用到自己的仪轨范围内。……许多巫教神仅仅由于讲一句‘金刚’(我们已经指出,此词被认为其中含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赋予这些神灵一些比较符合密教术语的新名称就可以进入喇嘛教万神殿。”[12]209二郎神在这些地区也有了新的名称,如“阿尼哇宗”“阿尼巴宗”“阿尼木洪”等。
可以说二郎神在藏传佛教的视域下有了全新的内涵与解读,不再是汉族地区治理水患的二郎神,也不是卫所军屯之中的战神二郎神,而是当地地方的保护神“阿尼木洪”。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较为清晰的二郎神成为藏传佛教地方保护神的过程就显现出来。二郎神信仰在明朝之前就已经扩展到了岷州地区,至晚到明初出现了战神形象的二郎神。明初朝廷在安多地区设置大量卫所进行军屯,大量移民随之进入,而贵德移民多来自临近的河州卫,二郎神信仰也随之进入这一地区。在整个有明一代的西北战事中,二郎神起到了为地方官员所认可的“阴祐”作用,因而祭祀不衰。清代,由于疆域的扩大和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屯军身份的取消,使得信仰二郎神的群体与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体接触越来越密切。经过活佛的阐释和信仰群体的彼此接受之后,二郎神被彻底归入了藏传佛教体系,成为一名藏传佛教的地方保护神。
不管是从祭辞还是民间传说,抑或祭祀仪式中,都可以看到贵德的二郎神形象与最初在岷州出现的完全不同。从最初的治理水患、护佑百姓的水神到保佑国家对外战争的战神,再到地方保护神。在这一过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两次对二郎神形象的“刻划”。两次“刻划”意味着二郎神形象的两次转变,这转变正与杜赞奇所说的“神话的不连续性”相契合。来自官方、藏传佛教内部和民间的三重力量合力刻划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藏区二郎神的形象。
在每一个群体对二郎神的“刻划”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特定的因素为这些不同的群体提供素材。最初的农村地区,普通乡民祭祀二郎神是因为他可以斩杀制造水患的恶龙。当这个区域变成国家对外战争的前沿战场时,二郎神又演化为可以阴祐战士的战神。明清易代之后,国家疆域扩大,这一地区成为国家地理上的“腹地”,二郎神对藏作战的战神形象又显得不合时宜。在深入藏区同时面临藏传佛教较大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对二郎神形象刻划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二郎神化身为藏传佛教的保护神就是这一“妥协”的产物。但即使是藏区强大的藏传佛教也没有办法完全主导二郎神形象的刻划,依旧在其故事中保留了被皇帝派来屯垦守边的内容。安多藏区对二郎神形象的“刻划”过程反映了这一地区在由“边疆”到“腹地”和朝代更替之下的文化变迁过程。
注释:
①关于关帝信仰在藏区的演变过程可参见陈崇凯的《藏传佛教地区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喜饶尼玛等的《试论藏族地区的关帝崇拜》,载于刘成有、学愚主编的《全球化下的佛教与民族——第三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42-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