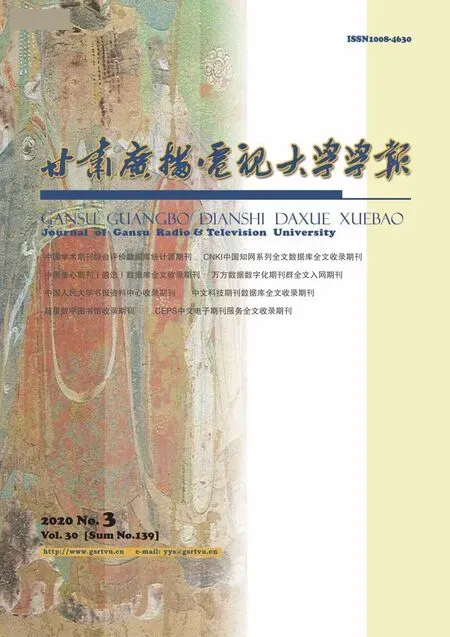唐康国猧子的传入及其在诗歌中的境遇
——西域物种对传统诗歌审美形象影响的个案考察
安天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中国的恋情诗词中,“狗”逐步演化为一个特殊形象。唐以前,“狗”的形象一直是传统的家狗,随着时代变迁,其形象几经发展丰富。考察这一变化,不仅可以看到恋爱中的男女从“憎狗”“惧狗”到“爱狗”的思想转变,也可以窥见男女间恋爱方式、情感特质和时代文化变迁的线索。唐初丝路再度畅通繁荣,沿线国家、民族以朝奉或商贸的形式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其中来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地区)的新型犬种“康国猧子”——哈巴狗输入中原地区。这一新型犬种先是流行于宫廷内苑,后逐渐扩大到民间,受到女性的喜爱,引起了恋情诗词中“狗”与“男女”关系模式的新变,衍生出新的艺术内涵,并长远影响着唐以后这类作品的创作。考察哈巴狗流行的社会原因及其在诗词中的新形象生成,可以折射出唐朝丝路文化交流对传统诗歌形象的影响,具有以管窥豹的意义。
一、传统家狗形象在诗词中的演变
(一)鸡鸣狗吠:早期民间诗中憎狗憎鸡现象
狗的形象首次出现在恋情诗中,见于《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1]615
《传》云:“尨,狗也。”[1]616这首诗历来聚讼纷纷。开篇“野”字已点明故事发生在野外,前二章写男子(吉士)以白茅包裹死鹿为礼物送与女子,以期与其定情。但最后一章描写大胆,“帨”是古代女子放于腰间的佩巾,女子叮嘱男子“无感我帨”,怕惊动了旁边的狗,狗叫则容易使她们的幽会暴露。关于其旨意,《毛诗序》认为:“《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1]615郑玄《笺》对“无礼”做了更明确的解释:“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胁以成昏,谓纣之世。”[1]615欧阳修《诗本义》目为刺淫之诗:“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动我佩,盖恶而远却之辞。”[2]朱熹《诗集传》则认为:“贞女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并说最后一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辞。姑徐徐而来,毋动我之帨,毋惊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3]汉儒宋儒解此诗多揆之以礼,牵强附会,对男女之情则避讳不谈,无异于以纸包火。清人姚际恒已有批驳,其《诗经通论》指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4]若抛弃礼教外衣,剥离经学属性,还原其文学本质,则此诗细腻记录了当时民间男女相恋的过程。当两情不能自已之时,女子忽然担心男子大胆的举动引起狗吠,“非礼相陵则狗吠”[1]616,狗吠容易引起旁人关注,将两人私密幽会,你侬我侬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在恋爱幽会中女子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态跃然纸上,而此时狗的吠声,则未免在女子心中有些顾虑担忧,这种顾虑担忧在以后此类诗歌中遂发展出“憎恨”心理。狗的形象一出现在恋情诗中,便以这种不合时宜的角色引起恋爱中男女的顾虑,这是由于狗吠的习惯和男女秘密幽会的恋爱方式,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共同造成的。钱钟书《管锥编》指出此诗:“幽期密约,丁宁毋使人惊觉,致犬啀喍也。王涯《宫词》:‘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高启《宫女图》:‘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可与‘无使尨也吠’句相发明。李商隐《戏赠任秀才》诗中‘卧锦裀’之‘乌龙’,裴铏《传奇》中昆仑奴磨勒挝杀之‘曹州孟海’猛犬,皆此‘尨’之支与流裔也。”[5]132钱先生上引诗中“猧儿”“乌龙”实为狗形象的另一个阶段,与“尨”的形象并不相同,所以说“此‘尨’之支与流裔也”。
同样,因为鸣叫属性在恋情诗中受到“憎恨”的还有鸡这一形象。试举几例与狗的形象互相阐发。《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篇:“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1]719《笺》云:“此夫妇相警觉以夙兴,言不留色也。”[1]719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三二条指出:“笺语甚简古,然似非《诗》意。‘子兴视夜’二句皆士答女之言;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女催起而士尚恋枕衾,与《齐风·鸡鸣》情景略似。”[5]178《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1]737旧说亦莫衷一是。若按钱钟书解释,此篇也只是鸡鸣天曙,女子催促男子起床,而男子耽溺枕衾,借口赖床不起。上引两首尽管众说纷纭,但无论传统解释还是今人理解,都无法忽略诗中场景乃男女帏房,诗中对话乃男女私密之语这一点。鸡鸣是东方欲晓的特征,这对男女来说意味着良宵已尽,所以鸡的形象在这里并不讨喜。
故而,在恋情诗中,狗见生人则吠与鸡鸣良宵将尽,常打破男女幽会的私密氛围和美好时光,所以遭到人们的厌恶,以至于“憎恨”。这种“憎”究其本源来说是由于男女恋爱幽会时的“憎声”心理。这是狗形象一进入恋情诗就被打上的角色烙印。南朝徐陵《乌栖曲二首》其二:“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6]诗中描写的场景可以看作上引《诗经》诸篇的遗韵,而情调更偏明艳,情义更加直白,以至于直接说出“憎”鸡鸣夜尽。隋朝无名氏《读曲歌》其五十五首:“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7]675此诗当出自民间,所以词意浅白,已经由“唯憎”发展到要“打杀”长鸣鸡的地步了。而两汉乐府诗《有所思》则明确地将“鸡鸣狗吠”目为同类: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7]230
女子因“闻君有他心”,十分坚决地决定和男子分手,最后又产生了复杂心理,回想到当初秘密约会时“鸡鸣狗吠”,恐怕已经惊动了家里的兄嫂,恋情已被曝光,只能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二)乌龙食奴:惧与喜的复杂心理生成
《搜神后记》卷九载:
会稽句章民张然,滞役在都,经年不得归。家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私通。然素在都养一犬,甚快,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假归,奴与妇谋,欲杀然。盛作饮食,共坐下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未得啖,奴已当户倚,张弓栝箭拔刀,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盘中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数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唯注睛舐唇视奴,然亦觉之。奴催食转急,然决计,拍膝大呼曰:“乌龙!与手!”狗应声荡奴。奴失刀杖倒地,狗遂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妇付县,杀之。[8]
在这个传说中,张然驯养的这只叫“乌龙”的狗可谓忠诚无比。在妻子和奴仆合计准备谋害张然的关键时刻,扑倒奴仆,“咋其阴”,使张然有机会杀死奴仆而逃过了一场生死危机。这一故事在后世流传甚广,如杨维桢《狗马辞》:“狗有乌龙兮马有的卢,的卢徇主兮乌龙食奴。于乎交之借兮无解,孤之托兮无婴。吁嗟乌龙兮狗之解,吁嗟的卢兮马之婴。”[9]58将乌龙和的卢并称,乌龙食奴故事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乌龙”形象随着这一故事的流传在男女恋情诗中大量出现,而且总是和它忠诚的属性联系在一起,充当“看管者”和“考验者”的角色,男女之间恋情自由的憧憬和尝试从而受到了考验和阻碍。因为这种形象横亘在男女主人公面前,使得他们在偷偷相会时,常常表现出惧怕“乌龙”的心理,不得不看“乌龙”的脸色行事。
“唐人艳体诗中,以‘乌龙’为狗之雅号。”[5]443唐人以“乌龙”命狗,除了词意雅致,方便对仗之外,可能也和“乌龙食奴”故事有一定的关系。元稹《梦游春七十韵》追忆昔年恋情写道:“未敢上阶行,频移曲池步。乌龙不作声,碧玉曾相慕。渐到帘幕间,裴回意犹惧。”[10]731“乌龙”在此处充当了阻隔恋情的角色,诗人逡巡曲池,有所顾忌,不敢直入,可能便有惧怕“乌龙”狂吠的心理原因,但正是因为曾“相慕”,所以“乌龙”才不做声,元稹也就提起胆子“上阶行”了。在白居易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也出现了“乌龙”这一形象:“转行深深院,过尽重重屋。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渐闻玉佩响,始辨珠履躅。遥见窗下人,娉婷十五六。”[11]4856这里也提到“乌龙”静不做声。和元稹诗一样,作者用“乌龙”的沉默和青鸟相逐来表现两情相悦和顺利相会。正是因为两人已经有情在先,所以“乌龙”才通人性一般,没有惊起狂吠,这就给作者提供了便利,作者对“乌龙”的惧怕也自然转变成了“乌龙卧不惊”的喜悦。明代杨慎《南歌子八首》其四:“青鸟飞相逐,乌龙卧不惊。镜约与钗盟。月沈星欲堕,奈何情。”[12]797则化用元白而来,同写这种“乌龙”不惊而情约已定的暗喜。唐人《联句》:“绣床怕引乌龙吠,锦字愁教青鸟衔。”[13]9021韩偓《妒媒》:“洞房深闭不曾开,横卧乌龙作妒媒。”[13]7836很好地表现了恋人对“乌龙”的复杂心理。一直到北宋柳永《玉楼春》词:“乌龙未睡定惊猜,鹦鹉能言防漏泄。”[14]20仍可见男女恋人间惧怕“乌龙吠”,唯恐其“定惊猜”的恋爱心理。
唐以后“乌龙”作为狗的雅称,不自觉地带有“乌龙食奴”故事的影响。在恋情诗中,男女双方相会常常惧怕“乌龙”猜疑而狂吠,这种狂吠一方面继承了“尨”形象吠声引人的特点,一方面又发展出忠犬护主的新特点。男女相会时,如果“乌龙”狂吠,则表示相见不得,相会失败,男女双方不得不因为惧怕心理而就此作罢,长相喟叹;若这种狂吠转为“卧不惊”,则表示情约已定,相会无阻,惧怕心理也就随之转为暗喜。男女相会的惧与喜就这样和“乌龙”的惊与不惊、吠与不吠联系在了一起。
(三)黄耳传书:浪漫温情色彩的产生
男女一别两地,天涯海角,相思徒生,锦书难托,因此在诗歌中萌生出了一系列动物代人寄言传信的浪漫想象。在这些想象中,归雁可以衔思,青鸟能为探看,甚至鲤鱼亦能寄信。作为一种忠诚的家畜,狗也被寄托了神奇浪漫的色彩。《太平广记》载: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驲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纳)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之为“黄耳冢”。[15]
在诗歌中,羁留他乡的诗人总是希望能出现像黄耳一样可以两地传书的神犬以寄托相思,消解距离的无奈与无力。“黄耳传书”故事因此得以在后代诗人的笔下展开。林景熙《黄耳冢》:“筠筒音断水云村,吠入空林枸杞根。我亦天涯音信杳,卢令诗在为招魂。”[9]425即表达了这种情感。在这些包含美好希望的诗句里,黄耳所传的书信多融进了家人亲友间的问候或诗朋文侣间的关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友朋间书信往来以及对父母兄弟儿女的问候叮咛之外,在家书中也断然少不了对妻子的思念和关怀。且看宋人姚勉《思家信不至》一诗:
又是秋风入芰荷,尚无黄耳到如何。慈亲想自精神健,娇女应添智慧多。踪迹自嗟成漫浪,利名底苦欲奔波。几时了却胸中事,只傍南溪理钓蓑。[16]
诗中以黄耳代家信,家信不至,诗人只得遥想家人近况聊以自慰。他先想到父母身体应当依然健康,精神矍铄,又想到小女儿应该已经长大略通人事。但就在这“慈亲”“娇女”的对举中,妻子却被轻易地忽略了。这显然与诗人顾忌礼法,不多于诗中细论男女关系,尤其是正式夫妻关系的传统有关。我们不难推想,在作者日夜期盼的家书中自然少不了对结发妻子嘘寒问暖的只言片语的期待。再看吴伯固女《寄外》诗中的几联:“自此知君无定止,一片情怀冷如水。既无黄耳寄家书,也合随时寄雁鱼。日月逡巡又一年,何事归期竟杳然。”[9]157这里女子思念未归的丈夫,但是丝毫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在唏嘘感慨丈夫家书不到,相思难凭的同时,也印证了上述诗人所寄家书中必然包含对妻子的思念与关怀这一点。再引宋代著名女词人朱希真一首闺怨词(原调已佚):
苦汝临期话别,与君挽手叮咛。归期誓约十余朝,去后又经三四月,鱼沉雁杳,空倚著六曲阑干。
凤只鸾孤,谩独宿半床衾枕。欲寄花牌传密意,奈无黄耳堪凭。待修锦字诉离情。[14]3854
在朱希真的笔下,不再有所顾忌,黄耳终于和青鸟、鲤鱼一样,带着它们被赋予的浪漫色彩,来往于分隔两地的情人中间,替他们传递浓情蜜意了。但现实情况往往是落空的,“奈无黄耳堪凭”,而诗人们对黄耳的期盼和喜爱则为恋情诗中狗的形象抹上了温暖与浪漫的色彩。
二、唐朝康国猧子的流入及社会普及
上引诗词中狗的形象虽然几经变换,但品种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家狗,在诗中的角色定位超不出传统家狗的性格特征。唐宋以后,这种传统家狗形象虽然继续出现在诗词中,但并未开拓出新的形象内涵。唐初国力强盛,丝路的畅通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康国进贡了一种新品种的狗——哈巴狗。这一新型犬种首先在宫廷中受到欢迎,并逐渐走进民间社会,成为唐代妇女的新宠。由于养猧子这种社会风气的盛行,在此后描写恋情的诗词中,除了上述传统家狗形象之外,这种新型的宠物犬成为诗人们乐于描写的新宠,并逐渐成为主角。《旧唐书·高昌传》载:
可见,唐高祖时期由于西域进贡,中国便开始出现了叫“拂菻狗”的小狗,有学者指出,它可能是古代马耳他种的犬,也就是古典时期的巴儿狗[18],但数量并不多,只限于宫廷内室。到了玄宗朝,这种新型小狗已深受杨贵妃的喜爱,成为她的宠物了。《酉阳杂俎·忠志》载:
上(玄宗)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19]
这种能够在棋局上捣乱的康国猧子就是后来所谓的哈巴狗,因为娇小可爱,受到了宫廷妇人的宠爱。史载开元十二年(724):“(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献侏儒一人,马、狗各二”[20],其中很有可能就包含这种小型犬。可见,由于外来不断进奉加上进奉品种再繁衍,这种新型小犬的数量不断增多,逐渐成为宫廷妇人身边的宠物。这种风气可由传世画作及出土文物得到印证。今传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便记录了猧子这种小犬如何受到宫廷妇女的喜爱。图画中,一位宫廷妇女手持绒线摆动,逗弄猧子,猧子前扑嬉戏,十分生动可爱。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唐人宫乐图》亦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在画面左下方,宫女围坐的桌子下,就安静地卧着一只猧子,惹人怜爱。此外,在今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有三尊出土唐俑,这三尊俑中狗的形象值得注意。其中,第一尊,博物馆命名“褐釉小瓷狗”;第二尊,名“三彩抱狗女坐俑”;第三尊,名“粉彩抱狗女立俑”。从其体貌特征来看,其中的“小狗”很有可能就是猧子形象。若是,则可见,在唐代猧子这种小狗已经被制作成俑陪葬。遗憾的是,博物馆并没有公布它们出土自何时何地,不能藉此推知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三尊出土俑却是探讨猧子在唐代社会流传的重要资料。
开元天宝以后,猧子这种新型哈巴狗的数量开始增加。不仅宫廷贵妇养有猧子,社会上的一般女性也以争养这种小宠物为时尚。这一点,可以借由唐人传奇小说和敦煌变文来印证。牛僧孺《玄怪录》记载了一则关于民间妇女与猧子之间的离奇故事。
洺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俞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存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瘗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21]
在这一故事中,洺州刺史卢顼表姨养了一只名为“花子”的猧子,被人杀死之后,卢氏不久也身亡。随后,卢氏与猧子在冥间相遇,猧子为报恩,为卢氏改增了二十年寿命。后来,卢氏遵嘱为其收尸礼葬。“花子”尸骸所在的“履信坊街之北墙”位于东都洛阳,可见,养猧子的风气,已经从长安宫苑内扩散至东都洛阳的普通妇女阶层了。而且,从“每加念焉”“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以子礼葬之”中也可窥见当时女子对这一犬种的宠爱珍视。养猧子在社会上的流行不仅限于两京地区,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仍能发现它的身影。如唐人传奇《时太师溥》主要写徐州廉使时太师溥的故事,其中记载:“忽见一猧儿,遂敲药少许,揾饼与食,其犬须臾之闲,化为烈焰一团,腾空而去。”[22]3286《马自然》一篇,写到他南游的过程,见一菜园,求之不得,于是作画相戏:“湘又画一猧子,走趁捉白鹭,共践其菜,碎尽不已。”[22]3084猧子在这些传奇故事中出现,可见在当时,已经是较为普通的犬种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变文中,也可见到佛教用猧子举例,来宣教佛法,启育民众的事例。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附诗:“见伊莺(鹦)鹉语分明,不惜功夫养得成。近日自知毛羽壮,空中长作怨人声。可憎猧子色茸茸,抬举何(荷)劳喂饲浓。点眼怜伊图守护,谁知反吠主人公。”[23]1111《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一)》附诗:“婴孩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猧儿。”[23]1473佛教变文是为了向俗众宣扬佛法,追求通俗晓畅,易为大众理解接受,那么,在这些变文中,以猧子为例,来宣扬佛法,是否也反映了猧子已经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东西?
三、猧子在诗歌中的审美境遇
猧子在唐代社会普及开来后,历经宋元明清几朝的发展,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伙伴[24]。不仅在绘画、民间杂技中开始大量出现哈巴狗形象,在恋情诗中也不乏其身影。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比乌龙、黄耳等传统家犬价值更高,而是因为它可爱有趣,同鹦鹉一样,具有玩赏价值,能够给女性无聊寂寞的闺房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同时,哈巴狗对人若即若离的依赖,能够惹起恋爱中女性的怜爱,牵动女性的思绪,给本来就多愁善感的女性提供了一个情感寄托对象。这种作为移情对象的哈巴狗,在恋情诗中除了猧子乱局故事的隔代遗响和男女幽会模式的关键象征之外,一方面演变成了诗歌中女性环境描写的点缀物,一方面又和女性闲愁相思心理密不可分。
首先,李杨爱情遗事自安史之乱以后就成为诗人们争咏的对象,在描写男女浪漫生活的诗歌中便常常见到猧子乱局故事的隔代遗响。如“小院铜环双扣,何事堪消残酒。漫拂玉纹楸局子,赌个今宵无偶。半局便知郎欲覆,先逐康猧走……”(董以宁《百媚娘·弈棋》)“曲阑干外红兰吐,绿窗人静闻鹦鹉。两两赌围棋,沉吟金钏迟。郎夸中正手,向姊偏多口。解意小猧儿,恼人将负时。”(王世禛《菩萨蛮·弈棋》)“窃香凤子纷成队,撼局猧儿太作狂。”(朱祖谋《鹧鸪天》)可以看到,清人对这一“猧子撼局”故事的钟爱,以至于屡次用到这一事例。
其次,在男女幽会赴约中,哈巴狗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同上文所论尨、乌龙、黄耳等传统家狗相比较,又表现出新的形象色彩。上引元稹《梦游春七十韵》还写道:“逡巡日渐高,影响人将寤。鹦鹉饥乱鸣,娇犭圭睡犹怒。”[10]731“娇犭圭”有本又作“娇娃”,陈寅恪先生考证“娃”为“犭圭”误,而“犭圭”即“猧儿”。结合上引唐人传奇小说及变文材料来看,玄宗朝在宫廷尚属于珍贵物种的猧子,贞元年间已经流向社会,普通女子已有驯养[25]。上文引此诗前段,已见诗人徘徊逡巡,终于因为门外乌龙卧不惊而进入室内,得度春宵,此刻醒来而此室内“猧儿”仍睡意半酣,但诗人对其却无丝毫的惧怕意,反而觉得其“娇”。唐末无名氏的《醉公子》二首:
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
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13]10162
听到猧儿吠,女主人公得知自己的情人到来,不再像此前那样担心狗吠惊人,反而满心欢喜。在敦煌的曲子词中,恰好也有一首与此十分相似的《鱼歌子》:
绣簾前,美人睡,厅前猧子频频吠。雅奴卜,玉郎至。扶下骅骝沉醉。
出屏帏,正云起。莺啼湿尽相思被。共别人,好说我不是。得莫辜天负地。[26]
藉此也可见,中晚唐以后,哈巴狗已经普遍流行,当时一般女子多有驯养。这种哈巴狗在男女幽会中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威胁,猧儿吠不再让男子和女子担惊受怕,反而成了男子赴约的信号,引起女主人的欣喜。外来物种哈巴狗的流行,使恋爱中男女对传统家狗形象的惧怕心理演变成了对这种新型宠物犬的宠溺心理。
再次,猧子这种哈巴狗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不仅成为女性身边常见的宠物,也成为诗人们争相刻画的对象。王涯《宫词》其十三:“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13]3878以宫廷中白雪猧儿只晓得吠晚萤的形象来表现深宫女子的寂寞,这里的狗吠声较上文已经有了新变色彩。元稹《春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犭圭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以猧子撼动钟声的巧妙构思,来表达天欲破晓的时刻。南唐成彦雄《寒夜吟》:“猧儿睡魇唤不醒,满窗扑落银蟾影。”在描写女子深夜寂寞情怀时,也以猧儿形象加以渲染。这种手法到了宋、明诗人的笔下,得到继承。如“昼下珠帘猧子睡,红蕉窠下对芭蕉”(宋白《宫词》),“联房自信无人到,闲放猧儿自在眠”(王世贞《西城宫词》其十二),与唐人同调,都以猧儿无吠人之声,来表现深宫无人到访的寥落凄凉。这些描写女子闺情的诗句中,都以猧儿作为点缀,可见这种小动物已经成为女子生活中的常见物,和女子闺房形象密不可分,也成为了恋情诗词中重要的表现形象之一。
最后,哈巴狗还常常和女子的相思闲愁联系在一起。哈巴狗既然已经成为女子闺房中的常见形象,那么必然成为表现其相思闲愁的寄托物,这种手法在清人词中屡有使用。如“澄澄人坐碧琉璃,今夜清光定属谁。干瓦鸳鸯俱露宿,紫衾轮与睡猧儿。”(曹勋《闺词》)“塞云横,关月远。帘外霜浓,寒重呵金剪。手擗绿橙香雾溅。绣被兜罗,只许猧儿伴。”(曹吉贞《苏幕遮·冬闺》)女子独守闺房,寂寞冷清,只好猧儿相伴,恋爱中的浓浓怜爱之心遂转移至此娇小可爱的宠物身上。因为这种相思闲愁以至无限寂寞,夜不能寐,这个时候往往将寂寞之苦转移到对猧儿的埋怨中来。如“笼鹦不语帘猧睡。怨无聊、个人愁寂,重门深闭。”(姚燮《金缕曲》)“风片片,雨丝丝。春情偏在晚春时。氍毹红稳猧儿睡,帘幕青摇燕子归。”(许嗣隆《桂殿秋·雨中》)猧儿只顾自睡,全不解漫漫长夜主人辗转反侧,回肠已断如篆香。“倩小玉、摘相思子。好把猧儿打去,休搅春宵睡。”(陈维崧《有有令·咏画眉鸟》)当女子好不容易枕入华胥,在梦中获得一丝一缕安慰,又被猧儿打破,自然满心怨恨。“又是同云酿雪天,猧儿嫌冷唤愁眠。为郎憔悴有谁怜。”(项鸿祚《浣溪沙》其十四)冻云酿雪天气,猧儿犹嫌冷而愁眠,女子之憔悴永夜亦可想见一斑。总之,在闺房之内,猧儿已成为女子少有的陪伴之物和移情对象,寄托着女子的相思闲愁,也倾听着女子的寂寞冷落。至此,恋情诗中狗的形象已经从传统家狗发展出了闺房宠物的新内涵。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唐朝康国猧子传入之前,作为传统的家狗,因为它吠声有惹人关注的特点和男女幽会的恋爱方式冲突,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恋人们的憎恶。而狗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家畜,又因为忠诚属性,遂被人们赋予了诸多浪漫的想象,带上了传奇色彩。“乌龙食奴”“黄耳传书”等故事不断流传,使恋爱中的男女也经历了从惧怕乌龙阻断相会,以乌龙吠与不吠来表现爱情约定的有无,发展到期盼黄耳再现,能代为两地传书,传递相思之情。唐朝以降,受中外文化交流影响,新犬种——哈巴狗得以流行。这种新物种一出现,立刻受到了宫廷女子的喜爱,也成为了诗人和画家争相表现的对象。随着哈巴狗从宫廷内阁走向民间闺帷,这一新兴犬种逐渐融入到女子的闺房生活,成为了女子的移情对象。在恋情诗中,原来对狗的憎恶、惧怕心理也发生了转变,哈巴狗已经成了描写女子寂寞生活和相思闲愁的重要表现者。在考察狗的形象在恋情诗词中的演变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其背后透露出的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这其中折射出的男女恋爱心理、爱情中女子形象的变化,以及外来物种本土化后对传统诗歌审美形象的影响等深刻复杂的信息,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