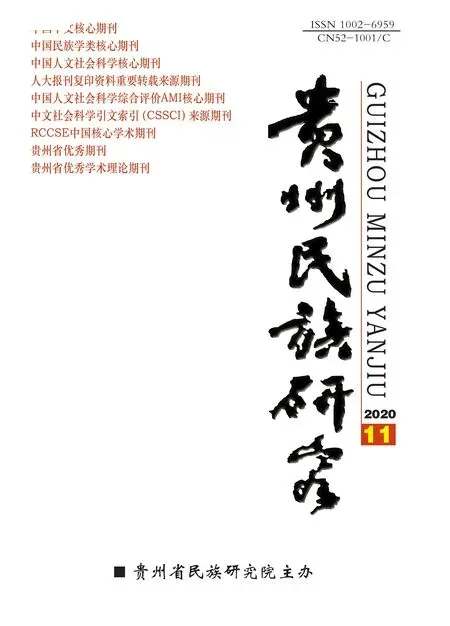口述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实践与反思
——以影像志《龙州史话》为观照
卢芳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一、拍摄缘起:民族政策流变与社会发展
平武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平均海拔3000 米,平武东接青川,西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南邻北川羌族自治县,无论是历史上的“州治”还是解放初期的自治,平武都被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所包围,也是四川省民族散杂地区拥有民族乡最多的县。在道光《龙安府志》中提道:“龙郡边界陕甘,番羌杂处。”在《序》中也说道:“我龙郡僻处边陲,介在氐羌,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笛凄凉迟暮,地则刀耕火耨,人半耐冷披毡,舟车不到,贾客罕闻。”[1]自古以来,平武就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现在是以藏族、羌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从分布上看,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全县有汉、藏、羌、回等20 个民族,总人口18.6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6.65万、占全县总人口的35.8%,是四川省杂居县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该县民族乡比例高。全县辖9镇16个乡,其中8个藏族乡为白马、虎牙、泗耳、黄羊关、木座、木皮、土城、阔达,5 个羌族乡为锁江、平南、徐塘、旧堡、水田,占乡镇总数的52%,另有3个羌族人口占90%以上的镇(平通、豆叩、大印),民族乡和羌族聚居镇占全县镇总数的64%。
平武县作为和平解放、民族团结典范的历史与现状,从“民族团结示范创建”角度考量,具备特殊意义。随着对该县历史、民族政策流变过程的发现,结合影视人类学专业背景,通过口述影像志来展现70年来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实践与社会发展。影像志试图呈现平武县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实践:从全国最早筹备建立县政一级的“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到和平解放、开创广大藏区地区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从落实少数民族比照县待遇政策到逐步恢复民族乡、落实民族政策,展现70年来平武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从中可见70年来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流变过程。从历史长河看,作为氐羌之地,平武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在“羌番杂处”的龙州大地上,各民族相处和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0个不同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共同体,目前正在争取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典范”县。这段共同书写的历史记忆,在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具备值得正视的典型意义。
影视人类学学科路径具备文本记录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正如之前学者指出的那样,非文本的口述具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其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纳日碧力戈2013年)。由影视人类学作为研究路径的“非文本”的口述,无疑具备以上归纳的诸种优势,通过在摄影机前的全息记录,具备文本所不及的生命感、直观与感染力。同时又避免“在用文字形式颂扬口述史价值的同时,无意中使它脱离了时空语境、失去真人真事的鲜活”[2]这种遗憾,这是影视人类学作为记录手段的优势。而如何通过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开展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笔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没有预设任何拍摄提纲,而是在工作中通过阅读史料、走访经历过的老人等方式来逐渐获得对这些横亘70年的民族政策实践的认知。通过广泛地阅读、接触当地群众,逐渐明确10多名70岁以上的不同民族的历史见证者,作为口述影像志的访谈对象。这样的学术路径与工作方法,与之前在传媒大学得到的影视训练迥异,影视人类学强调的“不做预设”、在研究中逐渐产生问题意识、在研究中逐渐确立影片结构,成为完成该部口述影像志的逻辑起点与创作基础。
从民族史的角度考量,建国初期我国的民族关系史,被誉为民族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平武县和平解放恰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平武县于1949 年12月27日宣布和平解放,早在平武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平武的地下党组织对平武土司做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之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完成了旧政权的更替。《龙安府志·土司志》载世袭白马路番地的王氏土司家族中之长官司道:“国朝顺治六年(1649年),王瑶首率番夷投诚,仍袭长官司之职,防御阳地隘、黄关等关,管辖白马路簇十八寨番夷。”[1]民国时期,川北与甘南地区的人们,依然沿袭明清以来的旧称,把王氏土长官司与王氏土通判世袭管辖的这部分氐羌系民族,称为白马番或白马西番。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身体操演的概念。康纳顿认为研究社会记忆的重点在于探讨它的传授行为,他特别提出注意社会记忆研究中两个十分重要的领域——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而身体操演又是其中最核心的课题。奥力克等人的研究聚焦于社会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涉及的范围包括意识与无意识、公共与私下、物质与沟通等等。他们认为社会网不同,记忆实践也会不同,社会记忆不是一件孤立的事项(Olick,Robbins,1998 年)。有学者认为:“社会记忆实在就是社会行动,因为口述史的操演本身就是社会行动,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或鼓掌喝彩,或专心倾听,或有问必答,那不是行动又是什么?”“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者以第一人称或以见证人的身份,以‘说来话长’‘很久很久以前’之类的句式开始,以令人信服的口吻,给公众讲故事。口述者、听众、特定的时间和场景,彼此相嵌,浑然一体,让口述史变得有权威。说话就是历史本身。”[3]对于平武县藏区的和平解放的历史,平武县本土学者曾维益在口述中表示:“平武民族工作就作为一个典型,平武民族工作搞得好,稳定了地方形势,少数民族爱国爱党。它的结构呢,我的理解是传统中国的进行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民族区域自治州、自治县的框架的结构和形式,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针对新形势、新条件下新的形式。”[3]在他的叙述中,“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要得天下,但是作为普通的少数民族不知道,这个时候,平武县是1949年12月27日宣布和平解放”。对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社会力量构成,他认为:“当时社会是由以下几股力量构成:第一股,就是统治这个地方700年、将近800年的土司王实秋手下有两百多支枪炮;第三股力量没有浮在表面、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在社会即将发生变化的时候,他的力量很大。而真正的解放军并没有来,正在广元、青川这边走。”[4]其后,1950 年1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武县政府正式成立。至此,自元明以来就被称为“白草番、白马番、木瓜番、白草羌”等少数民族,遂被当时的川北行署统一地定成藏族,对另一部分已失民族语言、不穿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则全部划为汉族。
根据史料,1950年1月19日,世袭土司长官司王蜀屏与白马路达番官杨汝散发《给松潘各部落的信》,提道:“我已得到文县解放军的信和今天解放军来城,共产党已与二十四年(编者按: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 不同了,尤其是对我们藏胞,说依然是照我们的旧土司番官制,信奉我们自己的教,不拉夫出款,所来的解放军都很和蔼,连我们平武的衙门都未驻扎。”1950年6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川北行署主任的具体指导、安排下,平武县率先(全国最早) 筹备、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在筹备会议期间,川北行署亲临平武地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1950年6月23日至7月1日,四川省川北行署在驻地南充市,召开了川北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平武地区的世袭土司长官司、土通判、土知事中三大土司和龙州三番(白马番、木瓜番、百草番) 这三种少数民族中番官、头人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平武的少数民族代表们,也就是番官、头人、少数民族代表们发表了“告藏族同胞书”。其中提道:“这回我们硬看到了共产党的好处,胡主任亲自招待我们,刘部长给我们点火吃烟,又派汽车到处带我们去耍,从没见过的机器工厂都见过了。回来又给我们缝绸衣裳和画布,又叫我们自己管自己,又借给我们卅万斤苞谷叫我们养羊喂牛,还跟着办学校给我们,所以一切粮款都不问我们要,同胞们生下来从没见过这样的政府。”[5]1950年7月31日,在平武县城内召开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这些举措,没费一兵一卒,实现了平武县藏区的和平解放,开创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我国广大的藏族地区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成为我国进行民族团结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典范。
在不同角色的讲述者中,讲述内容相互依存,互为印证。马登清老人(回族阿訇) 的口述则恰好作为学者的补充:“我父亲当时没放一枪一弹,看到那个城楼上斧头镰刀,就把他们迎进城了……”这些来自不同角度的叙述互相印证,分别从学术层面的描述、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对“和平解放”的记忆做出不同层面的诠释,学者的记忆显然着眼国家记忆:“南充时川北行署驻地学习,领导发指示:平武有少数民族很可贵,要把少数民族工作按照共同纲领做好,所以就筹备成立平武县藏族自治筹备委员会,就成立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改成平武县藏族自治区。”而马阿訇的叙述则着眼于往昔个体回忆:“我们平武是平安解放的,当时解放平武过后50年成立川北行署,平武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招牌就挂在现在的王坝楚,这是县级当时成立了供销社,就为那一方民族,慢慢地有盐巴吃了。以前交通不便,他们靠挑牲口拖运往上,在1951年第一次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这里的讲述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老人的讲述延展画面空间与历史纵深,家国记忆交织,较之文本记录,影像的直观性、丰富性显著增强。
二、结构呈现:身体实践与社会记忆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 中指出:“事实证明,或多或少属于非正式的口述史,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这是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6]他提出:“我们可以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人互相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作描述,通过相信或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份的故事。”[6]影像志试图通过平武县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亲历者的追忆描述当时的生活,建构是历史真实与社会记忆。当试图描述1956 年平武县建立民族乡、落实民族政策落实实践时,笔者遇到的困难即是:经过民主改革运动的老人非常少,能够讲述的人已然不多见,这客观存在的现实困难也凸显出口述影像志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根据史料,1956年7月,平武县藏族自治区正式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并将白马、木座、虎牙、泗耳、木皮、黄羊关由土司制度改为乡人民政府。在历史上持续了几百年的土司、番官、头人制度正式结束。1956年11月17日,中共平武县县委在《关于藏族地区民族宗教上层任务的安排意见》中明确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后,不降低上层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的精神,对所有民族上层代表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方针,根据其代表性大小、各方面的表现和现实家庭经济状况,分别在政治上予以安排,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来自平武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资料) 这一历史阶段,在73岁马阿訇老人的回忆中如下呈现:“1935年,当时我们把红军迎接进城,称为和平解放迎进来就在我们清真寺成立苏维埃政府。第二天就在报恩寺坝坝里开群众大会,当时的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什么呢?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字、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改善生活、一律平等民族,就提出来了,选举杨汝番官任副县长。”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虎牙乡绒木塔的口述则侧重于“民主改革的温和”,而这确实是平武县民主改革的特点。“我们民主改革很温和、和平地解决了把剥削过去的大地主、有名气的番官、头人们都是共产党团结过来要不就县政协、要不就去省政协。”在口述史的撰写中,学者提出:“当我们成功地识别和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把某个事件、情节或者行为方式,放到一些口述史的脉络中。”[6]康纳顿提出的这点,这也是创作该影像志的重要方法之一:“把某个事件、情节或者行为方式置于口述影像志的脉络之中。”“口述史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表述的是亲身经历和肺腑心声,这样的表述内容不存在性别之分和年龄之分”(纳日碧力戈)。在82岁的白马藏人、尼苏老人忽然落泪的往事回忆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回忆起1967年国庆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时的激动心情;能够感受到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在那个年代的工作热情与对家乡发展的殷殷期盼;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活着为了讲述”,而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影音资料中间选出最能体现彼时民族工作特点、民族政策实践的片段?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的“情节”、“事件”或“某个行为方式”成为工作中的重要细节(无论前期记录还是后期剪辑工作),个人记忆的鲜活生动地取代了简单的政策图解。同时,结合现存遗址、当年红军留下的镌刻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石碑画面,勾勒出了历史的记忆。而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互为印证,避免个人记忆的误差,亦是开展影像志口述史的重要方法。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道:“我们至少要回忆有关某个行动的两种脉络,才能识别那个行动。我们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6]这也是笔者结构该部口述影像志的工作原则,关于“回忆某个行动的两种脉络”,分别是从民族工作与个人生活记忆角度双重进行。影像志的总体结构是以大的时间节点来展开,而个体的生活记忆包含其中,对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记忆中夹杂个人回忆。同时讲述人有学者、汉藏羌回各民族老人,有乡书记、藏区区长,宗教人士、人大代表、参加早期国家民族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对于虎牙藏族乡在不同历史时期均保留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这侧面说明了民族工作的重点,亦是“尊重少数民族”在政策在政治方面的一种重要体现。
回溯历史,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省对平武县民族工作给予极大关注,在四川省民研所主持的“白马藏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高度评价解放初期民族自治政策给平武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充分肯定了平武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地位。
从1986年起,同属白马藏族的木皮乡藏族群众要求恢复建立木皮藏族乡,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93 年(川府民政【1994】42号) 同意平武县将木皮乡改建为木皮藏族乡。1999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平武县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川府函【1999】40 号)。省人民政府批准平武县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县待遇,是充分尊重历史,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2003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改建徐塘、锁江、平南3个乡为羌族乡。2007 年,省人民政府以川府民政【2007】 13号文,批准平武县水田、旧堡改建为羌族乡,土城、阔达改建为藏族乡。时下,平武25个乡镇中民族乡13 个(8个藏族乡,5个羌族乡)。关于落实民族乡的政策实践,除了通过当事人口述,相关历史资料画面的加入也称为组织影片的重要手段。影像志试图通过视听语言综合组织史料、现存文献、搜集历史影音资料,试图以个体记忆勾连时代变革,呈现以下历史记忆:平武县如何逐步恢复建立民族乡,使边远民族地区享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力扶持,有效地促进了文化交流、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完善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启示与反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影视人类学的现实关怀
建国70余年来,在龙州大地上,汉、藏、羌、回各族和谐相处。各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互助协作,共同书写龙州历史。从历史的维度看,龙州历史向来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从现实角度来看,在今平武境内定居的人口包括汉族、回族和藏族这3大部分。而平武藏族包括白马藏族、虎牙藏族、泗尔藏族这3个地方性的小分支。平武汉族多为由番转汉的土著汉人,和由外来移民与本地的氐羌系少数民族通婚后的后代这两部分组成。
据《隋书·地理志》载:“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在古代的平武,该地是既有氐又有羌,还有氐羌存在的多民族共存的地区。据《龙安府志》载,历史上真正使平武地区的民族构成产生重大变化、并影响至今的是清代中晚期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战乱之后,为恢复残破不堪的社会秩序和衰败之极的地方经济,在龙安三土司以及平武县的允准、默认之下,经过“湖广填四川”和近两百年时间的发展,早已处于“人满为患”的川中丘陵地区的汉族,就以此为契机,逐渐地移入平武地区。而龙安山区自南宋末期以来,直接隶属世袭土司管辖。“在改土归流之后,龙安境内的少数民族,事实上属于两种体制管理,一种仍归世袭土司署理,另一种则隶流官知县管辖”,而各山区寨子里的少数民族都有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划界标准,如“山齐梁,水齐沟”,对于外来的汉族移民可供开垦的土地范围,需要得到世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意才被获准进入该地落户耕种。在抗击白莲教农民军战争后,由于少数民族丁壮大量死亡,而当地少数民族有入赘传统,这种方式亦成为当时外来的汉族移民在当地定居的最佳选择。这既增强了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家庭中一员,通过相互结亲,经济上又使汉族移民因此少缴纳土地税,土司又相应地增加了人丁和相应的人头税,税赋增加,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
除了入赘,平武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还包括历史上的历次战争、抵御自然灾害、瘟疫等各种天灾,他们互相融入,彼此融化,在坚持各自文化传统的同时共同谱写了龙州历史,并在几百年的相互交流交往交融中生生不息、共同进退、通力协作,应对各种人为或大自然的各种灾害。逐步形成了平武今日各民族、各种宗教和谐共处的典范局面。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有学者分析“因嘉庆五年(1800年) 的战乱而导致的汉族移民开始移入平武地区,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趋势,至今仍在进行。其最终的结果是:将几千年来原本为氐羌民族聚居生存的龙安山区,逐渐地演变成了氐、羌、藏、回、汉等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区域。”[6]平武的回族,系由明朝洪武初年随军而来,后奉命戍守定居于此,之后又从松潘等地陆续迁来。氐羌系少数民族主要由世居其地的土著,和少许属于同一族系的外来移民(从松潘、南坪、文县移入) 构成。嘉庆七年(1802年) 之后,外地汉族陆续移入龙安山区,汉族移民在移入当地后,充分利用海拔高度适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地广人稀等优势,迅速发展茶叶生产,使县南羌区成为四川知名优质茶叶生产基地,所产边茶畅销于松潘藏区。在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的同时,当地白草羌人的传统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也已迅速消失,但当地仍保留传统习俗,比如穿白衣、尚白色和在坟头上放置白石、穿羌人的云云鞋、居住三层吊脚木刻结构楼房、北川羌族还北上到平武豆叩地区向当地的端公学习,更加说明:平武县的豆叩地区是羌族居住区。随着外来汉族移民的迁入与定居,与本地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交融,不但在血缘关系上,而且在生活习俗上开始逐渐地融合在一起。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三次“改土归流”之后,世代生活于斯的各民族仍在生存与发展,相互依存,守望互助,共同繁荣。
除却展示平武县70年来民族政策的落实实践,影片试图传递本土人对于现实问题的隐忧与思考,白马乡代表尼木修老人的讲述中表示:“我们源头就是涪江上游,我们觉得对下游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提到生态补偿的问题,认为“应该下游对上游要有一定的补偿机制”。也有老人表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提出“当时县上觉得平武靠山吃山,就靠大山资源过日子,(因生态保护)啥子路都堵住了,农民出路、生活来源、农民今后挣钱的门路在哪里?”该问题的提出,始自50年代至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依然存在。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出发,影像志关注到当地各族人士的本土观点,从各自的工作经历、生命历程角度,他们从经济、教育、生态、社会发展角度表达出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议与愿望。
四、结语
影视人类学通过关注身体实践何以联结社会记忆的关系,完成知识生产,进而呈现平武县这一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政策实践。作为口述影像志的拍摄过程、口述史的操演本身就是社会行动。口述民族志应当聚焦真问题,在结构作品的同时产生知识,凸显当地人的主体性,而非简单的信息堆砌。而这段民族工作的历史,充分说明“民族区域自治或者民族地方自治颇有渊源,并非外部强加或者赏赐”,从该县域民族工作实践历史可以看出:我国70年来民族政策的流变过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多年来各民族政治协商的结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需要多维视角,需要对历史过程的仔细考察,才能比较稳妥地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是对于影视人类学学者创作的启示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