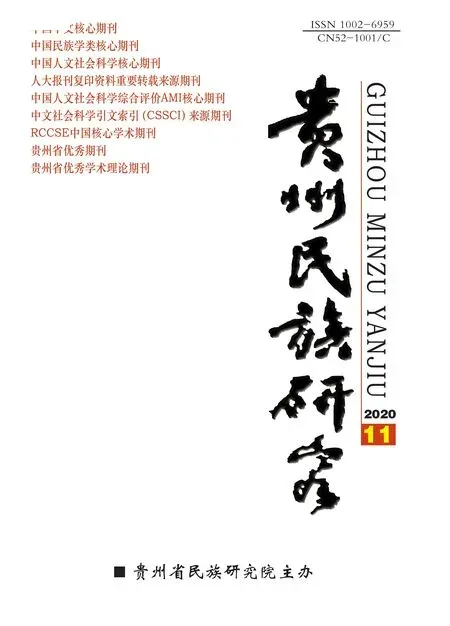“卡果哇”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
——以同仁县江什加村结夏安居欢庆仪式为例
骆桂花 马文利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广州 510000;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 810007)
同仁县地处青藏高原游牧区与黄土高原农耕区的缓冲接合带,这片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方面交流互动的空间场域。“Kha-mgo-ba”(藏语音译) 中文表述为“卡果哇”,意为组织人或负责人,由藏区部落内临时推选或选派产生,是藏区部落内部灵活高效的组织团体,时而指挥生产,时而组织处理应急或临时性活动。同仁地区的“卡果哇”从起初基于战事互助的部落联盟到平衡供求关系的部落协作,再到行政区划确定后乡村社会非政府组织,经历了藏区社会的多重转型。
1956 年之后,民族地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土地收归国有,实行集体所有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藏区传统的部落组织经受了制度性变革,但“卡果哇”这种传统社会组织并未丧失其在村落中的调控和管理职能,一直在村落社会组织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卡果哇”在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运行、专业力量方面都能与藏区基层社会的需求能对应起来,因而对研究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很多时候“卡果哇”类似于村内权威的组织方,村内任何集体活动都由“卡果哇”这样的组织团队协调管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因此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是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
在新时期社会治理中,依靠地方性知识以及当地传统文化的“软实力”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仁县江什加村在举行一些特定仪式活动临时选举出来“卡果哇”,通过其特有的文化背景与实际经验,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了其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传播的功能和作用。“卡果哇”的存在与运行不仅能够提升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同时对于其本身“软实力”的提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藏区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举办某种仪式或活动时,原本为“个体”的家庭因“卡果哇”的组织而变成“集体”。通过“卡果哇”的组织与协调,家庭的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在基层社会中发生变化,作为个体的家庭变成集体,作为集体的村落又变成个体。本研究拟以藏传佛教结夏安居欢聚仪式的组织负责人“卡果哇”为例,探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组织的作用。
一、村落与仪式: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场域
江什加村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曲库乎乡的一个行政村,西邻古德村,东接江龙村,南接索乃亥村,北与同仁县牙浪什乡接壤。地处隆务河谷底,气候干燥,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302 省道穿村而过,省际间连接道路,链接了江什加村与外界的经济文化。全村常住人口约200户共有1061人,耕地面积600余亩。村子里目前都是藏族人,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定期会举行一些重大活动及宗教仪式。笔者此次进行参与观察的结夏安居欢庆仪式就是其中的一种宗教活动。
结夏安居也称佛欢喜日,是佛教僧侣在每年雨季不便出行时集中学习经律的一种制度。安居之制始行于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其中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皆为盛行,之后被佛教所吸收,并成为佛教戒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佛教的向外传播,因各地的地理气候及岁时节俗等差异,使得安居制在各地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各地佛教僧侣也会按照当地雨季的时间来决定结夏安居的具体时期,僧侣们每完成一次结夏安居学习僧龄便增长一岁。
历史上,同仁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寺院隆务寺为了便于僧侣们集中精力学习经律,特定于每年藏历六月十五到八月初一集中进行封闭式念经活动,这便是同仁地区的结夏安居。在结夏安居活动期间,僧侣全身心投入学习经律,不与外界接触,时间长达一个半月,直到藏历八月初才开禁。为了庆祝僧侣圆满完成经律学习任务,寺院会为僧侣分发一定的食物、钱财等,有时也会组织到寺院附近的草坪或树林进行野餐和歌舞[1]。当今,同仁地区的隆务寺及其属寺仍然在藏历六月十五到八月初一举行结夏安居活动,而在八月初开禁时,庆祝仪式不再由寺院僧侣负责组织举办,而是由信众们承办举行, 在当地称为“Dbyar-ston”(藏语音译),翻译过来就是结夏安居欢庆仪式。
通常,希望承办结夏安居欢庆仪式的村落或家庭会提前申请举办,以此来获得福报。在整个仪式的筹办过程中就不得不提“卡果哇”,这个从传统社会组织中保留下来的职位,如今依然在村落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卡果哇”和以前一样,它的身份特征具有灵活性,可以临时成立,也可随时解散,选举的方式也是由村里人推选或者选派。
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表述为“双轨政治”,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按照两条平行的轨道进行:一条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轨道,以皇权为中心建立一套官僚体系,由官员和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另一条则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士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2]。
在藏区传统社会中,“卡果哇”类似于费先生所言的“士绅”角色。据笔者了解,当村子里出现一些重大事项或纠纷事件时,“卡果哇”会临时聚集起来调节纠纷,当村子发生一些自然灾害时,“卡果哇”会带领村里人集体解决困难。“卡果哇”这种存在于村落中的传统社会组织是藏区村落有序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与国家基层组织形成互补,共同为乡村平衡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
二、仪式过程里的“卡果哇”: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表现形式
自元朝结束吐蕃在青藏高原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之后,包括青海在内的广大藏区在政治上首次统一于中央王朝,至此推行政教合一来进行地方统治。同仁地区作为元朝的统辖区形成了以隆务寺为核心的热贡十二族来布置供施关系,地方内部依然以传统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青海省黄南州隆务寺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所属僧侣约有500 名,下辖子寺众多,在隆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当地僧侣们的结夏安居欢庆仪式由附近村落里的家庭自愿承办,隆务寺主管人员根据经验一年会选8个家庭来承办结夏安居欢聚仪式,笔者参与观察的场所是承办2019年度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活动的第七个家庭。
2019 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五)笔者到达本次仪式承办家庭所在的村落——江什加,此时距仪式开始还有一天半的准备时间,正值“秋收”时节,在经过村子主干道时看到村委会广场前有几位妇女在收拾麦子。据报道人旦增(化名,下同)说:“结夏安居欢庆仪式近两年由村落或家庭承办的比较多,我知道的仪式承办方已经排队到2022 年了。这些承办方按照隆务寺执事僧的安排按顺序负责仪式的承办。我们家是今年负责承办仪式的第七家,自接到仪式举办的通知后,我们在仪式开始前的一个月就开始准备,现在基本上已经准备完成。”(访谈对象:旦增,男,32岁,教师)
旦增家自得知能够承办今年结夏安居欢庆仪式起,家庭成员们就进入了初期筹备阶段,而在距离举办结夏安居欢庆仪式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们也逐渐忙碌起来了。
根据村子里的传统习惯,每次举办大型仪式活动前,都会选举“卡果哇”,即临时负责人,此次仪式一共选了17位具有仪式承办经验的临时负责人,具体有仪式流程负责人、仪式供品摆放负责人、后厨负责人、接送僧侣事宜负责人等。临时负责人召集村民们参与筹备仪式各项事宜。
对当地人而言,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是一项大型宗教仪式活动,承办家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展开了一系列动员和人员组织工作,具体方案通过“卡果哇”来实践与协调。
(一) 主管仪式供品的“卡果哇”——精神层面的统筹与协调
主管仪式供品的“卡果哇”大多是寺院僧侣,被推举为“卡果哇”的僧侣一般会提前到达仪式举办地,在他们的指挥与协调下,人们有序地制作所需的仪式供品。在藏族社会里,家庭内部的两性劳动分工有着特殊的模式:一般男性承担家庭宗教仪式与对外交际事宜,女性则进行生活中的饮食准备等各项家务劳作。在结夏安居欢庆仪式里,这一点也有体现,即仪式供品的准备全是男性来制作并参与摆放的。
主管仪式供品的僧侣“卡果哇”负责的是神圣区域,不容玷污,选举出来的僧侣“卡果哇”都是有经验的。
在藏区基层社会中,由僧侣们出面做的事情一般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结夏安居欢庆仪式里由僧侣“卡果哇”负责仪式供品的准备与摆放,这表示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与信仰是纯净而又至高无上的,僧侣“卡果哇”可以满足信众们精神上的追求,这是藏区基层社会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在藏区,僧侣“卡果哇”一般也协助当地行政组织协调治理基层社会。
(二) 负责仪式场所的“卡果哇”——社会空间治理的微观模型
2019 年9月1日,仪式举办场所已经在基层社会临时选举出来的各位“卡果哇”指挥引导下搭建完毕,饮料坚果糖果等小食已被摆放整齐;中午时分,仪式场所中有一部分男性正在做悬挂唐卡等最后的完善工作。据了解,在前期准备过程中,村子里的人们在负责仪式场所的“卡果哇”召集下过来帮忙。仪式场所里摆放的桌子、暖壶、地毯等物品,也都是向村子里的人借的。仪式场所空间上的协调分工与位置区划是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借鉴的微观模型。
你看这个区域(指着仪式场所),差不多十几列的桌子还有地毯,都是从村子里各大队借过来的,每一列都有对应的负责人“卡果哇”。每个“卡果哇”不是随意分配的,是有顺序的,比方说,我们在搭建这个棚子时,就分好了,这一块归一队负责,接下来是二队、三队和四队,那一队的区域就由来自一队的“卡果哇”负责,二队的区域就由来自二队的“卡果哇”负责。来自各队的“卡果哇”负责从各队的家庭里借来桌子和地毯,做上标记,等仪式结束后,再负责还回去(访谈对象:旦增,男,32岁,教师)。
(三) 后厨“卡果哇”——仪式有序进行的后勤保障
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正式开始的前一天,即9月4 日,各类蔬菜和奶制品及米面主食等所需食材已经在后厨“卡果哇”的安排统筹下准备完毕,等待仪式当日加工成熟供僧侣们食用。仪式当天大约需要准备1000人的饭食,此时后厨“卡果哇”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他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各种菜品:凉菜、包子、蕨麻米饭、面条和酸奶陆续出场,不断慰劳着为大家念经祈福的僧侣们。与大多数地区举办大型活动时的场景一样,村子里的女性是后厨的主力军。
负责后厨的“卡果哇”有两个,一个是男性,他负责食材的采购与所有菜品的制作流程。另一个是女性,主要是协调大家一起来帮忙。男人们都去前边(指仪式场所) 忙活了,我们就来干这些,大家干的活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洗菜、有的添柴,但大家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就是尽可能地照顾好僧侣们,这样大家都开心(访谈对象:措吉,女,45岁,家庭主妇)。
(四) 车辆“卡果哇”——推进仪式进程的重要环节
完德是笔者在本次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活动中结识并进行过深度访谈的一位“卡果哇”,他主要负责接送僧侣们的车辆安排事宜。对于他来说,参与筹备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活动是自己积德行善的具体表现,能够参与筹备活动,也是大家对自己的信任。
我是被推选出来的,我目前在县政府机关工作,可能是我工作性质的原因,大家信任我,觉得我能把这一块儿的事情负责好。我能来负责这个事儿,也是我的荣幸,能够为活佛为众僧侣做事,是求之不得的,我们都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把僧侣们照顾得好了,对大家都好(访谈对象:完德,男,45岁,公务员)。
僧侣们是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活动的主要参与人,为了确保周围寺院的僧侣们准时到达仪式举办场地,完德在仪式举行的前一个月就着手协调身边的车辆资源了,仪式当日往返于僧侣所在寺院与仪式场地的将近100辆小型汽车,大多是完德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协调沟通来的,车辆“卡果哇”完德趋近于完美的工作组织过程是推进仪式进程的重要环节,“卡果哇”的个人魅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 迎宾“卡果哇”——与外界社会互动交流的连接点
仪式前一天的下午,旦增家的亲戚朋友们带着酸奶和馍馍陆续前来。
村子里的生计方式是半农半牧,以前与纯牧区的牧民交往时,牧民会送来他们的牛羊肉和酸奶,村里人也会将自己做的馍馍送予对方以示谢意,这也是牧区和农区之间的食物互补,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双方的交往交流。后来由于现代化的影响,村子里养牛羊的人越来越少,酸奶对于村里人来说属于珍贵物品,一般只有在招待客人或者举行一些仪式活动时才会出现(访谈对象:旦增,男,32岁,教师)。
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们被迎宾“卡果哇”安排到另一个院落里,这个院落里准备的一切都和旦增家为僧侣们准备的东西一样,这表明了大家对亲戚朋友们的感谢与尊重:
他们都是从外边赶过来的,都是旦增家的亲戚朋友,我们不能怠慢了,大家都一样,我们去别人家做客时人家待我们也好,都是相互的,都热情(访谈对象:多杰,男,48岁,村民)。
迎宾“卡果哇”与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交流互动,是基层社会里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渠道之一,这也体现了结夏安居欢庆仪式的另一种功能,它不仅为不同寺院的僧侣们提供互动交往的机会,也为参与仪式的普通人提供了信息与物资交换的渠道,迎宾“卡果哇”在仪式结束后将获得的信息传递给村民们,开阔大家的视野,丰富人们的信息储存量,为居民们后续参与村民自治做铺垫。
结夏安居欢庆仪式的筹备工作强化了人们对村落的认同。承办方通过凭借个人关系延伸出的社会关系网络、亲属关系、社区成员关系等,动员人们参与到仪式筹备当中,使得村里人由日常中“分”的状态变为非日常中“合”的结果。
9 月6日是欢庆仪式结束后的第一天,承办家庭为村里人准备了答谢宴会,感谢大家多日以来的帮助。举办宴会是对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成功举办的总结性庆祝活动,传达的是一种福报降临全村的吉祥寓意。此次宴会不仅是针对全体村民的,也是针对村落空间的,从而象征着村落社会的整体性,直接影响到身份和归属的认同及凝聚力。
三、仪式“卡果哇”与基层社会治理
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三种社会关系的纵横交错,构成村落的社会体系。血缘关系是村落社会结构的基础,父系骨系的单向联系又是其核心,村落之间的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扩大和行政关系的界定;行政关系则带来村落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全方位联系。这3种关系形成与一般村落不同的3个层次的社会体系。在藏区基层社会,“卡果哇”成为联结3个层次社会的纽结点。
(一) 社会个体与集体的组织与运行
总的来说,以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家庭,以及带地缘性的邻里和村落体系是村落社会的基本框架。而村民小组—村委会—乡—县等行政体系,则构成一般地区村落社会的控制系统。而在同仁地区的藏族村落里,除了上述3种关系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即村民们遇到大型事件时的临时组织“卡果哇”,由他们负责大型事件的各项流程事宜。“卡果哇”作为村落社会里的非正式团体领导人,带领村民们协作互助,家庭作为社会个体由日常生活状态里的松散状态迅速凝结为团结合作的集体,在结夏安居欢庆仪式的筹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点:
正值秋收时节,隆务地区的各家庭都在忙于晾晒田里收割的粮食,而结夏安居欢庆仪式使他们放下手中的忙碌,纷纷前往承办仪式的家庭,在“卡果哇”的指挥下,各司其职。
此时,村落不再是一个由零散家庭构成的集体,在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期间,它变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个体,这个村落的一切事物都围绕结夏安居欢庆仪式而存在,村民们不在田间劳作,而是在仪式承办家庭帮忙做事情。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当地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村子,并且村子里所有人都信奉藏传佛教,而结夏安居又是佛教传统仪式,因此,结夏安居欢庆仪式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具有全民参与性的活动。
仪式当天早上7点,村子里的男人们就出发去接各寺院的僧侣,大约8点,村子里所有在家的女人和孩子,手捧鲜花,站在道路一侧,虔诚地等待着活佛和众僧侣的到来,在他们心中,这是神圣的一天,活佛及众僧侣将会吃上她们精心准备的饭食,并为他们念经祈福。
不仅仅是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村子里其他的重大活动、宗教仪式或遇到婚丧嫁娶等大型事件,也都是全民参与的。这体现出了村落社会组织运行里的分与合:即日常生活事件中常态的分与非日常生活事件里的合。分是指日常生活中村子里的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进行生产生活,合则指在非日常的生活状态里,如举办大型活动与仪式时,所有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做好同一件事而付出努力。
对于村民们来说,分是常态,大家之间虽有日常互动,但实际交集是不多的,而在非常态的合时,村落里的人们体现出一种独具魅力的状态,结夏安居欢庆仪式里的礼物流动也能表现出这一特征:
仪式当天早上,天刚微亮,僧侣们还未到达承办结夏安居欢庆仪式的家庭中,村子里的女人们就陆陆续续端着刚做好的热馍馍过来了,主人家热情地接受她们的馈赠,并把馍馍放到僧侣们用餐的桌子上,然后回赠她们水果。
文化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3]“仪式的直接目的显然存在于参与者意识之中,但同时也掺入了一系列复杂的宇宙观念,正是这些观念使仪式具有某些意义。”[4]“仪式的象征意义实际上是通过仪式中所涉及的民俗物和仪式本身所进行的行为来实现的。”[5]任何宗教仪式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具等都具有其可探究的象征意义,其所有的象征意义在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
就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本身而言,在这个“佛欢喜日”,举办这个欢庆仪式是一种具有福报的表征。为了获得这份福报,全村人自愿参与,于承办方而言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于村子里的人而言他们有此机会来亲自参与到仪式当中是一种福报的积累。
(二) 权力文化网络与基层社会治理
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是藏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卡果哇”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尽管“卡果哇”的治理实践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能通过其所具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关系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
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运行依赖于文化、知识与伦理的支撑,文化网络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载体。杜赞奇曾通过对华北乡村的实证分析,从底层文化的视角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在其表述中,“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解释乡村社会中国家、士绅以及民众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范式[6]。传统社会里,如秦汉时地方沿袭乡里自治制度:百家为一里,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啬夫、游徼。三老管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其权尤重;游徼管治安,均由当地推举名望之士充任[7]。即秦汉时期基层治理的表征为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中的公共事务处理主要由三老、啬夫、游徼等负责,三老主要承担民风教化的事务,啬夫负责民事纠纷调解和向民众征收赋税,游徼则主要承担社会治安工作,打击盗窃行为。他们构成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人员构成上,一般由乡村社会中掌握文化习俗、熟悉人情、恪守规矩的人员来担任。
权力文化网络编织的关键基础在于共同的文化背景。藏区“卡果哇”的产生扎根于当地基层社会,与民众具有共同的文化与习俗,“卡果哇”与民众生活在同一地方知识圈,这一点恰似费孝通所言的“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为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及运行提供了土壤。在国家正式的规则之外,藏区基层社会中的非正式规则或文化是“卡果哇”治理的工具。
藏区基层社会里的“卡果哇”一般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考虑的缘由就在于其权力与“卡果哇”权威之间的契合,地方性知识的供给为“卡果哇”正式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辩护,增强“卡果哇”地位、行为以及话语的合法性。在地方文化网络中,“卡果哇”的权力并非直接来源于上级权力的授予,也不是天然获取,而是在地方性意义、象征、认同、价值等要素的共同编织之中产生的,本土性知识是“卡果哇”权威建构的重要来源。
(三) 传统组织与藏区社会治理
现代治理理念要求传统文化的社会性参与,“卡果哇”作为藏区传统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不仅是以组织形式成为集体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其在基层社会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的功能,以及所具有的文化资源对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有柔性秩序建构的力量。“卡果哇”在藏区基层社会里,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层社会精英一样是地域社会历史记忆与习惯延续的一种结构性文化,这也是地域社会实现整体性治理所具有的有效文化资源。
民族文化具有社会秩序规范功能,人们可以从民族文化中获取参与感和认同感[8]。“卡果哇”作为藏区现代社会治理目标与地域历史文化内在契合的连接点,将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组织囊括在藏区现代治理之中,显然具有广义治理内涵的考量与关注,能使治理从形式到内容都涵盖现代社会实现多元治理的张力。发扬民主,充分征求各种意见,并立足藏区社会实际,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强“卡果哇”等传统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能为藏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理想的社会治理形态是政府与基层社会对地方事务的合作共治,也是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最佳协调状态。对于藏区而言实现理想社会治理形态这一目标,必然需要政府与基层民众在协商合作的前提下共同治理,作为传统社会组织的“卡果哇”就在实现发挥文化功能且服务于社会治理的这一目标。
传统空间社会在重大事件或活动期间,“卡果哇”将一个个家庭个体凝聚成社会整合形式。它的形成既有人们对传统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的惯性延续,同时这一社群凝聚力的牵引又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邻里间互惠、互利、互助的一致性、安全性需求的体现。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理性及传统文化因子让“卡果哇”这一藏区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彰显有效性。
四、余论
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在学术研究上的成熟和在实践中的探索,已经成为国家及基层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路径。“卡果哇”在藏区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其独特的社会功能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文化资源。社会治理是一个必须符合自身发展诉求的具有前后承接关系的、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动态调整过程。显然,与正式的国家法律制度相比,“卡果哇”自身的魅力及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在藏区基层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公务处理上提供了低成本的治理工具。文章的落脚点是从宗教仪式活动里的“卡果哇”体察传统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和意义。
承办结夏安居欢庆仪式活动的整个村子,通过“卡果哇”的召集而迅速组织起来进行有序的分工与合作。原本为“个体”的家庭因社会共同利益而变成“集体”,体现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关系的重组,具体表现为临时集体化,即大家因为这件事情短暂的聚合在一起,彼此之间呈现出一种“合”的状态,大家发挥群体协助的力量,体现出异于常态的凝聚力,说明民间组织在现代藏区基层社会里仍具有较高的统筹治理作用;在仪式结束后,又迅速分解为独立的各个家庭,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奋斗,并为下一次集体化活动贡献出更多的力量做准备。在日常与非日常中切换,呈现出一种有规律的“分”与“合”,村落社会组织也因此而有序循环往复地运行。
目前,藏区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村、支两委有合法性,合作社有资金资源、“卡果哇”有组织优势,搭建多元参与、合作共管的藏区基层治理模式,这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现实议题。植根传统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新时期政治更加清明、体制更加完善,传统组织不再是基层社会发展的障碍,它应是连接基层社区意志的制度资源,是基层社会秩序建构的现实基础。社会治理要借助教化的手段,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政治与手段,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构建社会信任,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功能。对于藏区基层社会而言,“卡果哇”的存在是传统基础上不断积淀至今的结果,尊重传统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卡果哇”作为村民自治基础上的传统组织形式,满足了当下藏区社会发展中乡民要求获得更多自主权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