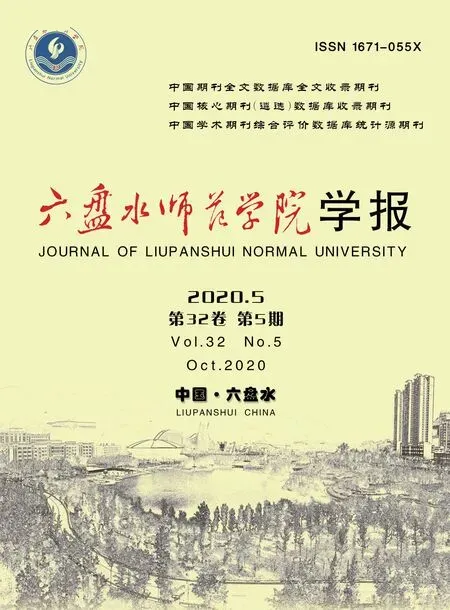《天堂》对现实世界“乌托邦”之困境的展现和反思
金立
(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黄山245021)
“乌托邦”作为“理想国”的代名词,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乌有之乡”,即“不存在的地方”,等同于“在别处”[1]17。在中西方文本对于“乌托邦”的想象中,大多数作者也都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强化“乌托邦”在“别处”的背景,并且竭力把“别处”塑造成一个几乎完全闭合的“虚幻空间”。它与“此处”所代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无比玄妙,带着“天机不可泄露”的色彩。不过一个例外是,美国作家莫里森在其小说《天堂》中则致力描述了两个居于“此处”现实世界中的“乌托邦”——鲁比镇和它附近的修道院。鲁比镇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纵深处,是美国黑奴的后代为了摆脱白人种族迫害建立的“纯黑人”的“乌托邦”。鲁比镇几公里之外的修道院则是不堪生活折磨为了逃离人生困境的女人们创建的庇护所,是一个“纯女性”的“乌托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莫里森在《天堂》里如此选择的寓意,我们先要探明为何大多数作者更偏好最大限度地强化“乌托邦”在“别处”的虚幻设定。
一、总是居于“别处”的虚幻“乌托邦”
中国东晋末期的文学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世界[2]166。我们细细研读不难发现,无论是“理想世界”中的居住者,还是“理想世界”本身,“在别处”的虚幻色彩都被一再地强化。首先,被作者设定生活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并不是普通的世人,而是“在德行上提升了的世人”,是“贤者的群居”[3]160。因为“非贤者”是没有能力创建和维系一个没有战乱和纷争,没有掳掠和欺诈,也没有饥荒和人祸的理想社会。但是这些贤者不可能生而为贤者,那么他们是如何从“此处”的普通人变成“别处”的贤者的呢?“现实世界”中的当世之人也有可能成为这样的贤者吗?作者陶渊明也无法回答这些疑问,所以《桃花源记》中创建桃源的贤者并没有设定为从“此处”的当世而来,而是设定为“为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的秦人,这样一来,作为贤者的“秦人”便与居于“此处”现实世界的当世之人在时间轴上拉开了漫长的距离,他们是在“别处”的。而随着时间距离的延展,读者心中关于“何以成为贤者”的疑问因缺乏对时间轴另一端的那个时代的真实体验而变得无从考究。而“桃花源”的地理位置更是在“别处”的,它几乎与外界完全隔断,并没有一条真实可得的路径能让“此处”的世人进入桃源,渔人的闯入也纯属“偶得”[3]157,而何时何地可以再次“偶得”则是一个谜,这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于居于“此处”的普通世人的德行是不信任的,《桃花源记》中关于违背诺言的渔人的描述也证明了这一点。渔人似乎从未把自己对于“不足为外人道”的承诺当回事,他一出桃源便“处处志之”,一到郡城,便“诣大守,说如此”[2]166。因此,作者断定桃源一旦暴露于如此德行的普通世人面前必将毁灭于无形,而在文本的结尾部分,从“此处”的现实世界出发去寻访在“别处”的桃源的人要么被设定为“不复得路”,要么被设定为“寻病终”,更是作者为了解除“此处”现实世界对于“别处”的威胁而把“别处”从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强化成了一个“禁地”[2]167。
香格里拉王国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中描写的“理想世界”,它双重“在别处”的带有虚幻色彩的设定显然也被强化了。首先,香格里拉王国实在是一个太完美的乌托邦了,其完美体现在来自不同国家以及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在香格里拉始终能团结友爱、和平共处,而这种和平安宁在作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作者希尔顿创作该作品时正值一战时期,当时西方强权们试图相互吞灭。信仰的不同,宗教的不同,种族的不同,政见的不同,任何一种差异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纷争。毫无疑问,在香格里拉王国,能长久地维系和平安宁的局面的管理者必定是贤者,因为当世之人还未找到建立完美世界的方法,他们依然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饱受折磨。所以,文本中作为香格里拉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的贤者被设定为从遥远的过去而来。他250多年前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香格里拉,100多年前成为喇嘛寺的最高喇嘛并开始理政。也就是说,作为香格里拉王国灵魂人物的贤者就时间轴而言是在“别处”的,和当世之人相隔遥远,这是文本中第一重被强化的“在别处”。而作为香格里拉王国的统治中心的喇嘛寺所在的地理位置构成了被强化的第二重“在别处”。喇嘛寺位于中国藏区蓝月山谷前端28 000米的卡拉卡尔雪山之上的一片林海中,这显然是普通世人难以企及的地域。同时,蓝月山谷在藏区的具体位置也是模糊的,康维一行人得以进入山谷同样是因为“和个人努力及品格无关”的偶然,他们所乘的飞机是在被劫持后因故障被迫降落在蓝月山谷附近的。这一切都表明作者希尔顿深深地担忧“此处”所代表的“现实世界”与“别处”的“理想世界”之间是二元对立不可兼容的。更糟糕的是,作者也无力打破和改变这一切。文本中的主人公康维曾被最高喇嘛选为继承人,但最终康维还是离开了香格里拉。表面上他如此选择是因为在同伴马里逊的劝说下没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是作者希尔顿对于如何成功地去治理理想世界仍然不明了。关于最高喇嘛的治世之道,在文本中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康维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并未如愿。通过康维和最高喇嘛的交谈我们了解到,最高喇嘛试图用东方的中庸哲学来平衡西方文明中追求极致的观念,从而最终形成“一种松散而富有灵活性的统治”[4]322。同时最高喇嘛一再提及“适度”一词:“我们的人民适度地节衣缩食,适度地忠诚老实”“我们总是适度地行动。”[4]289但是中庸哲学在实际运用中,究竟到什么程度可以被定义为“适度”呢?作者通过主人公康维最后找到的也是一个极其模糊的答案,那就是,这种“适度”看起来像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应付”[4]330。文本的结尾部分,位于“别处”的香格里拉王国的满族姑娘罗珍在跟随康维他们一起进入“此处”的现实世界后,她就失去了原本永葆青春的容颜,日渐苍老,再次展现了作者对于无法使“此处”和“别处”兼容的无力感。既然无法使两者兼容,那么“乌托邦”也只能永远地停留在“别处”了。
其实,包括陶渊明和希尔顿在内的大多数中西方作者对于自己笔下所描述的“乌托邦”都是非常珍视的。他们在作品中都竭尽所能守护心目中的“乌托邦”,极力杜绝“乌托邦”所在的“别处”和“现实世界”所在的“此处”可能存在的任何交集。因为他们都极其担心笔下的“乌托邦”一旦进入现实世界,就会遭遇困境而毁灭,那将是他们难以承受的结局。
二、《天堂》对于现实世界“乌托邦”困境的展现
与大多数中西方作者乐于描写在“别处”的虚幻乌托邦不同,莫里森的《天堂》恰恰就描述了两个居于“此处”现实世界的乌托邦——鲁比镇和它附近的修道院,一个“纯黑人”的“乌托邦”和一个“纯女性”的“乌托邦”。《天堂》在故事的第一幕就展示了现实世界里两个乌托邦的破碎和毁灭,九个鲁比镇的男人袭击修道院,射杀了五个女人,场景血腥骇人。这一幕把大多数中西方作者对于现实世界里“乌托邦”结局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但莫里森的创作意图并不是为了印证人们对于“此处”现实世界里“乌托邦”结局的设想,而是希望通过引领人们直面在现实世界里普通世人建立的“乌托邦”的种种困境乃至毁灭的历程,来探索如何把根本不存在的“别处”的虚幻乌托邦转变成“现代人类行动可以企及的一部分”[5]167。这比以往大多数中西方作者更侧重于从打造虚幻乌托邦的瑰丽幻境中获得精神慰藉的创作意图更具现实意义。那么现实世界的“乌托邦”究竟会面临何种困境呢?
困境之一,居于“此处”的现实“乌托邦”的创建者们作为普通世人,不可能坐拥最高等级的智慧,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需要验证的。我们不难发现,“别处”的虚幻“乌托邦”的创建者们总是被设定为拥有远超常人的智慧,在认知和判断上也总是绝对的正确,周身笼罩着“贤者”的光环。关于他们的创建“乌托邦”之路从未有过历尽坎坷的描述。可是,居于“此处”的现实“乌托邦”的创建者们都是普通的世人。不论是创建鲁比镇的黑奴的后代,还是来修道院建立庇护所的女人们,他们在能力和认知上都完全无法与“别处”创建虚幻乌托邦的“贤者”相媲美。所以他们的现实“乌托邦”创建之路和真实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必然会经历“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进”,总是在肯定、验证、否定、推翻、肯定中向前发展[6]167。比如,鲁比镇的创建者们就正在经历着验证后的被否定。其一,在这个新建的黑人的乌托邦乐园里,他们依然坚持“唯血统论”,只不过这一次是像“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那样的黑肤色才是最纯正高贵的血统,白人甚至浅肤色的黑人都处于该血统论鄙视链的最底层。为了维系并巩固新的血统论,他们带领镇子里的居民一起歧视并压迫外来的浅肤色黑人,使浅肤色黑人遭受巨大精神创伤甚至被迫逃离。同时他们执意要将“深肤色黑人至上”的血统论贯彻到底,导致小镇居民通婚的范围越来越小同时畸形儿不断出生。其二,鲁比镇的创建者们建立的是一个夫权至上的乌托邦,在“男权中心思想”的主宰下,小镇的男性以“控制”的方式来表达对女性的爱和保护。而小镇的女性没有感知到来自他们的爱,反而因为个人情感和自我意识被阉割觉得窒息和痛苦。鲁比镇的男性也同样被不融洽的两性关系所困扰。然而,即使鲁比镇的创建者们的所作所为经过验证后被否定,作为居于“此处”的普通世人,他们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累积足够的智慧控制自己由于歧视而产生的愤怒,从而修正所有的非理性举措。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迅速构建起“和谐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这样的认知。这也是居于“此处”的“乌托邦”几乎无法避免的困境。同样,在修道院建立乌托邦的女人们也要面对验证后的被否定。女人们在修道院之外曾饱受暴力和情感伤害,所以她们以修道院为围城把所有可能的伤害都隔离在外,包括曾伤害她们的男性们。她们最终创建了一个男性缺失的“单一性别”乌托邦。从表面上看,摈弃了男性的乌托邦是一个真正的乐园,女人们在这里互诉伤痛和苦难经历,在情感共鸣中获得慰藉和力量。然而,作为居于“此处”的普通世人,女人们有血有肉,对异性之爱的渴望是她们无法否认和超越的合理的自然欲望。以修道院的康妮为例,她在过了三十年无比虔诚的禁欲生活后,遇到了迪克,小说中写道,“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6]513。迪克唤醒了康妮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渴望,所以即便知道迪克是有妇之夫,康妮依然神魂颠倒地任由自己的爱和欲望突破道德的边界。欲望并不会在修道院的围墙内消失。虽然福柯认为完全不压抑人的欲望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以剔除人的合理欲望为代价建立起的乌托邦在被验证后显然也不能归为理想世界[7]87。
困境之二,居于“此处”的现实“乌托邦”与其外部世界处于同一空间,不可能完全隔绝外部世界对它的影响以及彼此的关联,换言之,现实世界的“乌托邦”不可能彻底摆脱其外部世界而自行运转。即使鲁比镇和修道院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纵深处,已极其荒僻,但它们依然不是完全闭合的空间,依然无法全然断绝来自外部世界的渗透。在黑人乌托邦鲁比镇,年轻人没有体味过先辈被白人种族主义迫害时的苦楚,无法理解先辈的伤痛,他们开始不加甄别地效仿着他们所向往的外部世界,他们酗酒、斗殴、未婚同居,离开小镇的年轻人也不再愿意回来。而危机不仅仅来源于无法阻挡的外部渗透。由于背负内心伤痛的鲁比镇老一辈始终引领小镇故步自封,鲁比镇还面临着日趋落后于时代步伐的困境。在内外交困之下,内心风雨飘摇的鲁比镇的老一辈如溺水之人急需抓住救命稻草般地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袭击修道院来力挽狂澜。当然,袭击修道院并不能避免鲁比镇衰败的命运。赞成此举的领头人也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另有打算:莎君特是一直觊觎修道院的土地,波尔是因为兄弟姐妹们不再受他控制而希望借此重新找回掌控的感觉,弗利特是因为家中畸形儿的接连降生而要寻找一个愤怒的发泄口,领导小镇的摩根一家则是要为小镇的失控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在《天堂》里,莫里森对于促成此举的原因的层层剖析再一次揭示了居于“此处”的普通世人所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及人性之恶。与此同时,作为“纯女性”乌托邦的修道院几乎无法避免这种无妄之灾。因为修道院是居于“此处”现实世界的,这意味着它和其外部的世界同属一个空间。即便它努力地隔绝着空间里的其他部分,也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同一空间里的每一部分和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休戚相关的。无论是否愿意,他们都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于生活在父权统治下失去话语权的鲁比镇的女性来说,修道院女人们不依赖男人的独立生活方式打开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可是,在鲁比镇的男人眼中,修道院的女人们简直是离经叛道、违背传统,为鲁比镇的女人做了极坏的表率,所以即使毁灭她们不能挽救日渐衰败的鲁比镇,也必须这样做。终于,毁灭的这一天来临了。九个鲁比镇的男人在一个清晨袭击了修道院,五个女人被射杀。至此,居于“此处”的两个乌托邦都陨落了。
三、《天堂》对于现实世界“乌托邦”困境的反思
“逃避于一隅”是被黑暗、不公、歧视、恶毒伤害的人们在第一时间下意识地会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当遭遇白人种族歧视迫害时,美国的黑奴后代选择逃避到俄克拉荷马州的纵深处,建立“纯黑人”的“乌托邦”鲁比镇;当在“男权中心社会”遭遇压迫和情感伤害时,女人们选择逃避到废弃的修道院,建立一个“纯女性”的“乌托邦”。但是,在他们都选择“避于一隅”建立乌托邦后,光明、公正、平等、善良并未如期而至。相反,这两个乌托邦先后陷入困境并陨落了。莫里森在《天堂》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黑人“乌托邦”鲁比镇的陨落与“我族中心主义”。在鲁比镇的外部世界,当时“白人中心主义”盛行。具有更强大经济、政治实力的白人中心主义者们在社会等级的划分中,将本族群的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置于等级的最高层,而视相对落后的黑人群体为劣等族群并加以排斥。白人成了不公正的种族次序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鲁比镇的黑人们坚信白人以不公正的方式创建的这个世界对于白人自己来说已然是一个理想世界,并且只要他们复刻白人世界的统治制度和思想,反过来就能建立一模一样的黑人的理想世界。然而事实的走向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推行“黑人中心主义”的乌托邦鲁比镇最终在重重危机中陨落了,他们并没有获得期许已久的宁静和幸福。莫里森认为鲁比镇陨落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我族中心主义”,它表现为:某个族群将本族群的核心价值和本土传统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要求其他族群进行复刻,试图以一种“同质化”[8]6的方式将其他族群转变为自己的复制品,完全无视其他族群的自尊和文化价值。“我族中心主义”有两个危害:首先,任何一个“唯我独尊”的族群都无法借鉴其他族群的优势实现取长补短,而与其他族群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从而共谋发展就更无从谈起。其次,其他族群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一旦被推行“我族中心主义”的族群压榨为零,族群之间的仇恨、冲突乃至战争都会一触即发,难免会两败俱伤,共同消亡。正如布里格斯在混沌理论中所讲,“从混沌理论的角度看,注意系统间如何彼此竞争,不如关注系统间如何彼此依赖、相互关联更为重要”“在一个系统中,若削减多样性,使其更均匀同质,那么该系统将会变得更加脆弱,容易导致非线性的崩溃”[9]65。简而言之,推行“黑人中心主义”的乌托邦鲁比镇与所有推行“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互成镜像。鲁比镇的陨落就是一个镜像式的预言,警示着所有“我族中心主义”者反思自我。
反思之二,女性“乌托邦”修道院的陨落与群体中的人性之恶以及“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的出路。鲁比镇这样的纯黑人“乌托邦”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但是把修道院作为另一个乌托邦与鲁比镇并置一处是莫里森颇有寓意的设计,以期触发更多角度的反思。其一,毁灭修道院是鲁比镇的人们在自身危机困扰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其折射出的群体中理性丧失和人性之恶在失去约束时的极速放大令人心悸。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10]78。通过修道院遭遇无妄之灾被毁的结局,莫里森试图引发人们对群体中人性之恶的反思,同时提醒世人不要在群体中纵容自己成为恶行的追随者。其二,修道院——为逃离男人伤害而建立的“单一性别”乌托邦——却最终毁于男人之手。显然,逃避并不能使女性真正摆脱困境,走向新生。女性要在“男权中心”社会实现真正的解放,势必要踏上一条更艰难的直面困境、奋起抗争的道路。她们不仅要避免被男性主体意识同化,还要唤醒自我意识并重新构建自我,同时在此基础上争取实现自我并提高自我,最终反向影响男性的观念,才能够推动两性关系切实有效的变革。莫里森不断为被压迫的少数族裔及女性群体发声直至获得诺贝尔奖的创作之路正是对女性奋起抗争的最好注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结语
大多数中西方“乌托邦”文本的作者为了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不惜将它们永远留在虚幻中。不同于这些理想主义者,莫里森在《天堂》中反向而行,用倒叙的手法从现实世界乌托邦毁灭的悲剧结局开始,花大量笔墨引导读者在文本中自发搜寻线索以探求乌托邦在现实中陨落的原因。在寻求实现“乌托邦”的道路上,莫里森是一个意志坚定、勇于在绝境中发现希望并吸取教训的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作为非裔美国作家,她努力超越民族和自我的局限,对于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始终如一,“对社会的真实敢于正视”[11]55。她始终希望能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她是用笔来战斗的真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