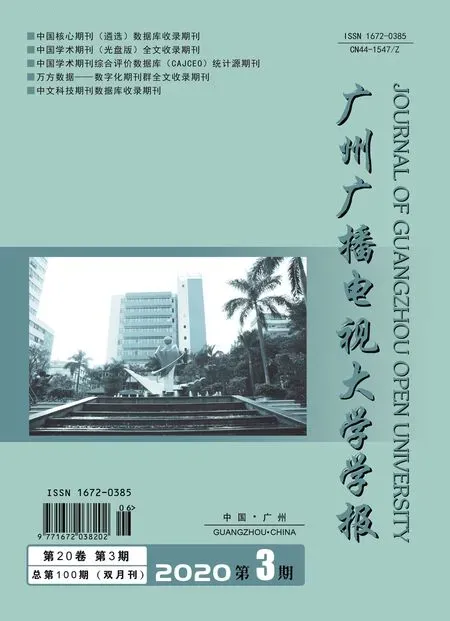竹林风范中的人格魅力*
彭 姣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随着曹植这一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后一位作家的逝去,以何晏和阮籍为代表的新的文学阶段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文人志士受正始玄风的深刻影响自然也反映到他们各自的文学、生活以及人生理想中。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中有:“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1]很明显,刘勰也有注意到这一时期老庄思想所占的重要地位。“竹林七贤”也因此崇尚老庄、蔑视礼法,呈现出放达之态。此外,政局的影响也是促使其风范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此时,曹氏与司马氏之间正在进行权力争夺,政局动荡,这般局势始终贯穿于这一时期。“正史九年(248)司马懿发动兵变杀曹爽,著名士人何晏等人并受诛戮,‘天下名士去其半’”。[2]司马氏为了巩固新政权,对待异己进行大肆铲除,为了统一舆论,文人自然也成为其重点整治的对象。自此,朝野上下、文人志士无不惶恐,人人自危,不敢乱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龄、生活背景各异的“竹林七贤”走在了一起,加之当时盛行的玄学之风,他们七人便寄情山水、托怀诗酒,于竹林间欢会畅饮,成放达洒脱之态,促成一时代之独特精神风尚。
一、放达中的独立人格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它从那个产生了慷慨悲凉不朽诗歌的建安开始。这开始就弥漫在战火、饥荒和疫疠之中。”[3]其时如走马灯般更迭的政权给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身处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漩涡中,竹林名士如同一芥浮萍,在宦海沉浮中寻求生存便成为他们一生都为之努力的目标。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其自然追求一种自由独立的崇高人格,他们对于儒家教士的虚伪更是深恶痛绝,常“以极端的方式来破坏和摧毁礼法,并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追求人性的自由”。[4]面对司马氏一行的残暴统治,他们敢怒不敢言,内心挣扎苦闷却又寻不得解脱。于是,几位文人纷纷走向了酗酒傲狂、放笑山林的道路,视为对各类礼法名教的蔑视与抗衡,形成任诞放达、率性自然之独立人格。
阮籍,七人之中翘楚,他狂放、简傲,对司马氏集团心存不满,却又缺乏向残酷政权提出反抗的勇气。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指出:“他对于东平及亢父民风的评价,显然带有借题发挥、兼及世俗的痕迹,把一肚皮对于世俗的不满与牢骚,借写东平与亢父发泄出来。”[5]可见,阮籍对礼法之士的厌恶与不满昭然若揭,何曾对他的诋毁,钟会的寻衅,都让他苦闷不堪。正如他在《咏怀诗》第三十三首中写道“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6]这便是他一生苦闷不得志的真实写照。为此,他只得以酗酒作掩,作出一些不符合礼法名教的行为,希望以这种方式摆脱当前政治困境。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对阮籍的特立独行进行过刻画,他数次借醉酒躲避司马氏集团的笼络。他之所以愿意担任步兵校尉,仅仅是因为在步兵营酒窖中存有的那三百斛美酒。他高唱“礼岂为我辈设也?”,[7]于是在他大醉时可以躺在邻居妻子身边,可以为一个未婚逝去的少女嚎啕大哭,也可以在为母亲服丧期间饮酒纵情,甚至敢在有司马氏人存在的宴会上发出“杀父乃可,至杀母乎!”的惊世言论。[8]在《猕猴赋》中,阮籍对礼法之士更是憎恨至极。除以醉酒避乱外,阮籍还擅青白眼,“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9]以青白眼示人也是阮籍不拘礼俗、任诞放达的表现。
相比阮籍,嵇康则是一个彻底的礼法反抗者。他主张回归自然,厌恶繁琐礼教,是为离经叛道的典型。他曾试图通过探索道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这一途径,为处于困境中的名教思想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10]也因此在《声无哀乐论》中写道“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11]他认为情为人性本然,顺应通至物情便是自然,名教自然成为“逆物情”的一类存在。嵇康性格刚烈,为人正直不阿。隐士孙登也曾喟叹:“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2]嵇康在与钟会的交往以及拒绝山涛的推举中将这样的性格体现得更为鲜明。一次,钟会(司马昭心腹)虚情假意拜访嵇康,嵇康只一心打铁,对其不闻不问,临走时嵇康问:“你听见了些什么而来的?你又看见了些什么又离开?”,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3]话语之间,针锋相对之意显而易见,此后两人便结下怨愁。再者,当山涛推荐其担任曹郎一职时,嵇康大为愤恨,夜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14]自说不能忍受宗教礼法的管束且不尊崇周孔孟程,最后更是与山涛断绝往来。清代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论及此,指出嵇康以拒山涛为由头,实则是在讽刺打着虚伪名教旗号的司马氏集团,“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 因此就非死不可了。”[15]正因为如此,嵇康得罪了司马昭后招来杀生之祸。在狱中,未曾料想自己会命丧于此的嵇康仍作《忧愤诗》为自身鸣不平,并在诗尾写道“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16]表示自己一旦离开困境便会归隐山林,体现出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内心对于生命、对于自由的留恋与渴望。
“七贤”中其外的几人的独特事迹史料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刘伶脱衣于房屋中行走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身处魏晋之际,除却政局影响以外,“通达”的用人制度也是形成其独立特行个性的又一重要原因。两汉的察举与征辟制到后来逐渐变成封建帝国的枷锁,[17]在此用人受阻的情况下,曹魏集团一改此前用人之法,秉行“唯才是举”的原则。[18]用人思想的改变在一众士人间引起轩然大波。“传统上儒家用人的那一套已需要有所变化。”[19]用人思想的改变直接冲击了各文人志士的言行,他们纠旋于儒家与曹魏这两种用人制度中,于是作出一系列与传统礼教不符的言行。此外,自东汉后期始兴起人伦识鉴活动,人们纷纷以修“异行”博取世人关注,因此,“竹林七贤”为规避祸害所体现出的任诞放达的独立人格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二、清雅中的脱俗人格
以曹植为首的魏晋名士开启了晋代“任诞放达”之风,其《赠丁翼诗》 “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20]指出君子胸怀广阔,不为世俗小节所拘束,通达大道,不愿做这人间俗儒。“七贤”否定虚伪的名教礼法,心怀一颗清雅脱俗的超功利之心亦在情理之中。经历过汉末的残酷战乱使得像“七贤”这样的魏晋士人们将注意力纷纷转至生死,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更倾向于探寻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世界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有了这种意识,士人们的自我意识方得以合理存在。在“七贤”看来,追逐现世的欲望必然会成为虚伪礼法名教的帮凶,并且乱世之中这条通往欲望的道路荆棘丛生。也因此,追求老庄思想中的自由、清雅脱俗、逍遥游仙成为当时饱受迫害士人的普遍心理。
“七贤”的创作中体现出“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之态,[21]即将老庄哲学、人格追求与文学创作相结合。阮籍的一首《咏怀诗》便是魏晋更迭之际的时代悲歌,他反观庄子的逍遥世界,描绘出一处超凡于世俗的桃源景象。《咏怀诗》第二十三首这样写道:
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
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噏成露霜。
沐浴丹渊中,照耀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22]
此诗将道冥合一的逍遥境界跃然于笔端,此处的“射山”“汾水”“兰房”“丹渊”等意象体现出阮籍笑傲山水、闲游林泉的人生态度,“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流露出他访仙人之足迹,欲如庄子一样逍遥于物外,不再与俗世凡尘相牵连,充分展现了其放达的情怀。再看其第八十一首: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
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
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23]
诗人深知人生苦短、世事险恶,于是通过虚幻的描写刻画出诗人心中遗世长存的仙人境界,想以此摆脱现世困扰。但求仙无缘,人生却有限,于是以“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获得心理上的抚慰。正如庄子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4]于山野林泉避世远祸皆为同一时期文人所盼之事。阮籍亦不例外,这首诗便是诗人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是文学创作与老庄哲理的完美融合。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阮籍的游仙诗与前人的游仙诗存在不同,他的诗歌具有深沉、冷峻特点的同时又伴有丝丝感慨淋漓的味道在里面,与前人诗歌喜欢铺陈渲染仙界的审美特征不相符合。如其第三十二首: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貌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25]
“朝阳”“晨露”等意象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这些意象均有体现人生短暂、稍纵即逝之意。阮籍用之于诗中无不慨叹人生如梦、转瞬即逝。“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看似对逝去光阴的无所谓,实则隐藏的恰恰是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有限生命的极度留恋。此种心境下,便生发出与赤松子同游的念想。阮籍的游仙诗无不带有一丝悲情,同时他也是矛盾的,他吟唱“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26]又慨叹“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27]这也是现世的他与游仙矛盾的真实写照。其实,阮籍的逍遥游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尘世难以居处,世俗的压抑令他悲痛不已,唯有在精神世界寻得平衡之法,托玄思于游仙便成为不错的解决途径。这样的情况在他的赋作里也常常出现,如在《清思赋》中他幻想了一位至纯至美的佳人,诗人自己也知这样的美人不存在,便在文章最后选择放弃。
反观“七贤”中的嵇康,他主张的逍遥境界就变得更加从容、了无牵挂,在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又多了份人间的情趣。如《游仙诗》: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
愿想遊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
飘颻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
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
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別,谁能观其踪?[28]
同样,在《酒会诗》中也有对人生情趣的表达: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
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29]
这些诗作体现诗人不受世俗所约束,闲适、任情,获得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刘伶也不例外,他在《酒德颂》中也有向往老庄的逍遥理想: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30]
文章里的“大人先生”以“天地”为门,以“月亮”为窗,放旷不羁,气势恢宏,与阮籍的“佳人”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均体现出老庄式逍遥自在的人生理想。
总的来说,“竹林七贤”的逍遥游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仙,只是在无力改变现实的境遇下对自我内心的一种尊重。当时大多数士人与他们一样无法违背内心随波逐流,势必追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他们清雅脱俗,不滞于物,醉于逍遥畅快的神仙世界,这样的方式对于快节奏的现代人来说也有可兹借鉴之处。
三、隐逸中的清淡人格
魏晋士人们素有林薮之好,“七贤”也不例外。他们时常放酒山林,吟咏山川风月,于自然山水间肆意酣畅、抚琴赋诗,于清淡隐逸中寄托胸怀。
阮籍在其《咏怀诗》第六首表现出乐于退隐田园的思想: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31]
“东陵瓜”这一典故源自《史记·萧相国世家》,讲的是邵平官至东陵侯以后甘愿沦为一介布衣,并以种瓜为生的有趣故事。诗人借此表达他对平凡农人生活的向往之情。阮籍晚年学道,产生退隐避世的想法,当他不再对现实生活报以希望的时候,便很自然地走向隐逸之路。同样的心境还体现在《咏怀诗》第三十二首: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32]
诗中诗人自觉沧海桑田,慨叹世事变化无常,面对广阔天地,凡尘世俗不过是沧海一粟。诗人借“孔圣”和“齐景”两个典故慨叹时光一去不复返,曹魏皇室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如此,诗人企望登上太行山与赤松子遨游,即使不能,也要像楚国的渔父一样乘流水、驾轻舟归往隐居。再看《咏怀诗》第三十四首中,诗人云: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
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
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33]
一句“愿耕东皋阳”道出诗人内心所求。但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诗人是矛盾的。此时的诗人内心饱受折磨、精神萎靡,面对当前窘境,只得借酒消愁。面对酒又不自觉回忆起昔日一起饮酒作乐的好友嵇康和吕安二人,两人均成为司马氏的刀下亡魂。以酒消愁徒增伤悲,无可奈何的阮籍自然渴求归隐于东皋田园。即便如此,阮籍还是会有愁苦,可是,又有谁能陪伴自己过这般守真的生活呢?最后,正如他在诗歌末尾所说那样,就像龙蛇一样蛰伏起来躲避乱世祸害吧。阮籍有理想和追求,有时他羡慕归隐的生活,有时又不忍心真正远离世俗,因此他的一生都在苦苦思索。
此外,向秀、嵇康等人更是以实际行动主张归返自然、隐逸求乐。向秀与吕安一道居住于山阳地方灌溉田园,过着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闲逸生活。恰巧嵇康也住于此,他们三人一边躬耕田地、种植作物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一边利用空余时间携手出游、品味自然山水之趣,逃脱黑暗的政治樊笼,寻求精神上的满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魏晋时期政治高压使得文人志士朝不保夕、感时伤怀,崇尚自然、向往隐逸的清淡思想便成为士人们在浮萍乱世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善于清淡的士族文人也成为当时世人崇拜的偶像,清淡隐逸之风一时间盛行开来。在这样的境遇下,“竹林七贤”对林薮生活的热衷追求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四、“七贤”对世人之影响
竹林名士作为魏晋时期备受关注的文学群体,其影响自然不可估量。《世说新语·任诞》在注引《晋阳秋》时谈“竹林七贤”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34]“七贤”的人格魅力流传人世,经久不息,后人为其著有诸多例如乾隆皇帝的《七贤咏》这类诗词文章,白居易、苏轼等人诗歌中更是常常出现“七贤”的名号,以至于竹林七贤成为后人不时引用的典故。关于“竹林七贤”对世人的深远影响可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促进魏晋玄学发展
事物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魏晋玄学在促使“七贤”独特人格形成之际,“七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魏晋玄学并推进其不断向前发展,其中尤以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影响为甚。
在思想观念方面,一是崇尚自然。这一点尤以嵇康为典型,他一生成就卓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皆是其代表作,这些著作里面均有不少对老庄自然思想的阐释。众所周知,在当时嵇康坚决主张自然、反抗虚伪名教,也因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自然与名教”之争。二是“贵无”思想。阮籍提倡“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35]其思想与老子的“无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在当时自然遭到名教人士的强烈抨击,裴頠更是直斥阮籍、何宴为“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36]这批名教人士所倡之事利于当时司马氏集团的新政权,自然得到司马氏的大力支持。即便如此,仍旧无法阻挡玄学思想的盛行,因当时“自然无为”这一思想早已经流行开来,加之王衍、乐广等一批有影响力士人的极力推动,魏晋玄学的兴盛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则体现为行为层面。竹林士人任诞放达、追求清淡自然的行为对世人影响更深。刘伶在屋中赤裸行走,人们讥讽其“疯癫”行为,他回击道:“天地作为我的房屋,屋室作为我的裈衣,你们这一众人又为何要入我裈中来呢?”是以对虚伪礼法名教的反抗与嘲讽。王戎痛失幼子,一时悲伤难以释怀,山简去看望时劝慰,戎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37]无意间对“圣人有情无情”这一玄学的重要话题进行了相关阐释。“七贤”正是以这样的怪异言行诠释着他们所理解的玄学思想,影响着士人,影响着整个魏晋,从而促进玄学思潮的不断发展。再有“七贤”聚会这一谈玄形式也为各士族所继承。或有西晋名士共至洛水戏,谈玄论道、议论奥妙之事;[38]又或有东晋名士于兰亭雅集,饮酒作赋、谈天说地。[39]这些聚会并非组织于帝王或皇亲贵胄,而是一群如同“竹林七贤”的志同道合者自发组织的一类聚会,相比于前期的梁园之游、邺下之游,这类聚会多了些诗酒意、世俗意,这些变化多多少少是受到竹林风范的影响。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提到阮籍的影响时说:“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40]可见,竹林名士无论是在其思想、文章亦或是任诞放达的言行举止上都对同时期的人们乃至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兴起“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思潮
“七贤”的人格魅力之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行为、文章创作,也体现在对世人审美观的丰富中。魏晋时期人们的审美趋于刚健、阴柔、雕饰美等特征,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对男性形象的描写可谓用“琳琅珠玉,朗然照人”八字来形容。如“捉刀立床头”的曹操,[41]“啖饼依然皎然”的何晏,[42]“姿容妙有”的潘岳,[43]“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等,[44]加之服药的影响,其中一些“美人”甚至带有一种病态美。至于竹林七贤,人们的审美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七贤”由于自身际遇,故而审美自成一派,任诞自然个性前提下的审美更趋向于不加雕饰、放浪形骸。《世说新语·容止》有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45]从这段叙述嵇康的语句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之美,但这一系列用以形容其容貌体态的语词全是纯自然化的、不事雕琢的、富有诗意化的,传达出的便是“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观。再看刘注引《康别传》中:“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46]此处的“土木形骸,不加饰厉”与“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凸显的也是一种不加修饰、顺乎自然的纯天然美。值得注意的是“七贤”中还有一位比较出名的丑男——刘伶。刘伶身材矮小,容貌甚丑,“悠悠忽忽,土木形骸。”[47]“可以说,摆落形体带来的世俗拘囿,不事修饰,萧然独得,顺其自然,构成了‘竹林七贤’整体的人格风貌。”[48]引得世人纷纷追捧。
(三)自然任情思想成为文人的精神自慰工具
竹林名士常以向往自然、企羡隐逸的任情思想构建自身精神空间,试图从苦闷现实中超脱出来,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自由、和谐的审美境界。阮籍是典型,为求得生存,他不得不向司马氏集团委曲求全,在政治中小心翼翼度过一生。在此境遇下,任情自然成为他情感的避风港,以求得自身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庄子思想对于士人的影响,阮籍之前主要是任自然,任由情性自由发泄。到了阮籍,才被用来作为解脱人生苦恼的精神力量。”[4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阮籍以任情自然来规避人生苦恼,成为后世文人人格建构的蓝本,这在龚自珍《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50]一句中得以体现。后世文人像杜甫、王维、司空图等人的诗歌作品中都出现过类似阮籍的“清季名流”,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与竹林风范息息相关。“竹林七贤”不单是一个名人群体,他们已逐渐成为我国传统士族文人人格的一类符号代表。
五、结语
“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更迭之际,他们“弃经典而崇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51]经历了比许多常人更坎坷的人生。即便如此,极富鲜明个性的他们也以超俗的文辞章句、道德理念以及社会行为,有力地影响着两晋士风,堪称为时代之风骚。作为魏晋时期颇有影响力的士人阶层,他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52]以其文学造诣、人生态度乃至他们对精神自由以及人生的追求,对当时社会风气、魏晋士人士风的研究以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透过“竹林七贤”,细读其文,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方能进一步明白他们的身不由己、无可奈何,才理解他们为何如此任诞放达、企慕隐逸。追随他们的生命轨迹,了解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们也更能清晰地探究魏晋这一时期的士人生活风貌和社会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