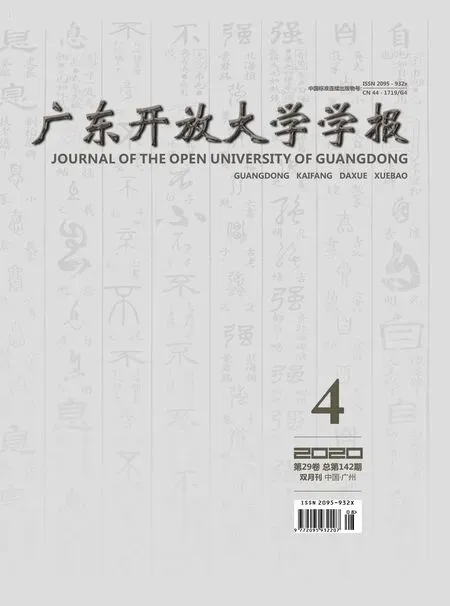论陈霆《渚山堂词话》的词学思想
李林晓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530006)
吴梅先生《词学通论》云:“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亦云:“词至于明,而词亡矣。”[2]诚然,词发展至明代,恰巧处于宋词和清词两座高峰之间,相形之下,明词之衰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词学发展的低谷期,词学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态势也并非是直线下降的,而是有高峰,也有低谷。正如王昶《明词综序》所言:“然一代之词,亦有不可尽废者。”[3]陈霆所生活的弘治、嘉靖年间正是明词发展的小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词人、词作、词学论著涌现。陈霆作为明代中期重要词人之一,著作等身,成绩斐然,他的作品主要保存在《水南稿》十九卷中,词学思想则主要集中在《渚山堂词话》中。相较于同时代的《词品》《艺苑卮言》等词话论著来说,《渚山堂词话》未能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渚山堂词话》是明代第一部词话专著,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崇为“明人词话之善本”[4]1826。考察词话内容,可知陈霆于词体本质论,词体本色论和词体艺术表现论均有自己的论断。陈霆的词学观点虽然不完全出自独创,但在明中叶词坛中,他的词学思想仍然展现出超拔时人之处。
一、情志统一的词体本质论
明代尊情之风弥漫,小说、戏曲都受此影响。作为最适宜表现个人性灵的文体,明词当然也以言情为尊。《渚山堂词话》虽未正面提及词体的言情本质,但从陈霆品评词作的偏好来看,他对言情之词较为青睐。在“张靖之念奴娇”一条中,陈霆评价明词云:“予尝妄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5]378在这里,陈霆虽是从艺术技巧的角度评价明词,但“赋情遣思”一词仍然透露出他对词体言情本质的认可。综观陈霆《渚山堂词话》所选词作,“情”之概念意义广泛,既包括相思离别、伤春悲秋等个体情感,也包括家国兴亡等忧国忧民情感。
明词所提倡的“情”主要指儿女之情,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就直接表达了对“词言情”的高度认可:“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6]385联系王世贞“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於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6]385等语,可知其所言之“情”更多指代儿女之情。陈霆亦并未脱离明代“主情”风气的影响。他所理解的“词言情”之“情”首先指的是相思离别、伤春悲秋等个体性情感。在《渚山堂词话》中,他所引欧阳修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秦观词“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等都是描写相思离别之情的佳作。此外,他还收录了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全词,并解释“雁丘”得名之由来。这种生死相许、不离不弃的真情、至情让他十分感动,因此特意拈出。陈霆此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词坛轶事,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尊情主张。陈霆所推许的这种委婉动人的儿女之情有别于晚唐五代的“艳情”而带有更多庄重的意味。“仲殊艳词”一则就体现了他对滥情、艳情的批判。他对于仲殊“好作艳词,其同袍孚草堂者,尝寓诗箴之,迄不为止”[5]366的行为颇有微词,认为仲殊的大部分作品“大率淫言媟语,故非衲子所宜也”[5]366。可见,陈霆还是有意识地以“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诗学观来评价词体的。贺裳《皱水轩词筌》认为:“词虽宜于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7]明词主艳情,因此清人多不喜明词。实际上,在明代词坛上,对词体之“艳”作出限制的人亦不少,陈霆正是此中代表之一。
除了儿女之情以外,陈霆尤为认可那些发抒忠愤之情、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词作。他在《渚山堂词话》中多次列举张孝祥、刘过、刘克庄、文天祥、辛弃疾、刘基等人的词作,高度认可词作中所寄寓的政治性情感。试举几则材料:
评文天祥《酹江月》二篇:“其曰‘还障天东半壁’,曰‘地灵尚有人杰’,曰‘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曰‘只有丹心难灭’,其于兴复,未尝不耿耿也。”[5]367
评李好古《谒金门》(花过雨):“玉楼歌舞数句,语意不平,岂非当时擅国者宴乐湖山,而不恤边功故耶。”[5]367
评刘基春怨词:“刘伯温春怨,盖感叹时事也……观豹关深之句,知元季兵起,贤者感时伤事,非不欲献言于上,以销祸乱。而九重阻深,无路自达,徒登高怅望而已。”[5]374
以上数则,均有意挖掘词作中所寄托的家国之恨和英雄失路之悲。这些由时事和身世所引发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与“言志”相通。家国之恨本身隐藏着重整乾坤,实现中兴大业的志向,失路之悲也常常伴随着实现人生理想和个体价值的追求。在陈霆看来,词既可言情,也可言志,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上述词作就以其充实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情感力量实现了情志统一。
词作中所展现的情与作者的人品息息相关。为了避免词作落入伪情、俗媚之情,陈霆还提出人品与词品相结合,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解释词作。在《渚山堂词话》中,陈霆主要通过考察词作背景和词人品行来表达这一见解。第一,人品与词品俱劣,如卷一“傅按察词”一条。元代傅氏《钱塘怀古》一词“咏宋氏之亡”[5]357。傅氏之举,是不辨正统和夷狄的表现,与深明大义,忠于南宋的信云父迥别。因此,陈霆分别引用文天祥的两句诗来评价两人,称赞信云父为:“东鲁遗黎老子孙,南方心事北方身。”讽刺傅按察为:“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人久矣化豺狼。”在这里,陈霆对傅氏的词品和人品都进行了否定,认为其作“大率吠尧之意”[5]357,而其人则“有愧于信云父多矣”[5]357。第二,词品佳,而人品不佳,如评张商英《南乡子》(向晚出京关)一则。张商英在这首词中刻意表现出不惧宦海沉浮,追求适意归隐生活的情绪,但陈霆“迹其为人,议论反复,复冒求荣进,去元祐党人远甚”[5]354,认为张商英追名逐利的性格与词作中展现出来的“用则斡旋天下事,何难,不用云中有别山”的精神面貌并不一致。因此,这首词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伪情,而不是真情。第三,人品与词品俱佳。这类词人词作最为陈霆所称赏,在《渚山堂词话》中亦记载颇多。
评吴履斋《满江红》:“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5]359
评文天祥《齐天乐》:“文文山词,在南宋诸人中,特为富丽……史称文山性豪侈,每食方丈,声妓满前。晚节乃散家资,募义勤王,九死不夺。盖子房所谓韩亡不爱万金之资者也,真人豪哉。”[5]362-363
以上两则均是词品与人品俱佳的例子。陈霆选取的均是豪迈之作,所认可的也是忠君爱国、坚贞不屈的人品。唯有具备这种品格,才能抒发真情、豪情,才能真正做到情志统一。
由上观之,陈霆所认可的词言情之“情”内涵宽广,既包括儿女之情,也包括家国情思。相较于明中叶杨慎、王世贞等人的词学观点来说,陈霆关于词体本质论的观点更为客观。杨慎、王世贞等人所重仍是传统的相思离别主题,偶尔涉及言志之作,亦是以苏辛为代表,而陈霆却对南宋和明初的爱国志士尤为垂青,独具慧眼,展现出明词创作繁盛期时一代词学家高瞻远瞩的眼光。
二、不主一格的词体本色论
陈霆论词以宋词为标杆,他在《渚山堂词话》中多次提及“宋人风致”。考察其对“宋人风致”的阐释,可知陈霆取法各家,于宋代的婉约词风、豪放词风及清空词风均有所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不主一格的词体本色论。
陈霆论词首倡婉约。《渚山堂词话》中诸如“语意蕴藉”“清楚流丽”“富丽”“圆转流丽”“婉约清丽”“轻便绮丽”“绮靡蕴藉”等词语多与婉约词风有关。推崇婉约,自然就会以时兴选本《草堂诗余》为参照。他自编的词选《草堂遗音》虽已亡佚,但从书名来看,亦是追步《草堂诗余》。陈霆评论陈铎冬雪词云:“论者谓其有宋人风致。使杂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也。虽然,大声和草堂者,求其近似者盖少。”[5]364陈霆虽认为陈铎的拟作与《草堂诗余》有差距,但是也间接地认可了《草堂诗余》就是宋人风致的代表。“《草堂诗余》以圆美流畅、声情柔婉为词之本色,亦是选词的依据”[8]。可见,陈霆对婉约词风还是颇为认可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词之语言与情感方面,提倡含蓄蕴藉。在“张靖之念奴娇”一则中,陈霆籍由明词“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5]378来表明自己的词学主张。“蕴藉”一语,首先指的是语言委婉含蓄,涵咏不尽,如陈霆评杨基“绿阴深树觅啼莺,莺声更在深深处”一句“语意蕴藉,殆不减宋人也”[5]357。此句表面写绿树啼莺,实则写环境的清幽与词人的闲情逸致。其次,“蕴藉”也指情感深沉内敛。陈霆评欧阳修《蝶恋花》“珠帘夜夜朦胧月”曰:“道幽怨则欧为蕴藉。”[5]368此句明写月色,暗写思妇辗转难眠,孤身赏月,在淡淡的笔触中道出无尽幽怨,言有尽而意无穷。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批评明词“字面往往混入曲子”,“去两宋蕴藉之旨远矣”[9]。此语虽道出了明词的俗化倾向,但亦并非是明词的全貌。陈霆在词话中反复提及“蕴藉”之旨,试图从理论的角度纠正明词过分俗化之弊,可见其词体观是清醒的,也是自觉的。
第二,在词之气象方面,提倡富冶、绮丽。实际上,早在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就有类似言论:“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10]词产生于这样一种富贵环境,自然也就具备了富贵之气。晚唐及北宋前期词人如晏殊、晏几道父子和欧阳修不仅对词之富贵气多有论述,而且身体力行地写作了很多带有富贵之气的词作。“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拥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11]受前人影响,陈霆在《渚山堂词话》中也以“富贵语”与“富贵气象”来区别时人词作,如评价瞿山阳《巫山一段云》“为真知富贵者”[5]356,而杨基《花朝曲》“语虽富丽,然正宋人所谓看人富贵者耳,未必真知富贵也。”[5]370所谓“富贵气象”,主要指的是一种雍容闲适,从容不迫的气度和精神。又如“文山齐天乐”一条,陈霆列举文天祥《齐天乐·甲戌湘宪种德堂灯屏》,认为:“文文山词,在南宋诸人中,特为富丽。”[5]362这首词写元宵观灯的情景,灯屏上的精美彩绘,观灯人的愉悦心情,词人与朋友“把瑶尊,满斟醽醁”直至深夜的情景都刻画得十分细致。末句“回首宫莲,夜深归院烛”与白居易《宴散》中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现出宾主尽欢的心情。历来学者多关注文天祥词作中的爱国豪情,对其中的艺术特色却绝少提及。陈霆关于文天祥的评价发前人所未发,角度新颖。在陈霆看来,这种富贵气度不仅仅只有富人才能具备,即使是衲子仲殊也能写作富冶之词,“类能脱绝寒俭之态”[5]366。陈霆持论公允,并未因为仲殊“好作艳词”而否定其艺术成就《四库全书总目》称陈霆词“豪迈激越,犹有苏辛遗范”[4]1568。陈霆的经历与苏轼相似,都是以朋党之名被贬职,但自身又有经世致用之志,不平之气梗塞于心,所以尤为欣赏那些饱含忠愤之情的词作,在实际创作和词论中均表现出对豪放词风的青睐。在《渚山堂词话》中,他列举了许多豪放之作,表现出对豪士、豪情的称许。如“张安国赋六州歌头”一则,陈霆记录张孝祥《六州歌头》引得“魏公流涕而起,掩袂而入”[5]354的轶事,言语中不无称赏之情。又如“邵公序赠越武穆词”一条,邵公序作《满江红》一词,赞赏岳飞驻师鄂州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行为。全词气势恢宏,感情激荡,风格豪放,塑造出一个英勇善战,性格豪迈的岳飞形象,陈霆引鄂王遗事曰:“此词句句缘实,非寻常谀词也。”[5]360也表达了自己对此词的认可。当然,陈霆对豪放词风的认可建立在词作充实的思想内容与词人高尚伟岸的人格基础上。他称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是因为此词对靖康年间统治者苟安江南致使北方沦陷的历史事实鞭辟入里,具有深沉的现实意义,而张孝祥“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12]的爱国精神也使得全词洋溢着充沛的情感力量,使读者振奋。他称赏邵公序《满江红》一词,也是因为此词展现了岳飞作为抗金英雄的英勇表现,展现了个体在国家危难之际所迸发的爱国热情与大无畏精神。又如“文山别友人词一条”:
文丞相既败,元人获置舟中,既而挟之蹈海。厝山既平,复踰岭而北。道江右,作酹江月二篇,以别友人,皆用东坡赤壁韵。其曰“还障天东半壁”,曰“地灵尚有人杰”,曰“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曰“只有丹心难灭”。其于兴复,未尝不耿耿也[5]367。
文天祥所作《酹江月》,同样属于豪放词风的代表。文天祥有意用东坡赤壁韵,既是追慕先贤,也是有意效仿东坡豪放词风。他早年生活优裕,为了国家却能“散家资,募义勤王,九死不夺”[5]363,从物质层面的“豪侈”过渡为精神方面的豪情、大义,因此得到了陈霆“真人豪哉”[5]363的赞美。自张綖《诗馀图谱》提出“婉约——豪放之正变”以来,明人多推许婉约词风为正,豪放词风为变,如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就称许“宛转绵丽,浅至儇俏”[6]385的婉约之词,“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6]385陈霆却能够超拔于时风之上,对豪放慷慨之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极高的赞美。如今看来,是非常具有远见的。
张仲谋先生认为:“东坡之旷放,稼轩之雄健,白石之冷峭,这三者相调和,即是陈霆词的主导风格。”[13]学人已经注意到陈霆词作中清空冷峭的一面。事实上,在《渚山堂词话》中,陈霆已经表现出对清空词风的认可。如“如晦与瞿宗吉卜算子”一则:
僧如晦作春归云:“有意送春归,无意留春住。毕竟年年用著来,何似休归去。目送楚天遥,不见春归路。风急桃花也似愁,点点飞红雨。”瞿宗吉一曲云:“双蝶送春来,双燕衔春去。春去春来总属人,谁与春为主。一阵雨催花,一阵风吹絮。惟有啼鹃更迫春,不放从容住。”二词皆咏春归,皆寄卜算子。然比而观之,如晦则意高妙,宗吉则语清峭,殆不相伯仲也[5]370。
“意高妙”“语清峭”都是骚雅派论词观点。陈霆引用此语,可见其于清空词风亦有所关注。
总的来说,陈霆对于词体本色的认识较为开放和包容,虽受《草堂诗余》的影响,却能跳出藩篱,于婉约、豪放词风均有称扬,对清空、骚雅词风也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可,并不胶着一端。统合各种词风,本意是丰富词坛的内容,开辟词学发展的新路,为实际创作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
三、多样生新的词体艺术表现论
《渚山堂词话》以品评词作为主,因此词作的艺术特色也是陈霆关注的重点。在词话中,陈霆多摘录前人的名篇佳句,称赏其中的警句妙语,或者批评某些词作的俗词滥调。总的来说,陈霆认可的佳作,一般具有精心锤炼而又自然而然的特点。
首先,陈霆主张化用前人尤其是唐宋诸贤的成句,且能自出机杼。陈霆论禁体词曰:“予谓雪词既禁体,于法宜取古人成语,匀之句中,使人一览见雪,乃为本色。”[5]365不仅是禁体词如此,陈霆在论述其余词作时也主张化用前人成语。如“少游八六子”一则:“少游八六子尾阙云:‘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唐杜牧之一词,其末云:‘正销凝,梧桐又移翠阴。’秦词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二语妙甚,故非杜可及也。”[5]355秦观《八六子》为怀人之作,首句写离愁无边,如芳草般潜滋暗长,随后写词人追忆与佳人相聚和分别的片刻。在这种无边的忧愁中,啼叫的黄鹂忽然将词人唤回到现实之中。全词到此戛然而止,任由读者想象词人清醒后的失落之情,有余音绕梁之感。虽是化用,秦词却较杜诗意蕴悠长。陈霆所说的化用并不是简单模拟,如果仅仅袭用前人成句而不翻新出奇,就可能会陷入“偷句”“盗言”之嫌,如“陈大声袭欧词”一则:
欧公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陈大声体之,作蝶恋花。落句云:“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虽面目稍更,而意句仍昔。然则偷句之钝,何可避也。予向作踏莎行,末云:“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或者谓其袭欧公。要之字语虽近,而用意则别。此与大声之钝,自谓不侔[5]353。
两人用语虽近,但是用意并不相同。陈铎之语仍然沿袭欧阳修原意,写闺中思妇凭栏远眺,极目相送的情景,而陈霆之作则是表达思妇意欲询问游子归期而无人可问的失落与无奈。又如“瞿山阳袭后村词”,陈霆指出瞿佑“怕绿叶成阴,红花结子,留作异时恨”一句“全用后村句格”[5]353,随后又为其开脱曰:“或者宗吉诵刘词久熟,不觉用为己语耶。不然,则连盗数言,恐渠亦自知避。”[5]353可见,陈霆对于直接袭用前人语句而不加翻新的行为是极其不认可的。
其次,在使事用典方面,陈霆主张用典圆妙,浑化无迹。在《渚山堂词话》中,陈霆主要以辛弃疾词作为代表来论述此观点。历代不少词论家认为辛词用典过多,有碍行文。如张炎《词源》就认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14]张炎指责辛刘二人之词为“长短句之诗”,实际就是指他们的作品使事用典过多。陈霆却一反前人之论,为辛弃疾翻案。“辛稼轩词,或议其多用事,而欠流便。予览其琵琶一词,则此论未足凭也。”[5]363他引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一词,认为“此篇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称是妙手。”[5]363辛弃疾此词列举多个与琵琶有关的典故,用典密集却能流转自如,原因在于这些典故契合词人心中所思所感,共同营造出一种繁华已逝,无可奈何的哀怨氛围。
最后,在语言方面,陈霆重视炼字炼句,以自然之语阐发奇思异趣。他称赏完颜亮《昭君怨》一词“和平奇俊”[5]370,而“亮之他作,例倔强怪诞,殊有桀骜不在人下之气”[5]370。“和平”指的是自然而然的语言风格,但自然并不等同于浅白,所以陈霆认为,在语言平易的基础上,还要注重炼字炼句,以传达出“奇俊”之思。如“杨孟载新柳清平乐云:‘犹寒未暖时光。将昏渐晓池塘。记取春来杨柳,风流全在轻黄。’状新柳妙处,数句尽之,古今人未曾道著。歌此阙者,想见芳春媚景,暝色入帘,残月戒曙,身在芳塘之上,徘徊容与也。”[5]356早春时节,乍暖还寒,词人徘徊在池塘边,突然瞥见岸边初生的,嫩黄的柳芽。“轻黄”二字生动准确地描绘出早春柳眼的新鲜可爱,生机勃勃,呼应了“犹寒未暖”的早春天气,也为“将昏渐晓”的画面增添了一抹鲜亮的色彩。寥寥数笔,已将早春之风神勾勒殆尽,因此得到了陈霆的赞许。又如“欧词用出字”一则,陈霆引前人之语,赞赏欧阳修“绿杨楼外出秋千”中的“出”字“是人著力道不到处”[5]368,又引欧阳修“绛旗风飐出花梢”一句,认为“虽同用出字,然视前句,其风致大段不侔。”[5]369前一个“出”字,让人联想到少男少女荡秋千的欢乐情景,意在言外。后一个“出”字,只是实写红旗飘扬的情景,且与“飐”同属动词,弱化了表达效果。陈霆虽未明言二字各自的艺术效果,但我们仍可看出其于炼字炼句的着意。此外,在《渚山堂词话》中,陈霆还常常为前人词作改字改句,如改章良能“雨馀风软碎鸣禽”一句为“暖风娇鸟碎鸣音”,改周邦彦“今朝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为“今宵正对江心月,忆年时、水宿蒹葭”,改邓剡《摸鱼儿》“临皋一枕三生梦,还认岷峨乡语”为“临皋一枕三生梦,还认青城乡语”等等。虽然陈霆此举颇有恃才自负的味道,但他于字句锤炼的用心可见一斑。
从创新性的角度来说,陈霆关于词体艺术表现论的看法多沿袭前人观点,并无太多新意。但是在俗风弥漫的明词坛中,陈霆却力避粗率、曲化之弊,将目光聚焦到词体艺术技巧,这是很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陈霆《渚山堂词话》展现了其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他主张词在保存与生俱来的体性特点的同时,容纳更宽广的内容。情志统一的词体本质论、不主一格的词体本色论和多样生新的词体艺术表现论都是为了开拓词的表现题材,展衍词的表现功能,提升词的审美品格。他在命意造语方面的着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词一味重情而忽视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缺失。遗憾的是,他未能在音律方面作出更为详细的阐述。总的来说,《渚山堂词话》是陈霆在总结与继承前辈词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词学风格、词学发展方向进行的有意识的探索。在整个明代词坛上,《渚山堂词话》成书最早,内容丰富,对于我们了解明代中后期词的发展方向和明人的词学观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