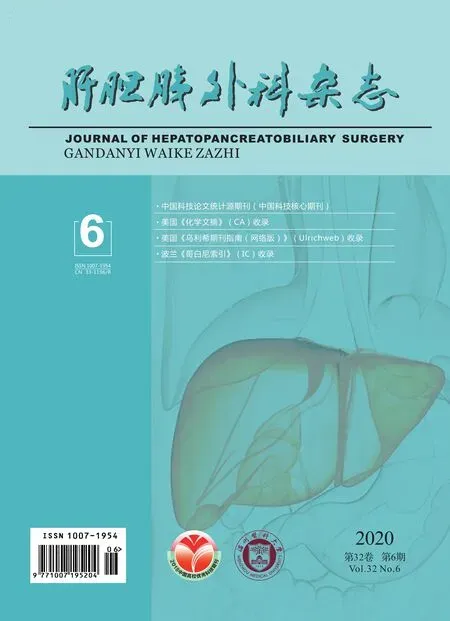肝内胆管癌的治疗难点及应对策略
敖建阳,程庆保,刘辰,姜小清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胆道一科/胆道恶性肿瘤专病诊治中心,上海200438)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A)是指肿瘤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生长在肝内二级分支胆管以上部位的胆管恶性肿瘤。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胆管癌尤其是iCCA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1]。根据肝内胆管癌的大体形态学特征,其经典病理类型有3种,分别为“肿块型”“胆管周围浸润型”“导管内生长型”,而两种常见组织病理学亚型是:①大胆管型:以高大柱状肿瘤细胞为主,以大腺体排列;②小胆管型:具有立方细胞至低柱状细胞组成,胞浆稀少。以胆管内或胆管周围浸润性生长为主要类型的iCCA常为大胆管型,更易发生肝内外及淋巴结转移。对于进展期的iCCA,现代生物医药科技的进步也为系统性治疗带来了更好机会和希望。在本文中,结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一科的经验积累,对iCCA的概况、治疗难点、最新技术及综合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1 肝内胆管癌流行病学概况
胆管癌的国际分类并未区分肝门部胆管癌(pCCA)和远端胆管癌(dCCA),以往常将这些癌症归为“pCCA/dCCA”。在美国诊断的所有胆管癌中,pCCA(50%~60%)和dCCA(20%~30%)约合80%,其余20%为iCCA[2-3]。胆管癌的全球发病率以泰国东北部最高,男性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s)约为100/10万人,而女性约为50/10万人。在西方国家,iCCA的ASIRs的范围为(0.5~2.0)/10万人[4-5]。泰国及周边地区胆管癌的高发病率归因于地方性肝吸虫感染,尤其是泰国肝吸虫(Opisthorchis viverrini)[5]。鉴于iCCA的不良预后,患者病死率与发病率应几乎相等,但多项研究显示西方发达国家这两者并不平行,其影响因素可能有人工因素、科技因素和人口因素。
1.1 国际肿瘤疾病分类版本更新
由于pCCA和dCCA之间缺乏区分,因此在大型流行病学数据中胆管癌亚型分类存在问题。国际肿瘤疾病分类法(ICD-O)的版本每隔几年会更新,但各国在不同的时间点采用新版本,也会造成发病率的人为波动。此外胆管癌亚型之间缺乏区分时,胆管癌最常见的亚型pCCA可能被误归类为最不常见的亚型iCCA,这也是造成iCCA发病率的歪曲报道的原因。
1.2 胆管癌的不正确分类
通过回顾性调查发现,各国可能会发生iCCA的发病率及病死率登记不全的情况[6-7]。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iCCA的发病率增加的同时,原发部位不明肿瘤(CUP)的发病率随之下降[8]。在一项前瞻性II期临床试验中,共纳入289例未曾接受其他治疗的CUP患者,通过分子肿瘤特征分析可以确定98%患者的肿瘤起源组织,预计其中18%的患者肿瘤来源为胆道[9]。因此,CUP和iCCA之间临床鉴别诊断技术的增强可能是iCCA发病率明显增加的因素[10]。
1.3 人口趋势
除了技术分类问题以及诊断工具的准确性和可用性的提高以外,一些人口趋势也可能影响胆管癌的真实发生率,包括肥胖率上升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目前这两项是iCCA和肝细胞癌(HCC)的公认危险因素[11]。随着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引起的iCCA发病率将来可能会下降。
总之,胆管癌发生率的趋势很复杂,需要谨慎对待。未来需要临床和公共卫生等机构协作统一、准确地记录流行病学数据。
2 肝内胆管癌的诊治
2.1 诊断
大部分iCCA患者缺乏典型症状,往往体检进行影像学检查时候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在肝硬化肝脏中,HCC和iCCA的鉴别诊断可能相对困难。动脉相增强及延迟相消退可诊断为HCC,iCCA可表现为动态增强MRI和CT扫描时,动脉期由边缘增强,在延迟相可为向心性增强。CT和MRI在评估iCCA原发病灶和卫星性病变方面具有类似价值,但CT成像在观察强化的血管以及评估可切除性方面更具优越性。肝内胆管癌易发生腹腔淋巴结转移和肝外远处转移,CT和MRI对淋巴结转移诊断价值有限,而PET/CT可提高诊断的正确率,合理运用该检查措施对术前肿瘤分期,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较高的意义。
CA19-9是诊断胆管癌的主要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并且CA19-9>1 000 U/mL与胆管癌转移相关[12],但路易斯抗原阴性的患者(占总人口的7%)的CA19-9可低至无法检出的水平[13],CA19-9在临床中应用价值有限。组织标本活检并进行病理学评估是诊断iCCA的金标准,进一步行标本测序对于iCCA的后续治疗也至关重要。
2.2 治疗
肝内胆管癌的综合治疗包括肿瘤局部治疗(外科手段、放疗、消融、动脉灌注栓塞)和全身系统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但是针对上述手段有效性评价的多项临床研究结果仍存在矛盾之处,使得iCCA个体化治疗原则和临床路径是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鉴于肝内胆管癌的临床治疗均需采用综合治疗方案,并根据肿瘤及全身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因此本文从局部治疗及全身系统治疗分别进行论述。
2.2.1 外科手段:手术切除是治疗肿瘤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在iCCA的实施上却存在一定的争议。多数报道表明根治性切除术可为胆管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2,14-16],也有报道显示R0切除并不能显著提高肝内胆管癌的术后生存率[17-19]。至于疗效,2014年一项荟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手术切缘阴性,肝内胆管癌术后5年生存率仍很少超过30%~50%,中位总生存期仅为28个月[20]。不同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可能与纳入组的患者病情及手术方式不一致有关。对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一项367例iCCA手术切除资料分析表明,手术切缘(<1 cmvs≥1 cm)不影响患者总生存期[21]。2015年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报道,583例接受肝切除的iCCA患者,大范围肝切除(83.5%)与局部肝切除(16.5%)相比,更有可能在显微镜下呈阳性切缘,与≥1 cm无瘤切缘相比,5~9 mm、1~4 mm、切缘阳性均与较短的无瘤生存时间呈线性正相关趋势,表明切缘宽度和预后存在相关性[22]。2016年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R0切缘超过10 mm的iCCA人群预后优于切缘在10 mm以内的R0手术人群[23]。2017年报道的一项国际14个中心1 142例iCCA手术资料分析显示,实施大范围切肝与术后总生存期无关,却增加围手术期风险,不同肿瘤切缘宽度对预后存在显著影响,肝内胆管癌切缘宽度应≥5 mm[24]。
由于存活时间短、预后差和复发风险高,传统上认为iCCA是肝移植的禁忌证。然而在2014年一项回顾性多中心研究表明,8例合并肝硬化的“非常早期(直径≤2 cm的单个肿瘤)”iCCA患者,其肝移植后5年的存活率达到73%[25]。2016年另一项更大范围的国际化多中心肝移植患者队列随访研究发现,非常早期的15例iCCA患者的5年生存率是65%,而33例“进展期”iCCA(单个肿瘤>2 cm或多灶性)患者是45%[26],这已接近肝细胞癌术后的5年生存率,表明肝移植可成为部分肝硬化合并早期iCCA患者有效治疗的选择方案。
2.2.2 淋巴结清扫:若iCCA发生淋巴结转移,联合淋巴结清扫范围可能未使患者获益,而当iCCA无淋巴结转移时,常规实施淋巴结清扫依据不足。我们中心临床实践中,肿块型一般淋巴结转移发生率较低,可不行淋巴结清扫,而胆管周围浸润型则具有很高的淋巴结转移潜质,需常规行淋巴结清扫,术前阅片基本可确定大体分型及治疗方案[27]。多项研究表明,乙肝相关型iCCA淋巴结转移率较低,肿块型iCCA切除后初期复发时淋巴结转移风险较低[28-30],而结石相关性iCCA发生淋巴结转移的风险相对高于肝内胆管癌[28,31]。根据文献结果[32]及我们观察到的证据,起源于肝内大胆管的iCCA往往表现为“胆管周围浸润型”或“胆管内生长型”的病理类型特点,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手术作为一种局部治疗方法,需要联合辅助治疗手段以控制疾病的整体情况。因此,对大胆管型的iCCA采取“局部肿瘤根治性切除+区域淋巴结清扫、联合放化疗”的系统治疗策略可能更为有利。基于肿瘤恶性程度较高的特点,区域淋巴结清扫的范围宜局限在肝十二指肠韧带、胰头后方、肝下下腔静脉旁及胃小弯侧范围,追求更大范围的淋巴结清扫可能并不会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获益。
2.2.3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长久以来临床传统观念认为,肝内胆管癌属于乏血供肿瘤,并非TACE的良好适应证[33];但也有肯定其治疗价值的报道。在局部无法手术切除的iCCA的患者中,回顾性研究且采用实体瘤RECIST标准评价存在一定局限性,使TACE治疗CCA或iCCA的术后辅助应用TACE的价值仍未明确。对于iCCA切除术后TACE的价值,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各有一项均采用5-氟尿嘧啶、表柔比星和羟基喜树碱及碘化油方案的回顾性研究。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研究表明,对预后不良的iCCA,患者肝切除后辅以TACE可能获益[3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研究发现,肝切除后辅助以TACE能够延长TNM II期、III期和V期iCCA的生存;但对于TNM I期的患者不仅不能延长生存期,反而促进肿瘤复发。笔者推测可能与TACE诱导局部血管生成因子促进肿瘤复发转移的机制有关[35]。
2.2.4 放射治疗:对于局部无法切除的iCCA的部分患者,大剂量适形的体外放射治疗(EBRT)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对于右肝的肿瘤,远离胃肠道,放射治疗尤为适宜[36]。先进的EBRT技术,例如3D适形放射疗法(3D-CRT)和强度调制放射疗法(IMRT),用于在不损害正常组织的情况下向目标适形照射。另外,带电粒子(质子或碳)束比常规X射线束具有更有利的物理剂量沉积轮廓,这在保留正常组织方面可能有优势。总之,这些技术进步可能使放射治疗剂量增加至胆道肿瘤和改善对非肿瘤组织的保护,从而提高胆管癌放射治疗的效果。术后EBRT加化疗可使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患者生存获益,特别是对于淋巴结阳性或切除边缘阳性者[37-39],这些结果奠定了正在进行的评估放射治疗用于吉西他滨和顺铂化疗后III期临床试验的基础(NCT02200042)。
2.2.5 细胞毒性化学疗法:吉西他滨和顺铂的联合治疗是当前的一线化疗方案,适用于不能手术或局部治疗的进展期iCCA患者。2016年有报道:在所有胆道肿瘤类型中,该化疗方案组合治疗队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1.7个月,而单独使用吉西他滨的中位生存期为8.1个月[40],但单独针对iCCA患者的数据较少;一项III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在R0或R1胆道癌切除术后3个月开始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GEMOX)辅助化疗并没有显著改善无瘤生存率[41],总体而言,化疗尚无二线标准治疗方案,需要更多的证据来阐明辅助化疗在iCCA治疗中的作用。
2.2.6 分子靶向疗法:iCCA的异质性使有效靶向疗法开发困难。随着分子谱研究的进一步深入,iCCA的基因组和转录组学得到了更好的描述和更深的理解。在Nakamura等的研究中,发现在iCCA中主要有IDH1/2、FGFR1/2/3、EPHA2和BAP1的基因突变[42],且仅在iCCA患者中发现了导致该受体酪氨酸激酶非配体依赖性激活的FGFR2融合蛋白,与以前的研究结论一致[43-44],该靶点可能是iCCA的阿喀琉斯之踵,可为后续药物研究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
虽然有已上市的iCCA明星靶点FGFR2靶向药物pemigatinib,但在2020年1月初被FDA授予快速通道资格的另外一款新药infigratinib也显示出了令人欣喜的临床疗效,试验组患者疾病控制率(DCR)高达83.3%[45]。
另一个明星靶点IDH1/2的靶向药物Tibsovo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试验组的DCR达到53%,对照组为28%[46],目前Tibsovo已处于计划补充新药申请。
2.2.7 胆管癌的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在多种肿瘤类型的患者亚组中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抗肿瘤活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疗法和新的过继细胞疗法已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巨大的希望,可改善当前的肿瘤治疗应答率、改善药物选择和解决治疗耐药性等问题。
对肝内多发病灶合并区域淋巴结转移的肝内胆管癌患者,免疫联合治疗是大趋势,尤其是免疫联合放疗、免疫联合靶向带来了较好的效果,肿瘤病灶缩小甚至灭活,获得部分或完全缓解,无进展生存时间延长;此外有部分患者肿瘤降期后实施了肿瘤切除治疗。这些令人鼓舞的初步临床数据为胆管癌的免疫治疗方法提供了希望,同时强调了生物标志物开发的重要性:以识别最有可能做出反应的患者,并指导合理选择联合疗法。免疫联合治疗方兴未艾,具体方案细节还需要多中心、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进一步确认。
3 结论
当前早期识别胆管癌并进行可能的治愈性手段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进一步研究新型生物标志物,可以设想应用先进技术例如通过质谱或2D凝胶电泳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以及用于检测包括胆汁、血清或粪便样品在内的生物样品中的胆管癌生物标志物的microRNA分析。
iCCA中的基因融合等突变需要在功能研究和临床试验中进一步深入。前景广阔的新兴疗法包括FGFR抑制剂、IDH1/2抑制剂以及免疫疗法。鉴定用于选择具有相关突变的生物标志物是靶向治疗的重要因素。应根据疾病亚型和遗传因素对患者进行分层分类治疗,利用生物标志物突变等检测手段对于开发有效的胆管癌药物疗法必不可少。iCCA致癌作用涉及的各种信号通路之间的广泛相互作用,更凸显了组合治疗方法的重要性,局部治疗、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的结合值得进一步研究。随着基础医学和生物医药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对于肝内胆管癌生物学特性认识的不断加深,有朝一日我们必将完全将其治愈,给患者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