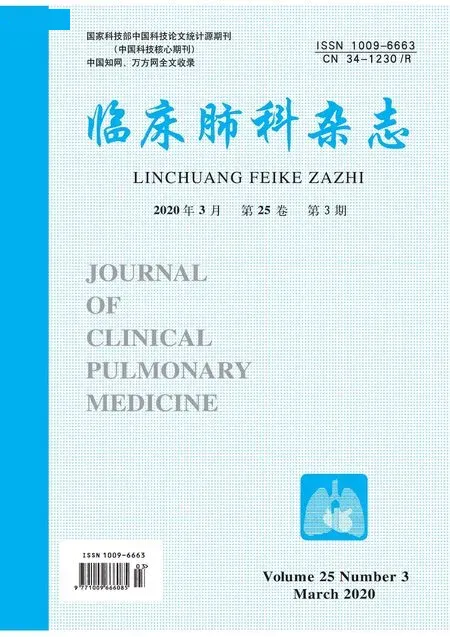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的研究进展
林敏杰 张英为 邱玉英
肺纤维化是以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大量细胞外基质聚集并伴炎症损伤、组织结构破坏为特征的一大类肺疾病的终末期改变,肺气肿是指终末细支气管远端的气道弹性减退,过度膨胀、充气和肺容积增大或同时伴有气道壁破坏的病理状态。当肺纤维化和肺气肿同时存在时,则称为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Combined pulmonary fibrosis and emphysema ,CPFE),CPFE是一种不同于肺纤维化和肺气肿的综合征,由Cottin在2005年首次提出[1],肺部高分辨率CT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表现为上肺的肺气肿以及下肺的肺纤维化。8%~33%的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患者存在肺气肿,因此特发性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在CPFE中占有重要地位[2]。 Sato 等[3]认为可以把IPF合并肺气肿作为CPFE的表型之一,对于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和评估预后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尚缺乏统一的CPFE诊疗指南,本文就CPFE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做一综述,以期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病因及发病机制
一、吸烟
几乎所有的CPFE患者都有吸烟病史,其吸烟量为5~73包/年[4]。吸烟是肺气肿和IPF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其中肺气肿和IPF发病过程中的共同通路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吸烟者的表观遗传学发生了大量改变,尤其是DNA的过度甲基化,并且其影响在戒烟多年后依然存在[5]。此外,在吸烟患者中,IPF合并肺气肿较非IPF合并肺气肿的肺纤维化面积更广,提示吸烟患者中IPF与肺气肿对肺纤维化扩大存在协同作用[6]。
二、职业暴露
部分CPFE患者有特定的职业暴露史,提示职业暴露在CPFE的发病中有一定作用。一些文献报道了长期暴露于农用化合物的CPFE的患者以及轮胎工的CPFE的患者,提示某些职业暴露与CPFE的发病存在某种关联[7]。
三、结缔组织疾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
CTD相关的CPFE患者多发于年轻女性,与特发性的CPFE相比病情相对较轻[7]。CTD往往能促进CPFE的发生发展,Antoniou等[8]研究发现,在吸烟人群中,类风湿关节炎引起的继发性间质性肺炎与IPF相比,出现肺气肿的吸烟量更少,年限更短。此外,CTD继发的CPFE患者的抗核抗体阳性率更高,在纤维化的肺组织中发现大量的CD20阳性B淋巴细胞的浸润[9],提示其发病机制与淋巴细胞浸润有关。
四、基因易感性
Xu等发现在我国人群中,基质金属蛋白-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和TGF-β1的基因多态性与CPFE的易感性有关,MMP-9和TGF-β1更多的T等位基因是IPF患者肺气肿形成的危险因素[10]。此外,早些年的文献报道了ABCA3基因和SFTPC的基因突变与其发生有关[11]。
病理表现
CPFE患者的病理常兼有肺气肿和肺纤维化的表现。上肺主要表现为肺气肿表现即终末细支气管的过度膨胀并伴有气道壁的破坏,下肺主要表现为肺纤维化的表现,即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大量细胞外基质聚集并伴炎症损伤、组织结构破坏。但肺气肿和肺纤维化并非按肺叶截然分开,每一肺叶中均能发现以上表现[12]。其中肺纤维化的病理表现复杂多样,可出现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UIP)、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脱屑性间质性肺炎、机化性肺炎、淋巴细胞性间质性肺炎等[13]。
临床表现
呼吸困难是其最主要的症状,cottin报道的61例CPFE的患者中均以呼吸困难为主诉,另外,咳嗽、咳痰、胸痛、乏力等症状也常常出现[1],与IPF相比,CPFE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更为常见[14]。查体上87%的患者存在肺基底部的爆裂音,43%存在杵状指[1]。
辅助检查
一、肺部HRCT
肺部HRCT是目前诊断CPFE最主要的方法,典型的表现为上叶的肺气肿和下叶的肺纤维化[15]。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常表现的小叶中央型肺气肿不同,CPFE的肺气肿常表现为小叶周围型和间隔旁肺气肿,有73%的患者存在直径大于1cm的囊腔。在纤维化病灶中,最常见的表型为UIP型,即表现为两肺弥漫性分布的不规则的线状影或网状影,牵拉性支气管扩张,蜂窝形成,肺容积的减少等,也可出现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脱屑性间质性肺炎、机化性肺炎、淋巴细胞性间质性肺炎等[4,15-16]。Sugino等[17]发现通过双源CT能将CPFE中的肺气肿和肺纤维化区域更好的区分开来,其中肺纤维化的氙气增强区域较多(72.2 ± 15.1%),而肺气肿的氙气增强区域较少(45.2 ± 23.2%),另外肺纤维化所占两肺体积的比例与FEV1/FVC和FEV1%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二、肺功能
CPFE的肺功能特征为FEV1和TLC基本正常,而一氧化碳弥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the lung for carbon monoxide ,DLCO)往往表现为显著的下降。Yoon 等[18]的研究发现CPFE患者的肺容积比IPF多10%,并且FVC下降速度更慢,FVC下降的速度与其肺气肿占肺总量的比例有关,当其截断值为10%时,大于该截断值表现为更慢的FVC下降速度。Mendes 等[19]发现与肺气肿相比,CPFE患者的 RV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TLC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和 RV/TLC 更低,而FEV1% 和 FEV1/FVC 更高。
三、血清学表现
Kokuho等[20]发现克拉氏细胞分泌蛋白(Clara cell secretory 16-kD protein,CC16)在CPFE患者当中普遍升高,联合上升的Ⅱ型肺泡上皮表面抗原-6(Krebs yon denlungen-6,KL-6)浓度能够有效的鉴别单纯的肺气肿,血清 CC16值在吸烟对照组、肺气肿组、CPFE组分别为5.67±0.42 ng/mL、5.66 ±0.35 ng/mL 、9.38 ±1.04 ng/mL (P<0.0009)。因此联合CC16和KL-6在病理学和影像学不典型的CPFE患者的诊断中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通过血清学筛查对发现自身免疫病相关的CPFE有重要意义,在继发性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的CPFE患者中,有45%的患者与CTD相关[21]。
诊 断
CPFE目前缺乏明确的诊断标准,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患者一般有长期的吸烟史,症状主要为呼吸困难、咳嗽、咳痰,查体常能闻及两下肺的爆裂音,部分病人存在杵状指。肺部HRCT的表现常需符合以下三条:①存在与正常组织分界清楚的透亮区,气肿壁<1mm或不存在壁,伴或不伴有上肺直径>1cm的肺大泡②两下肺和胸膜下为主的纤维化病灶,伴或不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③磨玻璃区域和肺实变区域较少[1]。
并发症
一、 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是指在海平面水平下平均肺动脉压大于25mmHg,是CPFE常见的并发症[1]。CPFE、IPF、COPD的肺动脉高压的发生率分别为47%~90%、31%~46%、50%。其中CPFE肺动脉压的水平较IPF高,Tzilas等发现CPFE和IPF在诊断之初,两者的肺动脉压没有统计学差异,但12月后CPFE组的肺动脉压显著高于IPF组[7,22-23]。此外,COPD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的压力一般也较CPFE低[7]。Hirano等[13]在一例严重肺动脉高压的CPFE患者尸检中发现较大的肺动脉分支出现内膜纤维化和纤维肌性增生,而较小的肺动脉血管壁明显增厚,肺泡腔边缘还能发现少量微血栓,提示CPFE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可能与肺动脉各级分支的纤维化、管壁增厚和微血栓形成有关。
二、 肺癌
IPF和肺气肿均为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IPF的肺癌发生率为22.4%~31.3%,肺气肿病人的发生率为6.8%~10.8%[24]。CPFE患者的肺癌发生率13%~46.8%,可能与IPF、肺气肿和吸烟的三重因素有关[25]。病理类型以鳞癌最为常见(42.3%),其次为腺癌(34.4%) ,其他病理类型相对较少[26]。与不存在肺气肿或肺纤维化的肺癌患者相比,CPFE组的患者病理分级更高,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更高,术后肿瘤复发几率更高[27]。
三、急性肺损伤
CPFE合并肺癌患者中常常出现急性肺损伤,通常发生在肺部手术和化疗后,其发生率为25%[7,28],其原因可能与治疗后发生的感染有关[28]。血清KL-6可作为预测CPFE急性肺损伤的血清生物学标记物(OR= 1.0016,P=0.009),当其截断值为1050 IU/L时,高于此截断值对预测CPFE急性肺损伤的意义较大[29]。此外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肺癌和性别年龄生理 (gender, age, and physiology,GAP)评分均为CPFE患者急性肺损伤发生的阳性预测因子[30]。
治 疗
目前CPFE没有特异性的治疗方法。对仍然在吸烟的患者应予以戒烟,出现呼吸衰竭的患者应予以氧疗,为减少下呼吸道感染,可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链球菌疫苗, 长效毒蕈碱受体拮抗剂(long-acting muscarinic receptor antagonists,LAMA)作为COPD的基础治疗亦可选用[31]。此外,Dong等[32]发现长期吸入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ICS)/长效β受体激动剂(long-acting β adrenergic receptor agonists,LABA)能改善其肺功能,减少其急性加重的频率及其严重程度。Oltmanns等[33]发现接受吡非尼酮治疗的CPFE患者肺功能下降速度延缓,其治疗效果与IPF相似。Tomioka等[34]发现CPFE患者的FEV1能从肺康复中获益,但与COPD组相比,其获益较少。肺移植可能是终末期患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现阶段CPFE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治疗方法不多,还需积极开展各类临床试验验证一些药物的治疗效果。
预 后
CPFE的预后较差,其中位生存期为2.1~8.5年[35],与肺气肿相比,其死亡率更高(aHR 4.62, 95%CI2.25~9.47;P<0.01)[36]。CPFE与IPF预后是否存在差异目前存在争议。Kohashi等[37]报道CPFE较IPF的中位生存期显著缩短,其中CPFE组的中位生存期为1734天,而IPF组为2229天(p = 0.007)。而Jacob等[38]报道称IPF患者中发生肺气肿对其预后没有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各研究的入组标准存在差异,组间混杂了其他的间质性肺病以及一些病例出现并发症有关。不同纤维化亚型的CPFE的预后存在差异,Alsumrain等[21]发现在CPFE中肺纤维化表现为IPF的预后差于其他类型的肺纤维化(P=0.036)。Jacob等[23]发现肺动脉压与患者的预后相关,存在肺动脉高压的CPFE和无肺动脉高压的CPFE 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8个月和44个月。当CPFE合并肺癌时,其生存率显著降低,中位生存期约19.5月[27]。Malli 等[39]的研究发现DLCO对预后具有显著的预测价值,当其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小于39%时,其预计生存期显著缩短。CPFE较差的预后说明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尤为重要,加强对COPD和肺纤维化患者的随访可能可以改善患者的预后。
总之,CPFE的概念在2005年cottin提出后,有关CPFE的研究得以开展,但目前的诊断标准仍延续着最初的标准,需要对诊断标准进行科学量化,还有其发病机制仍不完全清楚,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治疗方面,目前还没有特异性的治疗方式,既往适用于COPD和肺纤维化的药物对于CPFE的作用需要进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