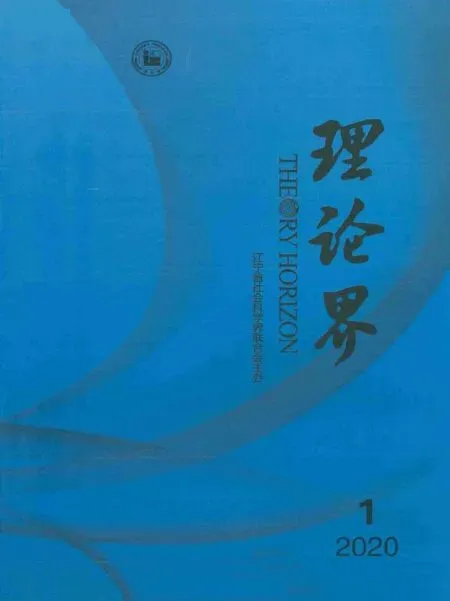论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于桂凤
哈穆特·罗萨(Hartmut Rose)是当代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也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霍耐特批判理论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试图复兴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重新诠释现代性。通过对晚期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批判性分析,罗萨揭示了隐含于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加速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引入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构建了他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理论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之一,为我们深度发掘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深入把握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思考。
一、晚期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社会加速
准确揭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及其问题所在是晚期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宗旨。罗萨认为,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反思的“古典”社会学文献,虽然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如韦伯和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合理化”,涂尔干和卢曼所论证的“分化”,齐美尔和贝克所声称的“个体化”,马克思、阿多诺等所指出的“驯化或商品化”,但忽略了对普遍存在的社会加速问题的深入研究。此种研究之所以必要,关键在于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贯穿并作用于“合理化”“分化”“个体化”“驯化或商品化”,直接关涉现代社会的潜在病状与现代人的美好生活。
罗萨关于现代社会核心特质的判定基于他对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分析。在罗萨看来,时间并非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而是整个社会领域的核心构成要素,一切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都具有时间上的过程性,并通过时间加以整合。所以“以时间作为分析社会的切入点,是一个分析的‘诀窍’,它可以为分析与批判不同的社会行动领域提供一个稳定且一贯的焦点”。〔1〕罗萨认为,时间规范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社会中最具支配性、控制性的规范。时间规范不同于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它没有披上伦理的外衣,也没有佯装为一种政治规范,而是表现成一种赤裸裸的事实、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2〕整个现代社会,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通过时间结构联结起来,并受严密的时间体制控制。正是这种特性,使时间规范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带有集权主义性质。最能够表达现代时间结构变化趋势与特征的概念则是“加速”,时间规范对现代社会的“规范力”或“控制力”集中展现为社会加速。社会加速“界定了现代社会的动力、发展与改变逻辑,以及推动力”,〔3〕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罗萨得出此种判定的重要依据是尽管现代社会还存在一些减速甚至反抗加速的现象,但加速的力量始终占据优势。
罗萨把减速或停滞现象概括为以下五种类型:一是自然的速度极限,如自然资源的再生产、感冒、流感和怀孕的过程。从原则上说,这些过程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提速;二是减速绿洲,指没有被现代化进程所侵蚀的社会或文化“孤岛”,这里的时间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也表明,加速与现代化相伴而生;三是因社会加速失调而造成的病态减速,如交通拥堵、长期失业等;四是刻意减速,包括功能上的减速和意识形态上(反抗性)减速,前者如过度疲劳之人暂停工作,后者如反现代性的“深层生态学”等社会运动;五是结构惰性和文化惰性,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耗尽了梦想的能量,不可能再有重要的新观点、新事物产生,如福山“历史的终结”论。对于这些减速现象与社会加速的关系,罗萨指出,第一、第二种减速现象只是社会加速的限制力量而非反抗力量。第三种减速现象仅仅是社会加速的派生物,因而从属于社会加速。第四种减速现象则是加速过程得以可能的条件,是加速本身的构成要素。第五种减速现象虽然不是加速的派生物,但却内在于现代加速当中。正因如此,相对于社会加速力量而言,这些减速力量在状态、重要性和功能方面都处于次要地位。即使现代社会存在对加速的反抗,但事实证明,“在所有的减速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跟现代加速趋势有真正且结构性的不分轩轾抗衡之力”。〔4〕从经验层面看,现代人也深切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加速,并在现代文化中得到证明,如葛莱克(James Gleick)观察到“加速牵涉所有事”,卡普兰(Douglas Coupland)所写的《一个加速文化的传说》,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声称“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5〕
基于以上分析,罗萨得出,整个现代社会都被一种强大的社会加速逻辑所控制,并改变了我们与伙伴、社会、时间、空间、自然、无生命对象的世界(客体世界)和人类主体形式(主体世界)及其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模式、生命经历和集体历史,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及新的主体形式,并最终引发新的异化。这也是社会加速之所以重要的关键所在。
罗萨认为,指认并批判分析阻碍人们迈向美好生活的“社会病状”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宗旨,因而也是每一位社会批判理论家的责任。在他看来,“社会加速”就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社会病状”。由于他对现代“社会病状”的这一诊断完全有别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家,他被看作是对当代社会进行原创性诊断的社会理论家。按照罗萨的观点,以往社会理论家关于现代社会的诊断及解决方案,如哈贝马斯的以“相互理解情境”为基础的沟通行动理论,霍耐特的以“相互承认情境”为基础的承认批判理论,其实践也会受社会加速的影响——无论是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还是相互承认,都需要时间。此外,关于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等的判断,虽然准确抓住了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但这些特征也都与社会加速密切相关。他特别指出,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诠释为一种社会加速的历史,社会加速是现代性的独立的基本原则,也是阻碍现代人过上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因此,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必须关注社会加速问题。
二、社会加速:概念内涵与推动机制
界定社会加速概念的内涵是建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罗萨指出,以往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加速的讨论,涉及生活的速度、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甚至时间本身,但还没有形成定义清晰并被普遍认同的社会加速概念。因此,他试图从一个不同的分析框架,为社会加速提供一个“在理论方面是清楚的、在经验上是合理”的定义。
借助于牛顿物理学,罗萨认为“加速可以定义为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6〕为进一步说明社会加速的本质内涵,罗萨在此基础上又从纷繁复杂的诸多加速的社会现象中,归纳出三组加速范畴: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这三组范畴,既代表三种不同的加速形式,也是三个不同的加速领域,各有不同定义。
第一,科技加速。它可以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输出’的增加”,〔7〕表现为运输速度、信息传输速度、生产速度、服务速度、消费速度等变得更快,是目标明确、最明显、最易测量和证明的加速形式。科技加速属于社会“当中”的加速,因而对社会现实影响巨大:它导致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再造且发生变化,促使现代的科层体系和管理体系中的各种过程加速,甚至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即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体验。例如由于受人类自身的知觉器官和地球重力的影响,在过去人类对时空的体验中,空间具有“自然的”优先性,但现在时间获得了这种优先性。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时间“甚至消弥了空间”。
第二,社会变迁的加速。它可以定义为“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8〕属于社会“本身”的加速,涉及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家庭以及政治、职业等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实践。因其变迁的速率本身的改变,使得“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习惯(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9〕正因为这种加速是社会“本身”的加速,且速率持续提升,所以测量有些困难。罗萨建议可以“当下时态的萎缩”这个概念作为测量的准绳。所谓“当下时态的萎缩”指社会各个事物、信息的时效性越来越短。罗萨以家庭与职业为例,对“当下时态的萎缩”进行了经验的证明。在早期现代,家庭与职业以“数个世代”的步调发生改变,在“古典”(大约是1850年到1970年)现代是“每个世代”的改变,而到了晚期现代则是“世代之内”就已经改变。现代社会变迁速率的不断提升意味着现代社会制度和实践稳定程度的普遍下降。
第三,生活节奏的加速。它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即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测量此种加速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尺度。“主观”的尺度指个体对此种加速的直观感受。其中,最直观的主观感受是“时间匮乏”。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由于无法跟上社会生活的快速节奏而被淘汰,甚至对这种“时间匮乏”产生恐慌感。“客观”的尺度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测量可界定出来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比如测量吃饭、睡觉、散步、娱乐、家庭谈心的时间。另一种是测量行动时间与体验时间的“压缩”,比如在一定时间段当中,通过减少休息或间隔时间而做更多事。在此,罗萨也从社会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科技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之间的“矛盾”关系。从逻辑上看,科技加速会使自由时间“增加”,从而应该让生活节奏“放缓”或“变慢”。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时间匮乏”。罗萨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需要完成的“事务量”在持续增加。科技加速提供了让“事务量”得以增加的条件,但并不是“事务量”增加的“肇因”,因为“事务量”增加的速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的速率。而且从历史上看,工业时代的科技革命似乎就是为了回应“时间匮乏”问题。那么“事务量”不断增速的原因到底何在?又是什么推动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这就涉及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问题。
罗萨把社会加速的动力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动力是竞争。罗萨认为,竞争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社会结构上看,不仅经济领域、体育领域,而且政治、科学、艺术领域,甚至宗教领域,都充斥着竞争逻辑。同时,从主体角度看,这种竞争逻辑既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又存在于个人之间。因此,竞争是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之一。然而,“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10〕这样竞争就成为社会加速的主要推动力。第二,文化动力是“永恒的应许”。罗萨指出,“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加速的功能等同于永恒生命的(宗教)应许”。〔11〕这源于现代社会重视此世而非死后的彼岸世界。根据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文化逻辑,好的生活就是有丰富的体验与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但是在个人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可以实现的事物,总是比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有鉴于此,生活节奏或步调的加速就成为消除这种差异和矛盾的重要策略。“现代加速的幸福应许,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它认为‘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我们在面对有限与死亡的问题时,所作出的(亦即是现代性的)回答。”〔12〕第三,加速循环。按照罗萨的观点,到了晚期现代,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在此,罗萨深刻分析并揭示了三种加速形式或领域之间“令人惊讶的反馈循环”关系:科技加速推进社会变迁的加速,加速了的社会变迁造就生活步调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又必然要求科技加速。这种循环推动晚期现代社会不断地加速。罗萨把社会动力和文化动力看作社会加速的外在驱动力,而把加速循环视为内在驱动力。总的来看,罗萨的分析主要是在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观察基础之上的“现象学”分析。
三、社会加速批判:功能批判与规范批判
罗萨指出,在晚期现代社会,社会加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对所有主体的意志与行动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几乎无法逃避,更无法抵御和反抗,并最终导致人的新异化。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批判。
罗萨对社会加速的批判相对区分为功能批判和规范批判。功能批判实质是揭示社会加速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消极后果。依据经验观察,罗萨认为虽然当代社会“所有的过程”都倾向于加速,但不同领域、不同事物的加速能力、加速程度存在差异,由此造成“诸多制度、过程和实践之间的界限的摩擦与张力”,〔13〕他称之为“去同步化”问题。这种“去同步化”既存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各领域中。前者如人类消耗石油和耕地等自然资源的速度远远高于这些资源再生产的速度,后者如经济转变、科技发明的速度总是领先于政府决策的速度。从功能性质上看,“去同步化”已经引发社会各种系统性的功能失调,如政治失调、经济失调、文化失调等,并有可能最终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断裂,削弱、破坏现代社会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因而极其有害和危险。在此,罗萨不仅论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现代人的抑郁症与“去同步化”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期现代社会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的“去同步化”及其危害。在政治领域,民主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过程,民主的民意形塑和决策的速度远慢于社会变迁、文化变迁和经济变迁的加速过程。因此,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之间明显存在着“去同步化”。这使“政治操控”在晚期现代成为社会变迁的障碍,而在早期现代和古典现代它曾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工具。这也是晚期现代政治功能失调的反映。在经济领域,罗萨认为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就源于金融领域投资流动、资本流动与生产、消费之间步调的极其不一致:经济或金融可以无止境地加速,而生产和消费却不能。在文化领域,文化规范和知识的传承也是一个耗费时间的过程,反映了社会世代之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但是社会生活的快速变迁,使世代之间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从而破坏了世代之间的稳定性。此外,不断追求创新与变动的现代社会还会从根本上损害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的适应能力,在“表面上过度动态化的晚期现代社会背后,出现了一个最僵固的硬化、冻结形式”。〔14〕
规范批判包括道德批判和伦理批判,罗萨比较侧重于后者,并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加速违背了现代性对自主性的承诺。罗萨认为,让个体实现自主性既是“现代性的计划”,也是“现代性的承诺”。原则上,社会加速与自主性应该相辅相成,因为个体要实现自主性,“必须得超越稳固不变的社会秩序,不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以及政治威权和宗教威权)终身固定下来,也不要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再生产下去”。〔15〕由此加速被人们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种可以实现自主性的手段。但是社会发展现实表明,在晚期现代社会,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们发现社会加速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变成了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同时,社会加速不再保证个体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不再保证社会能够根据正义、进步、永续等观念进行政治改革。这意味着承诺赋予个体自主性的“现代性的计划”与社会加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社会加速对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起了否定作用。第二,社会加速造成新的异化。罗萨在这里所说的新异化,是相对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而言的。罗萨把马克思所理解的异化概括为五个方面:人与自身行动(劳动)的异化、人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物)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罗萨认为,晚期现代社会加速已经使人类的异化不再局限于上述五个方面,又出现了新的异化形式。由此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基础上,罗萨提出了一种新异化观。
按照罗萨自己的分析,这种新异化观之“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异化概念本质的重新界定。与马克思一样,罗萨也把异化定义为一种负面的关系,但他认为这种负面关系表达的是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层、结构性的扭曲,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是与我们的真实内在本质产生异化,而是与我们吸收世界的能力产生异化”。〔16〕从这可以看出,罗萨所理解的异化是一种能力异化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本质异化。他完全接受了当代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拉埃尔·耶基的建议,即重新引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需要再回过头去处理人类本质或人类本质概念。二是对异化形式的重新归纳。罗萨把社会加速造成的异化概括为以下几种形式: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社会异化与自我异化。空间异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相关性与空间邻近性之间的脱节。物界异化是指我们自己生产和消费的物本应该是我们日常体验、身份认同、生命史的一部分,标志着我们的个人特质,但社会加速使人类没有时间去好好了解这些物,人类与它们处于相互疏离中。行动异化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事,所有人都被“要事清单”的工作所支配。时间异化表现为社会加速使经典的“体验短/记忆久”或“体验久/记忆短”的时间体验和记忆模式变成了“体验短/记忆短”的模式。罗萨认为,上述四种异化必然导致我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破坏,使所有我们所经历的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所有我们的抉择,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需要的物等确立我们身份认同的素材,无法好好地被吸收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最终造成“自我耗尽”。
深入思想实际,我们会发现,罗萨对新异化的批判性分析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首先,他对异化概念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还相当模糊不清,也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哲学方向的意涵”。〔17〕这使他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从人类本质高度把握异化的“真正的意义”。正因如此,罗萨对异化的理解显得过于泛化,甚至认为有些异化形式是人们想要的、不可避免的,所以“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理论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18〕这意味着有些异化的存在是合理的,不用消解、没有必要克服。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对立。其次,他所发现并归纳的新异化形式,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理解的范围,即使是他自认为很有新意的空间异化、时间异化,在马克思那里也都有论述,只不过没有直接表述为空间异化或时间异化而已。最后,他的异化批判也没有达到马克思异化批判的深刻性、彻底性。罗萨虽然把异化概念重新引入了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多基于对具体的异化现象的经验性描述,而非本质高度的理论性分析。另外,他把异化的直接原因归结为社会加速,又把社会加速的动力概括为社会“竞争”、“永恒的应许”、“加速循环”等,但却没有进一步追溯它们的“最高因”。因此,他的异化批判并没有上升到社会制度、生产关系批判的唯物史观高度,他所提出的解决异化的可能方案,即建立主体与世界相互回应、充满“共鸣”的社会关系,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些恰恰从反面说明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当代依然具有其他批判理论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