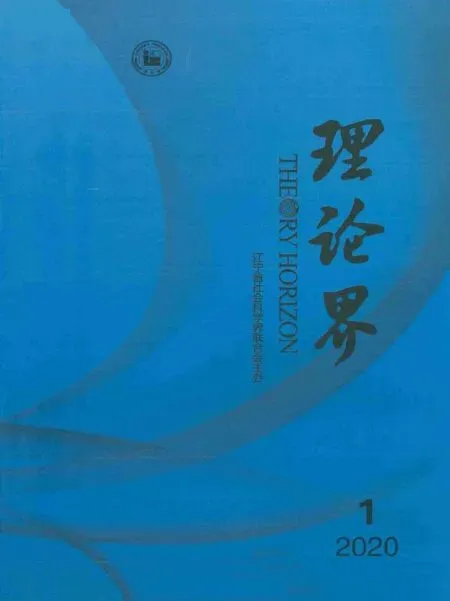农村“漂妈”进城生活困境及对策研究
姚 蓉 张伟豪
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及流动政策的放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一、二线城市生活、工作,经过艰苦奋斗后定居在了陌生城市。但是由于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找到稳定工作、结婚生子后的年轻人由于时间和成本问题无暇顾及家庭、照料自己年幼的孩子,因此,本该退出劳动力市场,在老家安享晚年的老人们不得不背上行囊,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场所来到子女生活的他乡,帮助其照料家庭。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被媒体及学术界形象地称为“老漂族”。从熟悉的地方来到陌生的城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人际交往、语言文化等都与之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年老精力消退、休闲时间被占据、艰难的社会网络重构等问题,都使老人在帮助子女承担家庭养育的过程中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
“老漂族”的基数不断增大,其群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日益突出。一方面,基于现实原因,相对原本就在城市生活的“老漂”,农村“老漂”的不适感更加强烈。在进入城市生活以前,农村“老漂”大都以务农为主,有着稳定的人际关系圈以及带有农村特色的娱乐方式,但是迫不得已来到了之前从未生活过的城市,跟随子女住进了封闭的高楼大厦,生活习惯改变、陌生感来袭、生活圈子狭隘、经济无保障、医疗福利享受不到等问题相继出现,因此,较之于城市“老漂”,农村“老漂”来到城市生活后身体及心理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困境和压力。另一方面,调查发现相比于男性“老漂”,女性“老漂”在照料孙辈后会出现更多负向效用,“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给老年女性带来了积累终生的社会和经济劣势,加重女性老人的照料负担,给她们的身心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双重弱势身份的加持,产生了“老漂族”群体当中更特殊的一个群体,即来自农村的女性老漂族,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农村“漂妈”。
一、农村“漂妈”的城市生活困境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称,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2.471亿;其中60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约1800万人,占总流动人口的7.2%,占我国老年总人口的8.4%,其中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人为43%,而当中来自农村的流动老人约占59%。再根据调查发现,按照传统的家庭生活伦理及女性善于操持家事等特性,来城市帮子女料理家务、照顾孙辈的主力军多为女性“老漂”,庞大的农村“漂妈”群体足够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重视。农村“漂妈”城市生活的困境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空间“困守”问题
环境不适是农村“漂妈”进入城市生活后所要面对的首个困境。居住空间的局限和出行的不便,让厨房、幼儿园、社区公共娱乐场地成为了她们主要的活动空间。农村“漂妈”进城之前住在敞亮的平房大院里,热闹的街坊邻居和道路畅通的乡间小路都给予其较大的自由空间。来到城市后,空间密闭的高层建筑、错综复杂的城市道路在给城市带来活力的同时却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居住空间变小、楼层阻隔经常使她们感到压抑和不适应,邻里无法有效交流、环境封闭使她们不愿意呆在高楼里;但是拥挤的公共交通、道路的错综复杂又使她们不愿外出活动,出门搞不清方向、迷路的问题常常出现。大部分的农村老年流动人口仅受过最低等的教育,其中老年女性更是占到了79%,当这些农村老年妇女来到城市外出迷路时常常会因为语言和不识字的问题而更加增长了她们出行的困难。因此,空间和交通的不便把她们的出行范围固定在了子女生活的小区里,环境在塑造心理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空间“困守”很容易使农村“漂妈”在精神上出现孤独、排斥、焦虑等消极情绪,产生自我隔离和社区隔离。
2.文化适应问题
文化震惊是指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初次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混乱与心理上的压力。农村“漂妈”在乡村生活多年,当来到陌生城市后,许多原有的生活方式因年老以及身心不适应而很难改变过来,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造成“文化震惊”。在进入城市生活以前她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乡下生活依旧会遵循类似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安排,生活安静且简单;来到城市照顾孙辈以后,嘈杂的小区环境,儿孙辈上下班、上下学时间都使她们原有的生活作息被打破,引起身体的不适。
另外,正所谓“胃知乡愁”,饮食方面的习惯改变对于农村“漂妈”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子女较早地来到城市求学,饮食习惯和时间与其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南北饮食差异大,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的随迁也不可避免地使她们面临着饮食的极大改变,老年女性的身体适应情况远不如同辈男性,当饮食习惯不同时,不仅引起农村“漂妈”身体的不适,也加深了其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
所以不仅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城市气候、风俗的不同都使农村“漂妈”把在乡村生活了很久的习惯抽离出来,导致她们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此外,多数农村“漂妈”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有限,平日里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新知识,由此带来的挫败感也对其心理造成压力。
3.家庭关系问题
在中国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中,作为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血缘关系依旧是最重要和值得信赖的。但是由于现实原因,农村“漂妈”进入城市后也遇到了与老伴儿、子女之间的困境:
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由于生活成本的压力,农村“漂妈”往往独自来到城市照顾孙辈,老伴儿留守在农村料理庄稼。在即将步入老年享受生活时,夫妻却要面临两地分居的情况,这无疑给她们的精神和情感上带来了双重打击。一方面,农村“漂妈”担心农村老伴儿的生活状况,日思夜想。另一方面,当她们在城市遇到种种不适与摩擦想要与自己多年生活的老伴儿倾诉时,却苦于不在身边,只好将所有的不快憋到心里,长时间势必会影响其身心健康。
“农村漂妈”义不容辞地来到城市承担起隔代照料的任务,也尽最大努力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和育幼负担。但是由于两代人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差别,与子女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她们在城市生活中所要面临的问题。她们来到子女的“小家庭”生活,传统的权威感和话语权自然会逐渐瓦解;子女因为忙于事业,也无暇顾及对陌生环境并不适应的母亲,久而久之会使其在心理上产生很强的寄居感,形成主观上的无能和自卑。婆媳冲突也是家庭关系中亘古不变的话题。农村婆婆与城市儿媳朝夕相处,难免会因为生活琐事和育儿观念产生冲突。据调查,当与儿媳产生矛盾时,大多数农村“漂妈”会因为家庭和谐选择隐忍,尽量避免与儿媳发生正面冲突,生活的不适应及情感的无法宣泄势必会加深其在城市中的孤独感。
4.社会融入问题
一方面,社会融入体现在农村“漂妈”对社区及社会关系的归属感上,社会关系不强,归属感低会导致其在城市生活中出现持续边缘化的困境。在农村,“漂妈”有较多密切的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非正式照顾资源较多,但进入城市之后,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跟随距离的移动而濒临断裂,陌生的“公共空间”使农村“漂妈”的生活变得拘谨,城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脆弱,因此,在建构新的关系时,往往会变得慎重和保守,久而久之使她们对城市产生了疏离感和冷漠感。另一方面,人的社会融入可以从人们对于正式的社会组织的参与中表现出来。但是农村“漂妈”不被包括到居住地的社会制度中,也不曾拥有城市社区完整的居民身份。无论是文娱活动抑或是福利政策,农村“漂妈”更多的是接收不到其所在社区的服务信息。受自身生活环境、文化程度和阅历等限制,大部分农村“漂妈”也因害羞、自卑等不愿参与社区活动。新的环境、陌生人群、社区的排斥以及自我否定,都使她们陷入情绪纠葛和生活困境之中。
5.社会保障问题
外来移民和当地居民都是城市的纳税人,他们的父母也应当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但由于政策不到位等原因,其依旧站在了均等社会福利的门槛外。一方面,农村“漂妈”享受不到当地居民拥有的服务政策。另一方面,城乡分割也使她们在农村的保障制度断裂。我国现有的服务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户籍分割特征,特别是在医疗保障方面,并未真正实现跨区域联网互通。而家务劳动是一项时间、精力、体力丝毫不亚于产生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长时间的劳作经常让年龄渐长和水土不服的农村“漂妈”感到疼痛缠身,生病也时有发生。因此,当农村“漂妈”进入城市之后却因为户籍的限制,既享受不到“利随人走”的动态性保障,也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的公共性,导致她们陷入一种公共性断裂与失衡的双重困境。据调查,部分农村“漂妈”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和“两不靠”的医疗保障困境使得她们放弃治疗,长此以往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二、农村“漂妈”城市生活困境的解决路径
农村“漂妈”的形成及其发展壮大,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场、社会、文化与国家多种结构性力量对于流动的农村女性老人的裹挟与形塑,社会、不断涌入城市的流动家庭、农村“漂妈”都应该采取积极态度应对城市生活面临的挑战,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漂妈”要学会自我调节
首先,入乡随俗,主动适应城市环境。一方面,主动提高继续社会化的能力,学习在城市生活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减少对新环境的排斥。另一方面,放弃旧观念,调整生活习惯。进入城市后,农村“漂妈”要改变在农村老家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主动适应和调整饮食和时间安排,增强体能,提高自己的城市适应能力。
其次,提高主体意识,防止“边缘化”。一方面,农村“漂妈”来到城市帮助子女照料孙辈时也不要忘记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面对进入城市后无法自我排遣的压力,要善于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如跳“广场舞”、学习上网等,充实休闲生活,消除焦虑。另一方面,寻求各种渠道打破“自我边缘化”,积极向城市靠拢,如尽量多地向子女敞开心扉、积极参与社区举办的文体活动、寻求老年伙伴儿,以便加强与子女、新伙伴儿之间的交流,排解不良情绪,消除精神困扰。
2.子女要给予老人更多关怀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子女应明白母亲从家乡来到陌生城市照顾孙辈的不易。因此,在忙于事业的同时也要了解农村“漂妈”身心的需求。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在生活上关心和照料,如主动提供经济资助、多抽时间带母亲去熟悉城市;定期带她们去医院进行体检,知晓其身体状况等。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也要给予关怀,给农村“漂妈”精神上的安慰。第一,与她们分享自己生活和工作当中的趣事和喜悦,增强她们在子女“小家庭”中的存在感;第二,要调整好“漂妈”与女婿或儿媳的关系,充当真正的调解员,而不是一味迁就或不顾及;第三,多与独自在老家生活的父亲打电话和交流,做到让农村“漂妈”安心,家里父亲放心。
另外,农村“漂妈”和子女应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坦诚交流。农村“漂妈”要主动向子女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子女也要尽力了解母亲的困难,作出恰当的回应和关怀。当身体出现不适时,及时告知子女而不是刻意隐瞒导致延误;对子女考虑不周或做得不好的地方,相互理解和包容,以恰当的方式让子女知晓,子女也要积极改正自己的不当之处,切忌憋在心里或独自生闷气,从而减轻“漂妈”的身心压力,促进家庭和谐。
3.社会层面要进行帮扶接纳
社区和政府要意识到农村“漂妈”这一群体的到来不仅帮助年轻人解决了后顾之忧,促进了家庭幸福,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因此,社区和政府层面的帮扶也是必不可少的:
社区及居民应该改变对农村“漂妈”的偏见和误解,将其纳入社区大家庭中。一方面,社区应当多给予其物质和精神上的关爱,提供生活、娱乐及交往的支持和机会。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应主动与她们交流,不仅要从心理上接纳农村“漂妈”,而且要从行动上关爱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漂妈”群体的重视程度,努力优化老年流动的顶层设计,提高社会保障。首先,逐步降低福利保障门槛,深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的统筹水平,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险报销的全国联网制度,从而解决农村养老金微薄且异地无法领取、住院看病需来回奔波的问题。其次,积极筹办各种社会组织多为其提供专业服务,提高农村“漂妈”对城市的归属感,安心为家庭和社会服务。
三、结语
农村“漂妈”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在城市中“漂”的状态,不仅给“农村漂妈”的身体带来了很多的“不适感”,也导致了她们心理上的“漂泊感”。空间环境的“困守”、文化差异的不适、缺失的亲情关心、孤独的社会交往、未到位的社会保障等,都直接反映了农村“漂妈”的在城生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感和支持度。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城市家庭对子女抚育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只要构造农村“漂妈”的各种结构性力量没有消失,她们的规模就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所以为了能够促进农村“漂妈”及家庭的生活幸福,促进社会稳定,如何解决其城市生活困境成为了不可小觑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