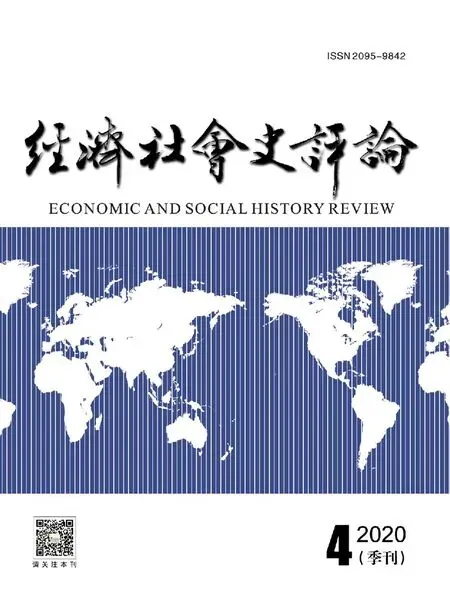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路径与逻辑*
——以《法律选编》为中心
李继荣 徐家玲
一、引 言
早期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处于罗马帝国转型与变革阶段,基督教思想不断融入帝国社会,开启了基督教观念和罗马法制传统相结合的新时期,至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最终实现了帝国立法基督教化,此时颁布的《法律选编》以基督教法典的模式成文,成为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过程中的重要案例,为后世立法奠定了基础。《法律选编》是继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后,拜占庭伊苏里亚王朝皇帝利奥三世与君士坦丁五世因时代变迁之需于740年共同颁布的一部新型简明法典,共18章,以民法为主、刑罚为辅,体现了基督教圣典的立法精神,以及家庭和睦、社会公平和刑罚“仁爱”的立法原则。与《民法大全》仅在形式上包含了基督教的内容相异,《法律选编》真正将基督教的思想融入到了法典的具体条款之中,成为利奥三世皇帝时期流传下来的弥足珍贵的官方文献之一,历来备受学界珍视。自该法典的稿本发现之日起,“诸多学者就开始对其进行校勘、整理和翻译,其希腊文本、英文本、法文本及德文本均先后问世”(1)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ix.;20世纪30年代后,各国学者展开了对该法典的深入研究,如著名拜占庭史家瓦西列夫注意到,该法典虽然充斥着使获罪者肢体致残的惩处规定,但因其多数情况下是用致残来代替死刑,故不能认为这是一部野蛮的法典(2)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2, p. 242.;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和伯里则认为该法典受到教会的影响较大,使罗马法的精神开始在基督教的宗教气氛中发生变化;奥尔顿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该法典是一部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基础上被简化、基督教化的法典(3)李继荣:《拜占庭〈法律选编〉“仁爱”化原因探微》,《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4期,第86页。。国内学者如陈志强教授等在其论著中都谈及该法典,但研究多是将其置于历史的总的进程中加以阐释,并没有对之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法律选编》文本出发,由点及面,对早期拜占庭立法基督教化的成因进行初步探析,以期能对学界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二、君权神授理论与皇权强化趋势的契合
在古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固都与其所依仗的宗教系统密不可分,罗马ˉ拜占庭帝国皇权的强化亦是在与基督教信仰的博弈、认可与利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和时期,虽然罗马宗教与希腊的多神教体系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它毕竟产生于罗马历史与文化的基因之中,其神名、神性与神的功能等诸多方面亦拥有自己的特性,“宗教的风貌大相径庭”(4)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73页。。它源起于罗马家庭—氏族守护神崇拜,融合了意大利本土的诸种自然神的崇拜,加上一些人们想象中的抽象概念(如和平之神、希望之神、勇武之神)形成一个神族系统,并以实物(牲畜、家禽或其他)(5)瓦西列夫在论及背教者朱利安恢复罗马传统宗教的举措时,特别提到他亲自操刀参与宰杀牲畜,于是,一首民谣广泛传播:“小白牛向马可恺撒问候!如果你取胜,那将是我们的末日。”参见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7页。献祭方式展示人们对神的敬仰。但是随着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利用宗教意识加强和神化皇权逐渐成为帝王不断获得权力和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并通过思想或道德的灌输方式“温和”渗入,利用道德和伦理掌控和管理帝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早在公元前27年,屋大维创立元首制时,帝国就逐渐开始了皇权神化、君主崇拜的历程。但因帝制创建初期,传统元老贵族实力依旧较大,故皇帝只能借着“元首制”的共和外衣,隐秘地利用宗教来加强帝制统治。故而屋大维为了使自己的称呼在避开独裁者身份的同时,还能彰显其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一方面,他赋予自己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新名字“奥古斯都(Augustus)”,该词源自于古罗马的一个古老职业“占卜者(augurium)”,意为“神圣”;另一方面他还兼领罗马宗教中的“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意在表明其与神明之间的密切联系。屋大维以带有宗教色彩的称号和头衔神化王权的手段被后世皇帝继承,如马可皇帝开始自称为全体臣民的“君主和神”(dominus et deus),戴克里先皇帝则自诩为“大神朱庇特的助手和代理人”(1)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330页。,罗马皇帝日益成为帝国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方面的最高权威,任何可能威胁其权威者都可能遭受皇帝的残酷镇压。
屋大维建立起来的以罗马诸神为核心的神化皇权的体系虽然被之后的皇帝所继承,但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发展却开始对其造成新的冲击。公元1世纪,基督教发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因其早期的活动受到外界压力,各地区社团之间也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加之多在犹太会堂中以隐秘的方式进行活动,故其被认为是犹太教的分支,在帝国享有合法权利。但是“当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趋于统一时,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统一的团体,安条克主教伊格纳修斯称这个团体为普世教会”,(2)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0页。其组织形式日益完善,传播范围与日俱增,与帝国传统多神崇拜的宗教(基督教化时代被称为“异教”)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激烈,特别是基督教的“天国”概念,使作为“异教”的最高代表者的皇帝们总感到自己的统治会被颠覆。于是,剪除可能会引起帝国混乱和王位不稳的基督教力量,成为“异教”统治者的根本职责。
因此,自公元64年尼禄皇帝借罗马城大火,以“纵火罪”对基督徒进行捕杀,到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连发数道敕令对基督徒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判罪,掀起了对基督教断断续续200余年的迫害运动。但是历史地看,皇帝对基督教的积极迫害,并非因为其认为基督教十恶不赦,而是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引起的皇帝自我危机意识和内心不安所致,正如塔西佗所言:“他把那些自己承认是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3)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99页。在皇帝看来,基督教是一个离经叛道、有违祖训的秘密团体,对帝国稳定和皇权巩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应是帝王对其进行迫害的主要原因。
但是1—4世纪帝国的基督教迫害政策,不但没有消灭这一团体,相反却使其获得巨大发展。一些基督教“护教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孜孜不倦地向帝国民众宣传基督教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信条,消除了一些人对基督教的误解,皇帝也开始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起初只是个别皇帝对基督教相关政策的临时性改变,以尤西比乌斯所记载的图拉真与两个基督教农民的故事最具戏剧色彩,“当皇帝得知他所审问的这两个被视为帝国危险分子的人只拥有2.5英亩土地(约合15亩),而且他们所追求的‘将来的国度’,并不是在地上,而是在来世的天上时,轻蔑地嘲笑了这兄弟二人,并把他们释放了,然后皇帝下令停止迫害基督徒”。(1)徐家玲、李继荣:《“米兰敕令”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70页。4世纪后,基督教的不断发展最终使帝国皇帝也逐渐落实在整体政策的考量上,代表性的文件是311年伽勒里乌斯皇帝颁布的《宽容敕令》:
朕认为应将最及时的宽容亦给予他们,以便于他们可以再次成为基督徒,且组织集会——只要他们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对于朕的宽容,他们要在上帝面前为朕之健康,吾邦之安全,亦为他们自己之健康祈福,以使吾国四面八方安宁无忧,他们亦能安居乐业。(2)李继荣、徐家玲:《“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文本考——兼论“伽氏敕令”的历史地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71页。
起初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帝国统治者担心基督教的发展将会有害于帝国统治,现在承认其合法性则是皇帝发现其于自身统治无害。加之,其时皇帝伽勒里乌斯本人已感染疫病数月,原先崇尚的异教神明并没能使其摆脱病魔的“纠缠”,故其窃以为是自己得罪了基督徒的上神,遂改变态度,希望自己对基督教的承认能换来基督教上帝之宽恕与庇护,助其恢复健康,护佑帝国安宁。但是他态度的改变终究晚了些,未及该法令实施,便与世长辞,帝国复又陷入混乱。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乌斯颁布“米兰敕令”重新确认了“伽氏敕令”中的原则,使基督教正式在帝国境内获得合法地位。(3)传统观点认为,“米兰敕令”的颁布标志着基督教合法化的开始,近年有些学者则认为早在“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中就已经认可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只是将其重申。参见李继荣、徐家玲:《“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文本考——兼论“伽氏敕令”的历史地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徐家玲、李继荣:《“米兰敕令”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当然,就在皇帝对基督教从坚决镇压到逐渐认可最后完全接受的全过程中,基督教也在不断调适着自身的理论精要,期望能与帝国的皇权达成一致,以获得帝王的支持。事实上,早在耶稣赴难后,基督教徒为了迎合罗马皇帝,就已经开始试图与罗马皇权合作,保罗的著名论断“那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由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4)《新旧约全书·新约·罗马书》(中文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2012年,第180页。已经明确地向基督教众说明皇权受之于上帝的理念,坦言了基督教是支持“君权神授”原则的,这成为皇权与教权合作的根基。
皇帝需要新的宗教理论使皇权合法化,基督教则需要皇权对自身进行保护,在这一“需要—契合”的相互支撑下,君士坦丁重新恢复帝国大统之后,决定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积极以上帝代理人的身份,打着“维护神的和平”之旗号,敦促人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并在干预和主宰教会事务方面亲力亲为,积极主动地依靠基督教实现君权的神化。从此,教权与皇权的依存与斗争贯穿于整个拜占庭帝国,325年君士坦丁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亲自参与“正统基督教义”的制订,晚年接受基督教洗礼,并促使他的诸子成为基督徒。当然,皇帝积极干预宗教事务,完全是从帝国社会稳定出发的,从他以下的一段话可见端倪:“如果上帝的人民——我指的是我那些上帝的仆人弟兄们——因他们当中邪恶和损害性的争吵而分裂成如此状况,我的思绪如何能够平静下来呢?你们要知道,这给我带来多大的苦恼啊。”(1)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林中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55页。
狄奥多西王朝的皇帝不仅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工具,更是将其逐渐上升并渗入到制度层面,用基督教塑造帝国的形象与思想,来达到稳固帝国的目的。当狄奥多西一世于379年应西帝格拉先(375—383年在位)之命掌控东方帝国的帝权之后,明确表示放弃罗马皇帝之“最高祭司”的头衔,表明其放弃罗马传统宗教,决心从罗马诸神的侍奉者转为基督教上帝之“仆从”的意向。381年,狄奥多西主持了君士坦丁堡主教公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信经》中的原则,392年更是下令禁止任何场合向罗马古代神祗献祭,异教神庙一律关闭,使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国教;而狄奥多西二世面对帝国日益基督教化的现状,在立法方面开始进一步涉及有关基督教政策的法令,其于438年颁布的16卷的《狄奥多西法典》中,专设一卷用于收录关于基督教的法令,开启了皇帝立法与基督教内涵的相互结合。(2)详见Theodosiu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 by C. Phar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而真正利用基督教使皇权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是查士丁尼大帝。476年,罗马西部地区被蛮族取而代之,给罗马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此后罗马ˉ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便进入到一种“恢复往昔”与“面对现实”的矛盾循环的境遇之中,也为拜占庭帝国逐渐脱离古典罗马的特质奠定了基础。查士丁尼继位后,以“一个帝国、一部法典和一个宗教”的战略目标,通过多次“收复”战争、编纂新型法典和镇压尼卡起义,不仅打击了帝国内外的诸多敌人,而且形成了以查士丁尼为核心,狄奥多拉、特里波尼安、贝利撒留等大批支持者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集团,特别在镇压了“尼卡起义”后,皇帝终于取得了对贵族的绝对控制,“他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君主,任何人都不能与他的权力相抗衡”,(3)A. A 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I.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pp. 102-103.皇帝的权力进一步提升,标志着查士丁尼与古典主义传统的决裂。
除了在军事上取得成功,查士丁尼还希望借法律和信仰维护社会的稳定。他认为,“皇帝的威严光荣既需要兵器,也需要法律”“皇帝既是虔诚法律的伸张者,也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4)J. B. Moyl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3, p. 1.因此基督教成为皇帝加强自我权力的有力手段,一方面,面对异教、异端势力仍然在挑战基督教绝对权威的现状,查帝于529年下令关闭了宣传和讲授古希腊哲学(异教思想)的异教徒庇护所——雅典学园;另一方面,在奉行“政教协调”原则的前提下,他更加明确了“教会应该成为政府机构手中的有力武器,应尽一切努力使教会服从自己”(1)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 148.的主张,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五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强行软禁了拒绝在‘三章案’辩论会文件上签字的罗马教宗维基里乌斯”,(2)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p. 150-153.这些事实表明查帝笃信绝对的权威,强调在秩序良好的国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教权要依附于皇权,皇帝可以用宗教的灵魂来塑造帝国的躯体,使其合二为一,于是才会有《法学阶梯》的开篇“以我主耶稣基督之名”(3)J. B. Moyl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p. 1.来强调君王之立法与治国是上帝所赋予的,体现出皇帝自身权力威严与神圣,这也是对基督教经典中“君权神授”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查士丁尼在位时大规模战争引发的国库亏空和去世后帝国衰微带来的外族压境,终使其欲将地中海变成帝国“内湖”的宏图大志也逐渐付之东流。6—8世纪,拜占庭帝国陷入内忧外患、群雄争霸、灾疫不断的混乱时期。人们在困境面前的精神崩溃,加速了基督教所宣称之“上帝愤怒”和“人生而有罪,要尽一生实行救赎”的教义精神在拜占庭帝国的传播,也进一步推动了君权神圣观念的形成。希拉克略王朝的皇帝在其新律中也借用基督的名义,但与查士丁尼不同的是,其更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将君主形象与《圣经》中君王形象进行比拟的方式来达到神化皇权的目的。如希拉克略皇帝完全击败了波斯人后,为表其功绩,宫廷诗人乔治在其《六日》的作品中,将希拉克略对波斯征战的6年比喻为《旧约·创世纪》中的创世六日,而在其《十字架的复还》的诗篇中,他更是一改以往将希拉克略比拟为古典英雄的宣传手法,将其描绘为基督教的君主,主要凸显其630年夺回圣十字架,使其回归到耶路撒冷的功绩。(4)M. T. G.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 680-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2015, p. 32.这种形象展现出皇帝的威严、军事首领的战绩和对基督教的虔诚。
717年,利奥三世建立伊苏里亚王朝后,帝国境况已与2个世纪前的查帝统治时期大不相同,一方面,基督教已经融入到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在利奥三世的文治武功,内外兼修的努力治理下,帝国局势趋于稳定,虽然领土面积进一步缩小,但国家集权得以完整,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此在面对刚刚复苏的帝国,利奥三世需要强化基督教的精神统治,以进一步改造和稳定帝国局势,达到重建帝国秩序的目的。
所以,利奥三世皇帝在《法律选编》开篇中,即公然打出了“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义:虔诚的罗马皇帝利奥与君士坦丁(Eν oνoματι τοu πατρoς καi τοu υiοu καi τοuaγiου πνεuματος Λεων καi Κωνσταντiνος τιστοi βασιλεiς ρωμαiων)”的名号,不仅彰显了伊苏里亚人承嗣皇统的正统性,更是突出了帝位之合法与皇帝对神的虔诚,强调皇帝与上帝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自身权力的神圣性:
我们的神、上帝、造物主创造了人,赋予其自由意志,并据先知所言“授其律法”以助之,以此使其明了万事万物中,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使他可以选择前者成为被救赎者,摒弃后者而避免成为受惩者;没有人可以置身圣戒之外,不遵守或藐视圣戒者,便会因其行为受到报应。(1)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p. 66.
可见,上帝是原初最伟大的立法者,其话语的权威是永恒的,正如《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第35节所言,“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为了使法律更具有神圣性权威,《法律选编》将其改编为“上帝的圣谕的权威将不会过时(θεoς……τwν λoγων n δuναμις……οu παρελεuσεται)”。法典中充斥着上帝永恒之言和对罪恶的明确阐释,遵循上帝已经创造了人,并授予其律法,将帝国委任给了伊苏里亚人的主旨。因此,《法律选编》明确表示,“正如上帝吩咐十二使徒之首的彼得一样,上帝命令我们(皇帝)司牧他最忠实的羊群”(2)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pp. 66-67.,表明皇帝及其在法律中的形象不断被神化。这次立法活动,借使徒中最权威的彼得之言颁行具有重要意义,皇帝被置于圣徒的继承者,也就是基督教的继承者的地位。法典中以广而告之、勿容置疑的命令形式,要求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要关照其信徒,以便于他们可以从牧羊者基督那里获得救赎。因此,皇帝不仅代表着拥有圣徒的权威,也有责任引导和保护其基督教的子民,《法律选编》的基督教化是在帝国基督教“君权神授”思想演变过程中,与君权强化之理念达成的一种契合与需求,这既是王权强化的一种表现,更是强化王权的一个结果。
三、政局动荡不稳与缓解社会矛盾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学者彼得·布朗教授的《古代晚期世界:150—750年》出版,“古代晚期”的概念就此诞生。这一概念主要运用罗马帝国“转型理论”对统治学界长达200余年的“衰亡理论”发起挑战,认为2—7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并非走向衰亡,而是进入了从古典世界向中世纪过渡阶段,“衰亡是指帝国西部省份的政治结构,而作为古代晚期文化核心所在的东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地区却没有受到影响,甚至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存活下来的地区仍是当时世界上的最伟大文明之一”。(3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 19.“)古代晚期”为学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罗马ˉ拜占庭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体现出了帝国在“裂变—整合”、“危机—应对”的循环往复中,度过了帝国漫长的转型与变革时期,而促发其转变的核心动力便是3—8世纪的社会动荡。
3—8世纪社会动荡的第一个表现便是内外战争频繁发生。自2世纪末,罗马帝国对外征服步伐放缓,内外矛盾日益凸显,吉本认为帝国的麻烦“是从180年马克·奥勒留皇帝的驾崩开始的,该皇帝的逝世标志着一段和平时代、繁荣和良好的政府管理时期的结束”,(1)W. Treadgold, A Concise History of Byzantium, Palgrave Maciillan: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2001, p. 6.是所谓的“3世纪危机”爆发的节点,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内战全面爆发,王位频繁更替。据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统计,罗马“从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其余都因战争和宫廷内争而暴亡。
君士坦丁大帝在帝位之争中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胜利,通过内外改革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稳定了局势,此后的皇帝也沿用并不断完善这一体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帝国内部战争的影响,人口锐减,城市遭到破坏,整体实力受到极大地折损,帝国周围的外族趁机给帝国施加压力,东边的波斯人,北边的日耳曼人均对帝国疆域虎视眈眈,如朱利安皇帝统治时期,因对外战争屡遭败绩,不得不“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小块边境地区割让给了波斯”,而“伊利里亚的一些边境地区也先后短暂陷于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掌控之中”,(3)W. Treadgold, A Concise History of Byzantium, p. 37.378年,哥特人进军君士坦丁堡,双方会战于亚得里亚堡,结果“皇帝瓦伦斯在战斗中被杀,罗马军队彻底战败”(4)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 87.。
476年,蛮族首领奥多亚克罢黜了西部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罗马帝国西半部地区皇统结束,此即历史上经常强调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的标志,也是罗马周边“蛮族”对罗马帝国长期蚕食的最后一个阶段,一个世纪之后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才标志着蛮族对罗马帝国西部入侵行动的最后完成。即使如此,东罗马皇帝(拜占庭)试图收复“失地”的“光复”之梦不仅没有因此而破灭,反而使50年后登极的拜占庭皇帝更强烈地感受到恢复君士坦丁大帝之辉煌的迫切性。于是,527年登上皇位的查士丁尼皇帝,便积极投身于实现“一个帝国、一部法典和一个宗教”的战略目标,对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实行了长达30余年的“光复”战争,并在他逝世之际,完成了再度使地中海变成罗马帝国之内湖的伟业。但是大规模战争,也致使帝国耗损巨大,先是希拉克略王朝的皇帝在7世纪上半期的对波斯战争中失利,丢失了耶路撒冷的“真十字架”(5)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431.;而后战胜了波斯人,志得意满地夺回了“真十字架”,却又很快在阿拉伯半岛新兴的阿拉伯人征服战争中一败涂地,致使7世纪末的帝国面临多方面危机难以自救。
除了战乱,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集中爆发,也成为“古代晚期”社会动荡和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早在“3世纪危机”前后,罗马帝国就先后爆发了“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虽然这两场瘟疫的具体伤亡情况已无法查证,但从史料零星记载及皇帝伽勒里乌斯死于后一场瘟疫的事实来看,其必定对帝国人口造成了巨大影响。之后的“查士丁尼瘟疫”当属3—8世纪地中海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次瘟疫了,对其情况的记载也最为详尽。据普罗科比记载,这场瘟疫“起初死亡的人数较低”,但之后死亡的人数不断攀升,再后来甚至上升到日均死亡5 000人,甚至有时会达到万人及以上”,“在掩埋尸体时,开始还可以参加亲人的葬礼,后来死者太多,导致全城处于混乱状态,很多家庭整户死亡,一些身份尊贵的人竟也因为瘟疫当中无劳动力可用而在死后多日无法掩埋。很多尸体被随意地扔进塔楼,等尸体堆满后再封顶,全城弥漫着一种恶臭”。(1)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 trans. by H. B. Dew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4, pp. 465-469.这场瘟疫在帝国肆虐四月有余,其中三个月为死亡高峰期,仅君士坦丁堡按平均每日5 000人,共90日计算,死亡人数就至少高达45万,帝国首都一时间成为死神横行的真正人间地狱。之后瘟疫周期性、多城市爆发,如史家阿加西阿斯记载了558年瘟疫第二次爆发的情况,“那一年初春,瘟疫第二次来袭,肆虐帝国首都,夺取大批居民的性命,并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2)Agathias, The Histories 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trans. by J. D. Frendo,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1975, p. 231.。
与瘟疫相伴的还有地震的破坏,据学者唐尼统计,“自324年至1453年,拜占庭帝国1100余年的历史中,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的大小地震共55次,仅6—8世纪就有15次”(3)G. Downey, “Earthquake at Constantinople and Vicinity AD 324-1453”, Speculum, 1955 (4), pp. 597-598.,525—740年间,大约每18年就有一次大地震,如526年帝国第三大城市安条克的地震破坏性就是极大的,“所有房屋与教堂都被震塌,城中的精美物品都被摧毁”(4)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p. 264.,“那些没有来得及逃离房屋的都成为了一具具尸体”(5)John,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Vol. 90), trans. by R. H. Charl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916, p. 137.,“死亡人数约有25万”(6)John Malas, (Vol. 18).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2.。而之后557年君士坦丁堡的地震中,“不仅毁坏了城中两座城墙——君士坦丁城墙和狄奥多西城墙,还摧毁了大量的教堂,特别是赫布多蒙教堂(Hebdomon)教堂——即圣撒母耳教堂(St.Samuel)和周围的一些教堂……该地震带来的毁灭无一可以幸免”(7)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p. 339.。
可见,战争、瘟疫和地震等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已经成为帝国“古代晚期”的帝国社会常态。因而就连查士丁尼大帝的辉煌统治时期,也被吉本批评:“战争、瘟疫和饥荒三重重灾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臣民的头上,人口数量的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的一个极大污点”,(8)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0页。其不仅直接导致帝国人口锐减、经济衰微和政局动荡,更重要的是对帝国百姓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战争、瘟疫和地震中,百姓直面的是死亡的威胁、流离的生活和不断的苦难,看着周围之人大批去世,城市境况日益破败,饥荒生活逐渐临近,百姓内心的恐慌、精神上的无助,在当时的史家记载中得到生动描述,例如在551年的亚历山大大地震后,阿加西阿斯记载道,“所有居民,特别是年老之人都被眼前的境况惊到了……大家聚集街头,纷纷陷入到因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所引发的极度恐慌中”,(1)Agathias, The Histories 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trans. by J. D. Frendo, p. 48.而在559年君士坦丁堡的大灾之后,不仅引发了“人们突然闯进商铺和面包铺进行哄抢,仅3个小时,城中的面包就被抢光”(2)武鹏、刘榕榕:《六世纪东地中海的地震灾害造成的精神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80页。情形的出现,还导致“谣传查士丁尼已经去世,民众陷入恐慌,官员信以为真,整个城市一度陷入极度混乱”(3)武鹏、刘榕榕:《六世纪东地中海的地震灾害造成的精神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78页。的局面。
面对生命的无助,一些民众也试图向帝国的古典诸神求助或者试图去在希腊哲学理念中寻找应对之术。但是当灾难来临时,诸神的代言人、异教的祭司,却无法对灾难发生的缘由做出任何解释,更甚之,许多祭司与宦官、富人竟然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迅速逃离疾疫流行之地,留下陷于更加恐慌之中的平民百姓于不顾;而希腊哲学所强调的非个人过程和自然规律,也无法解释死亡突然不加选择地降临到老人孩子、富人穷人、好人坏人身上的原因。古代世界的神明在民众迷茫、恐惧与面临生死边缘逐渐失去了其往日受尊崇的地位。基督教的“博爱”与“互助”精神、今生与来世的图景以及行医布道的慈善救助活动,却为帝国百姓将精神上的疑惑指明了方向。
对于自然灾害和社会激荡,基督教拥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在其看来,当时瘟疫等灾害的发生,均是因为罗马人做了错事、行了恶举所应得到的报应,例如在安东尼瘟疫爆发时,教会史家奥罗西乌斯从基督教的视角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这是对马克皇帝在高卢对基督徒进行迫害的惩罚,而对于这种惩罚,也并非不能得到解决和规避,只要民众能努力“赎罪”便可以化解。所以,《圣经》中明确表明“义人必因信而生”(4)《新旧约全书·新约·罗马书》(中文版),第168页。,要求人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5)《新旧约全书·新约·罗马书》(中文版),第82页。,这里不仅对生死的原因做出了基督教神学的“合理”解释,为死后的人描绘了“来生”的图景,更为现世的人指明了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出路。因此,在这种教义思想的指引下,基督教会在实践中将自己打造为关爱弱者的庇护所,6世纪后其慈善行为更加普遍,收容所、医院、孤儿院、救济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开始建立,而民众对于基督教的依赖和信任亦愈发强烈,据文献记载,533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大地震后,“所有城中百姓都聚集到君士坦丁广场进行祈祷”,(6)武鹏、刘榕榕:《六世纪东地中海的地震灾害造成的精神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78页。“安条克地震后数日的基督升天节,幸存的民众也聚集到教堂前,在教士的带领下,进行祈祷,以求上帝的拯救和获得心灵的安慰”。(7)John,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Vol. 90), trans. by R. H. Charles, p. 137.
因此,自313年的“米兰敕令”正式获得合法地位,392年获得国教地位后,4—8世纪间,作为皇帝稳定民心、抵御外敌的助力,民众抚慰心灵、医治创伤的药剂,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在皇帝的支持和民众的追捧下一路扶摇而上,至717年伊苏里亚王朝建立,利奥三世登基后,已经完成了对帝国的基督化改造。但是利奥是在阿拉伯军队一路北上,日日进逼君士坦丁堡、帝国政权风雨飘摇的危难之际登上皇位的,作为对支持他上位的元老贵族势力的承诺,他必须阻止敌军于首都之外,稳定帝国政权、救助天灾、安定民心,而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解决长期以来天灾人祸引起的帝国民众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的问题。关于此,从726年利奥三世发起“禁止偶像崇拜”的禁令也可看出端倪,当时塞拉岛(Thera)发生了火山喷发,影响地区甚广,皇帝认为这是因圣像崇拜惹怒上帝所致,为了平复社会的混乱,安抚上帝的愤怒,利奥三世下令将都城“铜门”上的基督像取下,禁止偶像崇拜,恢复昔日十字架崇拜。但是令皇帝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要禁止圣像崇拜的禁令,不仅没有达到稳定民心的作用,还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混乱与反抗,帝国的民众的思想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
在直接干预民众信仰无果的情形下,利奥三世也注意到要真正实现帝国民众思想的稳定,还需借助立法制度,特别是要着手运用罗马帝国的立法传统修复因社会动荡造成的立法颓废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解决在一个希腊化的帝国如何有效地将当年查士丁尼钦定的拉丁文法典付诸实施的问题。换言之,在现实社会的需求下,刚刚稳定不久的帝国,需要利奥三世在司法领域引入基督教的原则与精神,实现法典的基督教化和完全的希腊化,达到慰抚民心,稳定帝国秩序的目的。
于是利奥三世皇帝和他的儿子、共治者君士坦丁五世于740年决定制定新的、便利可行的基督教化的希腊文法典。他在《法律选编》的前言中突出了自己的意向和改造传统立法原则的决心,并在全文中多处直接引用基督教的“公平”与“正义”理念,要求法官以基督的博爱精神执法立威。对那些蔑视公正和不义的法官,则引用《旧约·诗篇》第58章第1—2节中的内容进行严厉质问,“世人哪,你们所说之词,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暴(εi αληθwς aρα δικαιοσuνην λαλεiτε, εuθεiας κρiνατε τaς οi υiοi τwν aνθρwπων. καiγaρ εν καρδia aνομiαν εργaζεσθε εν τn γn, aδικiαν αi χεiρες ὑμwν συμπλεκουσιν.)”,对于卖官售爵者也援引《德训篇》第7章第4—6节中的内容进行告诫:“不要向上主求做大官,也不要向君主求荣位;不要谋求做大官,怕你无力拔除不义(μήτε παρaκυρiου nγεμονiαν ζητεiτωσαν, μήτε παρa βασιλεως καθεδραν δoξης αiτεiτωσαν, μήτε γiνεσθαι κριταi προαιρεiσθωσαν, aδικiας οuδαμwς εξαiρειν iσχuοντες)”,所以皇帝要求任职的法官“切莫据表象来断案,要据公正判断是非(μn κρiνετε κατ’ ὂψιν, aλλa τnν δικαiαν κρiσιν κρiνατε,πaσης δωροληψiας aπεχεσθαι δiκαιον.)”。(1)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pp. 68-70.此外,《法律选编》中还进一步落实了“仁爱”的举措:如对死刑进行了严格限制,废除了一些严酷的刑罚。可见,在经历了基督教的快速融入发展及长期动荡混乱的时期后,公正、正义与博爱无疑必然会成为帝国臣民安定内心,追求未来的重要精神药剂,在此公正与博爱是融为一体的,在当时的境况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若无前者,后者也只能是虚无不实的概念。
总之,在“古代晚期”社会急剧变化、百姓思想极度混乱的时期,基督教在与诸多异教信仰相互争论和斗争中,完成了自我理论与当时社会背景及民众心理需求的紧密结合,具有了抚慰恐慌中百姓的功能,正如陈志强教授对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中所言,“广泛出现的社会恐惧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人们对现存政治和国家看法的改变,进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的改变,使人们更加笃信‘上帝’”,《法律选编》最终完成法律的基督教化,正是利奥三世皇帝应社会之需,用“上帝”之信仰来抚平社会动荡的一种手段和表现。
四、余 论
行文至此,本文以《法律选编》为中心,基本上完成了对早期拜占庭立法基督教化的生成逻辑的考察与分析,对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上有王权加强的需要,自下有民众慰藉的需求,上下二元的相互助力,促成了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形成路径逻辑生成。
首先,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形成,与基督教所含有的“君权神授”的思想符合了3—8世纪皇权强化的趋势有很大关系。自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罗马的帝国建制日益明显,加强王权和构建一套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统治体系成为帝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期间利用宗教神化王权也成为各代皇帝的惯用手段。在帝国早期古典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屋大维担任“大祭司”之职将自己塑造为诸神的代言人和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威,便开启了这一进程,之后历史上的多次基督教迫害,实质上是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引起的皇帝对个人权威丧失的担心所致。但是随着帝国模式渐成和基督教的日益完善,皇帝发现多神崇拜已经无法满足帝国统一思想的需求,而讲求“一神”和“君权神授”的基督教却对王权加强和统一思想大有裨益,于是从311年的“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颁布后,皇权与教权紧密扶持与配合构成了3—8世纪拜占庭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利奥三世登基以后,面对帝国的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也希望利用教权强调自身权力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于是在《法律选编》的序言开篇便说明这部法典是“以圣父、圣子、圣灵,虔诚的皇帝利奥与君士坦丁之名”颁布的。这与查士丁尼《法学阶梯》的开篇“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将神与人共置一处,更加凸显“君权神授”的意味,《法律选编》基督教化与其说是基督教发展的顺势结果,倒不如说其“君权神授”的思想和“一神教”的形态,适应了8世纪王权加强的社会需求。
其次,“古代晚期”因瘟疫、地震及战乱所引发的社会动荡,需要立法的基督教化来抚平社会和民众遭受的创伤。“古代晚期”的帝国经历了3世纪危机、蛮族入侵、大瘟疫和大地震等诸多天灾人祸,导致帝国人口急剧下降、疆域面积不断缩小,特别是灾难中,面对死亡的威胁和生活的困苦,传统的古典宗教信仰无法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做出合理的解释,帝国民众陷入到极度恐惧和信仰危机中,但是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讲求互助与博爱、公平与正义、今世与来世,赋予死亡以生命的意义。因此,大灾大难面前,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适应于充斥着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乱世思想和情感体系,其完整理论阐释及实践上的善举——哪怕仅是最基本的护理,都可能极大地减少死亡率——都会使民众在相互依存间获得温馨感觉,获得在其他信仰中无法获得的希望,对受到重创之后的民众具有抚平创伤、维护稳定的功效。因此,利奥三世的《法律选编》引用了大量的基督教仁爱与公正原则,要求司法公平和追求刑罚人道,其目的就是希望以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安抚民众的情绪,重塑百姓的信仰,这是民心之所向,更是社会之所需。
正是在“君权神授”理论的支持下和“安定民心”现实的需求下,早期拜占庭法律一步步将基督教的思想与原则融入到了法典之中,至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法律选编》的颁布最终完成了这一过程。该法典以基督教化的形式,担起了完成对帝王权力加强和抚平民众心理创伤的使命,也因此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第一部官修基督教的法典,拉开了中世纪拜占庭立法的序幕,而其在稳定社会局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之后马其顿王朝“黄金时代”盛世局面的出现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