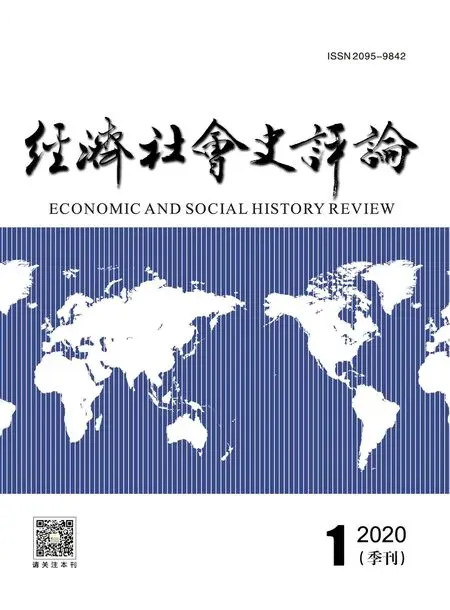卡尔马联盟:北欧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起点
刘俊豪
卡尔马联盟(the Kalmar Union)是中世纪晚期丹麦、瑞典、挪威在丹麦王室统治下结成的联盟,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联合。①当时芬兰从属于瑞典,冰岛被挪威征服,所以这一联盟具有地区整体性。卡尔马联盟的建立保障了北欧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效地遏制了德意志汉萨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势力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扩张。其后,联盟共主埃里克七世(Erik VII)又分别与英、德两国联姻结成了两个重要同盟,增强了卡尔马联盟在欧洲的影响力。但是,联盟隐含的离心倾向和丹麦王室的一些政策性失误导致其他王国的强烈不满,最终在汉萨同盟的挑唆下,瑞典单独拥立贵族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I Vasa)为国王,宣告了联盟的解体。卡尔马联盟作为一个北欧国家联合体的尝试,其历史意义不容小觑。
北欧国家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中就把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视为欧洲六大民族之一②利奥波德·冯·兰克:《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付欣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而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也说,“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虽然加入较晚,然而这一方面完全无关紧要”③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p. 50.。汤普逊(J. W. Thompson)曾指出卡尔马联盟成立后很大程度上排挤了汉萨同盟在北海、波罗的海的势力。④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近年国外学者更有一些新的认识,如斯韦勒·巴奇(S. Bagge)认为卡尔马联盟的成立并非是国家形成的倒退,因为它推动了一种新型国家形态——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进步;他还提出现代国家是君主制的衍生品,也是教会的衍生品,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尤为明显。①Sverre Bagge, Cross and Scepter: The Rise of the Scandinavian Kingdoms from the Vikings to the Reformation,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Introduction.《新编剑桥中世纪史》认为卡尔马联盟是北欧国家为了对抗汉萨同盟在北欧的商业贸易垄断和政治干涉而成立的。②Christopher Allmand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71-706.《剑桥斯堪的纳维亚史》论述了14世纪末北欧地区局势的急剧变化使得三个北欧王国走向联合,而随着1523年瑞典的独立,中世纪晚期北欧三国联合的卡尔马联盟时代最终结束。③Knut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83-770.国内也偶尔有学者关注卡尔马联盟问题。④敬东主编:《北欧五国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5—79页;孙培培:《卡尔马联盟的历史演进——从14到16世纪》,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本文聚焦于卡尔马联盟的历史发展脉络,以瑞典和丹麦为主要考察对象,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几个国家中,只有瑞典和丹麦在几个世纪里历经了建构独立国家的过程⑤Tim Knudsen and Bo Rothstein, “State Building in Scandinav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2 (January 1994), p. 204.,重点则论述卡尔马联盟对北欧王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影响。
一、“前卡尔马联盟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1.汉萨同盟与瑞典的混乱政局
早在吕贝克(Lübeck)建城起,德意志商人就与瑞典建立了商业联系。13世纪中期,汉萨商人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经营手段盘活了瑞典经济。如吕贝克人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控制了贝格斯拉根(Bergslagen)⑥贝格斯拉根位于瑞典中部地区,当地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的采矿业。德意志移民逐渐在瑞典商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瑞典经济随之对汉萨同盟产生了依赖。到13世纪末,瑞典国王不得不通过给予特权、免除义务等优惠条件迎合德意志商人。德意志人“相对充足的资本和使用的大商船,使他们比瑞典商人更具优势;不仅在哥特兰地区,在瑞典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⑦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1250年以降,哥特兰(Gotland)岛上的主要城市维斯比(Visby)已由德意志商人控制。14世纪初,吕贝克完全控制了哥特兰岛,主导着斯德哥尔摩一线的贸易。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瑞典国内政局混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权,大贵族相互倾轧,无法全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
中世纪瑞典政治的特点是缺乏一种稳定的王位继承秩序,导致贵族轮番把控政权。1317年,瑞典贵族利用国内爆发的大规模反国王浪潮攫取了政权,两年后在乌普萨拉(Uppsala)推举年幼的马格努斯·埃里克松(Magnus Eriksson)为瑞典国王。他们“选择马格努斯·埃里克松的一个因素是,国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亲政,这将给显贵们提供巩固自己特权的机会”。①Birgit and Peter Sawyer,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irca 800-1500,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81.他们的利益在随后起草的一份具有宪章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得到保证。条文确认了贵族和教会的特权,提出君主征收新税必须得到政务会(Council of realm)的同意,强调瑞典国王要由选举产生。成年后的马格努斯努力扩大王权,与贵族矛盾激化,1363年贵族们合力将国王驱逐。但是,国王在位时将幼子哈康(Hakan Magnusson)与丹麦公主玛格丽特(Margrete I)联姻,“这一举措为长期的王朝冲突提供了解决办法,并有利于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未来都联合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②尼尔·肯特:《瑞典史》,吴英译,第29页。。这为卡尔马联盟的建立埋下一支伏笔。
2.丹麦与德意志在波罗的海的较量
丹麦与德意志对波罗的海的争夺由来已久。斯堪尼亚(Scania)在13世纪后期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贸易区域,吕贝克人利用对盐准入市场的垄断逐渐控制了此地的贸易。“奇怪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中最强的丹麦,却是最后一个针对日耳曼贸易采取保护性立法的国家——之所以奇怪是因为,丹麦比挪威更早感觉到日耳曼商业特权的影响。”③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王春法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
到13世纪后半期,丹麦王权衰弱,“不能应对贵族和高级教士日益膨胀的野心”④Michael Jones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 c.1300-c.14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21.。在1282年召开的尼堡(Nyborg)会议上,国王埃里克(Erik V)被迫与贵族签署了一份法令,宣布贵族可以组成政务会为王室提供政策性建议。从此,丹麦贵族就可以合法地限制君权,其势力更加膨胀。直到丹麦历史上伟大的瓦尔德玛四世(Valdemar IV)在位时,国王才通过教会的支持、收回王室领地和给予部分城市特权的方式逐渐增强了王权。瓦尔德玛四世为恢复昔日丹麦在波罗的海上的强盛地位,从14世纪60年代起,他收回斯堪尼亚、攻占维斯比,这威胁到了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的利益。汉萨城市为继续其垄断地位,在1367年组织了科隆军事政治同盟(the Confederation of Cologne),于1370年彻底击败丹麦,并与之签订了《斯特拉尔松和约》(Peace of Stralsund),规定丹麦将斯堪尼亚租给汉萨同盟15年,允许同盟船只在松德海峡自由航行,汉萨同盟有权干预丹麦的王位继承。此和约使汉萨同盟完全控制了这一区域的贸易,主导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的贸易集市。“其实汉萨同盟城市对整个波罗的海地区保持一种严格的政治、经济霸主地位,实际上将波罗的海地区当作它们的‘后花园’,只能接触汉萨同盟的商人。”①克努特·耶斯佩森:《丹麦史》,李明、张晓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页。出于对吕贝克及德意志势力的恐惧,三个王国均有了结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指玛格丽特——引者注)想把这三个王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存在。”②Knut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p. 686.
3.北欧联盟的建立
1363年,瑞典贵族操纵政务会选举梅克伦堡公爵的次子小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 the younger of Mecklenburg)③他是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 of Mecklenburg)与马格努斯的妹妹之子。为国王,在汉萨同盟的支持下,小阿尔布莱希特随之顺利入主斯德哥尔摩。“阿尔布莱希特国王向他的德意志同胞授予了重要封地和职位,这让瑞典贵族无法容忍,并逐渐出现了强大的反对派。”④Vivian Etting, Queen Margrethe I (1353-1412)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dic Un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04, p. 52.而且小阿尔布莱希特还要求贵族归还他们之前从王室手中非法夺走的财产,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瑞典贵族转而向丹麦的玛格丽特女王求助,他们认为三个王国在一个共同的君主统治之下会有利于保持自身特权。1389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在阿斯勒战役(the battle of Åsle)中击败了小阿尔布莱希特,她被三个北欧王国拥戴,斯堪的纳维亚在中世纪晚期达成联合的基础由此奠定。
卡尔马联盟是以王朝联姻、五国⑤这一联盟在地域上涵盖了今天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等国家,当时是丹麦、瑞典和挪威三个主要王国的联合。共主的方式建立的。1389年,丹麦和挪威的贵族们选择玛格丽特作为两国女王后,瑞典也如法炮制,授权玛格丽特提名未来的国王,玛格丽特选择其养子——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Erik of Pomerania)作为继承人。1397年,埃里克作为三个王国共同的统治者在瑞典小城卡尔马(Kalmar)加冕,即埃里克七世(Erik VII)⑥丹麦世系为埃里克七世,在瑞典则称埃里克十三世。。“6月17日,包括隆德和乌普萨拉大主教在内的三个王国的贵族以及教士,都目睹了埃里克的加冕。”⑦Michael Jones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 c.1300-c.1415, p. 722.至此,北欧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治联合体——卡尔马联盟正式诞生。盟约规定:各王国应保持各自主权;各国按照本国原有法律统治,在任何一个国家被判处犯罪的人,在其他国家也被视为罪犯;如果其中一个王国与别国处于战争状态,其他盟国也必须全力援助。另外,盟约还提出“每个王国都应保留自己的法律、习俗、参议会和各种特权;最高官员应从当地人中挑选”⑧Paul C. Sinding, History of Scandinavia: From the Early Times of the Norsemen and Viking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udney and Russell Publishers, 1859, p. 148.。
二、卡尔马联盟的历史演变
1. 联盟成立初期的成就
“联合起来的北欧王国已成为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因素之一。”①Knut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p. 728.卡尔马联盟的版图覆盖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有无数个岛屿,如冰岛、格陵兰岛等。玛格丽特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无冕之王,实际上在其有生之年都对整个联盟有着行之有效的控制。玛格丽特致力于中央集权,建立了高效的中央财政管理体系,聚敛了大量的财力,1408年从条顿骑士团手中赎回了哥特兰岛。同时,她限制贵族力量,增强王权,“在丹麦,她禁止兴建私人城堡。……她尽量减少对教士和贵族的免税地产,当然这一做法受到反对。在地契被彻查后,大量的土地被划归王室所有”②Christopher Allmand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VII, c.1415-c.1500, p. 676.。这显示了联盟成立初期君权得到强化,1398年梅克伦堡人归还了斯德哥尔摩,诺尔兰和芬兰也不再反抗,而一直抵抗的哥特兰人也于1408年最终屈服,整个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似乎安静了。更重要的是,它的成立严重地削弱了汉萨同盟的势力。“女王强迫同盟放弃对丹麦的直接政治控制,交出同盟占据的堡垒,废除同盟实行的税收。同盟不得不接受其在丹麦水域的巨大损失。当同盟向她找麻烦时,女王便暗中支持海盗袭击他们,报以双倍的骚扰。”③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249页。这个被丹麦人世代崇敬的女王以勇敢对抗外敌著称,直到临终她也没有放松对汉萨同盟的打击。
为了巩固卡尔马联盟的政治影响力,埃里克亲政后,通过联姻结成了两个重要的同盟,一是他本人迎娶英国公主菲利帕(Philippa),再是其妹妹卡特里娜(Katerina)嫁给神圣罗马帝国王子巴伐利亚的约翰(Johann of Babaria),“这些行动有助于更牢固地强化他的地位,使他跻身欧洲势力最强的统治者之列”④尼尔·肯特:《瑞典史》,第31页。。卡尔马联盟及政治联姻无疑对中世纪晚期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2.丹麦霸权的出现
北欧大联盟建立起来后,由于丹麦国力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为强大,更兼女王玛格丽特精明强干,在她实际统治的十几年里,政权向中央集权方向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她派遣直接听命于君主的行政官员负责推行国家行政管理,王室权威逐渐增强。在15世纪初,玛格丽特和其继任者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都时常把丹麦利益凌驾于其他王国之上,丹麦王权压制了各地贵族,“在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一连串的统治者都努力在丹麦建立控制权,并说服挪威和瑞典的大贵族接受他们的统治”⑤David Kirby,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Modern: The Baltic World 1492-1772,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3, p. 42.。“她在瑞典建立了强大的财政管理:税收被简化、永久化,估价都采用货币而非实物。在那里,国王地区代表通常从丹麦更低层的贵族中选拔。最后,大约在1400年,她完成了对地产的大规模回收——这些地产都是皇室在14世纪下半叶晚期在丹麦和瑞典失去的。”①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326页。显然,这伤害了瑞典王国的利益。
埃里克国王继承了女王玛格丽特的货币税改革政策,这固然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与实物税相比,货币税收却给瑞典民众增加了实际的负担,同时埃里克国王实施的货币贬值政策大大损害了瑞典的对外贸易,这是后来瑞典爆发起义的重要原因。另外,石勒苏益格ˉ荷尔施坦因问题也成为丹麦与各方争端的焦点。石勒苏益格原属丹麦,但是由于与德意志互相通婚以及封建采邑制的影响,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埃里克亲政后意图强制回收该地,召开政务会讨论石勒苏益格问题,并作出决议,“石勒苏益格公爵由于反抗过埃里克国王,他的属地被没收,重新归属丹麦”②Christopher Allmand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p. 679.。石勒苏益格领地归属丹麦使得后者实力大大增强,引起了汉萨同盟的恐慌,双方发生战争。汉萨同盟封闭了斯堪的纳维亚各港口,战争不可避免地连累了瑞典,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员损失,同时也阻碍了该地原材料与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瑞典民众苦不堪言,反抗已不可避免。
从深层次来说,卡尔马联盟初期实行的中央集权是由政治上的独裁体制导致的,不是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所以这种中央集权或者王权膨胀只能靠强有力的君主来维持,一旦出现王位变更或者政策失当就容易出现动乱,1434年瑞典王国大起义便是例证。
3.卡尔马联盟后期的动荡局势
1434年6月,在小贵族恩格尔布莱克特松(Engelbrektsson)领导下,瑞典各阶层联合发动了一场反丹麦大起义。起义有矿工、商人和大量平民参与,同时得到本地教会和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后来瑞典政务会也联名响应。1436年,起义军领导权转移到卡尔·克努特松(Karl Knutsson)手中,1438年他在政务会得到广泛支持。“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贵族加入了叛军,他们一起推翻了埃里克国王,先是丹麦和瑞典(1439年),最后是挪威(1442年)。”③Sverre Bagge, Cross and Scepter: The Rise of the Scandinavian Kingdoms from the Vikings to the Reformation, p. 251.随后丹麦政务会支持了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III),1440年克里斯托弗即丹麦王位,次年也于瑞典加冕,1442年在挪威他也得到了拥护,联盟得到恢复,而卡尔·克努特松则以补偿芬兰土地的方式被强制流放。1434—1439年瑞典大起义是一场瑞典各阶层参与的反丹麦、反压迫斗争,各个阶级不同程度地团结起来推翻了埃里克的专制统治,给瑞典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起义中瑞典民族意识开始萌发。
1442年,克里斯托弗颁布法典规定,瑞典城堡的土地应该授予政务会及其支持者,不应给予德意志人,这有助于瑞典国土的完整。1448年克里斯托弗逝世,丹麦政务会推举奥尔登堡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I)为国王,1449年在挪威政务会也承认了他,而之前被流放的卡尔·克努特松却谋取了瑞典国王(尽管他仍想做北欧国王),联盟再次出现二主。到1471年,克里斯蒂安一世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准备彻底收服瑞典,但不幸在布伦克贝格战役(the battle of Brunkeberg)中被击败。这次战争使丹麦再也无力对瑞典进行实质性控制,瑞典进入了斯图雷(Sture)家族掌权时期。到1515年,时任瑞典摄政(regent)的小斯图雷(Sten Sture the Younger)与乌普鲁萨大主教发生严重冲突,1517年小斯图雷及其盟友被开除教藉。这时丹麦王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II)趁机出兵瑞典,经过几次苦战,到1520年才击败小斯图雷的军队,得以重新入主斯德哥尔摩,并于当年11月加冕为瑞典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为彻底根除瑞典贵族的分裂势力,制造了“斯德哥尔摩惨案”(Bloodbath of Stockholm),“他在加冕盛宴那天,杀死了所有他怀疑反对自己的那一派贵族”。①Anders Bure, A Short Survey of the Kingdome of Sweden, London, 1632, p. 71.斯德哥尔摩事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惨案消灭了大批实力派贵族,导致瑞典贵族力量受到很大损害,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为后来瓦萨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瑞典民众对丹麦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瑞典人再也无法融入联盟之中。三年后的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被拥立为瑞典国王,联盟解体。
三、卡尔马联盟与北欧王国的转型
卡尔马联盟于1397年正式成立,其间分分合合,终于以1523年瑞典独立为标志,宣告寿终正寝。虽然挪威还继续留在联盟内,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丹麦的属地,而芬兰则跟随它的宗主国瑞典脱离了联盟,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卡尔马联盟此时已经解体了。
卡尔马联盟对北欧现代国家转型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民族贸易得到关注,本土商人阶层崛起。以往汉萨同盟能在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畅行无阻,从侧面反映出斯堪的纳维亚本地商人的弱小。卡尔马联盟存续期间,总体上比较注意保护本地商人的利益,商人团体的力量渐趋壮大,这使得联盟政府能够制定积极的财政贸易政策,以对抗汉萨同盟的斯堪的纳维亚政策,体现了北欧国家对民族贸易的关注。联盟出台了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立法,直接针对外国(主要是德意志)商人的商业垄断,“保护主义立法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末的挪威和瑞典以及14世纪中叶的丹麦,然而直到大约1400年联盟形成后,这项立法才得到认真落实”②Anders Andrén, “State and town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8,No. 5 (September 1989), p. 600.。正是卡尔马联盟增强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整体力量,才使得保护民族贸易的立法得以落实。在挪威,卡尔马联盟把它从中世纪虚弱的政体中解脱出来,尽管后来它仍长期处于丹麦的统治下,但在历次反丹麦斗争中,挪威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同时挪威本地商人逐渐壮大,开始往返于国际贸易,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避免了外敌利用经济封锁达成窒息挪威本土生活的目的,这是一个历史进步。在丹麦的支持下,早已沦为汉萨同盟据点的卑尔根也伺机收回一些汉萨商站占有的特权。1423年,联盟国王埃里克下令在松德海峡两岸设点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行税,并不惜为此与汉萨同盟开战,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汉萨同盟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垄断出台的,反映出联盟自成立以来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及整体实力的增强。丹麦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在位时期,曾利用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力量来牵制大贵族以建立集权统治,“他鼓励市民从事对外贸易,改善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条件,甚至还擢用市民出身的人到各级行政部门直至中央机关做官”①敬东主编:《北欧五国简史》,第31页。。“除此之外,他的计划中还包括设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商业同盟,希望在荷兰人的协助下把汉萨同盟商人排挤出去。”②安德生:《瑞典史》,苏公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73—174页。这些措施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即使到卡尔马联盟解体之后,保护地区工商业的做法在近代早期瑞典和丹麦也被保留了下来。
其二,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意识逐渐觉醒。15—16世纪以降,西班牙、英法等国王权得到加强,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北欧国家的政治走向。“直到15世纪,欧洲巩固王权的发展趋势才导致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经济政策的出现——它们受到一些模糊的社会目的的影响。但是,当这些真的发生时,汉萨对国家贸易的垄断就成了引起政治争端的主题。”③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336页。北欧整体民族意识躁动,驱使它们走向联合去应对汉萨同盟的贸易垄断和政治经济控制。另外,联盟盟主埃里克国王对城市贸易实行保护性政策也并没有随他之后被驱逐而中断,而是在后来的贵族统治中得到延续,丹麦城市市民力量的不断增强,当然这一政策也有利于下层群众。15世纪70年代,丹麦王克里斯蒂安一世下令禁止德意志人在丹麦永久居住,并取消了丹麦行会,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丹麦民族意识的萌动。更为关键的是,当卡尔马联盟解体过程中,具体说在其他民族反抗丹麦王室控制的过程中,“丹麦人”也和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开始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正像近代瑞典史正常情况下是从1523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与卡尔马联盟决裂开始,近代丹麦史也可以从这个时刻开始。”④克努特·耶斯佩森:《丹麦史》,第10页。丹麦能从一个北欧混合体转变成现代单一的民族国家,卡尔马联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催生了丹麦的民族意识,使丹麦开始了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漫长历程。卡尔马联盟的解体、汉萨同盟的衰落以及新航线的转移,使得波罗的海的位置越来越重要。1523年北欧王国分家后,位于丹麦境内的厄勒海峡成为波罗的海主要贸易航道,这一地理位置使丹麦成为波罗的海守门人,对它未来的发展起着重大影响。当然,联盟的最终瓦解还是要直接归结于瑞典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瑞典人对联盟统治者的不断反抗逐渐发展为一种瑞典民族认同意识”①Tracey R. Sands, “Saint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Kalmar Union Period: The Case of Saint Margaret in Tensta”, Scandinavian Studies, Vol. 80, No. 2, (Summer 2008), p. 141.,“联盟主义已被瑞典的国家主义所击败”②Michael Roberts, The Early Vasas: A History of Sweden 1523-16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p. 23.。北欧联盟解体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为增强王权以应对丹麦王室和其他外部威胁,在北欧率先进行了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这相应地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复兴。1526年,《新约》的瑞典文本首次发行。“无论是从宗教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瑞典语的《新约》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③N. K. Andersen, “The Reformation in Scandinavia and the Baltic”, in G. R. Elton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I, 1520-15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8.在乌普萨拉大主教劳伦提·彼特里(Laurentius Petri)的组织下,瑞典文的《新旧约全书》在1541年正式出版。“上帝的话语必须用母语向人们宣讲以及应该让其有机会用方言阅读圣经的原则,有助于在欧洲偏远和隐秘的地区创造和培育新的书面语言。”④E. I. Kouri, “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Sweden and Finland c. 1520-1560”, in Ole Peter Grell (ed.), The Scandinavia Reformation: 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 to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7.此后,各阶层的识字者都可以通过本地语文去阅读圣经了,这是推动瑞典民族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瑞典语在民族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民族语言的普及是瑞典民族意识充分觉醒的生动写照。
其三,绝对主义王权在夹缝中生长,并逐渐获得本国民众的认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几个国家和波兰,中世纪中期的几个世纪几乎没有带来王权的巩固,反而发生了许多政治上的混乱。”⑤朱迪斯·M. 本内特、C. 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10页。实际上,即使是到卡尔马联盟成立之时,也没有确立起世袭的王位继承制度,玛格丽特女王和埃里克国王都没有取得对贵族的绝对优势。“虽然继承人是从王室中选出的,但是由三个王国的政务会任命,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他的政府;玛格丽特女王可能对这一决定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传统上确实只有挪威拥有世袭君主制。”⑥Vivian Etting, Queen Margrethe I (1353-1412)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dic Union, p. 99.1523年,古斯塔夫·瓦萨带领瑞典彻底脱离联盟,并于1528年在乌普萨拉大教堂加冕,成为瑞典第一位世袭君主,随后他正式确立了世袭制度。“古斯塔夫在这一领域中最大的成功就是使1544年在韦斯特罗斯(Västerås)召开的国会接受了以下原则:从此以后,君主将不再由选举产生,而由瓦萨家族世代相袭。”⑦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王位世袭制的现实意义是能够巩固主权国家自身的稳定,因为以往推举制下的王位继承很容易造成国家政治的混乱无序。对外方面,瓦萨能够在对丹麦的反抗中获胜,跟汉萨同盟的援助是分不开的。“但是,一当古斯塔夫·瓦沙登上王位,便与曾经帮助过他的吕贝克人断绝关系,宣称‘瑞典王权作为汉萨人经商对象的时间太久了’。”①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250页。到16世纪30年代,随着瓦萨地位的巩固与瑞典国力的增强,他彻底放弃了吕贝克的支持,转而发展瑞典自身的力量,迅速将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建立起来。在瑞典历史上,瓦萨君主政府是第一个足够强大、能够有效抵抗吕贝克的政权,这正是卡尔马联盟留下的历史遗产。瑞典成功脱离卡尔马联盟为瓦萨建立绝对君主制度提供了条件,推动瑞典向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转型,其后进行的新教改革则进一步巩固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16世纪以后,北欧民众对各自的共同体产生了极大的民族认同,拥有了“归属感”。国王已经享有本国民众一定程度的自发效忠,这种“自发效忠”就是已经觉醒的民族意识,就是14—15世纪开始出现的民族向心力。实际上,王权走向集中的过程就是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四、余 论
从历史纵向发展来看,卡尔马联盟成立前夕,斯堪的纳维亚整体的民族意识已处于朦胧之中,而在联盟前期共同反抗汉萨联盟的控制、以及联盟后期各地反抗丹麦的专制统治时,北欧诸王国的民族意识已逐渐显现,由此推动了各王国向现代国家转变。从历史的横向发展来看,卡尔马联盟延续期间,正是欧洲许多地区民族意识逐步觉醒的时代,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正在形成,特别是西班牙、英国、法国等相继转型为强大的民族国家。北欧各国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与之相比则相对弱小,因此卡尔马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有力地维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共同利益,为各王国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同时促进各国内部结构的转型。
卡尔马联盟的成立是斯堪的纳维亚君主国在与德意志商人的斗争中,通过王朝间的联合赢得的政治胜利。从欧洲的大环境看,进入近代早期,旧的中世纪欧洲标准和价值观已经开始崩溃,中世纪普世天主国,即一个由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领导的普世理想破灭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领土边界相邻的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国家(state)逐渐取而代之。卡尔马联盟的终结并非孤立现象,和它具有相似性质、渊源颇深的汉萨同盟、条顿骑士团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在德意志强大一时的天主教会也大约于同时代轰然坍塌,这一切并非偶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尔马联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成立于斯堪的纳维亚各王国孱弱之时,面对汉萨同盟的威胁,各王国贵族通过妥协共同成立了一个联盟国家,抵制了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持了本地区国家的独立。“这三个大国的紧密联合成为维护它们安全的有力堡垒,并使它们在一个多世纪内成为欧洲体系的仲裁者;北方半岛的三个民族呈现出一条密切而统一的阵线,这使得他们能够蔑视任何外来国家的侵略。”②Paul C. Sinding, History of Scandinavia: From the Early Times of the Norsemen and Vikings to the Present Day, p. 149.
16世纪20年代,瑞典、丹麦已成长为可以单独应对外来干涉的君主制国家,商人阶层也陡然崛起,这一切都增强了北欧地区的综合实力。联盟成立之前,总的来说各国贵族势力相对强大,君权虚弱,中央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推行,无法采取一致措施应对外来威胁。而在北欧联盟时期,君主在夹缝中伺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为建立中央集权而盘旋于贵族之间,“这个联盟主要是为了对抗德意志商人和汉萨同盟的商业统治而宣扬王室权力的一种策略”①Tim Knudsen and Bo Rothstein, “State Building in Scandinavia”, Comparative Politics, p. 205.。联盟解体后,各国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体,这一点在瑞典表现得最为明显,有序的王位继承制度、君主治下的中央集权体制推动瑞典向现代国家大步迈进。“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个大北欧王国的迷梦已被粉碎;另一方面,卡尔·克奴特逊和几个斯图雷所怀抱的理想——在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手下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却实现了。”②安德生:《瑞典史》,苏公隽译,第178页。卡尔马联盟起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是将北欧各国从汉萨同盟的后院改造为具有现代特色的新型欧洲国家的摇篮,继而深刻地影响了北欧各国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