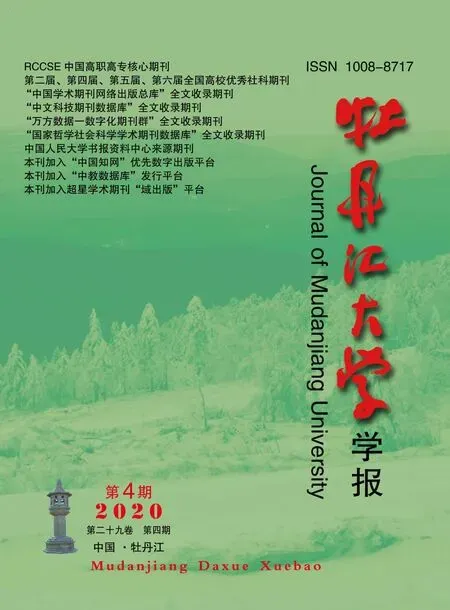乌帕马尼亚·查特吉《英语,八月》的反讽艺术
陈嘉豪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引言
印度英语文学作家乌帕马尼亚·查特吉(Upamanyu Chatterjee)1959年出生于比哈尔邦的帕特那(Patna),1983年从德里圣斯蒂芬学院(St.Stephen's College,Delhi)毕业后进入印度行政服务部门担任公职,现供职于印度石油天然气管理部门。1988年,乌帕马尼亚凭借处女作长篇小说《英语,八月》在文坛出道,特殊的公职身份及其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使他收获了大量读者的关注与喜爱。在30年的创作经历中,乌帕马尼亚陆续创作了《英语,八月》《最后的负担》(The last Burden)等6部长篇小说以及《非素食者的复仇》(The Revenge of the Non Vegetarian)、《刺杀英迪拉·甘地》(The assassination of Indira Gandhi)等中短篇小说。2004年,凭借《福利国家的乳房》(The mamma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一书,斩获印度文学院文学奖。2009年,乌帕马尼亚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以表彰其“对文学的卓越贡献”。
《英语,八月》副标题为“一个印度故事”(An Indian story),讲述了习惯大城市生活,并热衷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阿加斯特亚·森(Agastya Sen),毕业后成功进入印度行政系统工作。但作为新手,他被派往小镇马德纳(Madna)作为见习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岗前培训。马德纳是无数印度落后小镇的缩影:炎热、狭小、肮脏、无趣,充斥着对传统文化的狂热,初来乍到的阿加斯特亚与这里产生了可观的“排异反应”,他拒绝融入也无法融入马德纳,厌恶这里的人与事,始终对同事、邻居怀有戒备,用谎言隐蔽自己的真实想法,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背后隐喻的正是在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西化”印度人于这片古老土地的彷徨与迷茫。印度学者M·大卫·罗杰(M David Raju)指出:“乌帕马尼亚在讽刺及黑色幽默方面具有非凡的天分。”[1]《英语,八月》便是浸染这一特色的典型作品。小说主标题中“English”同副标题“一个印度故事”(An indian story)便鲜明地揭示出后殖民时代印度社会文化中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与融合,同时预示着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冲突与讽刺。
“反讽”(Irony)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滥觞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展,内涵日益丰富,米克认为:“反讽不仅具有不相同的形式,而且从理论上说,它也依然在发展之中。”[2]这就意味着反讽概念不仅存在于文学、艺术、哲学等广大领域,同时它的范畴仍在不断地革新与变化,即使今天我们也很难为反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针对小说中的反讽修辞,我国学者李建军在扬弃浦安迪、维科、弗莱等人观点的基础上,给出以下定义:
“它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它通常采取对照性的描写或叙述、戏拟、独特的结构、叙述角度的调整、过度陈述、克制陈述、叙述人评价性声音的介入等具体手法。”[3]
《英语,八月》中的反讽手法颇具匠心。微观方面,特殊视角的运用使阿加斯特亚对马德纳公职人员的抗拒在主人公的沉默中展现给读者,阿加斯特亚置身事外的态度使他对当地官员荒唐可笑的行径保持清醒的评价,实质构成了戏剧反讽;诸多隐喻在丰富作品内涵的同时,强化了作品中反讽的力度。宏观方面,批判印度行政体制与表现西化青年身份困境两大主题之间构成了整体反讽,体现了作者对当时印度社会发展前景的悲观看法。
一、戏剧反讽
米克在谈到剧场中的反讽时提到:“在戏剧里,人物必然‘不知’剧作家、导演、演员、情节和观众的情况,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反讽……似乎促成了某些‘内在话行动’的实现。”[4]并且,这一类型的反讽,“踪迹不限于剧院。”[5]《英语,八月》对印度官僚主义无情的戏谑与揭露来源于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同时也是这部作品最为精彩之处。但作者很少对所描写官员的行为进行直接的评价,他所做的只是展现与还原,并不滞于对价值取向的绝对把控。主人公阿加斯特亚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下属,仿佛参与其中却始终同各色官员保持距离,对他们的可笑行为保持清醒,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戏剧反讽。作家在这部作品中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聚焦于主人公阿加斯特亚的所见所闻及内心世界,使作者同角色站在了同一视角上。随着章节的推进,阿加斯特亚不断与不同人在不同的场景对话,构成了类似戏剧的篇章结构。不同于视角反讽,阿加斯特亚长期接受西式现代教育,体现出高于马德纳小镇官员们的智力与判断力。他善于做一个安静的听众,始终同这里的公务人员保持距离,排斥融合;而他初出茅庐的实习生身份又使这里的官场老手们在他面前可以肆无忌惮的暴露自我。阿加斯特亚被塑造成类似于古典戏剧中的“愚人”形象,或被迫或主动地隐藏起自己的认知与看法,以“装傻”的方式暴露当地官员的愚蠢,而自身则保持为一个看客,笑而不语。实际上马德纳官僚系统被建构成了一座“剧场”,外乡人阿加斯特亚同读者成为了“观众”。在他的面前,表面上官僚作为权力行使者的身份同私下中虚伪无耻的言行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产生反讽效果。
阿加斯特亚刚刚来到马德纳的税收局报道,他便感觉到自己同这里的格格不入,进而利用谎言为自己同这里的上司之间拉开了安全距离:
“坐在这三人之中,他被一种不真实感所包围。‘我并不像一个当官的,我在这干什么?我应该去做一个摄影师,一个电影制片人,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业,肤浅一点,世俗一点。’”
“‘你多大了,先生?’”
“‘二十八岁。’他实际只有二十四岁,这些人讨厌的脸勾起了他说谎的欲望。”[6]
一系列的谎言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等,“在场”的阿加斯特亚在谎言中藏匿自我,达成了事实上的“不在场”。阿加斯特亚得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与思考,官僚们不为人知的“内在行动”也随之映现。在马德纳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当地税收长官斯特瓦斯塔夫(Srivastav)最能体现当地官僚的无能可笑。这位税收局的官员利用一切机械迂腐的行为为自己树立官威,不停的发怒、大喊、摔砸文件,他的下属们沉溺其中,像敬神一般畏惧。而读者从阿加斯特亚的视角读出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位税收长官将完成的文件随手扔在地上,这些文件利用各自重量的优势发出抑扬顿挫的声响。不久,长官面前的公文大山慢慢被风蚀掉,地上的文件就像战场上被击杀的敌军,形成了这位勇士胜利的幻影。”[7]作者将言语反讽流畅地融入这一场面,对于阿加斯特亚、作者以及读者来说,斯特瓦斯塔夫陈旧迂腐的行为丝毫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在作者的夸张陈述下造成了滑稽可笑的效果:“阿加斯特亚得出结论,论自吹自擂的水准,梅农仅仅够得上平均线。而要说其中翘楚,还得是斯特瓦斯塔夫。”[8]对印度官僚体制的批判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线索,这类反讽既数量可观,同时为整体上灰暗消沉的风格染上了一些幽默的亮色。但会心一笑之后,又会引起读者对印度现状的深深反思。“(解决问题)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花钱...而且我们任期是有限的,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9]可以说,在公众语境下,这些公职人员往往被异化为政府的肢体,不断树立着自身的政治形象,使大众很难了解公职人员的真实想法与行为。正是阿加斯特亚的特殊视角使其得以潜入这一群体的背后一探究竟,促使普通民众难得一见的“伪君子”们的奇谈怪论以及荒诞行径得以不加修饰地展示,既可笑又可悲。
二、隐喻的反讽色彩
《英语,八月》中另一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文中隐喻所体现的反讽色彩。主人公的本名“阿加斯特亚”来自印度教中吠陀仙人的名字,承载着父辈给予的来自传统文化的美好祝愿与希冀。阿加斯特亚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印度教徒,而母亲则是果阿邦的一位基督教徒。作者对主人公的命名隐喻了主人公身上父权至上的印度传统力量以及古老宗教文化的基因。但是,阿加斯特亚却成长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西化印度人。他先后在大吉岭、加尔各答以及德里求学,并在大学中主修英语。西方与现代文明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他渴望成为英国人,喜欢被别人称呼昵称“August”(Agastya的谐音)或者“Ogu”,他的叔叔这样评论他:
“寄宿英语学校的教育和你那来自神话的晦涩名字放在一起,让你看起来像个怪胎。”[10]
阿加斯特亚代表后殖民时期困于身份迷茫之地的印度青年,对殖民者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使其无法对本土文化产生认同感,这使其无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找到自我定位,理想中的西方文化也不能带给他们归属感。而同阿加斯特亚发生碰撞的小镇马德纳恰恰隐喻了印度广大的传统、落后,但也是最能代表印度的地区。作为一位印度行政服务机构的实习生,他被派往这里天然地负有建设与管理的责任。阿加斯特亚是印度社会中被同龄人羡慕的青年精英,拥有殷实的家境、出色的学历。他本应在这里成长、进步、有所作为,他论眼界、能力在这里都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但讽刺的是,同之前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将他拉入了无限的困惑与迷茫之中。“我感觉很迷惑、很糟糕……脑子里被未来的选择和过去生活的美好画面搅得一团糟。”[11]而对马德纳人与事的排斥则将阿加斯特亚的自我圈禁在集体公寓的房间内。这个房间,就是他的避难所。印度学者萨姆布·纳西姆(Sumbul Nasim),将阿加斯特亚的房间同品特的房间联系起来,认为阿加斯特亚同品特戏剧《房间》中的人物一样,惧怕走出自我的安全地带。“在马德纳这一荒诞的微观世界中,‘房间’是他神秘而私密的空间,它拒绝一切的外来入侵。”[12]阿加斯特亚所逃避的正是他应当有所作为的领域,他在马德纳与房间之间的选择将它所代表的西化印度人的软弱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暴露无遗。除了以上贯穿文本并起到揭示主题作用的重要隐喻,我们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很多隐喻参与到反讽的个例,比如在马德纳税收局前面“矮胖的甘地塑像”[13]隐喻着当地官员的愚蠢以及对国家尊严的轻视,同这一重要政府部门的严肃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讽刺。米克认为,反讽的表象与事实相对立,且对照越明显,反讽越鲜明。[14]乌帕马尼亚利用隐喻加深了意象与符号的内涵,使之与被嘲弄者的反差拉大,产生了发人深省的张力与反讽效果。
三、双重主题的反讽
《英语,八月》展现了后殖民时代印度的发展困境,即印度社会从上至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敏感而尖锐,而在殖民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不梳油头的一代”[15]却无法找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共鸣,陷入对身份的迷茫与彷徨,无法自拔,从而沦为社会中的“多余”高知分子,浪费自身的能力与资源,最终成为社会恶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阿加斯特亚在马德纳的工作区域以及他的房间是小说展开的两个主要地点,而这也延伸出故事的两条线索:阿加斯特亚“被迫在外的听与看”以及“逃避于内的思与想”。两条线索相反相成,一方面,对马德纳各色官员以及人民生活的描写探讨了印度在独立后的真实现状,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宗教陋习与宗教冲突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在西方文化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印度青年人可以清晰地看到问题所在,但“自我”被置于印度的他们既缺乏对印度的深入了解与认同,同时他们也对眼前的棘手任务无从下手。“问题”同“解题者”之间便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平行关系,主人公阿加斯特亚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被消解,即使在最后调查周边村落奇潘提(Chipanti)的用水问题时,阿加斯特亚表现出了难得的真诚以及对所面临问题的关切,但这并不是一次“戏剧化转折”,而只是“自我中心者向外部的一次示意”。[16]整体上,两条线索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看不到交叉点,甚至逐渐相互背离,也就意味着阿加斯特亚和马德纳小镇的问题似乎难以看到解决的出路。双重主题的互斥奠定了作品整体上的反讽基调,注定了阿加斯特亚自我实现的遥不可及。虽然作品中充满诙谐、幽默、戏谑的因素,我们很难从小说中找到社会和人性中的积极因素,看不到阿加斯特亚走出自我中心的希望,整部作品都笼罩在一层阴暗、消极的色调之中。
四、结语
《英语,八月》体现了作者典型的“无情节”(plot less)[17]创作特色,我们很难看到这部作品中事件的直接发生,主人公总是在聆听,被动接收着来自周围的各种有用、没用的闲言碎语,这同时也几乎是读者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他整日做着一些重复的工作,只能在自己房间的狭小空间中求得安全感,用沉默反抗着灰暗、畸形、扭曲的社会环境,作品整体带有突出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作者曾自我调侃道:“面对这样的情节(指“plot less”)你应该给读者多准备点笑话”。[18]反讽的运用为作品增添了黑色幽默的元素,从言语、意象、符号到结构,这一手法无处不在,成为作者深入混沌社会体制内解剖、揭露其现象根源的一把利刃。可以说,反讽在乌帕马尼亚笔下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而更像是传达一种苟且于当代印度社会苦中作乐,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但是在创作意图上,乌帕马尼亚对印度的未来并不是绝对消极的,他试图利用文学作品激起人们对印度当前问题的反思。“查特吉的文学强调了反省和反思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时代的需要……他的文学作品常着眼于现代印度正转向阴暗和腐朽的现实,而他在严肃问题上的讽刺和诙谐,意在让人们摆脱自负和中产阶级自满,迫使他们站起来采取行动。”[19]公职身份为乌帕马尼亚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视野,对印度社会问题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及超乎常人的社会责任感。面对当代印度的社会问题,乌帕马尼亚的希望并没有寓于某个英雄形象或者先进群体,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阿加斯特亚这样平凡而自我的形象,他们就在人群之中,在这片土地上饱受磨砺,并没有谁能获得印度教神明的恩赐而置之度外。作者的希望起始于警醒,他选择利用反讽、幽默、戏谑等平和而温柔的方式刺痛读者,试图用消解的方式重塑印度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