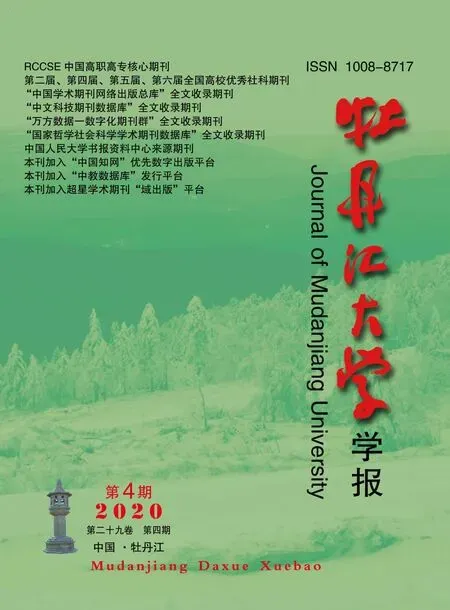“强制阐释论”核心在于摈斥“强制”
尚敏帮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自2014年5月,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一文发表以后,“强制阐释论”的探讨风靡中国文论界。后来张江又分别发表《强制阐释论》、《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和《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还与朱立元、王宁和周宪以通信(已来往十多份)的方式,逐步“对‘强制阐释’做深入的理论补充和修正”[1]。在国际上,张江及国内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俄罗斯十月杂志社共同主办的“西方与东方的文学批评:今天与明天”学术研讨会上,继续展开对“强制阐述”的国际对话。张江在《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一文中明确界定了“强制阐释”的概念——“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特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随后张江及其他学者关于“强制阐释”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这个定义展开的,其讨论都离不开作为基石的这个定义。2015年张江《阐释的边界》以“文本的边界”和“阐释的有效性”命题、2017年以“开放与封闭”和“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主题分别探讨阐释的边界问题。2016年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一文思考两年来关于“强制阐释”的讨论,指出“从阐释的结果辨别和定义强制阐释是困难的。强制阐释的要害不在文本阐释的结果,而在阐释的路线。”[3]这俨然是对之前讨论的反思。2017年《公共阐释论纲》可以看作是《强制阐释论》讨论从“强制”发展到“公共性”深入阶段的“论纲”——“公共阐释”具有“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4]六个特征。后来又通过与迈克·费瑟斯通对话方式和“阐”“诠”之辨的考究方式讨论阐释的公共性。自此,强制阐释的讨论又深入一步,对“阐释”“理论”“西方文论”“本土理论构建”等主题的丰富性探讨形成了一个连续性和阵地化的特征。这些丰富、多元的讨论维度也是张江“强制阐释论”讨论引发的重要意义。
“强制阐释”从提出伊始就是一种针对理论的批判和反思的探讨,有其鲜明的侧重点,有其核心的理论框架,那就是“强制”。尽管后来的更广范围的讨论丰富和深化了“强制阐释”,但究其目的是在引发出其他讨论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回到起初“强制阐释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上,离开“强制”这个概念基石,就会南辕北辙,使得探讨挂着“强制阐释”的名义而在寻求着不相干的讨论意义,这种探讨必将会走上一条没有方向的不归路。回顾其提出背景、探究其陷入原因和路径、认识其警示意义和寻找对其的摒弃策略是继续深入探讨“强制阐释”的一个归纳总结,也是对探讨本身的一个反思。
一、“强制阐释论”提出背景
究张江“强制阐释论”提出背景,具体说来有三方面。第一,从阐释者主体的国界出发。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一大批国外理论引进和翻译到国内。这对经历了十年以及前十七年思想封闭和沉寂期的学术界无疑是一缕春风。于是学术界被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开放和广阔所折服,当代西方文论无论是以被动或主动形式,对国内文学研究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影响作用,以碾压式的方式融入并称霸中国文论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德里达解构主义、弗莱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等曾一度被当作万能钥匙运用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然而,异常繁荣的西方文论给中国文学理论注入活力的背后,每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必须怀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西方文论如此强势,使得我们被动或者主动的“拿来主义”式的运用呢?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是否对西方中心主义反思之后有一个自立自强的信心建构呢?张江“强制阐释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下提出,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西方眼中的“他者”难道就应该以奴仆的心态接受他们“自我”的一切?黑格尔认为,“他者”的承认使人类的意识认识自身成为可能。如此看来,“自我”和“他者”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相互的。西方中心主义恰恰使这个角色凝固起来,以高扬的姿态蔑视非“自我”。
第二,从阐释者主体的理论自觉出发。张江“强制阐释”是基于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赫施的解释的有效性和艾柯的过度诠释进行理论推进得出的。其实,早在2004年,聂珍钊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西方文论在我国运用中的三种缺憾:“文学理论与批评逐渐脱离文学”、“生搬硬套和故弄玄虚”和“文学批评走极端路线,一味地拒绝传统,对传统批评方法的精华也采取摈弃的态度”[5]。这与张江“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可谓殊途同归。聂珍钊在论述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之前,首先指出西方文论的这些短弊之处,然后在阐发中处处以文本为基点,紧扣逻辑,以宏观视角出发,抛弃此前诸多西方文论不该犯的错误,所以聂珍钊阐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在摈弃“强制”阐释的要旨下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强制阐释”的发生是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冲击文学研究的结果。正如朱立元分析,文化研究“逐步启用跨学科的泛文化模式强制压缩乃至剥夺专门的文学研究,强制征用非文学的诸学科知识谱系、概念术语、思路方法等从事研究文学,开展文学批评,最终却不知不觉地陷入文学研究、批评自身的沉沦和迷失”[6],造成“强制阐释”。
第三,从跨学科意义上的反思出发。中国当代文论缺乏一种来自文学自身内部的生发力,却将视野更多地转向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缘于当代学科愈分愈细的境况对于文学研究的局限,加之“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其“宽广胸怀”,促使文学研究转向容易创新和出料的交叉学科。当代文学学科出现式微,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影视传播学、地缘政治学等的繁兴,使得文学研究产生对于自身的自卑进而投入关注过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视角移向其他更具光环和出场力的交叉学科。当然,这并不是导致“强制”阐释的必然原因,因为理论的“场内”和“场外”是人为划分的,必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主观性。在跨学科理论盛行的同时,我们应考虑到各学科及其理论首先是有其自在性和内向性的。跨学科研究终其目的是为了打破和拓展单一学科的封闭性和狭窄性,提供一种圈外的研究视野和思维,并通过借鉴圈外理论和方法,丰富、发展和全面地进行学科研究,提防 “强制”阐释。
综合起来从中国当代文论自身的局限性出发,也可以发现“强制”阐释生成的背后原因。一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一体化追求的约束,同时又要面对当时同国际上思想、文学交流的贫乏状况,这极大地束缚了学人的思想和生发理论的积极性。这就不难解释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思想喷涌般进入中国的情境。二是对本土文学理论的不自信,尤其是现当代文论。民族国家面对世界,特别是现代性后发国家进入全球化潮流当中,会有“不适”症。本土文学理论的不自信就是不适症的体现。三是对西方文论的崇仰之情。基于西方现代性发展进程的较超前一步,如生态批评、女权主义、消费理论等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国人的头脑,于是对西方文论的膜拜之情油然而生。四是对本土文学理论的相轻看待。由于中国传统文论重中庸转化式的儒家气质缺乏西方纯粹的辩证性,影响到当代文论构建便会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文论形式,这是同行们对本土文论鄙弃的重要原因。最后,面对阐释者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自觉、阐释者主体性的自觉和理论自觉以及面对跨学科研究的“强制”“跨学科”,“强制阐释论”应运而出。惟其如此,构建中国文论的“本体阐释”迫切紧要。张江“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既关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自然适恰的阐释,又“关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重大理论问题”[7]。
二、何以陷入“强制”阐释
张江关于“强制阐释论”的核心探讨都是围绕“强制”展开的,也就是说“强制阐释论”就是“强制”阐释论,而有的讨论者没有抓住这个核心,将重点放在关于“阐释”的偏颇方面,这与张江的论述逻辑是背道而驰的。具体从张江总结的“强制阐释”的四个基本特征出发,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文艺批评者是怎样陷入“强制”阐释中去的。
其一,场外征用是将场外理论不加选择地“征用”到文论场内。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一语中的——“今天的文学理论,是更大的哲学思辨的副产品。”[8]文学理论是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文学理论研究须以“文本”为中心。若将文学以外的理论在被认为“文学是人学”这个基础上,自然而然地运用到文论场内,殊不知自己已陷入“强制”征用的危机当中了。文学固然不只是“纯”文学,任何存在于历史中的其他学科思想都会在文学中得到一定体现,或者说文学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虽然文学理论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特质,必将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才是最基本的出发点。这里并不是说文学较其他学科自我崇高并力图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而是从文学文本的产生机制和反映内容出发,这是必须且最为贴近文学本质的研究路径。张江总结的场外征用的“话语转换”、“硬性镶嵌”、“词语贴附”和“溯及既往”四种策略前面其实都省略了或是隐形的有一个前缀,那就是“强制”。“强制”场外征用导致文学研究变形扭曲,文将不文,理将不理,文不对理。当代文学研究对于西方文论的追捧,“一方面是理论的泛滥,各种西方文论轮番出场,似乎有一个很‘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是理论的无效,能立足中国本土,真正解决中国文艺实践问题,推动中国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理论少之又少。”[9]“场外征用”就好似不去注重“量体”而去轻率“裁衣”,最终造成衣不合体而闹出笑话的结果。
中西方思想文化基于两套迥然不同的价值系统,伴随着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和全球化进程,再加上中国近现代“救亡”的迫切目标面向西方而拒绝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方哲学范式进入东方中国,并在思想、文化、学术、学科等诸多方面形成纲领性的导领作用。中国哲学少有西方式的纯粹的辩证性,器重如阴阳、乾坤等两极转换的概念范式,缺乏突破性和发展性。这也使得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国传统文论,必然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经历了近代的西方著作翻译、留学、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并燎原中国、共和国特殊时期的封闭、改革开放,西方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刺激使得我们一味“西化”,西方思想在给中国思想界和文论界带来新鲜“热风”的同时,致使遗忘和忽略了许多传统。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西学”盛行,问题开始涌现,展露在我们面前的研究习惯不是脚踏实地,而是被西方理论牵着鼻子,少了实事求是的追求。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和崛起,中国自信开始彰显。
其二,张江指出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10]。文学批评作为理解与评介文学文本的职能,批评家的主观意识不可避免。但是主观意识不等同于“主观预设”,主观预设是批评家带着自己的前置立场、前置模式和前置结论“强制”进入文本,以获得符合目的性的理论结果。这种“强制”来势凶猛,横冲直撞,把文学文本作为证明自己前置理论的套用工具,失去文学研究的意义。从另一面来看,主观预设其实是将文本与理论置换过来研究的。理论“文本”的意义已经完成而且已有结论,而现在把理论作为“文本”,做的只是套用文学文本来丰满理论的间隙。欧美新批评的开拓者艾略特就曾极力反对批评家带着“个人偏见和怪癖”强制进入文学文本。以赋配的方式,把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文本,去解读,去阐释,试图以中国的文学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去印证该文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不是去发现意义,这里出现主客观混淆或是主体与对象的混淆。符合论特征——便是对“主观预设”最恰切的解释。
其三,非逻辑证明,显然不是从文学应不应作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对象或是文学应不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个方面提出的,恰恰是从文学研究的自身的逻辑谬误出发的。自相矛盾、无效判断、循环论证和无边界推广无不带着“强制”的前缀。文学文本虽以作者主观创作而成,但文学理论研究须要本着客观意义的在场去进入,也就是沿着逻辑的踪迹深入。文学文本不能简单地提炼成类似数学公式或三段论等逻辑式的符号形式,这使得“强制阐释”在文本这个面纱的遮掩下“强制”进入了非逻辑证明,理论研究者堂而皇之地侃侃而论,内心其实是打着非逻辑证明的旗帜。“强制”阐释分主动强制和被动强制,因此文学研究更要谨慎,有时是自己“强制”运用非逻辑,有时可能也被非逻辑“强制”胁迫。
其四,张江称混乱的认识路径也为反序路径,指“理论构建和批评过程中认识路径上的颠倒与混乱”[11]。文学理论,是在文本阅读实践之后的理论凝结。当今的文学研究,大有拿着现成的理论(不论场外还是场内理论)套用文学文本之势,运用最新的西方文论去套用国内的文学文本已成为一种时尚,“强制”颠倒实践和理论的逻辑顺序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理论生成过程中“强制阐释”从抽象出发“强制”“肢解具体”[12],还“强制”“隔绝抽象,抵抗抽象”[13],使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发生具体与抽象的错移。就文学文本研究中的局部与整体而言,“强制”阐释显然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要么“强制”地偏执于局部,要么“强制”地固守于整体,都不能将两者统一起来,不能生成和谐统合、自相一致的理论体系。综上,不论“强制阐释”的理论探讨还是“强制阐释”的实际陷入都是以“强制”出发的,这是“强制阐释论”的核心基础和逻辑起点,这也是我们值得提防和避开“强制阐释”的唯一路径。
三、“强制”阐释的警示意义和摈弃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开始就理论提出反思性见解,如米切尔“反抗理论”、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尼尔·路西“理论之死”、保罗·德曼“理论的抵抗”、卡维纳“理论的限度”等,进而提出以反对中心和反对本质主义、提倡多元与差异为特征的“后理论”时代的到来。因此,现代性后发国家更要反思,西方文论背后的权力与知识逻辑。福柯说“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14],萨义德也说“知识带来权力”[15],所以在西方文论启示和活跃中国文论思想的同时,也要警惕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权力逻辑,因为知识传播与权力播撒构成唇齿相依的联系。
“强制”阐释对批评实践构成侵蚀性的破坏。首先,“强制”阐释导致批评主体的缺失以及失语。丧失主体的实质是遮蔽和隐藏了主体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却直接面向和陷入了不同于东方中国场域的西方文论所处的历史境遇。在这种情况下,批评主体面对的是场外理论,缺乏直接的理论体验。批评是作为主体性而存在的理性实践活动,否则批评实践会被场外理论以及场外历史语境的实体和属性的关系所覆盖,所以批评的存在意义也无从寻求。批评同样是一种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失去了主体性的批评活动必将丧失对于批评活动的能动和积极的认识目标。更进一步来说,主体性缺失的批评同样丧失了获得主体间性批评的权利的可能。从批评主体的丧失看“强制”阐释,处处陷入被动和失去批评主体的自我便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也就达不到批评主体的自觉澄明。“强制”阐释于是“主观预设”了一个没有主体的理论框架。批评的主体性缺失,还主要体现在自觉的假借或不自觉的牵制下将他人的主体性视作自我的主体性,于是批评实践成为主体意识欠缺情况下的盲流和混沌行为,其结果也是失去主体性的无效阐释。其次,“强制”阐释致使批评对象的隐匿和缺席。作为批评的对象,首先要和批评主体处于关系当中并达成目的性意向才能成为对象,否则就是游离于批评主体之外构不成具体对应关系的散漫体。批评活动是批评对象化的实践。“强制”阐释在批评对象化过程中一方面使对象发生错置,错将文本和理论互换,将理论误当对象;另一方面,批评主体在生发对象化批评对象的过程中,失去了主体的能动性和本质性力量的作用和体现,这样便脱离了主体和对象的交互关系也就失去了批评的真正意义。最后,主体缺失和对象缺席则使批评宗旨消解。桑塔格《反对阐释》中批判理论阐释剥夺了艺术本身的丰富性。主体缺失的批评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中既美丽又自由但却不是属于你的放飞。对象缺席的批评只是握着断了风筝的线,虽手握连线但另一头是空的或许是其他。就理论本身而言,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所以文学理论的形成和适用差异性是文学研究者首先所要审视的,“强制”阐释恰恰在各种主客观原因之下忽视了这一点,批评结果的舍本逐末就不可避免。再者,将文本作为理论的注解,批评可谓是无效的或是无结果的。由上述可知,批评主体缺失和批评对象缺席必然导致“强制”阐释,反之,“强制”阐释其鲜明的本质特征也主要体现在批评主体的缺失和批评对象的缺席。
百年前,胡适面对大批仁人志士为“救亡”建立新式中国、建构新式民族国民性而纷纷向国外借鉴并试图运用于中国的各种“主义”情况,在“五四”重刊《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开头就重申他几日前的文章主题——“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16]。正如胡适指出社会“舆论家”和张江“强制阐释”论所指出的当下的文艺研究者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17],并且要清楚“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18]胡适总结出空谈“主义”的三种教训:一是谈主义易谈问题难,二是空谈主义无用,三是空谈主义是危险的(背后带有权力逻辑)。胡适批驳的空谈主义与张江警惕的“强制”阐释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度量。“强制”阐释是套用场外现成理论,省略了自我建构理论和考察理论适用性的步骤,因而是无效的,并且要警觉场外理论尤其是带有自我中心主义形态的理论,因为背后是顺带着的权力逻辑话语。所以要回到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思路,摒弃“强制”阐释。
当下,我国迫切且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本体阐释,而非不加选择地“强制”运用西方文论来阐释文本,这是强制阐释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怎样阐释好中国文本,是每一个批评人深刻思考的问题,更是自己的责任。此外,我们在运用和构建文学理论时,切记不能再走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弯路。借着“强制阐释”讨论的契机,构建中国本体阐释,是迫切而必要的。“强制阐释”讨论必然带着“东方主义”以及“被压抑的现代性”印记,来反对西方文论对中国文本阐释和中国文论的挟制。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强制阐释”,主动、积极、勇敢的态度批判西方文论从而构建中国文论的自信,建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要有本土理论信心,拒绝对西方文论举捧的心理,也要学会新“拿来主义”——要选拿、选用,要看到被拿物的优点也要不讳其缺陷与对拿者的不适。在理论盛行的时代,更要时刻警惕自己以防掉入“强制”阐释。张江的“强制阐释论”给我们敲响了这口警钟,让我们进行文学研究时,不要把理论作为文本,颠倒理论与文本研究的逻辑顺序,打着研究文本的幌子,实则将文本当作佐证结论的例子或是证明理论的工具。回到文本,回到公允评介,拒绝“强制”,摈弃“强制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