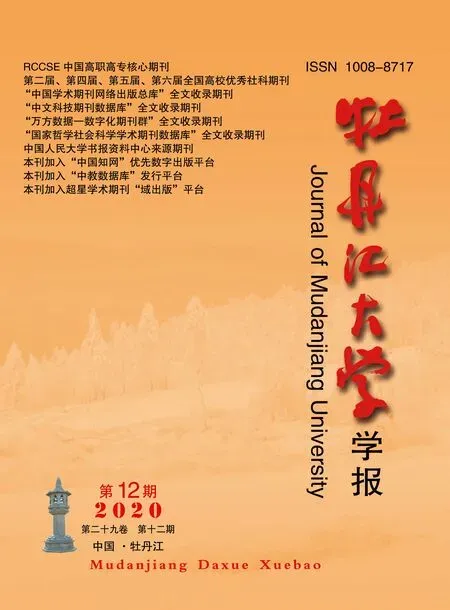在乡村自然中盛开极花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极花》探析
刘 毅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0)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讲述了被拐卖到西北贫穷的农村的女性胡蝶的悲惨遭遇,她被拐卖、被强暴、被解救又主动返回买主家中。不同于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下与家人团圆的完满结局,在《极花》里她被解救后又坐上汽车返回买她的黑亮家中,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极花》的故事来源于他的一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的故事,现实中这位老乡的女儿被救后又主动回到了当初被拐卖的村子里,但作者并不想将这个故事简单地写成纯粹的拐卖妇女类的社会新闻纪实,“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1]207可见贾平凹的关注点不限于这个被拐事件,而是整个正在凋敝着的农村,他执着地延续着一贯的农村题材写作,执着地刻画着现代化进程下的农村的真实生活风貌,就像王庆生先生指出的:“他的中长篇系列作品大都能敏锐地把握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脉搏,对时代的诸多种精神症候给予充分的艺术透视,全景式的展现了当代乡村在后改革年代中的城乡冲突,发人深省。”[2]
对于《极花》这部作品的探究,多数学者多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探究其作品反映出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的生存困境,如徐继伟指出《极花》展现了中国当前偏远农村农民在城市化背景下遭遇的严重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来自城市对农村经济和劳动力的掠夺以及对农村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农民自身的愚昧麻木、闭塞保守、自私狭隘等精神缺陷。[3]如吴景明与蔡译萱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乡村书写转向了对城乡冲突中乡村文明的衰落、农村社会凋敝的反映与思考上来,他围绕传统艺术的没落、乡村政治生态的恶化、进城务工人员的艰辛、妇女被拐卖与农村男青年失婚等社会热点问题向世人揭示着乡村的破败与凋敝,带给人们对新世纪乡土中国最深广、最严肃的思考。[4]还有的学者从《极花》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出发,如学者郑冬玲对《极花》中的蝴蝶、黑亮以及被拐卖的其他妇女(訾米、麻子婶)等人物的分析指出贾平凹通过胡蝶坎坷的经历,描绘出在中国乡村男性话语霸权的世界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也揭示出男性霸权是环境使然,时代使然。[5]又如兰奂铮学者通过对被拐卖女性蝴蝶的视角,以被拐女性的心理视角为切入点,探究被拐女性“去与留”的生存困境以及在传统伦理、道德立场与社会法治的夹缝中演绎着的矛盾生命形态,[6]还有许多学者通过对《极花》的伦理与叙事的研究,如王继超就从被拐卖的女性胡蝶出发,他认为作家站在民间乡土立场对文本本身的故事伦理进行批判,达到了对故事背后的问题和原因进行理性审视和智性思考的效果,[7]王怀昭从故事的情感伦理之维与妇女生存困境之维的角度对《极花》当中的叙事伦理进行分析,并通过有关农村女性小说的文本互相对照,对在转型时期的农村女性的出路进行探讨,[8]谢有顺先生通过对《极花》的故事文本的叙述分析,认为《极花》的故事很简单,但在叙事上却具有特殊的分析价值,可视为作家如何讲述苦难、建构写作伦理的样本。[9]以上学者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有很大的价值,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从故事中看到《极花》中的许多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如《极花》中胡蝶作为一名女性从农村到城市又因思念生育的孩子回到乡村,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中女性因为生养和抚育孩子的善良天性,因而能更亲近自然,更适合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对发展的再思考,城市的发展吸走了农村的人口资源,吸走了农村的土地和女人,导致留守在贫瘠的农村的男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他们无法成婚娶妻,最终导致城市越来越壮大而农村越来越贫瘠,就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1]208这样不平衡的城乡发展终将导致许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应当对这样不平衡的发展予以重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运动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环境问题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同时女性主义运动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两相结合,法国女权主义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的作品《女性主义·毁灭》是生态女性主义兴起的标志。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反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和自然是平等的,自然孕育着人类文明,自然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生存需要,人们在从自然那里获取生活所需的同时应该努力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反对男性中心论,认为过去世代男性不仅占有、支配和驱使着女性的肉体,而且有意制造各种文化来腐蚀、钝化女性的精神,这种状态是不对的,提倡男性与女性之间平等相处。[10]生态女性主义还认为当前对发展的理解存有片面性,将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这种发展需要更多资源,破坏了整体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些本身被用于自身生存的资源被用于商品生产,从而造成了真正的贫困、苦难和资源破坏。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发展应该是这样一种发展:它应与自然相契合,重返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尊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类型的危机出发,揭示《极花》其中所展现的深刻的生态关怀与尊重女性意识。
一、枯萎的极花,自然生态的破坏
自然生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宝贵的资源,人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从自然中获得水、空气等必需品,对于我们来说如此重要的自然,在如何对待自然方面当然也就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之一,不仅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甚至在文学上,如同男女爱情故事一般,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也日益成为文学创作讨论、研究的主题,随着人们的关注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品中展示出了现实中人们与自然环境的不和谐,如描写人们过度砍伐森林植被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荒木化、沙尘暴现象的《愤怒的葡萄》,人们过度开垦导致草原植被减少、沙尘肆虐的《狼图腾》等,警醒人们要爱护自然。
在《极花》中我们也可看见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如故事一开始,黑亮家门前那光秃秃的树枝上站着的一排排的乌鸦,干涸的黄土地,向我们显示出当地的干旱与缺少森林植被覆盖的现象。虽然村子是在西北贫困地区,但是村内产有一种名贵的药材,当地给这种药材起名为极花(也就是冬虫夏草),随着越来越多药材商开始收购药材后,导致村内开始大量采挖这类药材,过度采掘终究导致这类药材越来越少,生长的地方也越来越偏僻与危险,自然生长出来的草药少了但采摘还在继续,导致采摘的人从山上摔下来,可见这样的无节制过度采摘,终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导致自然对人的惩罚。但是即使在这样自然与人类关系不和谐的情况下,村子里的村民们也从未意识到重返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性,无论是路边那开放的极小的花朵,还是那干旱荒漠化崎岖不平的道路,甚至村内山坡的一整面都被开采为窑洞,时不时会有山体滑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却心安理得地居住在窑洞内,并且觉得这个窑洞的年岁越久,能结成蜘蛛网,越能得到庇佑,可见村内的人们从未想过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在故事中麻子婶就被山体滑坡掩埋造成昏厥,差点死去。贾平凹凭借其客观冷静的叙述,向我们展现出真实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态,让读者在故事中看到贫穷的疙梁村村民们将大自然的资源据为己有,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却从未想过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最终只能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自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生活,作品中出现的生态危机与自然灾害恰恰体现出作者对于农村自然生态的关注与担忧。
就像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的人/自然这组二元对立项中,人站在高点对自然的统治一样,作者将荒凉贫瘠、遭到破坏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展现在我们眼前,旨在提倡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者将不加美化的真实农村的生态环境展现在我们面前,将这“枯萎”“凋敝”的农村、遭到破坏的农村生态环境展现在读者面前,实际上也体现出作者对整个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的重视与关心,对于在城市与农村现代化发展中农村所遇到的问题,予以深刻的思考。
二、社会生态的危机,女性悲惨境遇
生态女性主义除了对于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视之外,还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也即是社会环境下男性、女性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突出地表现在胡蝶与买她的黑亮组成的小家庭关系中,在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胡蝶作为一名被拐卖来做黑亮媳妇的女性,在故事一开始时就被黑亮买来关在家中限制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阴暗的窑洞内,用一条链子拴住她的脚,让她不能逃走,她被限制在只有一扇窗户通风的昏暗的窑洞,甚至还没有电只靠一盏煤油灯照明,吃喝拉撒都在窑洞内,可见买她回来的作为买主的男性黑亮并未想到她个人的生存需求,黑亮买她回来只是想着自己终于娶上媳妇,只关心她什么时候能生孩子,就像文中村民不顾胡蝶的意愿只一味询问胡蝶的肚子有没有动静一样,这种不将其作为一个女性而将其看作一个生育工具的观点,也暗示着被买来的胡蝶若反抗所带来的只有更残酷的暴力镇压,胡蝶在故事中趁着黑亮不备逃跑出去,可是还未跑多远就被村内的村民抓回来,“村里的一群男人五马分尸似地将其拖进窑洞,并且对其踢来踢去。在反抗中,胡蝶像皮球一样被人打得左冲右撞,胸罩也被拽去了,上身完全裸光,只能蜷着身子蹴在地上。”她不愿与黑亮生孩子就被村内的许多男性绑在板凳上,让黑亮对她实施了强暴,在这场她毫无反抗能力的压迫中,她的灵魂跳脱了出来,灵与肉的分离让她站在半空中清晰地看到了作为一名女性的自己被黑亮统治、占有、支配和驱使着自己的肉体并无法反抗的恐惧,男性的强迫之力令作为女性的自己无法反抗,能做的只有服从压迫与统治。
当然不仅是她一个女性在村内受到作为买主的男性的残酷对待,在这个荒凉贫瘠交通不便并且与城市隔绝的村子里,在传统农村的家族生育观念加持下,村内的男性都团结起来,不将贩卖妇女作为不道德的事,反而认为只要能娶到媳妇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就可以了,因此村内大多都是通过人贩子买来的媳妇,她们被其囚禁在家中,甚至打断买来的女性的腿以防逃走,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中所反对的男性/女性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在故事中男性占据统治地位,对女性实施的是压迫和榨取,男性以暴力等压倒性的权威,无视女性的意愿,将女性视为可以随意买卖的物品。我们可以看到当胡蝶被当做生育工具,被强暴、被殴打、最终九死一生地生下名为小兔子的孩子。也可看到被物化之极致的訾米,她直白地被作为一项财产列入腊八与立春的分家清单中,原因就是当初买訾米的三万块钱是他们兄弟俩共同出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她完全被当作花重金买回来的物品,后来訾米就被当做一件物品分给了腊八。
作者并未陷于为这被拐卖的女性作新闻写实类报道,也并未陷于帮人物憎恨或帮人物喜爱的强烈主观情感之中,相反贾平凹以其一贯的冷静客观的审视,同情并理解这群被拐卖到村里的女性,不为她们强行添加看似救回家去团圆的结局,而是充分理解她们在压迫下的选择,就像谢有顺先生所言:“文学不仅呈现苦难,它还思考苦难为何会发生,人在苦难中的复杂心理,同时也探究苦难背后人的不幸,以及对这种不幸的同情与爱。”贾平凹对胡蝶等被压迫的女性的苦难书写,甚至在故事结尾为其留下还有母亲来救自己的希望,可见作者对受苦难女性的同情,作者不仅探究了被拐女性苦难背后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倾注了对被拐卖女性的同情与爱,展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中所提倡的反对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反对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压迫,希望构建出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精神生态的破坏,传统道德观念受冲击
相对于经济对人们生活的直接影响,精神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影响但却更加深远,在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传统淳朴友善的精神道德文化所遭到的破坏,如故事中对待被拐妇女的认识上,村内的村民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不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与压迫,他们认为自己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媳妇,因此并不存在亏欠的心理,就如胡蝶一语道破的就因为有买所以一直有卖。就因为村内男性不引以为戒,反而认为拐卖是合理的正常的金钱交易,完全没有违背道德,这才使拐卖人口一直持续,可见其精神文化完全遭到破坏。
贾平凹在这个故事中不仅延续着他一直以来对城市发展中的农村的关注,同时也延续着他对农村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及精神文化的关注,在《废都》中他看到知识分子的情感堕落,在《极花》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然、社会环境下女性生存状况,同样也可看到在农村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的道德、精神文明的影响,原本的这个荒凉的西北农村遵循着以老老爷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例如作为村中长者的老老爷,起着传统家族中长老的作用,村民做错了事都向他磕头请罪,他在为村民起名时为村内的男性起着带有仁义等寓意的名字,都可见其农村传统文化道德的气息,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这个交通不便的农村也受其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这个村的村民不再遵守传统道德观念,将毛草混合着干花伪装成极花卖给商贩,黑亮也偷偷在唯一的小卖部里往卖的醋里加水,以及村长收拿卡要村民在外地买来媳妇的报酬等,都可见其传统的道德遭到的破坏,又如村长仗着自己的权势叫訾米晚上给他留门,想占取她的便宜,要求村妇菊香与他私通,才答应给菊香村里戏台上的木料(村里集体财产)等,为了村子内子嗣的繁衍,不仅老老爷,村内其余男性也都为拐卖妇女这种不符合传统道德的行为作掩饰,他们昧着良心将此事隐藏起来,甚至阻拦警察带走被拐妇女,都显示出村内精神生态及传统道德文化观念遭到的破坏,也反映出村内男性对被拐卖而来的女性的压迫。
作者将这精神生态遭到破坏的农村展现在读者眼前,体现出作者对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农村精神文化、传统道德的担忧与思考,也体现出作者一贯的对于农村与农民的深切关怀。
结语
《极花》展示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胡蝶的故事,但是贾平凹的讲述却与众不同,他并未将这个他老乡女儿的故事简单描写成为纪实的新闻报道,也并未美化农村将胡蝶回归的农村视为美丽和谐的世外田园,他以其超越善恶的同情与理解的叙述伦理,不对黑亮和返回农村的胡蝶作道德至高点的评判,他真实记录下城市化进程中给农村发展带来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的背景下胡蝶被拐卖的真实生活遭遇,同时也展现出他对于农村生态与女性的担忧与同情,他发出的疑问一直都是城市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城市是怎样的肥大而农村又是怎样的凋敝,当我们审视文本中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精神生态遭到的污染,女性遭到的压迫时,我们会更加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爱护自然、尊重自然、尊重女性,构建和谐多元的良好发展,也更能感受到作者对自然与女性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