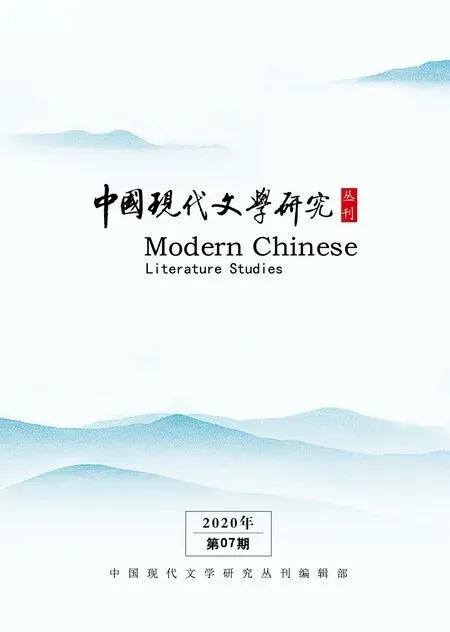沈从文集外文考论
内容提要:新发现1935年沈从文署“炯之”的一篇佚文《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主要评述了文学革命以降至1935年的新文学之历史与现状。本文同时就1981年8月24日沈从文致戴思杰、邝雪林与易征的两封集外书简略作“勾连式”考读,并对《我的二哥》一文的作者与版本问题进行爬梳。
在查阅资料时,笔者陆续检得沈从文民国时期的一篇佚文,以及1981年致戴思杰、邝雪林与易征的两封佚简。兹将这些集外文字介绍于此,并略陈考证过程。同时就《我的二哥》一文的作者与版本问题略作爬梳,以期对沈从文研究有所裨助。
一
1935年11月1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第37期刊有一篇《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此文是该期的首篇文章,足见编者对它的重视。细观署名“炯之”,不由让人将其与沈从文建立起联系。沈虎雏《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中明确著有“炯之”这一笔名:“1935年8月18日发表文论《谈谈上海的刊物》时的署名,为抗战前用于发表文论作品的笔名之一。”①《谈谈上海的刊物》载《大公报·小公园》第1769期,是目前见到的沈从文最早使用这一笔名发表的作品。同年10月28日、11月29日沈从文先后发表署名“炯之”的《时间》《读〈新文学大系〉》。1936年10月,沈氏再次以“炯之”的笔名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挑起了“反差不多运动”的文坛论争。1937年,沈从文又用这个笔名陆续刊发《艺术教育》《一封信》《再谈差不多》。这些文章除《时间》外均为文论作品,基本符合沈虎雏关于这一笔名的描述,只是《再谈差不多》发表于1937年8月,已不能划在“抗战前”了。以上诸文现皆已收入《沈从文全集》,并被《沈从文年谱》著录。但《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却未见《沈从文全集》收录,《沈从文年谱》亦无相关记载。据上文,“炯之”这一笔名主要用于1935年8月至1937年8月间,《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表时间正在这个时段内,并且也属文论,故可初步判为沈从文之手笔。
进而从刊物本身分析,沈从文与《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更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现代文艺》副刊创办于1935年2月15日,由时任武汉大学教员的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担任主编,而凌氏的好友兼同事苏雪林、袁昌英实际上亦参与编务。早在1925年,沈从文就因剧作家丁西林的介绍而在创办不久的《现代评论》兼作收入微薄的发报员,与刊物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等熟识,成为《现代评论》的长期撰稿人之一,因此长期被批评者列入“现代评论派”②。1930年,得益于胡适的推荐,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邀请沈从文来校任教。沈从文在武大执教一个学期,与陈源、凌叔华夫妇相交甚欢。沈从文自1933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凌叔华曾为此刊撰写《衡湘四日游记》《悼花狗》等文。1935年9月起,《大公报·文艺副刊》改版为《大公报·文艺》,由沈从文、萧乾合编,凌叔华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提供稿源。文洁若在《悼凌叔华》中曾转述萧乾的话:“一九三五年萧乾接手编《大公报·文艺》时,凌叔华正在汉口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他们二人曾相互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对方的作品,更多的是彼此转稿,并戏称作‘联号’。”③这虽然是就萧乾与凌叔华而言,其实也适用于沈从文与凌叔华。沈从文在1982年给紫平的复信中回忆:“凌叔华似曾编过《武汉日报》或武汉《中央日报》文艺副刊,部分作品是我为转的,时间当在卅一年之后。”④1935年5月10日,沈从文的《废邮存底》曾刊于《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第13期⑤。编者还特意在文末添加“编者附志”:“沈先生答应了给本刊送文章过来,但为了点事,文章久久未寄出,最后寄来这一篇。”可见,同为编辑的沈从文与凌叔华为了让自己的刊物更加出彩,经常彼此约稿,互通声气。故《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亦应是凌叔华向沈从文拉来的稿子。
《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主要评述了文学革命以降至1935年的新文学之历史与现状,以开阔的视野阐发了对于革命文学、幽默小品文的看法,时有犀利之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是从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书业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复杂过程。在他看来,白话文运动为新书业的崛起与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契机,文学由此逐渐拥有了商品属性,写作者也随之从“玩票者”转变为职业作家。然而,新书业的繁盛亦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各色作家鱼龙混杂,与出版商和批评家“通力合作”,争相“从花样翻新上吸引读者”,迎合读者。即使是致力于促进中国革命、具有反抗与破坏精神的革命文学也不能免俗,与大商人炮制出一些标明“伟大作品”的货色。沈从文还对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性灵派文学提出了批评,讥之以当代“东方朔”。最后沈氏寄语中国青年应保持健康的理性,做“有感觉有血气对一切事肯认真之‘活人’”,而非信奉个人主义、遇事得过且过白日做梦之“文人”,这样中国新文学的未来才会大有希望。
可以发现,该文的一些观点可在沈从文同时期著述中找到近似的表达。如在稍早的《风雅与俗气》中,沈从文已经对幽默小品文刊物既示理解,又表不满。《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沈从文评价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编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存心扮小丑,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它(指《人间世》——引者注)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郎中’,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⑥无论是将幽默文学称为“扮小丑”,还是“杂耍”,倾向性可谓十分明显。由文末所具时间可知,《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写于1935年双十节。同日(10月10日)沈从文还曾给一个来信建议他组织作家集团的读者复信,三天后发表于《大公报·文艺》。此信亦收束于新文学的将来,提出因为还有许多“不预备上文坛却在努力作品写作”的朋友,“中国新文学的将来,应该乐观”⑦。而针对出版机构与新文学作者关系的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迨至1947年,沈从文集中就此论题写下《新书业和作家》,从而引发了郭沫若的批驳⑧。
该期《现代文艺》将沈文作为头条文章,或因作者主要见解与编者凌叔华、苏雪林的文艺观念有相通之处。在1935年2月15日《现代文艺》发刊词中,作者指摘新文学初期文坛“一部分作家利用读者这种心理,粗制滥造,拼命生产,只讲量的丰富,不求质的精良”⑨,这就与沈从文反对文学的商业竞卖抱相近立场,无怪乎有学者将这段话归于沈从文名下⑩。
《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观点显豁,言辞恳切,“辩说譬喻,齐给便利”,平和之中不乏锋芒,显示了沈从文关于新文学如何健康发展的深入思考。他对革命文学、幽默文学虽以批评为主,但也不忘“理解之同情”。如他指出革命文学的理想是“健康”的,“使新文学从‘游戏’地位转变成为‘工作’”,只是成绩不佳;幽默小品文在与读经风气流行相左这一层上,也有其正面的意义。
在《现代文艺》的停刊词中,凌叔华提到有批评者将该刊“与沪津大公报的‘文艺’相提并举,认为是国内日报刊中对于文艺有相当贡献的两个刊物”⑪,但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文艺》在华中地区乃至国内的影响明显比不上《大公报》副刊。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沈从文为何选择将《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刊于《现代文艺》而非《大公报·文艺》。倘若揭载于后者,这篇文章必然受众更多,甚至可能引发争鸣。就目前材料来看,限于《现代文艺》的影响力,此文“非但不曾引起一个波澜,而且简直不曾惹起一点涟漪”,因而它长期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作家、导演晓寒2012年结集出版的散文集《顺水漂流》内收有一篇《沈从文的一封信》,介绍了沈从文的一封书信(附有信封与信文原件),全函如下:
思杰先生:
从正仪先生处转来尊作,我已看过,印象很好,觉得你若能继续作下去,肯定会取得多方面成就,因为你已懂得如何运用文字,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这个工作按个人经验,似乎得以一个素朴持久的工作态度,去处理不同题材(包括文字叙述及全篇形成的气氛),又能采取个客观方式,明白它的得失,再反复从试探中去讨经验,才可望在一堆习作中得经验,心领神会。一个短篇之所以成功,不是情节离奇,倒是近情合理;不是才华惊人,却是素朴亲切。质的提高或许又和量的多样化也密切相关。有的作者能以少胜多,一生不过写五七个短篇,或一个薄薄小本子,也就留传下来,成为历史上名著。我们却不妨把工作看得扎实点,认为质的提高和量不可分。检查作品得失,不是五七个短篇,以至不是二三个小集子的成就,必需用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写出十本八本的内容不一,以至文字风格也不相同的作品,才能作出更适当的判断。这是三十年代千百位同行共通的认识,因为目标明确,所以几个站得住的作家,大都沉沉默默留下大分量习作,“空谈作家”即或调子唱得极高,皮又做得极大,相形之下,还是无济于事。社会变动虽大,读者重视还是有内容的作品,并且还不是一些“跟得极紧”的作家能办得到,恰好相反,或许倒是些从表面上看来,思想、活动,都显得比较保守,见解也比较落后的作者,作出的成绩反而结实经久。我说的不一定正确,因为事情特别显明,我由于不易适应新的社会要求,所有习作早已焚毁三十年,对于文学已无什么发言权。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那⑫来无作品的作家?你那个作品已为试转给广东的《花城》,请那边熟人看看,如《花城》《广东文艺》或《随笔》有一刊物用得上,即留下,用不上时就照我附去信封还给先生。所以寄过广东,因为那边人较熟,刊物容纳量又大,编者且不大受成见拘束,(原文我一字不改,因为,我无能力在别人作品中任意改动的知识。)认真一点说来,我如今做一读者的资格,也大有问题!改业转入博物馆搞杂文物,只好老实学个十年八年,以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的程度,想不到学了整整三十年还不易达到目标,不能不再降级,求于今后数年作到一个“合格公民”,就太好了。事实上这点希望也怕不容易办到!因为年纪已快到八十岁,报废是迟早间事,报刊上说的什么国外“沈某某热”和国内报刊经常称道的某某文物专精独到成就,通通不宜信以为真!仅以常识而言,常识也有限,虚名过实,不免转增忧惧!
即复颂学安
沈从文 八月廿四日
这是一通失收于《沈从文全集》,《沈从文年谱》亦未著录的集外书简。据晓寒所述,此信是法籍著名华人作家、导演戴思杰赠给作者的。作者还交代了其由来:“原来他是通过一位老教授认识沈先生的,他要去法国留学时,在北京逗留了几个月,恶补法国美术史,在这期间,他多次去过沈先生家里和办公室,当时沈老先生已在故宫工作多年,书写他的中国服饰史,粗心的戴思杰,一直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代文学大家,有一天早晨,他去见沈先生,约在故宫外的一石桥上,他说沈先生一边拿着街头买的烧饼,一边匆匆而来,与他这后生相见,其情其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戴思杰爱好写作,想找刊物发表,沈先生告知他,他有个学生在广东《花城》杂志作主编,他约了茅盾先生,一起郑重地为戴思杰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了推荐信,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小说仍然未能发表。沈先生很为此事过意不去。”⑬信封上的收信地址为“四川成都四川医学院光明路卅一栋戴保民先生转戴思杰先生收”,可见戴思杰正是沈从文此函的收信人,当时身在成都。戴保民是戴思杰的父亲,曾任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教授。
戴思杰1983年留学法国,就读于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国立电影学院,后用法文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并将自己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拍成电影,获得广泛关注。戴思杰曾在多个场合谈及沈从文对自己的帮助与影响。如2003年他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时,有如下回忆:
在我读四川大学的时候,文学很热,我突然有创作的愿望,于是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一个朋友是沈从文的亲戚,他就把我写的短篇小说寄给沈从文看,后来沈从文就改了改寄还给我,在信里,他有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写小说,该注意什么,我们通信约有两年时间。后来我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就去找过他几次,那个时候他还不太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价值,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作家。□□
沈从文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挺善良的人,帮助过很多人。在他那得到的教诲,对我的影响很大。⑭
这段话虽与晓寒的说法略有不同,但大体可与信中内容相印证。据信首“从正仪先生处转来尊作”,“正仪先生”即戴思杰的朋友,沈从文的连襟王正仪⑮。王正仪曾系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教授,与戴保民有同事之雅。信中所言《花城》的熟人,应指本刊编辑。1979年至1980年代初,为出版《沈从文文集》事宜,苏晨、邝雪林、林振名等人与沈从文联系频繁。邝雪林在回忆文章《我和沈从文先生的一次工作接触》中披露了沈从文1981年8月24日致易征和自己的一通书信:
雪林、易征两兄:
在穗一段时间中,多多搅扰,弥增感谢。到长沙工作复半月,回到北京便已进入夏季,为一堆杂事忙忙乱乱,就进入真正夏天。日来北方格外闷热,住处当街一面,经常有上万大小汽车来往闹哄哄情形中,真正是热闹得人昏昏沉沉,长日如猪悟能坐蒸笼中,只希望悟空师兄即时前来搭救出险。既无从希望成为现实,因之人便不免形成一种半低能痴呆状态中,浑浑噩噩度过此炎炎盛夏,直延续到近三天方从一雨中得救,稍稍松一口气。转来一小文,由弟看来,文章还好,作者似为一医学生,望为看看。如还可用,不论安排在《随笔》《广东文艺》或《花城》均无妨,且可去信将他别的作品寄广州看看(还有不少较长的)。如觉得平平无奇,就还给本人,甚感费神,并候佳好。
弟从文八月二十四⑯
经查,此函同样为《沈从文全集》所失收。沈从文于信中首先对广州期间(此行主要目的是审校《沈从文文集》及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搜集、补充新材料)得到邝、易的照顾而表达谢意。其次以幽默的语气道出了新居临街的烦恼。最后则转上一位年轻人的稿子,请两位过目。若将上述两函联系起来,可知本信中“似为一医学生”的作者即戴思杰,不过他实为川大历史系学生⑰。且能确定两函作于同一天,即1981年8月24日。沈从文读了王正仪转来的戴思杰文章后觉得甚好,于是转给邝雪林、易征两位编辑,并函告戴思杰本人。就目前资料看,虽有沈从文的推荐,戴的作品最终并未发表。
面对青年写作者,沈从文并不以文坛前辈自诩,而是坦诚相待,指点迷津,希望提供投稿方面的帮助。关于对“沈从文热”这一现象的冷静与警惕,沈从文在当时写给许多朋友与研究者的信件中皆有体现。“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那来无作品的作家?”“报刊上说的什么国外‘沈某某热’和国内报刊经常称道的某某文物专精独到成就,通通不宜信以为真!仅以常识而言,常识也有限,虚名过实,不免转增忧惧!”这样的表述,与1982年10月12日沈从文致向晓晖信中的“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在近半世纪风风雨雨中,居然尚能健在,只宜说是十分幸运,实万万不宜相信近年来报刊消息,即以为真有如何成就。其实虚名过实,不免转增忧惧不安也”⑱,可谓毫无二致。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沈从文对文学青年的善意与热忱,也能感受到远离文坛已久的沈从文面对“新社会”的复杂心态。同时,我们还可窥见此时沈从文朴素的文学观:反对紧跟形势唱高调的“空谈作家”,提倡扎扎实实的创作态度。今天的戴思杰已是知名作家与导演,来自沈从文其人其文的影响兴许还将伴随他继续前行。
三
最后,笔者在1933年7月10日杭州《文学新闻》第7期上见到了一篇署“岳萌”的《沈从文小传》,内容上与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我的二哥》大部分雷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沈从文小传》以纯粹的第三人称介绍传主沈从文,而《我的二哥》使用的是妹妹的口吻;两文分别为8节、6节,其中前文第3—5节、第7节与后文第2—5节文字大体相近,其他节则迥然有异。《我的二哥》1934年4月曾入上海大东书局版的《沫沫集》。据张兆和意见,此文为沈从文所作⑲,《沈从文全集》第16卷收入此文时附有编者的说明文字:“本篇原载刊物不详,为作者拟自己九妹口吻所写的自己的传略。”⑳《沈从文年谱》1930年3月谱条:“在上海吴淞,沈从文拟九妹沈岳萌口吻写了《我的二哥》一文,但后来刊于何种刊物不详。现收入《全集》第16卷《沫沫集》。”㉑显然同样采录了张兆和的说法。经查考,本文以《沈从文——我的二哥》为题,1930年5月20日初刊武汉《日出》第一期(目录署“岳萌女士”,内文署“沈岳萌”),文后附有高村编的《著作目录》《一九二九年中发表的短篇》。此目录是沈从文著作最早的汇总,共著录1926年至1930年沈从文的20部单行本作品集,其中提到晨报社的《市集》《第二个狒狒》,可惜两书至今尚未被发现,邵华强编《沈从文总书目》中在两书条目下均注“编者未找到此书”,认为它们约出版于1926年冬。同期还揭载了沈从文的《论郭沫若》(评论)㉒、《春天》(小说)㉓,并在目录页后刊发了一幅沈从文的照片。《日出》主编盈昂,原名杨克毅,笔名杨赢牲、樊崩等。他在《编辑后记》中特意用较多笔墨评述了《论郭沫若》与《沈从文——我的二哥》:“沈从文先生曾说以工作求完全,这里开始刊载了他的现代中国文学评论。从文先生是小说创作的人。眼光犀利,现在写批评,实在还全是创作。看见了道出了大家忽略的或者人所共见未能言的事情,自然这次论郭沫若先生是从作品一方面的论断。可是中间仍不缺少大量的真见地。只要看的人能够耐心细读下去。作者以另一种风度的笔墨写下这批评,皱眉的人也许有,不过这是有素养的人的享受。工作是求完全,作者以这个勉励了自己也同付了别人作希望,所以态度是客观的,性质是研究的。再看岳萌女士写作者传略,也就不难看到作者生活的背境,及其创作的边际了。”㉔
据杨仲益《回忆父亲杨克毅》,杨克毅1927年赴上海复旦附中读书,后因向《中央日报·红与黑》投稿而与沈从文结识,1930年至1933年在武大英文系就读㉕。不过文中“家父到武汉读书与沈从文联系少了,后来几乎音信全无”之说似不够准确。身在武汉的杨克毅不仅约沈从文为《日出》供稿,而且将沈从文之前发表的文章编集为《生命的沫》(最终并未问世)寄给他,沈于4月24日写下题记,并交付赵景深主编的《现代文学》创刊号发表㉖。沈从文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武大时期的学生时便提到过杨氏:“随后又转到武汉大学去,同事有闻一多、梁实秋、孙大雨等人,学生有杨克毅等。”㉗1930年9月至12月,沈从文在武大中文系任教期间,杨克毅大约听过他开设的“小说习作”等课,在文艺方面继续向其请益,始终以弟子自居,并将弟弟杨作材也介绍与沈相识。晚年沈从文与杨氏兄弟再次建立了联系,书信往来频繁。《沈从文全集》书信卷现收入1976年至1982年沈从文致杨克毅的书信十通,致杨作材的残信一通。
1982年2月,学者王紫平曾就《日出》月刊的情形致函请教沈从文,沈在复信提及:“你说的沉樱作的《我的大哥沈从文》,应是《我的二哥……》,作者是沈芷嶙,是我最小的一妹所作,已于三年困难中饿死于家乡。”㉘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沈从文——我的二哥》初稿应是沈岳萌所写,成文过程中沈从文可能作过修润,后将其改题《我的二哥》收入自己的《沫沫集》。入集时内容上也有一些改动,如“现在则将小说到《小说月报》,《新月》及《日出》上发表”中“及《日出》”被删去;“约计有四十七种”中“四十七”被改成“三十七”,附录《著作目录》《一九二九年中发表的短篇》则被完全删汰。
回头再说《文学新闻》。它由文学新闻社编辑发行,主编不详。该刊1933年6月10日第5期登有一篇黄萍荪的《驼铃社宴客回忆记——浙江文艺史料之一》,其中忆及作者六年前在一个穷报馆中当副刊编辑,执笔人中有金满成、许钦文、沈从文、孙福熙等。这里提到的报馆应指浙江《民声报》,创刊时间待考,停办于1928年6月㉙。据晚年黄萍荪在《至情待人沈从文》所述,他与沈从文1927年前后即已开始通信㉚。故1928年左右黄萍荪约请沈从文为《民声报》副刊写稿是有可能的,只是此报不易寻觅,无从查阅是否刊有沈的文章。考虑到沈从文与黄萍荪相识,《沈从文小传》或许正是沈氏投寄的。当时,沈从文与杭州文人颇多联系,常为《西湖文苑》供稿,并且曾与林庚、高植、程一戎等合编《小说月刊》。《沈从文——我的二哥》以“他今年是二十八岁”作结,而《沈从文小传》末段为:“他今年是三十二岁,今年春与张兆和女士订婚于青岛。他曾任吴淞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文学教授”,可知《沈从文小传》当是据前文增补而来。也就是说,此文共有三个版本:《日出》上的初刊本,《沫沫集》中的初版本,《文学新闻》上的增补本。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②参见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沈从文晚年在演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说:“其实那时我只廿三四岁,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说得上是什么‘现代评论派?’”显然他不同意自己被划入“现代评论派”。
③文洁若:《梦之谷奇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1~52页。
④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⑤《沈从文年谱》与《沈从文全集》仅注明此文发表于《武汉日报》,未提《现代文艺》副刊。
⑥⑦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400页。
⑧李杨:《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
⑨此文未署名,1938年曾收入苏雪林的作品集《青鸟集》,故当是苏雪林执笔。
⑩参见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⑪凌叔华:《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16页。
⑫“那”通“哪”。
⑬晓寒:《顺水漂流》,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⑭张英、戴思杰:《小裁缝变了,我也变了》,《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
⑮张允和在《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中称“我们的堂妹夫王正仪先生”(张允和:《最后的闺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8页),张宗和《宗和日记》称王正仪为“八姐夫”(王道编:《似水华年》,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可推沈从文与王正仪乃连襟关系。
⑯邝雪林:《我和沈从文先生的一次工作接触》,《花城》2010年第1期。
⑰关于戴思杰的教育经历,不同资料略有出入,较常见的说法是: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入南开大学艺术系公派出国研究生,1983年年底赴法留学。
⑱此信亦系集外书简,全文如此:“晓晖同乡:前日因从日本回京,长途飞行,体力不免感到相当困顿,相过失迎,十分歉仄。承兄示尊文,盛意深情极感谢。内中旧事小有误记处,试就弟记忆所及,为小作更正,想不以为意也。弟因为人顽固,在新旧社会都近于‘吃不开’人物。实学不足,徒有虚名。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在近半世纪风风雨雨中,居然尚能健在,只宜说是十分幸运,实万万不宜相信近年来报刊消息,即以为真有如何成就。其实虚名过实,不免转增忧惧不安也。敬复并颂安好。沈从文八二年十月十二日北京。”颜家文《沈从文回乡记》(《民族文学》2000年第4期)一文已有详述,故本文不赘。
⑲[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 447页。
⑳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㉑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
㉒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系1930年:“本年,沈从文还有作家评论《论郭沫若》在《日出》月刊第1卷第1期发表。《日出》月刊由武汉狂涛社编辑出版,只出一期,出版的月份不详。”吴俊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误认为该刊创办于1930年5月10日。
㉓《沈从文年谱》失记,仅云此作“在收入集子前未见发表记录”。
㉔盈昂:《编辑后记》,《日出》1930年第1期。
㉕参见蔡宗周主编《中大童缘》上,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159页。
㉖《沈从文年谱》认为此文发表时间是4月1日,有误。赵景深的《编辑后记》写于6月28日,故创刊号出版时间应在7月。赵景深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中说“1930年7月份,我开始编辑《现代文学》”,当指创刊时间。
㉗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47页。
㉘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徐迺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词典 第1卷 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紫平(当即王紫平)撰写的“日出”条仍有“沉樱的散文《我的大哥沈从文》”之语,可见沈从文的回复未被采纳。
㉙《浙江民声报被封》,《时报》1928年6月3日第3版。
㉚黄萍荪:《至情待人沈从文》,《上海滩》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