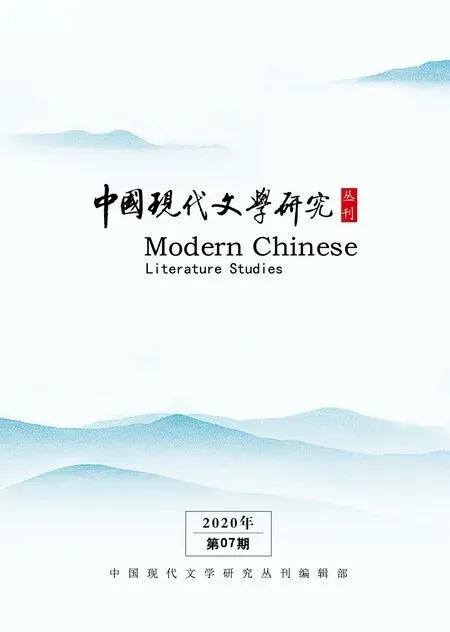张柠《三城记》的城市经验
内容提要:《三城记》以“80后”文艺青年顾明笛在上海、北京、广州的精神历险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讲述其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细节与经验来呈现青年个体的精神诉求。顾明笛游荡于“世界”与“书斋”之间,但内心里却向往“民间”,这是在遭遇城市生活中的人和事之后所做出的内心抉择。小说塑造的城市青年的成长之路摆脱了传统成长叙事主题追求的固化与僵硬,进而转向于去拿捏一个诗性与理性都在蜕变中的“新人物”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丰富并拓宽了当下的青年书写。
顾明笛农学院毕业后进入公园管理处工作,衣食住无虑无忧,如果不是在职取得一个文学硕士学位和坚持创作的话,这位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80后”很可能就和父亲顾秋池一样终老于体制内的日常琐碎中。《三城记》所写的顾明笛就是要告别父辈,并且追求“过一种目的不明的、随性的、混乱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生活”①的新青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新的城市青年生活理想、生活法则和生活方式的出现和生长。归结为一点,即“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终结,他们要追寻的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意义”②,小说即以此为逻辑起点对主人公在上海、北京、广州所经历的精神漫游展开叙述。
为了摆脱单调而枯燥的生活,顾明笛便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个人寻求离家远行是自我启蒙下对自身价值和生活志向的寻找,并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完全由个人来权衡,不再由父母来支配自己的选择。这同样是向父辈生活理念说告别的一种形式。顾明笛依赖的远行冒险资本并不丰富,就集中体现在作为文艺青年所持有的心态和刚刚积累起来的创作经验上,至于闯荡一番之后获得的结果并不在预想之列,或者说就没有去考虑过。也就是说,敢于行动的本身最为重要。把顾明笛的个人形象放在当代文学史的线性节点上来判断,和父辈孙少平们相比,在城市中出生成长起来的“80后”事实上已经确立起来了新的价值观,文艺创作进入新一代人的生活理想中,它承担的是对生活乐趣生活兴致的发掘与体认,它不再对物质获取、生活改观和人生改变的沉重使命负责,它进入到对“轻生活”追求的自我满足中。孙少平们拥有的文艺才华停留在以此告别黄土地进而由乡进城最终完成改变命运的生存层面上,也可以说首先要实现物质层面的需求,然后再成为一个自己寄予理想的文艺青年。《三城记》设置了顾明笛祖辈以来的家世背景,由其父辈的人生历程来看,到了顾明笛这一代,安居乐业就是父辈们期望的生活态度,根本不需要什么冒险。当然那是前辈们的眼光和心理。笔者无意于刻意将顾明笛的身前史进行历史化,但作为“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之路一定要有父辈们积累起来的生活资本作为基础,这样顾明笛的精神蜕变才能得以伸展。
一
顾明笛作出离沪进京的决定是其独立成长的关键一步,也是真正迈出自己人生抉择的第一步。离家出走这样的情节安排在革命叙事的小说中并不少见,一般都被打上主人公脱胎换骨的成长烙印,但在《三城记》的城市经验叙述中,这并不是说顾明笛这个年轻人要和整个家庭决裂,而是要表明其在自身独立判断下以一种探究未知的心理作出选择,这本身和习惯性地被寄予跻身成功、思想飞跃、荣耀等身等宏大主题叙事没有关联,顾明笛的一举一动只关乎自身对生活的期许。和园林管理处办公室的清闲相比,进京入职《时报》之后,给他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他要凭借自身的判断力来认识社会。文青的精神生活从接触身边的人和事开始。从顾明笛在柳童面试时表现出来的书生意气就可以看出来,充满文艺范儿的知识青年历世尚浅,相较于上海期间参与的沙龙、笔会和在《南天》发稿子这些单一的小群体活动,《时报》是一张报纸阅尽整个社会,所以在报社工作增强了顾明笛的阅世能力,也给了他看清社会的诸多机会。形象一点说,报社是顾明笛进入的第二个朋友圈,只不过成员都换成了承担不同工作角色的同事及好友,而自身的意志取向自然也要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发生位移。
《时报》的读者群和获得的市场利润归根结底依赖于报纸是否能够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用柳童的话来说,报纸要同时刊登好消息和坏消息,而选择发出来的消息都得做到对阅读群体产生有用性,要不这份报纸在社会竞争中就失去了该有的价值。顾明笛被安排到旅游周刊部工作,入职后他主打京郊民俗旅游线路的开拓,从承德坝上之行就可以看出来,上海来的小伙子在现实生活体验中对文化市场秩序的理解深度并没有跟上现实社会的节奏,所谓的现实就是客观的存在,就是柳童所说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叙事而不是抒情。他写出来的第一篇稿件充满抒情笔调,所以在上版前被大量删改,所写的文字几乎面目全非。这是顾明笛认识传媒业的开始,他怀有的还是文青的眼光,缺少对消费行业捕捉专业信息的灵敏度和感知度。对于承德之行,顾明笛的收获除了对塞罕坝“皇家猎苑”受伤的动物充满怜悯情怀之外,还满足了自己对鲜活的民间文化的视觉体验,同时也映衬出自身内心情感和既有良知的流淌倾向。这一点就决定了顾明笛并不适合从事以消费文化、快餐文化为导向的大众产品的输出,他随之被调到深度报道部更符合自身的沉稳秉性。“20世纪80年代所特有的‘启蒙情结’和‘英雄情结’在他们身上还有一定的遗存,对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保留和疑虑”③,作为“80后”的顾明笛,报社派出去让他感受的是如何倡导人们去消费,但收获更多的却是文青情结,当然也可以说在他的身上还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裴志武带着顾明笛来到家乡武威暗访,我们可以看作两位新闻人践行职业操守和展现济世情怀的现实之旅。西北的荒漠、污水、毒烟和放任污染的企业就摆在眼前,加上当地行政部门对GDP的过分追求,现行乡村治理办法亟须解决。问题曝光后,这在参与暗访的顾明笛看来本应该得到报社领导的积极认可,但结果事与愿违,他和裴志武被认定为跨省违规采访。紧接着拟订暗访水果基地的计划也迫于流产,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看,顾明笛介入真实社会的举动屡屡碰壁。但是,顾明笛凭着正义感和正直情怀获得了同行们的尊重。获得尊重源自顾明笛的认知立场和现实勇气,或者说可贵的精神导向是人格独立的象征,事业上虽不如意,但顾明笛却和施越北、唐婉约、彭姝等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然而事实上,个人的发展空间在现有体制约束下很难再有作为,因而施越北被迫南下,顾明笛尚且留在文化新闻部,按理说这份新的工作更适合文青的个人发展,但结果依然不顺。作为时事报纸的文化板块,自然不能完全是学术的,也不可能是学究的,它还应该是面向大众的,也就是那种适合大众口味的轻阅读和快阅读。实际上,顾明笛安排的文化访谈、主题书评都有针对性,选取的内容都是严肃务实的,也曾得到报社的一些好评。然而最终还是迫于无奈辞去这份媒体工作,原因出在其自身持有的价值观念没有和现实境遇达成妥协,一个精神上有追求的顾明笛看不惯去做文化掮客,一个独立思考的顾明笛过于推崇符合自身思想观念的文章,这些都是导致事业上再度遭遇滑铁卢的直接所在。
把《时报》每天发行的不同版面拼贴起来,就构成了近日社会的整体表情,要是把它们拆解开,就是观照生活细节的一面面镜子。王春林认为《三城记》“是一部敏锐深刻地洞察表现纷纭复杂世象的社会小说”④,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报社的经历就是和社会的纷繁复杂进行对话的过程,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不能脱离对话和交往,也必须和现实产生关联,这样才会走向成长。顾明笛的报业经历,表明他和真实的社会化活动还有隔膜的一面,这是初入京城获得的体验。
二
考取中国现代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后,顾明笛从现实遭遇的社会再次回到象牙塔。从选择这个专业来看,“80后”的顾明笛依然怀着自己的真切情怀,读书研习可以暂时躲避繁杂世事,也可以为丰富的精神活动的开展提供自由的空间。然而,校园中的现实境遇同样不容乐观,眼下的象牙塔不再具有逃避现实的屏障,重回校园被寄托的精神所求并不现实,这种溃败对顾明笛来说异常残酷,此前期望的充分释怀和有所作为在遭遇冰冷之后,生发出的痛苦、无助和迷茫不断逼迫自己去承受。在求学过程中,导师朱志皓教授会议繁忙、社交繁忙,对师门弟子其实无暇顾及,专业指导空白,思想探讨无从谈起。难得的师门见面汇报会,除了已是讲师的卫德翔侃侃而谈外,真正专业上的交流少之又少,顾明笛充当的是听众,所以师生一场,二人彼此之间缺少足够的了解。和师姐何鸢的交往仅为一个插曲,表现在两人仅仅完成了一次肉体上的交欢,何鸢的不幸和母性感染了顾明笛,真正的情感体验是不存在的,此后也没有继续交往。至于和卫德翔的交流,不管是诗性的,还是理性的,在现有的交流中已显得弥足珍贵。对于韩梓厚的才学,顾明笛是佩服的,但得知其职称难以晋升,特别是地方院校本科文凭的出身,光有才学还难以在学术圈立足,他于是对高校更是失望。在学业上,自己研究乌托邦思想的选题胎死腹中,再加上所学课程大量掺水,性格上的木讷寡言和淡然清高造就了其成长中新的隔膜,所以所见到的本该充满活力的大学却成了一片荒原。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压在一个有追求的青年身上,精神恍惚、颓唐乏力、无助无味,就如同陷入无物之阵,孤独感孤僻感叠加而起,除了对顾明笛有所了解的程毓苏外,身边人几乎都把他看成了异类。遭遇到如此隔膜的人和事,顾明笛求学之路越发困难重重,压抑、焦虑、困惑自然随之而行。
顾明笛研究思想史却没有找到既有的研究目标,这番读博深造反而成为现实中的一幕反讽,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撕毁自己的开题报告并扔出窗外,其本身就完成了对自己人格理想走向破灭的宣判,也是对博士求学生涯的无奈反抗。从报社到大学,顾明笛选择这条路的本意是想回归形而上的理想殿堂,但现实的读博生活清醒地告知,生活中的围城无处不在。精神漫游在象牙塔中迷失了方向,顾明笛的北漂求学依然没有实现自己想要的理想。住进医院后,顾明笛在日记中写下一句话:“实践哲学认为,我们不但要认识世界,更要改变世界。”⑤思想的行动,要借助于和现实的对话才能不断加以展开,顾明笛曾一度失语,自然也就无力去改变现实。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把北京经历完全看作顾明笛遭遇挫折走向失败的过程,因为这样一个追求精神成长的人物,每向前走出一步都是在艰难地去抵达心灵。所以对此进行判断的标准也不能局限于固有的成长小说的叙事范畴,多元的开放的判断眼光才适合这样一个“新人物”。
小说对顾明笛生病调养期间的叙述是通过施越北翻看主人公过去的日记来推进的,而这个时候的“精神患者”已经来到了广州并开启了新的生活。从叙事的角度看,主人公在广州的经历和北京生病中的心路历程构成了一种互文本效应,施越北对顾明笛的了解一方面通过眼前在公司工作的本人来完成,另一方面依靠裴志武给他的那个日记本展开对读,两种叙述话语的交叉进行构成了复调叙事,进而展现了更加丰富的主人公。文本对身居广州的顾明笛的成长其实还是沿着他要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思路展开的,如果说此前的主人公对世界的看法多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那么南下之后则变得有了人间烟火气。“城市文化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和交往的结果,或者说是以‘陌生性’为基础”⑥,从顾明笛的异性交往上看,他从上海到北京一直存在着恋母情结(对象如田园风味小吃店老板娘、房东夏慕春、师姐何鸢),通过管窥和她们的相遇或交往,我们看到的是文青存有的精神症候。到广州结识劳雨燕后,顾明笛迈出了重要一步,由此平等交往并慢慢解开心结。顾明笛曾向乌先生提出疑问“何为理想生活”,他的广州生活进入到一个和施越北、裴志武、劳雨燕等产生交往的熟人社会,主人公积聚而起的精神病灶,随着交往的深入渐趋消除。
三
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在顾明笛的精神生活上也有十足的体现。顾明笛在公园管理处工作时就开始患上失眠症,对多数人来说,失眠并不需要以进入到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范畴为考量手段,它多指向生理机制在现代生活节奏变化下引起的一种反应,出现这种轻度症状一般也不需要药物干预,也不需要进行临床上的介入治疗。26岁的城市青年顾明笛就已经是轻度患者,潘医生诊断后建议他调养休息,至于患上失眠症的原因,还应归结在其精神诉求上的不如意。在《时报》工作期间,虽然事业上坎坷不断,但病症也并没有因此加重。反而是回归校园后压力增大,精神负担加重,随之演化为一起校园事件,也让顾明笛神经性失眠症转变成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小说写到了同一病房的老杨、陈金忠、西岛,三位知识分子都愿意待在医院,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其张扬的精神气质不能说就是精神病患者,还都是清醒者。包括顾明笛在内,这些人的症结都在于个体理想的破灭。实际上医院和医生都治不好顾明笛的疾患,或者说他也不需要住院治疗,适度的调养和有效的精神互动就可以帮助他走出困境。
早在上海,顾明笛就已经产生了心病。乌先生作为人生导师,是唯一让顾明笛心悦诚服的智者,也是其精神疾病的理疗师。这个特殊人物每每出现在他人生困惑之时,提出的行动哲学对顾明笛产生了积极促动,并且让他坚定了离开上海去体验新生活的念头。所谓的行动理念,其指向的就是实现自我,不拘泥于自我,敢于去成就自我,这符合顾明笛不想安于现状的想法。从根源上说,顾明笛进京冒险,也有乌先生积极推动的介入,并且把他的行动哲学理念带到了以后的生活中。入职《时报》则打开了顾明笛的视野,京城世界也的确激励他付诸行动,但这个知识者向往的是有思想的行动,即行动起来的人生得有符合期待的附加值。遭遇不利后,乌先生对顾明笛选择考博的举动以“顺其自然”回应,实则是对其前景表示担忧,这句预言更像是对事后的宣判。从“世界”回返“书斋”,顾明笛在焦躁不安中引发了精神上的痛楚,所以本该产生思想的象牙塔反而加剧了主人公的心理落差,北京的书斋生活阻碍了精神漫游。
竺秀敏接回生病的顾明笛回上海后,他又和乌先生有过一次谈话。二人探讨的还是如何才能拥有理想如意的生活,如同乌先生早期对其启蒙时所言,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圆形的,这个时候的顾明笛行走的轨迹恰似一个回到原点的圆,如果把这种人生路线作为象征对象来看的话,小说文本的弹性还是非常丰富的。如顾明笛这个“80后”的成长者所走过的路向打破了习惯性的螺旋上升式的程式化套路,小说摆脱了我们熟稔的固化的奋斗者模式,塑造了新世纪追求个体价值观念的自由探索者形象。行动哲学贴上的标签,指向的是顾明笛行动自如并唤起内心的自我延展,它不需要用成功或者失败来加以衡量。《三城记》的主题叙述凸显了新语境下城市青年的精神图景问题,以病态回归上海仅仅是作为冒险经历的一个片段。智者乌先生是一个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也可以说是小说设置的和主人公心灵沟通的虚化意指,顾明笛到了广州之后就渐渐远离了这位导师,人真正的成长依赖的还是自己的判断和眼光。站在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也可以认为乌先生本身就是顾明笛自身的镜像,他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二者之间的了解、信任和沟通如同顾明笛的自言自语,所以从根本上来讲,顾明笛最终完成的还是自我的启蒙。把堆积的困惑解开了,所谓的精神疾患也就远去了,沪上休整可以看作顾明笛蓄势待发的间歇期,而奔向南粤则是属于新的精神历险。
小说中另一个微妙的意象是陪伴顾明笛的睡袋。“在他社会化的进程之中,自始至终都有一个非社会化诉求的象征物,这个象征物就是睡袋,就是母体或者土地或者自然”⑦,应该说顾明笛和睡袋之间的关系,也是其精神依恋的隐喻。表面上看,顾明笛睡眠不好精神状态不佳时都会躺在睡袋里休息,实际上这是对现实的一种逃脱,越是依恋睡袋就越是表明他在精神品格上缺乏独立性。抓住外在的物质维度象征的则是主人公内心的焦虑程度,从上海到北京,睡袋也成为顾明笛的必带品,而到了广州,这种精神寄托物也渐渐远去了。把睡袋和乌先生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非常微妙,实际上乌先生指向了精神维度,睡袋指向了物质维度,而帮助睡眠的睡袋本质上还是为了缓解主人公的焦虑症,同样指向了精神维度。睡袋和乌先生俨然孪生,最后的境遇也极其相似,顾明笛将其内化为心,进而弃之远行。
南下广州后,顾明笛的精神疾患大有改观,并渐渐回归到正常工作。施越北创办的公司正处于上升势头,裴志武和顾明笛的加盟算得上如虎添翼,所以在陌生的广州打拼,顾明笛并不会在人情世故上觉得隔膜和被动。此时的顾明笛还是一个在读博士生,因为病情只能延期学业,所以个人身份还比较特殊,他面临的选择也有多样,广州的工作经历可以在事业发展上助他一臂之力,也可以把工作之余作为调养身体的缓冲期,为后面的复学做出准备。《三城记》也基本上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叙述。但是,他究竟要选取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很关键,也就是说顾明笛如何思考如何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必须要明晰的。这里面有两个细节可以做出厘清,一个是他选择了劳雨燕,爱情的出现给了他足够的生活勇气,个人性情相应发生了变化;一个是他并没有和施越北、裴志武一样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如他们去歌厅K歌,顾明笛劝说来服务的胖姑娘回家务农并往她手里塞钱,叫她拿回去给父亲看病。对此,施越北和顾明笛产生了严重分歧。从社会现实看,胖姑娘的话大半都是假的,人性很复杂,施越北的生气和指责都有道理;从人和人的交往来看,顾明笛的悲悯又是对的,他只对眼前的判断负责。施越北显然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人,在多年的物质、欲望和现实辩难中对城市里的细节可谓了如指掌,用顾明笛日记里的话来说那是在“认识世界”,而涉世不深的顾明笛依然坚持知识者的认知逻辑,其实是想“改变世界”。从《时报》时期的骨干力量到自主创业成功,施越北在商业圈、人际圈积累起来的资本力量是顾明笛无法比拟的,而顾明笛始终坚守着骨子里的诗性特征,这是他经过北漂生活之后依然持有的文青情结,也暗示了他和城市有着摆脱不掉的隔膜。至此,我们看到的顾明笛在精神世界上已然明朗,疾病也已远离。
四
《三城记》的城市经验,还有一种隐蔽的抒情方式。乡土经验里的抒情倾向于自然、纯粹和朴实,它有着丰富的情感依托作为载体,这一点无须赘述。“城市不是抒情的世界,它是散文的世界”,“那种情绪和心绪是在那里面,是通过词语的缝隙散发出来的或者挤出来的”⑧,城市经验里的抒情是零散的,需要发现和辨析。小说虽以城市书写为重心,但也有关于乡村的叙述。顾明笛生活在城市中,但每到乡村去体验时,都可以感受到自由呼吸的顺畅。在承德塞罕坝,蒙古长调《辽阔的草原》如同天籁,顾明笛为此震撼是因为找到了共鸣之处,于是推杯换盏激情满怀。在和裴志武回家乡调查沙漠污染时,顾明笛一下车就对鸠摩罗什寺充满好奇,对于古凉州、古西域的想象占据了整个大脑,这和他的个人兴趣密切相关,如自己曾写过《象奴妇》的历史小说,还曾对九姓渔户的历史故事饶有兴趣,所以到武威急于走访古刹名寺就显得不足为奇,这也是顾明笛心底藏有的一种朴素情感。塞罕坝的蒙古歌声和武威的西域史留痕在顾明笛的心里都以自然本真化的民间经验而显现,民间艺术和民间情结一直静默于心,这是来自心底的抒情。
《三城记》也关注行走在城市之间的青年们的表情,它可能是零碎的,但它依然属于抒情的范畴。城市里的抒情见之于日常生活中的你来我往、琐碎繁杂,不比田园世界中的低吟或者高歌,不比牧歌情怀中的婉转或者悠远,不比对日出日落大好河山家国命运的抒怀或者比兴,也就是说现代城市里的抒情告别了我们业已习惯的直抒胸臆、悲愤慨叹、热泪盈眶等显现的呈现形式。城市抒情可以伴随着我们在咖啡馆、酒店、人行道、书本日记、电话邮件、写字楼、商场电梯等多样化的时间和空间载体上出现,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抒情基调和抒情内容越来越走向破碎化和平面化,它不再以外在的整体而全面的细节打动内心,而是在凝结了问候、争吵、眼神、想象、烦躁、呆滞等富有日常表情的琐碎中完成情感的输出和接收。个体的抒情范式和整个城市空间的表情有机衔接在一起,所以,城市人群中的情感表达在空间指向上更加多元化。我们结合相关文本内容对此作出分析。如第一个场景,彭姝带着顾明笛来湘菜馆吃饭,正巧碰上“时报四怪”,六人聚餐喝酒的场景就是外露的一种抒情。新人顾明笛碰上四位元老,大家聊的话题并不拘谨,涉及历史、战争、报社工作、采访造假黑窝点,一边啤酒下肚一边话题轮转,所谈内容没有重心、散漫无边但又串联起各自的性情和职业操守。作为公共空间的湘菜馆饭桌又带有私人意味的性质,施越北压低嗓门唱起陇西漫花儿,转而又改为Hip-Hop节奏的说唱,从民谣到流行音乐,这拨儿年轻人的思绪不仅从乡间跨越到城市,并且还触动了乡愁思绪。其间唐婉约还分享了她的新歌《致一位老北京》,歌词以八旗子弟的生活简史勾连起老北京市民的生活观,老炮儿形象是当下青年人对此进行的审美观照,流行文化在调侃和拆解中完成表意,而关于词与物的讨论则映衬出这伙年轻人的表情和情感流动的细节。再如小说写到了甲骨文书店的一次朗诵会。来自四面八方的诗人们不分地域不分长幼不分国别,以诗歌名义聚拢在一起,多声部、跨文化、直白、通俗、呻吟、口号、叫喊、恶搞,这些和诗歌有关的或无关的都集中在一起。城市空间流行俱乐部文化,并构成了文青们抒情、表演、狂欢的开放形式,本质上这样的大众文化形态还是在少数人活动的范围内,也像是城市里的民间所在,但顾明笛对此热情并不高,丧失了在承德坝上的兴致,由此也透视出其心系所在。
小说还写到顾明笛去郝家堡工友夜校给农民工上课的情景,城中村是城市的一道社会景观,参加这种社区义务活动,也是近距离观察进京务工人员遭遇现实表情的机会。在给农民工上课的过程中,顾明笛感受的是深切的温情和信任。从王德乾、刘振西、刘盛亮热烈的讨论中,城乡之间的情感流向瞬间浮现出来,有的农民工的老家面临着强制拆迁、村官村霸、资源不均等多种乱象,虽然人在北京漂泊,但内心里依然割舍不掉故乡,回家过年、看望爹妈、落叶归根甚至是安葬骨灰于故土这些最朴素的真实想法都一一呈现出来,作为倾听者和观察者的顾明笛深受触动。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中回望乡土世界的醇厚、感伤与凝重,这些骨子里流淌着的眷顾、刚毅与守望,也附着在城市的喧哗与躁动中。夜校体验再次让顾明笛回到民间,并体会到来自底层的艰辛,这种细节夹带着丰富的痛苦,但又很可能瞬间就淹没在城市的人群中。然而,对顾明笛来说,上夜课的经历为他抒发内心的悲悯提供了机会,所以当得知刘盛亮被市场巡逻队人员打伤,他鼓起勇气积极奔走去想办法。张柠也提到上述讨论的一些细节“实际上隐含有一种‘到民间去’的冲动”⑨,实际上冲动就可以理解成一种表情,一种夹带着个人意愿和个人选择的表情。
“广州给人的感觉是它永远都在忙碌,节奏相当快,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⑩,但对于顾明笛而言,来到广州还是在继续着精神寻找。小说渲染了南粤之城繁复的吃食、习俗、菜谱、方言等这些地域性较强的符号表征,主人公在施越北、裴志武、劳雨燕的关心下认知了饮食男女的生活景象。《三城记》以“民间”为卷名进行收尾,应该说这是在城市经验书写中留给顾明笛抒发情感的一纸空间,在经历了沪上和京漂的精神游历后,他的心性情怀也应该有个大致归属。显然,和在城市里打拼站稳脚跟知晓城市节奏的施越北相比,顾明笛在广州生活的探求还没有踏进这条路数,其向往田园的心性仍然一直相随,春节赶往白洋淀与劳雨燕会合是其诗性与理性融合的表现。从思想意识的流动来看,顾明笛一直在寻找属于真正的自己,当得知劳雨燕父亲退休要返乡经营山庄后备受鼓舞,自己也乐于有所为。可见,民间情感流淌在顾明笛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行动哲学中。城市的抒情虽然破碎,但顾明笛并没有远离民间,他是城市间一个平淡的抒情者。
本文力求在小说关于城市经验的书写中厘清顾明笛的精神活动,并找到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青年的个人成长路径。“《三城记》的文学理论是站在民间立场来立论的”⑪,从主人公三城行走的人生轨迹看,文青顾明笛心系向往的诗性理想的确一直纠缠在向民间回归的旨愿上。置身于思想文化不断变化的当下社会,“80后”的主人公以己所愿勇敢地去探寻自身的精神立场和思想品格,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城市青年的成长印象,如果说顾明笛“几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⑫也能够成立,那只能说我们审视的标准存在差异。不管顾明笛是个张柠所说的“未完成的人”,还是个“新人物”,他肯定是个案的,但又不仅仅就是个案的。
注释:
①⑤张柠:《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4、388页。
②③⑦⑨何平、张柠:《顾明笛是一个新人物》,《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④王春林:《从一己经验到外部世界》,《文艺报》2018年11月21日第3版。
⑥⑧张柠:《城市经验和城市研究》,《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⑩张柠:《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⑪贺绍俊:《〈三城记〉的文学理论》,《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⑫刘大先:《过盛的经验与过于理性的个体——〈三城记〉与后启蒙时代的精神成长问题》,《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