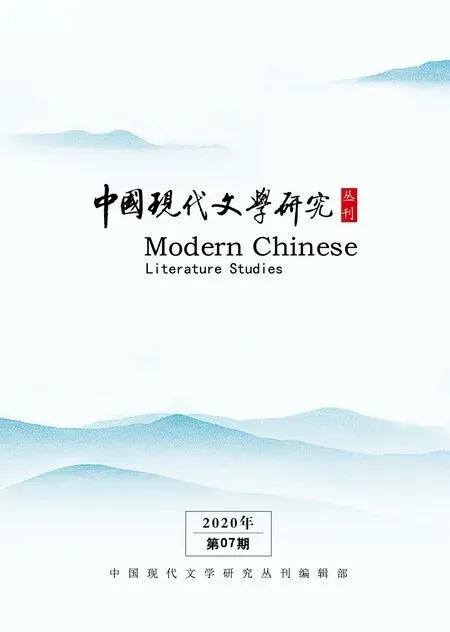与大海再续“缘”
——张爱玲译《冰洋四杰》(部分)的发现
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翻译是重要的一环。张爱玲的文学翻译,包括了英译中和中译英两大部分,还包括了把方言(吴语)译为国语(普通话)。这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家中很少见。张爱玲的英译中,基本上限于美国文学,如人们已熟知的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如华盛顿·欧文和爱默森等美国文学名家的作品,等等。但是,张爱玲还翻译了美国传记小说家佛兰西斯·桑顿(Francis Beauchesne Thornton,1898—1963)的长篇《冰洋四杰》,却一直不为人知。这是张爱玲继《老人与海》之后,第二次翻译大海题材的作品。
十年前,我写《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初探》,文中在分析张爱玲1952年夏再到香港后,何以用笔名发表译作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张爱玲甫到香港,对一九五〇年代初的香港文坛几乎一无所知,她不想过早亮出自己的曾毁誉参半的真名。这有一个有力的旁证。据慕容羽军在《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中说,他在《今日世界》编辑部结识张爱玲,后来他参与香港《中南日报》编务,拟连载张爱玲翻译的一部小说,张爱玲不愿自己的真名见诸报端,坚持使用笔名,与他再三交涉,几经改动,从“张爱玲译”到“张爱珍译”再到“爱珍译”,才算告一段落。虽然这篇翻译小说还没有发现,但慕容羽军的回忆应是可信的。①
这段话中写到的慕容羽军(1927—2013)②,原名李维克,又名李影,生于广州,香港作家。他以小说见长,也写散文和新诗,还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关键的是1950年代初,慕容主编香港《中南日报》副刊。我当时没有直接引用慕容的原话,而只是作了概括。慕容这段回忆出自他的《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一文,最初收入《浓浓淡淡港湾情》一书,现又收入新编的《看路开路:慕容羽军香港文学论集》。③这段回忆比较长,但为了重新提出并重新加以讨论,保持原汁原味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全部照录:
我参加了《中南日报》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今日世界》的朋友谈起张爱玲的译稿交得很准时。已经积存了三部稿了。我灵机一动,问他可不可以把一部稿交给我们的报纸连载。那位朋友大喜,笑道:这是最好不过的方式,反正印书也是希望多些人看到,连载之后再印书,会显得作品更受重视。当下,这位朋友便把一部小说的译稿交给我,然后说:这部小说请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可在报上登出,因为我们要办一个行政上的手续,手续完成之后,我会给你电话。
也不待三个星期,朋友的电话来了,告诉我可以开始连载了。于是我拟了一个预告,交给报社主事人,刊登在第一版的显眼处。
这一显眼预告一登出,立即招来张爱玲的电话。我一接听,她便呱啦呱啦的说:很对不起,想请你帮个忙,不要把我的名字登在报上,可不可以?我听了她这么说,陡然呆住了。我说:你嫌我们的报纸不够名气?这份报纸虽属出未几,销路还算不错呢!
张爱玲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不要给别人感觉到我参加报纸的行列。
彼此对话之后,都没有结论,放下话筒不久,交这份稿给我的朋友拨电话给我,说:张爱玲这人很难缠,她硬是不想在报纸见到她的名字。我说:她刚来过电话,她说的理由并不怎么充分,是否另有特殊原因?朋友说:我猜不出有别的原因,也许这就是有名气的人的怪脾气。
我告诉这位朋友,坦白说出我们的报纸也想借助一下她的名气。朋友也抱歉,表示拗她不过,不如顺她一下,把她的名字取消算了,反正有原作者,没有译者关系不大。
我说:预告也登出了,怎么办?朋友说:你想想办法,我知道你眉头一皱,便会计上心来,就这样吧!拜托你了。
没有商量余地,怎么办?我把这讯息告诉报纸负责人,负责人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说:为甚么不早点声明?她不肯用她的名字,我们又为何要这篇稿?
看来很僵,我忙解释说:这篇稿很好,反正付稿费的不是我们,不如用取巧的方法,把预告改一改,仍依原定的时间发表,把译者的名字最后的玲字改为珍字,正式刊出时,译者名字用行书写得近玲字,算是交代了。
负责人无奈,只好依我的建议,把译者张爱玲写成译者:张爱珍,绘制题头画时,用行书写译者的名字,把珍字写得有点像玲字,算是交代了。
事情并不就此完结,译稿正式登出的那一天,这位姑奶奶的电话又来了,她说:又来麻烦你,我知道你把译者的名字改了,但写出来的珍字,仍然有八九分似玲字,可不可以把张字删去?希望你再帮我这一点忙!很无奈,终于替她删掉了“张”字,变成了爱珍译。我给报馆负责人埋怨了很长一段时间……④
慕容羽军不愧是文笔老到的文坛前辈,这段回忆写得很生动,简直有绘影绘声之效,信息量也确实很大。它明确地告诉我们:一、在慕容主编香港《中南日报》副刊期间,连载了张爱玲翻译的一部小说。二、这部翻译小说在《中南日报》副刊连载时,因译者署名问题,张爱玲与社方搞得很不愉快。三、这部翻译小说在《中南日报》预告时,署名“张爱玲译”,最初刊出时改署“张爱珍译”,最后又在张爱玲的坚持下,再改署“爱珍译”。这就有必要对《中南日报》尤其是该报副刊作一简要的介绍。
香港《中南日报》应创刊于1953年6月18日。⑤关于这份中文报纸的详情,慕容羽军另写过一篇《谈〈中南日报〉——香港报业史作者最大的缺失》,以他曾任该报“副刊编辑”的身份对该报历史和特色作了追溯。慕容对已有的香港报业史和香港文学史著述均未提及《中南日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呼吁“对香港文化有责任的人和有责任的机构,要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有资格、有能力和有信念的人赶快来修补这一‘史’的缺失了”。⑥不少年过去了,慕容的这个呼吁是否已经奏效,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个不容忽视的“缺失”实在是事出有因,那就是《中南日报》已经存世无几,目前香港只有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室藏有零星的四天报纸,⑦就连上述《中南日报》的创刊日期也是我推算出来的,尚无实物可证。关于《中南日报》的资料是如此严重缺失,研究者又何以对这份被慕容认为很重要的报纸进行研读和评估呢?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五份《中南日报》副刊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只有寥寥五份,虽然出版日期并不相连,虽然还不敢说这很可能已是“孤本”,还是极为难得,令我惊喜莫名。这五份《中南日报》副刊的出版日期按序为1953年10月14日、28日、29日和11月2日、3日。从中可以得知,《中南日报》是对开的大报,副刊名“说荟”(或为说部荟萃之意),10月14日的“说荟”在第七版上,其他四天的“说荟”均在第六版上。“说荟”位于整版《中南日报》的中下部,占版面三分之二的篇幅,版面上部三分之一的篇幅为“乐园”版,专门刊载香港影剧信息和关于影剧的专栏文字。
正如慕容羽军在《谈〈中南日报〉》中所坦率承认的,《中南日报》是在1950年代初香港“绿背文化”的大背景下创刊的,这点毋庸讳言。但慕容也指出,《中南日报》自身也有一个衍变过程,“由一个带有‘援助知识分子’机构出版的报纸转变成为纯商业性质的报纸,前后历程超过三年,差不多接近四年光景”。⑧在此过程中,该报副刊“说荟”,就我所得到的五份和香港中大图书馆所藏的四份来看,办得可谓有声有色,用“名家汇集,佳作迭出”八个字来形容,大概并不过分。我所得到的五份“说荟”,均以连载小说为主,一直在连载的有平可(1912—2013)的《走马灯》、潘柳黛(1920—2001)的《一个女人的传奇》、南宫搏(1924—1983)的《杨贵妃新传》、费爱娜(1922—?)的《血染琴弦》,先后连载的有俊人(1917—1989)的《娜拉妹妹》和《有家室的人》,以上均为长篇。还有雷鸣远的《一杯泪》《深井魂》《绳上人》、璇冰的《高跟鞋自传》《佳期》等连载,则应为中短篇了。⑨来自上海的潘柳黛和南宫搏、来自广州的费爱娜,以及香港本地的平可和俊人,均为一时之选,长期活跃于香港文坛。《一个女人的传奇》《杨贵妃新传》《血染琴弦》和《娜拉妹妹》《有家室的人》五篇,后来各自在港澳台出版过单行本。⑩由此应可证明,《中南日报·说荟》确实具有不俗的水准。
现在终于可以说到张爱玲所译的《冰洋四杰》了。这五份《中南日报·说荟》上均刊有连载的《冰洋四杰》,均署“佛兰西斯·桑顿著 张爱玲译”,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具体连载情况如下:
《冰洋四杰》(四)“在血海里辛苦工作” 1953年10月14日
《冰洋四杰》(十八)“约翰做了神父” 1953年10月28日
《冰洋四杰》(十九)“手指似的半岛” 1953年10月29日
《冰洋四杰》(廿三)“鱼雷爆炸” 1953年11月2日
《冰洋四杰》(廿四)“船往一边倒” 1953年11月3日
这五天的连载并不连贯,既无开始,也未结束。我所得到的张爱玲译《冰洋四杰》就这样显得无头无尾,其间也断断续续,令人深以为憾。但从第一则1953年10月14日连载的《冰洋四杰》(四)推断,“说荟”连载张爱玲所译的这部小说应在四天之前即1953年10月11日开始。
佛兰西斯·桑顿作为美国传记小说家,擅长欧美宗教界著名人士的传记,主要著作有《亚历山大教皇:天主教诗人》《十字架:教皇庇护九世的生活》《我们的美国主子:十七位美国红衣主教的故事》等。《冰洋四杰》书名全称为《光荣之海:四位牧师的精彩故事》(Sea of Glory:The Magnificent Story of Four Chaplains)。1943年2月2日晚,纳粹德国潜艇U-223号在海上发现航行中的美国多切斯特号运输船,午夜后不久向该船发射鱼雷进攻。船上四名美国陆军牧师乔治·兰辛·福克斯、亚历山大·大卫·古德、克拉克·波林以及约翰·帕特里克·华盛顿,组织士兵分发救生衣自救。当最后一艘救生艇离开时,四位牧师与那些无法撤离的士兵与船员共同祷告,纳粹鱼雷袭击27分钟之后,多切斯特号消失在汹涌海涛之中,而这四位牧师手挽手站在甲板上祷告,与多切斯特号一起沉没……这部传记小说正是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光荣之海》也即《冰洋四杰》共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George Lansing Fax ,第三章Alexander D. Goode,第四章Clark V. Poling,第五章John P.Washington,分别叙述这四位牧师从军前的经历;第六章结尾,叙述沉船经过以及四位牧师视死如归的事迹。此书1953年2月由纽约普伦蒂斯霍尔(Prentice-Hall)出版社初版,马上3月再版,4月三版,⑪可见大受欢迎,堪称畅销了。这也应是当时香港“美新处译书部”或今日世界社选定翻译此书的原因吧!而张爱玲在当年就将其译出,动作也不可谓不快。有必要指出,她这项翻译工作与翻译《老人与海》《小鹿》《爱默森文集》⑫等一样,无疑也是“命题作文”。
更有必要指出的是,《冰洋四杰》的英文原本厚达250余页,但《中南日报·说荟》连载的张爱玲中译本,据这五天的连载文字判断,应是简短得多。与英文本相应内容对照,不难发现张爱玲的翻译并不忠实于原著,也就是说她并未完全按照小说章节和原文进行翻译,而是选择主要情节和精彩段落进行节译和摘译。当然,基本上中译文中的每句话都可找到英文原文,并非另行改写。所以,虽然我手头只有五天的连载文字,从中应可推断,张译的《冰洋四杰》固然经过删减,故事仍属大致完整。至于每日连载时的小标题,很可能是“说荟”编辑所加,以示醒目。连载第廿四节已是“船往一边倒”即快要沉没了,那么,这部《冰洋四杰》也许到了第廿七或廿八节就译完了,小说在《中南日报·说荟》上连载完毕估计也在1953年11月7日、8日左右,而整部《冰洋四杰》的连载时间当约一个月。
下面就选出内容密切相关的1953年11月2日和3日连载的《冰洋四杰》第廿三节“鱼雷爆炸”和第廿四节“船往一边倒”,以领略一下张爱玲翻译《冰洋四杰》的译笔:
廿三:鱼雷爆炸
船上的钟敲了两下。是夜里一点钟。从此那钟就没有再敲过。
一两分钟后,一只鱼雷猛烈地撞进“陶切斯打”号,在船腹里,远在水平线下。
鱼雷爆炸起来,那受伤的船踉跄摇晃着,士兵们和衣躺在舱位上,突然给扔到甲板上。也有人直飞过去撞在隔舱板上。
灯火管制下的幽暗的电灯立刻熄灭了,全船都陷入黑暗中,士兵们抢着到上面去,一路上只好四面乱摸,恐怖到极点。鱼雷撕破了这只船薄薄的外皮,正好在机器间里爆炸了,猛烈万分。蒸气管子炸了,蒸气冒出来,机舱的人不是被烫死,就是被灼伤。燃料舱都裂开了,把里面的油吐出来,因此每一个梯子,每一个狭窄的过道,都成了危险的地方。
在三十秒钟内,有一百人死了,烫伤了,炸得肢体残缺不全,或是淹死了。
士兵们向扶梯乱纷纷爬去,扶梯已经歪得很厉害了,因为那船往左面倾侧着。士兵们争先恐后爬上去,来到甲板上,甲板上大风呼呼吹着。
从前虽然屡次演习过,船要沉了怎样上救生船,也听过演讲,中了鱼雷怎样死里逃生,现在统统忘记了,这些人都是平民,突然变成兵士,新学到的军事纪律这时候完全忘光了。每一个人心里只有这一个思想,怎样救自己的命。
廿四:船往一边倒
然后,人们克服了自己的恐怖,在混乱中稍微恢复了点秩序。医生与医疗队的人把他们的皮包一把拾起来,就往下面走,和那潮水似的涌到甲板上来的人正是迎面撞。他们也许感觉到自身的危险,但是他们不去想它,继续往前走,去救那些受伤的人。他们的电筒射出微弱的光,在货舱的黑暗中戳来戳去,舱中已经充满了阿莫尼亚呛人的臭气。
远远在他们底下,在机器间里,一只锅炉爆炸了。
甲板上,情形也不比下面更好。刚中了鱼雷的时候,在最初的大混乱中,船主就伸手去抓那汽笛绳索,要拉出那六声警报,这是护航队还没离开国境内洋面上就约好了的信号。
汽笛吼了三次,第四声就断了气;在那汽笛的钢铁喉管里,那声音像一个空洞的嘲讽的咳嗽声。
因为船往一边倒,右舷的救生船向里面歪着,士兵们努力解开那些救生船。有几只船放下水去,疯狂地撞着大船倾斜的船身。也有几只滑脱了,就这么掉了下去;有些人在最初几秒钟的恐怖中纵身跳下海去,救生船掉下来正好碰在他们身上。
这时候风向转了,变成西北风,有几只救生船安全地下了水,又被大浪淹没了,把士兵又吐到水里去。处处有救生衣的红灯,在水上闪闪发光,像一星星的火。
人们仓皇地砍断救生筏的绳索,有的在黑暗中一颠一颠地漂走了,谁都没来得及上去。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中南日报·说荟》连载张爱玲译《冰洋四杰》的同时,也在连载潘柳黛著《一个女人的传奇》,这是潘柳黛到香港后所创作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张爱玲和潘柳黛一直不和,张在香港与邝文美聊天时明确表示:“想不到来了香港倒会遇到两个蛇蝎式的人——港大舍监、潘柳黛。”⑬而潘柳黛后来在香港写的《记张爱玲》中也毫不留情地揶揄张爱玲脾气很怪,“她不像丁芝那么念旧,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更不像苏青的人情味那么浓厚,说她像关露,但她却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⑭在上海时,张爱玲和潘柳黛从未在同一刊物同一期发表作品,而这次在《中南日报·说荟》上却同台献技,一是以创作,一是以翻译,大概她俩都未料到。这恐怕也是她俩以这种方式共同亮相的唯一一次。
本来写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新的疑问又随之产生。慕容羽军明明回忆,张爱玲在《中南日报》副刊上连载的那部外国小说,译者署名经过“张爱玲”到“张爱珍”再到“爱珍”的转变,但《冰洋四杰》的译者署名,我所有的五期连载,始终都是“张爱玲译”,并无任何变动,“张爱珍译”和“爱珍译”更从未出现过,这与慕容的回忆完全相反。我当初读完了这五份《中南日报·说荟》就疑窦顿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慕容记误还是另有隐情?
机缘凑巧的是,我不久前又有幸见到一位香港友人提供的另一部长篇译本《海底长征记》的书影,这个疑问或可迎刃而解了。《海底长征记》封面署“[美]比齐原著 爱珍译”,版权页署“原著者:E. L. Beach 译者:爱珍”,为香港中南日报社1954年8月初版。这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叱咤风云的美国海军潜水艇舰长E. L. Beach 具有自传色彩的纪实作品,书前有一篇落款“中南日报一九五四年八月”的《卷首语》:
这一篇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写实记载。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起在本报综合版“中南海”连续刊载,将及三阅月。全文长逾十二万字,译笔简洁流畅,深受读者欢迎。兹应各方纷纷要求,特提前出版单行本,想读者均以先睹全豹为快也。
这就清楚地显示,这部《海底长征记》最初于1954年5月6日起在《中南日报》的另一综合性副刊“中南海”连载了“三阅月”,由于“译笔简洁流畅,深受读者欢迎”,故即推出单行本。而译者署名“爱珍”是最大的亮点,因为这与慕容羽军所回忆的正好吻合,张爱玲确实用过“爱珍”这个笔名也就得到了证实。很可能《海底长征记》在《中南日报·中南海》连载,广告署名“张爱珍”,连载之初署名“张爱珍”,最后改定为署名“爱珍”,也未可知。这个推测当然有待连载《海底长征记》的《中南日报·中南海》真的出现才能最后证实,但即便有部分出入,也不至于太大,毕竟出版单行本时署名“爱珍”已确凿无误。何况在连载完《冰洋四杰》之后,张爱玲再继续在《中南日报》副刊上连载新的《海底长征记》是顺理成章的,就像当年她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十八春》之后又继续连载中篇《小艾》一样。唯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冰洋四杰》署“张爱玲译”在先,张爱玲并未提出异议,何以后来的《海底长征记》反要改署“爱珍译”,也许《冰洋四杰》仍属于传记文学作品,而《海底长征记》已与文学相距更远?总之,慕容羽军所回忆的那部张爱玲翻译“小说”应该就是指《海底长征记》,或者他把《冰洋四杰》与《海底长征记》混为一谈了。
张爱玲与大海有“缘”。她从上海到香港大学借读,来去都是航海。她再到香港后,曾短期赴日,去来也是航海。她远赴美国,仍是航海。有趣的是,张爱玲曾经明确表示不喜欢大海:“我对于海毫无好感。在航海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世界上的水实在太多。我最赞成荷兰人的填海”,⑮尽管她在小说中也曾写到航海。但又有谁能想到,她在香港期间,为了稻粱谋,竟一而再,再而三,先后翻译了三部与大海直接有关的美国作品,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桑顿的《冰洋四杰》和比齐的《海底长征记》,恐怕这只是个巧合而已。张爱玲有独到的文学眼光,她对《老人与海》的评价很高,称之为“伟大的作品”。⑯但对《冰洋四杰》和《海底长征记》这两部译本,张爱玲生前却从未提及,海内外张爱玲研究界以前也毫无所知。这个多年的空白现在总算得到了部分弥补。可惜的是,《冰洋四杰》在《中南日报·说荟》上的连载,我们现在只掌握区区六分之一,但愿完整的《冰洋四杰》连载全文还存在于天壤之间,我期待着它的出现。
2020年4月25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注释:
①陈子善:《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初探》,《张爱玲丛考》上卷,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②慕容羽军的生年,有两种说法,一为1927年,来自慕容本人所撰《自传》(刘以鬯主编:《香港文学作家传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6年版,第810页);一为1925年,系他夫人提供之身份证所示,为黎汉杰编 《看路开路:慕容羽军香港文学论集》所采用。本文采用“自传说”。
③慕容羽军:《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浓浓淡淡港湾情》,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看路开路:慕容羽军香港文学论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19年版。
④慕容羽军:《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看路开路:慕容羽军香港文学论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184页。
⑤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室所藏《中南日报》1954年1月8日第205号往前推算,《中南日报》应创刊于1953年6月18日。
⑥慕容羽军:《谈〈中南日报〉——香港报业史作者最大的缺失》,《看路开路:慕容羽军香港文学论集》,第236页。
⑦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室藏有的《中南日报》,依出版时间先后为1954年1月8日第205号、1月11日第208号、1月12日第209号和1月19日第216号,共四份。
⑧慕容羽军:《谈〈中南日报〉——香港报业史作者最大的缺失》,《看路开路:慕容羽军香港文学论集》,第236页。但慕容羽军2009年2月接受许定铭采访时,又说《中南日报》“出了两年多”(见许定铭《他冲天去了》,《城市文艺》2013年12月第8卷第6期)。到底《中南日报》存世“两年多”还是“接近四年光景”,待考。
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四份稍后出版的《中南日报·说荟》,仍在连载潘柳黛《一个女人的传奇》、平可《走马灯》、贾爱娜《血染琴弦》、俊人《有家室的人》,以及南宫搏新的长篇《西施新传》等。
⑩据刘以鬯主编《香港文学作家传略》所刊平可、潘柳黛、南宫搏、费安娜和俊人的《小传》所述统计。
⑪据《冰洋四杰》英文本1953年4月第3版版权页所示。
⑫张爱玲译《老人与海》1952年12月香港中一出版社初版、《小鹿》1953年9月香港天风出版社初版、《爱默森文集》1953年11月香港天风出版社初版。《冰洋四杰》应是张爱玲在香港继《老人与海》《小鹿》之后公开发表的第三部译作。
⑬邝文美记录:《张爱玲语录》,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3页。
⑭潘柳黛:《记张爱玲》,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⑮⑯张爱玲:《序》,《老人与海》,香港中一出版社1955年再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