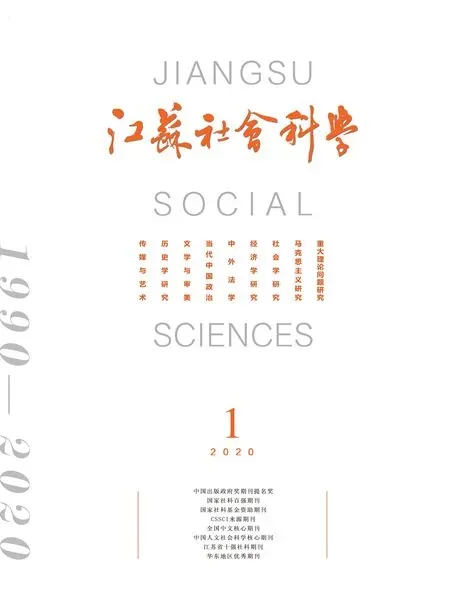中国电影中婚恋伦理的代际嬗变
贾冀川 王春晓
内容提要 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从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对“革命+恋爱”二元结构的探索、对爱情与婚姻政治化的审视,到对现代婚恋问题的思索、对自由恋爱的勇敢表达以及新世纪对多元化婚恋倾向的选择,中国电影中婚恋伦理的代际嬗变反映出几代中国电影人对理想婚恋模式的艰辛探寻,再现了中国人对婚恋幸福不懈追求的足迹,亦折射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不同时代的思想变革和社会价值观的曲折走向,中国电影亦由此呈现出鲜明的代际风格与时代特征。
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云:“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本说的是一对殉情大雁生死不渝之情,却常被用来描述人世间一见钟情的痴情男女。然而,人世间恋爱婚姻之复杂岂是殉情大雁可比?亦非痴情男女一见钟情那么简单。理想的爱情婚姻是什么?中国每一代描写了婚恋的电影导演和他们每一部描写了婚恋的电影,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不同的回答,既与导演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主张息息相关,和时代环境的风云变幻、社会氛围的瞬息万状、政治语境的波谲云诡相呼应,又折射出中国婚恋伦理乃至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辛脚步,亦由此呈现出鲜明的代际风格与时代特征。
一、对封建婚恋伦理制度的批判
辛亥革命后,除了皇帝没了,一切照旧,如鲁迅先生说的,“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1]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仍大行其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为妻纲”之类婚恋伦理与婚姻制度仍是青年人的枷锁和桎梏。取材于郑正秋家乡潮州封建买卖婚姻习俗,由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郑正秋和张石川1913年合作拍摄的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可以说是电影界发出的批判封建婚恋伦理和制度的第一声呐喊。郑正秋认为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这个观点自然也体现在由他编剧的影片《难夫难妻》之中。影片中的故事从媒人撮合说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婚姻中本该是主角的青年男女却成了被父母、媒婆和金钱所支配、根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这部故事片上映引起了空前轰动,人们竞相观看。柯灵曾高度评价这部影片,他说:“(《难夫难妻》)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比胡适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著名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还早六年,内容也比后者有深度。”[1]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柯灵电影文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然而,《难夫难妻》止于对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展示和批判,至于理想的婚恋应当是什么样,影片并没有能够触及。
进入二十年代,不少导演涉足婚恋题材,有但杜宇的《海誓》(1922)、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22)、管海峰的《红粉骷髅》(1922)、邵醉翁的《女侠李飞飞》(1925)、洪深的《爱情与黄金》等,其中的婚恋观念既有欧化的浪漫爱情,也有传统的才子佳人。也就在此时,离开电影十年的郑正秋重新回到电影领域,拍摄了大量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片,试图为封建婚姻桎梏中的青年男女指出出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郑正秋提出:“戏剧之最高者,必须含有创造人生之能力,其次亦须含有改正社会之意义,其最小限度亦当含有批评社会之性质。”[2]郑正秋:《我所希望于观众者》,《明星特刊》第3期《上海一妇人》号,1925年7月27日明星影片公司出版。然而,郑正秋接着提出:“取材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这是我们向来的老例。”[3]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明星特刊》第3期《小朋友》号,1925年6月5日明星影片公司出版。1925年,郑正秋编剧的《最后之良心》颇有代表性。暴发户秦仁伯逼迫一个债户把女儿王秀贞给自己的傻儿子做童养媳,逼迫另一个债户将儿子刘家麟做自己骄奢淫逸女儿的上门女婿。后来经历种种家庭变故,家破人亡的秦仁伯突然良心发现,在病逝时遗嘱家麟、秀贞结为夫妇,遗产悉赠二人。对封建婚姻深刻批判意识与调和矛盾的改良主义构成这部影片的基本内核,二者的缝合也是郑正秋这一时期社会片的基调。此外,朱痩菊与徐琥导演的《采茶女》(1924),洪深编导的《卫女士的职业》(1926),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玉洁冰清》(1926)等描写婚恋的作品,也表现出了调和矛盾的改良倾向。这种改良主义恰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精神的最大分野。
与郑正秋不同,第一代导演中的侯曜在大学时代就曾参加过文学研究会,且深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贯穿了他早期的问题剧创作。进入电影领域后,他编导了一些问题电影,其中就涉及到恋爱问题、婚姻问题。《摘星之女》(1925)被称为“恋爱问题剧”,剧中白秋霞与画家冯月影自由恋爱,但横遭军阀之子强婚的干扰,历经磨难后二人终于走到一起。《爱神的玩偶》(1925)则是“婚姻问题剧”。少女明国英不满父亲和继母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到杭州一所小学任教,与校长之弟罗人俊相爱,历经艰辛,两人终于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在这两部电影中,青年男女不再被动无助地听候家长、命运的摆弄,而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将恋爱婚姻这样关乎一生命运的“终身大事”掌握自己手中。显然,与郑正秋相比,侯曜的婚恋观更站在了时代精神的前沿。
第一代导演所处的是现代中国民智初开的年代,落后的婚恋伦理与婚姻制度迟滞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郑正秋描写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社会片,揭露并批判了诸如寡妇守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蓄婢制度、童养媳等封建落后的婚姻伦理现象,随着这些影片的广泛传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侯曜在自己电影里倡导的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更多地是表达了青年一代对理想婚恋的美好愿望。尽管如鲁迅先生说的,没有经济的自主,出走的娜拉们“免不掉堕落或回来”[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但是,不管怎么说,以郑正秋和侯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毕竟推动中国电影在婚恋伦理方面迈出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二、“革命+恋爱”的婚恋模式
“革命+恋爱”本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以蒋光慈创作为代表的一种小说创作模式,前后持续了约四、五年时间。但是,由于创作的日益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这种模式遭到左翼批评家的批判后被摈弃。进入30年代后,在阶级矛盾没有缓解的情况下,民族矛盾又日益加深,两者叠加一起涌入到电影领域。于是,个性解放的“恋爱”加上群体解放的“革命”这种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关注现实人生、追寻理想婚恋的重要选择。当然,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别婚恋模式,也是中国电影婚恋伦理在现代化曲折进程中的重要界碑。
由程步高导演、夏衍编剧的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1933)公映后,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曾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的热烈欢迎。在电影《狂流》中,为战胜水患,小学教师刘铁生领导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代表傅柏仁的革命斗争是主线,而刘铁生与傅柏仁女儿秀娟的爱情是辅线。这种革命为主、爱情为辅的模式在早期左翼电影中风行一时。《狂流》之后,由洪深导演、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1933),由徐欣夫导演、郑伯奇和阿英合作改编的《盐潮》(1933)等影片也采用了这种模式。在这些影片中,封建势力、反动当局和地方恶霸沆瀣一气,残酷压榨和盘剥农民、盐民,农民和盐民团结起来奋起反抗,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两大阶级尖锐冲突中,影片中的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爱情可以超越甚至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然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大潮中,个人的爱情追求只是涓涓小溪,只有且必须汇入阶级斗争的大潮中才有意义,而这也恰恰是这些影片剧尾青年人通过生与死的革命斗争悟到的人生道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革命失败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这些“革命+恋爱”结构的左翼影片深受欢迎,鼓舞着青年一代投身于社会革命的历史洪流中。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的部分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抗日救亡的内容,“恋爱”的成分日益减少,重要性不断下降,在功能上甚至成为“革命”的障碍。在卜万苍导演、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1933)里,有关“革命”的内容就包括以周淑贞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女性走进工厂、工人小学、贫民窟、建筑工地,也包括她积极参加一二八战争抗日救护工作,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构成“革命”的主体。而大学生张榆的逃婚,与虞玉的热恋,与陈若英的爱情纠葛,以及对周淑贞的追求等“恋爱”内容成为时代最摩登女性周淑贞心无旁骛、矢志革命的有力衬托。这一时期其它经典左翼电影作品如《风云儿女》(许幸之导演、田汉和夏衍编剧,1935)、《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1937)、《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1937),乃至抗战胜利后的史诗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1947)也基本延续了这一结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在抗战期间,抗日救亡成了“革命”的唯一内容,无关抗战的“恋爱”几乎成为被制裁的对象,如有人提出:“我们要制裁一切胡闹的醉生梦死与抗战无关的电影作品。”[2]弃扬:《今后的电影与影评》,《抗战电影》杂志创刊号,1938年3月31日。在《中华儿女》(沈西苓编导,1939)的第三个故事《抗战中的恋爱》里,青年B听不见炮声、看不见血迹,他沉醉于个人的“恋爱”,这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整体社会氛围里是那样不合时宜,甚至几乎就成了犯罪。
当然,在30、40年代,亦不乏只有“恋爱”没有“革命”的电影作品,被左翼电影界严厉批判的部分软性电影就是代表。但是,大部分有良知的第二代导演都深刻地体认到:在恋爱婚姻方面的个体解放,必须以包括经济自主在内的群体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乃至民族解放为基础和前提。因此,在国家和社会动荡的年月,尽管每个人的婚恋各有不同,但青年人自觉地把个人的恋爱婚姻与阶级、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史册上书写自己精彩的人生画卷。这种爱情和婚姻令人神往,自然也就成为30、40年代青年人理想的婚恋模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不少影片通过“革命+恋爱”模式的内核,为我们展现了广阔复杂的社会风貌,工人生活的艰辛、青年知识分子失业的痛苦、达官显贵的纸醉金迷,在鲜明的对比中呈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革命”与“恋爱”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随着阶级、民族矛盾斗争的白热化,这种失衡也就愈发明显。这使得与“恋爱”紧密相连的自由、个性解放等内核,受到了与“革命”相关的纪律、集体观念等越来越多的约束乃至压制。但不管怎样,“革命+恋爱”模式是中国电影婚恋伦理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三、政治意识裹挟下的爱情与婚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于1950年4月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内容成为国家法律。在新的时代,电影导演们镜头中的婚恋必须面对新的时代语境。而随着第一代和第二代导演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淬炼的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下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电影界的主力军。爱情和婚姻在第三代导演的电影里呈现出新的风格特点,即爱情与婚姻不断政治化,这自然与“十七年”“文革”时期国家和社会日益政治化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呼应。
1950年,由歌剧改编的电影《白毛女》(王滨、水华导演)上映后很快红遍大江南北,超过当时任何一部中外电影的观众纪录。在喜儿和大春之间的感情上,电影对歌剧原作进行了较大改编。影片开始阶段,增加了两人互帮互助、情投意合及准备成亲的情景;在情片结尾,获救的喜儿头发变黑,与大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极富人情味儿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改编,十分符合中国老百姓朴素、善良的观影愿望,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歌剧原作的政治意识。当然,与左翼电影中还算独立于革命的婚恋相比,电影《白毛女》告诉我们:在地主阶级压迫下,以喜儿为代表的年轻人靠自己不可能获得爱情和婚姻的幸福,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给喜儿们带来幸福。《柳堡的故事》(王苹导演,1957)中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上海姑娘》(成荫导演,1957)里青年知识分子陆野和白玫的爱情,都始终被置于民族解放的革命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集体利益之下;其它如《芦笙恋歌》(于彦夫导演,1957)、《寻爱记》(武兆堤导演,1957)、《青春的脚步》(苏里导演,1957)、《花好月圆》(郭维导演,1958)、《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导演,1959)、《今天我休息》(鲁韧导演,1959)等影片对爱情也是类似的处理。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日益泛滥,爱情逐渐成了禁忌,“英雄人物都必须是奉行禁欲主义的样板,爱情是不成文的道德禁区”[1]罗以军:《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红霞》(冯一夫、华纯、李育五导演,1958)里的红霞与赤卫队长赵志刚是一对未婚夫妻,但他们只有为革命牺牲自己的革命豪情,极少儿女私情;《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61)里的洪常青和吴琼花之间只是领路人和追求翻身解放的女奴的关系,两人之间竟然没有发生爱情。不只是英雄人物,普通人的爱情也成了禁忌。前文提到的《上海姑娘》于1959年公映时的广告还注明:“该片有严重缺点错误,希广大观众批判”,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批判公映”的先声。由谢铁骊执导改编自柔石小说《二月》的《早春二月》(1963),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肖涧秋和陶岚的爱情,但这部电影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批为毒草。“文革”期间,在“三突出”原则下,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更加单纯、洁净,尽管他们外貌仍堪称俊美,但却没有任何个人的私欲,成了革命的符号。《白毛女》在“文革”期间被改编成芭蕾舞剧样板戏,后被摄制成样板戏电影,其中大春和喜儿之间的感情戏被全部删去,大量增加有关喜儿反抗性、斗争性的内容。影片结尾喜儿也不再是和大春走到一起,而是在党的引领下参加了八路军。爱情在“文革”期间完全离开了电影,样板戏电影中青年男女主人公只谈革命不谈爱情。
任何人都无法逃离政治,政治是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婚恋的过度政治化,电影里婚恋中的人也就失去了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复杂性而不断被符号化,中国电影婚恋伦理的现代化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对于“文革”时期文艺的凋零状况,毛泽东在1975年也表达了不满。他在两次谈话中指出,“样板戏太少了,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6页。
四、从传统婚恋走向现代婚恋的沉重脚步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文艺政策,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重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电影领域,中国第四代导演开始了自己短暂的辉煌时代。与前几代导演不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下,第四代导演镜头下的爱情与婚姻更加丰富饱满,也更加多姿多彩,从总体上展现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婚恋走向现代婚恋的沉重脚步。
在胡炳榴的《乡音》(1983)里,妻子陶春对丈夫余木生总是一句“我随你”,道出了传统婚姻中夫唱妇随、男尊女卑的婚姻内核,陶春即便最后得了癌症也无怨无悔。而与此相对应,陶春的妹妹杏枝独立、自主、前卫,常常批判木生家没有“民主”。通过杏枝,电影含蓄地表达出被禁锢已久的新一代青年追求自主婚恋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也是导演的希望寄托所在。黄健中的《良家妇女》(1985)中,十八岁的杏仙嫁给了六岁的小丈夫,这种大媳妇、小丈夫的畸形婚俗给当地女性带来了巨大痛苦。杏仙以巨大的勇气冲破这种畸形婚配枷锁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婚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冲破束缚、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现代婚恋内涵的基本要素。真正走入婚姻,在强大传统压力的惯性下,难保杏枝和杏仙又会缩回传统,甚至成为传统的卫道者。《人·鬼·情》(黄蜀芹导演,1987)以女性立场描述一个女人的成长史。尽管女主人公秋芸通过饰演钟馗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但她的爱情和婚姻却在若隐若显的男权秩序里不断遭到挫败。与前两部电影相比,从婚恋伦理的角度看,《人·鬼·情》从另一个层次上在追问,独立女性或准确地说取得事业成功的独立女性难道只能嫁给“舞台”,她们的美好婚恋在哪里?除此之外,王好为的《潜网》(1981)、滕文骥的《都市里的村庄》(1982)、张暖忻的《青春祭》(1985)、谢飞的《湘女萧萧》(1986)、陆小雅的《热恋》(1989)等影片,也从多个侧面探索了理想婚恋问题。
在第四代导演中,吴天明执导的《人生》(1984)和《老井》(1986)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把中国社会的婚恋观从传统走向现代脚步的沉重表现的更细腻、也更真实。《人生》里的高加林和刘巧珍本是令人艳羡的一对,但进城后地位提高的高加林却另攀高枝。高加林错了吗?追求个人的爱情和幸福不是现代婚恋观的真谛吗?然而造化弄人,高加林又被退回到了农村,社会地位重回原点。此时农村的巧珍已结婚,而城里的黄玉萍和他分了手,他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当全社会都在谴责高加林的负心时,或许《人生》已经叩击到了现代婚恋观的真谛,即婚恋的双方不仅要相爱,且在精神和文化的追求上也要平等。与传统婚恋观相比,在社会变动愈来愈剧烈的时代,现代婚恋里双方的关系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促进、提高的过程。如果一方迟滞不前,婚恋必然会出现问题。《老井》中的旺泉和巧英也未能走到一起,万水爷的阻挠只是显性的、外在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旺泉和巧英二人所受不同文化影响导致的性格、心态的差异。孙旺泉更多地受到了传统宗法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他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家族、部落责任的使命感;而赵巧英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文化新潮,她忍受不了家乡的贫穷,向往外面的世界。因此,即便没有万水爷的阻挠,两人也很难走到一起。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际,尽管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了近三十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造成的思想行为惯性,现代婚恋观为全社会普遍接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纵观第四代导演的电影,其中的婚恋或多或少都受到传统文化的沉重压力,甚至有意无意地认同、赞美传统。正如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的,“对传统文化,第四代导演既有批判和反思,但又似乎饱含温情,恋恋不舍”[1]贾冀川:《第四代导演的现代启蒙意识及其历史局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其实这也并不令人惊讶。陶春、杏仙、秋芸、高加林、刘巧珍、巧英、旺泉等人的命运,恰是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踯躅徘徊但又坚定前行的真实身影。
五、敢恨敢爱的悲剧人生
横空出世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就对婚恋的表达而言,第五代导演用自己独特的镜头语言表现了青年男女们敢恨敢爱,但又往往以悲剧结局的婚恋人生,既让人耳目一新,又令人唏嘘不已。
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红高粱》(张艺谋导演,1987)以对生命的礼赞、以对强烈风格化的影像追求、以内在精神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第五代成熟的标志。张艺谋在谈到这部电影时说:“影片《红高粱》是表现大胆,表露敢爱、敢恨这样一种热烈的生命态度。”[2]张艺谋:《张艺谋电影创作谈》,张会军、谢小晶、陈浥主编《银幕追求——与中国当代电影导演对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在影片中,那欢天喜地而又恶作剧式的颠轿、那惊心动魄的野合、那慷慨激昂的酒颂、那悲壮而惨烈的牺牲,无不表现出一种酣畅淋漓、豪放旷达的婚恋观念和生命意识。而那红色的太阳、红色的高粱酒、红绣鞋、红绣球、红盖头、红花轿等等,都张扬着一种生命的色彩,表现了对于自由婚恋的热烈追求。因此,在“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那强悍的野性的生命冲动、那敢恨敢爱的豪情,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化中人格萎缩、死气沉沉的消极面,也远离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冲淡平和的传统人格,使敢爱敢恨的人性观、爱情观在“我爷爷”和“我奶奶”身上表现得空前丰富和饱满。张艺谋此后的两部电影《菊豆》(1990)和《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这种婚恋观。菊豆被禁锢在无性的婚姻“秩序”中,寻爱的本能使她和杨金山的侄子杨天青相恋、偷情,生下了天白,并在囚禁了杨金山后半公开地生活在了一起。有着叛逆与反抗性格的十九岁大学生颂莲,因家庭变故嫁给财主陈佐千做第四房姨太太,为在勾心斗角的几房太太中争得专宠而费尽心思。然而,“一夫多妻制”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法则最终导致颂莲发疯。两部电影都以悲剧结局,但菊豆和颂莲敢于挑战封建婚恋禁锢、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气和行动令人肃然起敬。
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霸王别姬》(1993)和《风月》(1996)也表现了对自由和真爱的坚定追寻和坚持。《黄土地》里的翠巧受八路军顾青的影响,决心挣脱封建买卖式婚姻追寻八路军顾青,追寻自由。她逃离夫家,冒险夜渡黄河。《霸王别姬》中的菊仙尽管是一个妓女,但她比大多数人都更忠贞,对自己的爱情更坚持。在爱上段小楼后,菊仙可以为了他而付出一切。在《风月》里,苏州显赫家族庞府的主事——大小姐如意明知对方是骗子,但是禁不住深宅大院外的诱惑,竟与专门敲诈女人钱财的“拆白党”郁忠良发生了一场不羁之恋。在陈凯歌的这几部电影中,追寻自由和真爱的代价都是十分沉重的——翠巧消失在滚滚黄河水中,菊仙上吊自杀为爱而死,如意被郁忠良用鸦片毒害成神志不清的废人。此外,胡玫的《女儿楼》(1985)、田壮壮的《特别手术室》(1988)和《摇滚青年》(1988)、黄建新的《轮回》(1988)、李少红的《红粉》(1994)等电影,也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青年人在追求真爱中的困惑、伤痛与执著。
第五代导演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不同身份的女性,不论她们是农村妇女、大学生、富家小姐抑或是妓女,尽管等待她们的往往是一场场婚恋悲剧,但是,面对世俗的冷眼、婚恋传统的枷锁,“她们不屈从命运的摆布,勇敢甚至激烈地反抗命运,哪怕仅仅得到片刻的欢乐”[1]贾冀川:《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与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这种拒绝平庸、拒绝妥协、拒绝浑浑噩噩,努力甚至决绝地追寻自由、追寻真爱、敢恨敢爱、要活出精彩的生命态度感染了那个时代,影响了一代人。第五代导演的这种婚恋表达拓宽了婚恋伦理的内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电影婚恋伦理的现代化进程。记得《红高粱》中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在当年曾风靡一时,歌词云:“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呀,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中我的头呀!与你喝一壶呀!红红的高梁酒呀!”其中所蕴含的敢作敢为、敢恨敢爱、粗犷豪放的情感让当年观影的亲历者至今想来仍血脉喷张、心潮澎湃!
六、新世纪婚恋的多元化
如果说第五代导演侧重于表现传统文化给青年人的爱情和婚姻带来的悲剧命运,且其中还包含有不少对社会人生的传奇书写的话;那么,新世纪的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则聚焦于生活中的普通人。通过弱化人物形象,平静而冷峻地讲述平凡个体生活化的爱情婚姻,从而凸显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贾樟柯的电影《站台》(2000)结尾处,崔明亮倚靠在自家沙发上睡着了,尹瑞娟抱着他们的孩子看着眼前的炉灶。经过十年的艺术流浪之后,崔明亮回到家乡与尹瑞娟结婚生子。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普通的人,平凡的归宿。在《三峡好人》(贾樟柯导演,2006)中,这种平淡却艰难的情感生活被表现得更加显著。韩三明和麻幺妹的结合是非法的,分开十六年后韩三明看到幺妹过得并不幸福,毅然要与幺妹复婚,并承诺以当初买妻十倍价格赎回她。这就是底层人们呈现出斑驳而本色状态的婚恋故事:似有若无的爱情,却合乎民间情义的逻辑。贾樟柯曾经抒发自己的感想:“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受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2]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六十年代中国电影导演档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年版,第365 页。普通平凡人家的婚恋状态即在第六代导演群体的这种创作理念下得以呈现。
当然,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人的婚恋生活也出现了不同以往各个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张扬的《无人驾驶》(2010)、娄烨的《浮城迷事》(2012)、王小帅的《左右》(2007)和《闯入者》(2014)、贾樟柯的《山河故人》(2015)均表现了平凡人家婚姻的不稳定性:中年人受到越来越多的诱惑、第三者的介入导致婚姻的危机、夫妻双方经济力量的失衡、社会对婚姻的评价标准也不再统一……这些电影通过对不稳定婚姻的审视,管窥了新世纪普通人婚恋的困境与隐忧。
在新世纪,第六代导演之外还活跃着众多年轻导演,这些导演已经很难再用“代”来命名。而他们镜头里表现的婚恋更趋多元化,与这个多元时代人们的爱情表达方式更加丰富相呼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徐静蕾导演,2005)表达了一种女性主导的爱情。陌生女人从少女至死爱恋着邻居的作家,她执着地单恋这位男性,不求物质与名分。“我爱你,与你无关”,歌德在十九世纪写出的爱情诗句成为新世纪唤起女性自主意识、摆脱男性窥视的独立宣言。电影《小时代》(郭敬明导演,2013)展现了社会无论上层、中层还是底层对高端消费的执迷,爱情中的行为动机与表现也受到金钱的巨大影响。相较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独立的爱情观,这里的爱情成为资本控制力的一种符号,个体的自我意识消失,情感资本化。与此同时,在消费社会中,对青春时代爱情的怀旧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它通过给予大众想象性怀旧体验满足了当下电影受众的情感消费需求。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赵薇导演,2013)的上映引发了对青春爱情怀旧题材的拍摄热潮,《被偷走的那五年》(黄真真导演,2013)、《匆匆那年》(张一白导演,2014)、《同桌的你》(郭帆导演,2014)、《致青春:原来你还在那里》(周拓如导演,2016)即这种爱情模式的复刻。
在当今这个多元的时代,人们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婚姻的内涵也日益多姿多彩。与此同时,在今天日益成熟的消费社会,电影作为一种消费品需要满足不同观众群体对不同婚恋内容的需求。于是,普通人甚至边缘人,青春、怀旧,悲剧、喜剧等各种题材、风格、体裁的婚恋多元表达就成为这个时代电影的真实书写。这种多元化、内涵丰富的婚恋状态构成了当前中国电影婚恋伦理的主要内容,是婚恋伦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当然,婚恋伦理的现代化是永远的进行时,中国电影人对此的探索永无尽头。
结 语
其实,爱情、婚姻本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论高低贵贱,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爱的权利和自由。然而,这种美好的婚恋理想却不是轻易得来的,它是经过几代人的抗争、奋斗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自20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多年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风云变幻,催生了不同时代的婚恋表达,而中国几代电影人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爱情和婚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追寻真爱的坚定脚步,展现了电影婚恋伦理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又透过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为我们或再现、或折射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的变迁。
当然,我们也不必否认,每一代导演在电影中展现的婚恋伦理观念是丰富多彩的,甚至同一位导演在不同电影中呈现的婚恋伦理观念也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代导演电影中呈现婚恋伦理的整体风貌是鲜明的,代际嬗变的轨迹是清晰的。尽管每一代导演镜头里的恋爱和婚姻都涂染上了那一时代的斑斓色彩,但是青春不变,一代代年轻人对理想婚恋的追寻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