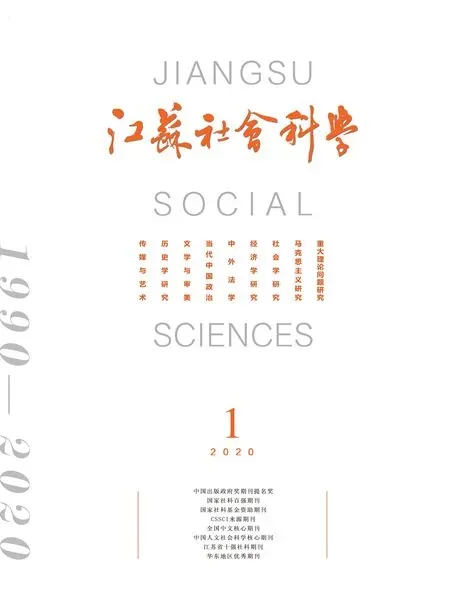论开明派的小品散文
姜 建
内容提要 在小品散文方面,开明派作家以共同的追求形成了独特的风貌。他们善于描写江南的山水风物,尤其偏爱民间与乡土,体现着平民式的审美情感;他们追求真诚质朴的情感表达,有着能够映照其人格的“本色”风貌;他们的散文,隐含着兼顾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维度,在表达美好感情的同时,以日常语言的运用为焦点,努力推广现代汉语基本的语言规范。
作为新文学作家,开明派成员以众多的作品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其中许多都成为经典。他们在众多体裁和题材领域都体现了非凡的创造力。比如朱自清曾经是诗人,他的抒情长诗《毁灭》一发表即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被誉为新诗运动以来,利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技巧的第一首长诗,是新文学中的《离骚》和《七发》;叶圣陶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家,除大量短篇小说外,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描写辛亥革命至大革命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历程,被茅盾称为是新文学的“扛鼎”之作。不过,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它们更多地显示了个人对于相关体裁、题材的独特兴趣和独特理解,更多地打着鲜明的个人烙印。唯有在散文方面,开明派作家显示了共同的兴趣和惊人的一致。朱自清和丰子恺是著名的散文家;叶圣陶不仅是小说家,也是重要的散文家;夏丏尊的作品虽不算多,但他的《平屋杂文》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郑振铎有《山中杂记》《海燕》《西行书简》《蛰居散记》等多种散文集。此外,宋云彬的《破戒草》《骨鲠集》、刘薰宇的《南洋游记》、章克标的《风凉话》、贾祖璋的《鸟与文学》、周建人的《花鸟虫鱼》等等,显示了他们在散文领域多方面的探索追求。即使理论气质最重的朱光潜,除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外,也有《慈慧殿十号》等这样的抒情散文。
所以,在回顾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散文成绩时,郁达夫在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就收录了丰子恺、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四人的作品,占入选十六家中的四分之一。而按周作人的理解,《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本拟收入”而未能如愿的,还包括了章克标等人的散文。此外,问世早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专注于散文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与“大系”一样,向来被视为深具文学史意识的经典选本。此选本入选散文十六家,其中就包括了朱自清和叶圣陶。此书后删削更名为《现代小品文钞》,朱、叶二人依然在列。就此可以看到,开明派作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更在散文领域做出了突出的建树。
问题在于,从广义的角度,散文家族有众多成员,它不仅包括抒情散文或者说小品散文,也包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这样偏于说理的议论文,包括《破戒草》《风凉话》这样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的杂文,包括《孔子》《陶渊明》这样重在叙述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包括《鸟与文学》《花鸟虫鱼》这样把文学与科学融为一体的“科学小品”等。但小品散文一向居于散文家族的核心位置,也最能体现这一文体的特质、代表这一文体的成就。鲁迅所说的“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指的是此类散文,《中国新文学大系》所选录的主体同样是此类散文。在通常的意义上,它构成了判断一个人、一个社团或一个流派散文成就的基本点。由此,本研究将把其他类型的散文暂时搁置或者放入相关论题,而着力探讨其小品散文。
问题还在于,散文是一种最富于个人色彩的文体,正如郁达夫所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2]郁达夫:《现代散文导论(下)》,《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06页。这种鲜明的个性,对于完整地展现作家的个人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本文的着重点在于从文化文学流派的层面去揭示他们在众多散文作品中所蕴含的共同精神质地与审美气象。为此,这里将努力割舍对专属于作家的个人风格的探讨,而将目光聚焦于他们个人风格背后的更深层的共同特征。
鉴于此,我们的论题将围绕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郑振铎等几位擅长小品散文的开明派作家展开。
一、自然江南与平民江南
阅读开明派作家的散文,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对江南山水风物的鲜活描摹,和缱绻其间的浓浓乡情、乡思、乡愁。春天歇在石埠头边的小船和舱中嫩绿的莼菜,夏日清晨深巷传出的“卖栀子花来”的爽脆叫声,新秋时节的青花头巾、夏布短裙,和紫赤的胳膊、玉色的藕枝,冬令深夜霜月当窗、松涛如吼、湖水澎湃的白马湖风声,以及水光迷离、灯影晃荡的蔷薇色秦淮河,穿梭在城墙的倒影、飘拂的柳枝、酒旗茶幌中的小艇和艇中悠然的茶客、艇尾粗头乱服的船娘,小河边的弯弯钓竿和中秋月下的紫砂酒壶,白胖胖的蚕虫和紫甜甜的桑葚[3]详见朱自清《看花》《扬州的夏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叶圣陶《藕与莼菜》、夏丏尊《白马湖之冬》、丰子恺《忆儿时》诸篇。……,交织成一幅立体的多姿多彩的烟雨江南风景风情风俗画,也明确无误地给这些作品打上鲜明的江南印记。
开明派作家绝大多数是江南人,其余个别成员也在江南生活多年,早已被江南所同化。所以,对他们而言,江南不仅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家乡,也是他们的题材宝库和灵感源泉,是他们审美触角最敏锐、情感趋向最稳定的所在。可以说,江南始终是开明派作家的一个情结,是他们创作内容和美学意象的一个巨大存在——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固然几乎通篇说的是江南,朱自清写得最动人、流传最广的散文也始终离不开江南。郑振铎身材的高大魁梧似北方人,性格的质直单纯也似北方人,然而他却是福建人。他甫离家乡,立刻兴起浓浓的乡思之情,他从翻飞的海燕身上,看到了家乡燕子的身影:
当春间二三月,轻飔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集市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灿烂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声,已由这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再几只却隽逸的在潾潾如谷纹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1]郑振铎:《海燕》,《郑振铎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23页。
这样的景色,分明不是北方也不是福建,而是江南。江南水土的成长经历和江南文化的多年浸润,早已把他锻造为一个地道的江南人,所以他的眼中景色和心中景色都是江南,他的“家乡”也只能是江南。这或许应了叶圣陶的一句话:“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2]叶圣陶:《藕与莼菜》,《叶圣陶集》第5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发现他们江南风景风物描写中的一个核心元素——水。所谓“烟雨江南”,离开了水,江南就不再是江南了,至少也大为逊色。所以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湖、河、潭、塘、瀑等各种形态的水,和各种与水有关的物象、意象,更满溢着由水引发的情思。仅在朱自清笔下,就不仅有人们熟悉的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与满溢着荷香月色的清华园荷塘,还有荒寒素净的玄武湖,蔓衍曲折的护城河,绿得醉人的梅雨潭、梅雨瀑,淡若飞烟的白水漈……朱自清甚至觉得北方无水,水是江南的专利。显然,对朱自清和开明派作家而言,这里的水不是实指,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审美内涵丰富的情感指徵。无论是朱自清《春》那样的欢快、《绿》那样的缠绵,还是郑振铎《海燕》、叶圣陶《藕与莼菜》那样的怅然,抑或丰子恺《忆儿时》那样的从容,开明派作家在对与水相连的物事的描画中,丝丝缕缕之间,都浸透着对江南故乡的无言夸耀和“能不忆江南”的深深情愫。
水的元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开明派作家而言,水不仅是一个审美对象,更是一种审美方式。水的轻盈灵动、清新秀美,赋予了江南文化的婉细精巧,也磨练了江南文人审美触角的细腻柔婉、舒卷自在。开明派作家的散文中无处不在的那种对自然物象、意象的灵巧捕捉和精致表达,那种糅合了自然风物与人生感悟的物我无间的韵味,有着一种江南文人专属的审美风致。当他们用这样的审美方式去面对并非江南的景物时,也能写出江南特有的氤氲气息。清华园里的荷塘,是北国常见的景色,并非江南所独有。但在朱自清的笔下,“我”因郁闷而踱步荷塘,视线由亭亭如舞女裙的荷叶和碧天星星般的荷花,而过渡到流水般泻在花与叶上的月光,由光影奏出的和谐旋律而注意到树上的蝉噪水中的蛙鸣,由眼前的热闹而联想起六朝江南的风流,由慨叹历史的旖旎不再而回归现实的冷寂,于是,散文在工笔与写意的交织、描摹与想象的转换中,借助视觉、听觉、联觉的延展,和写景与抒情的穿插,一笔笔、一层层地渲染烘托出了江南游子在北国美景中的所见所感所思,传递出一种触目伤怀的感伤和隐隐约约的不安。朱自清所见所写并非江南,但在作者“江南式”的审美观照下,北国的风光却因江南的意象、江南的人文和江南的情致而被赋予了浓浓的江南趣味。于是,清华园的荷塘,其地理属性早被忽略,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它分明属于江南。
如果对开明派散文的江南风味作进一步解读,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身边的日常琐事、凡间景物,与乡土和市井有深刻的关联,充溢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和世俗的平民喜好。叶圣陶对乡野秋虫的牵挂、对在水门汀天井中种植花草的执着,丰子恺对二胡的赞许、对杨柳和燕子的偏好,都充满了平民气息。朱自清钟爱的江南美食,从扬州的红烧猪头、烫干丝到南京的芝麻烧饼,都是寻常物事,不脱平民享受。同样,天井里的牵牛花,路灯下的麻将桌,深巷夜半的叫卖,松江街头的胡桃云片[1]详见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天井中的种植》《牵牛花》《骨牌声》《深夜的食品》、丰子恺《山中避雨》《杨柳》《松江的胡桃云片》、朱自清《扬州的夏日》《南京》等文。,也与市井凡尘紧紧相连。这样一类景象,与由婉转的昆曲、名贵的绣品、雅致的书斋、闲逸的谈吐、意境悠远的文人书画以及散发着墨香古韵的线装书等物事所构建的江南意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把这种江南称为“文人江南”的话,那么开明派作家笔下的江南,姑且可以称为“平民江南”。在我个人的理解中,一般而言,在精神向度上,“文人江南”指向由历代文人创造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经典,指向文人推崇的闲雅精巧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尚,与江南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精神结晶相勾连;“平民江南”则指向鲜活的市井生活和乡土气息,与江南文化中那些质朴本真的世俗生活和清新灵动的自然环境相勾连。从它们都能够涵养江南文人的文人情怀、都能够传递江南文化特有的诗性诗意的角度看,它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共通性,但“文人江南”更多代表着人文的精神的层面,“平民江南”则更多代表着世俗的自然的层面,两者分属江南文化的两翼,其精神向度由此也存在明显区分。开明派作家对自然和泥土的依恋,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与投入,对民间的情感寄托和精神皈依,指认了他们平民的文化身份和情感趋向,是有别于文人士大夫所代表的“文人江南”的。由此,他们无疑应该属于“平民江南”的文化阵营。
需要指出的是,在开明派作家身上,这两种江南并不是对立的、互相隔绝的,他们的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就内在地规定了他们并不排斥“文人江南”,只是,平民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们在“文人江南”与“平民江南”之间取舍的情感天平。
1926年夏,郑振铎为逃避沪上的酷热,与几位亲友来到风景胜地莫干山,他的散文集《山中杂记》便记录了这次山居避暑的经历。摆脱尘俗,投入自然的怀抱,在潺潺流水和皎洁月光的陪伴下,偕三二好友随兴闲聊,谈往事,思故友,论才学,诗酒相伴,清静悠闲,这是江南文人所激赏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历代江南文人的笔记书札中常见的场景。无独有偶,《山中杂记》集中所收《月夜之话》,也给读者提供了这样一幅场景:
月色是皎洁无比,看着她渐渐的由东方升了起来。蝉声叽~~叽~~叽~~的曼长的叫着,岭下涧水潺潺的流声,隐约的可以听见,此外,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月如银的圆盘般大,静定的挂在晚天中,星没有几颗,疏朗朗的间缀于蓝天中,如美人身上披的蓝天鹅绒的晚衣,缀了几颗不规则的宝石。大家都把自己的摇椅移到东廊上坐着。
初升的月,如水银似的白,把她的光笼罩在一切的东西上;柱影与人影,粗黑的向西边的地上倒映着。山呀,树林呀,对面的许多所的屋呀,都朦朦胧胧的不大看得清楚,正如我们初从倦眠中醒了来,睁开了眼去看四周的东西,还如在渺茫梦境中似的;又如把这些东西都幕上一层轻巧细密的冰纱,它们在纱外望着,只能隐约的看见它们的轮廓;又如春雨连朝,天色昏暗,极细极细的雨丝,随风飘拂着,我们立在红楼上,由这些蒙雨织成的帘中向外望着。那末样的静美,那末样柔秀的融和的情调,真非身临其境的人不能说得出的。
……红栏外是月光,蝉声与溪声,红栏杆内是月光照浴着的几个静思的人。[2]郑振铎:《月夜之话》,《郑振铎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7-178页。
这是他们“文人江南”的一面,同样在《山中杂记》中,还有“平民江南”的一面。从“月光光,/照河塘,/骑竹马,/过横塘”的童稚天真,到“共哥相约月出来,/怎样月出哥未来?/……不论月出早与迟,/恐怕我哥未肯来”的痴情女对负心郎的怨怼,从“采萍你去问秋英,/怎么姑爷跌满身?/他说相公家里回,/也无火把也无灯”的妻子对夫君的猜疑,到“真鸟仔,/啄瓦簷,/奴哥无母这数年。/看见街上人讨母,奴哥目泪挂目簷。有的有,没的没,/有人老婆连小婆!/只愿天下作大水,/流来流去齐齐没”的独身汉对社会不公的愤恨,这些民谣都充溢着民间乡土的质朴爽利,和赤裸裸火辣辣的激情。于是,雅与俗、庙堂与草野,两种情调在散文中相遇相碰撞,形成明显的张力。如果说,散文起首所渲染的意境是搭建了一座优雅的文人舞台的话,那么这个舞台所上演的,却是一出俚俗的乡野大戏。或许有人认为,散文中的场景设置,并非郑振铎的刻意选择,更多只是不经意的如实的再现。然而,惟其不经意,也许更能体现那种无意识的文化偏好。对民生艰辛的关注,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这是可以从散文集《山中杂记》中的《三死》《苦鸦子》等散文中反复得到验证的。
二、真诚质朴与本色品格
与开明派散文对自然江南、平民江南书写紧密联系的,是其真诚质朴的情感表达。当我们关注开明派散文家创作个体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朱自清的清新隽永、叶圣陶的凝重厚实、丰子恺的流畅平和、夏丏尊的愁苦慈悲和郑振铎的真率质直等等,但把他们合为一个整体的时候,真诚质朴便成为他们情感表达的共同基础。
抒情本是小品散文最基本的文体特征。只是,如何抒情,常因作家知识背景、个性气质、文学观念、审美追求的不同,和对作品构思立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表达。正是基于这些不同,才造成了散文世界的千姿百态。在新文坛上,无论是周作人的平和冲淡,还是徐志摩的繁复富丽,抑或郭沫若的激情慷慨,冰心的轻倩隽丽,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都有很高的成就和影响。但对于开明派散文家而言,他们则以抒情的真诚质朴,构成了不同于他人的共同特点:第一,在对日常琐事的娓娓叙述中,自然地触发情感的开关,导入情感的流脉,既保留着生活原生态的毛茸茸的质感,也由此进入以情主导情理相融的境界。第二,情感的表达完全尊从个人生活和精神欲求,不做作也不滥情,不夸饰也不雕琢,质朴诚挚,直抒胸臆,有一种英华内蕴、温润腴厚的美感;第三,对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的真诚表达,是从他们生命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成为他们自我灵魂的写照,作品的“文格”直接对应于作者的“人格”,有读其文如见其人之感。
这样一种抒情方式,源于他们质朴本真的个性气质,和他们所尊奉所追求的君子文化人格,也与他们建立在“真诚”文学观基础上的对散文的独特理解和审美追求直接相关。正是这种理解和追求,决定了开明派散文的独特面目。在他们看来,散文是一种非虚构文学,这种“非虚构”的特性就内在地、本质地规定了散文无法借助于叙事作品的虚构戏剧化或抒情作品的夸张想象,不仅需要忠实于个人经验,更需要见个性见心灵见人格。在这个意义上,散文的本质和生命便在于“真”。
这种“真”至少包含了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散文所表达的,是“真”的生活和情感。它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性情的自然要求,任何虚伪浮夸玩戏的、只注重形式而忽略“真”精神的文字,都是有违真实必须力戒的。郑振铎曾经直率地指摘旧文学:“我们中国的文学,最乏于‘真’的精神,他们拘于形式,精于雕饰,只知道向文字方面用工夫,却忘了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表现。”[1]郑振铎:《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二》,《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版。《文艺知识》编者曾询问朱自清“《背影》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怎样发现题材?怎样产生那意境?怎样写成的?”这些问题都隐隐指向朱自清从谋篇立意到运营文字的匠心,指向散文写作的技术层面。但朱自清的回答却拒绝了编者的诱导而直指情感层面:“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1]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表现“真”的生活和“真”的情感,成为了开明派散文的立根之基。
第二,正源于对这种“真”的情感的看重,散文必须勇敢地袒露“自我”、直视心灵,也不回避自己的心灵弱点或精神杂质。朱自清说他自己“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2]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第34页。,这并非是一般人们以为的作家的自谦,而是他的大实话。夏丏尊在《怯懦者》中,以大量细节描述了他自己在面对兄弟病危亡故时的种种手足无措的纠结怯懦,那种“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的真切况味,打着夏丏尊特有的印记。叶圣陶曾经说:“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剖析自己尤其深刻,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象听一位密友倾吐他的肺腑之言。”[3]叶圣陶:《夏丏尊文集·序》,《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把“我意在表现自己”[4]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第34页。当作自己散文创作的基本准则或根本旨归,叶圣陶也奉劝青年朋友“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5]叶圣陶:《诚实的自己的话》,《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这里,“表现自己”和“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的内涵,至少如叶圣陶所说的“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主张,一个意思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象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6]叶圣陶:《读者的话》,《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82期,1923年8月6日。。1924年,朱自清曾写过《旅行杂记》等旨在揭露讽刺大人物可笑嘴脸的散文,但叶圣陶却不喜欢此类作品,认为他“是在模仿着什么人”[7]见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失去了作者自己的面目,而对朱自清的《背影》《飘零》之类的重在表现作者自己情感的作品则大加赞赏。这一褒一贬,其价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因为这样的“真”是与作者的自我心灵和精神世界紧密相连的,因而它不应该是部分的浅层次的真实,而是整体的深层意义上的真实,从而,作品中隐含的人格形象须对应于作者的人格,两者形成相互映衬的关系。余光中曾经批评朱自清的散文“摆不脱自己拘谨而清苦的身份”,说:“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余光中认为:“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风格(亦即我所谓的‘艺术人格’),往往是他真正人格的夸大,修饰,升华,甚至是补偿。无论如何,‘艺术人格’应是实际人格的理想化:琐碎的变成完整,不足的变成充分,隐晦的变成鲜明。读者最向往的‘艺术人格’,应是饱满而充足的;作家充满自信,读者才会相信。”[8]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上海〕《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这里不打算评价余光中“艺术人格”说的对错,也无意由此推断余光中散文中的艺术人格都是作者“夸大”“修饰”“升华”“补偿”的结果,只需要指出的是,在开明派散文家那里,这种理解不仅不适用而且是尽力避免的。任何在作品中将其艺术人格“夸大”“修饰”“升华”“补偿”的做法,都偏离了开明派散文家所追求所坚守的“真诚”立场。果真如此,则他们的作品,就不再是心灵中自然流淌出来的“真”的结晶,而是与他们所批评的旧文学一样,是“做”出来的。
正因为开明派散文家普遍坚持从自己的身边琐事出发,自然地袒露内心情感,所以众多论者都肯定、激赏他们的散文带着“体温”,能够映照其人格的“本色”风范。比如对于朱自清散文,赵景深说:“朱自清的文章有如他自己的名字,非常‘清’秀。他不大用欧化的句子,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像淡香疏影的梅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他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9]赵景深:《现代小品文选·序》,北新书局1933年版。杨振声说:“他论人论事,遣词造言,到处是那末恰当,那末正常,那末入情入理。他的文章没有惊词险句,也没有废词败句。没有奋郁不平,也没有和光同尘。有的是讽刺但不是刺激;有的是幽默但不是冷嘲。与他的为人一模一样,一切是平正,是温厚,是情理得中,一句话,中庸之至。”[1]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新路》第1卷第16期,1948年8月。对于叶圣陶散文,丁玲有这样的判断:“叶老的文章,正如他的为人一样:严谨、仔细、温和、含蓄、蕴藉,才情不外露,不随风使舵,不含小便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2]丁玲:《叶圣陶论创作·序》,《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对于夏丏尊散文,郑振铎的评价是:“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绝不急就。”[3]郑振铎:《悼夏丏尊先生》,《文艺复兴》第1卷第5期,1946年6月1日。
在这个意义上,开明派散文家带着真性情的散文,常常成为作者人格的真实写照。他们作品的感人,不完全来自于艺术上的高妙,而是与他们人格的坦荡率真紧密联系,是人与文互相支撑的结果。由此,他们的散文,实实在在进入了古人所说的“人文合一”的至高境界。
三、散文语体与教育维度
朱自清在提到自己的散文《谈抽烟》的时候说:“《谈抽烟》下笔最艰难,八百字花了两个下午。”[4]朱自清:《你我·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如何“艰难”不得而知,但无外乎作者从谋篇立意到遣词造句各个层面的反复斟酌再三推敲,因为朱自清曾经说自己“写作散文,很注意文字的修饰。语句的层次和词义,句式,我都用心较量,特别是句式”[5]朱自清:《关于写作答问》,《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不妨即以《谈抽烟》为例提供一则旁证。文中有这样一段:
客来了,若你倦了说不得话,或者找不出可说的,干坐着岂不着急?这时候最好拈起一支烟将嘴堵上等你对面的人。若是他也这么办,便尽时间在烟子里爬过去。各人抓着一个新伴儿,大可以盘桓一会的。[6]朱自清:《谈抽烟》,《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此文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前,两位编辑杨振声和沈从文为文中一个字的用法发生了分歧。杨振声觉得“时间”如何“爬”?应该用“消逝”才准确。但沈从文则同意作者的用法,觉得“爬”字更好。揣度沈从文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个“爬”字,将抽象的“时间”概念过程化、具象化了,有动感,见精神,是比“消逝”更好的。有趣的是,这一字之争,本为细枝末节,但显然,朱自清为沈从文体察并认同了自己的匠心而欣然而得意,所以郑重其事地在日记中留下了一笔[7]1933年10月1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说:“容(按指容庚)告我金甫拟改《谈抽烟》中‘爬’字为‘消逝’,从文为余辩护,‘消逝’二字似不如‘爬’字为好。”详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如此考究语言,在朱自清那里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他曾在《欧游杂记·序》中,以“是”字句、“在”字句和“有”字句为例,具体说明他是如何“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8]朱自清:《欧游杂记·序》,《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的。对此,叶圣陶曾深有感触地说:“他作文,作诗,编书极为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的翻检有关的材料。文稿发了出去发现有些小节目要改动,乃至一个字的不妥,宁肯特写一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9]叶圣陶:《朱佩弦先生》,《中学生》1948年9月号,总203期。
朱自清如此重视散文的语言问题,是因为其中隐含了他对自己散文创作的独特定位。朱自清说过:“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一方面是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1]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这段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朱自清散文与他的国文教师身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就是说,朱自清在创作散文的时候,心中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读者,那就是青年学生,尤其是需要通过阅读和写作来理解把握白话文的表情达意功能的中学生。始终关注中学国文教育的朱自清,对于文学教育之于中学生的作用和中学生国文教学的关键点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加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所以文艺教学应该注重词句段落的组织和安排,意义的分析”[2]朱自清:《中学生与文艺》,《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2-475页。。由教育而国文教学而语言,朱自清建构了一条三段论式的清晰的逻辑线索。这条线索,揭示了朱自清散文隐含着一个许多散文家所忽略的与教育功能相联系的独特维度。
重要的是,朱自清散文的教育维度,并非仅是朱自清散文的个人特征,而是开明派散文家群体的共同特征。比如叶圣陶对自己的散文,也表达过与朱自清几乎完全一样的意思:“由于识见有限,不敢放笔乱写,就把范围大致限制在文字和教育上。”[3]叶圣陶:《西川集·自序》,《西川集》,文光书店1945年版。普遍的国文教师经历和对中学国文教育的持续关注,使得开明派散文家们熟悉青年学生的国文程度,并根据他们的国文训练水平创作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作品。翻检开明派作家的散文创作,他们的大量作品本就是为青年学生而作,如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如《中学生》杂志上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人的大量散文作品。即使是面对社会发声,他们也努力将散文写得符合青年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习惯。阅读他们的作品,无论作者是谁,都离不开质朴平实、温润蕴藉、周密妥贴、简练晓畅、明白如话、清新隽永的基本判断,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甚至,针对不同作者的评价,经常是可以互换的,比如在说到朱自清散文的时候,叶圣陶称“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4]圣陶:《朱佩弦先生》,《中学生》1948年9月号,总203期。,而这样的评价,是完全可以移赠给叶圣陶自己的。
之所以强调开明派散文内在的教育维度,是因为这一维度构成了开明派散文最与众不同的特质。简而言之,它不再是一种纯粹放飞自我的个人精神游戏,也不再是仅仅考虑文学审美的单向度结构,而是构成了兼顾文学与教育的复式空间。在这个复式空间中,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规定。在内容层面,重在体现作品的“美育”功能,讲求意义的表达。但这个“意义”,不是那种完全个人化的超迈甚至幽玄的深思妙想、灵心慧性,而是人类基础性的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认知。在形式层面,为建立现代汉语写作可遵循的基本规范,在结构上讲求层次丰满而不复杂,意思表达清楚完整、文气贯通;在语言上力避冷僻晦涩的字眼,也不堆砌形容词,更不夹杂外来语,通过对质朴真切的常用语词的有效组织,达到准确生动、朴素传神、洗练流畅、朗朗上口的效果;在笔调上不主张天马行空呈才使气或掉书袋抖机灵,而是提倡有真意、勿卖弄,去雕饰、见平实,追求一种清新隽永的韵味。证之夏丏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叶圣陶、朱自清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叶圣陶的《文章例话》等,可以轻易发现,开明派的散文与他们的文章学、语文教学论著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完全可以互相说明的。
这里不妨以朱自清的《春》与俞平伯的《赋得早春》为例,来具体观察两类散文的差异。之所以选择《春》与《赋得早春》,是因为两者有太多的相同,也有本质的不同。两文可称同题,且均作于1933年,写作时间仅差一天;作者年岁相仿,时年朱自清三十五岁俞平伯三十四岁;二人同时出道,1920年代初均以新诗闻名于时,1920年代中期以后均把主要用力点转移到散文方面;二人经历类似,又长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同一所校园,任教于同一个院系,经常出入于同一类文学空间甚至同一个文学活动;二人为挚友,往还密切,心意相通,凡有新作均相互传观,相互评点。只是,如此多的相同依然掩不住两文的明显差异。虽说朱自清文是为初一国文教材所写的课文,俞平伯文是给大学毕业生的临别赠言,为适应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要求,两文在行文语气上自然会有所差异。但即使考虑到这种差异,两文在整体面貌和精神气质上的不同,依然是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
朱自清的《春》,在内容上,围绕着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等自然和生活景象,一步步描摹出春意盎然的鲜活画面,一层层渲染出春天来到时的勃勃生机和人们对于春天的欣悦之情,洋溢着逼人的青春气息。在形式上,经过提炼的纯粹口语,形成生动流畅的语势;短句构成的轻快节奏,如春泉般的活泼、富有弹性;精心挑选的常用语词经过周密安排恰如其分,构成画面饱满笔调单纯、不含一丝渣滓的澄明纯粹。由此,全文从内容到形式互相照应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不同于《春》的重在抒发人类对于春天的共同感受、和示范语体文的基本描摹技巧,《赋得早春》则重在传递作者对于春天的个人体验,和借叙议相间笔法体现的独特审美追求。作者以自己与春有涉的诗词文旧作为主体,以一种悠哉游哉的文人风度,在从从容容、散散漫漫的笔调中,传递出生命如“风霜花鸟互为因缘,四序如环,浮生一往”的人生感慨。在内容上,作者将八股应制的陈年古董、鲁迅与成仿吾的笔墨官司、开明书店的专题稿约、雪莱关于“春天”的诗歌名句都信手拈来,古今中外,涉笔成趣,颇得议论风生之妙;在语言上,作者杂糅文言与白话、书面语与口语、中文与英文音译,嘻嘻哈哈、曲曲折折,也很见亦庄亦谐之趣。不同于《春》的清澈见底,《赋得早春》如浑浊的老酒,在涩味和回甘中,散发出十足的书卷气,笔调老到老辣甚至有点老气横秋。其文如阅遍人世、饱经沧桑的老者,他袖笼着双手,眯缝着狡黠的眼睛,看着自己恍如隔世的生命过往和四季代序的春花秋月,面对在残梦与新梦中交替的学生,以“究竟滋味怎样,冷暖自知”的不置可否,见出某种过来人的洒脱闲逸或者满不在乎。所以朱自清称它“文太俏皮,但老到却老到”。
显然,《春》与《赋得早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位作者也意识到这种差异,所以俞平伯称《赋得早春》“与《春》比殆差二十年也”[1]1933年2月23日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而朱自清则把此评语记入了自己的日记。作为同时出道的同龄人写于同时的同题散文,笔法韵味的老嫩相差了二十年,这显然不是才具高下或用心与否所能解释的。唯一的可能性在于:在散文写作方面,两人有着不同的美学追求,由此带来不同的用力方向。朱自清关注着白话文或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进程,将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向青年学生推广语体文的教育性散文,并在文学性与教育性之间寻找到语言这个关节点。这就决定了他的散文偏于普及性,追求“切题”,着力方向在于基本的语言规范。他曾向青年学生推荐自己的写作经验:“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入手。”[2]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他反复告诫青年学生:“先把话写清楚了,写通顺了,再注重表情,注重文艺性的发展。这样基础稳固些。否则容易浮滑,不切实。”[3]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朱自清全集》第4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484页。俞平伯则不考虑散文的教育功能,而是在意于周作人所指点的“涩味与简单味”,在意于物外之言题外之旨,追求文人的雅趣高致和纯属个人的文学气息,追求“人书俱老”的为文境界。这是两类质地完全不同的散文,周作人分别称为“纯粹语体文”与“雅致的俗语文”[1]见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周仁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朱自清散文和俞平伯散文恰可视为两类散文的代表。他们两人,一个以“平民化的文化人格”体现“淑世主义(民本主义)的文学精神”,追求散文的“雅俗共赏”;一个以“贵族心态的知识分子情趣”体现“趣味主义、审美理想主义”,追求散文的“曲高和寡”。由此见出,“趣味主义的小品文与淑世主义的‘语体文’之间确乎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2]周仁政:《朱自清与俞平伯:京派散文的两极》,〔长沙〕《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这样的观察,不管其界限是否“不可逾越”,无疑是深有见地的。
对开明派散文的这种兼重国文教育的特点,他们的同时代人看得很清楚,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早在1930年代中期,郁达夫就说过:“叶绍钧……所作的散文虽则不多,而他所特有的风致,却早在短短的几篇文字里具备了,我以为一般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3]郁达夫:《现代散文导论(下)》,《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版。1948年朱自清去世的时候,多篇悼念文章都提及朱自清的散文的教育性及其与语体文运动的深刻关联。李广田说:“作为文学工作的一部分,在语文方面朱先生下过许多工夫。语文是文学的主要工具,他对于文学的看法也就决定了他对于语文的看法。”[4]李广田:《朱自清先生的道路》,《中建》(北平版)第1卷第10期,1948年12月5日。沈从文说:“对于生命在成长发展中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属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的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正,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5]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新路》第1卷第16期,1948年8月28日。朱光潜说:“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上品古文,而用字却是日常语言所用底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底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也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佩弦先生的作品不但证明了语体文可以做到文言文的简洁典雅,而且可以向一般写语体文底人们揭示一个极好底模范。我相信他在这方面底成就是要和语体文运动史共垂久远底。”[6]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正因为开明派散文突出的教育功能和示范意义,所以在不同时代它们均受到教育家们的青睐,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郑振铎、丰子恺等的多篇作品,都反复出现在中小学各级国文教材中。即使在语文教育体系已经相当成熟的当下,他们的散文,还依然是语文教材中的常客。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做到了如朱光潜所说的“在这方面底成就是要和语体文运动史共垂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