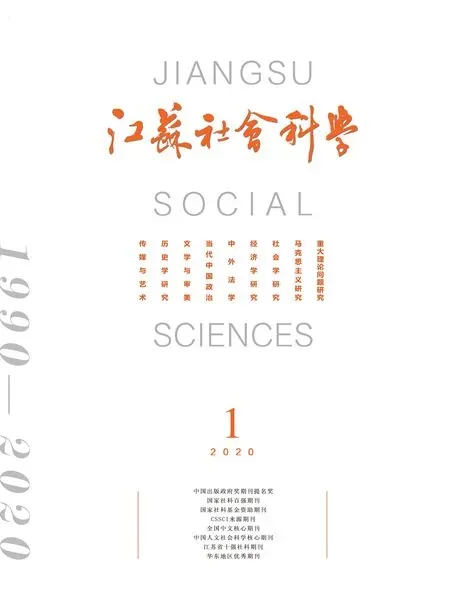论被遗忘权法律保护的必然性及其法理依据
吴姗姗
内容提要 被遗忘权一词来源于法语“le droit à l'oubli”,即犯罪人在服刑期满后要求其犯罪信息不再公开的权利,以保障和促进其再社会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数据上传便捷,搜索引擎发达,信息终端的存储量激增,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的问题显得愈加迫切。有鉴于此,本文从被遗忘权的权属之争以及法律自身完备性需求等方面着手,探讨被遗忘权保护的必然性及其法理依据;主张被遗忘权保护已成为立法与司法实践肯定的普遍性权利,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对于与之相关的被遗忘权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就全球范围而言,有关被遗忘权的研究,学界似乎大多是从民法保护、商法保护、人权法保护等角度展开的,而且在理论上呈现出日趋成熟的态势。而相关研究表明,被遗忘权实际上是源于刑事司法领域,只是在民商法中被深入研究和应用,在刑事法中反而遭遇“被遗忘”[1]参见郑曦:《“被遗忘”的权利:刑事司法视野下被遗忘权的适用》,〔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4期。。有鉴于此,本文将探讨被遗忘权法律保护的必然性及其法理依据,从刑法、民法、商法等方面论证被遗忘权保护的必要性。
一、被遗忘权的提出
1.被遗忘权的缘起
关于被遗忘权的缘起,学界各种观点杂陈,莫衷一是。有研究者认为,首次提出“被遗忘权”这一构想的是有着“大数据之父”称号的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2]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201页。。舍恩伯格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大数据的取舍之道是把有意义的留下来,把无意义的去掉,让遗忘回归常态。”[1]Lawrence Siry,“Forget Me,Forget Me Not:Reconciling Two Different Paradigm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Ken⁃tucky Law Journal,2014(103),p.313.而另一些学者则否认了这一说法,在他们看来,被遗忘权显然来自法国于1978年颁布的《隐私法》(Loi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Vie Privée,1978)。该法的第40条(Article 40)首次提出了“le droit à l’oubli”(被遗忘权),当时相应的英文则表述为“right to oblivion”[2]Chris Conley,“The Right to Delete”,AAAI Spring Symposium: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ivacy Management,2010,pp.53-57.。根据这一法律条款,所谓“被遗忘权”,即对生活中不再重现的过往事件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条款通常用于刑法实施过程中,直接将这种被遗忘权赋予一部分有过犯罪记录的人或有过特别轻微犯罪的人,以及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官方所保留的他们的相关犯罪记录因此而永远都不能够予以公开,惟其如此,这部分人群才可以获得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公平生存的机会[3]参见郑文明:《数字遗忘权的由来、本质及争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12期。。与此同时,这一条款也赋予了每一位信息主体或数据主体一种权利,即要求信息或数据控制者修改、完善、更新以及屏蔽或删除与信息主体或数据主体相关的、不准确的、有争议的或过期的信息或数据[4]Loi No.78-17 du 6 janvier 1978 relative à l’informatique,aux fichiers et aux libertés[Law 78-17 of January 6,1978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Data Files and Civil Liberties],JOURNAL OFFICIEL DE LA REPUBLIQUE FRANÇAISE[J.O.][OFFI⁃CIAL GAZETTE OF FRANCE],Jan.7,1978,art.40.。
然而,真正从理论上将“被遗忘权”与刑法相结合的则是弗莱彻。他于1989年首次提出与隐私信息、数据相关联的“被遗忘权”,并将其界定为:在释囚案件中犯罪记录的被遗忘[5]参见郑远民、李志春:《被遗忘权的概念分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即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罪犯享有一种权利,即要求自己的犯罪记录不被公开,或者要求删除自己过去的犯罪记录[6]参见郑文明:《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遗忘权》,〔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
2.被遗忘权刑法建制的条件
从已有的各种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到,被遗忘权包含了三大核心要素:主体个人信息、公共空间、隐私空间。因此,我们不妨尝试将被遗忘权界定为:公民应当享有对主体个人信息控制与支配的权利,即可以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从公共空间中撤出来,使其回归隐私空间。其实,在“被遗忘权”这一概念提出之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刑事司法已经开始了这一概念的早期实践,最为典型的当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如法国的罪刑不公开制度。1808年颁布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法国《法典》)规定:未成年犯罪记录相关登记卡可予以撤销。它提出了两种撤销方式:其一,自动撤销。根据法国《法典》第769条第7项的相关规定,依据相关法令,对未成年人宣告采取措施的,自宣告裁判之日起至三年期限届满,只要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轻罪或重罪的判决,也没有涉及任何刑事和解的执行,那么,之前的犯罪记录便可以获得自动撤销。其二,申请撤销。依据法国《法典》第770条的相关规定[7]《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 条规定:“对未满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做出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做出后3 年期限届满,如该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的申请或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少年法庭做出终审裁判,经宣告撤销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保留在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登记卡应予以销毁。”,在对未成年人做出裁判之日起至三年期限届满,只要未成年人已经得到了再教育,或者在这三年期间,涉案者已经超出十八岁成年年龄,都可以向少年法庭、监察机关等提出相关申请。少年法庭拥有终审裁定权,一经受理并裁定对相关前项裁判登记卡予以撤销,原处罚决定便将不会再出现在犯罪记录之中[1]参见汪娜:《法国青少年犯罪预防措施及其借鉴》,〔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第5期。。
再以新西兰《2004年犯罪记录法(清白法案)》(Criminal Records Act,2004)为例。根据该法案第7条的规定,只要符合一定条件,涉事人的犯罪记录可以得到封存。相关规定的主要条件包括:1.在过去七年之中,未曾因涉及其他案件而被判有罪;2.从没有被判处监禁类刑罚,诸如监禁、矫正培训、青少年管教等;3.从没有因为精神状态原因而被法院判令羁押于医院;4.从没有因为诸如性侵儿童,性侵年轻人或精神残障人士等“特殊类型犯罪”而被定罪;5.已经根据法院的判令全额支付所有与刑事案件相关的罚款、费用或赔偿金等;6.从没有因为违反《1998 年陆地交通法》(Land Transport Act,1998)或其他较早的相关规定而被剥夺驾驶资格[2]Section 7 of Criminal Records(clean slate)Act 2004.。
日本《刑法典》关于撤销犯罪前科记录的条件分为两类:其一,针对被判处监禁及以上刑罚的犯罪人。在其刑罚执行完毕或免除执行之后的十年内,没有再次因为涉嫌犯罪而被判刑。其二,针对被判处罚金及以下刑罚,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犯罪人。在分别经过五年、两年之后,没有再次因为涉嫌犯罪而被判处刑罚。一旦撤销犯罪前科记录,所有刑罚的判决随之失去效力,犯罪人即可重新获得正常的法律权利。而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日本的《少年法》有专门的规定:“当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者免于执行,则适用人格法律的规定,应该被视作未曾受过刑法处罚的少年。”[3]孙云晓:《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日本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章,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就包括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根据《诉讼法》第275条规定[4]《刑事诉讼法》第275 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被判处五年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相应的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我国201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03条也有相应的规定[5]《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03 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时年龄不满十八周岁者,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民检察院收到判决后应该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恰恰是因为有了诸如此类的犯罪记录封存、撤销制度,犯罪人不再因为曾经的犯罪行为而难以回归正常的公民身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制度具有公权力意义上的强制力,将公民权利赋予了回归正常的公民。
可以说,刑事法律对于犯罪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撤销等相关规定本身就具有了刑事被遗忘权的性质。诚然,各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仍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在我国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而非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权利。对犯罪记录的相关封存,在新西兰更多地适用于轻微犯罪的犯罪人,且不适用于重罪犯罪人。但是,对刑事被遗忘权的保护无一例外地凸显了刑法建制本身的特性,体现了刑罚的本质与目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刑罚不外乎就是社会的一种自卫手段,用以对付违反它生存条件的行为,无论这些是怎样的条件[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从根本上来说,刑罚的终极标的是维护国家政权,保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利益;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使他们得到相应的规范与矫正,在他们重回社会之时不再造成破坏。
二、被遗忘权的权属划分
1.被遗忘权的权属问题
被遗忘权既然是公民个人信息自主的一项权利,这就涉及到被遗忘权的权属问题,也就是说,被遗忘权的权能是如何界定的?确权与赋权又是如何确立的?
权属是权利的构成要素,也是确定权利性质的关键之所在。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中,可以指认被遗忘权的人格权基础;从民法所赋予的权利中,则可以指认被遗忘权的隐私权基础。由于公民个人信息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财产权益裹挟到了一起,例如,数据企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建立起来的信息数据系统包含了交易主体盈亏流转模式,随着信息数据的不断流转,隐私权基础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资产快速形成,数据产权亟待得到适当性保护,商法保护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被遗忘权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获得了看似清晰的权属。然而,不同的权属之间或许存在着功能性的关联、价值的彼此引证,而其中呈现出来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又抑或是相互排斥、相互抵触,几近颠覆被遗忘权原本应该有的价值实现,被遗忘权的交流性、不确定性共时并存。被遗忘权与上述各项权属之间似乎难以存在可通约的构造。
至此,我们不得不说,“权利不应当是一套不证自明的道德与责任伦理,而应当是一套可操作的明确的概念体系,即‘建制性规范’”[1][1〔]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然而,被遗忘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事实上,人格要素、隐私要素、财产要素等等都杂糅其中,例如,公民曾经的个人信息具有人格价值、隐私价值、财产价值等,这几种价值之间存在彼此交叉、彼此叠加、彼此包容的关系。如何有效地对被遗忘权进行切实保护,首先就涉及到被遗忘权的权属划分问题。
2.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所凸显的权属问题
任某某自2014年7月1日起就职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体负责相关教育工作。2014年11月26日该公司向他发出《自动离职通知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任某某发现网上有自己这段工作经历的信息,且与负面信息形成相关搜索,因此向法院提出诉求:要求公司删除网上相关链接。任某某主张:鉴于其与某企业的相关业务已经结束,与该企业不再存在任何业务上的往来,自己的相关经历就不应该再继续被互联网所传播。考虑到某企业在业界的口碑较差,给自己的就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并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因此曾经的信息应该被网络用户“遗忘”。
百度方面则辩称:网民输入关键词后形成的互联网信息是客观存在,该公司并没有对相关信息进行人为的干预和修改;并且这个搜索结果会随着关键词的内容及搜索频率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也会进行自动更新。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是对任某某过往工作经历的客观反映,任某某在案件审理阶段还在继续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因此,之前的工作经历属于他从业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或相关客户用来评判其专业资质所需的重要信息。任某某不属于我国法律框架下需要受到保护的特殊群体(例如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其所从事的教育行业与律师、医生等属于专业的领域,其过往经历被互联网传播、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评判无可厚非。
该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任某某继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书。。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被遗忘权”做出相关的规定,也还没有对其进行权利类型划分,因此权属问题成了这一案例的最大症结。法院认为,任某某被遗忘权的主张无法归入我国现有类型化的人格权保护范畴,任某某只能从一般人格权的角度提起诉讼。但是,根据一般人格权法条,任某某所主张的权利并不适用,也就是说,法官找不到判断的具体标准和依据,因此任某某的主张被判定为“不具有正当性”,“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不应成为侵权保护的正当法益”。显然,“被遗忘权”尚不属于我国的法定权利[1]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
3.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所凸显的权属问题
西班牙公民冈萨雷斯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EPD)投诉西班牙《先锋报》、谷歌西班牙公司和谷歌公司,提出两项诉求:第一,《先锋报》删除涉及他本人名字的网页;第二,谷歌删除与他本人名字相关联的个人数据以及相关搜索。他的第一项诉求遭遇否定,第二项诉求得到了支持。谷歌不服裁决结果,直接上诉到西班牙最高法院。西班牙最高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第234条有关预裁决的相关规定,请求欧洲法院对1995年颁布的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以下简称:欧盟《保护指令》)[2]Judgment of the Court(Case C-131/12),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62012C J0131&qid=1475918185755&from=EN,2016-9-27.相关条文做出解释,其中包括:第2条(b)项和(d)项、第4条第一段(a)项和(c)项、第12条(b)项删除权、第14条第一段(a)项拒绝权等等。与此同时,还向欧洲法院提出另一项请求,即对《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以下简称:欧盟《权利宪章》)[3]参见周辉:《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概要》,〔北京〕《网络法律评论》2015 年第2 期。的相关联条文做出解释,其中包括:第7 条,规定隐私生活受到尊重权;第8条,规定个人数据受到保护的权利。
西班牙最高法院所提出的请求涉及如下主要条款:欧盟《保护指令》第14 条“数据主体的拒绝权”:(a)数据主体若有特殊情况的有说服性的合法理由可拒绝数据处理;(b)在数据处理是免费的情况下,拒绝控制者处于营销目的的数据处理。第6 条“个人数据的处理应遵循”:(a)被公平合法处理;(b)以特定、明确、合法目的进行收集的,进一步处理不能违反这些目的;(c)与收集或处理的目的有充足联系且不能超越这些目的;(d)如必要的话应保持更新,并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删除或更正对与其收集目的和进一步处理的目的来说不精确和不完整的数据;(e)出于历史、统计和科学使用的目的长期保存个人数据的,各国应制定适当的保护措施。第7条“符合以下条件才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a)数据主体明确表示同意;(b)对于履行与数据主体的合同是必要的,为根据数据主体提出的要求而在合同生效前进行的;(c)对控制者履行其合法义务是必要的;(d)对保护数据主体的重要利益是必要的;(e)对为公共利益或执行官方授权的任务是必要的;(f)对管理者、第三方或信息获取者的合法利益是必要的。第12 条相关的“访问权”:(a)数据主体有权无延迟及免费地知悉数据处理情况;(b)当数据处理不符合该指令的规定时,特别是由于数据性质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应当对数据进行恰当的更改、删除;(c)控制者应尽适当的努力向数据已经向其公开的第三方通知更改、删除的情况。
欧盟《保护指令》和欧盟《保护宪章》对欧盟成员国法律适用范围、数据管控与数据处理行为及数据主体、删除权与反对权的范围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逐一明确的指认与界定。历经两年多的审理,欧洲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冈萨雷斯的最终判决:谷歌有义务删除相关链接。
这一案件是一件典型的疑难案,因为它没有适用性具体法律条文可依,而看上去有些关联的法律概念似乎又有内涵不清、边界模糊、张力不足之嫌。这些都给司法归类造成了相当的困难。但是,此案的法官对具有关联性的法律条文文本进行各种层面、各种角度的解释,其中主要包括:针对文本单一概念的语义解释、根据法条所处的关联性位置所做出的语境解释、以法律立法标的为基础的目的解释、从位阶高低关系出发所进行的合宪性解释等等。同时,采取各种方式权衡这一案件中的利益关联,做出相应的价值取舍,实现了对被遗忘权的根本性保护,为“被遗忘权”在法律上的创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此可见,两个“第一案”都遭遇了法律适用的窘境。在我国“第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法官尊重既有的法律规定,以法律条文作为审判的直接依据,没有做出任意裁判。也就是说,这一案件的审判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现有法律规范对法律适用所实施的严格约束。而在西班牙“第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法官同样遭遇法律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案件、法官既不可以随意超越法律文本也不可以自行制定法律规则的困难。他们通过寻找关联性最强的法律文本,进行理性、得体的解释与分析,最后在法律框架之内对被遗忘权实施最为现实、最为恰当和最大限度的保护。
三、被遗忘权法律保护与刑法前科撤销制度
至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国的“第一案”审判是否矮化了既有的法律文本?是否指认了既有法律缺乏应有的张力与潜在的适应性?西班牙“第一案”的审判是否对既有法律进行了事实上的调整?是否在既有法律的基础上创设了新的权利?是否从既有的法律中发现了原本并没有得到指认的权利?是否是在填补既有法律可能存在的漏洞?是否体现并诠释了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或者整个法律立法的终极目标?思考这些问题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对这些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更在于对整个法律框架体系前瞻性、完备性的追问。
有研究者提出,虽然我国现有法律并没有设立被遗忘权的相关规定,但在现有的规定和办法中,已有对于个人信息删除的条款。如2017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第43条规定:当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所拥有的其个人信息中存在错误,可以向网络运营者提出修改或删除的要求;如果网络运营者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个人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删除。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2017版)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信息处理主体必须确保个人信息可追溯、可异议和可纠错。第11条个人信息权中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进行了如下定义:信息决定、信息保密、信息查询、信息更正、信息封锁、信息删除、信息可携、被遗忘,依法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第19条为被遗忘权,这里的被遗忘权指的是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出现时,信息主体得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无条件断开与该个人信息的任何链接,销毁该个人信息的副本或复制件。此外,在201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对于删除互联网上个人信息涉及的问题有着明确的要求及规定,即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个人信息控制者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收集和使用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控制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违反了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的协议。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在个人信息主体主动提出删除其个人信息的要求时,个人信息控制者必须满足个人信息主体的要求,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当个人信息控制者在违反法律规定或未遵守与个人信息主体约定的情况下与第三方分享、转让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主体提出删除的情况下,个人信息控制者以及第三方应及时删除;个人信息控制者违反法律要求公开披露了个人信息,在个人信息主体的要求下也应及时删除已经披露的信息;个人信息主体授权个人信息控制者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后,也可以向其要求撤回授权同意。《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是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推荐性的规范准则,在涉及个人信息处理及删除方面,在我国尚未有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出台前,可以看作是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问题的操作指导,虽然它还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对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又涉及到与刑法上的犯罪前科制度冲突问题。众所周知,刑事责任的严厉性不仅在于刑罚对犯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限制和剥夺,还有伴随着刑罚而来的犯罪前科制度。前科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而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被赦免后,在一定期间内的一种法律地位,体现在刑事法律方面主要表现为累犯制度和再犯制度[1]参见于志刚:《“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北京〕《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从本质上讲,前科是对犯罪记录的一种规范性评价。被遗忘权的建立将是对犯罪前科制度的一个挑战。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刑法第100条是全国人大在修订刑法时增设的刑法条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该条进行了部分修正。《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对犯罪的时候未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刑法第100条确立了前科报告制度,从而使得向有关方面报告自己的犯罪前科具有了强制性属性,与此同时,刑法的规定也限定了国家要求有前科的公民披露犯罪信息的范围,旨在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尽管如此,犯罪前科制度对于已经服刑完毕的犯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带来诸多限制,特别是对于从事特定职业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24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服兵役。公共事业单位从业的限制。例如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公证员;因受刑事处罚,在特定时间内不得担任注册会计师或者执业医师;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担任教师等。在企业中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限制。例如,因特定经济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五年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不能担任破产管理人;受过刑事处罚,不能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以及保险公司的法律责任人等。前科的资格限制大多数是终生的,只有少数存在一定的期限,如行为人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的,自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不予签发护照。
犯罪前科制度的存在,对有犯罪前科的公民回归社会生活会带来多大程度、多大范围的负面影响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被遗忘权与前科制度的冲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有被遗忘权法律保护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学术界应当在司法领域对被遗忘权开展深入的研究,准确界定这一制度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它的适用方式等等,需要更为严谨、更为精准地进行被遗忘权的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更加全面地平衡各类法律价值。这是建立被遗忘权制度的前提。
四、司法价值平衡是被遗忘权法律保护的建制性基础
关于司法价值取向,需要厘清司法价值的基本内涵,而后才有探讨司法价值取向对被遗忘权保护的意义。所谓司法价值,就是司法总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即人道价值、正义价值、自由价值、效益价值等。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一定的主体在面对或处理各类矛盾、冲突、关系的时候所持有的价值态度、价值立场,在处理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前后基本一致价值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一定的主体才能够做出相应的价值选择。价值取向至少表现出三种动态性特征:其一,一些价值取向看似恒定,却历久弥新,例如人道价值。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价值取向逐渐走向弱化,而另一些价值取向则逐步得到强化,例如低效益价值与高效益价值。其三,一些价值取向可能发生偶然性的改变,例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前者认为个人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后者认为集体是生存的基本单位。总之,价值取向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彼此之间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形成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共存。
如上所述,由于司法价值构成的多元化和司法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加之个体之间的认知差异、地域历史文化之间的差异、司法环境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司法行事主体以及各类主体对价值前提的选择具有倾向性,这就有可能导致同类案件获得截然相反的判定结果。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和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截然不同的判定结果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法官以自己业已体认的司法价值来处理“被遗忘权第一案”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关系。也就是说,在对事实前提进行选择之前,在对法律条款进行选择之前,他们便已经有了相对比较确定的价值立场。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也是如此。应当说,价值取向具有根本上的实践性。从理论上,我们可以界定正确的司法价值取向,并认定正确的司法价值取向对司法社会可以发挥重大、积极的影响。然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司法价值取向往往杂糅着司法行事主体个人的司法能力、认知能力以及阐释能力。应当承认,司法价值取向的合理化有待进一步发展,但在此之前,更需要刑事被遗忘权的独立建制,以弥补价值取向的不同可能带来的不一致、不严谨、不充分的裁定结论,真正实现公民对人道、正义、自由、效益的期待,彰显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这恰恰也是司法价值的目标所在。
按照逻辑推断,从司法价值的整体设计出发,每一个单项的价值都有别于其他价值,在概念上是完全可以进行明确的区分的。而从理论上来说,一种单项价值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其他各个单项价值的并存而得以凸显,各自具有独立的区别性特征。各个构成要素价值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维护着一个相对完整的、相对稳定的统一体。也正因为如此,司法价值呈现出一个体系状态,有着它独有的内涵与边界,但是,它同时又是开放的,不断接纳业已达成共识的价值,挤压个体非稳定、非主流的价值判断,以足够的内涵张力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包括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先进技术的不断更新、判案材料及信息的激增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司法体制构建体系不仅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协调的、统一的,同时也应该具有适度的结构性开放特征。
客观地说,由于司法价值取向的动态性存在,司法价值平衡的稳定性、有序性注定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与司法价值平衡发生一定的冲撞与对抗,随之而来的便是既有司法价值平衡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应当说,这样的波动往往具有或然率,可能是偶发的、暂时的、非决定性的。只要从一定的角度对相关联的司法条款进行一定层面或一定部分的协调、综合、完善,便可以基本实现司法价值的平衡。从时间角度出发,任何一个司法建制,在它颁布的那一刻起,便具有了与生俱来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突出地表现在一个方面,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不断补充、不断设立。加之司法价值取向的动态性,司法价值平衡的机制便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其一,司法价值平衡的恒定、稳固状态;其二,司法价值与时俱进的能力。
例如,1970年代随着电脑在欧洲和美国的逐渐普及,电脑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储存人们的信息和数据。由于新兴的信息科学技术被政府机构和商业领域广泛运用,人们开始担忧新的信息技术是否会出现数据错误、故障,又或者是给政府及商家提供了对自己进行秘密监控的路径。所有这些担忧都出自于对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的维护。政府也开始思考相关问题,并着手寻找解决方案,以消除那些可能会给民众个人数据带来的潜在损害。而此时,相关的立法才逐渐开始显现,慢慢进入公众的视野。“数据保护”开始出现在欧洲国家民众隐私保护的相关立法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数据隐私”,它成为美国的相关研究与立法颇为常见的法律术语。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有关民众数据保护或数据隐私的立法一直处于发展与变革的过程中,立法机构为了维护司法价值的平衡,不断地权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包括个人、商业机构、政府机构、执法机构、国家安全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如何规制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美国并没有形成全国通用的独立法律建制。其实,每一届国会任期内,都会有代表就此递交提案,期待建立一个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化联邦法案。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美国相关法律法规却像是一幅由联邦系统和州法律拼接在一起的作品。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政府机构和行业组织颁布的指导性文件,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特别规定。这些规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各行各业的各类业务中,却提供了指导性的框架,也可以说是很好的规范。例如,金融类的个人信息、医疗类的个人信息、电子通讯类的个人信息等等。这些在各个领域逐渐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并且已经开始被监管者当做是强制性的义务。可见,在相关司法独立建制设立之前,行业规定对司法价值的平衡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而具体建制的全新设立更是为司法价值的平衡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1974年12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隐私权法》(The Privacy Act)。1979年,美国第96届国会修订《联邦行政程序法》时将其编入《美国法典》第五编“政府组织与雇员”,形成第552a节。该法又称《私生活秘密法》,是美国行政法中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了解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就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公开和保密等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以此规范联邦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矛盾[1]参见周健:《美国〈隐私权法〉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长春〕《情报科学》2001年第6期。。《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是一个用来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规。该法案明确禁止不公平或具有误导性的线上和线下隐私及数据安全条款。企业是否遵守各自的隐私条例,是否存在未经授权就公开个人数据的行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对这类问题的监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的审理过程、裁定结论以及法官具体的价值判断、论证说理来分析,既有法律体系已表现出局部的滞后性,司法价值的平衡机制相应失语,这就需要诉诸新的系统化的相关司法条款作为支撑,并维护司法价值的平衡。这是司法价值平衡的能力所在,更是司法建制生命力的真实体现。尽管中国“被遗忘权第一案”的原告败诉,但是,这一案例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表明被遗忘权的独立建制的缺失已经给司法价值平衡提出了切实而无从回避的挑战。有了司法价值的平衡,被遗忘权才有可能获得建制性的基础。有了这一建制性基础,被遗忘权的内涵与外延才可以获得清晰的界定,这不仅具有权利救济、保护隐私的社会意义,更有对社会价值的指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