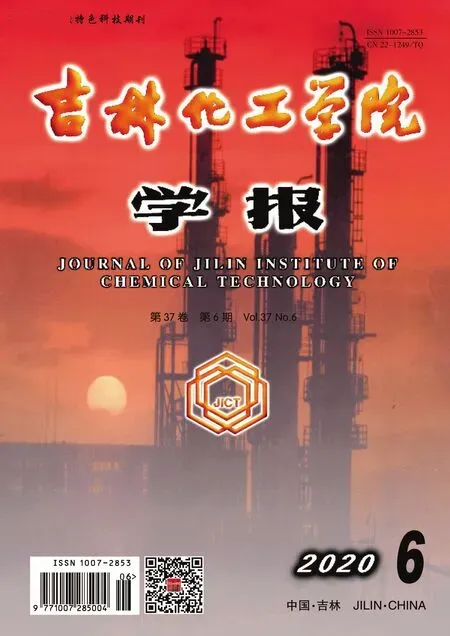日伪时期日本对哈尔滨工商业的掠夺及其影响
李 智
(吉林化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22)
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在外来资本的刺激下,哈尔滨成为近代以来东北地区重要的商贾云集之地。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占领了哈尔滨,随即开始对哈尔滨工商业进行垄断、掠夺,企图为推行所谓“大陆政策”打造重要的经济支撑。哈尔滨“现代城市化”的进程被打断,原有工商业多元的特征逐渐消失,其结果是国人民不聊生,城市发展退步。以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工商业发展情况作比,阐释日本侵华战争对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的多元工商业形态
哈尔滨地区位于松嫩平原东端,区域内水系十分发达,为陆路和水路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工商业发展潜力和优势巨大。清末时期,哈尔滨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聚集的富庶之地。1896年6月3日,沙俄政府威逼利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1898年,中东铁路动土开工,哈尔滨成为铁路核心枢纽城市。虽然沙俄建筑中东铁路实则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领土,但是依靠中东铁路的连通,大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政治经济的互联。哈尔滨依靠在中东铁路中枢纽地位,在开埠通商之后,在四面八方而来的工商业资本刺激下,从一个传统的以分散的自然村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区系统转变为国际大都市,成为远东地区商品集散地。西方列强国家的机器工业产品从这里走向中国各地,本土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由此输送世界各地,形成了哈尔滨特有的多元工商业形态。
中东铁路的通车意味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哈尔滨自行开埠通商进一步打破了清王朝的“封禁政策”,这便吸引了大批的外国资本涌向哈尔滨。伴随中东铁路的修建,俄国商人便参与其中,也成为最早来到哈尔滨的外国商人。1898年,俄国人波波夫兄弟商会专门从事中东铁路木材的供应买卖,随后又有很多其他俄国商人进入哈尔滨。在几年的时间内,俄国商人就涉猎面粉、啤酒、烟草、肉类食品、服装、化工、五金、百货、金融、交通等行业。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务处下属的商务部,成为沙俄政府在哈尔滨设立的最大的商务机构[1]。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哈尔滨作为俄军物资供应城市的重要地位凸显。1905年11月30日,在哈尔滨埠头区(道里区)成立了俄国商会,开始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
哈尔滨的快速发展很快便吸引其他列强国家工商业实体入驻。1907年7月,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办办事处。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实际上就把哈尔滨作为日本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哈尔滨人口成倍增加,工商业水平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2]。1920年6月,哈尔滨市日本实业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分门别类设置棉丝部、药品部、银行部、宣传部等7个业务和职能部门,至1921年6月正式成立了哈尔滨日本商工会议所,包括日本企业82家。1916年,英国商人依附英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成立了英国商务会,计有英国企业18家,经营范围为制油、制铁、机械进出口、毛皮进出口等。1921年德国商务会德亚商会在埠头区(道里区)成立。1925年哈尔滨德国商务会成立,包括15家德国商家会员,主要从事车辆、机械、电力设备,建筑材料,化学制品等。1917年美国商务会成立,至1932年日本占领哈尔滨之前,共有美国商家41家,主要经营皮货、制药、保险、烟草、汽车、皮革等行业。1921年波兰商工会议所成立,后陆续有35家波兰商家加入,主要从事啤酒、林木采伐、制糖和卷烟等。1923年法国商务会成立,拥有会员10名,业务包括取暖设备、粮食出口、纺织品出口和日用化学等。其他还有爱沙尼亚、南斯拉夫、丹麦、瑞士等小商行的经营,虽然影响有限,却使哈尔滨工商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3]。
为了适应哈尔滨快速发展的国际营商环境和面对来自国外同行的竞争和挑战,20世纪初哈尔滨埠头区、傅家店(道外区)、田家烧锅(香坊区)等地都备案成立了商会,如:哈尔滨商业公益所、滨江公益会、田家烧锅商务公议所等。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1903年设立商部,颁布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这些都推动了哈尔滨民族商会和行会的形成与发展。哈尔滨商业公益所是哈尔滨最早的商会组织,成立于1900年,1908年改名为哈尔滨商务总会,活动区域基本为道里和南岗。1901年傅家店商户成立滨江公益会,1908年成为正式商会。1901年,田家烧锅地方成立田家烧锅商务公议所,1913年改称上号商会。商会之下还有行会一级,其数量很大,经营内容涉及方方面面,门类俱全,例如:杂货业、绸缎业、五金业、茶业、钟表首饰、面粉业、中药业、西药业、印刷业、木业、麻袋业、估衣业、运输业、渔业、染业等等,由此可以估算依附行会之内各类商铺数量更是庞大。
适宜的自然通商环境和中东铁路带来的便利交通使哈尔滨成为国内外商家青睐的聚财之地,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工商业呈现繁荣的多元特征。1912-1931年,哈尔滨的各国工商企业达到1 754家[4]。以当时哈尔滨市场上出现的商品种类,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征。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在傅家甸市场上出现的外国商品有花旗布20 000匹,340 000吊;大连布7 500匹,127 500吊棉丝60包;白糖22 000斤;红糖33 000斤;煤油3 000箱,15 600吊;连纸5 000扛。国产商品有大尺布1 300匹;4 970吊;套布7 500匹,82 500吊;清水布7 500匹,44 100(吊);盐500 000斤[5]。
二、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哈尔滨工商业的掠夺与垄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东北地区,1932年2月5日日本关东军占领哈尔滨。为了整合东北经济,完全适应对外侵略政策的战争需要,日本及其控制下伪满政府开始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开始了对哈尔滨工商业的全面掠夺和垄断控制,至此哈尔滨工商业的多元形态戛然而止。
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中,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首当其冲成为被控制、排挤、打击的对象。首先,在关东军的支持下,通过组织日本本土企业联合和扶植日资控制企业,以超强实力“竞争”哈尔滨本土民族企业。1934年,以制粉业为主体的十多家财团出资1 000万元,成立日满制粉株式会社,在哈尔滨工厂日产量25 500袋,极大地冲击了哈尔滨民族制粉业[6]。日本通过技术和加大投资手段,促进日资控制制油企业不断进行商业扩张,迫使哈尔滨本地制油业逐年萎缩。第二,通过管制手段加强对哈尔滨实业控制。日伪政府采取偏袒的“统制”政策,帮助日企获得足够的原材料,而本地企业则因为原材料不足而停工,例如:1938年11月的《米谷管理法》、1939年11月的《主要粮谷统制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1940年8月的《粮谷管理法》针对制粉业;1939年3月的《原棉、棉制品统制法》针对棉业;6月的《主要产品统制法》针对制酒业;1940年的《物价物资统制法》针对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商品。此外,日伪政府还对本地企业苛以重税,敲诈勒索,致使很多企业都难以维持。第三,日伪政府以“工厂整顿”为名,制定苛刻标准,强行关闭本地企业。1933年,哈尔滨有商户9 287户,到1936年减少到5 753户。其中华商由7 604户锐减到4 754户,资本仅剩1 000万元[7]。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对留存哈尔滨的其他外国企业和资本进行施压、排斥、驱逐与垄断。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日本把自己打扮成远东反共反苏的急先锋。1932年7月8日,日伪当局查封哈尔滨八区中东铁路商务代表部;12月28日,又查封哈尔滨苏联国营贸易局和远东贸易局。因受日伪当局“莫须有”的罪名骚扰,苏联在哈尔滨设立的各种商务机构、代办处等陆续关闭[7]。1936年1月28日,哈尔滨苏联远东银行被封闭[8]。
日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实现对东北经济的吞并和垄断,在哈尔滨随即开始驱逐西方国家的商业企业,甚至轴心盟国法西斯德国也概莫能外。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香烟曾在东北地区占有70%的市场份额,在哈尔滨建有工厂。日伪政府通过(伪)满洲烟草公司实施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联合另一家日本控制的Toa 公司,将产量由最初的年产量15亿支卷烟提高到43亿支卷烟,可以与英美烟草公司年产量67亿支卷烟相较量[2]。在竞争中,英美烟草公司败下阵来,业务开始不断萎缩,最后只有等待停产和被收购。1933年,日伪当局为了占有哈尔滨犹太人卡斯普家族的财产,不惜使用卑劣手段绑架小卡斯普,以此勒索钱财且最终杀人灭口,一手导演了震惊国际的“卡斯普绑架案”[9]。(伪)满洲国内唯一一家法国资本银行法亚银行(Franco-Chinese Bank)哈尔滨支行处境十分困难。随着银行经理,同时也是哈尔滨对外商业议事会的主席白俄人布恩诺夫斯基(M.Buenovsky)的自杀,这家银行也被清算,它的储户只拿回存款的70%。类似的情况还包括:1935年10月5日,哈尔滨美国信济银行破产倒闭,1936年6月30日,法国哈尔滨法亚银行关闭,1941年1月18日,哈尔滨美国花旗银行关闭[8]。德国西门子·舒科特公司(Siemens-Schukert)一直在东北地区经营车辆、机械、电力设备、建筑材料、化学制品等,当时中东铁路局等都是这家公司的客户。从日本军队占领和傀儡政权宣布就职时起,该公司已经面临着最大的困难,已经无法与前中东铁路和其他日本人控制的公司下订单了。昆斯特·阿尔伯茨公司(Kunst and Alberts)是唯一在哈尔滨留存下来的“仍在运转”的德国公司,但也近乎倒闭,因为(伪)满洲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市场。
日伪通过胁迫压低市价的方式,大肆收购白俄企业和房产。由于哈尔滨地区整体的营商环境恶化,商铺无法经营。哈尔滨白俄商铺实际价格50 000美元,低价卖给日本人只能得到8 000哈大洋。东拓公司(Totaku)是一家东方发展公司,属于半官方机构,主要为俄国人和中国人办理房产抵押。一座白俄六层楼的房产当时估价是200万日元,但是实际上只抵押了15万日元。秋林公司是白俄在哈尔滨的老店。日伪政府以日德合作为名,通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公司(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将秋林公司低价以600万美元收入囊中[2]。以合办为名,行独占之实。根据(伪)哈尔滨日本工商业议事厅的调查,1932年白俄控制着哈尔滨及北满所有商业的60%,哈尔滨白俄居住区的75%的房屋,但至1936年白俄现在只拥有哈尔滨及北满所有商业的22%,所有房屋的33%,所有农业公司的13%和工业的28%[2]。
日本对哈尔滨工商业的掠夺不可谓用心不明其恶,手段不用其极,这与其变东北地区为殖民地的既定政策是相一致的,使得哈尔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著名的商贾之都变为萧条之市,成为日本商品倾销地,伪满洲国经济得以维持的方式徒有殖民掠夺。
三、哈尔滨工商业畸形发展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对哈尔滨的占领和掠夺直接造成九一八前后哈尔滨城市迥然不同的两种局面。哈尔滨作为城市的出现是与列强入侵、国门洞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中东铁路的修建分不开的,这些都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挑战和践踏。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帝国主义在不自觉间充当了历史的工具[10]。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哈尔滨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由一个社区系统转型为在远东地区有影响的大都市,表现出多元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和社会特点,成为近代“现代城市化”的典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仅打断了很多城市的“城市现代化”转型过程,也破坏了哈尔滨“现代城市化”的进程。在日伪政府的殖民统治下,哈尔滨工商业进入到畸形发展的状态,任何行业都被直接垄断,大到大宗商品贸易,小到日常衣食住行,包括棉花、毛织品、刀具、肉类、蔬菜、柴火等。哈尔滨商业倒退,民不聊生。日伪对哈尔滨的商业“管制”直接造成商品价格上涨。以面包为例,白面包和黑面包以往价格从未超过每磅5分和8分,当时价格上涨为每磅8分和12分[2]。1941年日伪又开始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全面“统制”配给。由于食品短缺,每年都有大量穷人冻饿而死。殖民地经济体系的建立造成使哈尔滨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步。哈尔滨城市工商业完全被改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依靠,偏离了原有的发展轨道,丧失了在远东的经济地位,重新回到一种封闭的状态中去。近代哈尔滨是中国东北北部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合市场和密切内地经济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1931-1945年,哈尔滨工商业的一蹶不振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经济衰弱的一个侧面。
哈尔滨在近代出现并崛起,没有沿着传统城市的轨迹发展,而是越过农业文明,直接成为以“商”立足的国际都市。在日伪统治之下,哈尔滨工商业逐渐凋零代表着哈尔滨工商界的式微,也注定哈尔滨丧失本有的活性。冷酷的政令统制代替了热闹的喧嚣竞争,活力无限的聚商之地被重新改造,进而被拼摆进了日本侵略者的“版图”之内,同时也被绑在了冰冷的侵略“战车”之上。遭遇此种情况,西方国家的公司和商人尚有退路,多数选择变卖资产,快速“止血”,另谋发展。然而,哈尔滨本土工商界已然退无可退,向来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北部民主资产阶级[11],毅然投身于激烈的反满抗日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