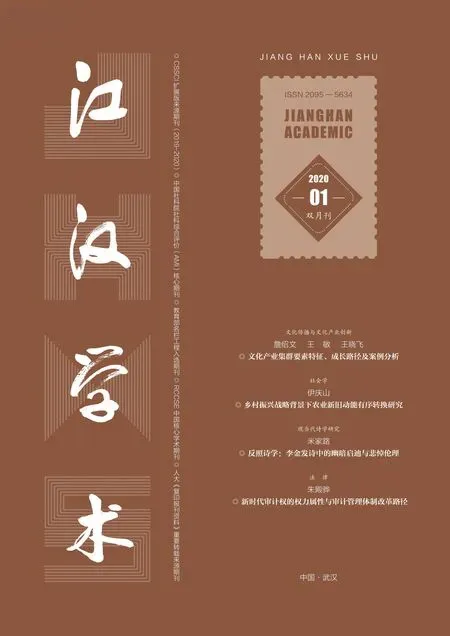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
——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孙 广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元代《孟子》学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科举制度以《四书》为核心,将《孟子》正式推上了“经部”,代表了“孟子升格运动”(周予同《群经概论》)的完成。二是孟子在孔庙中的位置,由“十哲”之下跃升为仅次于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的“亚圣”①,代表了孟子在儒家道统序列中地位的巩固。可以说,到了元代,《孟子》学乃真正成为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代的《孟子》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这一时期《孟子》学的发展,一直是作为《四书》之一。而对于元代《四书》学的发展,四库馆臣云:
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于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语孟旁通》、薛引年②《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1]734
“发明义理”“考究典故”,正是元代《四书》学两条齐头并进的发展途径。对于“发明义理”这一进路,现代学者将其概括为“纂疏之学”或“附录纂疏体”“纂疏体”③等。其特点是纂辑诸家文集、语录中的文字,对《四书》中的义理进行阐发。而“考究典故”这一进路,笔者将其概括为“旁通体”(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言④),其特点是纂辑经史传记文字,对《四书》中的典故进行考核。这两者共同的特点,元人张存中《四书通证凡例》有很好的总结:
《四书集注》明理用事,简明为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云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则理通矣。今《笺义》出而事益繁矣,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从其简,则事亦通矣。此二书之所以作也。[2]639
吴真子《四书集成》、赵惪《四书笺义》,分别是“纂疏体”与“旁通体”的代表,张存中此处所谓“理愈晦”“事益繁”,可谓正中这两种经疏的弊病。然而,如胡炳文《四书通》、张存中《四书通证》,乃至后来集大成的倪士毅《四书辑释》,虽然对前人著作多有删正,但仍是沿袭其体式,并无大的改变。
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奉命编纂《四书大全》,便是以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底本,益以吴真子《四书集成》并二书所遗漏者而成。顾炎武云:“《大全》出,而经说亡。”[3]1010此说恰当与否且不论,但自此以降,凡论元明学术转向,便基本上从《大全》说起。这种理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则《四书大全》的主体内容都来源于元人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可谓直接元代学术传统;二则一般对洪武朝学术与文化的认识,也向来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是“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多文字之祸”等等“暴政”。落实到《孟子》学史上来,也基本承袭了这一理念。就笔者所见,除具体对象的研究之外,明确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研究明代《孟子》学的,有佐野公治《四书学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年)、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孙计康《明代〈孟子〉考据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0年)、陈育宁《明代前、中期孟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 年)、黄英《明后期孟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 年)、王园园《明代前期四书学考论》(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年)、周冰冰《明代〈孟子〉义理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5 年),总共八部论著。在八部论著中,仅佐野公治先生对科举制度有较深入的研究,可以算是涉及洪武一朝;另外则是陈育宁《明代前、中期孟学研究》对洪武年间的《孟子节文》有所涉及,所谈也无非是皇权对学术的宰割。其余六部,几乎全不涉及洪武年间的《孟子》学。因此,从现有的《孟子》学史来看,洪武一朝几乎是一片荒漠。
但是,洪武一朝长达数十年,又是各项典章制度建立之初,对于有明一代学术来说,其重要性不可低估。研究《孟子》学史而置此不论,无疑是人为造成了一种学术史断层。而仅有的研究,基本上仅仅从一部《孟子节文》来窥测洪武朝《孟子》学的发展情况,也很难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近年来,以宋濂为代表的洪武朝学者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如宋濂等学者乃阳明心学的先声,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⑤而宋濂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这一结论的得出,也正提示了我们洪武朝《孟子》学发展的重要性。职此之故,本文着重从洪武一朝《孟子》学的发展来梳理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博方家一哂。
一、洪武朝与《孟子》学相关的三大政策
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之前,《孟子》就已经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许多支持明朝的儒者引《孟子》为新王朝歌功颂德。唐仲实、章溢均以《孟子》“不嗜杀人”称许朱元璋,认为他未尝妄杀,功超前代[4]。许存仁也引《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4]至明朝开国之时,也在许多方面采用了《孟子》的思想。明太祖与刘基商讨生息之道,言及《孟子》“仁心仁政”之说[4];在决定以“仁义”为统治思想之时,也着重承袭了《孟子》“辟邪说”的理念[4];在决定祭祀礼仪时,又以《孟子》“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为据要求省牲[4]。由于“明初文人多不仕”,为了笼络士人、巩固统治,朱元璋在洪武前期对《孟子》多有提倡和表彰。洪武元年,即“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5]7302,并“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官属并从衍圣公选举,呈省擢用”[4]。不过,上述这些措施,包括洪武三年开科举等,都是统治者建国初期常见的复兴手段而已。洪武一朝,集中体现了朱元璋个人意志的、对明代《孟子》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有三:一是洪武六年(1373)暂停科举,二是命儒臣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三是罢孟子配享和命刘三吾等人编纂《孟子节文》。
1.暂停科举
《明会要》载:
六年二月,谕中书省臣:“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非朕责实求贤之意。各处宜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自注:已上《弇山集》)十五年八月,复行科举。三年一行为定制。(自注:《三编》)[6]868
此时明朝初立,求贤若渴,为了扩充人才储备,朱元璋不仅连开三年科举以“利诱”,更杀了不愿出仕的姚润、王模、夏伯启叔侄等人以“威逼”。但是,朱元璋很快就意识到,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人才,“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不得不暂停科举,仍令有司通过“察举”来选拔人才,一直停了九年才恢复。这一方面说明了元代模式培养的学者普遍缺乏“措诸行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朱元璋对事功的重视。
2.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
延续前代传统,洪武朝编纂了许多类书⑥,而与《孟子》相关者则有二⑦,对于明初《孟子》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孔克表等人用通俗的语言对经典进行解释,撰成《群经类要》。宋濂《恭题御制论语解二章后》云:
右解《论语》二章,乃皇上所亲制,以赐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经籍,以为经之不明,传注害之。传注之害,在乎辞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诏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刘基、秦府纪善臣林温取诸经要言,析为若干类,以恒言释之,使人皆得通其说,而尽圣贤之旨意。又虑一二儒臣未达注释之凡,乃手释二章以赐克表,俾取则而为之。克表等承诏,释《四书》、《五经》以上。诏赐名曰《群经类要》,复装褫所赐为卷。以臣濂尝与闻斯事,请识其左方。[7]875
如前文所述,元代“旁通体”和“纂疏体”两类经疏,正是这里所说的“辞繁而旨深”者。至此,朱元璋命孔克表等人“取诸经要言,析为若干类,以恒言释之”,从内容上来说只是选取《四书》《五经》的部分内容,从体例上来说更是有一定的分类排纂,从诠释方式上也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解释。佐野公治先生说:“太祖洪武帝忌讳宋儒,写成《论语》二章的新解释。”[8]6其言良是。《群经类要》的编纂,确实是对元代《孟子》学的一种否定,对于经典的普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洪武十六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吴沉等儒臣又编纂了《精诚录》。《明太祖实录》载:
二月己丑,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精诚录》。先是,上将享太庙,致斋于武英殿,召沉等谓之曰:“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其以圣贤所言三事,以类编辑,庶便观览。”至是,书成。上览而善之,赐名《精诚录》,命沉为之序。书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书》七十二章,《诗》十七章,《礼记》二十七章,《孝经》、《论语》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学》、《中庸》各一章,《书》四十六章,《诗》十章,《礼记》十四章,《左传》六章,《国语》一章,《论语》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亲》一卷,取《易》二章,《书》三章,《诗》九章,《礼记》四十八章,《论语》十一章,《孝经》十九章,《大学》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4]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到,《精诚录》的范围,仍是《四书》《五经》外加《孝经》,不及其他。不过,相比经典本身的内容,这里选编的内容非常少,这一选择的过程,无疑是有极强的目的性的。“敬天”“忠君“孝亲”三条宗旨,均指向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其目的性不言而喻。而其编纂方式,则是按照既定的宗旨,将经典文献予以类编。这种编纂方式,对经典本身的独立性予以极大的消解,使之成为论证“敬天”“忠君”“孝亲”三大核心主题的论证材料。简言之,《精诚录》的编纂,体现出朱元璋极强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推动了经典诠释方法的转变。后世如明宣宗所编《五伦书》等,即是此书导夫先路。
3.罢孟子配享与编纂《孟子节文》
《明史·礼志》“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条云:“五年罢孟子配享⑧。踰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5]1296又《明史·钱唐传》云: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5]3982
夏燮《明通鉴》论曰:“盖太祖终不悦于孟子,而其复配享也,实出于一时之清议,故修《孟子节文》而自护其短也。据《典汇》所记,其所节者,自‘草芥寇雠’外,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然则其所节者,大概可知已。”[9]273按核原书,仅就章节数而言,《孟子节文》删去了33.85%,超过三分之一;若就文字数量而言,则删去了46.67%,将近一半的内容。⑨而删去的内容,一是“不以尊君为主”之类,二是可以为“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作合法性论证的涉及仕隐态度的叙述,三是孟子本身的辩论纰漏、论史不实的部分。自容肇祖先生《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至今,学界对这一行为的认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认为这是朱元璋集权过程中对学术、思想以及儒者的打压和钳制。而从《孟子》学的角度来说,罢孟子配享和《孟子节文》的纂修,无疑是对孟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的压制,对《孟子》文本的删节本质上也是对《孟子》思想的阉割,强迫《孟子》为新朝的统治服务。而从删节的内容来看,《孟子节文》所删多与政治相关,这样一来,研究《孟子》的学者,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自然下降,这或许是促成明代《孟子》学向心学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
通观洪武朝的三大政策,实则完全背离了元代《孟子》学的发展线索。首先,元代的学术模式,培养的人才多不能“措诸行事”,缺乏实践能力。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既否定了元代的学术模式,又提倡了崇尚事功的学术趋向。其次,元代的“旁通体”和“纂疏体”经疏,总体上表现为“辞繁而旨深”。朱元璋则通过编纂《群经类要》,否定了这种经典诠释范式,转而提倡简易通俗的经典诠释,极大地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和接受。再次,元代的“旁通体”和“纂疏体”经疏,均是以注疏形式对经典进行疏解。朱元璋通过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打破了这种注疏形式,对经典的独立性予以消解,将经典内容转变为政治或哲学理念的论证材料,使得理念的阐发和论证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最后,朱子之人性论,由于主《中庸》“天命之谓性”,所以在《孟子》“生之谓性”章时便不得不出现困难,⑩这是作为整体的《四书》学的必然困境。朱元璋通过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将《孟子》中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大肆删节,使得《孟子》学的研究集中在心性论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孟子》心性论的发展,也使得《四书》学人性论的矛盾愈发凸显。
二、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孟子》学趋向——以宋濂为叙述中心
洪武朝《孟子》学的新动向,几乎全部是政治层面的运作,再加上这些运作完全背离了元代《孟子》学的发展线索,似乎正印证了洪武一朝是皇权对学术的宰制。但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孟子》学,却与这些政策的施行保有极大的一致性,透露出这种变革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龙门子,谥文宪。元世隐居不仕,宋濂大半生都生活在元朝。直至至正十九年(1359),才应朱元璋征辟,时宋濂已50 岁,学术理念早已定型。其后为太子朱标等授经,主持编纂《元史》,参与明初礼制的建立等,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他的《孟子》学,正可作为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学术理念中,我们轻易便能找到洪武朝《孟子》学变革的“同类项”。
1.宋濂对“近世”儒者徒以博学为高而昧于力行持批评态度,强调“经”指导事功践履的作用。
宋濂本身的志向,便是能够在事功上有所作为。《龙门子凝道记》借弟子之口云:“天下有道,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治,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先生志也。”[7]2186是可见其人生志向。因此,与朱元璋一样,宋濂也对当时的儒者缺乏“措之于政”的能力予以了批判。《钱塘沈君墓志铭》云:
司马迁谓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近世师丧经晦,为士者以强记多识为高,而昧于力行。问之,则无不知,措之于政,则患不能。于是迁之言若可信矣。吾尝私病之,以为儒者之道,岂以多识强记为哉?亦论其行与事而已。其行诚非也,虽多识强记,乌足谓之儒!其行诚君子也,为身则端,为家则和,何暇计其余哉?[7]1449
“问之,则无不知,措之于政,则患不能”,正是针对元代学术模式培养下的学者缺乏实践能力的批判。
宋濂继承元代《孟子》学的观念,将《孟子》视为“经”,他说:“《孟子》以大贤明圣人之道,谓之‘经’亦宜。”[7]225而之所以称作“经”,是因为“不违戾于道而可行于后世”。《经畬堂记》云:
圣人之言曰“经”,其言虽不皆出于圣贤,而为圣人所取者亦曰“经”。“经”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统天地之理,通阴阳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状,气运之始终;显之政教之先后,民物之盛衰;内之饮食衣服器用之节,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仪;外之鸟兽草木夷狄之名,无不毕载。而其指归,皆不违戾于道而可行于后世,是以谓之“经”。[7]225
虽然仍然高倡“不违戾于道”,但落脚点则在于“可行于后世”,这是“经”的“指归”所在。在他看来,“五经孔孟之言”,其核心就在于施用,而不在于文本上的考究。《经畬堂记》云:
学者眩于其名,趋而陷溺焉者甚众,而五经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过也,学五经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见诸事功故也。夫五经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尧、舜、禹、汤、文、武,其臣皋、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义、礼乐、封建、井田,小用之则小治,大施之则大治,岂止浮辞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顾切切然剽攘摹儗其辞,为文章以取名誉于世,虽韩退之之贤,诲勉其子亦有经训菑畬之说,其意以为经训足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于学经矣乎?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于彼者之众也。吾所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政则断,以处富贵则固,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来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7]226
学者陷溺,孔孟道晦,根本原因在于后世学者“不能明其道、见诸事功”。学经的目的,在于修身、行政、处世、垂法等方面的“小用之”“大用之”。在此之外,宋濂以经为“文之至”,因而论文之时,也每每以事功作为评价标准,如“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7]75、“秩然见诸礼乐刑政之具者即文也”[7]834、“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7]2002等等。凡此种种,数见不鲜,其推崇事功之义,已表述得淋漓尽致。
宋濂对元代理学家“辞费”的解经方式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龙门子曰:“孔子之传《易》,孟子之释《诗》,加以数言而其意炳如也。是何也?辞不必费也。辞之费,其经之离乎。汉儒训诂经文,使人缘经以释义,必优柔而自得之,其有见乎尔也。近世则不然,传文或累言数百,学者复求传中之传,离经远矣。其造端者,唐之孔冲远乎?”[7]2197
所谓“传中之传”,即是“疏”,故宋濂说是孔颖达造其端。而元代的“纂疏体”“旁通体”经疏,正是以孔颖达《五经正义》自比⑪,其著作也正是“辞繁旨深”的“传中之传”。而宋濂认为,“传文或累言数百,学者复求传中之传,离经远矣”,这种“辞费”的经典诠释范式,反而造成了读者和经典的疏离,无法使读者真正体会到经典的义理。
宋濂认为,“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7]431,要理解经典,就应当直接考之经典本身,而不必拘泥后儒之说。《河图洛书说》云:
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可强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其言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画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止也。故程子谓观象亦可以画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一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7]1950
后儒之说,皆“不必”牵合,否则难免“强而通”,这本就是经典与其诠释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宋濂提出了他的经典解读方法,即“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六经论》云:
惟善学者,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始焉,则戛乎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7]1878
这种说法,与黄宗羲所说的“当身理会,求其着落”“屏去传注,独取遗经”[10]48如出一辙。在宋濂看来,只有“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才能逐渐将经典的道理涵养于心中,最终达到“经与心一”的境界。这种解经的方式,无疑是最为直解简易的做法了。
3.宋濂虽然尊经,但是并不拘泥于经,而要求学者能够超出经的文本,去直接感悟与把捉形而上的“心”与“理”。
考虑到测试方便及实际工程需要,我们结合仿真数据,对背靠背功率分配/合成器进行了一体化样件加工,并进行了组装、测试。工作频段高和结构相对复杂等特点导致了功率分配/合成器对结构尺寸非常敏感,进行精细加工及组装已非常必要。将整体结构分成总功率端口盖板、空间径向波导盖板、阻抗过度变换,探针,聚四氟乙烯支架、连接波导6部分进行加工,加工精度要求控制在±0.02 mm,表面镀银处理,加工完成后,按顺序用螺钉紧固连接,保证安装过程中滤波器内部腔体无污染。加工组装后实物照片如图4所示。
宋濂认为“六经皆心学”,而六经与“心”的关系,则是影与形。《六经论》云: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心譬则形,而经譬则影也。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其道不亦较然矣乎。[7]1878
“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以此言之,“心”及其中之“理”,其重要性是肯定要超过经本身的。宋濂更进一步说:“使人人知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7]2199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理想的境界,连六经也不必作了。职此之故,为学的关键,在于把捉此“心”此“理”,而不必拘泥文本。若只是屑屑于文本之间,就“末矣,陋矣”。《龙门子凝道记》云:
子以为《易》在竹简中耶?阴阳之降升,《易》也;寒暑之往来,《易》也;日月之代明,《易》也;风霆之流行,《易》也;人事之变迁,《易》也。吾日玩之而日不足,盖将没齿焉。子以为《易》在竹简中耶?求《易》竹简中,末矣,陋矣![7]2237
下文更借弟子之口云:“非惟《易》独然,而诸经亦皆然也。”只要能把握诸经所蕴含的“心”中之“理”,不仅不能拘泥于文本,反而应当超出文本之外,去直接感悟与把捉。
“心”也好,“理”也罢,都是形而上的“本体”式的学术理念。宋濂的这种思想,实则将理念的重要性置于经之上。由此出发,对理念的诠释,也较经的文本解读为重。宋儒借用佛教术语,对“体用”大加发明,本就是对理念的推崇,其最著者,莫过于朱子补《大学》一举。宋濂的这种思想,可谓其来有自。然而也正如朱子补《大学》使《大学》成为了理学的论证材料一般,宋濂的这种思想,也使得诸经成为了论证此“心”的材料或探求此“心”的工具,故曰:“《易》《诗》《书》《春秋》,吾器也。”[7]2199
三、结 语
宋濂的学术渊源,包括金华朱学、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佛学五个方面,可谓是集诸家学术传统于一身。⑫要选择一个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代表,宋濂当之无愧。而通观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对事功的推崇、对简易解经方法的提倡,还是对经典本身独立性的消解上,宋濂的思想始终是与朱元璋的三大政策具有一致性的。由此看来,朱元璋对《孟子》学的改革,实际上是与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学术趋向是一致的,并非简单的是皇权对学术的宰制。换言之,元末明初的士人群体,早已酝酿着《孟子》学变革的学术理念,只不过是待朱元璋的三大政策才得以真正落实罢了。这一点,通过宋濂参与《群经类要》的编纂便可以看得出来。
相比而言,永乐朝编纂的《四书大全》,基本上承袭自元代的《孟子》学传统;而洪武朝的《孟子》学变革,则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的发展更为契合。首先,《四书大全》仍是“辞繁而旨深”的解经方式,而随着心学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的《孟子》学著作日益通俗、简洁。如鹿善继《四书说约》,只是将自己的理解一一罗列,不再繁琐地征引前代注疏;如题为李贽的《四书评》,更是以小说评点的方式对《孟子》进行解读。其通俗性与简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与《群经类要》《精诚录》的编纂具有一致性。其次,《四书大全》仍是注疏的形式,而明代中晚期学者的著作,有许多都跳出了注疏的形式,而以语录、文集为主,许多名家如吴与弼、王守仁等,一部注疏都没有作。他们以自己的理念为核心,需要论证时,才将《孟子》等经典用以佐证。这与朱元璋以《四书》、五经论证“敬天”“忠君”“孝亲”理念的做法是一致的。再次,朱元璋对《孟子》的删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孟子》研究侧重心性论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洪武朝对《孟子》学的变革,虽然看似行政因素较大,但一则与元末明初士人群体的学术趋向相适应,二则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乃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观永乐朝的《四书大全》,不仅跳过洪武朝的变革直接元代,而且与此后《孟子》学的发展大相径庭。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与其说是发生于永乐朝,毋宁说发生在洪武朝。
注释:
① 唐代以前,“亚圣”仅表示“亚于圣人”,因而许多人都被称作“亚圣之材”“亚圣之贤”等,并非专称。自唐代以降,“亚圣”即为颜子的专称。到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乃称孟子为“亚圣”,而将颜回改为“复圣”。
② 按,薛延年,字寿之,此处有误。
③ 参见谷继明:《试论宋元经疏的发展及其与理学的关联》(《中国哲学史》2014 年第1 期)、刘成群:《“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 年第3 期)、廖颖:《元人诸经纂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 年)等。
④ 拙文《理学的考据进路——论元代“旁通体”经疏的发展》尚未正式发表,然已于孟子研究院“第二届国际青年儒学论坛”、华东师范大学“首届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获评优秀论文)、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儒学·理学·心学:第三届上海儒学博士生学术论坛”(获二等奖)三次会议上宣读,读者可参考三次会议论文集。
⑤ 参见唐宇元:《宋濂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87 年第3 期)、陈宝良:《明初心学钩沉》(《明史研究》第十辑,2007 年)、李玉亭:《宋濂与宋明理学》(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8 年)、甄洪永:《明初经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 年)、刘玉敏:《六经皆心学:宋濂的心学特色及其影响》(《孔子研究》2016 年第4 期)、路鹏飞:《明初理学思想辨析——以刘基、宋濂、方孝孺为例》(《贵阳学院学报》2018 年第3 期)等。
⑥ 参见戴克瑜、唐建华:《类书的沿革》,成都:四川省图书馆学会,1981 年,第 63 页。
⑦ 严格地说,《群经类要》由于增添了注释,与“类书”的概念不符,不当归入“类书”之中,然其以类编纂,勉强亦可以归入“类书”之属。
⑧ 据现代学者考证,罢孟子配享之事当在洪武二年。参见张佳佳:《〈孟子节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7 年。
⑨ 按,笔者以中华书局1983 年本《四书章句集注》计算,除去标点,《孟子》正文共260 章,35337字,《节文》所删88 章共16492 字。朱高正先生的统计结果小异:“实则朱熹审定的《孟子》全文,共计二百六十条,《孟子节文》则保留一百七十二条,实际删去的应是八十八条。除此之外,文字删减、税(引者按,当作“脱”)漏或分章有异者有三处(自注:不计在删除的条目中)。若以字数计,《孟子》全文总字数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二字,删除的字数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九字,而在《滕文公下》第一章中,《节文》多加了一个‘兽’字。因此,《节文》只剩一万八千(引者按,脱“八”字)百五十四字。(引者按,有脱字)而言之,被删除的字数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一。”见朱高正:《孟子劫文》,《孟子研究》第2辑,首尔:韩国孟子学会,1999 年,第 369 页。
⑩ 李存山先生云:“统观朱熹对人物理气同异的论述,除了在解释《孟子》‘生之谓性’章时遇到困难之外,其余占据主流的是‘理同气异’的思想。”见李存山:《从性善论到泛性善论》,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49 页。
⑪ 赵顺孙《四书纂疏序》云:“顾朱子之奥,顺孙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强陪于颖达、公彦后,祇不韪尔。”见赵顺孙:《四书纂疏·四书纂疏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4 页。
⑫ 参见陈寒鸣:《简论宋濂思想的特色》,《孔子研究》1993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