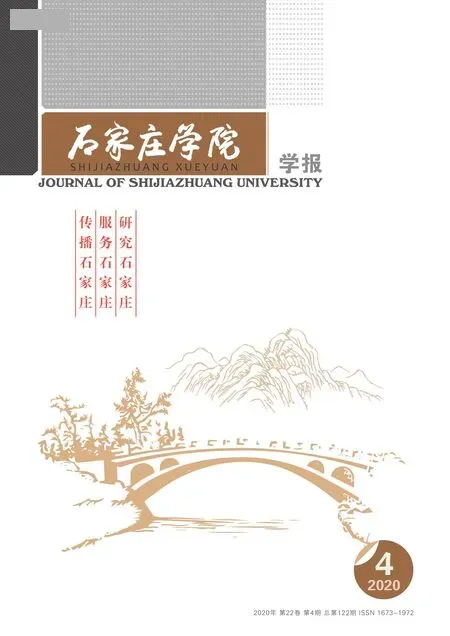试论叔向“礼”的思想
高瑞瑞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叔向,名肸,因其家族食邑于羊舌,后以采邑为氏,故而又称为羊舌肸、杨肸。羊舌氏出身晋国公室,[1]是晋国强宗之一,叔向的父亲羊舌职、兄羊舌赤、弟羊舌鲋均为晋国的大夫。[2]1280-1281叔向本人是晋国的上大夫,多次参加诸侯国间的邦交活动,以“直”闻名,孔子称赞他为“古之遗直”[3]1367。与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和吴国公子季札都有交往,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目前学界对叔向的讨论,虽充分肯定其高尚人格,但多将之定位为保守的礼治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主张是以礼治国,反对变革。叔向所谈之“礼”内涵究竟为何,则未见学者专论,仍可补申。本文拟结合叔向的政治实践以及晋国时局对其所谈之礼进行探讨。
一
晋悼公时,叔向因习于春秋,经司马侯举荐,担任太子彪的傅。[4]445太子彪即位后,叔向便成为晋君的傅,[3]1026,1172彪就是历史上的晋平公。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羊舌氏被灭,记述这一事件时,文献未见叔向言行,故叔向在此前或已去世。①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曾经告诫叔向“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并未记载叔向对此的回应,从之后来看,未见其行事风格有明显转变。季札在《左传》中所作的预言后来都有所应验,故叔向或在此事件中遇难。唯因叔向生年不详,故无法推知此时叔向的年纪。所以,文献所载叔向的活动集中于晋悼公、晋平公、晋昭公三位国君时期。
叔向重言辞,亦善言辞。正因如此,史书对其言辞记载甚详,而对其活动叙述较略。据《左传》记载,其活动主要集中于诸侯邦交领域。
学者论及叔向,多因叔向曾言“礼,王之大经也”[3]1374,主张行事要“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3]1267,而将之视为传统的、保守的礼治主义者。若仅就叔向对礼的重视程度而言,此言或是。叔向的思想及其言论中,礼的因素非常浓厚。然叔向所谈的礼,是否完全等同传统意义上的礼呢?这点还需进一步考察。
传统意义上的“礼”是以维护周王权威为核心。[5]检视史书所载叔向的言辞,直接关涉周王的并不多,可见其在周王身上投放的注意力并不多。此外,从叔向言谈的字里行间,尚可窥见其对周王的态度。《左传》昭公九年言周王就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大夫梁丙、张趯帅阴戎伐颍二事,派人来责备晋。叔向劝告执政的范宣子曰:
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3]1 309-1 310
学者多据此认为叔向尊王,[6]从“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来看,这有一定道理。然详审其逻辑可知,他所强调的是若不尊王,会导致诸侯对晋国怀有贰心,进而影响晋国的盟主地位,并以此解释文公以来,晋国霸业渐衰这一现象。换句话说,叔向仅是将尊王作为维持晋国霸业的手段。这段话还特别提到了王的“辞直”,也就是说,周王要保证自身利益,已不能仅凭“王”之地位本身,而要和其他向盟主诉讼的小国一样,依靠作为盟主的晋对其“辞”的评判。周王已经没有作为王者的威风了。叔向之所以说要慎待此事,一方面是因为周王的言辞于情于礼都无可辩驳,更重要的是,叔向把周王作为晋国霸政体系的一个因素来考虑,担心处理不当,影响晋国霸业。
此外,叔向就另一事件所作出的评论,更为明晰地表达其对周王的态度:周景王王后去世,晋国派遣荀跞和籍谈去吊丧。丧礼完毕之后,周王宴请二人,在宴席上,周王问荀跞为什么别的诸侯都对王室有所贡献,唯独晋国没有?籍谈回答说是因为其他诸侯国始封时,王室对他们都有所赏赐,故他们能有器物贡献给王,而晋国封地偏远,且受封时未得赏赐的彝器,所以无法贡献彝器给周王。周王当即反驳籍谈,细数唐叔受封时所受赏赐,并且告诉籍谈,他的祖先就是因为曾经执掌晋国典籍,所以才以籍为氏,籍谈怎么能把这些都忘记了呢?周王的一番话让籍谈哑口无言。籍谈回来之后,告知了叔向这件事。于是叔向有了下面的一番言论:
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于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3]1374
叔向在言谈中直指周王失礼。客观而言,周王之言行固有不当,但与晋对王室不曾贡献器物以及籍谈对历史的无知是两码事。叔向言谈之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周王身上,显系替晋国君臣开脱。原本作为“王之大经”的礼,核心在于维护周天子权威,而叔向却以之指责周王。可见叔向所说的“礼”,重心并不在周王,而在晋国,进一步而言,是晋国的盟主地位,而非晋君个人权威。就此来看,叔向论礼的出发点已不同于传统的“礼”。
二
叔向眼中之礼所指为何?其判别“合礼”与否的标准何在?笔者以为,叔向所谈的“礼”大致可分为邦国与个人两个层面:
就邦国层面而言,叔向强调礼的场合集中于诸侯邦交活动这一情境下,这种场合他所谈的礼,大部分以晋国作为盟主为前提,以诸侯是否对晋国表现出应有的敬意,作为“合礼”与否的标准来发表评论。可见,在叔向的观念中,“礼”是维护晋国霸政的一种手段。例如,晋在栾盈出奔后,为锢栾氏而召开商任之会。会上,齐侯、卫侯不敬,叔向认为二君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3]1063有学者认为,叔向在此处将会朝作为“礼之经”进行强调,是为了适应霸主政治的需要,[7]此说甚是。
叔向十分重视会盟,他认为“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3]1355-1356。将诸侯间的朝聘会盟看作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实际上,此时会盟的主要内容是盟主协调盟国之间关系,所谓“诸侯讨贰,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3]1355在这一活动中所规定的一些礼,无非是各个盟国表达对盟主的尊崇与恭顺,故而会盟的实质是盟主展示自身地位以示尊于诸侯的活动。叔向对会朝及其“礼”重要性的强调,目的在于说明各诸侯国当向作为盟主的晋表示自己谦恭顺从的态度。这种场合下的“礼”,往往包含“敬”的因素,主要是指对事情的重视,一般体现在对人的礼节周全这一方面。①《国语·周语下》记述叔向对单子的评价时,对“敬、俭、让、咨”进行了阐述。其中隐约可见这一思想。
就个人层面而言,叔向运用“礼”这一标准对人物进行评价,故从中可知其对“礼”之内涵的认识。
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晋侯使郊劳,辞曰:“寡君使叔弓来继旧好,固曰‘女无敢为宾’,彻命于执事,鄙邑弘矣,敢辱郊使?请辞。”致馆,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3]1229
叔弓得到叔向“知礼”的评价,是因为其言辞处处以国事为重,做到了“辞不忘国”和“先国后己”。浑言之则是将邦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叔向不仅将之作为礼的原则来要求个人,对如此行事的宗族亦大加赞赏。
郑国的罕氏在郑国饥荒时,以家产出贷赈灾;宋国的乐氏在宋国遭灾时,不仅以家产出贷,而且不言己功。叔向闻后,评论曰:
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3]1157-1158
叔向对以邦国为重、不孜孜于私家利益的宗族如此不吝称赞,足见其对“先国后己”的推崇。这一观念也融汇到叔向自身的政治实践中。晋楚弭兵之会,将举行歃盟时,晋得知楚人“衷甲以入”,对此,叔向表示“弭兵以招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3]1132,表现出叔向不计个人安危、唯图求利晋国的思想。
叔向对“礼”内涵的这种认知,在当时思想界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此试作一简要分析。
春秋时代,人们普遍重视礼,诚如刘泽华先生所言:“春秋时代尽管是社会变动的时代,但这种变动没有也不可能把礼从生活中抛弃。”[8]65当时思想家几乎都谈礼,与叔向同时的如晏婴、子产等人,言辞之间同样充满了对“礼”的关切。概括而言,晏婴认为礼“与天地并”,将之作为加强国君权力的手段,国君通过“以礼治国”达到“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3]1480这样一种君臣上下秩序井然的局面,有学者据此认为晏婴所说的礼表达的是实行中央集权的思想。[9]146另一位思想家子产,虽将礼认定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3]1457,却无法将礼的准则在政治实践中加以贯彻,面对现实问题不得不以“救世”为标准,采取一些“不合于礼”的措施来应对,并且对此毫不讳言。[3]1277
与他们不同的是,叔向言谈间很少关涉晋君平公。仅在与晏婴论季世时有所涉及,且有指责之意。[3]1237。以情理度之,叔向身任平公大傅,负有陪伴君侧、朝夕讽谏之责,但文献记述的这类事情很少,仅有叔向谏勿杀竖襄之事。[5]461-462
另外,因为叔向的“礼”以维护晋国盟主地位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换言之,叔向在政治活动中,始终可以将礼作为自己各种行为的理论支撑。经过叔向改造之后的礼,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精神内涵,而非是具体的条文,因而并不妨碍叔向根据实际的政治形势,采取灵活而务实的对策。
三
叔向这种礼的观念的形成,与晋国当时内外的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自齐桓公开创霸主政治以来,作为盟主的诸侯国在享有一些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特定的政治责任,晋国也不例外。自文公开创霸业以来,晋国国势虽几经起伏,却始终保有盟主地位。晋平公时,有人曾明确表达出对晋国的期望:“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3]1117然而,自晋厉公加强君权的努力失败后,晋国内部,卿权已然尾大不掉。卿族甚至不需要借助君权来平衡和分配彼此利益。
叔向时期,此风更甚。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此时身为国君的晋平公的身影稀见于诸侯邦交活动,政事几近专任于正卿。子产曾评价晋平公说“晋君少安,不在诸侯”[3]1248,晋平公喜妇人、筑宫室、[3]1221,1237说新声,[5]460不再以晋国的盟主地位为念。而先后为政的范宣子、赵文子和韩宣子,更是汲汲于家族利益,无心图霸。
范宣子为政,专注于打击政治对手,发展家族势力,在逼迫栾盈出奔后,甚至动用晋国盟主的地位,先后两次①襄公二十一年商任之会和襄公二十二年沙随之会。通过会盟禁止诸侯接纳栾氏,挟邦国之势,谋一族私利。在国内与和大夫争田,闹得舆论沸沸扬扬。[5]455赵武继士匄为执政后,面对楚国的积极求霸,步步退让。同时,在处理卫国内乱时,以晋国盟主之尊为臣执君,对孙氏庇护有加。而韩起执政时,面对楚国伐吴灭陈的扩张行为却袖手旁观、毫无作为,反而忧虑自己财产不足。[5]480这些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引起了诸侯对晋的不满,从根本上导致晋国盟主地位的动摇。
国内情势如此混乱,必然导致对外软弱。面对楚国势力的增长,晋国霸权已然衰落。长期活跃在诸侯邦交领域的叔向,对这一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叹曰:“晋少懦矣,诸侯将往。”[3]1208在此背景下,叔向不得不以非常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晋楚关系。襄公二十七年的弭兵之会,在“晋楚争盟”时,叔向根据当时的形势,劝说赵文子不要争先,而是让楚人先歃;[3]1133陪同韩宣子送女如楚时,明确表示要按照礼的要求恭敬行事,以避免落人口实;[3]1267劝说晋君不要意气用事,要对楚国公子以礼相待等。[3]1279可见,相比某种高高在上的道义,现实利害已然成为叔向处理对外关系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一切从政治现实出发,尽力维护晋国的盟主地位才是叔向所奉行的准则。当这一准则贯彻到叔向“礼”的思想时,则体现为对“礼”作为一种个人修养的淡化,而突出了礼在邦交秩序层面的意义。
实际上,面对这一形势,作为政治家的叔向,仍力图有所作为。对晋国内部,叔向一方面对晋公室“无度”感到忧心忡忡,[3]1237另一方面将“礼”的内容强调为“辞不忘国”“先国后己”,主张以国事为重,反对一心谋求一家一族的私利,在当时的晋国,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怀。对外,叔向努力维持晋国的盟主地位,扩大并巩固晋国的影响,颇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如虒祁之宫之事所引发的平丘之会前夕,对不愿参会的齐国,叔向义正辞严地陈述了盟会之礼的重要意义,谴责齐国违礼。而对不被允许参会的鲁国,叔向则不顾晋与鲁为“兄弟之国”,按照周礼应当相亲相近这一要求,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胁。[3]1357透过这些具体行为,更足见叔向所言之“礼”的实质,是以晋国的利益为核心。这也正是叔向被称为“社稷之固”[3]1060的原因。
四
叔向作为霸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一直致力于维护晋国的霸主地位。晋国的政治形势,决定了他不再奢求通过加强君权来巩固晋国的盟主地位,同时他又不满于卿族之间争权夺利,不以国事为念。于是在邦国层面上,将礼规定为对盟主国,亦即晋的恭顺尊敬;在个人层面上,主张“礼”的内涵是“辞不忘国”“先国后己”,这些都是为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传统“礼”命题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叔向所强调的礼,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传统的礼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叔向论礼的核心是晋国,不是天子和国君,这固然与晋国的政治形势有关,但同时这一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表明,此时的邦国,逐渐开始超越天子、国君个人而开始成为政治和外交的主体。由此可见,叔向“礼”的思想是对传统礼进行适应霸政改造的结果。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在有些场合,叔向大谈礼,而在另一些场合,叔向却对礼的要求刻意的轻忽。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不能将叔向礼的思想简单定义为传统的、保守的、反对变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