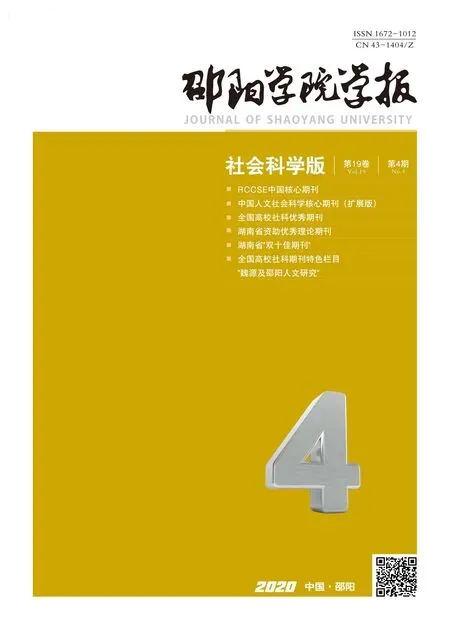从《荀子》成书流变谈荀赋的俳谐讽谕
陈祥谦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荀况之书长期受到冷遇。及至现当代,《荀子》的价值才为人所重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世多有其书。”[1]457又《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1]511这是有关荀况著述及其流布情况的较早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因内秘府藏书颇多散亡,成帝遂诏令刘向校雠整理。刘向校雠荀况文章为两类:一类为《汉志·诸子略》儒家“《孙卿子》三十三篇”,即子书;一类为《诗赋略》“孙卿赋十篇”,即后世所谓别集。
《孙卿子》在汉魏六朝既未列于学官也无传注,而“孙卿赋”却备受推崇。皇甫谧《三都赋序》:“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赋之首也。”[2]1873刘勰认为荀况、宋玉等“并辞赋之英杰”[3]80。荀况在此期间已然被当作一流辞赋家,《荀况集》到梁阮孝绪《七录》著录时尚存二卷。《隋志》著录“《荀况集》一卷”,注曰“残缺,梁二卷”“《孙卿子》十二卷”[4]1056。两《唐志》均著录“《荀况集》二卷”“《孙卿子》十二卷”,说明《荀况集》《孙卿子》在唐开元年间是见存的。杨倞以“《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5]7522,整理编定《荀子》为20卷,并予传注;《新唐志》著录该注本。《宋史·艺文志》亦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6]5172,但未著录《荀况集》。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国子监刊刻杨注《荀子》;其后官府坊间翻刻、影刻、摹钞、影钞该注本多达百余种。清末王先谦以谢墉安雅堂刻本为据,参校黎庶昌《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唐仲友台州公使库翻刻熙宁监本、明虞九章和王震亨合校订正本,采诸家之说择善而从,编成《荀子集解》。今之通行本仍为王氏《荀子集解》及其翻印本。
关于《荀子》文本的真伪、作者、篇目、篇数、版本等文献学层面的诸多问题,在学界激起争辩且分歧较大。这些争议,也影响了大家对荀赋价值的认识。本文在厘清《荀子》成书流变的基础上,解析荀赋的俳谐讽谕价值。
一、刘向对荀况文章的归类整理与定编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启了系统编纂图书目录之先河。刘向自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至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20年里从事书籍整理工作。阮孝绪《七录序》:“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本书。”[7]262刘向每校一书即撰《书录》(叙录)一篇,并载于所整理之书,后结集为《别录》20卷。刘歆继承刘向未竟事业,在总成《别录》基础上,去详从略而成《七略》。《别录》《七略》二书虽佚,但仍可据后世辑佚之书,以及班固以《七略》为蓝本撰成的《汉书·艺文志》推知其大致的情况[8]。
刘氏《七略》之于众家篇章书籍,或为按作者文章著述性质归类及数目记录。如班固依《七略》编成的《汉志》类分众籍为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三十八种”,其中《六艺略》“书”著录“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春秋”著录“《新国语》五十四篇”注曰“刘向分《国语》”;《诸子略》“儒”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道”著录“刘向《说老子》四篇”;《诗赋略》著录“刘向赋三十三篇”[9]325-339。显然,刘向以上文章著述是依一定标准分别著录的,而且,其各种著作并不互相包含。又如《七略》分贾谊文章著述为两类,《诸子略》“儒”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阴阳”著录“《五曹官职》五篇”注曰“汉制,似贾谊所条”;《诗赋略》著录“贾谊赋七篇”[9]332-339。据《汉书·贾谊传》《文心雕龙·诸子》等,贾谊有《吊屈原》《鵩鸟》诸赋,《隋志》集部注记“《贾谊集》四卷”,是即其别集;“《贾谊》五十八篇”即《隋志》诸子所录“《贾子》十卷”[4]997,刘向称其“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9]496,刘勰谓之《新书》。考今本《新书》有《过秦》等58篇之目,但不含贾谊赋。此则足以说明自刘向定著贾谊文章为“诸子”“诗赋”,二者就不曾混编。实际上,《七略》归类颇为严谨,如班固为消除《七略》归类著录瑕疵也仅有三处调整:一是从《六艺略》“乐”中“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因《琴颂》属赋,当在《诗赋略》;二是从《诸子略》“出蹴鞠一家”入《兵书略》“兵技巧”;三是从《兵书略》“兵权谋”中“出《司马法》入礼”,即将《司马法》调到《六艺略》“礼”[8]。由此可知,刘向按既定分类体制和原则进行的著录基本准确,是严谨的。
笔者曾撰文就《汉志》继承《七略》及著录标准,“《汉志》著录的西汉著作中均未混搭作者其他性质的作品”,“属一家言的经传诸子不入别集”,“班固去《七略》或显或隐重复著录”[8]等问题有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七略》对先秦文章著述的分类大抵同理。如《诸子略》“杂家”著录“《五子胥》八篇”,又《兵书略》“兵技巧”著录“《五子胥》十篇”注曰“图一卷”,五子胥即春秋吴相伍子胥。《诸子略》“法家”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又《兵书略》“兵权谋”著录“《李子》十篇”,李子即李悝。《诸子略》“名家”著录“《黄公》四篇”注曰“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意即黄疵作有歌诗,但不在此四篇而是在《诗赋略》“歌诗”之“秦歌诗”中。即如《诸子略》“杂家”著录“《臣说》三篇”注曰“武帝时(所)作赋”,其本意是说武帝时臣说作有赋,《诗赋略》著录“臣说赋九篇”[9]337-340可证,此处校改加“所”字则大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上诸人文章,《七略》均按其性质的不同分类著录,尤其“子书”“诗赋”互不交集[8]。《史记》载荀况著有数万言,刘向校雠定著“《孙卿子》三十三篇”“孙卿赋十篇”[9]331-340,分别著录在《诸子略》和《诗赋略》,实为后世所谓子书、别集。显然,《七略》对荀况“子书”“诗赋”的著录亦不相类属,遵循了其既定分类体制和原则。嘉锡先生虽清楚《孙卿赋》《孙卿子》“本是二书”,却以为前者原本在后者,“盖别本单行者”[10]53,尚未明了个中关系。
关于荀况文章篇数,人们多依今本《孙卿书录》认定为32篇。据杨注《荀子》不同版本所载《孙卿书录》,其中数据、文字多有异,说明其在传抄、刊刻过程中有改易,已非刘向之旧。按《汉志》著录,荀况文章有43篇,即《孙卿子》33篇,《孙卿赋》10篇。王应麟所录《孙卿书录》较原始,其曰:“刘向校雠书录序云: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11]1408333篇除去290篇之重,正好43篇。此所谓“三十二篇”,当是王氏从众而改。《汉志》著录的“《孙卿子》三十三篇”,是为刘向校雠定著。《孙卿子》定编后长期得不到重视,以致亡佚残缺严重,这种情况《隋志》原注资料可佐证。杨倞重编《荀子》大抵有搜遗补阙,如《大略》《宥坐》等6篇皆可证,亦但得32篇。其所阙1篇,当是排除了刘向《书录》(叙书)篇。阮孝绪说“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皆载本书”[7]262,意即刘向所撰《书录》载于所编之书。如《邓析》原本只有1篇,《汉志》著录“《邓析》二篇”,其中就有《叙书》1篇。《邓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2]334
历代史志目录均以《孙卿子》为子书。然则,《孙卿子》在重编前不含“赋十篇”亦可肯定。一如《汉志》著录的《黄公》不含其歌诗,《臣说》不含其“赋九篇”[8]。刘向校雠定著,凡非作者著述和可疑者皆有特别说明,如《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2]332《晏子》8篇,明确为晏子所著者6篇。又《列子书录》:“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2]334《列子》8篇,其可疑者4篇。而《孙卿书录》无类似说明,则刘向定著的《孙卿子》均为荀况自著,大抵可确定。在主要以简帛为载体的时代,刘向校定本《孙卿子》被缮写者誊抄成简帛12卷,或未可知。后世沿用此数,如《隋志》、两《唐志》著录。至于书名,秘府、民间抑或不同,刘勰较早称之为《荀子》:“《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3]159《文选》李善注引称《荀卿子》《荀子》。故改《孙卿子》为《荀子》,亦非杨倞首创。
刘向校定、归类于《诗赋略》的“孙卿赋十篇”,即后世史志目录所著录之《荀况集》。此“诗赋”非特指两种体裁,而是当时分类名称,其涵盖赋、诗或楚辞、颂、成相杂辞、隐书、歌诗、歌谣、声曲折等,前5种总称为赋,后3种统称歌诗。刘氏《七略》之《诗赋略》可验诸《汉志》,荀勖《晋中经簿》四部分类在“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7]262而改《诗赋》为《文翰》,阮孝绪《七录》“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7]262而变《文翰》为《文集》,《隋志》依《七录》始作“集部”。实际上,《诗赋略》著录的诸家已具“集部”之楚辞、别集、总集雏形,只是类分种属标准不同而已。《校雠通义·汉志诗赋》:“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12]99别集即个人文集,兴于东汉,主要收集作者未入经传诸子的文章,如《司马迁集》与《太史公》(《史记》)之别。《司马迁集》至少收集《诗赋略》“司马迁赋八篇”,据《汉书·司马迁传》,其《报任安书》等亦当在集内。同理,《荀况集》当收录“孙卿赋十篇”,包括“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3]77的《礼赋》《智赋》等5篇;《韩诗外传》卷四所引《佹诗》(末章),以及《孙卿书录》“为歌赋以遗春申君”[2]333者;成相杂辞3篇。《荀况集》在《七录》著录有二卷,《隋志》著录一卷且残缺,两《唐志》复有二卷;《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已无著录,当与杨倞重编《荀子》而使《荀况集》失去单行必要有关。
二、杨倞合编《孙卿子》《荀况集》成《荀子》
众所周知,自刘向父子校定众籍以来,历经兵燹人祸无数,因此幸存的书籍多有阙佚亦不足为怪。如《战国策》到北宋仅存22篇,经曾巩三次校补方成今日面貌。曾巩云:“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13]1199又如《管子》于唐前散佚颇多,虽经多次校补,尚有《王言》等11篇亡佚,而且,最后定编者是将《轻重》裂为7篇才凑成86篇之数以契合《汉志》著录的。重编《荀子》的杨倞,两《唐书》未有传,生平事不详,约为唐宪宗时人。据杨倞自叙,其之所以要编校注解荀况之书,一是因荀书不及《孟子》彰显,“千载而未光焉”[14]51,且从未有过注解;二是因“编简烂脱,传写谬误”[14]51,有碍阅读学习。这抑或是杨倞重编荀书的主要原因,但杨氏却始终不言及荀书损失程度和亡佚篇目,显然有着特别考量,即可以“编简烂脱”为由合编荀况别集、子书而免遭后人诟病,其申明重编《荀子》“盖以自备省览,非敢传之将来”[14]52可证。如苏轼、姚鼐曾就编纂体例指摘昭明太子所编《文选》,萧统始料未及,当然这也不是杨氏之先见。而不言明亡佚篇目,整合更为自由。如赋、成相本属荀况别集,杨氏取之以为其子书篇名,与《劝学》《性恶》等明显不类。《赋》篇由去除《礼赋》《智赋》《佹诗》等篇题的6篇诗赋合成,《成相》由3篇(一说4篇)合成,与《孙卿子》一篇一题的体例亦不吻合。故杨倞以《孙卿子》《荀况集》合编成《荀子》毋庸置疑。
合编不同性质的著作是有先例的。如《七略》之《六艺略》“孝经”著录“《弟子职》一篇”,又有“《说》三篇”;《诸子略》“道”著录“《筦(管)子》八十六篇”注曰“名夷吾,相齐桓公”[9]330-333。《弟子职》与《管子》分别著录于“六艺”“诸子”,显属不同性质的著作。《七录》《隋志》未著录《弟子职》,至于作者,颜师古是据其时《管子》已有篇目判定的,其注引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考《风俗通义》,应劭未曾有此语。《意林》引《风俗通义》有“《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则之”[15]619一句,颜注或援于此,但应氏亦非直接从单行本《弟子职》引用,说明《弟子职》一书在东汉时就被编入了《管子》。而将作者别集、子书合编为一,杨倞确是第一人。自刘向定著荀书到两《唐志》著录,近千年里,《孙卿子》与《孙卿赋》(《荀况集》)一直独立行世。两《唐志》均以开元藏书目录如《古今书录》等为据编订,稍不同的是《新唐志》还著录了此后唐人著述,如杨倞注《荀子》。也就是说,元和十三年(818年)杨倞定编并注解《荀子》前,《孙卿子》《荀况集》仍是独立行世的。成书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的《崇文总目》未著录《荀况集》,《宋史·艺文志》亦无著录。而且,熙宁元年(1068年)国子监刊刻《荀子》依据的是杨注《荀子》二十卷本而非《孙卿子》原本。流传近千年不绝的《荀况集》却在杨倞重编《荀子》后的短时间内就湮没无闻了,合理的解释即杨倞整合《孙卿子》《荀况集》成所谓“孙卿新书”[14]52(仅杨氏一说)《荀卿子》后,《荀况集》失去了单行之必要,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
杨倞合编《孙卿子》《荀况集》为《荀子》,还可从其对篇目的调整、题注中见端倪。很多人为所谓《荀卿新书三十二篇》目录、《荀子新目录》所迷惑,实际上,这两个目录都是杨倞所编,只是次第不同,“荀卿新书”即杨倞新编《荀子》。杨倞之所以不为加有目录的刘向叙录题作《孙卿书录》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根本不是刘向旧有。前述杨倞不明言亡佚篇目,亦是基于自主编目的考虑。杨倞所编《荀子》实乃后世摹钞、刊刻之祖本,故考察王先谦本《荀子》可知其大概。《孙卿子》《荀况集》其时遗存情况,杨倞最为清楚。王先谦本《荀子》前23篇以《性恶》殿后,题注:“今以是荀卿论议之语,故亦升在上。”[14]434这是刘向《孙卿书录》中唯一提到的篇名,如此安排,则足以证明此23篇皆出自《孙卿子》,为荀况手著无疑。其中《儒效》《议兵》《强国》虽间杂疑似荀门弟子记录,但不仅不影响其著作权归属,还可佐证杨氏校补之实。《君子》可能补入荀门弟子记录多于《儒效》等篇,处在两可之间,但从杨倞将其升在第24篇并与《性恶》编为一卷来看,亦是确信其为荀况手著,与前23篇为一类。《成相》《赋》被编在一卷,分别是第25篇和第26篇。杨倞引《汉志》谓之《成相杂辞》,称《成相》“盖亦赋之流也”,又云“今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14]456。其认可《成相》为赋作,亦承认《成相》《赋》是荀况手著,但称之为“杂语”,显然不是以子书《孙卿子》中固有文章视之。那么,《成相》《赋》篇领括的诗赋,只可能出自《荀况集》。前已论,无论子家作家之诗赋皆不入其经传诸子著作,而是收在别集。如《史记》与《司马迁集》,《女诫》与《班昭集》,又如《王俭集序》:“(俭)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2]3203《大略》注曰:“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14]485又《宥坐》注曰:“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14]520以下即《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注解之意表明,此类6篇当为杨倞整合《孙卿子》之残篇及其搜集的相关资料而成。尽管难以明确其作者,但毕竟与荀况有关,故不宜一味指为伪作。明之上述,很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杨倞据《孙卿子》《荀况集》遗存合编成《荀子》并详加校注,成为后世模范之祖本,编校注释虽未尽善,然功莫大焉。
三、荀况赋的俳谐讽谕价值
荀况“赋十篇”,即杨倞重编《荀子》之《赋篇》《成相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5篇赋及《佹诗》和小歌。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荀况《礼》《知》“爱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3]77。《佹诗》之小歌的末章见于《韩诗外传》卷四及《战国策·楚册四·客说春申君》。《韩诗外传》卷四:“(荀卿)因为赋曰:琁玉瑶珠不知珮,杂布与锦不知异。”[16]157《客说春申君》:“(荀卿)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珮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13]567这里均径称《佹诗》及小歌为“赋”,可知《赋篇》皆赋。杨倞谓《成相》“盖亦赋之流也”。
荀况赋的成就,一是在于文体的开创,二是在于其承上启下的讽谕谲谏价值。刘向《孙卿书录》云:“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2]333班固《汉志·诗赋略》亦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9]342皇甫谧认为荀况赋“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赋之首也”[2]1873。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2]1905由此可见,自刘向校定“孙卿赋十篇”(《荀况集》)以降,赞誉颇多,论者基本认为荀子作赋是因为“离谗忧国”,故而“敷陈其志”作赋以“风”以“刺”,其赋“颇有古诗之义”,恰是对古诗“风刺”“谲谏”精神的继承。《毛诗序·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17]271显然,儒家倡导诗赋为政治教化服务,既要讽刺上政、改善政治,对执政者的政治得失予以劝诫,又要委婉曲折且具有一定效果,也就是所谓讽谕谲谏。荀况赋的“风”“刺”即如此。然而,自荀况赋被杨倞编入《荀子》,其文学地位却被掩盖了。这从章学诚的认识略知一二,其《校雠通义·汉志诗赋》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2]卷三章学诚已完全忽略了杨倞新编《荀子》以前论者对荀赋地位和价值的论断。诚然,其将眼光延展到横向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指明赋的形成并非只有一个源头,是诸多体例合力演化而成,识见也颇为高深。
荀况赋既是汉赋的源头之一,也是俗体赋的源头,但章学诚却不这么认为,其曰:“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12]20可见,荀赋尽管被章氏判定为“别集之体”,却依然将其当作一家之言的诸子看待,即其所谓“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12]99。杨倞新编《荀子》的影响不可谓不存在。章炳麟则认为:“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18]101“效物”恰是后世俗赋的主要表现形式。林颐山《重刻张编修〈七十家赋钞〉叙》提出:屈赋“为第一种家法,闳丽温雅者也”;陆赋“为第二种家法,嫚戏诙笑,较第一种而少变者也”;荀赋“第三种家法,风谕恻隐,较第一种侈丽闳衍,简练其式少变者也”[19]卷首。就讽谕谲谏而言,荀况赋具有了俳谐的性质。“俳谐”是由挚虞在其《文章流别论》中提出的“非音之正”[2]1905的、类似倡乐的俗体文学概念,即是刘勰《文心雕龙》所阐释的“谐隐”。其重在微言讽谕,这种谐辞隐语以诙谐、讽谕、嘲隐等为基本特征。《文心雕龙·谐隐》云:“(谐)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谲辞饰说,抑止昏暴。”“(隐)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3]133-135刘勰从政治、道德的角度论述了谐隐的文学价值及意义,指出“意在微讽”“谲辞饰说,抑止昏暴”“辞虽倾回,意归义正”“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的那些作品“有足观者”。其中的嘲隐之作“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3]137。也就是说,荀况不仅是赋体的开创者,也是谐隐的肇始者。
荀况赋颇有“古诗之义”,作为《诗三百》“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因为作者的“离谗忧国”,它并不着意“颂美”的功能,却“含章郁起”讽谕之意图。由于荀况赋采用隐语“谲谏”的方式进行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刘勰在《诠赋》篇论及其特点,即“荀结隐语,事述自环”[3]80。隐语,是指作者用隐讳的言辞来寄寓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示某件事物,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作用,就大的方面而言,是可以凭借它来进行政治教化,并且有助于自身的显达;其次也可通过它纠正某些错误,让迷茫之人醒悟,所谓“会义适时,颇益讽诫”[3]138是也,意即谐隐合于大义而又能用在恰当时机,将具有很大的讽谏作用。荀况赋之《礼》《知》《云》《蚕》《箴》,以及《佹诗》和小歌,皆具讽谕之义。正如《周书·王褒庾信传》传论所总结:“大儒荀况,赋《礼》《知》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谕之义。”[20]743《礼》赋主要写“礼”的作用。“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14]472-473荀况认为,如果完全按照“礼”的原则行事者则可以为王,不完全按照“礼”的原则行事者则可以称霸,完全不按照“礼”的原则行事者必然自取灭亡。因此,要想成为圣人或一统天下,必须“隆礼”。“隆礼”则需有“智”,荀子在《知》赋中铺陈“智”具有“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的功用,那么,“百姓待之而后宁也,天下待之而后平也”[14]473-474,依靠它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天下就能太平。实际上,荀子是借《知》赋规劝国君要以君子之智士执政。《云》赋以云喻圣人,“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14]475,言外之意就是要任用圣人。《蚕》赋以蚕喻贤士,其“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14]477,功勋卓著。《箴》赋则是喻指从事内政外交、忠君爱民的士大夫。荀子通过这些赋作,以物象寓意,塑造了一群理想的圣君、圣人、君子、贤士、士大夫形象,并用以讽谕朝政,敷陈其志。《佹诗》及小歌,与同篇的《礼》《知》诸赋相辅相成。《佹诗》起句曰:“天下不治,请陈诡诗。”[14]480这一表述清楚地说明了荀子写作《礼》《知》诸赋及《诡诗》和小歌意在谲谏讽谕。
战国是继春秋之后的大变革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社会动荡,阶级矛盾也异常激烈。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带来了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和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与之相适应,文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诸子百家的论战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他们游说于各国诸侯,彼此之间互相辩难。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主张,故而引类譬喻,极力铺陈,“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诸子文章的这种铺陈辩说、“假象尽辞”的手法,对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当然,这种纵横诡俗并非赋产生的源,而只是流;赋的直接渊源是承《诗三百》而下的楚地民歌,以及“与诗画境,六义附庸”的荀况赋。总之,在当时“天下不治”的背景下,荀况以赋作“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用客主问答的结构形式和隐语方式铺排叙写,看似体物状貌,实则借比兴、双关等手法托物言志,意在主文而谲谏,且对后世俳谐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四、荀况赋对后世俳谐文学的影响
荀况赋继承了《诗三百》“美刺”之讽谕传统,也对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劝百讽一”的传统具有很大影响。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21]374汉代大赋中继承荀赋“述客主以首引”的赋作形式由枚乘《七发》首发其端,开汉赋长篇巨制之先河。《七发》在赋体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讽谕精神。发扬光大者有司马相如、扬雄、傅毅、班固、张衡、张协,等等。对他们所创作的宏章丽辞之篇什,班固《两都赋序》谓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22]21,也就是说,汉赋的作用之一即是反映民情民愿,讽谕朝政。《汉书·司马相如传》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9]585司马相如的作品尽管“多虚辞滥说”“靡丽”,但依然保持和发扬了讽谕的传统,这个时期的赋作家大多能够如此。如《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聊因《校猎赋》以风”[9]860-864。《后汉书·傅毅传》载:“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23]765由于赋的“颂美”(宣上德而尽忠孝)功能在这一时期被强调,以及作者“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有的赋作或许将讽谕意图隐藏,出以更为委婉的“谲谏”。《汉志·诗赋略》称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之徒“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9]342。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失。”[24]8“颂美”和文辞的彩丽竞繁多少使得汉赋的讽谕意图显得微小或无足轻重,但讽谕才是赋作题旨所在。
自赋体产生之始,其与俳谐就有着密切关系。曹明纲先生说:“(冯沅君)得出‘汉赋乃是优语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后的支流’的结论。……任半塘在此基础上,于所著《优语集》录《史记·滑稽列传》有关楚优孟爱马之条下,先引《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然后下按语说:‘赋出于俳词,此条可证。’后来程毅中、周绍良也认为荀子的《赋篇》‘相当于《隐书》之类,刘向、班固所谓杂赋,应该是一种接近民间文学的诙谐文体。”[25]37-38这类赋虽写得诙谐,着意于调侃、嫚戏、嘲弄,但亦不乏讽谕、批判与自嘲精神。如“自称为赋,乃亦俳也”[3]133的“滑稽之雄”东方朔,敢于在汉武帝面前“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9]655又《汉书·枚乘传》载,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诵好嫚戏”[9]523,自比东方朔。扬雄为赋颇似俳优,其“杂以谐谑”[3]125的《解嘲》既有自我思考,又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撰《逐贫赋》以自嘲。崔骃的《博徒赋》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现实。类似的还有张衡的《骷髅赋》,赵壹的《穷鸟赋》,等等。
体物状貌以寓讽刺之意的俳谐俗赋也发展起来了,如魏晋时曹植的《鹞雀赋》,阮籍的《猕猴赋》《骷髅赋》,蒋济《豺獭赋》,费祎的《麦赋》,诸葛恪的《磨赋》,张敏的《头责子羽文》,陆云的《牛责季友文》,左思的《白发赋》,鲁褒的《钱神论》等。《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裴松之注曰:“济豺獭之譬,虽似俳谐,然其义旨,有可求焉。”[26]276左思《白发赋》“有所寄托和讽刺,一改‘明物’‘宜实’写法”[27]393。《晋书·鲁褒传》载:“元康之际,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28]2437这类以俳谐的笔调、客主问答的形式批判社会的作品,既有俳谐的意味,又取得了讽刺的效果。到南朝时,咏物俳谐俗赋达到了创作高潮。《宋书·范晔传》载:“撰《和香方》,其序之曰……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29]1829范晔撰《和香方》讥刺朝士和自嘲。袁淑撰《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常山王九命文》等,假“九锡文”以讥刺禅代。卞彬作《枯鱼赋》《蚤虱赋》《禽兽决录》《虾蟆赋》《蜗虫赋》等,或以自嘲,或指斥贵势。《南齐书·卞彬传》:“彬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其《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30]892-893再如萧综以《钱愚论》嘲讽其叔父萧宏,《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晋时有《钱神论》,豫章王综以宏贪吝,遂为《钱愚论》,其文甚切。”[31]1278等等,不一而足。
荀况赋的影响并未就此止步。如袁淑的作品继续影响着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云:“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32]卷下敦煌遗书中遗存有隋唐至宋的几十篇俗赋,如《燕子赋》《鹘赋》《鹰赋》《酒赋》《月赋》《茶酒论》《祭驴文》等[33]目录。这类赋的源头显然也是荀况赋中的成相杂辞、隐书等,其以叙事为主,运用问答形式,富有诙谐嘲戏意味,一如张衡的《骷髅赋》、曹植《鹞雀赋》等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客主问答,俳谐嘲戏的传统,因而有“俳赋”之称。
总而言之,现存《荀子》乃唐宪宗时人杨倞新编,由其将荀况子书《孙卿子》与别集《荀况集》合编而成。本来单行的荀况赋自此被纳入《荀子》,荀况赋的文学地位和价值亦因此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文体的开创而言,荀况赋即刘勰所谓“命赋之厥初也”,既是汉赋的源头之一,也是俗体赋的源头。就荀况赋的俳谐文化价值而言,在于其传承了《诗三百》“美刺”之讽谕谲谏精神。荀况处于天下纷乱的战国时代,在当时“天下不治”的背景之下,荀况以赋作“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用客主问答的结构形式和“荀结隐语,事述自环”的隐语方式铺排叙写,看似体物状貌,实则借比兴、双关等手法托物言志,即“敷陈其志”作赋以“风刺”,意在主文而谲谏。尽管荀况赋自被杨倞纳入《荀子》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其对后世俳谐文学的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