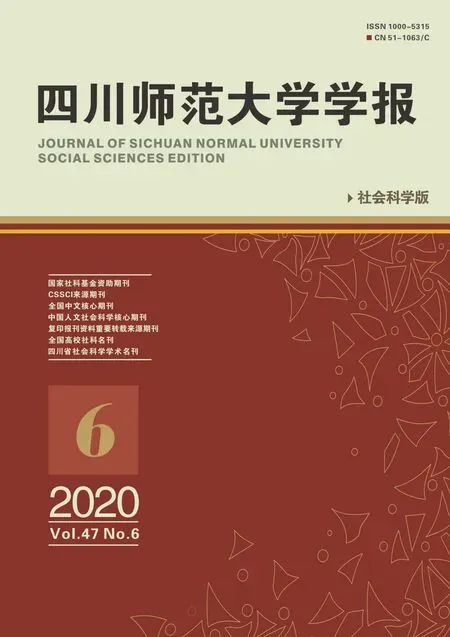学术大同与全球政教
——以廖平《大同学说》为核心的考察
杨世文,陶 亮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一 引言
在两汉以降的传统中国,经学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以《春秋》决狱、《禹贡》治水、《洪范》察变等,自不必说,就连帝王家事也往往需要“通经之儒”来协调、处理。故褚少孙评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1)司马迁《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2页。这一情况延续到晚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通经”能否“致用”,已经成为政学两界的一个疑问。及至20世纪,经典不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常道大法”,而被看成普通史料,甚至还面临被审查、辨伪的命运(2)如周予同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参见:周予同《治经与治史》,《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1卷36期,第358页),胡适宣称“儒教是死了——我现在大概是一个儒教徒了”(胡适《儒教的使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2册《胡适演讲集》卷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二人都否定了经学独立存在的价值。。章太炎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就写到:
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故知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3)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
章氏治经学以古文为宗,主张说经只是为了“存古”,否认经学在数千年之后还能致用,主要针对“季平、长素之侪”(即廖平、康有为)的今文学而发。廖平被章太炎视为追求“通经致用”的典型代表,而美国学者列文森(Levenson)则以不屑的口吻贬抑廖平“一事无成”,批评廖氏“只尚空谈,脱离那个时代的现实”,认为其“所阐释的儒学思想理论内容已脱离了历史”(4)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那么廖平究竟有没有关注社会实际?其思想到底能不能体现“通经致用”?这就成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儒生们逐渐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也被迫进入“全球化”时代,因此,无论是否愿意,学术研究都再也不能对这个新的世界无动于衷。尤其是戊戌之后,国变日亟,廖平敏锐地觉察到,当今“中外开通,共球毕显”,经学必须要面对世界,寻求出路。他认为欲挽救今日之时局,关键不在于学习“西法”,而在于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人才出,方有转机”(5)廖平《皇帝大同学革弊兴利百目》,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3页。。当时社会上“经学无用”论普遍流行,关于是否“废经”的争论亦颇为激烈,但正如廖平在《尊孔篇》中所云:“经不能通,何以致用?”(6)廖平《尊孔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0页。在他看来,经学能够致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有没有真正“通经”。廖平感慨:
大抵吾中国数千年之学术,皆以江河为瀛海,亦如河伯终身未尝至海,不能以支流为天下之大观。(7)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00页。
他在此借《庄子·秋水》所言河海为喻,正所谓“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批评数千年来中国学术的症结就在于知小而不知大,“以小康作大同”,而没有真正明白“孔经宗旨”。在廖平看来,传统音训、义理、典考之学(即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宋学)多流于破碎、空洞、迷惘,故经学反而成为“愚人之具”(8)廖平《群经总义讲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79页。。因此他提出“开士智”的主张,强调:“当今欲言变法自强,首在开士智;欲开士智,必先明圣人大同之宗旨”(9)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1页。。“开士智”即要跳出对孔学的狭隘理解,明白孔子为万世制法的真义,这才谈得上“通经”。而“学术大同”思想的提出,则是廖平追求“通经致用”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知圣续编》等著作中,廖平对“学术大同”思想有所阐发,但真正系统全面论述,则是写成于民国初年的《大同学说》(发表于1913年第8期《中国学报》上)。(10)目前关于廖平大同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刁春辉《廖平学术大同论研究》一文,该文从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经史关系、经子关系、经学与西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包括廖平经学六变的所有思想方面,内容颇为详尽,但“学术大同”在廖氏思想中是一个后起概念,虽在二变中可以看到“今学大同”等字眼,但是否就是该文所言之“学术大同”值得思考。该文着重探讨了廖平学术大同的思想内涵,但在分析学术大同与政教大同的递进关系上较简略,对廖氏学说的反思也略微浅显。参见:刁春辉《廖平学术大同论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该文不仅强调“诸子出于六经”,更直接将子学与西学相联系,从而构建起以“中学”为本位的“学术大同”思想体系,最终落实到以孔经为核心来规划未来世界的“全球政教”。对廖平“大同学说”做一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廖平后期经学之旨趣,亦可为理解近代经学转型提供一个标本。
二 “学术大同”与“全球大统”
“大同”学说主要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然而秦汉之后并不被特别重视。到了近代,由于内因外缘的刺激,学人政客多言大同。从胡礼垣《天人一贯》、谭嗣同《仁学》、康有为《大同书》到孙中山“三民主义”,均体现了传统大同思想在近代的重新诠释(11)关于近代大同思想的研究,可参见:张岂之《“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兼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第14-21、25页;吴义雄《孙中山与近代大同学说的终结》,《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第46-57页;操申斌《对中国近代几种大同思想的评说》,《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第312-314页。。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王汎森论其原因曰:
虽然传统儒家的基本关怀是现实世界,但是其中仍潜存一股乌托邦思想。当社会面临严重危机时,这一类潜流便会浮现,儒家的大同思想在清季流行便是一例。(12)王汎森认为《礼记·礼运》篇是“两千年来不被学界主流突出表彰的文献”,特别是宋明儒者强调“道统”意识,以为“大同”之说出自诸子,非孔门之正宗。参见: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45-246页;陈赟《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船山学刊》2015年第4期,第51-61页。
王先生认为正是由于“紧急的心情与压迫感”,使得传统中国旧经学的领袖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等都发展出了某种乌托邦思想。
其中,康有为的“大同”学说颇具代表性。康氏杂糅儒家大同理想、佛教“平等”教义、西方进化论等而构建了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乌托邦世界”(13)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大同书》之中,参见: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8页。学界对康氏“大同”思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参见: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房德邻《儒家色彩的乌托邦和孔教的启示录——〈大同书〉新论》,《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第77-84页。,他希望破除一切“界域”,最终达至“大同”。但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言,康有为“并不关注维护中国价值或移植西方思想,而是要为全人类界定一种生活方式”(14)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44-345页。,这种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大同”思想反而不自觉地将孔学价值观泯灭了。
与上述诸家之“乌托邦思想”不同的是,廖平从来没有怀疑经学的致用性,仍然坚持“中学本位”的看法,希望以孔学规划世界。不过,在他看来,经学又需要“改良”,以发挥其在新时代的作用(15)廖平著有《经学改良表》,系统提出“经学改良”的主张。参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11-821页。。他提出“大同学说”,即主要基于“改良经学”的初衷。他曾经自言:“戊戌以后,始言‘大同’,乃订《周礼》为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得其所。”(16)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884页。此处“大同”当作“大统”解。廖平早年治经分“今古”,然而戊戌(1898)以后改说“大统、小统”,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关注全球政教与治理的问题。其中的原因,除开他的“今古学”体系本身有无法弥合的矛盾(17)关于廖平今古学的内在矛盾,近年有学者撰文作了反思。参见: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载张岱年等著《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35页;路新生《廖平〈今古学考〉经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问题》,载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68页;郜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册,第33-77页。,招致学界反弹(如章太炎的《今古学辨义》、刘师培的《汉代古文学辨诬》等,皆针对廖平而发),特别是张之洞的警告(张对廖尊《王制》贬《周礼》尤其不满),还与廖平的经学思想从“通经”向“经世”转向有很大的关系。(18)参见:杨世文《至圣前知:廖平的大统世界》,《孔学堂》2018年第4期,第17页。廖平希望以此突破经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以突显孔子“百世可知”,让经学重新焕发出活力,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在廖平“大统、小统”学说中,六经是孔子为后世制定的“治法”,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小统”学说,为治理禹域中国而设;另一类为“大统”学说,为将来治理“全球”而设。孔经之中,《周礼》疆域广大,规划的是未来全球“大统”制法;《王制》疆域制度较《周礼》小,故为中国“小统”制法。如此一来,无论今学、古学诸经不再有真伪优劣之分,皆为孔子垂法万世之作,《周礼》之类原来被判为“新学伪经”的所谓“古文经”,也变成了“精金美玉”。经学通过廖平如此“改良”,实现了“群经大同”,其解释时空可以无限延伸,用他的话来说,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此外,他又将诸子、天学、地理、佛学、楚辞、山经等知识熔于一炉,开辟了一条与当时主流学界不一样的经学道路。
在《大同学说》中,廖平提出“学术大同”,并做了相当详尽的阐发。《大同学说》开宗明义:
大同者何?不同也。化诸不同以为同,是之谓大同。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类有群,自近及远,由小推大,始于同,归结于不同。(19)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5页。
“大同”包含在无数种不同之中。举例来说,自然界之飞鸟、走兽,皆属动物,此为之同;但飞鸟为禽类,走兽为兽类,此为不同。《周易》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都是从“同”的角度而言。因此,廖平指出:“凡人之智慧,世界之进步,皆以尚同为初级。”如人之交际,始于家庭,由家人骨肉之亲(同姓昆弟、异姓甥舅)推至乡党邻里,此为“小同”;再由乡推至邦国、天下,由黄种人推至世界各色人种,其亲疏之等以数十计,然五种肤色都同为人,所以说“不同之中,有大同者在焉”。“尚同”还只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同”正是由“不同”所构成,如以人推至自然界万物(动植物等),皆为天父地母,虽然其形不同,但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之至。(20)参见: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5-796页。
以上论述,显然受到《庄子》相对论的影响。《庄子·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2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160页。但廖平的理论兴趣不在于为《庄子》作注脚,而在于表达他自己对于学术、政治的看法,阐发其孔经哲学思想。他认为,从六艺经传层面来说,经传之所谓“小康、大同”,专就政术而言,“小康”相当于“王伯”之治,为“小统”;“大同”相当于“皇帝”之治,为“大统”。道德行艺的区分在于大小不同,小康大同的区别在于同与不同。大同、小康二者之宗旨,又专在“别同异”。大体在“王伯”小统阶段,已有“民胞物与”之量,但私心未能尽去,故囿于小康。到了“皇帝”大统阶段,贵异而不贵同,能化诸不同以为同,所以为大同。因此,“大同”实际上包含了无数的不同。“同”适用于“小统”,处于“各亲其亲”;而“异”则包含了无数不同,此为“贵异”之“大同”。
“尚同”与“贵异”是“学术大同”的两个阶段,层层递进,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意味。“学术大同”与“全球大统”构成廖平“大同学说”的两个“车轮”(22)魏彩莹指出,廖平的“大统”重点在于以孔子之道来“统”世界,而“大同”则是较纯粹的一种境界,认为先“统”而后“大同”。参见:魏彩莹《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469页。。简言之,“学术大同”侧重于各种学说“化异为同”,而“全球大统”则更偏重于全球“政教一统”。当然,“学术大同”的重点是“纳百家于孔学”,“全球大统”则是要将孔子政教推向世界。只有当孔子之道大行于全球,才有廖平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在廖平看来,实现学术大同的关键就在于“诸子之学”上。他认为子学是沟通中西学术的“媒介”,通过对“文质之辨”的创造性解读,强调道家、墨家皆源于孔学,而墨家尚质,儒家重文;质为西,文为中;道家则专言海外大统之事,孔学通过“老子化胡”的方式影响全球政教,消解了中学、西学之间的鸿沟,从而为进一步将孔经推至海外全球、实现“全球大统”提供了可能。所以,从这个层面说,“学术大同”应该是在“全球大统”之先,通过“化异为同”,将不属于经学的其他学说纳入孔经哲学体系之中。而只有学术达到了“同出于孔门”的状态,方能言世界政教一体。这与廖平先“通经”再“致用”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三 “常道”与“权变”
重新楷定六艺与诸子的关系,统合孔经与诸子,是廖平“大同学说”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子学出自经学,所以诸子与六艺之间能够调和,最终达到“学术大同”的境界。正如他在《三五学会宗旨》一文中所言:“子为六艺支派,故经外于子学特详,所以化诸异为大同。”(23)廖平《三五学会宗旨》,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67页。廖平一生以尊孔尊经为依归,为何会如此重视诸子之学?我们不得不注意他的西学观。他在《治学大纲》中对此做了解释:
泰西艺学,时人诧为新奇者,实在皆统于诸子家。非泰西新事不足以证发古子,非古子何以统括西书?子学为六经之支裔,即为西书之根原。(24)廖平《治学大纲》,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630页。
廖氏此语有着清晰的逻辑顺序,他认为“子出于经”,而“西学出于子学”,故“经学为西学之源”,以此来论证经学“百世可知”。可见廖平“大同学说”的落脚点不仅仅在“子学出于经学”(25)东汉班固即有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之说,参见: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但随着经学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宋儒提倡“道统”,将诸子排斥于六经之外。直至清初,傅山等逐渐重新思考诸子之学的地位与意义,但此时诸子学只是经学的附属品。到了晚清,子学地位一举超过经学,出现了“婢作夫人”的现象。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更想突出“非子学无以发明经学”的观点,这就超越了历史上“诸子出于六经”的传统看法了。廖平想通过更进一步抬高子学地位,达到经学与西学贯通无碍、互相比附的目的。
对于“子学即为西书之根原”的论断,廖平反复加以论说。以“地球”为例,近代海外开通之后,世人皆知大地为球形,并有五大洲四大洋,这是西洋传入的地理学知识。但廖平却从中国古典中找到了“证据”,认为早在战国时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与西人“地球”之说若合符节,而究其根源,邹衍之说源自孔学,只是前人没有发现(26)参见:廖平《书〈出使四国日记〉论大九州后》,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7页。。由此推衍,西人的地理知识早已为孔学所包,并不新奇。廖平就是用这种方式论证西学源于子学(27)廖平学说,参见:黄镕撰《经传九州通解》,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4册,第590页。关于邹衍之说,可参见:司马迁《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附传,第2344页。。然而,仅仅靠简单的推理附会,而没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和周密的逻辑论证,恐怕很难让人信服。那么,廖平为何要这样做呢?其实,正如邓实《古学复兴论》一文所云:
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一则我国自汉以来,以儒教定一尊,传之千余年,一旦而一新种族挟一新宗教以入吾国……于是而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28)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社说”第3页。
在清末,特别是庚子国变以后,引进西学已成为国人共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中学无用的鄙弃”,因此为了证明中学有用,“最省力的办法自然是说西学中有的也可以在中学里找到”(29)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05页。。这是当时“西学中源”论兴起的重要背景。廖平作为一个坚定的“文化自信”论者,自然从诸子学的复兴中看到了重现孔学价值的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晚清政学两界多有主张以宋学济汉学,汉宋兼采,出现宋学复兴之势。然而,廖平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无论是“东南谈时务者”所倡言之“新学”,还是“主持大教”者所推举之“宋学”,都没有找对医治当时社会各种弊端的药方。在廖平看来,宋元以来儒者提倡理学,侈言道统,贬低诸子学说,导致“人才日以困坠,举天下聪明材智群消耗于空疏谫陋之一途,于宗社之危亡漫不加察”(30)廖平《家学树坊》,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3册,第1261页。。时局的危机,归根结底在于学术的败坏。由于学术误入歧途,人人都成了自私自利的“乡愿”,导致国家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廖平精通医道,他以中医做了一番较为形象的比喻。中药材分上、中、下品以及无毒与有毒,以此满足病者的需要。如果治疗常见之病,“中正和平之方”足以见效。但如果遇到疑难杂症,要想“起死回生”,则非毒药不能见效。因病立方,君臣佐使,轻重生熟,丝毫不可苟且。他认为中医用药的道理,与学术相通。孔经六艺作为“常道”,正如五谷、六畜一样,属于“人所常食”的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诸子之学即如中药里的硝黄桂附,虽有毒性,却可以救急。(31)参见:廖平《大同学说》,见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7页。另外,廖平撰写的《诸子凡例》提要,也有类似表述。参见:廖平《井研艺文志·诸子凡例二卷》,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6册,第1263-1264页。就平时而言,六经对于生存已经足用;不幸而有疾病,还必须使用药物治疗。尤其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医者更要善用有毒性的药物来救亡图存。如治疗元阳虚脱、危在顷刻者,就要用“四物回阳饮”;救阴泻热,要用“承气汤”。六艺与诸子,“一常一变,一经一权”(32)如公羊家以“经”为常道,“权”则“舍死亡无所设”,作用在于“补弊救偏”。关于儒家“公羊学”中的经权之说,可参见:林义正《公羊春秋九讲》,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因此“天地之间,不能专言饮食而屏绝药物,一定之势也”(33)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8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廖平眼里,儒家的地位不如道家。他在《庄子经说叙意》中专门列有“砭儒”一章,认为庄子所砭之儒为“伪儒”,“伪儒不祛,真孔不明”,故“砭儒愈以尊孔”(34)廖平《庄子经说叙意》,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第301页。。究其原因,儒家局限于“王伯”小统,不知“皇帝”大统,专言小康,又贵王贱伯,以为“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35)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124页。。事实上,孔子并不排斥五伯,《论语》盛推管仲之功,《春秋》专言桓、文之事;后世儒者对于不合一己宗旨之说,都加以屏绝,这种“褊狭私心”,有悖于孔学真义。如果流为学术,喜同恶异,“于族类则中外之界最严,于学术则人我之见尤甚”,妄分种族,将中西学术截然对立,滋长盲目排外,必为国家大害,以至于发生“毀教堂,甚至有拳匪之事”。在廖平看来,中国变法维新久不能进步,“其无形之现象,实在于此”(36)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1页。,就是说后世“伪儒”要对此负责。
在贬抑儒家的同时,廖平给予道家以特殊的地位。由于道家“兼包天人”,不局限于中国一隅,所以在大统、小统学说中,道家的地位最为重要,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家还在其次。儒家治中国,道家则治全球。廖平在《庄子新解》中指出:
各经异义,实皆同出至圣。此篇(案:指《天下》篇)所列六家,皆道家支派。墨家专名,惠施、公孙龙后为名家,乃道之支派;法、农、申、韩、苏、张皆所不及,谓专详道家可也。(37)廖平《庄子新解》,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第319-320页。
廖平以“九流”皆出于孔门“四科”:道家出于德行科,儒家出自文学科。“四科”之中,显然德行科要高于文学科。他通过将道家收归孔门,归根结底是为了突显孔子的至圣地位。
对于墨家的看法,则更能体现出廖平对于“学术”与“政教”关系的见解。他认为墨家专言“夏礼”,属“孔子尚质一派”,而儒家则“从周而属文”。廖平举礼制以论墨家为西方之法,并结合时局云:
中外交通,为古今一大变局,墨家居简行简,质胜文则野,儒家一于主文,未免文胜之弊。(38)廖平《墨家道家均孔学派别论》,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517页。
就中国与西方而言,中国重儒家,未免“文胜于质”;西方主墨家,则未免“质胜于文”,各有利弊,故而需要“补偏救弊”,中国与西方需要互相学习。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廖平提出“改文从质”说(39)参见:廖平《改文从质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522-526页。,主张应当有限度地学习西方。廖平将六经与诸子以“经”与“权”的方式整合在一起,通过文质互补、经权迭用,希望以此来最大程度地扩大孔经的适用范围,发挥孔学在新时代的效用,突显经学的价值,消解西学的冲击与挑战,以维护经学的神圣性。
四 孔学、诸子与政教秩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廖平严格辨析了孔子与儒家、孔学与儒学。在他眼里,孔子为“至圣”,不能与儒家等量齐观,孔学为全体大道,兼包诸子百家。后世所谓“儒学”,只是孔子之后的儒家之学,无论是宗法汉学的考据学,还是宗法宋学的帖括八比之学,皆号称儒学,实乃“中正和平之术”。面对当今的内忧外患,实不足以救危亡,必须要以诸子之学来补偏救弊:“非诸子之学极光明,不能有真人才。”(40)廖平《孔经哲学发微》,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3册,第1065页。他批评当今之言学术、言政治者,“不讲医理,不审病势,深恶诸子,以为非圣人大中至正之道,流弊甚大,不可常服”。名公巨卿、老师宿儒多抱庸医所谓“中正和平之方术”,“日以败坏我国家,堵塞我聪明”,却自以为尊崇的是“内圣外王之学”,以至于外人轻视孔学,误以为“孔子之道”不过如此。更有甚者,“抱残守缺”的腐儒拒绝改弦更张,却天天想着为学术、政治“防流弊”,这是没有找到解决政治和学术问题的症结所在。廖平追问:
试问今日之政治学术,其归根究竟何如乎?盖知流弊之害,而不知防流弊之害,且十倍千万于所谓流弊也。(41)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8页。
“防流弊”一语,屡见于晚清诸人的奏疏、著作之中,廖平此处则专门针对时人排斥诸子之学而言。(42)廖平驳斥时人“防流弊”之说,似有针对张之洞的意图。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有《宗经》一篇,专门针对公羊学与诸子学的“流弊”而发,提出了全面的“防弊”主张。虽然廖平没有明言,但对比张之洞“防流弊”的论述与廖平的反驳,不难看出其中的联系。参见: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19-9721页。他强调中华学术的主体性,认为不能丢弃“祖学”固有的资源不用,却向西方寻找解决危机之方。在廖平看来,只谈诸子学的流弊,而不讲西学的流弊,是不恰当的,“所谓西政西学,其弊或且十百倍于我中国之诸子”。诸子学既然在孔学的范围之内,故可以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如果学术不思变通,那么“防流弊”的危害远大于“流弊”的危害。因此,面对“天下交通,中外一家”的现实,有必要“标明大同至公”,以“镕化小康自私之鄙吝”,才能“存国粹,强国势,转败为功,因祸为福”(43)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9页。,不能死抱着“防流弊”之偏见而拒绝改弦更张。
有别于上述所谓“抱残守缺”的“腐儒”,廖平认为天下没有无弊的政治学。他引《礼记·经解》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4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3页。六经虽为圣人之书,后人不善学者尚且有流弊。对于诸子之学,也应善学其长,避免其短。“良医以毒药奏奇功,庸医以常药酿杀运”,同样的道理,“良相用诸子而得平安,愚者因六经而致败亡”,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故而廖平声言:
药无论有毒无毒,在医者之善用;学无论诸子六经,在读者之善学。欲求世界大同,必先于学术中变大同,以六经为主,以九流为之辅,此吾中国学术之大同也。能化诸不同以为同,推之治法,乃有大同之效。(45)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799页。
“世界大同”的前提是“学术大同”。六艺、诸子同源共贯,如诸子百家同出于孔门,“庄、老之书,祖述帝道,与《礼运》大同相合”(46)廖平《〈百年一觉〉书后》,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0册,第121页。。将来世界大同,必然以学术大同为先导。学术大同之后,再推之于治法,才能“化不同为大同”,以孔学为根基重建全球政教。
当然,“化不同为大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则在于“开士智”,以“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思想”(47)廖平《群经总义讲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2册,第779页。。廖平强调读书人要解放思想,尤其要有全球眼光,善于运用孔经固有之义去解答全球和整个人类的问题,而不必盲目排外,将中学与西学截然对立。这些观点从廖平这样的经师笔下流出,颇耐人寻味。他为何主张要以“西学印证孔经”,强调“大同”,摈斥“小康”?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即自鸦片战争过后,面对“不带情感”的西学的冲击,中国知识阶层逐渐从传统“学派”之争的“内忧”转而直面西学冲击的“外患”,通过包容兼摄,寻求学术转型,以保持“祖学”的一席之地不被侵蚀。列文森分析说:
到了19世纪,尽管古典仍是价值的标准,然而西方的入侵促使中国人对过去各家学派之争论的评判发生了变化。与使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比较,中国各思想派别之间的小分歧和小冲突已变得无足轻重……西方的冲击使中国各派思想实现了联合,当西方成为一个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时,中国各派思想则紧密地团结了起来。(48)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40页。
事实上,当晚清学人发现被整合过的中学还是不能抵挡西学的冲击时,不仅不把西学当作“对手”,他们反过来以孔经含容西学。廖平便倡言“海内外政治学术,皆我分内所当考究”,希望以孔学统理全球政教。然而,他也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的情况:当前世界诸国林立,纷争不断,无所统一,正是所谓“乱世”。连小康一统尚属未能,至于大同则更属遥远,显然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张力。处此乱局之中,经学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廖平提出了“开士智”的主张。即学者要对世界做出贡献,就应当切合机宜,努力发掘孔经中的制度资源,为重建全球政教提供依据。过去地球未开,儒者囿于见闻,不知孔子“大统”之义,所以“儒家旧说,专详中国之一隅”。方今“中外开通,共球毕显”,孔子的大统制法一一得到印证。儒者就应当“由《王制》以推《周礼》,由中国以推外国”。大统、小统,一帝一王,大、小本属龃龉,然而三千里小统(中国),未尝不可为三万里大统(全球)之缩影?《王制》《周礼》大小虽殊,而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则“叠矩重规,初无二致,验小推大,不过扩充,固无所难”。简言之,通过“开士智”,尊经知圣,为将来的“大同”世界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就经典而言,当时世界万国并立,列强侵凌,适合用孔经《春秋》来治理。春秋时代由分而合,同样道理,地球五洲将来必至一统。只是孔子当时处于割据时代,不能不“因时立法”。《春秋》三传之中,《公羊》《穀梁》详于经例,至于邦交、政事,不如《左传》之详明,故尤以《左传》为切要。
其实,晚清学人主张利用《春秋》制法的不在少数,发掘了《春秋》(以《公羊》为主)的经世功能。改良派利用《春秋》宣传维新变法,革命派则利用《春秋》鼓吹革命。通过新的阐发,使经学“可以再次获得新的生命,以重建中国的国家秩序与政教体系”(49)陈壁生《晚清的经学革命——以康有为〈春秋〉学为例》,《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第35页。。虽然廖平也十分重视《春秋》大义,但他的做法与上述经学家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将时事与《春秋》进行比较,即可以发现,无论以往的历史,还是未来的方向,都不能超出经典的范围,“凡今日诸国所已行之陈事,即将来成败得失之归宿,皆可于经传中得其指归”(50)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3页。。他的这一观点,颇有历史目的论的意味。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在孔经规划之中,学者的任务即应当结合世局,以《王制》为基础,详考世界诸国的内政外交以及泰西历史与政治各书来证明经传旧事,“以今证古,以中统外”,制定“万国公法”,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
综而言之,廖平将“学术大同”推至“全球政教”,希望构建一个以《春秋》《尚书》为切用、《王制》《周礼》为制度基础,同时囊括诸子百家之学的学术大同体系,打通中学西学,给孔经注入新的生命,重建中国乃至世界政教秩序,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球大一统(大同)。在廖平的规划中,未来全球其所行政教,则是行于中国之孔子政教的放大版。当然,他所谓的“孔子政教”,已经整合了六经与诸子、中学与西学。在他眼里,中国古时南北之分,实即今日中西之界,后来者之视今也如今之视昔,验小推大,“世界大同,固可由中国之小同而决之者”。(51)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4页。
五 余论
近代以降,原来作为帝国政教根基的儒家经学黯然失色,甚至成为时代的“靶子”,成为被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在传统断裂之后,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经学究竟还能不能发挥其致用性?经学能否为中国甚至全球面临的困境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戊戌之后,廖平放弃了“今古学”,而主要致力于寻求孔经如何发挥其应有的致用功能。他撰写了大量的论著,倡导“经学改良”,不厌其烦地论证孔经、孔学不仅具有现实的价值,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六合之内)和整个宇宙(六合之外),可以放之四海、放之未来。他通过阐发“大同学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个性鲜明的“学术大同”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以经学统领诸子百家,山经楚辞、佛道医数乃至西学西理等古今中外一切学问都是构成“学术大同”的质料。他结合时局突显《春秋》的致用性,试图“通过重建经典与历史的关联,来勾通价值与存在”(52)李长春《廖平经学与中国哲学》,《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第121页。,利用“学术大同”来规划“全球政教”,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孔经媒介重新展现出来。
在晚清民初学界普遍“佞西”“趋新”的背景下,廖平的努力难免不受待见(如冯友兰指为“旧瓶”破裂之象、钱穆斥为“秋风候鸟”、胡适目之为“术士”)。其实,在那个时候,类似廖平这样学者还有一些,他们既不愿意放弃“旧学”,又试图从“旧学”中发现“新学”,通过或多或少的改变,使西学与中学、旧学与新学能够贯通无碍。如与廖平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康有为,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如《孟子微》《论语注》等),试图革新儒学、建立孔教,然而,由于他对经典文献阐释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反而影响到孔经的“神圣地位”,对经学造成负面的冲击。而被誉为“朴学殿军”的孙诒让,虽专注于《周礼》研究,亦不忘经世,著《周礼政要》,以西方政治制度比附《周礼》经制,发掘其中的制度资源,这也不失为另一条儒学革新的路径。就廖平而言,他通过整合经学、诸子和古今中外学术,建立“孔经哲学”思想体系,通过“化异为同”,期至“大同”,这是他针对近代学术乱象和时局而开出的另一付药方。以上三人,代表了“经学改良”的三条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正如论者所言,实乃近代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经学变形记”(53)参见:叶纯芳《经学变形记》,乔秀岩、叶纯芳著,陈美延编《学术史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09-445页。。面对经学自身的困境与西风的冲击,传统经学不得不“学随世变”,寻求出路。因此,容纳诸子百家与西学,乃成为近代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陈寅恪先生有言:“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5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在经学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已经崩坏的现实困境中,无论是古文经学家,还是今文经学家,都将“逃无可逃”,不得不寻求出路。因此,利用旧有资源,通过学术重构,关注甚至干预社会现实,希图给“旧学”重新注入活力,重显经学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康有为、孙诒让,还是廖平,都重视孔经中的制度资源。如果略加比较,则不难发现,康氏虽然披上经学的外衣,其所论制度基本上是西洋货;而廖平所论,则更具有传统经学意味。
就廖平“学术大同”思想体系来说,其前提在于“知圣”,即重新阐发孔经中的“微言大义”。他一方面抉发孔经中的“大统”学说,强调孔子早已制定了“全球治法”,为未来世界政教做了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从诸子学中寻求自强御侮、交邻化外的救世之方。他希望达到“新而不至叛归摩西,旧而不至堕落禅寂”的状态,有效地化解“新旧”与“中西”之争。廖平倡言“以大同为精神,以小康为实用”(55)所谓“精神”,即属于理想目标;所谓“实用”,即解决现实问题。参见:廖平《大同学说》,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803页。,其最终归宿则是“凡我孔教诸子,更当昌明圣教,放诸四海,以企同文同轨,致太平大一统之盛焉,是在吾党”(56)廖平《阙里大会大成节讲义》,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470页。。他坚信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同文同轨”的“太平大一统”(大同),全球政教应以孔经为准绳,孔经不仅为当下中国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且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
应该看到,廖平的经学著作中虽然不乏“精金美玉”,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廖氏解经未免“师心自用”,甚至牵强过甚,予人口实。其早年的“今古学”暂且不论,“三变”之后,其论说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传统解经的“轨范”,主观性和随意性触目皆见。当然,我们可以用“思想”与“学问”之不同来为其辩护,思想可以天马行空、无所拘束,学问则必须征实有据、不越雷池。但也需要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对孔经可信度与神圣性难免产生“不自觉破坏”,可能与“尊孔尊经”的初衷相背离。至于其学说之致命缺陷,正如论者所言,“在其根本假定”(57)李耀仙《廖平与近代经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廖平的所有论述,均是在承认孔子为“至圣前知”“百世可知”的前提下展开的。他所提倡的“学术大同”,实质就是将孔子早已经发明的经义,作为儒学与诸子、中学与西学的共同源头,以此论证“尊孔尊经”的实际价值,具有浓厚的“历史目的论”色彩。从理性角度来说,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不过,在批评廖平的论思方法、质疑其学说是否真的可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放弃偏见,走进其思想世界,对其加以“同情之理解”,直面廖平在近代“中西古今”之争的困局中试图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至少,在“音调未定”的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廖平所做的探索并非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