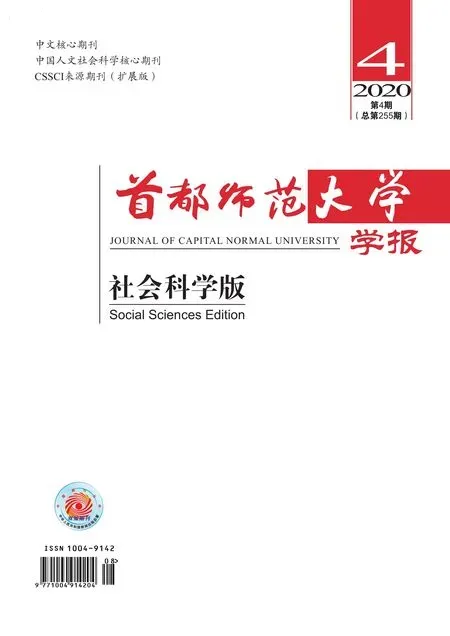中西文论对话中的身份重构与话语转型
——希利斯·米勒中国行的意义
曾 军
一、An Innocent Abroad:从“本土信息员”到中国同行的“耶鲁激进分子”
希利斯·米勒是美国解构主义批评“耶鲁四人帮”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尽管希利斯·米勒1988年才访问中国,但是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学术成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受到了中国关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8期和1966年第4期先后刊登了周煦良的《关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狄更司的一些新著》和《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前文介绍了希利斯·米勒的《狄更司小说的世界》,后文则将希利斯·米勒视为“重要的批评家”,认为“他的和新批评派的批评一样,都是非历史性的,但是他并不为某些特殊价值判断辩护,而去分析作为现实的一种特殊投影的作品”。①周煦良:《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6年第4期。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介绍希利斯·米勒的是张隆溪。他在《读书》1983年第12期的《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中介绍希利斯·米勒为“耶鲁学派”重要成员之一。王逢振的《“耶鲁四人帮”之一:希利斯·米勒》(《外国文学》1987年第11期)则是第一篇单独介绍米勒学术思想的文章。②这篇文章也被收录进王逢振编著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标题为“耶鲁‘激进分子’:希利斯·米勒”。因此,中国学者对希利斯·米勒的早期印象是既有别于新批评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致力于解构批评的激进批评家形象。
正是带着这种“‘耶鲁’激进分子”形象,希利斯·米勒开启了他的中国之行。从1988到2012年期间,希利斯·米勒先后在中国做了近三十场讲座,部分讲座发言稿经整理以《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首先是以“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为名于2015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③《萌在他乡》一书的创意来自米勒在加州大学的同事理查德·特迪曼的建议,他还为本书撰写了“编者的话”。《萌在他乡》一书的编者理查德·特迪曼认为,将中国演讲集命名为“An Innocent Abroad”体现了希利斯·米勒特有的幽默,这是他从马克·吐温那里学到的略带解嘲的狡黠④理查德·特迪曼:“编者的话”,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一方面,这个题目取自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可以直译为“傻子在国外”或者“无知的人在国外”;但另一方面,“abroad”这个词一语双关,“这个词既可以指‘在外国’,又可以理解为‘没有命中靶心、误入歧途、错误的’”⑤希利斯·米勒:“引言”,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因为他既不懂汉语,也谈不上中国通,因此他在此使用的就是第二种含义。希利斯·米勒的这种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对中国文化不熟悉的状态在西方学者中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不过,希利斯·米勒并没有将这种“无知”发展为“偏见”,而是从一开始就认真地观察中国、真诚地与中国学者交流。在希利斯·米勒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结识了大量的中国学者,其中不乏交往甚密者。如他在《萌在他乡》的“致谢”中点名表扬的中国同行:王逢振、申丹、王宁、金惠敏、夏艳华、秦旭、陶家俊、陈爱敏、宁一中、生安锋、盛宁、陆小红、李元、李作霖、陈永国、张一凡、黄德先、宫璇、丁夏林、顾明栋、谢少波、王月、易晓明、国荣、郭艳娟,等等。上述这些中国学者的名字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是希利斯·米勒“1988年之后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希利斯·米勒:“致谢”,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他们或是赴美访学时与米勒相识的,如王逢振;或是米勒来华讲学时相遇的,如申丹;还有邀请他做讲座、对他进行学术访谈、提供客座教授的机会以及翻译他的文章、撰写研究他的论文的;或是在米勒资助下赴美做访问学者的,等等。希利斯·米勒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鸣(如围绕“文学死了”的讨论)。
希利斯·米勒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频繁被邀请来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学者迫切地想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前沿情况。因此,希利斯·米勒自觉地扮演了“本土信息员”的角色。但同时,因为面对的是中国听众,他必须传递中国听众感兴趣的信息,回应中国学者感兴趣的话题。这就使得希利斯·米勒的中国演讲必须适应中国这一特殊语境。正如理查德·特迪曼所说:“就像那个时段出现在中国的其他西方学者一样,米勒也必须在自己的演讲中,小心翼翼地调试着他所要讲的内容与中国听众所熟悉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距离。”⑦理查德·特迪曼:“编者的话”,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希利斯·米勒确实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演讲策略——尽可能挑选中国听众可能比较熟悉的西方作家和文学作品作为例子,尽可能以相对清晰(同时也意味着不得已的简化)的方式介绍西方文学批评、文化理论研究面上的一些情况。虽然希利斯·米勒出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针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基于“文本细读”的解构式批评,但是为了满足中国听众的期待,他的中国演讲题目大多都是围绕“全球化”“电信时代”“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文学理论的未来”之类的宏大主题。这种包含着主动/被动的“迎合/调整”所形成的学术思想上的错位和张力,也成为促使希利斯·米勒反思自己的学术思想、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希利斯·米勒中国行作为一个中西文论学者学术交往的典型个案,能够有助于我们来透视这种学术交往对中西文论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希利斯·米勒对西方文论前沿问题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这也是他非常看重的方面。希利斯·米勒曾言:“他们告诉我,一篇论文或某书的一个章节,例如我的著述之一,有时可能会给一位教师或学者的事业进程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我几乎不敢奢望这是我在中国的情形,不过我仍然梦想我的著作在中国的阅读,对人们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谓的‘文学’、什么是我们所称的‘理论’,可能有时能发生某种作用。”①希利斯·米勒:“引言”,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理查德·特迪曼也认为:“对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些来自远方的创新,甚至可以更加惊心动魄,因为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上盛产实证性的研究,意识形态往往决定了文本的解读。西方学术界带到中国的这些新观点显然已经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②理查德·特迪曼:“编者的话”,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另一方面,希利斯·米勒对中国的观察和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也在改变其学术思想。正如理查德·特迪曼所说:“事情总有转折点,也确实会变”,“随着他对中国的理解不断加深,尤其是他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了解,他的演讲内容也逐步深化,他对历史、地域和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理解也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③理查德·特迪曼:“编者的话”,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希利斯·米勒自己也认为:通过这么多年对中国的访问和与中国同行的对话,“可以展示出我这些年的思想变化以及中国这个语境的变化轨迹,因为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④希利斯·米勒:“致谢”,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从“本土信息员”到“促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或者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同事”,这是希利斯·米勒对自己与中国交往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概括。希利斯·米勒与中国同行的对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让我们更好地思考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大的问题意识之下,如何通过中西双方学者的学术交往,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深化认识、转变态度、促进共识。
纵观希利斯·米勒的来华演讲、著述的译介及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其中国影响主要集中在解构批评、叙事学以及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文学危机三个方面。与此同时,希利斯·米勒也在不断加深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批评策略。所有这些都与希利斯·米勒的中国行及其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往密不可分。
二、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中西文论对话
颇为吊诡的问题是,希利斯·米勒作为一个有着新批评传统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一生所致力于的正是通过强调对文本的细读而彰显学术能力;而他在中国真正引起学界关注(或者说中国学界对他的学术期待)的,却是他在自己学术研究中努力回避的对文学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外部因素的直接关注,尤其是还要他以启示录的方式做出陷入危机中的文学“不死”的预言。在希利斯·米勒的三十篇来华演讲中,有十篇直接与“全球化”问题相关,再加上以“电讯时代”作为问题意识来讨论文学问题的演讲,已经有近三分之二的演讲与“全球化和电讯时代”为主要议题。①如1994年12月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大学所做的“大学人文研究的全球一体化倾向”(陈冬梅译,《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1997年4月在北京大学所做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对影响”(王逢振编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2000年7月在北京语言大学所做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2001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2003年9月在清华大学所做的“土著与数码冲浪者”、2004年6月在郑州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做的“物质利益:现代英国文学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张一凡、郭英剑编译:《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2006年6月在武汉大学所做的“谁害怕全球化?”2008年8月在清华大学所做的“全球化与新的电信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地位”、2010年8月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2012年在北京语言大学所做的“媒介从来都不曾分开过: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抑或说,文学研究的数字化变革”,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关注希利斯·米勒的中国行是如何展开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中西对话的。
与这问题密切相关的重大学术事件,应该要数发生在21世纪之初的“文学终结论”的讨论了。2000年,希利斯·米勒在北京语言大学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演讲,引发中国学者的激烈争论。②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的演讲引发中国学者热议,先后有童庆炳、余虹、金惠敏、陆扬、骆冬青、赖大仁、钱竞、刑建昌、李衍柱等数十位中国学者参与讨论。不过,严格意义上说,这场讨论没有真正在希利斯·米勒和中国学者之间展开。虽然希利斯·米勒以私下的方式与中国学者就此话题有过一些交流和沟通,但他并没有在正式的公开场合直接介入中国学者之间的“文学终结论”讨论。③希利斯·米勒对中国学界的“文学终结论”问题所做的唯一回应是在2004年6月参加“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期间,接受《文艺报》记者的采访。希利斯·米勒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种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它“是一种混和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和批评的理论”,未来的文学研究,与其说是“文学”(literature)研究,不如说是“文学性”(literarity)研究。参见希利斯·米勒、周玉宁:《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真正与希利斯·米勒展开以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文学研究为议题的中西对话的,要属王逢振、谢少波、金惠敏等。
《土著与数码冲浪者》同时出现在希利斯·米勒的两本中国演讲录中,其中一本还以之作为书名。显示无论是希利斯·米勒,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这篇文章具有代表性。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ARIEL(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杂志的 2003年 1月的专刊《全球化与本土文化》(globalization and Idigenous Cultures)上。这期专刊的组织策划者就是王逢振和谢少波。在这期专刊上,依次发表的是阿里夫·德里克、希利斯·米勒、罗布·威尔逊、布鲁斯·洛宾斯、王丽亚和陈永国撰写的文章,突显的正是中美学者之间围绕“全球化和本土文化”问题的对话。④与此同时,谢少波、王逢振还对希利斯·米勒做了一个书面访谈。访谈稿以“对雄辩有力的问题进行的有限答复”为题收录在《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逢振和谢少波认为:1.文化全球化是与信息技术的变革密不可分的,是新兴的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合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文化是组织资本和传播欲望产品的社会空间”。因此,资本必定以各种方式无所不在地通过媒介技术渗透到社会空间之中。资本与媒介的双重影响的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各种跨国公司的兴起。“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文化本身也成为跨国化的,因此成为一种全球文化”。2.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化,或者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US-centered global capitalism)。尽管全球化高举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帜,倡导文化多样性理念,但毋庸置疑的是,最具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的是来自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因此,全球化与美国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来说非常纠结的情感结构: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倡导的平等、多元的理念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另一方面,其美国中心、美国主导的美国化倾向又使得第三世界民族国家面临本土文化被打压和侵蚀的后果。因此,对于王逢振和谢少波来说,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拥抱的趋势,相反应该高度警惕美国化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看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正在殖民处于无意识和前意识状态的第三世界,正在按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正在将更多的土地占有为全球帝国的领土,将人民转化为奴仆、把事物转化为商品”。3.虽然王逢振和谢少波详细区分了“indigenous” “indigenes” “indigenization” 和“indigenism”,注意到了“本土”“本土化”“本土性”与“地方主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差异,但是他们的论述仍然主要建立在“全球化/本土化”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并且预设了全球化冲击之下,本土文化受到削弱的负面影响。⑤Wang Fengzhen and Shaobo Xie,“Introductory Notes:Dialogue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digenous Cultures,”ARIEL: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vol.34,no.1(2003).
针对王逢振和谢少波提出的“全球化与本土文化”这个议题,希利斯·米勒一方面对他们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和西方大众文化的破坏性后果”观点都表示同意;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需要“加上目前在美国政府发生的可怕的变化,即把全球资本主义和西方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直接演变成全球军事占领。这就意味着,把美国的公民社会演变成了永久的‘紧急状态’,永久的‘特殊状态’,永久的‘战争状态’。与之相伴的则是尚未解除和不可能解除的恐怖状态,正是这种恐怖状态为剥夺公民的自由和宪法权利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在希利斯·米勒看来,全球化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或者说已经成为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事实。虽然王逢振和谢少波描绘了一幅处处面临资本、权力和美国化支配的全球化图景,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一负面效应。希利斯·米勒认为“事情比王和谢所描述的还要糟糕”: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濒临发展的极限,“在过去,帝国主义的口号是:‘贸易跟着国旗走’”,而“按照现在的情况,把口号改为‘国旗跟着贸易走’,也许更为恰当”。美国正在凭借其主导性地位扭曲双边合作机制。米勒非常敏锐地指出:“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流氓国家。”与此相反,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①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200页。。他甚至非常直截了当地说:“一言以蔽之,在过去十五年中,中国和美国是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崛起,而美国在衰落。”②希利斯·米勒:“引言”,参见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因此,我们必须对全球资本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次,希利斯·米勒也非常尖锐地指出:尽管王逢振和谢少波采取了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警惕姿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王和谢所用的话语系统(discourse)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文化产品”,因此,他们自己也面临着理论思维的西方化、美国化、殖民化的困境。他们的批判表面上看是来自第三世界文化主体的外在性批判,实质上却成为第一世界主导的学术思想的内在性反思。再次,希利斯·米勒也对王逢振、谢少波“建立在土著(indigene)与我所说的数码冲浪者(cybersurfer)之间的二元对立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批评。希利斯·米勒认为,王逢振和谢少波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绝对吻合的,认为“我们是我们周围的文化的产物。当全球文化侵入一个地区时,那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渐成为数码冲浪者,而不再是土著”,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希利斯·米勒用南希的“社区”观点解构了王逢振和谢少波所提出的“土著社区”中的“社区”概念,认为“居住在所谓的土著文化的独特环境里,也就是说,没有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一种当地的生活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与其生活在全球同质化的文化中,还不如生活在这些相互独立的他者当中。全球同质文化正在迅速传遍整个人类”③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200页。。
如果说希利斯·米勒与王逢振和谢少波之间围绕“全球化与本土文化”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还主要聚焦于对全球化陷阱及其所产生的原因的分析的话,那么,希利斯·米勒与金惠敏之间围绕“全球对话主义”的讨论则落脚到破解之道的问题上。
针对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问题,金惠敏明确提出“全球对话主义”和“价值星丛”的主张,试图在保持全球化主导趋势的前提下,努力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弊端。在他看来,“全球化不仅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对象,……而且也必须成为我们考察一所由以出发的一个视点”,“文化研究已经自觉地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但是这并不必然地说,文化研究就已经取得了正确的‘全球意识’”。他以“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讨论作为对象,试图区分出“‘现代性’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进而认为“全球化内在地同时就是现代性的与后现代性的,即是说,它同时即超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因而可成一新的哲学概念”。金惠敏提出“全球对话主义”作为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解决方案,强调“作为‘他者’的对话参与者”,这一“他者”不是“绝对的他者”,而是“他者间性”之进入“主体间性”的过程。①金惠敏:《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该文的英文版为“Towards Global Dialogism:Transcending‘Cultural Imperialism’and it′s Critics”(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September 2016)。在另一篇文章《价值星丛: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理论出路》中,金惠敏提出:“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强调“坚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拒斥、抵抗西方的文化和文化霸权”。这种思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面临着自我定位为弱势、边缘、另类的位置,进而“阻碍其参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因此,金惠敏提出“价值星丛”的理论,主张“将各种价值符号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动态的对话”,进而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现。②金惠敏:《价值星丛——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理论出路》,《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该文的英文版为“The Constellation of Values:A Possible Path out of the Impasse of China-West Opposition”(Dialogue&difference,May 2015)。无论是“全球对话主义”还是“价值星丛”,都体现出金惠敏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寻求多元并存、平等交往的文化理想。
希利斯·米勒应邀对此做出回应,认为金惠敏的目标其实是“挑战中西方主流话语都在强调的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之间的完全对立”,“简而言之,他支持用一种包含多种变化的‘两者都’的模式取代‘非此即彼’的模式”。与此同时,希利斯·米勒也对金惠敏的不足做了分析,比如说他认为“金惠敏所举的例子在2015年看来似乎有些过时,尽管这些例子来自很多早期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运行方式的最好的学术调查”。他认为深刻影响中西方关系的是新媒介,并认为“数字革命几乎改变了一切”。针对金惠敏的“价值星丛”理论,希利斯·米勒指出:“提出‘价值星丛’这一概念的背景是当前中国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而金惠敏所主张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民族主义,即“用灵活的‘两者都’的思想代替僵硬的对立,可以避免徒劳无益的中西对立模式”③希利斯·米勒:《对全球对话主义和价值星丛的对话性回应》,《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4期。。
应该说,希利斯·米勒思考全球化问题时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同第三世界国家立场所批判的全球化中美国化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感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无可挽回地步入衰落通道的现实。这种复杂的全球化情感叠加上对电讯时代新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催生了米勒在21世纪到来前后“千禧年”的文学忧思。希利斯·米勒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探讨电讯时代的文学问题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也自然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其中。“新的通讯技术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影响文学研究的主要因素,当然,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包括在内”④希利斯·米勒:《中美文学研究之比较》,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不过,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最大的差异在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是不同的,其背后所支撑的文学观念也不同的。因此,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文学危机是多重的:首先,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危机,即新媒体所侧重的影视网络等新兴的视觉艺术和娱乐方式对传统的纸质文学阅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分区域、国别,是全球性的影响,“新的通讯技术弱化了纸质版的文学书籍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作用”⑤希利斯·米勒:《中美文学研究之比较》,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其次,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文学危机更是精神观念层面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评价标准的危机,即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在所谓的‘世界文学’中存在着明显的以欧洲或美国或英语文学为中心的观念,而中国文学与西方人观念中的文学是很不相同的,如何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呢?”其二,我们是否有可能统一评价标准?统一文学观念?对此希利斯·米勒表示存疑:“将比较文学综合化。
在英美文学专家之外,加入研究中国、日本、阿拉伯、印度等国语言文学的专家,人员齐全了,但思想如何统一呢?”⑥空草:《J.希利斯·米勒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此为希利斯·米勒“World Literatrue in the age of telecommunications”(World Literature Today,summer 2000)一文的摘要。再次,在全球化和电讯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还面临着“同质化”危机。2008年,希利斯·米勒结合他对中美文学研究二十年的观察,发表了《中美文学研究之比较》的演讲,详述了他所感受到的中美文学研究的异同:如学术会议和课堂教学的情形已经与美国没有什么两样;中国学界传达出来的文化自信,使米勒感到“中国却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让我隐约感到自己是‘少数族裔’的地方”;美国经济的衰退对美国的文学研究带来巨大冲击,而中国大学主要靠政府投资,还能够蓬勃发展;美国的文学研究缺乏统一性,即使是同一学科,开设的课程五花八门,缺乏共识;而中国的文学教育虽然有大纲,但教学过程中仍然也是鼓励创新;①希利斯·米勒:《中美文学研究之比较》,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256页。中美文学研究的强烈反差甚至让希利斯·米勒感觉“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感到,文学研究,包括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比在美国要繁荣得多。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严肃的英美文学研究已经迁移或者被‘转包’到中国了”,相反,“现在在美国,文学似乎是个无关重要的消遣”。②希利斯·米勒:“前言”,参见希利斯·米勒:《希利斯·米勒文集》,王逢振、周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三、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希利斯·米勒有着新批评传统培养起来的对语言、文字、文本、修辞等方面的极度敏感,同时也有着解构主义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拆解二对立结构、质疑宏大叙事的立场和策略,再加上身处于全球化浪潮如日中天、数字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所有这些都使得希利斯·米勒非常关心“美国之外”(同时也是“非西方”)的文学与文化问题。虽然希利斯·米勒并不懂中文(他也因此而颇为懊恼),但这并没有阻挡住他关注中文、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热情。在他频繁来华的这些年里,米勒对中国的印象日益加深,对中文的认识也更加清晰,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也不断增强。
希利斯·米勒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思想的了解有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华裔学者顾明栋。在顾明栋的《汉学主义》(Sinologism: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的序中,希利斯·米勒认为顾明栋是在美国华裔学者中少有的几位能够熟练应用中西学术资源的学者之一。顾明栋在《汉学主义》中努力想达到双重目的:“他想寻找到一些共同点,以便能够公平地比较中西方材料。同时,他想强调中国传统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独创性及其价值。”③J.Hills Miller,Foreword,Sinologism: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By Ming Dong Gu,Routledge 2013.p.x.为此,希利斯·米勒还概要分析了顾明栋的《中国的读写理论:诠释学与开放诗学之路》(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A Route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中国小说理论:非西方叙事体系》(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两部著作以及他的部分论文,并给予“杰出的和原创性的”的高度评价。通过《汉学主义》,希利斯·米勒意识到西方理论在阐释中国问题时面临着诸多偏见、误读甚至是错误,而“这套构成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话语的隐藏逻辑的经常无意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被顾明栋命名为“汉学主义”。为此,希利斯·米勒不无自嘲地说,虽然他多年来频繁往返中国,惊叹于中国这些年所发生的巨变,但越是了解越感到自己的无知,越是感觉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如果这么多饱学之士都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为什么我还要假设我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④J.Hills Miller,Foreword,Sinologism: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By Ming Dong Gu,Routledge 2013.p.xviii.
即便冒着曲解和误读的危险,希利斯·米勒仍然对中国语言、文字以及修辞方面的特点已有了初步印象。虽然解构主义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就已经将中文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摆在了德里达《论文字学》的重要位置,但是希利斯·米勒对中文的认识并非沿着德里达的路线前进的。希利斯·米勒更多的是继承英美新批评的传统,从经验和现象层面,从语言、文字、语音、语法、修辞等维度来感知中文。比如说对中文汉字的象形特征的理解,希利斯·米勒认为:“语言媒介和视觉媒介从来就没有截然分开过,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它们的融合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们不知道西方的字母文字当初是什么样子,反正现在这些文字体系的象形性大部分早就消失了,这一点不同于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在汉语中,‘出’(exit)这个字现在看起来仍然像一个张开的嘴巴或者一个门口,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在过去,中国人必须掌握一门书法艺术才可能走上仕途,上至皇帝,下至七品知县,皆是如此。”①希利斯·米勒:《媒介从来都不曾分开过: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抑或说,文学研究的数字化变革》,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希利斯·米勒了解到“汉语没有代词,也没有动词时态”(这里显然包含着希利斯·米勒对中文语法的误读——引者注),因此,如果想将一种语言翻译(编织,希利斯·米勒用的是“These are woven into the fabric…”)到另一种语言中,难免会削足适履,对原有的语言文字进行扭曲变形。②J.Hillis Miller,Reading forOur Time,‘Adam Bede’and‘Middlemarch’Revisited,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14.
不过,在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文学和文化问题接触和了解的过程中,希利斯·米勒也强调不能带着西方的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这种方法论和理论立场的自觉是难能可贵的。在希利斯·米勒看来,“所有文本都应该置于它所属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比如中国的‘文学’,应该从中国的‘诗学’的角度,而不是把西方的理论强加其上,像我现在这样子,使用‘literature’和‘poetics’这种术语(这两个词在英语中的含义曾几经变迁,现在一般译为‘文学’、‘诗学’,而有些理论家声称,中国没有诗学——译者注)”③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这种理论与中国学者在应对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巨大影响时所产生的强化本土文学立场、抵抗西方文论负面影响的态度惊人地一致。希利斯·米勒认为:“非欧洲的文学文本与欧洲文本一样也同它们的传统有着复杂的联系。”为此,希利斯·米勒举了一个中国文学的例子:“史蒂芬·欧文在他的扛鼎之作《中国文学选集:从开始到1911年》中,用了足足1212页来展现英文版的选文。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文学的选集2中如果只用寥寥几篇选段来表现中国文学是很有问题的。但就连欧文的这一选集,在选择和翻译上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④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然后,希利斯·米勒还以亨利·詹姆斯小说《贵妇人的画像》为例比较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亲吻行为的描写。这一例子还在他的另一篇演讲《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再度强调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亲吻缺席的现象,但用中国的“兴”与西方“转义”之不同:“就非西方文化来说,是否有名称或概念对应于我们的转义呢?举例说,陆机在他著名的《文赋》里讲了许多诗语逼真地形容事物之难的话:‘体有万珠,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虽然认识到诗歌写作中寻找正确语词的艰巨,陆机并没有诉诸隐喻概念,更不要说转义了。尽管这两者都属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但中文诗在大量使用我们西方人可能称为转义的手法。主观感受与客观景物描述的强有力并置就是如此。《诗经》中有这样的例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中国诗一直在使用转义,只是没有明确使用这一名称或概念,尽管中国人用‘比’表示比较,用‘兴’表示‘感发’或‘感性性的意象’。这种术语上的差异是否构成两种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只是不正当地把隐喻和转义强加于中国‘文学’,能穿越这种障碍吗?甚至文学这个名称本身准确吗?因为在没有哪个词确切对应于英文的‘文学’。我被告知,中文里的‘文’有迥异于西方的含义。”⑤希利斯·米勒:《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因此,希利斯·米勒“建议发展一种新型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⑥希利斯·米勒:《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不仅如此,希利斯·米勒还部分关注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关注主要来自于王宁对他的影响。2008年,王宁在《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上做了一期“在全球化语境中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Rethink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Global Context)的专刊。这期专刊中除了王宁、生安锋、顾明栋、李同路、陈永国、黄承元(Alexander C.Y.Huang)、鲁晓鹏(Sheldon H.Lu)外,还有柏佑铭(Yomi Braester)、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希利斯·米勒。从这个阵容来看,就是中国学者、海外中国学学者以及西方文论界的重要学者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的对话。希利斯·米勒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以一个西方文论家的身份通过对本期专刊所涉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希利斯·米勒在此之前对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少整体上的认知,因而他在回应这些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代分期、思潮流派以及主题、风格等诸多问题时,只能以相对“隔靴搔痒”的方式进行。希利斯·米勒在文中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自我反思的问题:为什么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一位美国学者来说是必要而且重要的?希利斯·米勒的回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全然的另外一个”超越了种族差别,能够让他“发现与自己大不相同的东西”。二是中国文学认知问题。通过对这期专刊的阅读,希利斯·米勒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个基本印象。其一是知识性方面的,对1919年之后中国文学史有了一个轮廓。其二是认识论方面的,希利斯·米勒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规范和传统形成了一些判断。其中最重要的判断是,希利斯·米勒发现了“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的那种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如果没有大量的西方影响杂糅其中,现代中国文学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作家、批评家还是研究者又都同时表态说“他们不是西方文学亦步亦趋的模仿者”,他们还“要传承古老的中国文学传统”,“现代中国文学将其独特的东西融入世界文学”。①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阅读现(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Reading (about)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9:1(March 2008).
四、“解构性阅读”或“修辞性阅读”:学术立场的自我调整/强化
如前所述,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学术形象主要体现为“耶鲁四人帮”的解构主义批评家、《解读叙事》《小说与重复》为代表的叙事理论家以及英国文学批评家等。其实这三个学术形象在米勒身上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有着英美新批评的学术训练,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更多是建立在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基础之上,而这些文学文本又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的作家作品那里。之所以会形成三个学术形象,主要是中国接受者从不同角度对米勒的学术思想展开的接受。20世纪80年代,作为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米勒是由张隆溪和王逢振建构起来的;作为叙事理论家的希利斯·米勒则主要是在21世纪初通过申丹翻译的《解读叙事》和由王宏图翻译的《小说与重复》两书建构起来的。②《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引发了中国学者从叙事学角度接受希利斯·米勒的热情。不过,希利斯·米勒的这些学术思想更多是以单向度的方式展开的接受,中国学者虽然撰写了大量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和“重复”的叙事理论,但是并不为希利斯·米勒本人所关注。
真正迫使希利斯·米勒回应对他自己学术思想质疑的,是中国学者张江。从2014年开始,张江先后提出“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本体阐释”以及“中国阐释学”等一系列反思西方文论研究范式,推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基础理论问题,引起中国文论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张江还先后与希利斯·米勒、哈派姆、约翰·汤普森、迈克·费瑟斯通、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伊拉莎白·梅内迪、西奥·德汉等十多位外国学者展开对话。其中张江与希利斯·米勒之间以互通书信的方式展开了研讨。③这些书信分别是:张江的《确定的文本与确定的主题——致希利斯·米勒》、希利斯·米勒的回信《“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张江的《普遍意义的批评方法——致希利斯·米勒先生》以及希利斯·米勒的《J·希利斯·米勒符合张江第二封信》。它们分别发表在《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和《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英文版分别发表在《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2016年第2期和第3期上。
这四封信以张江的“一个确定的文本究竟有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主旨,这个主旨能够为多数人所基本认同?”问题为起点,聚焦于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对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主题分析,展开解构主义理论的有效性的讨论。张江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是“否定以往所有的批评方式,去中心化,反本质化,对文本作意义、结构、语言的解构”,但是在希利斯·米勒对《德伯家的苔丝》的分析中却表现出对多个主题相互交织缠绕中指向某一个小说的主旨的特点。张江认为,这一矛盾暴露了希利斯·米勒在批评实践中对解构主义批评准则的背离,“给解构主义的理论立场一个有力的冲击”①张江:《确定的文本与确定的主题——致希利斯·米勒》,《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对此疑问,希利斯·米勒并不认同一个文本有一个主题,而且能够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确定一个主题只是一个对于特定文本深思熟虑的教学、阅读以及相关创作的开端”,并反问“为什么一个文本只能有一个主题?”指出中国各种教材中关于解构主义的介绍多集中在消极面,而且“差不多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大众媒体对所谓的‘解构’的理解”,并认为自己“从来不拒绝理性,也不怀疑真理”。为此,希利斯·米勒详细解释了引起中国学者误读的“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根本无法重新安装回去”的例子,强调他心目中的“解构”同时包含着肯定与否定、建构与解构。鉴于解构主义被误读和简化,希利斯·米勒表示:“我近来更愿意将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修辞性阅读’,而不是‘解构性阅读’(因为对‘deconstruction’这一词汇的解读通常是你们的教科书中,或者美国大众媒体所假设的那个含义)。而我所称的‘修辞性阅读’的含义是,注重我所阅读、讲授与书写的文本中修辞性语言(包括反讽)的内在含义。”②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张江在回信中对此表示积极地肯定,认为“这可以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对话有益于大家更准确地了解您的学术立场”。与此同时,张江继续追问,希利斯·米勒所主张的“‘重复’这个程式甚至已然是范式,来阐释天下的全部作品,这不是重走了结构主义一类其他主义的老路吗?”这是否也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误区?③张江:《普遍意义的批评方法——致希利斯·米勒先生》,《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对此,希利斯·米勒认为:“在西方,有很多套此类的批评方法存在,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但是,没有任何一套方法能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因此,希利斯·米勒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理论的价值在于对阅读起辅助作用,理论只是阅读的“一个处于从属地位(ancillary)的侍女”。④希利斯·米勒:《J.希利斯·米勒答张江第二封信》,《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综观希利斯·米勒对张江质疑的回应,不难发现,一方面希利斯·米勒再一次理清和阐明了解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思维逻辑;但另一方面也被迫做出了某种理论姿态上的调整:为了避免陷入被贴上被简单化、负面化、单一化理解的“解构”标签,希利斯·米勒强调自己“修辞性阅读”的批评立场。⑤早在2001年,希利斯·米勒在与金惠敏的对谈中,就明确表明了“永远的修辞性阅读”的主张。参见《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对话》,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84页。
就在希利斯·米勒与张江之间正在书信对话的同时,希利斯·米勒与印度学者兰詹·高希(Ranjan Ghosh)之间进行长达15年的文学对话,以《文学思考的洲际对话》(Thinking Literature across Continents)为名于2016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⑥Ranjan Ghosh,J.Hillis Miller.Thinking Literature across Continents.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该书也以英文影印版形式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在中国出版,书名为《文学思考的洲际对话》。本书以你来我往的形式,围绕“文学及文学重要问题”“诗与诗歌”“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伦理与文学”五个主题,每人撰写一章。在该书中,兰詹·高希和希利斯·米勒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文学、文化、文论及哲学思想等引入相关问题的讨论,如老子、庄子、孔子、顾恺之、陆机、陶潜、刘勰、孔颖达、姜夔、王夫之、严羽、杨万里、刘若愚、周蕾、刘殿爵、张隆溪、叶威廉、奚密、顾明栋,等等。在由希利斯·米勒所撰写的“绪论”之二“文学文本的白痴”(The Idiosyncrasy of the Literary Text)中,希利斯·米勒再次回应了他与张江围绕“解构”一词所引起的误读的问题,认为之所以“解构批评”在中国受到质疑和负面评价,或许与中国高校教育政策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有关,并提出“他们对所谓解构的戏仿是否也被他们视为一种西方价值观?”的疑问。⑦Ranjan Ghosh,J.Hillis Miller.Thinking Literature across Continents.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p.17.很显然,希利斯·米勒的这一看法包含着对当代中国文论现实的部分误解以及臆测。
尽管对话仍存诸多分析,但是中西方学者之间能够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和争鸣,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这场对话的推动者,王宁认为,这表明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西方文论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兴趣不仅体现于虔诚的学习,更在于对之的讨论和质疑”,“通过与原作者的直接讨论和对话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识”。⑧王宁:《米勒的中国之旅(中文版序)》,希利斯·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结 语
2018年9月,在由王宁和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共同组织的《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的专刊“中国与西方理论的接触”(Chinese Encounterswith Western Theories)中,希利斯·米勒再次应邀撰文《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回应本期专刊中王宁、张江和朱立元这三位中国学者的论文,①它们分别是:王宁的《法国理论在中国与中国理论的重建》(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Re]construction)、张江的《强制阐释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和朱立元的《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Hillis Miller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感受到了中国学者在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方面的强烈诉求,认为“中国人希望通过发展一种独特的、排除他们所说的‘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中国式文学理论来实现统一文学理论的目标”。在回应王宁的论文时,希利斯·米勒表达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亦即中国人是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这个问题的深厚兴趣。在回应张江的论文时,希利斯·米勒一方面继续解释了中国学者对解构主义的误读,同时另一方面也对张江“强烈反对文学批评的公式或模式”主张的赞同。在回应朱立元的论文时,感叹“此前我并不知道我的‘文学终结’的论文在中国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和讨论”。除此之外,希利斯·米勒认为当前最值得关心的问题“不是向视觉文化的转变,而是从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大规模转变”,“这种变化不是从语言转变为视觉,而是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体,即新的‘电信体制’”。②希利斯·米勒:《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李松译,《长江学术》2019年第2期。该文原文以“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为题发表在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Septermber 2018.
希利斯·米勒从1988年到2018年三十年时间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为我们提供了中西方学者如何通过对话、交流、研讨甚至论辩的方式相互了解,增强共识,求同存异的学术历程。中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文化对话”和“文学对话”不可能采取无接触式的“隔空喊话”的方式进行。尤其是面对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所形成的有关中国的美化/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唯有密切接触、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和破除。同样,中国的思想文化要想真正能够“走出去”,想真正地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也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希利斯·米勒三十年的中国交往也成为中西文论交往对话的最好个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