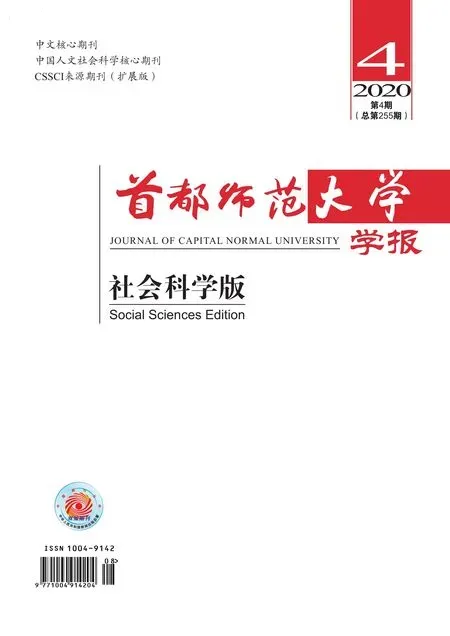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叙拉古的民主政治
晏绍祥
引 言
凡论及古代希腊民主,人们首先必想到古典时代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的确,在许多方面,雅典民主政治都堪称古代民主政治的代表。近代史学中第一个为民主政治翻案的史学家格罗特12卷的《希腊史》就是以雅典为中心。①关于格罗特《希腊史》的雅典中心特征,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00页。然而,古代希腊历史从来就是多中心的,作为希腊世界基本的国家形态——城邦,其制度中都包含程度不等的民主因素。公元前6世纪初,平等趋向同时出现于北非、小亚细亚和雅典等多个地区的希腊人城邦中②晏绍祥:《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平等趋向》,徐松岩主编:《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15页。,甚至民主政治都未必首先出现于雅典。①华莱士、霍恩布洛尔、默里等认为,斯巴达是第一个平等或民主政体,理由是重装步兵的战斗方式天然是“共同体的、合作的和平等的”,没有贵族“优秀”发挥作用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斯巴达基本文献《大瑞特拉》中,它肯定了平等者对国家的统治。见Robert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in Ian Morris and Kurt A.Raaflaub,ed.,Democracy 2500:Challenges and Questions,Dubuque:Kendal/Hunt Publishing Company,1998,pp.13-14;霍恩布洛尔:《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创立与发展》,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另请见晏绍祥:《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早期民主政治,见Eric W.Robinson,The First Democracies:Early Popular Government outside Athens,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97.虽然希腊史研究中雅典和斯巴达中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但对叙拉古的民主制,学术界的讨论仍相对较少。与汗牛充栋的论雅典民主政治的著作比较,新世纪以来,仅有鲁特和罗宾逊等专文讨论叙拉古的民主政治。②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in Roger Brock and Stephen Hodkinson,ed.,Alternatives to Athens:Varieti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Gree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1-151;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opular Government in the Greek Classical 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67-89.由于资料缺失,也由于研究不足,两人在叙拉古民主政治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鲁特否认公元前5世纪叙拉古的制度是民主政治,认为那最多是寡头因素与民主因素的混合,其中又以寡头制成分占优势。如果叙拉古真实行过民主政治,最多也就是公元前413年战胜雅典人之后的数年时间里。罗宾逊相对肯定,认为叙拉古民主政治始于僭主政治垮台之后,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末,前后约60年。演说术的流行、人民领袖的崛起、公民大会的强势地位以及橄榄叶放逐法等,证明叙拉古的民主政治有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在实际运作中,民主政治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是,他的观点并未得到完全接受,最近出版的德安格利斯的著作就公开质疑罗宾逊的结论,基本回到了鲁特的论点。德安格利斯尤其指出,叙拉古复杂的社会矛盾,土地所有者的优势,都表明它难以实行民主政治。③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07-210.
有关叙拉古民主政治的分歧和争论,一方面凸显了资料的不足,有限的资料,因为可靠程度和语境问题,也可能引向不同的解释,但同时也为我们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探讨留下了空间。本文的基本意图,是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初步重建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叙拉古民主政治的大概历程和基本制度,以求有助于对希腊历史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理解。
一、叙拉古国家的早期发展
据修昔底德,叙拉古是希腊人在西西里建立的第二个殖民地,古老程度仅次于纳克索斯,殖民者来自科林斯。如此,其建立年代当在公元前734年左右。但其他古代作家暗示的年代并不完全与修昔底德吻合。④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2(本文所引古典文献,除特别注明外,一般均依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之英译文,下同).关于叙拉古建立的年代,古代作家的定年差距颇大,早者到前8世纪初,晚者在该世纪末,当前的一般意见仍是遵从修昔底德。见A.W.Gomme,A.Andrewes and K.J.Dover,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06-207;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p.69.在西西里的希腊人中,叙拉古虽然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土地肥沃,有良好的港口,但最初并不引人注目。西部希腊人早期修建的豪华神庙,大多出自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其他希腊人城邦之手。在物质文化上,叙拉古最初并不显眼,原因部分在于,叙拉古殖民者来自不同的城邦,与当地居民西凯尔人矛盾尖锐,内部并不平静。修昔底德暗示最初的殖民者全部来自科林斯,但考古发掘和当地的地名显示,叙拉古境内有不少西凯尔人与叙拉古人混处,殖民者中,也有部分人来自优卑亚等地。⑤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p.71.居民成分的复杂,使得西西里的希腊人城邦不太容易形成统一的城邦认同,由于利益纠葛,土地分配不均,以及城邦自身的脆弱,不同来源的公民之间会爆发矛盾,甚至公开的武装冲突。如阿克比亚戴斯意识到的:
尽管西西里的城邦人口众多,但多族杂居,其公民人口易于迁徙和流入。由于这个缘故,谁也不打算代表自己的国家用武器保卫自身安全,或为耕作土地对其进行持久的改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动听的言辞,或者通过搞派别斗争,从公家捞取钱财;如果此路不通,就迁到他邦生活。如此乌合之众,不可能一条心地听从建议,也不能采取统一的行动;如果我们的提议合其脾胃,他们很快就会一群一群地跑到我们这边来,特别是在他们内讧之时……①Thucydides,History ofthe Peloponnesian War,vi,7,3-4。中译文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1页,有改动。
阿克比亚戴斯这番话发表于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上,意在反驳尼奇亚斯有关西西里远征困难重重的观点,煽起雅典人远征的热情,因此不免夸大了西西里希腊人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而且他所说主要是就西西里希腊人整体而言,不代表每个城邦内部都是如此。同时,阿克比亚戴斯显然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西西里僭主政治瓦解后城邦内部发生的纠纷以及人口迁移的影响②A.W.Gomme,A.Andrewes and K.J.Dover,A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4,pp.249-250.,不能完全代表民主政治建立之前叙拉古的情况。但是,他指出的西西里希腊人城邦的几个主要特点:公民内部矛盾复杂,缺乏牢固的城邦认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西里人自己的呼应。在叙拉古人的一次公民大会上,阿泰纳戈拉斯指出:“我们的城邦少有平静之日,经常处于内讧和斗争之中,与其说与敌人斗,不如说与自己人斗。有时还受僭主的统治和邪恶的寡头统治。”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8,3.两相印证,他们的发言的确反映了西西里的实际,对古典时代前期的叙拉古而言,也具有相当的真理性。
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叙拉古城邦建立之时,殖民者可能就来自不同的城邦。从后来的历史看,第一批殖民者中包含的优卑亚人和科林斯人成分,没有对叙拉古城邦的认同产生严重影响,以至于危及叙拉古公民团体的团结。但古风时代逐渐形成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土地占有的不平均,造成了城邦内部的分裂。
有关埃提奥普斯用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换取一块蜜糕的故事④Athenaeus,The Learned Banqueters,iv,167d.有关讨论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一方面表明殖民者出发之前已经确定了平等占有土地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表明,对土地的不平等占有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已经存在。埃提奥普斯的故事至少说明,他为了一块蜜糕出卖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殖民者的领袖阿奇亚斯至少借此获得了两份土地。⑤故事说埃提奥普斯为了那块蜜糕把自己在未来殖民地获得土地的权利转给了阿奇亚斯,见Athenaeus,The Learned Banqueters,iv,167d.但这样的情况终归是例外,因而引起了古代作家特殊的注意。一般来说,殖民者占有的土地仍保持大体平等。意大利、黑海周边等地的考古发掘暗示,甚至到古典时代,殖民者占有的土地仍相对平均,他们内部的分化并不严重。⑥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57-68页。以此类推,则叙拉古殖民者最初占有的土地可能也大体平等。但这仅仅是指最初的殖民者。公元前7到前6世纪西西里希腊人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肯定不完全是殖民地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应当有大量新移民来临。如同第一批移民一样,他们中有政治上的失意者,如斯巴达的多利欧斯,也有期望到西西里和大希腊发财者,还有些如弗凯亚人和美塞尼亚人那样,因为自己的国家被他国征服,而整体搬迁到西西里及其周边地区。⑦关于多利欧斯的殖民活动,诗人和音乐家阿利翁在意大利的活动,以及美塞尼亚人和弗凯亚人的西迁,见Herodotus,The Histories,i,24;i,166;v,42-43,45-47.他们中的部分人仅仅是过客,但也有相当部分人选择在西部定居,成为希腊人殖民城邦中的新来者。公元前7到前6世纪,叙拉古在原有的墓地之外,新增了两块墓地,显然是为应对人口移入和增长的需要。⑧M.I.Finley,Ancient Sicily,a Revised Edition,London:Book Club Associates,1979,pp.30-31.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第一批殖民者已经占据了最好最肥沃的土地,而且一般禁止对已经分配的土地再行分配,成为所谓的贵族,政治权力可能也被他们垄断。新来者虽然可能得到所在城邦的公民权,但只能满足于相对较差的土地。在政治上,新来者大约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在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西西里希腊人城邦大多形成了寡头政治,掌权者一般是最初的殖民者和他们的后代。“西西里的共同体很快就发现他们处于古老的希腊人模式之下。贵族家庭或家族掌握的权力在增长,他们占有了大部分财富,财富意味着土地,祭司职位和司法管理也是如此”①M.I.Finley,Ancient Sicily,p.38.。
对古风时代叙拉古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我们的资料非常稀少。但比较肯定的是最初的殖民者及其后代形成了一个名为土地所有者(Gamoroi)的集团,并与一般公民区分开来。根据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寡头统治一般的特征是不稳定。一是他们内部常常为争夺最高权力发生内讧,一是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下层阶级会起而暴动。②希罗多德借大流士之口宣布,寡头政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见取得胜利,由此引起纷争;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强调被排除在政制之外的人数众多的平民群众,一旦他们加入军队,会对寡头统治发难。见Herodotus,The Histories,iii,82;Aristotle,Politics,1321b13-21.在叙拉古早年历史上,有两个年轻人因为一桩简单的爱情事件,“各自集结对他同情的官员和公民互相攻击,终至整个公民团体分成了两不相容的党派”③Aristotle,Politics,1303b20-27.。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这件事情发生于何时,最终如何收场。如果这还是寡头内部的斗争引发的小规模冲突,公元前5世纪初年的争斗,则发生在上层土地所有者与下层民众之间。④盖隆最终于公元前485年取得了叙拉古的统治权,但土地所有者何时被驱逐并不确定。希罗多德的语气暗示发生在盖隆入主叙拉古之前不久,顿巴宾倾向于公元前491年左右,见 Herodotus,The Histories,vii,155;T.J.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8,pp.414-415.对于这次引起了严重后果的冲突,我们的资料仅有希罗多德有限的几句话以及亚里士多德一句不太明确的判断。⑤Herodotus,The Histories,vii,154-155;Aristotle,Politics,1302b31-32.此前叙拉古曾与盖拉僭主盖隆交战,不幸遭遇失败。科林斯人和科西拉人的介入,使叙拉古得以保持独立,但丧失了殖民地卡马利纳。此后不久,叙拉古内部发生冲突,平民联合为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的库吕利奥伊人驱逐了土地所有者阶级。后者逃亡卡斯麦奈,并对叙拉古开战。为了达成回国的愿望,土地所有者向盖隆求援,盖隆借机干预。与此同时,城内的民主政权可能政绩不佳,或者面对盖隆绝对优势的军队,感到力量不足,因此未加抵抗就同意盖隆入城。⑥E.A.Freeman,History of Sicily,vol.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91,pp.124-126.此后数十年间,叙拉古处于盖隆家族的僭主统治之下。
希罗多德这段记载虽然简短,仍给我们透露了叙拉古社会的诸多重要方面。首先,公民被划分为土地所有者与平民两个阶层,二者之间矛盾尖锐,迫使下层阶级发动革命,将土地所有者阶级赶出叙拉古。但土地所有者并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如阿克比亚戴斯所说的那样,宁肯引狼入室,也要重夺权力。他们宁愿向盖隆求援,也不愿与平民和解。同理,当平民面对盖隆大军时,或许他们认为,哪怕是接受盖隆的条件,也较直接让土地所有者重新掌权更加可取,因此他们选择不加抵抗的屈服。不管是土地所有者向盖隆求援,还是平民不战而降,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⑦E.A.Freeman,History ofSicily,vol.2,pp.127-128.其次,土地所有者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小地主,他们应该占有相对较多的地产,地产的规模不仅足以养活他们自己,而且足以养活为他们耕种土地的那些库吕利奥伊人。一般平民拥有的土地较少,或许只够糊口。库吕利奥伊人对自己的处境也不满意,在时机来临时,他们选择与平民联合,共同对抗土地所有者。两个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使端赖公民群体内部团结、公民集体共享城邦的天然民主倾向,⑧黑格尔早已指出:“只有民主的宪法才能够适合这种‘精神’和这种国家。”埃伦伯尔格也认为,希腊城邦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其中管理和做出决定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汉森则直接宣布,希腊城邦是公民国家。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Victor Ehrenberg,“Origins of Democracy,”Historia,Bd.1,H.4(1950),p.258;M.H.Hansen,“The Polis as a Citizen State,”in M.H.Hansen,ed.,Ancient Greek City-State,Copenhagen:Munksgaard,1993,pp.7-29.不容易在叙拉古成为现实。叙拉古最初的民主,是下层平民与库吕利奥伊人排除土地所有者的民主,而且试验不太成功。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政治不仅未能击败土地所有者,反而让国家陷入了混乱和无序,进而造成了他们面对盖隆时的软弱。⑨Aristotle,Politics,1302b31-32.
可是,盖隆家族的僭主统治,与古风时代希腊本土的同侪扩大城邦统治基础不同。他们不仅未能解决叙拉古固有的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大规模迁移居民以及由此引起的财产关系的变化。
据希罗多德①Herodotus,The Histories,vii,156.,盖隆取得叙拉古之后,并未对叙拉古已有的体制做出任何改变,也没有触动原有的居民。但他从此离开盖拉,把叙拉古作为自己的权力基地,并且开始加强叙拉古的实力。但他的扩张不是希腊大陆城邦那样简单地扩大所在城邦的领土,而类似于亚述和波斯等专制帝国的做法:大规模迁移居民。他首先征服了卡马利纳城,把那里的居民全部迁移到叙拉古,他还把一半左右的盖拉人移到叙拉古。随后他的目标是针对麦加拉和优卑亚人的城邦,强令麦加拉—叙布莱亚的富人移居叙拉古,把穷人卖到西西里之外为奴。对于优卑亚人的殖民地如纳克索斯和卡塔奈等,他可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盖隆的做法在短期内急剧增加了叙拉古的人口,扩大了统治区域,壮大了实力,从此使叙拉古成为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一城。②当希腊人向叙拉古求援时,盖隆声称他可以提供2万重装步兵,200艘三列桨战船,2000名轻装兵,2000名骑兵,2000名弩手。如果他所说没有夸张,则这是当时单个希腊人城邦能够提供的最大规模的军队了,甚至雅典和斯巴达都望尘莫及。普拉提亚战役中,斯巴达人虽然提供了1万名重装兵,但其中5000人是庇里阿西人;马拉松战役中,雅典能够出动的重装步兵不过9000人左右。见Herodotus,vii,158;奈波斯:《外族名将传》,刘君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但是,这种不顾过去的历史联系,大规模迁移人口的行动,无疑对叙拉古以及相关城邦的人口结构、财产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僭主盖隆的统治,更多地依靠雇佣兵而非平民的支持,因此在政策上不像希腊本土的僭主,多少偏向平民,扩大城邦基础,反而偏向富人,恢复他们的统治,因为他认为:“平民是最难于与之相处的人们。”③Herodotus,The Histories,vii,156.后来他的确授予部分人叙拉古公民权,但他们既不是平民,更非富人土地上的库吕利奥伊人,而是他自己的雇佣兵,数量可能达到1万人。④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72,3.因此叙拉古僭主不仅没有提升平民的地位,改造社会结构,反而强化了富人的特权,并且通过人口混合,削弱了城邦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认同感。“盖隆的政策代表的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本质上是复辟和强化”⑤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0.。即强化了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权力。事实上,僭主的做法从许多方面破坏了城邦的惯例,他们频繁地摧毁和重建城市,屡次成千上万地迁移人口,为了王朝的需要,实行多妻制。在希腊本土僭主政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际,西西里的僭主在公元前5世纪前期继续保持,而且表现出僭主所有恶劣特征中最为恶名昭彰的一面。⑥M.I.Finley,Ancient Sicily,p.55.在他们的统治下,叙拉古似乎不大可能培育出产生民主政治的土壤。
二、叙拉古建立民主政治
表面上,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是西西里僭主政治最为强大的时期。西西里主要城邦,从南部的阿克拉加斯到北方的希麦拉,包括东海岸的叙拉古在内,基本都处在僭主的统治之下。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整个西西里的僭主政治,包括叙拉古的在内,突然都崩溃了。首先垮台的是阿克拉加斯和希麦拉的僭主。虽然弗里曼早已指出,有关西西里史的资料非常不可信,相关描写大同小异,甚至可以相互置换,⑦E.A.Freeman,History of Sicily,vol.2,p.82.但古代作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所有城邦的僭主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垮台,民主政治代之而起。⑧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53,1-6;David Asheri,“Sicily,478-431 B.C.,”in D.M.Lewis et al.,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5,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4-156;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p.72-76.叙拉古是受这波浪潮波及的最后一个主要城邦。盖隆死后,僭主之位顺利传给其兄弟希埃罗。希埃罗死后,僭主家族内部爆发了一场继位之争,斗争以塔拉叙布鲁斯的胜利结束,但此人统治残暴。据狄奥多鲁斯:“他处死了许多公民,通过虚假的指控,迫使不少人流亡,为王家财政而觊觎这些人的财产。”①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67,5.此外,僭主大量招募雇佣兵以对抗公民兵的举动,也招致叙拉古人的痛恨。或许是在西西里僭主普遍垮台的影响之下,叙拉古人群起暴动,将僭主围困在卫城上。僭主以及雇佣兵聚集起来与公民对抗。叙拉古人转而向盖拉、希麦拉和阿克拉加斯等自由城邦求援。它们都做出积极响应,尤其是派来了海军。叙拉古人和同盟的海军一道,在海陆两边的会战中都取得了胜利,迫使僭主退位。经过谈判,塔拉叙布鲁斯不受伤害地离开,去了意大利。他留下的雇佣兵被驱逐。原本由叙拉古统治的周边城市随之独立,戴伊诺麦奈斯家族的僭主式帝国随之瓦解。“从此时起,叙拉古拥有了和平,繁荣大大增加;保持其民主政治将近60年”②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68,7.。
对于僭主垮台后叙拉古政制的性质,古典作家并无异议,一致公认此时的叙拉古是民主政治。我们首先有修昔底德的证据,他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与叙拉古民主政治几乎同时代,因此最有权威。他借阿泰纳戈拉斯之口宣布,当时的叙拉古实行民主政治,并且极力为民主政治辩护,“首先,‘人民’顾名思义指的是全体,而‘寡头政体’指的是部分。其次,富人最善守护财富;明智之士最善谋划;民众听了讨论后,最善评判。这三类人,部分地或全体地,都在民主政体里享有平等的地位”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9,1.。随后,他抨击了寡头政治让多数人分担危险,自己占有全部好处的行为。如果叙拉古当时是寡头政治,阿泰纳戈拉斯不太可能在公民大会上如此发言。他的话表明,叙拉古当时实行的只能是民主政治。在修昔底德的著述中,多次记录叙拉古举行公民大会的情景,而且几乎每次会议,似乎都有重大的事情需要处理。阿泰纳戈拉斯的言论,就发表在公元前415年雅典入侵前夕的公民大会上。后来,叙拉古人还就战争的策略、将军的任免、处置雅典战俘等多方面的问题,数次举行公民大会。至少在修昔底德笔下,叙拉古重要的政策,都出自公民大会的决定。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叙拉古人击败雅典海军之后,赫摩克拉泰斯本来期望叙拉古人能够连夜出兵封锁雅典军队的撤退路线,但当时叙拉古人正在狂欢,赫摩克拉泰斯只好诉诸计谋拖住雅典人。但他们都是以私人而非叙拉古人群体代表的身份,因为他们并未得到公民大会授权。所以,至少在修昔底德笔下,叙拉古的公民大会掌握着国家的政策,国家的制度根据公民大会的命令进行调整;官员由公民大会任命,并且处在后者的监督之下,随时可能被撤换;在公民大会上,演说家们发表演说,公民投票决定。这样的制度,的确有资格被称为民主政治。④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2,3-41,4;vi,63,2;vi,72,1-73,2;vi,103,3-4;vii,2,1-2;vii,73,1-4.
不过,学者们可能怀疑,阿泰纳戈拉斯的发言属公元前415年左右,而僭主政治垮台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两者相差半个世纪,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叙拉古是民主政治吗?至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僭主政治也可能转变为民主政治,犹如叙拉古的盖隆家族(垮台后)那样”。考虑到叙拉古此时主要的公民是农民,或许此时的民主属于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相对温和的类型。⑤Aristotle,Politics,1316a32-33;1292b21-23.
狄奥多鲁斯也非常明确地宣布,叙拉古僭主被推翻后,该邦实行了民主政治,“他们(叙拉古人)举行了一次公民大会,在讨论了组织自己的民主政治后,他们全都一致投票建造一座庞大的解放者宙斯的雕像,每年以献祭庆祝解放节……至于官职,他们建议将官职分配给最初的公民们,但那些被盖隆接纳入公民中的外国人,他们觉得不合适让他们分享这个荣誉”⑥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72,2-3.。从狄奥多鲁斯后来的叙述看,这些被盖隆接纳入公民中的外国人并非普通公民,而是雇佣兵。这些人是僭主政治坚定的支持者,将他们驱逐,是纯洁公民队伍的正常措施,与驱赶公民中的平民无关,也与所谓的精英阶级优势地位没有关系。⑦从狄奥多鲁斯的叙述看,公元前463年暴动反对叙拉古并与叙拉古人作战的,就是这批雇佣兵,而非任何其他人。参见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72,3-73,3.
不过,对于古代作家的一致意见,鲁特和德安格利斯同时表示保留。他们认为,考虑到叙拉古僭主的政策和它的社会结构,还有狄奥多鲁斯在使用民主政治术语时的随意,特别是民主政治这个术语在希腊化时代的贬值,他们所说的民主政治,未必是真正的民主。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该世纪末存在的政体,最多也就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民政体。①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3;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pp.207-210.即使有民主政治存在,历史也非常短暂:公元前413年打败雅典后到公元前405年狄奥尼修斯夺取权力之前的数年而已。②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p.141-151.那时叙拉古因海军日益重要,下层公民得以加入政治生活,并且有狄奥克莱斯的政制改革措施。不过,那显然是鲁特等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为了民主政治的典范,忽视希腊人城邦一般具有的民主特征以及城邦政治天然民主倾向的结果。③关于古风时代希腊城邦中政治平等的一般趋势,最近的论述请见:Kurt A.Raaflaub et al,Origins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Berkeley and Los Angel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22 ff.且不说当时人修昔底德有叙拉古人与雅典人性格最为相似的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远在民主政治术语贬值之前,他的见证应当得到我们足够的尊重。至于议事会在叙拉古的缺席,如果我们抛弃希腊史的雅典中心模式,不把雅典民主政治作为唯一的模式,而是一种合理的参照,则议事会的缺位不应成为认定叙拉古为民主政治的障碍。事实上,在古典时代的诸多民主城邦中,尤其是在那些相对较小的城邦中,公民大会的举行并不经常,类似五百人议事会那样的第二议事会,不一定有存在的必要。重要的是,即使鲁特也承认:“叙拉古似乎的确发展出了古代希腊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把主权置于民众大会之手。”在修昔底德笔下,“叙拉古享有主权的公民大会做出决定的方式,可以与民主的雅典相提并论”④如本文开头就指出的,斯巴达的议事会是原初的长老会,也无专门主持公民大会的议事会,但并不能据此否认斯巴达政治某种程度的民主特征。罗宾逊追溯了雅典之外若干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曼提奈亚、麦加拉和菲琉斯等邦似乎也没有第二议事会。参见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p.34-40,pp.46-50.引文见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p.150-151.。因此,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叙拉古,的确实行着民主政治。
我们更感到好奇的,是僭主政治垮台后,叙拉古为何选择民主政治?毕竟如埃伦伯格所说,一个城邦要发展到民主政治,即让自由人的多数或全体参与国家管理,是希腊政制发展的终极形态,需要一定的条件。⑤Victor Ehrenberg,“Origins of Democracy,”p.258.而叙拉古早期国家的发展,包括僭主的统治,并未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创造相应条件,毋宁说,是破坏了城邦走向民主的天然趋向。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学者似乎都并未留意。对古代作家来说,他们可能习以为常;对现代学者来说,则是缺乏相关史料。如鲁特指出的那样,叙拉古既没有梭伦,也没有克里斯提尼,更没有明显的制度上的创新和标志性的事件。⑥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1.
如同底比斯公元前379年突然转向民主政治一样,⑦关于公元前379年底比斯突然转向民主政治的原因,见晏绍祥:《比奥提亚同盟及其民主政治》,徐晓旭、王大庆主编:《新世界史》(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6页。叙拉古民主政治建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僭主政治崩溃后特殊的形势。首先,在西西里诸城邦中,叙拉古的僭主势力最大,崩溃相对也较晚。如前所述,僭主政治垮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公民突然在政治上觉醒,而是僭主自身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公民极大的反感。用狄奥多鲁斯的话说,在强令大量人员流亡,并且处死了许多人之后,僭主成为叙拉古所有人仇恨的对象,迫使公民们联合起来,“叙拉古人选择了领袖,决心团结如一人消灭僭主制。一旦他们被领袖们组织起来,他们就顽强地追随自由”⑧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67,6.。也就是说,如果说僭主最初尚能依靠土地所有者阶级和雇佣兵维持统治,但他的残暴,特别是针对富人的剥夺措施,消弭了叙拉古原有的土地所有者和普通平民之间的分歧,现在,所有的叙拉古人,不管他们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毫无例外地遭遇了僭主无法无天统治的威胁,从而使叙拉古人面对僭主变成了一个整体,在僭主统治末年无意中创造了统一的叙拉古人作为一个公民群体的意识。可以相信,由于僭主迁到叙拉古的大多是富人,叙拉古的公民大多都至少是家资中等以上的农民。因此,叙拉古人的多数应当是有能力成为重装步兵的中等富裕农民。与希腊本土不同的,是这个阶层从殖民地建立时就存在,在僭主时代获得了加强。到僭主垮台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城邦的主人。如汉松所说:“最初的希腊城邦最好被理解成一个独占但平等的农民共同体,他们如今生产自己的粮食,自己打仗,创造自己的法律。”城邦是“乡村民众中间广泛盛行的农业风气的结果”。①Victor Davis Hanson,The Other Greek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p.3-4.僭主垮台后的叙拉古,似乎就是这种状况。至于民主政治建立后返回的平民,一旦他们收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小所有者维持生计,应当没有问题。农民——公民群体的存在,是叙拉古民主政治产生最为根本的前提。
可是,面对僭主的公民群体并不能直接导向民主政治。叙拉古僭主的强大和顽固,成为民主政治产生的催化剂。当僭主发现整个城邦都与他为敌,而且已经发起暴动之时,他试图借助雇佣兵的力量压服起义者,并且控制了阿克拉狄奈和卫城奥提吉亚。两者都地势险要。起义的叙拉古人仅仅控制了城区的一部分。为对抗僭主,起义者必须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首先是叙拉古的民众。虽然如此,由于雇佣兵训练有素,叙拉古人无力将僭主彻底驱逐。于是,他们派出使者向已经建立民主政治的阿克拉加斯、盖拉、希麦拉等求援。这些城邦也迅速派出了骑兵、步兵和战船前来援助。②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68,1-2.僭主力量的强大和援兵的民主性质,使叙拉古人只能选择民主政治。一方面,僭主力量的强大,需要叙拉古人动员所有与僭主对抗的力量。狄奥多鲁斯说,叙拉古人“准备了船只并且把陆军列成战阵”,决心“在陆上和海上都决一死战”。③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68,2.也就是说,不能充当重装步兵的平民可能也作为水手参与了驱逐僭主的斗争,从而为他们在未来的叙拉古政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因此,叙拉古民主政治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城邦作为公民团体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如果说雅典人驱逐斯巴达国王及其支持者伊萨戈拉斯是一场革命④Josiah Ober,“‘IBesieged That Man’:Democracy’s Revolutionary Start,”in Kurt A.Raaflaub et al,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p.83 ff.,则叙拉古人驱逐僭主的行动,也是某种程度的“民主革命”:所有叙拉古人都被动员起来了。在完成了驱逐僭主的工作后,叙拉古人解放了被僭主统治的其他城市,“在它们中重建了民主政治”⑤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68,5.。这些行动既是叙拉古本身实行民主政治的直接证据,也是民主政治向其他城邦的自然扩展。
三、叙拉古民主政治:制度与运作
新生的民主政治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召回过去被流放的人,恢复被僭主消灭掉的其他国家。与雅典等不同,西西里过去并无深厚的民主传统,公元前485年叙拉古短暂的民主试验以失败告终。阿克拉加斯在僭主政治之前是否存在过民主政治,只有狄奥多鲁斯非常不可靠的间接证据。⑥Eric W.Robinson,The First Democracies,pp.78-80.尽管如此,僭主政治垮台后,西西里仍然在没有任何民主领袖、没有改革家或者宪政缔造者的情况下,创立了民主政治。同样奇怪的是,原来在西西里存在的大土地所有者,似乎在这次推翻僭主的革命中消失了,至少没有对民主政治的建立进行反抗,有的只是公民和僭主支持者——主要是雇佣兵——之间的对抗。⑦M.I.Finley,Ancient Sicily,pp.58-59.可能的情况是,公民的主体就是那些所谓土地所有者,以及迁移到叙拉古的富人。这里体现了希腊城邦本质上的民主特征:作为治权和主权寄托于公民团体的城邦制度,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有着天然的走向民主的倾向。然而,僭主数十年的统治,仍然严重毒害了西西里的社会和政治气氛,尤其是“多年的大规模流放,人口迁移,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一旦僭主之手被消除,它马上就造成了公开冲突”①M.I.Finley,Ancient Sicily,p.59.。在叙拉古,公民与盖隆赋予公民权的万名雇佣军发生了严重冲突。只是在经过损失惨重的战斗后,雇佣兵才最终被驱逐。除个别城邦外,有些地方如卡塔纳等,冲突更加激烈。由于僭主造成的人口迁徙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城邦,而是整个希腊人城邦共同的问题,西西里的希腊人决定为此召开一次所有城邦参与的大会,解决相关问题。经过讨论形成的决议,是所有盖隆派都应被驱逐;各自召回流亡者并发还财产,或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叙拉古放弃对卡马利纳的统治,让其重新独立,土地重新分配。这次会议大体解决了西西里过去流亡和迁移留下的基本问题,体现了新生民主政权处置的得宜,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又有什么人在这次城邦之间的大会上发言。②George Grote,History ofGreece,vol.5,London:John Murray,1870,p.92.
虽然城邦之间的争斗因为盖隆派的被逐暂时平息,各个城邦内部不同集团,特别是那些回归者与已经居住在当地的公民之间的纠纷并不是一次城邦间的会议可以解决的。叙拉古尤其如此,因为僭主盖隆将盖拉、卡马利纳、麦加拉—叙布莱亚等地的大量人口迁入叙拉古,同时肯定驱逐了部分叙拉古人,由此引出了无数的财产诉讼和纠纷。随着流放者的回归,相反的过程势必发生,尤其是数十年后,如何将财产归还原主,成为各个城邦面临的严重问题。“所有这些大量人员的迁移,造成了财产关系严重的混乱,因为土地每次被没收、加以分配和再分配,都是另一场运动。古代所存在的一个坚实传统到西塞罗和昆体良时代还在为人重复:随后产生的大量诉讼导致了法庭演说及第一批修辞手册的发展。无论这种因果解释是否正确,事实都是叙拉古的科拉克斯及其门生提西亚斯乃希腊修辞艺术的奠基者。该世纪后期,莱翁提尼的高尔吉亚为希腊世界修辞学最为著名的代表”③M.I.Finley,Ancient Sicily,p.61.。类似的争斗明显并未停息,直到公元前415年,雅典将领阿克比亚德斯在煽动发起西西里远征时,还做了前文已经征引的那段重要评论。④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17.除此之外,盖隆树立的先例,也没有被野心家们完全忘记。公元前454年,廷达利翁试图夺取叙拉古权力,重建僭主政治,结果被公民判处死刑。⑤George Grote,History ofGreece,vol.7,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Publishers,1875,p.121.然而,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在民主政治存在的60年间,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诉讼,还有僭主政治复辟的威胁,叙拉古并未爆发内战,反而保持了稳定,达到了繁荣,堪称奇迹。⑥据学者们统计,从公元前620—前278/269年间,叙拉古先后发生过27次冲突,频率高居希腊城邦前列。然而在民主政治时代,叙拉古居然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见M.H.Hanse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ed.,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25;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7,p.120.
对民主政治时期叙拉古的制度,我们略有了解,但仍不够全面。就公民队伍来说,随着叙拉古流亡者的回归,应当是所有叙拉古人都具有公民资格,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叙拉古公民中的大多数,可能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每日忙于田间劳作的农民,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出席公民大会,而宁愿让法律成为国家的主人。⑦Aristotle,Politics,1292b21 ff.,并请见N.K.Rutter,“Syr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3.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公民大会的组成、召开次数和具体权力,但它的确表现相当活跃。公元前466年僭主政治被推翻时,公民们就召开了会议,议决要为解放者宙斯建立一座祭坛,将官职限定在原来的公民中,对如何处理僭主留下的雇佣兵,也拿出了意见;约公元前451/0年,西凯尔人领袖杜凯提乌斯因与叙拉古作战失败,无路可逃之际,竟然夜间偷入叙拉古,并在广场的祭坛边寻求庇护。第二天早晨,当叙拉古人发现他时,就聚集了一批人。叙拉古官员们旋即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处置他们曾经的敌人。会上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绝对不要饶恕这个过去的敌人;另一种意见(在狄奥多鲁斯看来属于比较理性的公民)则认为,虽然此人过去可恶,但他已经受到惩罚,因此应当尊重神灵,同意杜凯提乌斯的请求。民众赞同了后一种意见,决议将他送往科林斯,规定他永远不得返回西西里,但由叙拉古官方每年给他提供一笔生活费。⑧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72,1-3;11,92,1-4.
上述会议表明,叙拉古的公民并非完全不熟悉议事机制,公民大会也可以因突发事件在官员们(而非雅典那样的议事会)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就在广场上。公元前415年,当雅典人入侵的消息到处哄传的时候,叙拉古人举行过公民大会,赫摩克拉泰斯和阿泰纳戈拉斯先后发言;同年在与雅典人初次交战失败后,叙拉古人再次召开了公民大会,就战争策略进行讨论,赫摩克拉泰斯再度发言;战争进行期间,叙拉古人肯定也举行过公民大会,讨论战争策略以及向斯巴达人求援问题;公元前413年,叙拉古人为如何处置战俘,再度召开了会议;公元前406年,当西西里面临迦太基人入侵、阿克拉加斯陷落时,叙拉古人又召集了公民大会。上述例证表明,至少在遭遇外敌入侵时,叙拉古人需要举行公民大会确定基本政策。①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2-35;6,7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ii,19,4-13,33,1;13,91,1-4.可惜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狄奥多鲁斯,都只提到了发言人,很少提到到底是何种官员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多少人。考古发现过叙拉古的剧场。学者们猜测那里可能也是公民大会会场。它面积不大,仅能容纳1000人左右。以叙拉古公民的数量(据估计在1.4万人以上),这个会场不免太小,即使与雅典的会场及其能够容纳的公民所占比例比较,也嫌太低(不足公民总数的7%,雅典大约是15%)。②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88.如果剧场真是会场,则它再次说明,希腊城邦在召集公民大会时,从来不指望所有公民出席。
会议讨论的问题应由主持人提出。开会之时,官员们可能会拿出初步意见。但面对突发情况,例如狄奥多鲁斯记载的那次决定杜凯提乌斯命运的会议,官员们明显没有任何预案,所以在公民大会上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发言人都是些什么人物,狄奥多鲁斯并未提及,可能并非特别知名的人士。会议上存在真正的辩论,而且都是从事实和道理两方面各自立论,以争取公民的支持为上,很有雅典公民大会的韵味。公元前451年的那次会议上,虽然叙拉古的公民面对的是过去的敌人,但他们仍表现了作为民主政治下公民的一般素质:遵守希腊人的习惯,不仅让求庇者得到保护,还送他一笔生活费,但为未来安全计,禁止他再返回西西里。据狄奥多鲁斯记载,当后一种意见提出时,“民众异口同声地高呼,他们应当赦免祈援人”③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92,4.。如果是否接受某个陷入窘境的祈援人(虽然此人是叙拉古过去的敌人)的事务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并通过非常具体的决议,则有关宣战、媾和和立法等重大的事项,理当也由公民大会负责,尽管相关会议可能也是在事发时临时召开。公元前413年,叙拉古人开会商讨雅典战俘的命运。据狄奥多鲁斯,当天的会上有4个人先后发言。首先发言的是人民领袖狄奥克莱斯,他主张处死被俘的雅典将军们,将战俘发配采石场劳动,在那里将他们折磨至死,雅典的盟友则一律卖为奴隶。随后赫摩克拉泰斯发言,希望仁慈处理战俘。但他的意见遭到民众反对,被轰下了台。随后发言的是一位年事颇高(据称连路都走不动)的老人尼科劳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保卫叙拉古时阵亡,众人以为他肯定会支持狄奥克莱斯的意见,不料他也主张善待敌人,且一度赢得叙拉古人支持。最后是斯巴达人古利普斯发言。也许出于对统帅的尊重,公民大会最终通过了古利普斯的意见。④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ii,19,4-13,33,1.修昔底德不曾记载叙拉古公民大会的辩论。保存在狄奥多鲁斯著作中的叙述,尤其是尼科劳斯和古利普斯的演说,基本可以肯定是狄奥多鲁斯或者他的史料来源蒂麦乌斯的伪造,但公民大会上发生过辩论,而且类似尼科劳斯这样的人都可以发言,以及会议上出现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体现了叙拉古公民大会议事机制的成熟。
从叙拉古的制度来看,那里应当有公民大会的定期集会,起码每年选举官员需要由公民大会负责。这些官员包括国内的行政和司法官员,还有将军等。对于官员的监督,可能也由公民大会进行。在叙拉古历史上,不止一个将军因作战不力受到公民大会制裁,有些甚至被流放。⑤公元前453年,法伊鲁斯当选水师统帅,受命镇压第勒尼安海海盗,但未能达到民众愿望,回国后受审并被判处流放;公元前414年,因对雅典作战不利,多名叙拉古将军被罢免。见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88;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6,103.民主政治时期,叙拉古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橄榄叶放逐法(petalism)。约公元前454年,廷达利翁企图建立僭主政治,阴谋被挫败,廷达利翁被处死。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叙拉古民众吸收雅典经验,创立了橄榄叶放逐法。据狄奥多鲁斯:
在雅典人中,每个人是把他认为最有可能对同胞建立僭主政治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在叙拉古,势力最大的公民的名字会被写在橄榄树叶(petalon)上。清点树叶后,无论是谁得到了最多的票数,就会被流放5年。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能在各自的城邦中打压那些最为强势的人的傲慢,因为他们寻求达到的一般目标,并不是惩罚那些破坏了法律的人,而毋宁是遏制这些人的影响和自我膨胀。……但在叙拉古,它很快就因为下述原因被取消。由于那些担任最高职位的人被流放,最有责任感的公民——那些因其个人完美因而能够创造大量政体变革的人——因担心这个法律而不再参与公共事务。……与他们相反,那些极无原则、极其荒唐的公民,则专注于公共事务,将民众导向混乱和革命……由于这些原因,叙拉古人改变了主意,仅在使用很短时间后,就取消了这个法律。①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87,1-5.
狄奥多鲁斯的记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引入放逐法的意图:对付那些影响过大、意图在叙拉古建立僭主政治的人。但具体做法与雅典有些不同。投票时使用的是橄榄树叶,放逐期限为5年。不过与雅典长期利用陶片放逐法相反,这个法律在叙拉古使用的效果不佳:上层拒绝再参与国家管理,并且造成了叙拉古政治和国家管理的混乱,因此很快被取消。同样的意图所引入的类似的法律,同样在希腊城邦中实行,而且惩罚的力度似乎还较雅典轻微(流放期5年),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值得思考。要说叙拉古人完全不负责任胡乱投票,似乎并不合理。至少他们在处置杜凯提乌斯的问题上,表现相当理性。对雅典战俘的处置,也不是全无道理。为何在这个问题上,反而遭遇失败?狄奥多鲁斯没有给予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具体说明法律到底使用了多长时间。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一种可能是该法设计不如雅典那样完善,如最低投票数限制等,确保其利剑高悬却不经常使用,而是过于频繁地使用,导致上层人人自危,集体退出政治生活,迫使平民取消该法。②George Grote,History ofGreece,vol.7,pp.121-122.但鲁特认为正好相反,投票始终被富人控制,以对付那些试图通过支持人民夺取权力的领袖们。见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p.147-148.另一种可能,是另有替代法律,因为在取消了这个法律后,叙拉古民主政治的运作似乎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在该法取消后至少延续了30年以上(如果是5年内该法被取消,则应在公元前449年前后)。由此推测,或许叙拉古人有了更好的手段来维护民主政治。而取代这个法律的,可能就是叙拉古存在的一个类似雅典非法提案法的一道法律:演说人不得在会上提出与现行法律违背的新法,否则会遭遇主持人罚款。公元前406年,因阿克拉加斯被迦太基人攻陷,西西里的希腊人一片惊慌。在叙拉古公民大会上,当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狄奥尼修斯开始发言,指控援助阿克拉加斯的将军们叛国,要求叙拉古人抛弃他们一贯的做法,直接把将军们处死。此时主持会议的官员以他的提议非法为由,对他加以罚款。但富翁菲利斯图斯走上前来支付了罚款,并承诺支付当天所有的罚款,支持狄奥尼修斯继续发言。于是狄奥尼修斯继续指控将军们叛国,号召叙拉古人选举受到欢迎而且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上层阶级有寡头倾向的富有公民为将军。③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ii,91,3-5.由于当时叙拉古和西西里的确处在危机之中,狄奥尼修斯的演说达到了目的,他从此一步步走上了僭主之路。可以设想,在此之前,叙拉古人肯定认真执行着这个法律,从而有效避免了非法行为和僭主政治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橄榄叶流放法的短命和雅典陶片放逐法的被取消,可能都是因为有了更有效的替代手段,而非全是法律本身的问题。④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71,pp.86-87.
就公民大会的运作而论,叙拉古的模式与其他民主制城邦差别不大。我们了解到的有限的几次会议,基本都是问题被提交到公民大会后,有所准备的人会在讲坛上发言,提出处理意见。无论是狄奥克莱斯,还是赫摩克拉泰斯,都需要通过自己的演说说服公民。在上文提到的有关杜凯提乌斯和雅典战俘命运的问题上,都出现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意见。能够在关键时刻发表意见的演说家,即所谓的人民领袖,在叙拉古很有市场。那个主张严厉处置雅典战俘的狄奥克莱斯,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我们还知道,战胜雅典后叙拉古政治进一步民主化,说服叙拉古人以抽签的方式选举官员、组建立法委员会改造叙拉古的政治制度、颁布法律的,就是狄奥克莱斯。这次的变革,也被亚里士多德视为叙拉古由公民政体转向民主政治的标志。①Aristotle,Politics,1304a27-29;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ii,34,6.但狄奥多鲁斯随后有关立法家及其立法的介绍,表明他把立法家狄奥克莱斯和古风时代另外一位同名的立法家完全弄混淆了。在这样的会议上,偶尔也会有尼科劳斯那样的人出面发言,暗示只要内容不违背法律,辩论会相当开放和自由。但如果违背法律,则可能被罚款。公元前415年,当雅典即将远征西西里的消息满天飞的时候,叙拉古人举行公民大会进行商讨。赫摩克拉泰斯首先发言,要求叙拉古人做好准备,以防备可能发生的入侵。但因所有消息都未得证实,在他之后,叙拉古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些人坚持认为,雅典人根本不会来,所有报道都是假的。另一些人认为,即使他们(雅典人)真的来了,他们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可以加倍报复。还有些人则相当鄙薄地把这件事情变成了讽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对民众最有影响的演说家阿泰纳戈拉斯发表了他的意见,认为雅典人不大可能会真的到西西里来。即使来了,西西里也有足够的资源对抗他们。修昔底德显然认为此人胡说八道,因为此前他刚刚叙述了雅典人的战争准备和舰队的出发。阿泰纳戈拉斯的意见影响了一批人。眼看会议可能在辩论中无果而终,一位将军走上前来,决定不再邀请任何人发言,自己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无论消息真假,都需要就战争做一些必要准备,同时派人到其他城市打探消息和联络。他的演说虽然简短,但具有明显的效果。“在将军说了上述话之后,叙拉古人散会了”②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2-41.。
修昔底德记载的这次公民大会,似乎与雅典或者叙拉古的其他公民大会并无本质不同,而且会上的辩论相当自由和开放。让人惊异的,是最后那位将军的举动。他似乎完全忽视了会议主持人的权力,走上前来终止了辩论,并且自己发言,显得相当权威。但他的意见,明显是最为合理的:进行必要的准备,派人出去打探消息,因此得到了叙拉古人的认同。这倒应了伯里克利在赞颂雅典民主政治时所说的话:“虽然我们在私人交往中避免开罪于人,但由于敬畏的畏惧感,我们避免不守法度,因为我们服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服从法律。”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i,37.修昔底德也曾评论,叙拉古人所以能够击败雅典入侵军,是因为他们与雅典人性格最为相似,④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ii,96,5.暗示叙拉古公民的性情,总体上与雅典公民相近。如果雅典公民大会一般来说文明和有序,那叙拉古的公民大会是否也应当表现出同样的倾向?
对于叙拉古的其他制度,我们的了解少得多。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将军。他们的数量在不同时期似乎有所不同,应当和雅典将军一样可以连选连任。赫摩克拉泰斯提到,与雅典人最初的交战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叙拉古人缺乏战争经验,另一个原因是将军太多,有15人,造成了混乱。所以他建议减少将军的数量,授予将军更大的权力。叙拉古人赞同了赫摩克拉泰斯的建议,当年只选举了3名将军。考虑到叙拉古也有水师,而且力量比较强,那里应当也有水师将领,可能是某一个将军担任而不是另外指定。公元前453年,为镇压第勒尼安海的海盗,叙拉古人任命法伊鲁斯为水师统领。但他作战不力,被阿佩莱斯取代。后者成功地捣毁了海盗的老巢并夺得大量战利品。僭主狄奥尼修斯时代,水师统领长期由僭主的弟弟或亲属担任。⑤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88,4-5.关于狄奥尼修斯时代的水师统帅,见D.M.Lewis,“Sicily,413-368 B.C.,”in John Boardman et al,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pp.120-154.因此,叙拉古的将军可能既有统领陆军的,也有指挥水师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应当享有全权,但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当叙拉古人认为法伊鲁斯未能完成他的使命时,就以受贿名义判处他流放。在对外事务上,将军明显也有相当大的权威。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除演说家和普通公民外,将军最多,其中赫摩克拉泰斯在不同场合做过多次发言。在公元前415年雅典入侵前夕的那次公民大会上,最后是一位将军终止了会议的讨论,让自己的建议得到通过后散会。
叙拉古似乎没有专门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的议事会,主持会议和提交议案的似乎是某种官员。当杜凯提乌斯在广场寻求叙拉古人庇护时,召开公民大会的就是官员;公元前406年,当狄奥尼修斯提出违法建议时,对他罚款的,还是官员。然而狄奥多鲁斯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些官员,有多少人。
结 语
在近60年的时间里,叙拉古民主政治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考验。首先,成功解决了僭主时代大规模没收、移民和再分配留下的后遗症,实现了统治的稳定;其次,挫败了廷达利翁建立僭主政治的企图,平定了当地居民西凯尔人的暴动;最后,也是最大的成功,是挫败了雅典发动的大规模入侵,将民主政治推进了一步。虽然在雅典人的围攻面前,叙拉古人一度表现软弱,但在得到斯巴达人援助后,顶住了雅典前后两拨大军的攻击,使入侵者全军覆没。正是在民主政治存续期间,西西里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繁荣和稳定的时期,哲学、建筑、文学、史学和艺术的发展,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哲学上有恩培多克莱;修辞学除传说中的科拉克斯和特西亚斯外,有莱翁提尼的高尔吉亚;史学家如菲利斯图斯成长于此时。①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7,pp.126-127.修昔底德在总结叙拉古人能够击败雅典大军的根本原因时,认为那是因为叙拉古人与雅典人最为相像。战争期间叙拉古人的某些做法,例如以公民大会上的辩论决定战争与和平,随时撤换将军,依靠海军赢得战争胜利,拒不听从古利普斯的命令,私下处死了雅典将军尼奇亚斯和德摩斯提尼②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i,86,2.等,很有雅典公民大会的“风范”。
但是,叙拉古毕竟不是雅典。在叙拉古,将军和官员们似乎拥有更大的权威。对于将军和官员们的命令,尤其是像赫摩克拉泰斯那样拥有经验和权威的将领的意见,叙拉古人表现得相对顺从。公元前415年的那次公民大会上,将军居然没有要求表决,直接就解散了公民大会;当年冬天,根据赫摩克拉泰斯的提议,叙拉古人取消了15将军制度,另选举3名将军指挥战争。对如此重大的决策,似乎没有进行严肃的辩论,“叙拉古人听了他的发言,投票决定一切照他的建议办,并选出了3位将军”,其中包括赫摩克拉泰斯本人。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72,1-73,1.公元前405年,老狄奥尼修斯公然违背法律,在菲利斯图斯支持下,在公民大会上公开指责其他将军,之后利用叙拉古人的支持,让自己先是成为了全权将军,后来成为了叙拉古僭主。④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History,xiii,91,1-96,3.遗憾的是,老狄奥尼修斯没有终结迦太基的入侵,却基本埋葬了运行60年的叙拉古民主制度。他的阴谋之所以得逞,固然有迦太基威胁需要一个强有力领袖的因素,但也与叙拉古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有关:叙拉古人的多数是农民,如亚里士多德注意到的,他们对管理城邦的热情,不如雅典人那么积极。而城邦政治的正常运作,特别是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转,需要公民方面的积极参与。雅典民主政治后来的衰亡,是“因为在希腊化世界变化了的条件下,德摩斯没有兴趣去运行它了”⑤P.J.Rhodes,“Athenian Democracy after 403 BC,”The Classical Journal,vol.75,No.4(Apr.-May,1980),p.323.。叙拉古公民大会可能没有定期集会的制度,公民大会讨论的问题,大多也和战争与和平等大事有关,日常管理,很可能落在官员们手中,让它的民主政治尽显温和特性。尽管如此,它并不影响叙拉古的民主像底比斯、阿尔哥斯等城邦一样,成为古代希腊世界民主政治的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