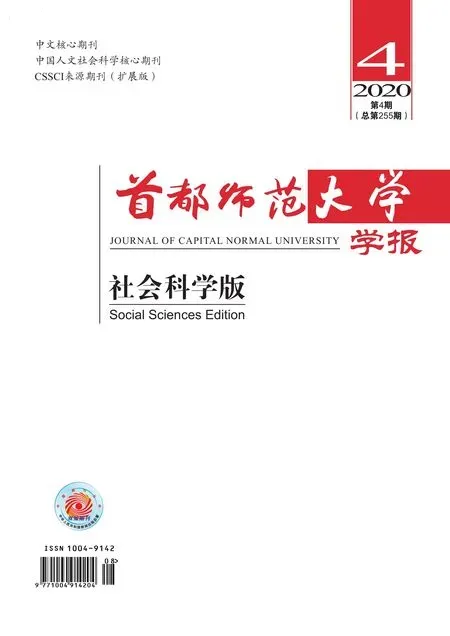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贵族传统
陈 超
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制性质的争论,也自然是史学界关心的重点。摩根·汉森、西格内特和奥斯瓦尔德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民主制的一些制度特征,如官员的轮番为治、有限权力、短任期、抽签选举等,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得到极大的发展,①Charles Hignett,A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Clarendon Press,1952,p.215.雅典民主制随之演化到最激烈的形态——“激进民主制”,民众的权力大到没有界限、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人民主权”的时代。②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and Ideology,trans.by J.A.Crook,Oxford and New York:Blackwell,1991,p.68,pp.150-152;Martin Ostwald,From Popular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Law,Society and Polit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类似的评价和批评自古有之。例如,修昔底德便指出,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政坛便被一群庸碌无能之辈占据;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trans.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2.65.10.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如未特别指出,皆引自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雅典政治在伯里克利时代便已经发生变化,海军势力日益主导城邦政治,大众逐渐掌控全部的政治权力;①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trans.by H.Rackha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27.1.色诺芬则借苏格拉底之口称,雅典公民大会中,漂洗工、补鞋匠、泥瓦匠、铁匠、农人、商人以及贩夫走卒占大多数,他们掌握大会的风向,大肆嘲讽精英政治人物;②Xenophon,Memorabilia,trans.by O.J.Tod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3.7.6-7.在他笔下,民众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③Xenophon,Hellenica,vol.1,trans.by C.L.Brown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8,1.7.12.古人的批评与近代西方政治精英的反民主制倾向相结合,便诞生了将雅典民主制视为“激进民主制”的学术传统。④Paul C.Millet,“Mogens Hansen and the Label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in Polis&Politics: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History:Presented to Mogens Herman Hansen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August 20,2000,ed.by Thomas Heine Nielsen and Lene Rubinstein,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00,p.344.
然而,这样的观点是否成立?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制是否称得上激进,或更具体地说,此时的雅典民众是否已经完全掌握政治权力,形成对贵族精英的压倒性优势?这需要更为全面和切实的考察。本文将着力讨论雅典政治中的民众领袖、政治组织以及政治话语等诸方面,说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并未如上述古代作家和当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占据全面的上风。相反,古风时期形成的贵族政治传统在民主政治中仍有相当的影响,贵族精英在民主政治中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此时的雅典民主政治并非纯粹的“激进民主制”,而是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期,新的政治制度虽然已经很发达,但旧的贵族传统仍有相当影响,新因素与旧成分相互合作也相互冲突,共同影响了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政治。
一、民众领袖与贵族政治传统
仅就制度层面而言,从公元前462年的埃菲阿尔特斯改革开始到伯里克利离世,雅典的民主制不断成长。⑤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24.这一时期雅典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公民法庭的发展;对陪审员和其他平民官员发放津贴;取消或者降低担任官职的财产门槛;大部分的官职选任采用抽签制;严格限制官员的权力;民众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公民法庭完全掌握国家主权。⑥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p.215.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民众的权力增长迅速。但这并不能说明此时的雅典民主制是“激进民主制”,雅典民众的权力已经处于空前绝后的巅峰,更不意味着贵族全面失去影响。事实上,古典时期雅典的政治文化、政治组织等领域都是在贵族政治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故而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中贵族的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相反,许多传统的因素得以保存。通过对雅典政治中的民众领袖、政治组织和政治话语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政治,更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就法律而言是民主政体,但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治理方式偏向寡头统治”⑦Aristotle,Politics,trans.by H.Rackha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4,1292 b 10-17.。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民众领袖与贵族政治传统的关系。民众领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不可或缺,同时也深受制度的制约,被视为纯然是雅典直接民主制的产物。⑧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ast&Present,no.21,1962,p.16.然而,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民众领袖发挥着超乎民主制度之外的作用,与贵族政体中的“统治者”扮演相似的角色。具体来说,虽然伯里克利等民众领袖往往与所谓“极端民主制”挂上钩,但详细考察可知,他们实际上出身于名门贵族。尤其伯里克利,其母系可以追溯到大名鼎鼎的阿尔克麦翁家族。他的为政方式也带有贵族政治的传统与痕迹,颇能体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民主政治“治理方式偏向寡头统治”的特征。故而,同时代的史家修昔底德称他是雅典的“第一公民”,称雅典政治体制只是“名义上是民主制,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①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trans.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2.65.9.
伯里克利“第一公民”的称号并非徒有虚名。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政敌老修昔底德遭到放逐之后,他在雅典政坛就再没有了敌手,连续十几年担任将军一职。借助将军一职,伯里克利持续在雅典政治中发挥影响。由于他对城邦政治举足轻重,同时代的喜剧诗人特勒克雷德斯和克拉提努斯将他视为当代的僭主、人间的宙斯,能力强大、无人能敌。②James F.McGlew,“Comic Pericles,”in Sian Lewis,ed.,Ancient Tyrann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p.165.喜剧诗人的话并非纯粹的调侃。公元前446年伯里克利极有可能通过贿赂,成功让斯巴达的年轻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从厄硫西斯退兵,使伯罗奔尼撒联军无功而返,避免了战争的爆发,维护了雅典的利益。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1.114.2;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3,trans.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1,6.16.3.事后,伯里克利向公民大会提交报告,其中包括10塔伦特所谓“不时之需”的花销。民众很爽快地同意了这笔款项,甚至根本不去调查所谓“不时之需”指的是什么。④Plutarch,Pericles,in Plutarch’s Lives,vol.3,trans.by B.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23.1.在该事件的过程中,伯里克利动用了超出民主制度的权力,利用了其贵族身份带来的政治关系。但民众并不反感此举,反而认可了他超凡的地位。斯巴达人也深知伯里克利对雅典政治的重要性,因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打之前,他们想要借口驱逐被复仇女神诅咒者的名义,在开战前将伯里克利赶出雅典,试图以此改变战局。⑤伯里克利的母系家属曾在扑灭库伦的僭主阴谋时触犯了复仇女神。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1.126.1-127.2.由此可见,伯里克利对雅典政治的影响确实强大。
不过,伯里克利的个人作用也不应该被无限夸大,将之视为雅典的帝王,做脱离时代背景的评价。例如,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前期讨好民众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在打败自己所有的政敌后,他便将之前那种轻快明亮、和风细雨的蛊惑民众之术,转变成了贵族式的、王政式的政治。⑥Plutarch,Pericles,15.2.这显然是将伯里克利想象为罗马元首式的统治者。事实上,伯里克利的伟大之处,并非由于他享有帝王般的权力,而是在于他能够将相对传统和贵族式的政治风格同民主的政治体制统一起来,使二者达到某种平衡,“凭借其名望、才智以及清正廉洁,能够以自由的方式约束人民,不是被人民领导,而是领导人民”⑦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2.65.8.,在促进民主政治和城邦福祉的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领导威望。
例如,雅典卫城山门、帕特农神庙等若干重大工程的修建过程,既离不开民主政体的运转,也少不了伯里克利的领导。毫无疑问,从制度的层面看,大型建筑的修建离不开民主政体的运转,远非伯里克利或其他民众领袖一人可以包办。同时代的材料也表明,在公元前450年之后,雅典就不再有个人捐献的建筑,所谓“伯里克利的伟大建筑”,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完成的,所有大型公共建筑中,仅有卫城南坡的音乐厅和伯里克利有切实的关系。⑧Lisa Kallet,“Demos Tyrannos:Wealth,Power and Economic Patronage,”in Kathryn A.Morgan,ed.,Popular Tyranny:Sovereign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ncient Greec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3,p.128.假设伯里克利想要发起某项工程,他也必须利用民主制度,在公民大会中说服民众,让公民大会通过法令推动剩余的工作。并且,他能做的仅限于此,至于样式、风格和建筑师等细节,则由议事会定夺,具体的实施则再交给公民大会选出来的专门委员会。⑨Vincent Azoulay,Pericles of Ath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41.这是因为,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中,作为将军和政治家的伯里克利不是帝王般的元首,没有机会独掌大权。他的权力来自公民大会,处在民主政体的各种制约之中。⑩Azoulay,Pericles of Athens,pp.146-148.某项政策最终之被推行和落实,很大程度要依靠民主政体的各个职能部门的运行。
然而,伯里克利这样的民众领袖的建议和领导也非常重要。例如,伯里克利便曾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拯救雅典的公共建筑工程。事情的起因是伯里克利的政敌将修建大型公共建筑视为他个人意志的体现,抨击他挥霍无度,浪费公帑。①Plutarch,Pericles,14.1.受到这项指责,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向民众发问,是否他们也觉得开销太大。民众也随声抱怨,认为开销过大。于是,伯里克利便称愿意自掏腰包修建公共建筑,但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民众闻之,立即表示他可以随意从国库中取钱修建公共建筑,不用吝啬钱财。②Plutarch,Pericles,14.1-2.伯里克利机智地化被动为主动,而且手段也非常富有智慧,利用民众的骄傲和自信,以及不愿个人风头盖过民众集体的心理,领导人民而不是被人民领导,成功挫败政敌的企图。伯里克利的保驾护航对公共建筑的修建非常关键,使公共建筑项目得以走出危机,得以继续进行。因此,即便这些公共建筑最终没有被冠以伯里克利的名字,更非伯里克利一手主持完成的,它们也多多少少是在伯里克利的建议和领导下完成的。
雅典的民众领袖未必都如伯里克利一样耀眼和举足轻重,但他们都在雅典的内政、外交等诸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且其作用或多或少是凌驾于民主政体之上的。他的权力和影响虽然不能与帝王相比拟,但却也超出民主政体的框架,有时甚至像古风时期的贵族那样,通过行贿和私人关系网络等超越民主制度的手段影响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这些证据都表明,至少在伯里克利时代,民众领袖身上保留了不少贵族政治的传统。
二、贵族结社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伯里克利去世之后,雅典政治家的阶层出身以及政治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政治人物都不再出身于传统旧贵族家庭,而是出身于在公元前5世纪迅速致富的新贵家庭;③W.Robert 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71,pp.153-155;P.J.Rhodes,“Oligarchs in Athens,”in Roger Brock and Stephen Hodkinson,ed.,Alternatives to Athens:Varieti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Greec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31.同时,带有贵族烙印的政治风格也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讨好民众的政治风气;这种政治风气在雅典政坛取得压倒性优势,使得想要从政的贵族青年也必须采取相似的风格。④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p.139-143.这种观点与古人对雅典政治的评价遥相呼应:修昔底德便批评平庸的政治家相互竞争,毫无底线地讨好民众,将国家大事也交给民众随意摆布,结果给雅典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⑤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2.65.10.阿里斯多芬则重点批评政治家克吕昂,通过戏拟的方式将他比作民众的奴隶,嘲笑他为了争夺民众的欢心,不断地与一名香肠小贩互相竞赛谁更下流无耻。⑥Aristophanes,Knights,in Aristophanes,vol.1,trans.by B.B.Rog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4,730ff.但众多史料表明,伯里克利之后的政治家虽然表现得更加讨好民众,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旧贵族的势力与传统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旧贵族家庭的子弟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伯里克利的养子亚西比得就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坛很活跃,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他出身名门望族,家世之显赫更胜伯里克利。其次,伯里克利之后政坛风气或许有所变化,但并非此时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或者道德水平退化,更不意味着传统的旧贵族因素丧失吸引力甚至完全消失。相反,雅典政治中的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保留了不少贵族精英的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贵族结社(hetaireiai)。
贵族结社历史悠久,起源于希腊古风时期的贵族社交宴饮,但它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仍旧相当活跃。阿里斯多芬的《马蜂》便生动呈现了它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剧中,反感雅典民主制的儿子说要带对民主制甘之如饴的父亲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去会餐,去会饮,去看演出”①Aristophanes,Wasps,in Aristophanes,vol.1,1005.。儿子“教育”父亲的过程,有着非常强的象征性,仿佛是阿里斯多芬带着雅典的下层人民参观雅典上层社会的生活。儿子要求父亲脱去他在行伍中的破旧衣衫,穿上华美的波斯长袍,学习上层社会的言谈举止,并称雅典重要的政治人物会参加会饮。这些上层精英,有不少都是政坛的大人物,如克吕昂、安提丰和“弗吕尼库斯的朋友们”②Aristophanes,Wasps,1122-1140,1176-1217,1220,1301-1302.。他们的政治立场或许不尽相同,但常常出席相同的宴饮故而彼此熟识,并围绕某些政治人物结成紧密的圈子。
然而,古风时代的结社组织为什么能在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中影响深远?首先,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步调不一致,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的政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但是“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其政治组织与社会关系仍旧保留有鲜明的贵族传统特征。其次,贵族结社恰好能够满足直接民主制中民众领袖的政治需求。正如芬利指出的,雅典的民众领袖在直接民主制中是独自战斗的,没有任何来自制度内的帮助和援手。③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p.9-10.并且,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决议都需要在公民大会中讨论,而每一次公民大会的人员组成以及大众心理都会发生变化。④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p.9-10.一旦民众领袖离开雅典,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参加公民大会,他对政治的影响就会大幅降低。因此,雅典的政治精英需要某种民主制之外的政治组织进行政治动员,而结社恰好能满足该需求。因此,雅典的政治精英都有大量的朋友,并参加这些朋友们组成的贵族结社,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确保政策连贯性。再次,结社并没有鲜明的反民主制的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并不被民众所敌视。贵族精英聚在一起未必都是讨论政治,更不是每天都在密谋推翻民主制,他们也可能是讨论个人遇到的问题,甚至可能只是为了宴饮享乐。⑤Oswyn Murray,“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Democracy and the Drinking Group,”in Oswyn Murray,ed.,Sympotica:a Symposium on the Sympos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150-151.因此,在修昔底德看来,贵族结社虽然很早就在雅典城中存在,但其目的是解决诉讼和行政中的问题。⑥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4,trans.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8.54.4.因为贵族结社未必都是政治性的,更未必都是反民主制的,故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通民众对贵族结社抱有相当宽容的心态。⑦Murray,“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p.150.
但民众对贵族结社的宽容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415年,以亚西比得为中心的政治精英结社遭受打击。是年,雅典爆发两起渎神案,即破坏赫尔墨斯石柱案和模仿密仪案。⑧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3,6.27.1-28.2.赫尔墨斯石柱主体为长方体,上部为赫尔墨斯的头像,立于家门口和道路两旁,以起到保护旅行者的作用。密仪是指雅典人在厄硫西斯举行的祭祀徳墨忒尔和她的女儿的密仪。由于密仪的仪式属于机密,只有加入密仪崇拜的人才能知晓,模仿密仪或者向外人展示密仪,都被认为是渎神的。民众认为,这两起案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民主事件。因为当时公民大会刚刚决议要远征西西里,而赫尔墨斯是保佑旅行者的神,因此民众将破坏赫尔墨斯石柱案视为噩兆,陷入深深的恐慌,并将整个事件视为推翻民主制的阴谋。⑨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3,6.27.3.在追查的过程中,亚西比得的朋友大量牵涉其中,⑩Plutarch,Alcibiades,in Plutarch’s Lives,vol.4,trans.by B.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19.1.因此他也被指控参与了模仿密仪案,并被视为阴谋颠覆民主制的背后主使。当时他已经被选为远征西西里的将军,在军队的影响极大。他的政敌害怕他在人民和军队中的巨大影响力,想办法让他率军远征。亚西比得离开雅典后,他的政敌立即起诉他,勒令他回国接受审判。他见情势不对,便在归国途中潜逃了。①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3,6.28.1-29.3,53.1,61.6-7.
亚西比得或许参与了两桩渎神案,但是渎神案背后未必有推翻民主制的阴谋。修昔底德指出,阴谋推翻民主制的罪名是政敌的刻意栽赃,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民众领袖的地位,不除掉亚西比得实难如愿。②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3,6.28.2.同时,根据奥斯温·穆瑞的研究,当时的模仿密仪事件不止一起,而且每次的参与者都不同,模仿密仪者和破坏赫尔墨斯立柱的人也没有太多交集。③Murray,“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pp.154-155.换言之,私下的渎神是当时的常见现象,很难说其背后有什么意识形态背景或政治企图,两桩渎神案与推翻民主制的阴谋也并无真正的关系。之所以亚西比得参与的渎神案会背上反民主的罪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家之间的斗争与栽赃。不过,出乎始作俑者意料的是,民众很快将对渎神案的追查变成对政治家猎巫般的追杀,政治精英结社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开始负面化。
不过即便如此,雅典的精英政治结社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在雅典政治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成为左右雅典政坛的重要力量。例如公元前411年初,亚西比得与雅典海军上层中有权势者和三列桨战舰舰长接触,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政体、召自己回国。④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4,8.47.2-48.1.这些权贵组成的临时性的结社,最终推翻了雅典运行近百年的民主政体。公元前405年到公元前404年,以克里提亚斯为核心的政治精英结社在雅典即将战败的时候大肆操控雅典的内政外交,迫使雅典人再度建立寡头制。⑤Lysias,Orations,trans.by W.R.M.Lamb,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12.43-44.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亚西比得这样的旧贵族身在结社中心,尼基阿斯这样的新贵也是政治结社的重要成员。虽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将尼基阿斯归为“贵族绅士”(kalos kagathos)⑥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28.5.,但事实上他和克吕昂一样,都是通过手工业致富的所谓“新贵”,而非伯里克利、亚西比得或克里提亚斯等传统土地贵族。⑦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403.Plutarch,Nicias,in Plutarch’s Lives,vol.3,trans.by B.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4.2.据载,尼基阿斯拥有一千名银矿奴隶用以出租,每天每位奴隶可以为他赚一奥波尔的租金。⑧Xenophon,Ways and Means,in Scripta Minora,trans.by E.C.Marcha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4.14.巨大的财富成为他从政的资本,他也因此成为伯里克利离世后雅典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成为重要的政治结社的核心人物。普鲁塔克称,他和亚西比得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要分裂整个雅典城邦。⑨Plutarch,Nicias,11.3.虽然该说法不无夸张,但也足见以亚西比得为中心的结社多么有影响。在二者相争之时,另一位颇有影响的民众领袖——虽然修昔底德称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⑩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4,8.73.3.——希波珀鲁斯试图坐收渔利,结果两人联手将他用陶片放逐法赶出了雅典。⑪Plutarch,Alcibiades,13.3-4.这说明政治精英之间的结社是灵活多变不稳定的。并且,更出乎意料的是,吕西阿斯的弟弟优克拉特斯在公元前415年参与了破坏赫尔墨斯神像的渎神事件。⑫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p.404.渎神案的参与者大多与亚西比得关系密切,由此可知,优克拉特斯即便不是亚西比得的密友,也与他颇为熟识。这也说明,贵族结社的成员范围是广泛而复杂的,彼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贵族结社在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逐渐受到怀疑和限制。因为虽然贵族之间的结社并不具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更不一定是反民主制的,但是这种组织形式毕竟是民主制度之外的力量。只要贵族之间团结起来,打定主意,便可以将贵族结社转化为推翻民主制的力量。故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最后几年,雅典民众便开始敌视这一组织形式。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民不但认识到了贵族结社和组织对民主制的危害,更是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组织结社(hetairikon),否则便是图谋推翻民主制、背叛城邦。①Hyperides,In Defense of Euxenippus,in Minor Attic Orators,vol.2,ed.and trans.by J.O.Burt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8.这反过来也说明,贵族结社在雅典政治中确确实实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朋友以及结社的鼎力相助对于政治家而言十分重要,不可或缺。②David Konstan,“Greek Friendship,”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17,no.1(1996),p.63.因而,即使在公元前4世纪,结社受到民众的怀疑和限制,柏拉图也称,“没有朋友(philoi androi)和伙伴(hetairoi),什么也办不成”,无法进行政治活动。③Plato,Epistle VII,in Timaeus,Critias,Cleitophon,Menexenus,Epistles,ed.and trans.by R.G.B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9,325 D.
三、贵族传统和民主政治文化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不但贵族的结社组织对雅典政治影响巨大,贵族的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是因为,虽然雅典的民主政体发展迅速,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相对缓慢,民众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并未取得对精英的压倒性优势。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政治话语中仍旧保留了大量贵族创造的词汇、话语和观念,甚至在葬礼演说和法庭演讲等民众占绝对优势的场域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首先,来看葬礼演说。古典学家罗厚指出,伯里克利在著名的国葬礼演说中为民主制辩护时,固然赞扬了许多雅典民主制的特征,如自由、平等、开放等,但也特别强调非成文法中体现的传统习俗和价值体系;同时,他承认雅典人之间实际上分化为若干阶层,认为有的人相对专注于政治生活,有的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活动;他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更多地限于私人生活领域,而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则主要以德性(arete)这一贵族传统概念为衡量标准,认为私人生活领域中每个个体拥有相等的权利,在公共政治领域中不同的人根据其德性的高低享有不同的权利;并且,伯里克利声称,不同于仅看重出身和财产的寡头制,民主制更加看重德性,卑微和穷困都不足以妨碍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实现其价值,换言之,民主制比寡头制更加体现以德性为准绳的贵族政体的原则与精神。④Nicole 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trans.by Alan Sherid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83-188.当然,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可能是修昔底德的建构,因而演说与其说体现伯里克利的观点,不如说体现对民主制持批判态度的修昔底德的看法。
其次,在公民法庭这样民众力量占据绝对上风,因而也应该最为体现民主精神的场域,贵族的传统价值体系依旧影响力巨大。⑤A.W.H.Adkins,Mo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Ancient Greece:from Homer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2,pp.119-126.例如,在吕西阿斯的第25篇演说辞中,演讲者在三十僭主当政时期选择留在城中支持寡头政体,因而被控意图推翻民主制。为了给自己辩驳,被告不但声称自己绝无支持寡头制的动机和理由,还向陪审团列举了自己为国家做的贡献,如五次装备战舰,四次参与海战,多次公益捐助等,并直言做这些事是为了让自己在人们心中更加“高贵”(agathos),进而在面临诉讼时占有优势。⑥Lysias,Orations,25.12-13.换言之,面对民众占主导的陪审法庭时,有寡头嫌疑的被告不但承认自己属于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agathoi),而且认为自己毫无疑问应该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样的想法不是权贵们的无知妄念,而是当时雅典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⑦Adkins,Mo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Ancient Greece,p.126.甚至,吕西阿斯在起诉三十僭主成员之一的艾拉斯托特涅斯时,不得不提请陪审团注意,虽然此人曾为城邦做过不少贡献,拥有德性(arete),但他对城邦的破坏更大,因而仍应遭受严厉惩罚。换言之,即便三十僭主成员这样的城邦公敌,如果他对城邦的破坏没那么大,而做的贡献足够多,雅典人仍有可能因为其高贵与德性,以及他曾对城邦行的善事而对他网开一面。①Adkins,Mo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Ancient Greece,p.125.这足见贵族传统和价值体系在雅典社会的影响多么深远。
雅典贵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不但影响了雅典社会,还塑形了雅典的城邦政治文化与民主意识形态,进而对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乃至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以反僭主传统为例。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便利用酒歌(soklia)纪念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两位英雄,称他们杀死了僭主,让雅典的法律变得平等。②Greek Lyric,vol.5,ed.and trans.by David A.Campbell,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86.这种用酒歌纪念诛杀僭主英雄的做法,很明显是贵族的专利,因为参加会饮是贵族的专利。而且酒歌是会饮中最后被演唱的诗歌形式,只有精英中最有才学的人才有资格吟唱。这种在酒歌中歌颂诛杀僭主者的传统,一直被保留到公元前5世纪末期。在阿里斯多芬的《马蜂》中,儿子带父亲参加贵族宴饮之前,还特意要父亲学会歌颂哈默迪乌斯的酒歌,要父亲将他当作克吕昂,他唱第一句,父亲接过来唱第二句。③Aristophanes,Wasps,1224-1226.这说明,酒歌唱和是贵族会饮中交流感情和思想的重要手段,反僭主的传统一直是贵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贵族们开始用酒歌赞颂诛杀僭主者的同时,克里斯提尼等人在市政广场树立了纪念诛杀僭主者的雕像,使诛杀僭主者的形象为全体雅典人所熟知,使诛杀僭主雕像成为城邦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雅典人还设立了祭祀诛杀僭主者的仪式,战争执政官负责每年在固定的时间向他们献祭牺牲;此外,雅典人还赋予了诛杀僭主者的直系后代各种特权,让他们有权享用城邦的公费食堂,有权免除赋税,有权在公共典礼中前排就坐。④Kurt A.Raaflaub,“Stick and Glue:The Function of Tyranny in Fifth-Century Athenian Democracy,”in Popular Tyranny:Sovereign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ncient Greece,ed.by Kathryn A.Morga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3,pp.63-66.通过一系列措施,民主政府成功将诛杀僭主转化为全城邦的意识形态,让反僭主的思想深入人心,使本来属于贵族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传统,成为全民所有的政治话语资源。不仅如此,反僭主话语还被用来规训和对抗贵族精英。普鲁塔克称,伯里克利最初并不愿意面对民众,更不愿意从政,因为他长得非常像雅典僭主庇希特拉图,而且出身名门显贵,这使得他一直害怕被民众视为潜在的僭主。也是因为这层原因,当他决心从政时便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的阵营,以洗脱自己的“僭主嫌疑”⑤Plutarch,Pericles,7.1-3.。饶是如此,伯里克利也时常被同时代的戏剧作家比喻成僭主。⑥Azoulay,Pericles of Athens,139.亚西比得更是一生都活在“僭主嫌疑”中。他被迫逃亡到斯巴达,名义上的罪名是渎神与试图推翻民众统治,但真正使他定罪的却是“不民主的违法生活方式”。亚西比得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据修昔底德记载,包括自私自利、违法乱纪、自命不凡等等。⑦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4,8.6.12.2,6.15.4,6.16.6.因此之故,早在西西里远征开始之前,雅典人就因亚西比得“渴望僭主制而敌视他”;雅典人下此结论的原因,不是因为亚西比得有任何具体的推翻民主制、建立僭主制的举措,而是因为他私下里的生活作风(epiteēdeuma)所带来的僭主嫌疑。⑧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3,6.15.4;Robin Seager,“Alcibiades and the Charge of Aiming at Tyranny,”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vol.16,no.1,1967,p.8.
由以上证据可见,属于雅典传统贵族精英的话语、词汇、价值观以及政治文化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城邦民主政治话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在最初构建自身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民主政治话语可供参考,只能在雅典贵族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自身。同时,贵族群体最初也乐于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平民化,以增强自身的支持力量。这使得贵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有的学者看来,“贵族的价值体系几乎没有遭到挑战”①M.M.Austin and Pierre Vidal-Naquet,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trans.by M.M.Aust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p.15-16.。这一说法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贵族精英的政治传统和价值体系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民众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全面压倒或消解贵族的政治传统。
结 论
当前学界普遍将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视为“激进民主制”,认为民众在该阶段的雅典政治生活中掌握绝对的权威,贵族的势力与传统受到全面的压制和排挤。然而,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贵族政治传统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即便是伯里克利这样被视为“激进民主制”代表性人物的政治家,其统治方式仍有许多贵族传统的痕迹。雅典政治家之间的组织和策动,也非常依赖结社这一贵族政治组织形式。此外,贵族的传统政治话语、符号和政治文化,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雅典已有的贵族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和构建而来的。固然,如果与当时地中海世界主流的王权和贵族政治横向比较,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无疑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但是,如果按照雅典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纵向比较,我们会发现,看似激进的雅典民主政治其实保存了不少贵族政治的传统。因此,贵族政治的传统与势力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激进”与“温和”作为19世纪诞生的政治概念,用它们来描述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并不准确,②Millet,“Mogens Hansen and the Label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p.338,pp.344-349.不仅会带来概念上的错乱,还会窄化研究视野,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而且,“激进民主制”一词显然带有价值和道德判断的色彩,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厌恶雅典民主制的精英主义底色,而所谓的“激进”,也并非以古代历史的发展为标准,而是以19世纪末西方学术界的政治好恶为准绳。汉森等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学术传统,并结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论述,将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民主政治和“激进民主制”画上等号,多少有些不准确。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政体的论述,更多是抽象的演绎,而非具体分析或实指某一政体。③Richard Mulgan,“Aristotle’s Ananlysis of Oligarchy and Democracy,”in A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ed.by David Keyt,Oxford:Blackwell,1991,pp.307-308.他也从未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等同于“激进民主制”。相反,他在《雅典政制》中明确指出,公元前403年之后的雅典政治中,“民众的权力一直在增加,将自己变成了一切事务的主宰”④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41.2-3.。如是言之,如果让亚里士多德使用“激进”一词描述雅典政治,他肯定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激进”。至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如下说法,即“就法律而言是民主政体,但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治理方式偏向寡头统治”。换言之,此时的雅典政治,虽然就制度而言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直接民主制,但在政治的运行和实践中,仍保留了相当的贵族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