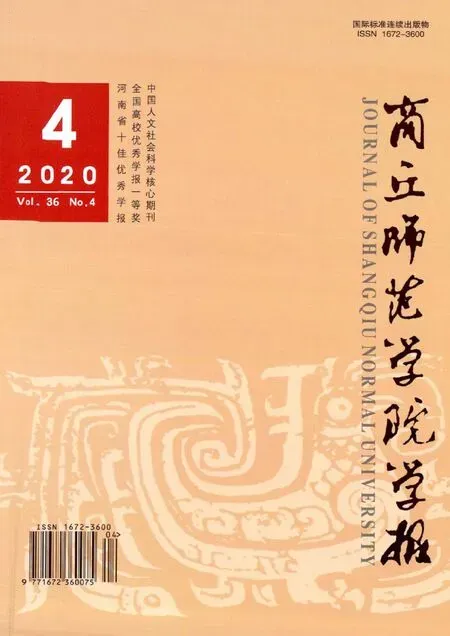“一题多体”
——对《文选》哀伤类作品文体形态的一种考察
赵 俭 杰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程千帆在《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中,通过比较陶渊明、王维、韩愈、王安石四篇同为桃源题材的诗歌,分析它们在诗歌主题、艺术形象、作品风格上的差异及原因[1]125。这是一种“同中见异”的比较思维,而比较思维分为“同中见异”和“异中见同”两种方式,前者便于考察个性,后者利于考察共性。受其启发,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一种可以称为“一题多体”的文体现象,即作家们采用不同文体表现相同主题的创作方法。这正是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来考察不同文体之间的共性及原因,以此探究不同文体得以交融互渗的可能性。
作为现存首部诗文总集的《昭明文选》(简称《文选》),收录的哀伤类作品(7篇哀伤赋、13首哀伤诗、3篇哀伤文)即以赋、诗、文三种文体表现一个哀伤主题,因而对于考察“一题多体”之文体现象具有典范意义。
一、篇幅、音律、构架的体制类同
体制是文体赖以建构的基本法式,不同文体有不同的体制规范,即“字句和篇幅的长短、音律的规范与变异、句子和篇章的构架”[2]6等形态差异。但《文选》哀伤赋、哀伤诗、哀伤文在篇幅、音律、构架的体制方面却有相似之处。
(一)篇幅
从字句和篇幅的长短看,哀伤赋的字句较多、篇幅较长;哀伤诗四言1首,余皆五言,篇幅不等,或仅8句,或达30余句;哀伤文字句较多,篇幅不短。
《文选》7篇哀伤赋,大致可分“序文”“正文”“重曰”三部分。其中江淹的2篇赋无序,其他5篇皆存,有自作与他作,交代写作缘起。司马相如《长门赋》4句序文,正文48句;向秀《思旧赋》8句序文,正文12句;潘岳《寡妇赋》6句序文,正文46句,重曰共20句;陆机《叹逝赋》5句序文,正文46句;潘岳《怀旧赋》4句序文,正文21句;江淹《恨赋》正文44句,《别赋》正文66句。
《文选》13首哀伤诗。其中嵇康《幽愤诗》篇幅最长,达86句;曹植《七哀诗》共16句;王粲《七哀诗》其一共20句,其二共18句;张载《七哀诗》其一共24句,其二共22句;潘岳《悼亡诗》其一共26句,其二共28句,其三共34句;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共26句;颜延之《拜陵庙作》共34句;谢朓《同谢咨议铜雀台诗》共8句;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共34句。
《文选》3篇哀伤文。其中潘岳《哀永逝文》没有序文,正文33句,重曰2句;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序文共8句,正文43句;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序文共8句,正文41句。
(二)音律
从音律的规范与变异看,《文选》7篇哀伤赋和3篇哀伤文中,《长门赋》《思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三赋一文,正文皆以骚赋特有之“兮”字为标志,分划节奏、调节音律;《叹逝赋》《怀旧赋》《恨赋》《别赋》等四篇骈赋,协韵可歌。可见,哀伤赋韵位固定、一般不换韵,通过句中或末尾虚词强化节奏、调整音律。另外两篇哀伤文,《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与《齐敬皇后哀策文》也有用韵。13首哀伤诗皆为古体,除《幽愤诗》为四言外,余皆五言,韵律和谐。
(三)架构
从句子和篇章的架构看,哀伤赋与哀伤诗皆句式整齐,对仗工整;哀伤文以四言为主,偶有骚体句,用“呜呼哀哉”分层。
《文选》7篇哀伤赋。《长门赋》之散句序文为后人所添,正文格式“XXX而XX兮,XXX而XX”,其中虚词多变,上下句多对仗,如“白鹤噭以哀号兮,孤雌跱于枯杨”[3]293。《思旧赋》序乃自作,以散句行,正文全为“XXX之XX兮,XXX于XX”,虚词包括“于、而、以、之、乎、其”,句式对仗,如“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3]296。《寡妇赋》序亦己作,全用散句,正文全为“XXX之XX兮,XXX之XX”,对仗严整,如“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难之匪忱”[3]300。另外,《哀永逝文》虽归为“文”,其实是“赋”,没有序文,正文句式有三:“XX兮XX,XX兮XX”与“XXX兮XX,XXX兮XX”和“XXX兮XXX,XXX兮XXX”。对仗工整,如“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与“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和“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3]1066。骚赋之条件有二:一是采用楚骚的文体形式,也就是以“兮”字句作为基本句式;二是明确用“赋”作为作品名称[4]96。据此推之,是为四篇骚赋。
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体制相似,序皆散句,正文大量“XXX之XX,XXX而XX”的六言句式,也有少量四言句式,如“仰睎归云,俯镜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和“弭节安怀,妙思天造。精浮神沧,忽在世表”[3]298。以虚词“而”“之”“于”“以”“其”绾结,而无语气词“兮”。江淹《恨赋》《别赋》,句式多变,大量四言、六言和少量“骚体”句型,四言句如“浊醪夕引,素琴晨张”,六言句如“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骚体句如“夏簟清兮昼不暮,钅工冬凝兮夜何长”[3]306。以此观之,是为四篇骈赋。
在13首哀伤诗中,除嵇康《幽愤诗》为四言外,余皆五言,结构不一。
《文选》3篇哀伤文,潘岳《哀永逝文》归为赋类,颜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与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之序文全是散句,正文以四言为主,偶有骚体句,每层以语气词“呜呼哀哉”结尾。
总之,《文选》哀伤赋、哀伤诗、哀伤文,字句和篇幅的长短都不相等,全部用韵,句式整齐,变化较少,且若去掉哀伤赋和哀伤文中的虚词,赋、文二体立即化作五言诗。可见,其时赋、诗、文三种文体的体制规范并未完全确立,同大于异。
二、语词、辞格、风格的语体同构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在文学作品中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和基本句型构成了文学语言的共核语言,这种共核语言表明各种文体之间异中有同,同大于异。但是,不同的文本语境要求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词、语法、语调,形成自身适用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由此构成一种文体特定的语体。”[2]9反之可见,《文选》哀伤类作品在同一主题的规约下,可以相同或相近的语词、辞格构成基本一致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进而形成类似的语言风格。
(一)语词
每种文体都有一套自成系统的语词[2]11,不同文体又因主题相同而构成共核语言,形成相似的语言系统。《文选》哀伤类作品或直言“哀”“伤”,或用与其相近者如“悲”“痛”,相反者如“乐”,甚至用一些因为哀伤而产生生理反应的语词表现哀伤之情。如“乐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3]297“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心”[3]429“呜呼哀哉”[3]1068“步庭庑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3]299“口呜咽以失声兮,泪横迸而沾衣”[3]300“悲风汩起,血下沾衿”[3]304,等等。在《文选》23篇哀伤类作品中,出现“哀”22次、“伤”12次、“悲”30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之相反的词语,它们分布在每一篇中。这些语词构成一套语言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言说哀伤,宣泄哀情。
(二)辞格
语体也包括语言修辞,大致分为语音(如用韵)、语义(如用典、比喻、借代、双关等)和句法(如对仗、并列、重复等)三个方面[2]11。
首先,在语音方面,《文选》哀伤类作品多用叠音词和联绵词。《悼亡诗》以“胧胧”“皎皎”形容明月孤照,以“烈烈”“凛凛”形容夜寒风冷,以“亹亹”形容时间漫长,以“茕茕”“戚戚”形容孤苦哀伤。听这叠词发出悠长声音,似与潘岳一同深陷凄苦,似被哀伤久久裹缠。联绵词以“徘徊”最为常见,如 :“步庭庑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3]299“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3]296“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3]428“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衿。”[3]429“停驾兮淹留,徘徊兮故处。”[3]1066一个“徘徊”写出抒情主体如许孤独、哀伤。其他如“辗转”“寤寐”“恍惚”“仿佛”“忉怛”也很常见,使得文章读来低回往复,深感其人哀情之沉郁。
其次,哀伤之情外弱内强,不宜过分倾泻,故而使用典故、比喻,既可丰富语义,更显含蓄深厚。
“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之一种。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俾耐寻味而已。”[5]1474如“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3]296。《黍离》《麦秀》乃遗民途经故国,叹昔日宗庙之地而今尽为黍麦,哀愍王朝颠覆、不忍离去之辞,向秀赴任途经嵇康旧居,见旷野萧条、人去庐空而哀伤丛生,更借李斯之事暗含自身性命之忧。
《长门赋》多比喻,如“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与“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及“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3]293,由于过于思念君王而将雷声听成车声,错把庭中月光看作冷霜,空旷宫室正如孤寂内心,所有比喻都是写心。“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面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3]428夫君似那翻飞上天的尘土,贱妾如同坠落水坑的污泥,她亦自拟长风,渴望吹入君王怀中,奈何浮沉异势、君怀不开,只剩渴慕。
对比产生的情感反差更能反映主体的孤寂感伤。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3]296写向秀途经嵇康旧居,慨叹物存人逝、人去庐空。张载《七哀诗》以今日凋敝、衰败之陵园与汉主昔日之辉煌、昌盛相比,发出“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3]429之叹。潘岳《哀永逝文》言“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3]1066,对比生年之短与逝日之长,回忆旧日之欢尤增今日之悲,抒发幽明悬隔、悲欢离合之哀伤。
最后,可将排比、重复、顶真、对偶等结构句子之法称为句法。使用排比,增强气势、强化感情。“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像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襜襜。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3]293从浮云四塞、殷雷阵阵、回风骤起,到桂树交纷、雀集猨吟、鸟来凤回,一切景象不过是哀情的外化。“去华辇兮初迈,马回首兮旋旆。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鸟俛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3]1066更从远近、上下写来,营造逼仄环境,衬托心中之苦。
为了强调哀伤之情,使文章层次清晰、条理突出,有意让能够表现哀伤的词语重复出现。赋末常以“重曰”总结、补充全文,此非简单重复,而是以韵语对正文主题进行强化、提升。《别赋》《恨赋》以“或有”“或乃”“乃有”“又若”“至若”“至如”“至乃”“若乃”“若夫”“及夫”等重复和排比引出哀词,理清层次、强化哀情。《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四言“平生”,追忆往昔、唏嘘感伤。哀伤文经常间隔重现的“呜呼哀哉”,既强化哀伤,又突出层次。
也有用顶真来贯通声情、增强语势的。《悼亡诗》其二:“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其三:“茵帱张故房,朔望临尔祭。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3]430其中“岁寒”“床空”“尔祭”皆为顶真,使哀伤之气绵延低徊。
(三)风格
语言风格是语言运用的综合表现,也是语言审美的最高范畴,形成要素包括语言系统(语音、词汇、语法)和语言修辞(辞格、文字、标点、图形)两类,使用相同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修辞,可以形成相同的语言风格[6]501。
总之,《文选》哀伤赋、诗、文以与“哀伤”相同、相近或相反的语词,构建了一个富于哀伤情调的语言系统,又用多种辞格协调语调、平衡语义、结构句法,从而形成共同的语言风格,即“凄怆哀伤”。
三、抒情、叙事、意象的体式融通
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如叙事、抒情、说明、议论,等等[2]13。《文选》哀伤赋、哀伤诗、哀伤文皆为“叙哀事”与“抒哀情”,故其体式都为抒情和叙事,再将“意象”视作“议论的风景”,与其构成“事、景、情”的融合,以此融通体式,表现哀伤主题。
(一)抒情
《文选》哀伤类作品的抒情方式主要包括生死对比、音哀景悲、梦中寄情。
首先,对比生死,凸显哀伤。如:“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3]429生前贵为天子,死后一抔尘土。“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3]1066昔日出双入对,而今阴阳两隔。“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3]296对比亡友今昔,心中无限哀伤。
其次,目睹遗物、听闻哀音,引发哀伤。如:“容貌儡以顿悴兮,左右凄其相愍。鞠稚子于怀抱兮,羌低徊而不忍。”[3]300“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3]430但见亡人生前所用奴仆、遗留稚子甚至墨迹、衣服诸“遗物”,便生哀伤。听闻哀音,亦复如是:“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3]430“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3]296“轮案轨以徐进兮,马悲鸣而局顾。”[3]300闻音念妻、听笛忆友、顾马怀旧,汇成泣涕一片。
最后,梦是现实的反映,可以梦中寄情。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3]293思念太深,似梦似幻。潘岳哀伤赋、诗、文皆写梦境:“愿假梦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寝。” “梦良人兮来游,若阊阖兮洞开。怛惊悟兮无闻,超惝恍兮恸怀。”[3]300“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3]430“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无兆,曾寤寐兮弗梦。”[3]1066愿与亡人梦中相见,却一夜无眠、或觉后更悲。
(二)叙事
借助时空迁移、场景变换、追忆往昔、人物对话的叙事手法和代言体及以抒情主体带动全篇进展的叙事结构,交代哀情产生原因。
从清晨在离宫盼望皇上临幸而无望,到日暮登台眺望又下台周览深宫,再从夜间月下抚琴与寤寐泣涕到曙光来临,《长门赋》以一天一夜的寡居生活和不断变化的场景推进故事发展。《悼亡诗》从亡妻遗物追忆昔日琴瑟之好,《思旧赋》由笛声追思曩昔游宴之欢,对比往昔之乐与今日之悲,抒发哀情。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可以借助对话沟通,而因对话一方缺位,又使哀情更加悲怆,曹植《七哀诗》即在一问一答中叙事。
代言指作者代拟他人言说,《长门赋》即司马相如代皇后而作,潘岳用寡妇口吻写《寡妇赋》,曹植《七哀诗》以夫妾关系言君臣之事,三篇哀伤文全为代言。尽管以代言结构叙事,抒情主体之地位仍然突出,《长门赋》全以皇后口吻叙述,时而以其眼观景、时而以其耳闻听、时而以其心言情,时地移换、情感表达,皆以皇后为线索推动故事发展。
(三)意象
《文选》哀伤类作品的意象类型可以分为自然意象和文化意象。
自然意象按有无生命分为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和无生命意象。首先,近身动物与抒情主体处在同一情感场域,二者情感指向相反或相通,都为抒发哀情。如:“孤鸟嘤兮悲鸣。”[3]300“肃肃高桐枝,翩翩栖孤禽。”[3]429孤鸟阵阵哀鸣,听碎孤独之人。“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啸而长吟。”[3]293“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3]430“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3]430以双映单、借此言彼。“轮案轨以徐进兮,马悲鸣而局顾。”[3]300“去华辇兮初迈,马回首兮旋旆。”[3]1066“仆人案节,服马顾辕。”[3]1068仆悲马怀,尤增哀情。其次,抒情主体将情感投射在植物上。“蔓草萦骨,拱木敛魂。”[3]304“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3]430营构感伤氛围,推进叙事发展,传递哀伤之情。“信松茂而柏悦,嗟芝焚而蕙叹。”[3]297“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3]432“陈象设于园寝兮,映舆鍐于松楸。”[3]1071墓园多楸柏松,既有标示之用,也寓坚贞不屈。最后,日暮、寒夜、孤轮等无生命物也因人的情感投射而产生意义。“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3]293“薄暮心动,昧旦神兴。”[3]304“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3]428由明至暗、从阳到阴的黄昏,一切由盛转衰,心中涌起悲凉。“宵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3]299“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3]428月冷宵寒,长夜无眠,悲情难遣。
文化意象由一些特定人物、实物积淀而成。“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3]300寡妇孤苦无依,甚至要如三良为穆公殉葬般追随丈夫死去。“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3]296借李斯为官遭祸、抽身悔迟来悲叹嵇康无罪而死,亦对自身性命有所忧惧。此二赋或反用故实,或充实典义,情意深重。“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3]430“渠怀之其几何?庶无愧兮庄子。”[3]1066陆机兵败遭诛、悔入仕途,庄子鼓盆而歌、超脱死亡。“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3]432“空悲故剑,徒嗟金穴。”[3]1071季札悬剑,守信重义,故人亡去,吾心伤哉。古代文人习琴,故被赋予“悼亡友、叹知音”和“伤亡妻、失爱侣”的情感意蕴[7]255,如:“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3]293“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3]428“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3]435写琴瑟谐鸣,感情和睦。
可见,《文选》哀伤赋、哀伤诗、哀伤文的抒情方式与叙事方式及意象类型比较接近,而其正是以此体式来表现三者共同的哀伤主题。
四、功能、形式、审美的体性趋同
“体性是在具体文体的题材质料、语言特征、体制结构等基础上,对文体作出的整体性把握。”[8]17而且“文体风格的形成与文体所特有的表现对象、应用场合及用途、文体的形式因素、文体自身的历史传统、时代审美思潮都有关系”[8]113。这就是说,文体形态是体制、语体、体式、体性的有机统一,而体性又是文体形态的最高审美范畴。
(一)功能
《文选》哀伤赋、诗、文之文体功能都是抒发哀伤之情,这也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即作品的主题,而主题决定题材的取舍,也与风格形成紧密相关。
从哀伤类作品的表现对象和应用场合看,它们基本分为两个层面:《恨赋》《别赋》与前六首哀伤诗,表现具有普遍性的爱恨离别之情和乱世之中的功业无成,这是社会层面;个体层面包括,为皇后遭弃、妇人丧偶的悲剧命运而哀伤的《长门赋》《寡妇赋》,为伤悼逝去亲友而创作的《思旧赋》《叹逝赋》《怀旧赋》以及后七首哀伤诗与三篇哀伤文,也是为伤悼他人死亡而作。
面对亲人、好友的死亡,抒情主体表现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惋惜、悲痛;面对社会的不公,抒情主体则多表现出无奈、怨愤。两个层面虽有较小区别而风格指向皆是哀伤。
(二)形式
作品风格之形成与文体自身的历史传统关系密切,一种文体需经漫长的创作实践才能形成一定的个性特征,如“文适于叙述、说理、议论,形式自由、流畅、平易;诗偏重抒情,受句式、押韵的限制而显得含蓄、凝练、典雅”[8]142,而在实现文体突破时又经常需要打破这种个性特征。
赋体长于铺排,便于叙事,可将哀情之由交代清楚,可以完整表达哀伤之情,既能如《长门赋》精微细腻地抒写感伤、孤独,也能如《叹逝赋》广泛深刻地表达情感、哲思。诗体远不如赋体自由,却多委婉之姿,故使哀情曲尽幽微、感人至深,又以比兴纳万千情思于数言,简洁不简单、深婉而动人。三篇哀伤文都是韵文,既有赋之铺排,又有诗之比兴,如同“赋的诗化”或“诗的赋化”,介于诗文之间。正是三种文体的个性化满足了哀伤作品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才使哀伤主题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三)审美
时代的审美风尚也关乎文体风格之形成,“文体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精神的感受方式相合拍,当特定的文体形态与群体和时代的感受方式相对应时,才得到接受,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8]3。《文选》哀伤类作品除《长门赋》作于西汉,余皆来自魏晋宋齐梁代,因而时代的审美风尚也是须加考虑的重要因素。
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社会局面促成以悲为美、以悲为乐的审美风尚,士人普遍存有哀伤心态,李泽厚说:“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到晋宋,从中下层到皇家贵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蔓延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9]91谁也无法摆脱时代,何况异常敏感又得风气之先的文人。《文选》哀伤类作品大多抒发的正是悲情时代的群体或个体的不幸遭遇和哀伤之情。除此而外,作者个人审美习惯亦与风格形成关系密切。
总之,《文选》哀伤赋、诗、文在哀伤主题的规约下,结合时代审美风尚、突破文体历史传统、从而实现表达哀情的功能,最终形成沉郁、哀伤的风格。由于《文选》哀伤赋、哀伤诗、哀伤文之主题或风格皆为“哀伤”,所以《文选》将其聚为一处,设立“哀伤”类目。也就是说,《文选》“哀伤”类目设立之依据,既可认作一种主题类聚,也可说是同一风格的凝成。
五、余论:不同文体与相同主题、题材、题目
从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丰富的文体形态理论看,“一题多体”之“题”至少涵摄“主题”“题材”“题目”三个方面,使用不同文体表现相同主题、题材、题目,势必产生各式各样的作品形态,如何平衡“题”与“体”间的张力,乃是每位作者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尊体”意识盛行时代出现“破体”与“辨体”现象,“辨体”在于区别不同文体的差异,突出个性;“破体”在于弥合不同文体的差异,强调共性。随着文体类型日益增多,文体形态日渐成熟,“辨体”方式日趋多样,文体个性随之突出而共性却被遮蔽。“文章以体制为先”和“文章莫难于辨体”无疑道出文体分辨的难度,其实文体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探寻文体之间交融互渗的可能,正有益于弥合日益烦琐的文体分化。按照“辨体”思维,不同文体应有不同形态,但在表达一个相同主题、题材、题目时,必然促使文体个性弱化而走向融合,也正是由于文体之间存在共性,各种文体才有相互交融的可能。
《文选》成于南朝梁代,此时“尊体”意识尚未成熟,故而赋、诗、文三种文体更多表现出“破体”的共性特征。《文选》依“主题”来“选文设目”,按“文体”来“分类编排”。本文正是通过考察《文选》哀伤赋、哀伤诗、哀伤文三种文体在表现一个哀伤主题时,其文体形态(体制、语体、体式、体性)所表现出的共性及原因,来总结赋、诗、文三种文体得以交融互渗的可能方式。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有不少“一题多体”的文体现象,可以以此审视其间的共性或个性,考察文体之间的交互影响,发掘作品更为丰富的意蕴,而且对我们理解和借鉴古人这种创作方法也不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