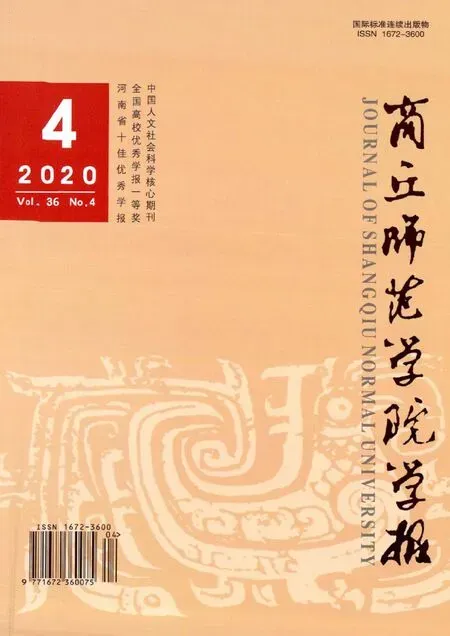有关气与理的超越、吊诡、反讽
——从庄子延伸至理学与佛学的讨论
任博克 何乏笔 赖锡三
任博克(BrookZiporyn):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目前出版有Evil And/Or/As the Good:Omnicentric Holism, Intersubjectivity and Value Paradox in Tiantai Buddhist Thought;The Penumbra Unbound: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of Guo Xiang ;Being and Ambiguity: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With Tiantai Buddhism; 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Ironies of Oneness and Difference: Coherence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Li; and Beyond Oneness and Difference: Li and Coherence in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and its Antecedents;etc.。近年来,其著作陆续被翻成中文,如《善与恶:天台佛教思想中的遍中整体论、交互主体性与价值吊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与异之反讽》(浙江大学出版社)。其天台与庄学研究,很值得关注。
何乏笔(FabianHeubel):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Das Dispositiv der Kreativit’t, Chinesische Gegenwartsphilosophie zur Einführung。近年亦在台湾编辑出版《若庄子说法语》《跨文化漩涡中的庄子》专书,并发表中、德、英、法多语论文。近年来,推动跨文化庄子学不遗余力,并准备着手进行《庄子》的新德译工作。
赖锡三: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曾获中国台湾地区科技主管部门授予的杰出奖。已出版《庄子灵光的当代诠释》(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丹道与易道》(新文丰出版社)、《当代新道家:多音复调与视域融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道家型知识分子论:〈庄子〉的权力批判与文化更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等书。目前正在校正出版《道家的伦理关怀与养身哲学》。主要学术工作在于“当代新道家”的重建、“跨文化庄子学”的推动。
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赖锡三到任博克教授任教的芝加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2019年5月,何乏笔从德国法兰克福来访。为延续他们过去讨论庄子wild card与天台吊诡思维的乐趣,三人于赖锡三在芝加哥大学的海德公园小白楼住处,进行了这场以文会友的讨论。
赖锡三:我虽然同情并欣赏使用“气”来诠释中国哲学的潜力,但如果将“气”视为过于神秘的力量,这说明学者对“气”的哲学反思有它的局限性,甚至还停留在巫术的层次。
任博克:对,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讲法很好,就是《庄子》当然接着那个东西,但是又把它转了,就是巫的文化。《庄子》采用了那个东西,但又很明显地讽刺它。
赖锡三:《庄子》有意思的地方,譬如说它用了很多神话,像“化”其实也是来自变形神话,但当它重新运用的时候,哲学创见的意义就不再是神话世界的意识状态。对我来说,“气”也是这样,不再适宜用巫师时代的身体感,那一种过度神秘隐晦的前反思状态,是没有办法作哲学洞察与转化的,甚至会被控制在那样的身体恍惚状态里。当《庄子》用“气”的概念时,那个意义已经很不一样了。
任博克:好,那先不谈那种例子了。其实我也不敢说我否定它,我不置可否,但我觉得我不要依赖那个东西,特别是那种用神秘而不可商量的直觉来判断人事如何如何,也就是巫咸的那个方式。
赖锡三:对,那就是“气”的神秘感应。《应帝王》的壶子就是要破除这种迷魅。
任博克:对,还有讽刺它。
赖锡三:不只讽刺它,其实是“破”它,因为那种可以完全揣度他人命运的能力,预设着一种透明而本质性的主体。神巫季咸是可以完全直观他人的透明主体,但对《庄子》来说,主体其实是无穷复杂而且不断变动,甚至永未完成的。例如壶子的四示,就显示出主体的化而无常、波随委蛇,神巫季咸所谓的神秘气感与直观,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最后落荒而逃。
何乏笔:这个东西在台湾的佛教里面也有,就是那些大师似乎可以知道所有一切。
赖锡三:大师可以知国运,可以知你有没有天命,可以知世界末日,大师什么都知啊!《应帝王》的壶子,就是专门用来反讽古往今来着迷于巫术大师的病根。
何乏笔:而且科学的所有发明俨然都被所谓的大师预期了!
任博克:所以可以这样说了,无论是气的理论,还是佛教怎么样的理论,有人说他有什么特权,知道具体的是非,或者每一个人的生命……
赖锡三:也不只“气”可以被这样操作,中国哲学有许多概念也可能被这样操作。
任博克:我知道你的意思,什么都可以这样错用,所以我对“气”的理论之保留不是立足于这个问题的。
何乏笔:那问题是不是针对整个修养论、境界论?某个人通过什么样的修行,达到了什么境界,这个境界是一般人达不到的,所以这个境界让他能够判断,而且能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什么直觉。
任博克:问题是,若说那个境界,有它更高的知识,也许可以;但是问题是知识的内容有没有包括对别人的判断,敢说具体活着的别人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如果说我现在开悟了,知道天上有另外一个天,那是另一回事,但这并不是说我知道哪一个候选人……
赖锡三:哈,佛教也有所谓“他心通”……
任博克:这些是我觉得都要敬而远之的。他可能说突破后获得某一种知识,但是所有的知识都不一样啊,不能说他心通啊,气通啊,什么通啊。如果是针对活着的别人、历史的事实真相之类,我觉得就会有问题。
何乏笔:这有什么问题呢?
任博克:问题是我怕他会用在我身上。
赖锡三:如果能用在你身上就好啦!我现在就不用那么辛苦阅读你对天台和《庄子》的文章和观点了,直接通了多好,哈哈!
任博克:如果他说我对于数学的一个东西有新的方法,那当然可以,确实有人有一种直觉能够突破一些东西。
赖锡三:我们跟乏笔透过“气”来重新诠释中国哲学的时候,不只是讲“通”,也要讲“不通”,要讲“边界”,要讲“差异”。
任博克:是啊是啊,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不是问题,这个不是“气论”专有的问题,这个是所有的神秘的东西都会有的。
赖锡三:我觉得神秘化一种境界论,或者被一种神秘境界所笼罩,也是人类普遍存有的现象。
任博克:没错,而且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的那个问题也可以同理讲,就是狙公是否推荐一种顺从权威的态度,你们觉得呢?一定有办法可以扭曲来控制人家,我也同意,但是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理论可以百分之百避免这样的滥用余地的问题(1)此处所提及的毕来德问题,读者可以参考前两次的对话,《关于〈庄子〉的一场跨文化之旅:从任博克的Wild card出发》《庄子与天台的吊诡性思维:延续Wild Card的跨文化对话》分别载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7期。其中的争论点在于,如何解读“朝三暮四”的寓意,它是一种处时应变的智慧,还是政治场域里的诈诡权术?。
赖锡三:是看人怎么用。
任博克: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只说“气”有这种问题。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比较接近你刚刚谈的那个自然哲学。正因为“气论”比较有自然哲学的内涵,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有从某一个角度的批判,譬如跟自然科学的冲突。当然这是误解不同层次的理论意思,但确实比较容易引起这种误会。而如果谈“理”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因为它的抽象度不会被误解看成有科学的内涵。所谓的“气”或“理”不是说明自然界有或没有哪些现象,而只是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对自然现象与事实(无论内容是什么)的一种诠释的方法。不是辩论自然界有怎样的内容,而是对任何内容的一种诠释立场。
赖锡三:有人嘲讽“气”能治百病,“气”像是万能的。其实任何概念都不是万能的,但透过有潜力的概念则可以重构系统,例如透过“理”可以重构中国哲学,透过“气”也可以重构中国哲学。学术一直在进行重构的游戏,但概念都有它的限制,也可能被误用。现在台湾学者透过“气”来重述诸多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它的 context,例如,在当前中国哲学的脉络下,看到“唯心”与“唯物”二元对立的限制,透过“气”的“非心非物,即心即物”的中介特质,或许有可能重新回应或松解一些困局,但绝不要把“气”这一概念本质化、绝对化,以避免自我意识形态化。
任博克:说得很有道理。针对唯心、唯物的无聊难题,“气论”确实是很棒的武器。而且不要误会,我不反对啊,我蛮欣赏的,我就在反省我自己完全用“气”来说明一个现象,我会有点不安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政治上的工具,或者一个压迫人的东西,“气”是这样,“理”当然很明显的也是这样。我们回头看一下,其实这本书已经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理”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做儒家的思想,原来也不是很关心儒家的理、气问题,而是关心天台宗内部的一个问题。北宋天台的山外派跟山家派,有很多争论,有一个是理总理别、事总事别,而华严宗则说理总事别,理是一,事是多(2)这里所提到的著作是Brook Ziporyn, Ironies of Oneness and Difference: Coherence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Li ( New York: SUNY Press, 2013 ),中文翻译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赖锡三:理一分殊。
任博克:对,就是“理一分殊”的模式,但是天台的四明知礼反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说总、别,理有理的总、理有理的别,事也有事总、也有事别,然后他就用这个来判断圆教和别教的界线。因着这个论争出来的专一跟多样,把论述间的不同脉络层次作了交叉的通贯整理:“理”可以说万事有一个统一的理,但是也可以说有三千不同而互通的理,都通啊。你可以说“每一个事”是万物的总,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差异的个体,也就是事别。一事能统万事,此事就是总。同一个事被一一万事所统,此事就是别。虽然可以说“理”是其所以能统,也是其所以能被统,但是“理”只是每事之所以能统,所以能被统,因为在天台那里,“理”就是空、假、中圆融三谛,“事”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指一样的圆融三谛,所以能统、能被统的事(无空、中而不假)吊诡地即是所以能统、所以能被统的理(无假而不空、中)。因此,每一个差异的“事”统万事的统法不一样,此三千不同的统法就是三千不同的“理”。三谛圆融指具体事物,又指抽象的义理,不分具体、抽象两界,不分形而上、形而下。三谛是形而上的、思辨的抽象对象,又是形而下的、手指所能碰、眼睛所能看的具体事物。圆融三谛是可以用手摸的!这就是天台理事论的妙处。这样才是理事圆融,不能说圆融然后还是把“总”完全属于“理”那边,如果这样就会分开不同的层次。
赖锡三:如此便造成存有论的等级,这是个问题。
任博克:对,所以必须把握他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问题。又回想到戴震啊,他们要批判朱熹,或者理一分殊的问题,就回头看古代的“理”字,说理字在佛教之前其实不是说“总”的东西,而是说“分别”的东西,它是指事物的个别,具体物的分类,就是跟“分”有关系。如果你看《韩非子》还是这个意思,我书中有谈到的,就是它有道,它有理,道是总,理是别,长短的对立就是理(3)语见《韩非子·解老》的两段文字:“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其中“道”和“理”的一、多关系如何诠说,有其不同的阐释空间,但“理”作为事物身上的纹理、纹路,用以分别差异,这个意思在文句里是相当明显的。。理有分开的意思,最早的用法是在《诗经》:“我疆我理”就是划出一个界线的意思(4)《诗经·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大雅·绵》:“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在这里,“疆”和“理”的意思是划定田界、治理田地。。在《庄子》,天理也是界线的意思,指牛的身体上的腠理,也是这个脉络(5)意指《养生主》的这段话:“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所以你看《说文》:“理,治玉也”,段玉裁意思是说,如果要剖开玉体,就要找出那个比较好剖的地方,纹理就是好分开的线。因此,我就发现关于总、别的问题,可能早就有一个暧昧的层次,从古代就含着一个一、多的问题,这点唐君毅也曾谈到。进一步,要问佛教为什么会说“空”就是“理”。“空”怎么会是“理”呢?如果从原来的“理”的意思,就是治玉的理,怎么会用“理”来代表“空”呢?“空”是无分别的共相,似乎正好是“理”所代表的“好分之处”的相反。所以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就是“理”字怎么可以慢慢地演变,从一个“分别”到一个“总体”,而且有一个可知的对象的意思,理是可以“原”、可以“循”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玄理”的意思,就是不可有特定指出来的内容、不可当作知识对象的玄理。所以,原来我那本书其实并不是要针对儒家的理学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理总事别”的问题。
赖锡三:也就是说,博克对于“理”概念的系谱学发展、追溯、爬梳,背后存在着更根本的判教关怀,也可以说华严跟天台的差异架构,依我现在爱用的概念来说,也就是“纵贯的系统”跟“水平的系统”的差异。从纵贯的模型来描述,“理”被拉上去成为一个根源性的总,但是如果“理”的发生原来总是离不开脉络,例如《养生主》庖丁解牛的“依乎天理”,又如“空”其实不离开“缘起脉络”来谈“空”,而不是缘起背后有个超然空理,或总体总源之理。纵与横的描述差异,会涉及形而上要如何理解的基本问题。而东方的形而上之道,主要并非一个先验本质的不变之理,而是在关系脉络中不断变化所展开的情理、事理。
任博克:所以这个故事就可以变得很精彩,就是朱熹批评佛教,他是按照华严的思想。朱熹认为,佛教不懂“理”,佛教的理都是单一的理,而不知道个别的理一分殊,每一个东西都有个别的理。朱熹就是同时把那个普遍性的理,跟那个个别有规范性的理,混合在一起。原本就算在华严,单一的理已经是空理,空本身的意思,并没有说要规范杯子、要做杯子,没有正名的意思,而且它正好是要否定这个的。那在天台就更彻底了,天台还有分别的理,但每一个理都是互具互摄的。而朱熹却是把超越的理跟个别的理结合起来,原来华严超越的理并没有作为个别物的原则规范的意思,只有一个诸法共同的单一规范之空理,对所有事情只有一个规范意思:就是不执着,合乎空理而体会事事无碍,放弃事事个别分开而有障碍的执着而相应无碍法界。华严没有个别说“有物有则”的意思,但是朱熹那边就是“有物有则”,然后把它跟华严的超越的理结合起来。
赖锡三:朱熹或新儒家的系统所立的理,终究是要稳立人间规范的价值系统,所以他们回过头来批评佛教的“空理”无法肯定世间。
任博克:对啊,所以才知道你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牟宗三觉得道家、佛家也是缺乏这一层,那个规范性的理,立法的理,有物有则的理,分殊的理。
赖锡三:就理学家的思维而言,给予规范性的“理”,要有一个根源性来保障。对牟宗三来说,不管是道体、性体或心体,“体”作为总源之理,虽然可以分殊流行下来,可是“理”作为创造性、本源性、规范性的优位源头,它的形上超越性是不能被取消的,这便是纵贯模型的思维。
任博克:个别的规范,有形上的永远不变的保障,所以也不能被取消。
赖锡三:所以,它的架构就是运用“理一分殊”的体用关系而想要克服二元性。
任博克:但这就很复杂,要用很多步骤才能让“理”这个概念达到这种超越含义的成果,理学费了很多力气扭曲原来的“理”的各种含义才挤出来这种超越规范的理的意思。我甚至觉得21世纪的新儒家,他们好像羡慕西方的绝对的形上学,觉得中国没有可以并谈的东西,只有一个稍微有点轻微的超越意识、形上绝对化的东西,然后就把它扩大了,把它的历史地位扩大了。
赖锡三:其实牟宗三系统的内部可能性是很复杂而丰富的,理解牟宗三可以从儒家跟华严系统的结合来观察,但是牟宗三所诠释的中国哲学系统也可能往天台模式去发展。如果让牟宗三的系统采取天台的解读,有可能可以重构牟宗三。也可以回来再看宋明理学,比如张载要怎么解释?可以不采牟宗三的解释啊,若采另外一种解释,例如唐君毅对张载的诠释,所发挥的理论意义就会不一样。博克你常提及唐君毅,而且你也受到钱穆的关键性影响,可是在新儒家的学生里面,唐君毅跟钱穆基本上并未发挥深远的影响。唐君毅对张载的解读向来不被凸显,因为那个解读跟牟宗三不一样,但它其实可以打开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不只是个单一例子,原来新儒家内部可以有多种可能性,比如说钱穆、唐君毅,就连宋明理学内部也有种种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张载、王夫之,都可以重新诠释与再开发。但是牟宗三的正宗解读影响力很大,这多少压抑了对牟宗三的多元诠释与价值重估。
任博克:你觉得他的弟子比他狭窄、比较单一吗?
赖锡三:弟子的心力通常花在吸收大师、继承大师上,可惜不是十字打开的开创性承继。
任博克:牟宗三的弟子把天台的读法差不多都抹杀了吗?
赖锡三:牟宗三的弟子有很重视天台思维模型的吗?有透过天台的思维模型来反思宋儒理学或重构中国哲学的吗?尤其放在当代的后形上学与跨文化脉络,天台“开权显实”的思维,有待整个价值重估,而不只是放在佛教史的判教脉络来讨论。换言之,牟宗三的天台学之哲学价值,已超出了佛教内部的专业化视域,可能对整个中国哲学或当代跨文化哲学,都有待价值重估。而牟宗三的学生们,志不在此。陈荣灼和谢大宁是少数的例外,但他们的关怀并未受到太多关注(6)陈荣灼和谢大宁尝试指出一条有趣的线索:牟宗三对于佛教天台命题“一念无明法性心”“一念三千”的慧心解读,很可能反过来构成对其所树立之系统模型“一心开二门”的挑战。以本文的话语来说,在牟宗三身上,同时存在着“体用论”与“相偶论”两种哲学模型,只是后者并未获得相应的关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陈荣灼《圆教与圆善》,收在《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内圣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3页;谢大宁《佛教诠释的“语言转向”》,收在《1996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思想的当代诠释》,台北佛光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任博克:就是说你刚刚提的那个,用天台的模式来解读牟宗三,不立一个超越的规范性的天理。
赖锡三:我觉得这个潜力基本上是隐匿的,开发得远远不够,或者说,潜力大有可为。
何乏笔:这里需要提及在牟宗三思想里面的重要区别——关于超越性的区别。他不只是羡慕西方的形上学,其实也是批评西方的形上学,所以提出“超越”与“超绝”的不同。后者是他反对的,认为是基督教的、西方的东西,跟儒家不一样,儒家需要超越性。根据我的理解,他有两种批评的方向,一个方向是针对中国传统超越性不够,另外一个方向是针对西方的超越性太多了。
任博克:中庸之道!但是你们认为牟宗三正确的解读,他所主张的超越是怎么讲呢?
何乏笔:我想他所谓的超越是指“内在超越”。当然,有不同解读的可能,但我想,我们也不会反对“内在超越”。《庄子》可能也有它内在超越的模式,但这种超越就不需要用形而上学的超越来讲。所以,牟宗三打开了一种可能,打开了一个框架,但是牟宗三的弟子把这个框架的可能性窄化了。所以无论是杨儒宾还是锡三,都是继承牟宗三,但这是一种间接的、批判性的继承,是一种批判性的反省。这种继承容易引起争论,因为牟宗三的一些弟子具有很强的正宗意识,所以也很难产生讨论,因为所有不属于正统的解读方式容易被看成是误解,或是错误。
任博克:康德化是问题所在吗?你觉得?
赖锡三:至少康德化的诠释“开显”,也是一种诠释“遮蔽”。
何乏笔:所以在这个“理”“气”问题上,我们不只是谈先秦理气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出发点是当代的争论!在当代新儒家那里,主张“理”就是很保守。就像李明辉或者其他新儒家的代表,在“理一分殊”这些说法上都很无趣、很保守。
赖锡三:所以说,重构这个概念是有我们的脉络,有我们要面临、要回应的问题。在牟宗三的系统里,“气”属于存有论的 ontic 次级概念,比如“气质之性”是要被超越的。“气”这个问题就变成形而下的、身体性的、物质性的具体分疏向度,可是在牟宗三的系统里面,虽不是说完全不被肯定,但毕竟在本体论上的等级是次级性的,只是透过巧妙的辩证,再去保障它们。不管你用体用论的模型啊,还是一心开二门的模型,终究要曲成地保障它们,因为儒家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寄身在这些具体性里头,可是在理论模型上,它就成了间接所成,是到后面才被肯定的。
何乏笔: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同的问题,在牟宗三那里对“气论”的批评,也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涵,不是巫术的问题,而是唯物论的问题,也就是“气论”的唯物论化。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至少在我的解读,他很明确地反对“气”的任何物质化或唯物论的理解(包含张载的唯气论倾向)。他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分开的核心议题。
任博克:你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历史脉络,我可能有一点忽略了这个层次。
赖锡三:非常重要!因为“气”始终就跨在这“唯心”跟“唯物”之间。
任博克:对,对!
赖锡三:早期国内的学者是透过唯物论来重构“气”,唯物论对牟宗三来说是个大弊病,因为牟宗三的德国观念论倾向,最优位性的概念是“心”或“神”。所以他看低“气”这一概念,这和他认为唯物论毫无超越性的浅薄鄙陋,可能有潜在关连。而在离开冷战时代、时过境迁的当前,我们反而认为“气”的“即心即物”正可以沟通两边,而“气”的“非心非物”则可以不住两端。而且这种“即心即物,非心非物”的吊诡之“气”,不是要去把这两边给予终极的综合统一,反而是要讲这两边的不断互为中介、持续相互转化。
何乏笔:“气”正好是一个吊诡沟通的核心概念。但是要理解的是,一直到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在这个地方是必要的,那么“气”就是形而下的,“理”或“心”是形而上的。
赖锡三:在先秦时期,例如在《庄子》一书,“气”这个概念没有稳定下来,可是“气”的潜力就在于它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气”可以合成“精气”,也可以合成“神气”,乃至合成“形气”这个概念,这就代表着“气”可以通于“形”,通于“神”,乃至通于“道”。换句话说,它原不是一个形而上、形而下完全切开来的东西,“气”既表现出不间断的连续性,但当它连结成“形气”(或物化)的时候,则又涉及个体的分别性。这便是“气”还没有被稳定下来、不被定于一端的“非心非物”状态。一旦把它定为“物”或定为“神”的时候,气也就失去了“即心即物”的两行沟通之中间性。
任博克:这样讲真的很精彩。“气”这个概念的不稳定性正好是它的长处。其实,这种“两行”倾向是中国哲学很多概念所带来的,就算想分清楚不同的阶次,这些概念本身的不稳定性就会带来一种抗力,最终还是分不清(7)“两行”一词出自《齐物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其实我那本书讲“理”的原因,也就是针对“理”本身也有此种两行性、稳定不下来,才会如此不断地引起争论。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因为似乎在中国哲学里头,最核心的几个概念都有这种稳定不下来的特性,可能“气”与“理”只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概念都很难很干净地、清楚地套上一个属性,决定到底是一是多,是神是物,是形上是形下,是动的是静的,是一元的是二元的,等等。每一代思想理论家都企图对它下定论,但是每次都马上有反抗,因为原来活用的“理”的概念,就像“气”一样,是永远在这些二分法范畴中套不住的。但是,只指出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自然而然地这些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无论是“气”还是“理”,都有这种“两行”的特性?《庄子》会很美丽地用“化”来描述此一内在吊诡的不稳定性,但是更进一步我觉得《齐物论》中的“彼是,是非”(8)《齐物论》的原文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的讨论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内在的必然结构、其所以然。正是中国文化存有论最根本的一些前提,也就是古文最根本的一些文法特色,就是以“连贯成形”(coherence)为存有,存在就是连贯,概念指谓意义也必当连贯才成为意义。连贯已经包含一个彼此连统而成为一形、又二又一的特色。因此,就算“非反讽”的连贯成形必带着“反讽”连贯成行的种子在其中。中国思想无论怎么想逃脱这种两行的、吊诡的、反讽的维度,总是逃不了。在最关键的概念上正好总会一再冒出来。比如说“气质之性”跟“天地之性”,“性”就有一个两行的本质,你不能说是先天,也不能说是后天。现在若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好,那现在我们来说清楚,有两个不同的阶次、两个不同的含义,同一个字的两种不同的意思,但最后它们并非两个,甚至朱熹也没办法说“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两个性。而“气”这个概念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
赖锡三:去年在高雄讨论《庄子》的“气”概念与天台的吊诡性思维时候,我曾经向博克作了一个和佛教“空、假、中”的类比:“形”偏于假谛说,“神”偏于真谛说,“气”则是为了描述中谛或中道观。“气”就是要突显:“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吊诡思维。换言之,也就是“中”的无所不在,如此才能显现不断中介、不断调节的变化。“气”的重构潜力,对我而言,就像是以气化(即物化)存有论的方式去描述天台思维的“不但中”。但是其中细节,有待将来进一步去沟通天台与《庄子》(9)相关讨论,参见《庄子与天台的吊诡性思维:延续Wild Card的跨文化对话》,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第1—30页。相对于区分出“理”与“气”“心”与“物”两层存有论等级,再花很多力气去说明两者有着“理一分殊”、彼此不可或缺的体用关系,天台佛教企图表述另一种观点:“空谛”与“假谛”的吊诡相即,“不但中”(“中道”不独立于世界之外、不外于两行之间)、“不断断”(不切断为两层的断)、“性具”(佛性与一切法共属互具)、“一念无明法性心”(清静与无明混然共存)。这类说法相契于《庄子》对于“彼”“是”连贯成形的体会,也即是当代庄子学所企图厘清的“游化主体”“吊诡的主体”,或者心与物的平等辩证、无所住的否定辩证过程。。
任博克:而且若是彻底发挥这一面,“气”的概念就可以免得那个神通的恶用。因为一想给“气”一个定向的含义,将它的意思限制在一个方面,它就会不堪、行不通,会因为概念本身的不稳定而突破。
赖锡三:《庄子》的气化论就是物化论,当然你直接用“化”来谈。对我来说,气化、物化、万化、造化,其实都是可以重谈,甚至以另类的存有论方式去重新描述缘起论的问题,而且直接从缘起论就可以谈超越性,不必离开缘起论而另立一个超越的根源,如此也就可以去描述你所谓天台思维的“遍中论”(10)此处的处理,可参见赖锡三的讨论:《诗意栖居与原初伦理——老庄的柔弱无用与海德格的泰然任之》,赖氏将晚期海德格所谓“世界的世界化”“物物化”与《庄子》的气化、佛教的缘起观联系互诠,并透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关于“气韵”(Aura)的讨论,指出“道在屎溺”含着一个直接于具体物身上思考超越性的理论潜力。“中道”既不离物化、两行,也就可说其遍在于各种不同的脉络之中。“遍中论”的意思,参见任博克《善与恶:天台佛教思想中的遍中整体论、交互主体性与价值吊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7页。。换言之,《庄子》的气化论可以深化佛教的缘起论,也可以契通你所谓天台的 ontological ambiguity。
任博克:天台就把真常心、如来藏等纵贯本体论判为别教的一种。别教也有它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是最终还是一个方便而已。我觉得我们应该广泛地用这个方法批判“根源”“本体”等概念:它们都是方便法,是一个阶段所需要的,甚至可能是必经的阶段,但是最后要“开权显实”,给它开花:“有一个万物之原,形上的第一因”之权,开为“万物个个是万物之原,互为因、互为果,一一法内在超越地变造一切法”之实。但是形上学还是最有趣、最有长智潜能的一种玩具(11)“权”(开花)与“实”(果实)作为哲学用语,源自佛教典籍的翻译与传播。关于“开权显实”的天台解释,参见任博克《善与恶:天台佛教思想中的遍中整体论、交互主体性与价值吊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任博克指出,在“开权显实”的譬喻里,原先的“花”不是被舍弃了,“果实”并不孤在,毋宁说,“开花显子”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植物本身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以“开花”作为起头,事情发展到了极致,自然要显露其“果实”。在这个哲学比喻里,“开权”与“显实”只是同一个过程(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貌,果实(事物的实相)一开始就蕴含在花开热闹的诞生之际:眼前纷然绽放的一切法、各种具体的世俗谛,发展到了最后,总会显露其“依因待缘”的性格。亦即,“权”与“实”不是存有论的两层关系。。
赖锡三:没有这个玩具我们都变禽兽啦,哈!哈!
何乏笔:形上学是玩具。从我们刚才所讲的,就可发现一个困难。你所谓 coherence 跟我们的问题意识,或说跟我们在台湾所面临的困难,到底怎么调和呢?这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切入方式,但“吊诡”似乎是我们共同的基础。你昨天说 paradox 就是你的出发点,之后才开始谈“反讽”(Ironic)。我想,这是一个共同的兴趣,也是共同的问题,但是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切入方式(12)前一晚的对话内容,参见Brook Ziporyn, Fabian Heubel, and Lai Xisan: “The Ironic and the Paradoxical: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rook Ziporyn, Fabian Heubel, and Lai Xisan”。?
赖锡三:如果用博克的一组概念,也就是 global incoherence 和 local coherence。我们可以尝试把“气”或“气论”理解为 global incoherence 或者 ontological ambiguity,而把“理”理解为 local coherence,而且两者之间是“不一又不二”的吊诡关系。所以“理”是可以不断被重构的,在不同脉络、不同情境下而不断要重构 coherence,于是不断出现规范性的“理”,因此不会掉入价值的虚无主义,但是这样的“理”却不能离开“气”的 ontological ambiguity。以《庄子》来说,物之天理可以不断被显示出来,但“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的无常之虚、无常之化,却不可被遗忘。
任博克:Coherence 翻成中文就是“连贯成形”,所以连贯成形就是说,它的形是靠着跟什么连贯,那你用一个形,一定是在某一个时代的这个 coherence,而它又有第二层的 coherence,它的自我重新脉络化是待在那个连贯成形的脉络里头的。不用说,有了它然后又必须加上一个重新脉络化,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连贯,它连贯才成形,那这个连贯成形跟另一个连贯成形又连贯,又成了另外一个形,有这个内在层次的构造在。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形,一个定理,就是因为它立足于一个连贯,因为连贯到某一个程度总是要连贯到那个界线之外的东西,前后、上下,它的关系性是内在化的。有分别、有规范,但如果说规范本身就是“连贯成形”,那规范本身已经有它的重新脉络化的不可避免的构造,它本身就是一个脉络化,所以它当然也不能一成不变,那是不可能的,“理”的规范的一成不变,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概念。
赖锡三:其实《庄子》的“物化”这个概念,本来就是“物”和“化”合组而成的一个吊诡性概念。“物”是就“连贯成形”的 local coherence 这面向来说,因为“物”有一个暂时站出来的 visible 特性,而且在什么脉络下就被称为什么物,跟什么情境组合发生关系就会如此命名组构。但“物化”之“物”,必然与“化”的 global incoherence同时共在。而“化”其实就是防止停住在特定脉络的“连贯成形”,于是“化而常新”地不断打开“脉络化的再脉络化”进程。
任博克:所以就跟那个“气”一样,它不可能完全是无相的,也不可能完全是有相的,它一定有相也一定无相,无论它在哪里,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形而上、形而下的二分法的分别,除非透过康德式的解读,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应该回到程朱那边本身的用法,虽然区分出形而上、形而下,而且很重视这个分别,但还是没有分得那么开,因为这原来是从《系辞传》而来的用语,它还是带着《易经》脉络的意思,原来“形”在这个脉络中指的就是卦体:“形”而上,“形”而下,都离不开形。
何乏笔:这是王夫之的解读。
任博克:这是正确的!那个《系辞传》它在讲发明具体的一些工具,就是“器”,一种器就是从一个卦的阴阳、某种特殊连贯而成的形而被发明的。“形而上”就是“此卦以及此卦所显现的连贯构造”,“形而下”就是“此卦以及发挥此卦的构造而发明的器”。形上、形下两者都包含卦本身、形本身①。虽然程颐他们有意要更发挥而严格化这个区分,但是就算程颐讲“理”跟“气”,也没有像牟宗三或康德的思路分得那么开,以为“理”和“气”完全没有重叠。
何乏笔:为什么到后来“理”就是形而上的,“气”就是形而下的呢?
任博克: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看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注解,也就是从太极到动静阴阳所谓的二气。所谓的“形而上”跟“形而下”的关系,无极而太极是所谓的形而上,到了阴阳二气是形而下,它们其实都跟“极”的概念有关系,朱熹也说“极”是枢纽的意思,道枢的“枢”、太极的“极”原来是这个意思,它是屋顶的中间,所以它有“中”的意思,它也有阴阳转向的点的意思。当然这个阴阳结合的“中”,是非阴非阳的,“非阴非阳”就是形而上。
赖锡三:也可以讲“即阴即阳”。
任博克:可以,所以“无极而太极”,也是很明显的吊诡,我的读法就是钱穆的读法,不是康德式的形而上、存有论的形而上形而下,而是钱穆讲的“摆动”。“中”是所谓的形而上,因为它是两变的共同点、连结点,无中则无两边,无两边而无中,此“中”必包含阴、阳两个相反的属性,即阴即阳,那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形,无形可言,非阴非阳,不是另外一层存有而是一切存有的一个必然属性。两边必联结到“中”才能成形,所以钱穆说,“中”也有所以然的意思,进一步也有当然规范的意思,而此规范性本身直接从“中”的连贯两变而使之成其两边的形,衍出“中”这个概念本有的“过犹不及”的规范意思。“善”就是两边的中,“恶”就是两边过或不及而彼此连贯不起来,成不了形。所以,“中”就不是什么神秘超越的另一层存有维度、什么无端存在的绝对道德规范,而是普普通通的所有形之所以为形的“中”。有形就必有彼此之形的联结处、界线、连贯,又分又接之处。这是钱穆解读程朱理学的“理”的说法,也是朱熹本人透过“枢纽”而解释太极的基本模型。我觉得,钱穆这种从“摆动”而解读“中”的意思才把握了中国理学的“理”的原味,不加欧洲进口香料,不必有超越的道德形上学,才有强而有力的规范性。其实朱熹解释“形而上”最根本的构造是怎么回事,只提供此“枢纽”太极的说法,没有别的。至于说形而上的其他属性(譬如先于气、无象、无运作等)都只是描述从此根本的搞糟而来的一些特性。因为在朱熹看来,此形而上的太极、理确实有它的殊胜而跟所有其他的存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这都是从这个基本的“枢纽”意思而引申出来的。
赖锡三:钱穆用这个钟摆的例子非常好,它可以用来说明我们现在谈的“吊诡沟通”或“吊诡运动”,其实正是为了用来描述一切活动现象,如果活动要不断地运动变化下去,它自身内部就会具有吊诡的结构或质性。你看那运动中的钟摆,每一个运动质点都包含着两端的力量,所以它才可以不断运动下去。每一现象、每一存在、每一活动,都具有“既对立又促成”的吊诡力量,而且不同情境下的每个质点内部的吊诡力量倾向,都不会完全一样。就像《齐物论》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彼是方生”结构。有“彼”就有“此”,有“此”就有“彼”,“彼”与“此”既“相互归属”又“互为他者”的吊诡关系,才促使“环中”的周转运动,永不固化。换言之,失去了“相反又相成”的吊诡力量,钟摆也就不摆了。而真正活动中的“环中”,必然要作用在每个正在周转运动的每个质点上,这便是无所不在的“遍中论”,而不是特定化、固定化的“一中论”。
任博克:这很重要,所以那个流动性是不可或缺的。但钱穆的想法还是以儒家为主,为什么儒家要讲道德什么的?道德、天理就是说那个动,不能是只动不反,只动就没有“形”成,这个就是没有礼法的地方,就变成纯粹乱动而不成为任何可指定而认识出来之物。要谈什么秩序、规范等,都是用传统中国到处所见的来回行动,两边摆动,阴阳消息,昼夜之道而说的。因此,就算有一种稳定性在其中,并不是一个静态东西在那里,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一个真正的点,所以必然要说:虽太极而其实无极,没有一个你可以抓住的点,也没有摆动停驻的地方,从来没有停驻,它一再让置那个地方的朝向处。类似有一个虚拟的点,虽然此虚拟之点可以说主宰变动之所以然,正像“中”从某意义上说是在主宰两边的所以然,但并不是多了一个存在摆在此“动—静”之外。正因此,要一再否认“理”是有气象的、是具体的存在之一。而且也正因此,等到西方形而上学传进来了以后,这些讲法就很容易被误解为类似的一种形而上的概念。钱穆如果要解释为什么朱熹他们会批判释老,只是因为朱熹确实会认为佛老的“中”不够稳定,不够发挥规范性的一面,也没有可以从“中”的太极观念演变出来各种“有物有则”的个别礼法。这是可以商量的,但无论如何这跟西方式形上学是没什么关系的。
赖锡三:可是从《庄子》或佛教来看儒家,由于对规范之理的守护倾向太过着实,于是把“不但中”讲成“但中”,“遍中论”的特质被削弱了。
任博克:Exactly,它是但中化。
赖锡三:对我来说,《庄子》不是反“礼”,它是想到“文”与“质”之间,保持情境化的吊诡张力(13)此处的思考与处理,读者可以参考赖锡三《〈庄子〉对“礼”之真意的批判反思——质文辩证与伦理重估》,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3期,第1—24页。。
任博克:有一个“中”的意思。
赖锡三:对,但《庄子》的“中”是没有定则、定法的。比如说:私跟公的张力,我们跟他人既有社会性的角色要扮演,但也有跟他人的具体情感殊异,所以情与礼的表达,没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客观性中道,可以永被遵循。“中”,反而是在公私之间,情礼之间,文质之间,不断要求我们给予回应的敏觉!而且无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
任博克:而且是同时在进行的。每一个“中”、每一个“部分”也有另外一个“中”、另外一个“部分”,它不可能稳定到哪个程度。
赖锡三:但是儒家担心,没有稳定到一个程度,规范就会立不住,他们担心理序乱掉,担心人民无所措其手足。
任博克:Right.
何乏笔:在汉语学界有这样的讨论吗?从这个角度来反驳以“理”为形而上的观点吗?
赖锡三:刚刚提及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读,还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的关系,其实这可能跟道教内丹有思想史的交涉关系。无极、太极、阴阳的关系,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的关系,在内丹的宗教修炼系统就区分出“先天”与“后天”两层。而北宋理学和内丹产生交涉,随后才发生内部的争论,例如:陆象山和朱熹才会争论到底无极与太极是一还是二,太极跟阴阳是一还是二,因为在内丹系统就是要追求一个更根源的形上超越界,可是理学则是要肯定“物物一太极”的万物界、人间界。所以先天和后天、形上与形下,到底两层还是一层?到底是纵贯还是水平的关系?常常陷入暧昧纠缠的情况(14)值得注意的是,“先天”与“后天”这组用语,同样出自《系辞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但其确切的意思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遭遇一样,有着不同的解释空间。相关讨论,参见杨儒宾《两种气学、两种儒学》,收在《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28页。。
任博克:没有错,而且你想,如果是道家的气论系统,所谓的“形”跟“无形”,无形是气,有形也是气。气质之性就是形,定形的、有相的东西,可是所谓的无就是无形,无形也是气的无形。所以,形而上的气也是形而下的,有时候,其实是形而外的。
何乏笔:我想杨儒宾就是这样认为,所以区分所谓“先天气”与“后天气”。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他基本上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反对“气”的唯物论化,强调“气”没有办法限制在唯物的层面,没办法限制在“器”或“物”的层面上。所以他很喜欢提“心者,气之灵”的说法,这也是朱熹对“气”的解释,所以“心”与“气”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分关系。但他的观点也引起了争论(15)此处的发言背景,可以参考杨儒宾的两篇文章:《检证气学——理学史脉络下的观点》《两种气学、两种儒学》,收在《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85—126、127—172页。简言之,“气”虽然是中国哲学的通行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思想家手上(医家的、黄老的、内丹的、道家的、不同理学派别的……)有着不尽相同的界义,甚至我们可以说,当代庄子学也正在厘清其关于“气”这个概念的有效理论范围。何乏笔的意思是,“先天”与“后天”这组用语,仍然维持着类似“形而上与形而下”“超越与经验”“体与用”的对举关系,如何更确切透彻地描述两端的吊诡相偶,仍是有待思考推进的问题。。
任博克:杨儒宾是你的老师吧?他也是很关心这个规范性不够强的问题?
赖锡三:杨老师应该也是赞成熊十力所谓无体、无理、无力的辟佛立场。有体、有理、有力,有其密切关系,“体”就是“中”,是一个扎扎实实的 foundation,这个形上本源之体作为“理”的源头、“力”的发处,乃是“化而不化”的那个“不化”。杨儒宾非常强调这个作为奠基的中心点,既是规范性源头,也是价值源流,实践起点,这也是他所理解的体用论模型。所以,如果从那样来看《庄子》谈虚、佛教谈空,都很难彻底避免无体、无理、无力的“虚无主义”嫌疑。
任博克:如果在气化论里头,讲“不化”应该是就“气”的无形状态来讲,也就是先天气的层面,问题是:既然无形也无分别了,那“无分别”也不能无视“有物有则”的意思吧?所以,它的有则、有规范性就会像是在“空理”或者“华严”来讲规范性,也就是要去思考那个“否定性”的规范性吧?
何乏笔:以“无”为体。
赖锡三:“以无为体”,或者“体无体”,某种方面说虽也肯定了“体”,可是它其实是“以化为体”。这里面要谈的是“化”跟“不化”的吊诡关系,杨老师虽然也不会反对,可是他在谈这个关系时,我认为他会坚持体用论模型,也就是“体”必然还是优先的,虽然他也谈“体”不能离开“化”,不能离开“用”,可是“体”跟“用”之间还是有极细微的区分。换言之,一个超然的本源本体,不能够不被预先肯定。我们跟乏笔、杨老师在台湾很亲密碰撞很久了,而且关键处,也和《庄子》能不能肯定、回应人文价值有关系。
任博克:好吧,但是那个“体”的内容是什么,它怎么有规范性的?它有内在的分别吗?比如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哪一类的呢?如果所立的那个本体,是虚的本体,我不是说玄妙的虚,而是说没有可指定的个别内容、无相可说,你说它存在、但却是无相无形的,那怎么来的?所以,他会觉得那个“理一分殊”或者“气一分殊”如何?
何乏笔:它就是桥梁,他两边都可以玩,我们只玩一边。
任博克:我纯粹要问的就是思想的构造,你要立一个规范。例如说:在朱熹那边,我可以了解在天理,宇宙本身有君有臣、有仁义礼智,那杨儒宾认为,“气—体”是有仁义礼智的吗?
赖锡三:他大概会认为,“气”的活动,就会流行出“理”来,不会是全然混乱的 chaos。例如他会说,为什么花朵很自然就会有几片花瓣?为什么人的身体结构和脏腑位置不会颠倒过来?这都是“天理”的显现。可是你也举过一个看似非常荒唐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确定下一次人类会有一样的器官位置?如果在不同的星球,你的“身体之理”就长成不一样的状态,你的头不一定就是现在的位置。
任博克:安乐哲(Roger T.Ames)有一个很喜欢提的例子,我觉得很好,如果你觉得松树的坚果,你看那个种子在树上长出来,你认为它的目的就是种在地上,然后长开变成花、树木,但是百分之九十几的种子并不是变成树而是变成松鼠的美食。这才是大自然的做法,大多数指定为有某个目的的东西并不达成这个目的,而分散到很多不同的目的去了。
何乏笔:松鼠也是一个扩散的方法,因为松鼠不是什么都吃光啦,松树也是透过松鼠散播啊。
任博克:也是。松鼠有时候可以帮松树达到它的目的,但是大多数就不会。可能被狗吃,被人吃,化解而不成松树。所以这个种子有很多条路可以发挥。
赖锡三:如果“理”是在不断脉络化中持续改变成长,对某种类型的理学家来说,可能就会产生“理”的危机感。毕竟“理”多少被视为具有必然性、普遍性,这样产生的规范才能被视为稳定有效。牟宗三最喜欢讲普遍性,例如“具体的普遍”和“抽象的普遍”,总之要有普遍性,不然就不叫“理”啦。
任博克:可能有人会说,对啊,我有规范性,只有那几个东西会变成树、松鼠,变成那五六七八、一百个东西,但那东西有限,如果我们把那个“限”记下来,还是有规范性的。
何乏笔:但是,我觉得从我们昨天的讨论角度来说,“反讽”里面有一个意涵:规范性恰好要透过反讽才能真正实现,它没办法直接实现,必须要“曲通”。真正的“道”在“道”的否定之后,才有可能。奇怪的是,这样的思维在新儒家里面比较少,牟宗三有时候是有的,但后来比较少出现这种曲折的思考方式。新儒家基本上是“非反讽的”。
赖锡三:他们基本上是一种直接的肯定性思维。也就是先立本体,然后再讲“时变”,但再怎么“时变”,还是有个内核(例如道德法则)不能变。内核若变了,普遍性、本质性、先验性,规范性的“理”就会摇动。这应该属于“非反讽”的思维方式。就像“反讽”的思维是说,所有的 coherence,所有的“理”,都是从情境中演化出来的。而且“反讽的理”会在新脉络化下,变化延伸出更多的“理”来。“变化”就是“反讽”,而且是变化生长性的反讽,不是虚无主义的反讽。我们所理解的《庄子》的吊诡思维方式,就像是和你现在使用“非反讽”“反讽”等概念的对话表达。以反讽为体,以便产生出更多 coherence 的变化之理。
何乏笔:问题是,要如何面对对我们现在的《庄子》研究的反感?一旦进入“反讽”,一旦从“非反讽”过渡到“反讽”,规范性不再是自立自足的,一旦它的实现依赖非规范性的东西,那就开始打结了。这个时候“规范性”就开始有问题,因为谈到“反讽”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诡辩。
任博克:你没有绝对化的要求,要求你一定要怎么做。
何乏笔:这就触及相对论的问题,陷入诡辩、诡辞。诡谲、吊诡这些转来转去的东西很麻烦。
赖锡三:我们不能忽略儒家从一开始就是要治理社会、管理群体。儒家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治理、治天下有关系,所以想要提供一个“总而理之”的东西。如果容许“变化”的速度太快,如果容许“偶然性”对传统之“礼”的修改太多,儒家可能会觉得不够稳当。因为古时候大部分人没有知识,圣人为你立法、神道为你立教,以提供百姓秩序规范。
任博克:早期儒家就已经说破了,你刚说“圣人要为人立法”,目的已经是讲得很清楚。那可不可以具体来讲呢?我总是有这种感觉,可能给你提过,我第一次去台湾,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人家在开车,如果是深夜凌晨两三点,没有人的时候,有红灯,在台湾,我没有看到一个人会遵守它。
何乏笔:现在比较不一样了,至少台北是不一样,高雄好像还比较……
赖锡三:高雄比较自由,所以你要来高雄。(三人大笑)
任博克:但这是个问题,你问人家,那当然我很遵守社会秩序,但是设红绿灯是为了要我们的安全,但现在没有车子,我自己可以判断没有车子,很安全,三点钟了。终极目标是定的,但是达到它的手段可以变通。
赖锡三:三更半夜一直停在那里,是笨蛋啊!
任博克:是的!但是在美国,大概德国也是一样,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会在那边乖乖停,等待,如果闯过去会觉得怪怪的。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如果你知道社会规范只不过是社会规范,本身没有形而上的意思,就不会像美国那样子,觉得有一个神秘的道德问题在这里,有一个绝对化的直觉会觉得:无论如何,闯红灯是邪恶的行为。当时在台北就是这样,好像没有把守规则当作一个形上绝对的要求。这是不是新儒家所怕的?他们是否觉得中国社会有太多那种不够有法律的敬畏。
何乏笔:这个例子或许还不错,也就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假如你被抓,警察抓你,你就开始诡辩。(三人大笑)如果那天晚上完全没有车,或者只有一两部车,但你什么时候觉得没有车呢?这诡辩是无限的。
任博克:但你不觉得之前的儒家,有了红绿灯,白天遵守就差不多可以了。
赖锡三:孔子就时常不遵守当时的礼,他的好玩也是这样啊!
任博克:所以为什么?是儒家态度变了吗?
赖锡三:孔子自己可以“缘情制礼”,他的礼法是可以随时随境而权变的,所以我们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可是后来的礼教,愈来愈烦琐、越严格,变成不那样做就有禁忌,违礼、犯礼的帽子,很容易被戴上。
任博克:当然我不是史学家我不知道,但是就你了解,如果是宋朝社会,一般的人遇到相当于红绿灯的深夜,是停的吗?还是不停的?(三人大笑)我觉得是不停的啦!我觉得如果是朱熹他也会觉得不要停啊,你觉得朱熹会觉得要停吗?我觉得不会,朱熹不是康德,就是在这里啊。
何乏笔:这就是诡辩。
任博克:不是,因为白天没有人会这样做。
何乏笔:白天你在乡下车子很少,那里白天也可以。(三人大笑)
任博克:那个并不是说没有规范,也不是说没有某种程度的可行度,所以还是行得通,可能是社会繁荣到某一个复杂度,就变质或什么的。个人我还是会觉得,这个代价是很值得付的,偶尔或许有车祸了,还是比大家都遵守得那么严格好。那是每一个人对人生不同的体验,如果你可以选择,住在一个很有知识,已经内在化法律到灵魂去,死死地在两点钟等红绿灯,或者另外一边,偶尔被车子撞死了。
赖锡三:生活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意外。坦白说,遵守规则也不是没有危险啊!我说真的,规则也有它危险的地方。例如严守规则可能会带来过度压抑,结果造成“规则”跟“反规则”的诡谲共在,有些人反而会刻意去冲撞规则。
何乏笔:诡辩!诡辩!
赖锡三:没有!没有!很多青少年就是刻意去闯红绿灯,就是要挑战规则,所以也不要都相信绿灯行是百分百的安全。白天时段的绿灯,我也不会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不知道对面有没有青少年会突然闯过来,这种事情不时会发生。
任博克:对,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我跟你完全一样,这种生活我会觉得生不如死,遵守规则到那种程度。遵守跟推翻是循环的,你说得很对,这个就会把那个推翻规则的英雄主义产生出来,会觉得我是邪恶的英雄之类的。
赖锡三:这种结构,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何乏笔:我想象新儒家的反应,他们似乎无法接受“规则”与“反规则”(或非规则)的这种互相产生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一般会认为,反规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教养不足呢?过度的道德会产生恶吗?在新儒家没有过度的道德问题。这是老庄才会深入思考到的问题:“上德不德”等。
任博克:真是奇妙的事,不可思议。如果要和这种人辩论,就是要明显地提出来,然后就有各种心理、文学、历史,很多种例子、理论上的依据。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因为这个前提可能是他们没有自觉的,你跟他们谈,你深深有这个体验,就是说太严格的遵守,就算成功了也不是好事,它一定的反作用。
赖锡三:《老子》举过很多例子。例如“六亲不和有孝慈”,标榜孝顺和家庭问题经常诡谲共在。
何乏笔:但这是不是你的文章所面对的问题?有人会批评,你就是不懂儒家的礼啊,太吊诡的讨论了!
任博克:要在儒家的经典找,儒家的也有。
何乏笔:这在儒家的手里就死掉了!“善”到什么程度是极端的,会反过来成为“不善”呢?
任博克:这在钱穆处理得很漂亮、很棒的。《善与恶》那篇文章(16)参见钱穆《善与恶》,收在《湖上闲思录》,《钱宾四先生全集》:3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9—53页。,善离开恶回不来,回不到恶的时候,那个善就不只是善,而是恶了。然后他也举很多例子,就像健康跟生病,你太健康没有小病,小病是什么呢?你想想看,你上厕所是小病,睡觉是小病,没有小病的作用就垮了,其实小病是为了要保持身体健康,但如果你健康到睡不着了,或者身体没有代谢作用,没有死掉的部分,那也不好啊。
赖锡三:那就是长生不老啦,长生不老是病态。
任博克:对啊,所以这个才是“中”,它如果太远了,远到飘了回不来,就是恶了。
赖锡三:只有死生一条一贯才会变化,只有生没有死,极乐世界也好,天堂也好,都是飘的太远而回不来。
任博克: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你要讲儒家,就算是朱熹、程颐,你问他们什么是善,那他们一定会说:“过犹不及”就是恶,“中”才是善。那“过犹不及”怎么判断,我觉得钱穆那段话说破了,基本上应该是有程度的问题在,孔子说“再可”,有人跟他说三思,是先要思,思是好事,但是思得太多也不是好事。太多的善就不善了(17)语见《论语·公冶长》篇19则:“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关于“再,斯可矣”一语的意思,可以参考钱穆《论语新解》,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72—173页。。
何乏笔:这不是“相偶论”吗?善、恶如果是互相依赖的。
赖锡三:相偶论,人跟人之间讲关系性。
何乏笔:阴阳或善恶。
任博克:那个是一个忌讳词吗?
何乏笔:在杨儒宾那边有“相偶论”与“体用论”两种理论模型(18)关于“体用论”与“相偶论”的意思,读者可以参考杨儒宾的两篇文章:《导论:异议的意义》《从体用论到相偶论》,收在《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36,37—83页。。通常新儒家是反对相偶论,肯定体用论。杨儒宾是肯定两者,试着调和它们的关系。基本上,相偶论是说“善”与“恶”是互相产生的,没有善恶之外的善,没有比在善恶关系中更善的善。新儒家反而会认为,如果没有超越善恶的善,那就没有道德可言。
任博克:杨儒宾就是这样觉得吗?
何乏笔:这就是体用论。
任博克:善、恶也不例外,善、恶恰当的让置中的状态,你可把它称为“至善”。至善好了,但是问题是下一步,下一步能不能说是“太至善”?这就是相偶的那个失调。
何乏笔:所以钱穆没有被新儒家接受,也不想被归类为新儒家。
赖锡三:说“至善”也好,说“无善无恶”也好,总之不能离开相偶,一不能离开二。如果先肯认一个先在的“本体之一”,再去辩证地包容“二”,那么这个至善之体或无善无恶之体,已经形上学本体化了。所以相偶的立场是,一定要在不断运动的关系里头来谈“中”。
何乏笔:我觉得,这是牟宗三无法接受的。我们想从“相偶关系”的内部来思考,这杨儒宾应该会同意。但“体用论”通常就是拉开距离,对不对?
赖锡三:还是要拉开一个超越的距离,“相偶论”对“体用论”来说,就是整个立体感被水平化。而水平化很难被他们想象为具有超越性,这也就是“无体、无理、无力”的老问题。
何乏笔:没有hierarchy。
赖锡三:对啊!没有hierarchy。超越性被想象成垂直性的,我认为这是受了语言的诱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metaphor 的问题。如何思考“天”的超越性隐喻?《庄子》的《逍遥游》是个好例子。文章一开始讲“鲲化鹏徙”而飞往高空、远方天池,以为那里才有“天之苍苍”的正色,可是当大鹏从天空俯视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才领悟其实“天”无所不在,哪里是往上才有“天”,四方一切尽皆“天”矣(19)《逍遥游》的原文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关于《逍遥游》此处“视下”的形上“反讽”意义,可参见赖锡三《〈庄子〉的关系性自由与吊诡性修养——疏解〈逍遥游〉的“小大之辩”与“三无智慧”》,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18页。。可是在人类的身体经验上,“天”被感知为升上、“地”被感知为就下。这种原始的身体知觉感所形成的语言,在概念化的过程可能会变成一种直观预设,不容易克服。但如果不透过纵贯的身体感来想象,改换成水平经验,那么你就要重新描述超越性,例如:可以透过 transformation 来重谈超越性,或是用海德格的方式来重谈超越性。当然新儒家接不接受这种超越性,是另一个有待辩论的问题。
任博克:对啊,所以这就是很微妙的问题,像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语言的问题,也许我可以跟杨儒宾一样,你要说一个“体用”也可以,说一个“相偶”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理解它。你说“中”,像钱穆那种说法,他也会自以为在说明朱熹,这个就是朱熹的意思,那为什么朱熹还要强立一个“理”,讲“理一分殊”?毕竟要有一个“中”,没有那个“中”,那些东西都会跑得太快太远,没有办法回到另外一边,这个就是恶了。无论是健康啊、势力啊,或者一般说是正面的东西,不要离负面的东西太远,这个就是“中”。我会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
何乏笔:This is all Naturalism.我要说的是,对当代新儒家来说,这就是自然主义,从自然的规律要谈出“道”是不可能的。
任博克:我觉得在朱熹那里,谈的就是一个构造,“仁义礼智”跟“春夏秋冬”是一样的构造,一样的构造就是“理”。“理”的构造是什么,就是相偶啊,相反相成的,春秋的关系,昼夜的关系,昼夜之道,它怎么可能没有吊诡,整个四季构造就是一个吊诡。所以,无论你怎么说,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你闯了红绿灯,确实就是吊诡的。他们所要的是这样,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的也是这样。
何乏笔:这个当然是比较粗俗的例子。
赖锡三:我想牟宗三可能偶而会闯红灯,牟宗三还满好玩的!
任博克:对啊,我也觉得牟宗三的生活满多彩多姿的呀。
赖锡三:我觉得这种 phobia ,应该来自于语言没有弄清楚,他们在很多的语言系统里面偏执单一种语言系统的描述,一旦你偏执了,你就会排斥其他不同的语言描述。而因为单一种语言不可能把事物描述清楚,也就是我们说的,必须让不同的是、非相互对照,你才会变化、才会明,才会变通。一旦你固着在一种语言系统里面,用这种系统把所有的事情纳进来,构成这个理,coherence 所有事物的时候,这个本身就会掉入一种恐惧,就会排斥别的描述,会觉得它很危险,这样就没办法自我转化了。很多的恐惧跟这个有关系,你的东西相对比较稳定统一,你所给出的东西就会更执着,因为你觉得这个很明确。但是你受到的质疑、撞击越少,你面对吊诡运动的能力也会越弱,越恐惧。这也是我观察牟宗三之后的新儒家,他们不太读别的东西,最简单的,他们不太读新儒家之外的东西。那你录放进来的 coherence ,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意义图像,这很容易就变成意识形态了。但是,若他能长期跟不同的系统这样那样,我不认为他的头脑不会被打开。当然会啊,没有固而不化的东西,再怎么固执也会化啊。
任博克:难道他们对天理的理解没有内在的矛盾,或是“吊诡”的成分,你觉得那个是牟宗三原来的想法吗?
何乏笔:例如天理人欲,我觉得新儒家这方面的讨论还是相当对立二分,根本不会承认任何的天理是离不开人欲的。一旦此区分不明确,岂不是在为一切欲望辩护吗?这种话语就陷入诡辩,丧失天理的崇高。
任博克:诡辩辩护自己的恶行,是吧?
赖锡三:天台的修恶多重要啊!处理欲望的问题,就是生命力的全部肯定。全面肯定包括自身的矛盾冲突,你要有办法回应或转化这些东西。
任博克:但是他们不会承认那个人欲是天理的偏,或者部分的,那是程颢的说法,程明道的说法。
何乏笔:灭人欲吗?
任博克:那是因为《乐记》刚好用了这个字,但是这个就是语言的问题,它指的所谓的“灭”是什么灭,你灭一个偏就是把偏包含到“中”去,这也是一种灭,不一定是实体化的消灭(20)原文参见《礼记·乐记》的两段文字:“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与“人欲”的对举表式,以及“灭”和“穷”这样的用词,在理学家手上形成以“一者”取代“另一者”(或者以“一端”辩证地涵有“另一端”)的体用关系表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24)“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12)“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13)。
赖锡三:问题是用这种语言的时候……
任博克:会一步一步地引导那个想法。
赖锡三:对!所以当我们使用语言表达,而没有吊诡觉察与反讽暗示的时候,二元性的语言陷阱就会时常出现。
任博克:对。在天台的话,就会说你要离欲,也要住欲望,可以说灭人欲,也可以说住人欲,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越住越离,越离越住,这样才对。
赖锡三:对啊,你去观察老庄与孔孟的用语状态。如果你是觉察的,你就会有吊诡的语言出现,一旦都没有使用到吊诡的语言,那就表示你对吊诡思维,对生命的吊诡性没有高度觉察。不然怎么会用语言强调“道统”到那种地步?批判异端为什么会批判到那种地步?
任博克:例如你说谁啊?
赖锡三:《孟子》不是就有这种倾向吗?例如所谓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善恶之辨。我知道你对儒家更为同情,我也有同情儒家的部分,但我现在是要讲思想的光谱偏向,在讲一个细部辨别的问题。如果《孟子》对“吊诡思维”是有高度觉察的,那么它在面对不同立场的是非问题,面对主体内部他者性的修养问题,就会呈现相当不同的取向来。所有的语言都有可能被误用、被误读是没有错的,大部分的语言表达都建立在二元结构,所以在实践操作的时候,也就容易掉入“一偏之见”“一端之知”,例如当理学家说“存天理、灭人欲”,佛教徒说“放下执着”,大部分人都会被引导到“断灭、舍离、放下”这一边来,这样一来,生命力便被切割成绝对对立的两部分,但《庄子》的“撄宁”或天台宗的“不断断”,正是回到吊诡的实践与表达。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便是掉入“去撄成宁”的片断之见。“不断断”才是“即撄成宁”的吊诡修养。
任博克:因此,我们有时候讨论这种问题会走歪了,你说得很对。其实如果你真的去研究那些东西,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用字难免会被误解,然后一代传一代。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用词?你说要解释“灭”这个字,天台会觉得:这里有个不同的方便法,我们说“灭”一般人第一次听,可以去灭,灭了一阵子,再去发现“非灭而灭”。
何乏笔:灭不了。
任博克:对,也许一般人就会开始有这种想法,这就是一般通俗的广播。
何乏笔:而且不只是灭不了,反而是加强了。
任博克:不只是加强,是法门啊。
赖锡三:所以天台会这样说,最好的灭法就是去实现它,通过欲望的实现,它会自然灭。一旦你不让欲望实现,你要完全消灭欲望,它只会增强或变形。其实这也不是怎么难理解的道理,每个人多少都可以自我体会。
何乏笔:这个道理,欧洲思想可能在20世纪才真正领略。例如,在精神分析里面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但之前几乎没有相关的讨论。不过,道理可能是无意识的,像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研究性史的时候,特别批评所谓的“压抑假设”(repressive hypothesis),强调基督教根本没有压抑性欲,反而加强了性,使得有关性欲的话语蔓延,因为要求每一个人不断地讲性。
任博克:变成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三人大笑)
何乏笔:而且,神父天天要听大家关于性想象和性经验的告解。但这里面的逻辑不是自觉的而是吊诡的。福柯认为,连精神分析都还在这个不自觉的逻辑里面,因为精神分析只是颠倒对欲望的态度、要解放欲望,但还是在欲望主体的逻辑里面。所以,对“吊诡”我们到底如何能自觉呢?历史常常显现出不自觉的吊诡。
赖锡三:不去自觉吊诡,其实也逃不出“吊诡运动”的命运。只是这种不自觉,经常会让吊诡运动从一个极端高速摆荡到另一个极端,因为摆动频率又大又快,人会被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很难在每一个点上,有定力地去觉察它。这样的话,历史命运会从此一极,很快地摆荡到彼一极。例如:禁欲的一极,很容易导致欲望解放的大泛滥,而泛滥太过又容易导致下一波段的大禁欲。我们常常看到这两种极端的“相反相成”,它们其实也是离不开“吊诡”的力量逻辑。
何乏笔:所以,福柯在《性史》有一个说法:恰好在大家主张“性解放”的时候,就要主张“性节制”。也就是说,到了一个极端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往另一个极端去发展。知识分子或哲学家的自觉也是如此吗?“自觉”似乎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联结在一起的。所以福柯也说,20世纪法国主张性解放的作家 André Gide 如果生活在古希腊,他就会主张性节制。不同的时代就要有不同的回应方式,不是对所有情境都有同样标准的回应方式。
赖锡三:大家都说“东”,你就要提醒“西”,大家说“西”的时候,你就要提醒“东”,钱穆不正是这样提醒吗!当说“东”说到已经没有“西”的时候,就不是好的“东”了,自身成了不好的东西了。
任博克:失去他的东啊,失东的东。
何乏笔:但这怎么自觉呢?
任博克:我觉得,你们现在讲的这个新儒家的问题至少是一步,就是要避免立任何一个完全脱开吊诡的自立的东西,那个逃不了吊诡的意思的彻底化,他们总是以为:这样我们解决某个问题,就没了。
赖锡三:要不断自我反讽,才能让自己避免往单边方向去极端化,《庄子》的《齐物论》就是这样提醒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别忘了“自我反讽”,既提醒自己,不要极端化地停在那里,同时也提醒读者,不要被我的表达带向回不来的远方。
何乏笔:“逃不了吊诡”这个说法,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吗?
任博克:所以,你一边可以说这个是否定一切形而上学的讲法,一边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必然性的顶点。天台就是这样,你要说什么是“体”或“无体之体”,你说哪一边都可以啊,但是看情况你要用哪一个用词,就是要提醒自己两个都是偏说。因为,奇怪的是,如果你想彻底消灭废除形而上学,那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如果你想立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其实你已经定了一个不变的框框,才能够从头到尾维持自然主义的立场。这个前提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而不变的形上前提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自身已经包含了吊诡的形而上学。其实说起来,我觉得哲学史上已经有了一些很有启发的例子。譬如,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实体形上学、一元论的形上学、理性主义的形上学,但是我觉得仔细看,斯宾诺莎所谓的“实体”正好是无体之体,无实之实,在他的定义之下,所谓一切皆实体就等于说一切无实体。把“实体”概念推到底就成为“无实体”。他讲的“一神”也是证明“无神”。黑格尔(G.W.F.Hegel)也是一样。他所谓的“逻辑”推到最彻底,并不是废除一切矛盾,而是证明一切都矛盾了。你要说他是形而上的吊诡,就是离不开吊诡的意思,春有秋、生有死、仁有义。所以,我觉得不用避免形而上学,反而要发挥到底,发挥任何形而上命题到底,它就会显现出来它很健康的吊诡性。问题不是有了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彻底推到底,推到它的吊诡处。新儒家应该也是:只要按照原来超越规范之立的路,一直推到它“枢纽”“四季”等内在构造,就会显现它的吊诡性质。
赖锡三:太棒了,这可以作为今天最好的结论:将形上学彻底化正是走向吊诡之道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