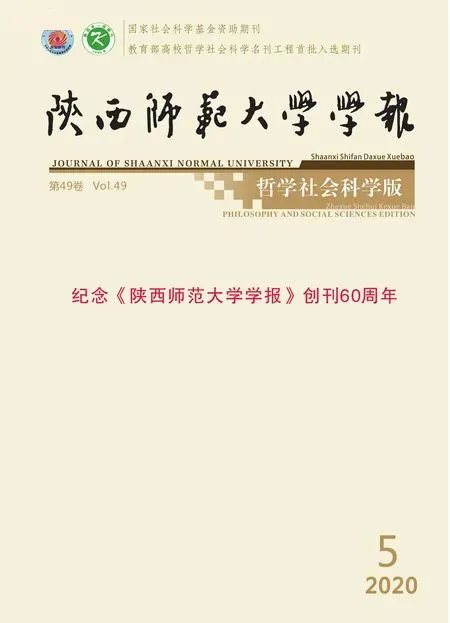从张载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阳的“性命双修”
——兼论“儒道互补”在关学与全真道之间的退守与坚持
李山峰,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35年前,陈俊民先生在其第一本著作——《张载关学导论》(1)该书实际上是陈俊民先生的《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在正式出版之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为陈先生出席国际会议刊行的“内部试行”本。的附录中有一篇《全真道思想源流论》的论文,当时丁为祥正跟随陈俊民先生读研究生,屡读而甚为不解,觉得澄清张载关学的著作何以一定要以全真道的思想源流作为附录?现在,数十年过去,笔者才约略感觉到陈先生的关怀所在,这就是究竟应当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关学这样的地方学派。当然,此中不仅涉及地方学派与地域学风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中国思想史中的两大骨干——儒与道的关系问题。今天,当我们面临如何振兴关学研究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振兴关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笔者这里不辞孤陋,尝试着在陈先生前文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一点思考,并试图将陈先生隐含的问题显性化,以助力于关学研究。
一、 地方学派与地域学风
说到关学与全真道的关系,就不能不首先面对地方学派与地域学风的关系问题。因为就学派而言,关学与全真道完全可以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学派,且分属于儒道两家,但是,如果我们跨越儒道两家思想之不同取向,则又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许多共同性,比如同产生于关中,时间相隔也不足百年;而张载所居的眉县横渠镇与王重阳所处的咸阳刘蒋村直线距离也不过百里左右。但这样的现象也同样逼出了黄宗羲(全祖望)那著名的一问:“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1]1 237黄宗羲、全祖望师徒当然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这一问题的,但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其视域却是由关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难道曾经“不下洛学”的关学竟在一夜之间消弭于无形,从而使黄、全师徒不得不发出“再传何其寥寥”的感慨。当然,黄宗羲、全祖望师徒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答案,这就是由于关中遭逢“完颜之乱”,因而使“儒术”陷入“中绝”的地步。
也许是对黄宗羲、全祖望师徒这一解释之不完全认可,所以陈俊民先生才执意在《张载关学导论》的附录中加上了对“全真道思想源流”的考论。但陈先生似乎也不能随意跨越儒道之间的藩篱,所以“完颜之乱”仍然是陈先生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基本解释。今天,当我们从关学这一地方学派出发来面对这一问题时,就可以发现在关学与全真道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因素。当然这些共同因素首先需要我们把地方学派与地域学风加以暂时的区分和隔离,然后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共同性与互通性。
当人们面对一个学派的时候,吸引人们目光且作为学派之为学派的标志性因素就是该学派所以成立的核心观点与基本宗旨,但这些宗旨和观点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首先是一定的地域学风的产物,也是在一定学风的基础上生成的,这就形成了本文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地方学派的宗旨、观点与其地域学风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更为根本的问题。从一定的时空横断面来看,一个学派的宗旨、观点固然是该学派之为学派的标志;许多学术争论往往就是因为对某学派的宗旨、观点的不同理解而形成。但是,如果我们从一种纵向的具体发生的角度看,则一个学派的宗旨、观点可能恰恰又是一定的地域学风的产物;而不同的学派及其不同的宗旨、观点也可能会因为时代的不同机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其地域学风却仍然可以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这就形成了一个视角的转换:从一个时代的共时态出发,人们对一个学派的认识往往会集中在其基本宗旨与某些主要观点上;但如果转向历时态,则所谓宗旨与基本观点可能就会成为较为相对的因素,而地域性的学风则往往具有超越学派分歧甚至超越时代的因素。
从地方学派与地域学风这种不同的视角出发,也可能会促使我们在关学与全真道之间看到更多的共同因素,从而让我们对黄宗羲、全祖望师徒对于关学“再传何其寥寥”的感慨作出新的理解。当然,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学派与学风的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地域学风的角度来理解从张载到王重阳这种从关学到全真道之间的转换现象。
二、 退守与坚持: 在儒与道之间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也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当张载从事学术探讨时,他并没有所谓“关学”的自觉,而只是从事所谓“道学”探讨。因而,其在答弟子范育的书札中写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2]349从张载的这一忧虑可以看出,他当时不仅自觉地从事道学探讨,而且还希望将“政术”纳入到“道学”的关注范围,即以道德理性作为各种政治举措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张载的这一忧虑,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嘲笑其迂腐,但“推父母之心于百姓”却绝不是一个所谓道德高调所能说明的,而是必须有其真实内容与具体举措的。所以,张载接着说:
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如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2]349
从张载师徒的这一探讨可以看出,张载不仅是今人所谓的“迂腐之儒”,甚至还迂腐地要求将所有的政治举措都纳入到儒家的道德理性——所谓“父母之心”的角度来权衡。所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376,大概也就首先落实在这种“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的“父母之心”上。
至于关学,其起源自然是因为张载讲学于关中,但“关学”之具体得名,则起码是南宋以后的事。自朱子编《近思录》而选辑张载文献于其中,张载思想便成为南宋理学主要继承对象之一,不过在朱子看来,“横渠之于程子,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3]2 363。很明显,这等于是将张载之学置于有所偏的先驱的位置上。那么,朱子何以持如此看法呢?他说:
横渠尽会做文章。如《西铭》及应用之文,如《百椀灯诗》,甚敏。到说话,却如此难晓,怕关西人语言自如此。[3]2 362
显然,这是朱子因为张载哲学之“难晓”从而将其归结为“关西人”的语言,大概也就可以说是所谓“关学”称谓之最初发轫吧。因为朱子既将张载归结为二程之伯夷与伊尹,又因为其意旨“难晓”而归结于关西方言,这可能就成为“关学”所以立名之初始(程颐时只有“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之类的赞叹,但没有将“关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学派)。此后,所谓“关学”也就成为张载哲学的代称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张载在从事“道学”探讨时,他既没有想到后来作为地方学派的“关学”,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整个宋明儒学之统称的“理学”,但对于“道学”,张载当时倒是非常自觉的。这说明,在张载看来,他的“道学”探讨,对于关中人之自觉而言,自然可以称为“关学”;但对全国士人而言,则可以称之为“理学”。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关中之“道学”或“理学”来称谓其所开创的“关学”了。
但作为地方学派,“关学”的探索宗旨究竟何在呢?简括而言,这就是以“三以”(2)所谓“三以”即张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宋史》将其概括为“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见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6页。为出发点,以“四为”(3)所谓“四为”则是张载道学探讨所确立的人生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见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为指向,并通过“诚明两进”,从而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用张载的话来表达,这就是:
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2]20
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2]20
虽然中国哲学一直以“天人合一”为最高指向,但遍检历史文献,可能还没有人比张载对儒家的“天人合一”追求表达得如此明确而又恰切的。
但就是这个曾经产生了张载道学的关中,却在不足百年之后又成为全真道的发源地,(4)张载(1020—1077)、王重阳(1112—1170),他们二人不仅都生存于关中的核心地带,而且也几乎在同样的年岁(张载57岁,王重阳58岁)去世,张载去世当在1077年年底。请参阅李山峰《张载卒年考》,《唐都学刊》2013年第5期。无怪乎黄宗羲师徒不得不以“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的感慨来表达其深深的不解。当然,从《宋元学案》到陈俊民先生的《全真道思想源流论》,都是将其归结为“完颜之乱”的。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看,这样的归结并没有错。但这种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归结能否说明二者之间就全然没有关联呢?难道产生了其盛“不下洛学”的关中,却在不足百年之后就“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未留下一丝痕迹?从社会思潮的影响与人文精神积淀的角度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让我们从王重阳的人生履历中寻绎其思想转变与演化的轨迹。请看陈俊民先生笔下的王重阳及其早年经历: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1112年),王喆生于终南刘蒋村,“始名中孚,字允卿。自稚不群,既长美须眉,躯干雄伟,志倜傥,不拘小节。弱冠修进士业,系京兆学籍,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然颇喜弓马,金天眷初(1138年),乃慨然应武略,易名世雄,字德威;后入道,改称今名(王喆)……”从政和二年到天眷初,仅仅二十七载,王喆三易其名字,这不正表明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坎坷之途和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动吗![4]145
陈先生的这一概述基本上厘清了王重阳出仕前的履历,尤其是其三易其名以及由“修进士业”到“慨然应武略”一点,清楚地表现了宋金之间的富平决战对于王重阳早年的影响。需要补充的是,所谓“完颜之乱”其实就指1130年宋金双方在陕西富平的一次战略决战。这一决战本来是为了扭转南逃的宋高宗被金人一路追打的被动局面,因为川陕一带宋人还有数十万兵力。按理说,由于金人的主力主要集中在江淮一带,因而这是一场很有把握的胜局,但由于主帅张浚求战心切,加之指挥失当,结果却被金人彻底打垮了宋人收复北方的军事实力,所以一直被史家视为一次最窝囊的决战。对于这一决战,由于王重阳当时正准备到长安“修进士业”,因而可能还说不上具体、直接的影响,但其此后“慨然应武略,易名世雄,字德威”的改名却不能说他没有受到这一决战的影响。可是,当其考中了金人的武举之后,却只在其朝廷当一名小官,于是,这就有了其后来的“三十六上寐中寐”[5]137一说,并由此埋下了其日后创始全真道的种子。
对于王重阳从修进士业而转考武举并三易其名这一点,按理说都属于报效民族国家之类的雄心壮志(张载早年也曾因为宋与西夏的军事对峙而研究兵法),其“易名世雄,字德威”的自号尤其表现了这一点。但是,王重阳为什么在进入了官场之后又萌生了创教的冲动,而且其所开创的道教甚至也无关乎民族国家,只关心个体之长生久视呢?这就成为一个十分费解的问题了。而其在开创全真道之后,又专门为自己挖了一个墓穴,并称为“活死人墓”,且自号“王害风”。今天,我们当然已经无法准确分析王重阳精神转向的主要动因与具体过程了,但起码应当承认,这样的穴居与名号包含着其对宋廷收复失地的绝望;而其“活死人墓”之穴居与“王害风”的自号也无疑包含着对陕西北宋遗民的一种明确的讽刺意味。这种讽刺、绝望的极致,自然会导致一种对现实自我的彻底否定,或者说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来表示其对时局的绝望。这一点,可能也就是其“活死人墓”之穴居与“王害风”的自号的由来。
从文武兼赅的“世雄”到以长生久视作为“活死人”的自我追求,历史上也许并不缺乏这样的先例。孔子就曾因为周礼的问题而专程赴洛阳向老子请教,但老子的回答却全然无关于周礼,而只是关心自我之如何免遭伤害,并以如下内容作为对孔子的回答: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6]2 140
证之于《道德经》中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7]29,说明老子确实兢兢念念于自我之存身关怀。在老子看来,无论从孔子所羡慕的历代先贤还是其拯救社会的愿望,其结果可能都是“无益于子之身”的。对当时的老子来说,其这样的看法无疑是面对当时的战乱而以隔岸观火之心的角度得出的;但对王重阳来讲,则其不仅有理智的思考,而且还不得不受情感的煎熬,所以说,其“活死人墓”的穴居与“王害风”的自号,首先表达了其对此前自我的一种彻底否定。
关于王重阳从“修进士业”到创立全真道的思想转向,陈先生还征引金代学者杨奂的分析说:
人心何尝不善,而所以为善者,顾时之何如耳。方功利驱逐之秋,而矰缴已施,陷阱布设,则高举遐飞之士不得不隐于尘外,此有必然之理也。然则古之所谓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兴邪。(5)转引自陈俊民《全真道思想源流论》,《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杨奂以“避地避言”之“隐”作为王重阳创立全真道的动力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足以说明其既然已经创立了全真道,为何还要以“活死人墓”的穴居与“王害风”的自号来惊世骇俗?所以,其穴居与自号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这个更深的原因可能也就表现在全真道“性命双修”的宗旨上。关于其教之所以称为“全真”,自然是指“全精、全气、全神”之所谓道教的“三宝”,而其“性命双修”的宗旨自然也是就其“全真”精神的人生落实而言的,就是说,所谓“全真”也必然要落实为现实人生中的“性命双修”。比如王重阳论述说:
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衮出入仙坛。[5]30
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名曰性命也。[5]294
宾者是命,主者是性。根者是性,命者是蒂也。[5]295
这不仅是明确的“性命双修”主张,而且还是非常典型的“先性后命”宗旨,并通过“先性后命”以实现“性命双修”的指向。
关于“先性后命”,虽然全真道在明代才表现出明显的南宗和北宗,[8]但实际上,自全真道创立以来,王重阳就直接通过“先性后命”来落实其“性命双修”宗旨,甚至也可以说,其“性命双修”主张本身就是通过“先性后命”才得以明确表达的。因为从王重阳创立全真起,此前的道教虽然也有关于“性”和“命”的各种论说,但并没有专门就“性”与“命”之主宾与先后的区分来立教。从历史的角度看,真正区分性与命的是孟子(庄子也有相近的论述(6)庄子说:“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8页。),其所谓“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与“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9]6 039可以说就是最早对性命进行区别与关联性表达的。而在两宋之际,距离王重阳时空距离最近而且明确对性命进行区别表达的恰恰是张载。请看张载的如下论述: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性通乎气之外,命行乎气之内。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2]21
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言其气也;论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2]23
如果将王重阳“性命双修”的宗旨以及其“先性后命”的主张与张载的上述论证稍作比较,那么无论王重阳如何论说,实际上也都可以视为张载论述的道教之用。当然,全真道“性命双修”的宗旨及其“先性后命”的主张,也可以视为张载的虚气、形神包括双重人性关系及其诚明两进主张的一个有力的反证,因为他们不仅同属于北方学派,而且都属于关中地域学风的产物。如果考虑到王重阳早年曾长时间地在长安“修进士业”,那么其所谓“先性后命”的主张与“性命双修”的宗旨也就有可能是对张载论述的借用或照搬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关学到王重阳坚持“先性后命”的主张及其“性命双修”的全真道,说到底不过是因为遭逢战乱,所以传统的“儒道互补”也就不得不落实于关学与全真道之间,并将张载弥贯天地万物的性命之德退守于士人个体的性命之间。所以说,全真道“先性后命”的主张与“性命双修”的宗旨不过是儒道融合而又“互补”的做人精神的一种退守性坚持而已。
三、 关学: 学派与学风之不同视角
从关学到全真道,思想的跨度不能说不大,而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到全真道完全从个体层面展开的“性命双修”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转向。如果从思想观点的角度看,这二者不啻有天壤之别,也根本无法结合在一起进行把握,但如果从地域学风的角度看,那么也可以说他们就源自同一的关学学风,是同一学风在不同时运下的不同表现。所以,在北宋“学统四起”的条件下,自然可以培育出张载的“四为”精神;但在宋金战乱的格局下,士人也就只能内缩为完全个体化的“性命双修”追求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的关学研究到底是指由张载所开创的从“三以”出发以指向“四为”的天人合一之学呢?还是也可以包括王重阳以“性命双修”为宗旨的“先性后命”之学?当然,无论怎么说,张载所开创的道学无疑就是纯正的关学,但从张载关学出发,吕柟所引入的程朱之学、冯从吾所引入的阳明心学以及李二曲综合程朱陆王所形成的体用全学,一直到近现代的刘古愚、牛兆濂之学,也应当说是标准的关学。但这样的关学标准实际上等于仅仅是从儒家立场上的取义,难道关中的地域学风就只能产生儒学吗?一当转向地域学风的角度,那么关学的范围肯定要扩大,起码扎根于关中地域学风的思想文化流派,都可称之为关学,因为在关中形成的学派说到底都是其地域学风的产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出黄、全师徒对于关学“再传何其寥寥”的感慨实际上仅仅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所发出的感慨;而其对这一现象之“完颜之乱”的归因也只是针对儒学而言。对于黄宗羲、全祖望这样的儒家学者而言,这样的归因无疑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也可以说是完全合理的,但对关中地域学风而言却未必就是合理的。因为关中地域学风不仅培育了张载这样的儒家学者,而且也形成了王重阳的全真道教;甚至,极而言之,东晋的僧肇、唐代的宗密似乎也同样可以划进受关中地域学风影响的范围,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关中地域学风的产物。如果说过去以张载作为关学的划界标准是因为儒学毕竟代表着我们民族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因而佛老之学理应不算在其中,但如果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毕竟儒佛道三教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应当仅仅研究儒学而不研究佛老之学。因为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只以儒学为对象,那么这对传统文化而言,毕竟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划界和取值,不利于其真正振兴。[10]
正是从地域学风的角度看,我们才可以理解陈俊民先生为什么要在完成《张载关学导论》之后立即对“全真道思想源流”进行考论,而陈先生当年所思考的实际上也就是试图从地域学风的角度对关学进行划界,以拓展其领域和范围,并借以回答黄、全师徒所谓“再传何其寥寥”的问题,因为关学确实已经从张载时代的“道学”变为王重阳时代的“全真”了。这样看来,狭义的张载关学虽已“寥寥”,但关中地域学风却并没有“寥寥”,而是在“完颜之乱”这种社会战乱的打击下转变为关中士人以“先性后命”为特征的“性命双修”之学了。
陈俊民先生的这一设想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这种设想毕竟是从地域学风出发的,因而并不局限于思想宗旨的范围,而是试图对这种地域学风基础上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与全面、多样的继承。就是说,我们的关学研究虽然是从张载出发的,但却并不局限于张载关学的范围,起码在关中这个地域学风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流派包括儒释道三教都应当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其智慧与精神也都是我们所应当继承的。
但仅仅从地域学风出发毕竟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在周秦汉唐时代,由于长安是国家的首都,因而从今文经学到古文经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也都纷纷以长安为祖庭,而全国各种不同的主流学派也无不流行于长安,但佛道二教甚至包括作为西方传来的景教、拜火教等思想流派却并不能算是关中的地方学派,也并不仅仅表现关中的地域学风。原因很简单,这些文化团体或思想流派虽然也流行于关中,并受关中地域学风的影响,但因为其主要代表着整个国家或外来的社会思潮,因而并不显现思潮的地域与学风特色。只有在隋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这才使关中显现出其地域与学风的特色。因而,关学作为北宋时代关中所形成的地方学派,才真正显现出关中之地域学风上的特色。所以说,虽然关中的历史上也曾经流行过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但关中的地方学派却一定要从宋代的张载关学算起。
这样看来,地方学派之思想观点与地域学风的关系就要被颠倒了。虽然就某一个学派而言,思想观点及其宗旨固然是其所以成立的依据,但就对它的研究而言,则所谓思想观点包括宗旨却只具有极为相对的意义。因为在同一地域学风的基础上,既可以产生这样的学派(比如张载关学),也可以产生那样的学派(比如王重阳的全真道)。而从地域学风的角度来理解地方学派,这样的地方学派不仅有含括度,而且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而这样的地方学派研究,才能真正使地方学派呈现出多样的趋势。
四、 结语: 学派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学风的培养
从张载开创关学到我们今天的关学研究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7)所谓“一千年的历史”只是相对于“张载千年诞辰”之概略而言,并不是说“关学”就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传承。在这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关学”的内涵、范围在发展变化,而且所有的地方学派也都在发展、变化。那么,仅从地方学派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
从对地方学派认知的角度看,对一个学派的思想、观点包括其基本宗旨的把握当然应该说是第一性的任务。因为对一个学派来说,其思想、观点包括基本宗旨就是决定该学派所以成立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观点和基本宗旨,那就谈不到对该学派的认知。在这一点上,一个学派的思想、观点和基本宗旨不仅是其所以成立的决定性因素,是对其进行认知的第一性任务,而且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标志。所以,仅从对一个学派的认知来看,这自然是第一性的、关键性的任务。
但人们研究地方学派的目的却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认知,而是要通过认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存现实。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一个学派的思想、观点和基本宗旨的意义就变得非常相对了;而对其进行客观准确的认知其实也只具有极为相对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仅是因为思想观点与地域学风相比而言的相对性——在同一地域学风的基础上是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思想观点的;而且还因为我们的认知相对于主体之未来运用的相对性——对于主体应用性的价值选择而言,客观的认知其实只具有较为相对的价值。在这种双重相对性的基础上,地方学派研究的价值与其说主要在于形成某种客观的认知,即对某一地方学派的思想、观点和基本宗旨的准确把握,不如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地域学风之多维度、多层面的透视以及其多种可能性走向的预期。因为我们研究地方学派的目的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显现我们的博览多识,而是为了对地方学派所表现的历史智慧与文化精神进行激活与继承,从而使其生生不息并充分展现其多样的可能与走向。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学派研究的目的与其说是要侧重于对其思想、观点和基本宗旨的掌握,不如说更应当侧重于其地域学风的培养、转进与提升。因为只有后者才不仅关涉到地方学派的未来,而且更关涉到地域学风的未来。
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的。比如说,在宋明理学中,由程朱理学到明清气学一系,本来是包含着一种客观认知的走向的,程朱理学之突出格物致知本身就包含着这一走向,而明代“肩负道统之传”的曹端将朱子的天理体系包括其理气关系扭转为对“造化之理”的探讨就更接近这一指向。[11]515但此后的气学家有没有自觉地自我定位为自然的探索者呢?当然,在集权专制的明代社会,要求科举出身的气学家以自然的探索者来自我定位也许有点强人所难,即使作为古代气学高峰的王夫之也绝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自然的认知者与探索者,恰恰相反,王夫之的自题楹联就明确认为自己是“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12]116。至于以后的乾嘉汉学,不管其有多高的聪明才智,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因而也就只能在文字狱的打压下变成文字训诂与古董考据之学了。
如果说在集权专制的时代思想家不可能专注于认知之客观原则的确立无疑是有情可原的,那么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的东南沿海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格致书院,而与这些书院同时兴起的工商、学校也都一致地指向了器物制造之学。但国人却始终集中精力于器物制作之技术层面,而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器物制作技术之根本支撑的认知与科学理论。这就仅仅成为一种为了满足当前实用需要从而津津于对西方科技制作之术的简单“移栽”了。新文化运动后,国人虽然已经认识到科学认知与科学理论的重要性。而从1915年起,北大首开“格致门”,到了1949年,所有的中学也都纷纷开设“格致课”,这显然是试图通过程朱所阐发的格物致知来归类并汇通西方的科学认知精神,但人们的注意力似乎又集中在某门科学、某个领域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以及所谓投入产出的价值核算上,仍然没有注意到科学精神、科学理论与科学学风对于科学本身的促进意义。对于近代以来的这种现象,梁启超曾嘲笑那些八股先生动不动弄个“格物致知的意见”(8)梁启超嘲笑说:“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梁启超《清代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页。——即不同的学术观点。而熊十力则将这种学风比喻为“海上逐臭之夫”(9)熊十力在《为哲学学会进一言》中说:“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风,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辙,一切废弃。”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至于侯外庐先生则又形容为“死的抓住活的”[13]16。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用技术与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主张和学术观点上,却仍然没有注意到科学学风对于科学认知包括所谓思想观点的援助与支撑意义。这就是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请来了“德”“赛”两“先生”,并且中国社会也给了科学家以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国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认知学风却始终让人汗颜。
所有这些,实际上就是因为国人只注意学术主张与思想观点这种“硬件”,但却未能注意学风与学术素养包括学术环境这种“软件”的结果。不注意学风与学术素养,就不会注意某种思想观点、某种科学发现的具体形成,从而只能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他人的思想观点进行为我所用式的品评与择取。这又是中国学术话语始终缺乏客观性、稳定性的根源。比如,对于同一个张载哲学,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明清气学的话语系统中就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再比如,从张载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阳以“先性后命”为特色的“性命双修”,虽然他们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儒学与道教之不同立场的分歧,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所赖以形成之共同的地域学风及其不同的历史遭际,那么他们之间不同的思想命题、学术旨趣与不同的人生追求指向之间的分歧也就并不像人们以往理解得那么大,而黄宗羲、全祖望师徒也就不会以所谓“再传何其寥寥”来质问历史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从地域学风的角度来理解某种学术主张的具体生成,那么原本似乎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同思想流派之间,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无法理解的思想鸿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