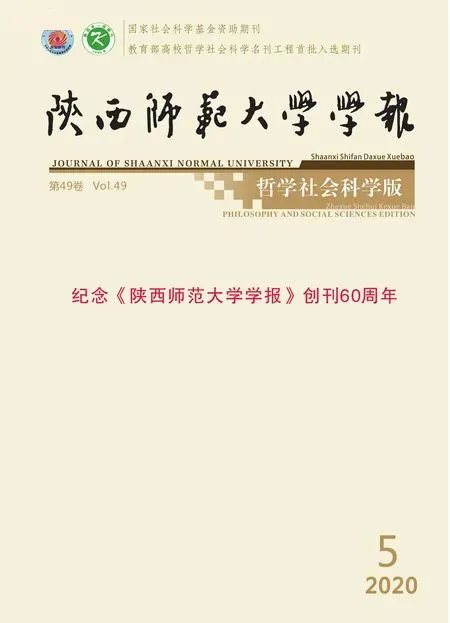语言适应与社会顺应
——语言视域下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思考
武 小 军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9)
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也促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并因此改变了人口流入地的整体社会结构。近些年来,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研究成果渐渐增多。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学界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以理性的观念审视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语言学界看来,当前的社会现实已呈现出和以往社会不同的形态差异,因此,一些问题自然浮出水面,引起必然的重视。例如,社会变革中的地域方言存现,城市社会融入中的方言变异与模式特征,新方言出现的可能性,语言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语言产业及其多样性发展、语言规划等等。因经济活跃而带来的人口流动,除了使得社会语言生活异常丰富之外,其产生的系列问题也令人不敢小觑。本文的立论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及笔者所做的两次语言调查(1)一是四川回流人口方言入声字口音调查,详见武小军《人口跨域流动与地域方言变化——四川方言入声字口音调查》,《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4期。二是流动人口在人口流入区的语言问卷调查,详见武小军《流动人口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主要探讨流动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城市社会对流动人口不断增强的语言适应能力等的顺应问题。站在推普和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的高度,本文认为,一座城市要实现和谐发展,除了城市个体要与之适应与融入外,城市社会也应与之实现共融。
一、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历时特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一直持续,未有断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我国虽“经历了3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但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历经的几个重要的时刻,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讲话、党的十四大等,不仅加速了城市化建设步伐,也促成了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性的人口流动,就一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受城乡收入、消费、福利等巨大差异影响与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等的诱惑,流动人口(主要指农业人口,农民工等)涌入城市,深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积极汇入城市经济环境,并由此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基本流动的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2)我国流动人口基本流动的阶段划分,依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 第6页。,即由流动数量相对较少、夫妻中某一人、外出逗留时间短、流动空间距离近等的第一阶段到流动数量相对较多、夫妻一起外出、在外逗留时间较长、流动空间距离扩大、人口流向多元化的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构成了漫长的时期,因其只是流动人口方式(人户分离)而不是人口迁移(农转非)方式[2]42,这就决定了其“流动”“暂住”以及“非融入”等的基本社会化特征。
1.从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的“流动”特质
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转移,“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在我国流动人口基本流动的第一、第二阶段,乡村“留守”(包括“空巢”)现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统计显示,因人口流动,全国农村共产生留守儿童约5 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有4 000万人,在全部农村儿童中占比高达28.29%。在这些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留守儿童占47.14%,父母双方外出留守儿童占52.86%,且多集中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如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等省,仅这6省的农村留守儿童就占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量的52%。[3]留守儿童的增多和留守现状从另一侧面也深刻反映出我国流动人口主要由中西部流出地向东部流入地大量涌入、靠打工获取经济收入的初始化特征。
伴随着乡村的“留守”现象,孩童跟随父母举家“流动”也逐渐突出,并随着人口流动的时间延续而日渐增多。统计显示,2008年举家外出的农民工为2 859万人,2009年为2 966万人,2010年为3 071万人,至2011年则高达3 279万人,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呈现出异常明显的增长态势。(3)数据出于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人口计生委报告》)显示,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4)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http:∥www.nhfpc.gov.cn/xcs/s3574/201610/58881fa502e5481082eb9b34331e3eb2.shtml流动人口的举家外出倾向,使我国的人口流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我国乡—城人口流动迁移正由第二阶段末期向第三阶段转变,其主要特征为:由夫妻外出务工经商,跨省跨区流动到在流入地站稳脚跟后,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流动人口的这种“流向”变化,除了使农村呈现的“空心化”并带来“人口的空心化”[4]特征继续加剧外,也造成了流入地城市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2.城市融入与“市民化”倾向
举家流动反映出了流动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深层的思想意识,这个思想意识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是单纯地受城市工作机会、收入以及生活居住环境的吸引,而后者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甚至孩童能在城市环境中定居、成长并最终脱离农村成为城市“市民”。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年,有30%的流动儿童是“出生后一直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即约有400多万流动儿童是在流入地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在那些出生后来“本乡镇街道”居住的流动儿童中,有30.1%的人是5年前流入的,而“出生后一直居住本乡镇街道”的流动儿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36岁(标准差为4.13岁),有至少一半的人居住时间为4年或4年以上,有75%的人居住时间为2年或2年以上。[5]由于城市融入的强烈意识和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排斥等“非融入”特征的尖锐矛盾,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倾向一直未能如愿以偿。随着这批流动儿童的长大以及乡村儿童(包括留守儿童)长大后的城市汇入,城市社会正刻不容缓地面临着重新的自我审视与调整。
近几年来,我国的流动人口开始经历着由“老一代”流动人口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且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老化速度快于全国人口。至2015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达29.3岁,较2013年增加了1.4岁,且居留稳定性持续增强,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5)参见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http:∥www.nhfpc.gov.cn/xcs/s3574/201610/58881fa502e5481082eb9b34331e3eb2.shtml这批“80后”“9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返乡务农的意愿大为降低”。(6)郭少峰《土地出让收入农民获利太少》,参见《新京报》2011年10月31日。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中,16—25 岁中41.4%的人没有承包地,36.4%的人没有宅基地,25—30岁中35.4%的人没有承包地,33%的人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只占7.7%。(7)郭少峰《土地出让收入农民获利太少》,参见《新京报》2011年10月31日。《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同时也指明了这批“80后”“9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注重体面就业发展机会,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并预测“随着流动人口总规模的继续增大,青少年(新生代)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总量将不断增加”。(8)参见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
二、 “市民化”驱动下的语言适应行为
伴随着人口流动,学界从不同角度积极追踪研究其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并冀望从一些社会表象深入挖掘其本质特征。在语言视域下,学界对流动人口到达流入地的语言变化进行了大面积的实证研究,并以此揭示出语言变化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关系。据统计[6],在2006至2017年间,针对流动人口(农民工)语言描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从研究范畴来看,既有语言使用问题,也有语言态度问题;既有流入城市内的语言研究,也有乡—城结合的研究;既有本体语言研究,也有应用语言研究。[6]研究调查地点广泛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宁波、义乌、绍兴、沈阳、武汉、长沙、东莞、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东、中、西部若干一线、二线城市。
1.向普通话趋同,方言内部进行调整
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也成为观察流动人口语言演变的重要窗口。屠国平通过考察宁波市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认为其普通话使用频率最高,“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被普遍认可”。[7]莫红霞调查了杭州市农民工后认为,“普通话已取代家乡话成为打工期间最主要的交际用语”。[8]付义荣通过对安徽无为县傅村进城农民工的采访研究,发现“傅村农民工普遍认为普通话‘更好听’‘更有用’”,对普通话的语言认同开始增强。[9]王玲在实证研究了外来移民在合肥、南京和北京3地的语言适应行为后认为,“外来移民,都从原来的单一语码使用者转变为双语或多语语码的使用者”。[10]俞玮奇的语言调查也证实,“进城后,在上海的公共场合以及工作场所约90%的农民工都是最常使用普通话,甚至在家庭中与孩子、配偶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极为明显”。[11]而新生代农民工向普通话趋同演变更是明显,张斌华的东莞调查证实,“98.7%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双言或多言者,普通话已经成为公共、工作等领域的主体语言”[12]。众多的研究结果无一不说明,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到达务工流入地,很快就改变了方言发音并向普通话趋同,虽然一些流出地人口普通话水平整体不高,发音不准,但他们仍然模仿普通话并尽可能多地在一些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和流入地人进行话语交流,并且对普通话的认同感增强;而随着流动时间的延续,对所属地域方言的评价度逐步降低。
笔者的语言调查也充分证实了流动人口的这种城市语言适应行为。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来到流入地,因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交际目的需要,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和在户籍地时完全迥异。在对外的语言交流中,方言使用量缩减,呈现出向普通话趋同演变的趋势。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42.4%的流动人口到达流入地工作、生活时,很快就学说普通话,有17.3%的流动人口则是“一段时间后”学说普通话,在极短时间内学说普通话的人数比率高达59.7%,流动人口表现出了较高的普通话认同感。[13]
在向普通话趋同的态势下,方言内部也主动积极地产生着变化。据笔者的语言调查,受城市社会的影响,流动人口到达流入地后,方言语音已开始普遍发生变化,方言语音的演变,在离开户籍地到达流入地(东、中、西部地区)时就可发生。[14]这种变化,不受流动区域的限制,也不受外出打工时间长短的限制,方言变化在向普通话靠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内部调整。笔者通过对四川方言入声韵的录音记韵观察,发现这种方言系统中相对独立、稳定的语言形态在人口流动中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其普遍规律是,流动人口将方言中的入声系统进行改造,使之逐步向阴声系统靠拢,从而更接近于普通话。同时,方言内部演变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特征,如中高元音央化,知章组入声韵母趋向为;中低元音阴声化,向对应的阴声韵母转化;借用阴声韵母,增加的入声读法;韵母范围不断扩大;多音入声字呈单音化发展等。这种演变规律不仅在流入地如此,而且还漫延至返乡回流地域。
2.顺应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语言角色定位
向普通话趋同和进行方言内部的调整,表面上看是一种语言演化现象,实则却是城市化融入中社会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流动人口为顺应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语言角色定位。因为“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农民工基于人力资本优势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普通话熟练者往往具有更多的培训机会、更高的工作技能、更为强烈的自我价值意识、更加健康的身心状态,以及更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关系适应能力”[15]。因此,流动人口的语言演化在与社会发展、社会交际要求等方面才显现出一致性特征。从整体面貌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种种语言行为,都表明了他们为实现城市社会融入而进行了自身思维和语言行为的改变,至少已作好了融入城市的准备,力求和城市人在语言等外在形式上先趋同以趋平等,再逐步向其他方面渗透融合。
我国已步入了新老“两代”流动人口更迭发展的社会历史时期,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的语言观、思维观以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融合度成为令人关注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在顺应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其语言的角色定位更加明确。一是对普通话高度的认同感业已形成,并产生出积极的心理评价; 二是在各类场合尽量使用普通话,并认同为自身素养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是在一些场合规避家乡方言,尽量消除“外地人”特质; 四是学说流入地方言,让自己快速成为城市市民。在笔者的语言调查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来到流入地“很快说普通话”的比率为57.3%,较其父辈提高了25.8个百分点,新生代流动人口自认为在言语交际时能较流利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为89.9%,较其父辈提高了13.5个百分点。[16]流入地城市问路、候车乘车、就餐购物等开放型交际空间(9)指交际时空间范围较为广阔,并且除谈话主体外,周围受众(非谈话主体)相对较多,或交际谈话行为有可能被其他受众注意、聆听等。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普通话使用分别达到了86.8%、87.9%和88.1%;而方言运用则缩减为8.4%、5.2%和5.9%;对流入地方言的使用分别为12.9%、12.4%和14.4%。在流入地城市工作、打电话等封闭型交际空间(10)指交际时空间范围较为狭小,一般仅有谈话主体,周围受众(非谈话主体)相对较少甚至没有,交际谈话行为一般不会被其他受众注意、聆听。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普通话使用分别为87.3%、84.5%;方言运用缩减至6.7%和9.6%;流入地方言的使用分别为15.7%和15.6%。[16]上述调查结果证实了受内在思想支配下的语言变化事实,学说流入地方言虽然量少,但已显现出一种必然化趋势。可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基本上改变了老一代流动人口对普通话的单纯模仿,而转变为一种自觉的语言行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方言会由原对普通话的“模仿”而形成的语言“突变”模式逐渐转变为向普通话真正趋同的“渐变”模式。而随着在城市成长及其工作、生活渐趋稳定,他们选择使用普通话以及转说新方言将成为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到达流入地,为了实现其“市民化”进而融入社会,率先在言语交际上主动改变方音发音,以流入地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形式去进行说话与交流。流动人口的这种主动的“语言适应”行为和这些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内在思维特征与“市民化”趋向可谓一脉相承。
三、 城市社会顺应与不足
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强调语言与世界观的必然联系,并认为“一个人所习惯使用的语言结构影响着这个人对他周围环境的理解和他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方式”[17]。本文无意识去推崇其“语言相对论”,但本文在综合考察流动人口基本流动的3个阶段后认为,流动人口在其流动的初始状态下,语言仅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而使用着,而随着举家流动以及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成长,语言就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交际工具了,同时还承载着其他社会功能。在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中,语言折射其世界观。所谓“语言适应”行为从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流动人口高度的语言认同观和城市认同观,但城市社会在顺应流动人口语言认同时,却表现出了诸多不足,也使得流动人口的语言演化、质量提升乃至全民推普工作遭遇了发展的瓶颈,若流动人口出现较多的融入不畅,也势必会影响到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
1.城市认同对语言认同的冲撞
从哲学和逻辑学意义看,“认同”常指“同一”或“相同”,反映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18]“认同”关联的两个主体,流动人口和城市社会,却并非双向对等,表现出极大的单向差异性。就流动人口而言,对城市认同的显著性表现就是语言认同,即作为一个群体对同一种语言(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方面心理活动的趋同现象。由于城市流入与交际的需要,流动人口普遍对高声望的普通话产生积极地评价并在语言选择上趋同,而地域方言由于评价度降低往往被局限于特定(或狭小)的交际空间和人群使用。
在语言态度方面,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到达流入地,对普通话和家乡话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评价与态度。有74.7%的人认为,使用普通话,大家都听得懂,便于日常工作、生活等的交流;有30.3%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有19.4%的人认为说普通话代表着一种时尚和发展趋势。[19]这种心理特征同时也伴随着在流入地对家乡方言的重新审视与评价,有77.3%的人认为,使用家乡方言,别人不容易听懂,不便于交流;除此,说家乡方言还显得土气、不好听,在外地说,会受到歧视和嘲笑等。调查中,当问及“回到家乡后,你是否还愿意说普通话”时,有41.4%的人表示愿意。当问及“若你再次外出或到其他流入区域,是否愿意说普通话”时,有84.3%的人表示愿意说普通话。而新生代流动人口较之老一代流动人口,对普通话的趋同及主观评价则更加明显。[19]调查中,在问及“你回到家乡后会否说普通话”时,有45.2%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表示“愿意说”,当被问及以后若“再次外出会否说普通话”时,有86.9%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表示“愿意说”。[16]
在语言行为方面,流动人口(农民工)在进城后为了适应城市生活,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态度以及语言能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改变以往的语言使用习惯,逐渐提升了自身普通话和当地方言能力。[11]较多的流动人口已由流动初期的单言人,逐步过渡成为双言(多言)人。因人口流动,普通话与方言紧密接触,在多语混杂状态中,普通话作为强势语言已对方言形成影响,社会语言面貌正向语言兼用(双语现象bilingualism )层次过渡。当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来到流入地,其语言往往会经历一个融合、渗透的过程,他们会由最初操家乡方言到经历普通话、打工地方言等的语言碰撞。这种碰撞的结果,就是将原有的单言人演变成为更多的双言(多言)人。调查结果表明,因人口流动已使得更多的人成为双言(多言)人,他们在流入地使用着普通话、家乡方言和打工地方言,并且语码转换日趋活跃。调查中,当被问及“目前,除了家乡话,你和他人交谈还可以较流利使用的语言”时,有82.4%的人选择了普通话,有17.6%的人选择了打工地方言。[19]可以说,流动人口的语言演变是由单纯使用家乡方言到学说普通话,再到学说打工地方言的过程。
以此看来,流动人口(农民工)“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必须在语言上做出调整,也即改变原来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等,在语言上完成农民工语言的再社会化”[20]。当我们把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看待时,他们的语言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适应行为,还只能称之为一种单向的运动变化。从认同理论角度看,流动人口的语言认同也代表着他们的社会认同观念,当“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21]时,社会认同便会产生。从本质上讲,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观念就是改变自己“流动人口”以及“城市边缘人”特质,积极地、潜意识地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城市“市民”的心理趋向。而站在流入地城市社会来看,流动人口则遭致了较多的社会不融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城市认同度较低。当我们把一个城市看作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单元之时,相对于异地、乡村,它是同质而有序的。这之中,包含了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地域认同(regional identification)、职业认同(career identification)和地位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等一系列可变心理因素的相对同质化,尽管这种同质化也包含了较多的异质化特征。流动人口积极的语言认同招致了长期积淀而成的城市认同——诸如穿着、习俗、口音、生活方式、城市户口、稳定工作、良好收入、子女城市就学、社区与环境、社会保障等的冲撞,从而减缓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以及“市民化”进程的步伐。因此,出现了一方面是积极地融入,另一方面却是消极对待的难堪局面。
2.语言变异模式下由量变到质变的维艰
由于城市社会的跟进不足,流动人口中出现了较多的“钟摆式”流动的“半城市化”城市暂住者,他们来到城市,多年勤苦工作,但却一直扮演着城市“边缘人”角色,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现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隐患。笔者的语言调查发现,流动人口来到流入地城市,语言面貌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语言具有临时性,二是语言具有非规范性。(11)参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该报告收录了笔者《四川籍外出务工人员语言生活状况》一文,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版。就前者而言,流动人口虽极力在改变方音,向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靠拢,但这种方音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尽快融入城市工作、生活,获取一份工作岗位和得到经济收入而致。向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靠拢的这种语言趋向具有很强的临时性特点,笔者通过录音记韵,发现一些字音呈“突变”而非“渐变”的模式,一些字的发音没有过渡音,直接由方言原读音跨越为新读音(即类似普通话的发音);一些字的发音还兼有新旧两种读音等,这些语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流动人口尚处于语言变异的“摇摆”阶段,其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的发音极不稳定。而随着城市认同的不足,流动人口返乡回流日益增多,他们由外出打工回到原居住地(或方言区)工作、创业,并受内部方言集团的深刻影响,重拾方言、放弃普通话,或在特定狭小场合才选择使用普通话,这些都是完全可能出现的结果。就后者而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语言变化,虽模仿普通话的发音,但普遍存在发音不规范、普通话水平低等语言问题,很多人使用着较浓方言味的普通话进行交流,因此,流动人口的这种语言面貌只能说是“量”上的变化,而绝非语言“质”的变异。
“在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之下,普通话的普及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22]站在推普的角度看,人口流动及社会融入作为一个重要契机,正好可以促成语言面貌由“量”到“质”的根本转化,但由于城市顺应的不足,流动人口在社会排斥之下,虽有语言认同和语言自觉,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语言质量和规范化水平,很显然,这种方言味的普通话与低水平的语言状况,对国家推广普通话以及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是极其不利的。
四、 结 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反映出和社会、城市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透过流动人口的语言演变现象,我们不仅仅感受到的是语言作为工具性的特征,同时也感受到一个城市如何在自身定位和经济发展中的顺应问题。语言与社会具有一种双向的作用。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种种变化首先会反映到语言中来,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化会启示城市的社会化进程。我们倡导社会及城市包容,但我们也倡导城市中的语言包容,社会及城市包容能显示其强劲发展和开放的力度,而语言包容能有助于形成城市的多元文化特色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一个社会、一座城市的开放与接纳,不仅能形成巨大的经济效能,同时也能加速语言的融入。目前,我们的城市社会及个体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做好,对城市而言,至今对流动人口的称谓还贴上歧视性的语言“标签”,如“外来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短期迁移人口”“两栖人口”“自流人口”等等,这些“标签”各自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界定了我国流动人口的基本特质,透过这些“标签”,则映射出社会的不平等,也折射出社会跟进的不足。就流动人口个体而言,语言适应只能反映出自身社会融入的一种心理特征,要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加强并提高自身的行业应用技能,以合拍城市经济发展的脉搏,努力拓展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等,以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已开始大力部署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从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强民生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议题,到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关注民生,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已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让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尽力消除其“流动”特征,已成为大势所趋。目前,全国各省(区)、市相继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全国各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要求推动和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并落实城镇化率规划,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语言适应要求社会顺应,二者和谐发展,方能对城市经济、文化甚至推普等产生积极作用。本文虽以语言视域观察城市社会,但透过流动人口的语言变化,内中牵扯到的相关社会问题是我们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应值得充分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