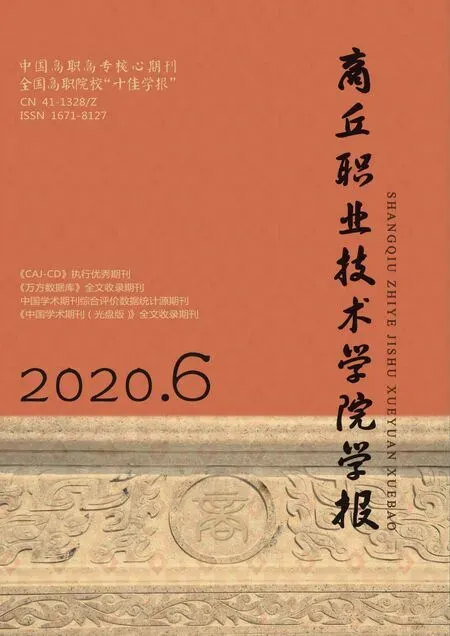冲淡·旷达·飘逸
——苏轼的词风探析
叶 冲
(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 201209)
在我国古代词人中,苏轼无疑是最为优秀的一位,无论是其词作数量,还是对后世的影响,一般词人难出其上。关于苏轼词风,常人多将之归于豪放一派,然而翻检其词,可见婉约词隐约其中,光影斑驳。因此,仅以豪放或婉约来定义苏词,难免有遗珠之憾。进言之,苏词中蕴含着一股冲淡、旷达乃至于飘逸之气。掩卷良久,仍觉清风袭来,暗香盈袖。
冲淡、旷达与飘逸本为三种不同的词风,它们是如何在苏词中得以呈现并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的呢?进言之,这三者又是如何在苏词中获得统一,形成如“水中盐味,色里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1]的妙境呢?更重要的是,苏词这种复杂多变的词风,与前代先贤的遗风流韵、儒释道的文化心理以及词人自身的生命历程存在何种勾连?本文将对此做一分析。
一、苏词冲淡、旷达与飘逸之风概览
“人知东坡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调,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官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2]这是诗人陈延焯对苏词的评价。既传“绝诣”,说明词在东坡的艺术创作中成就之高。
据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现存苏词344首,比北宋任何词人留下的词都要多。这344首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艺术世界。苏轼在这批杰作里,以其鲜明独特的创作风格,抒发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叙写他对朋友、亲人的深切怀念,诉说失意苦闷时的淡泊旷远,描绘千姿百态的美丽河山。其词感情深沉,寓意深刻,妙趣横生。一篇有一篇的情感,一句有一句的韵味。从他的词中,我们感受到了词人波澜壮阔的情感,窥见了词人在追求美的道路上伟岸的身影。
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说:“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3]这代表了一般人对苏词的看法,衍生开去,人们常将柳永作为婉约词的代表,而苏轼则被尊为豪放派的宗师。
艺术风格的呈现是建立在作家整体的艺术作品之上的,它是独特的表现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它体现了一种整体美,单从某一方面来断定作者的艺术风格是不合适的。苏词既有体现阳刚美的豪放词,又不乏阴柔婉美的婉约词,那么,统一这两类词的风格是什么呢?
苏轼词风,豪爽放诞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淡秀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婉转者有之。其词如其文,做到了“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4]。苏轼词风变化多端,似乎难以捉摸,但无论是他的豪放词还是婉约词,我们读时总会感觉一股冲淡、旷达、飘逸之气迎面而来,令人觉得“忧乎遗尘绝迹”“无穷步骤”“语意高妙似吃烟火食人语”“类有神仙出世之姿”“有天仙化人之笔”[5]。
既然冲淡、旷达、飘逸的风格是贯穿苏轼的豪放与婉约词中,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在这两类词中得以具体的表现呢?对此下文将具体展开论述。
二、苏词冲淡、旷达与飘逸之风探微
苏词现存344首。在这些作品中,冲淡无疑是一道主流。
晚唐诗论家司空图在其《诗品》中有云:“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6]30所谓冲淡,就是以平淡处世,须淡到无迹,以静默养生为足,最忌追求之念。把吐纳真气、驾鹤遨游作为人生的最高享受。读苏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这股冲淡之气。
如《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陶渊明虽沉醉于酒和睡中,但他酒醉心明,他的醉与梦不过是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他的“了了”与“醒”则表现为“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尝遍人间辛酸苦辣,方知要保持高洁的品格,躬耕才是唯一的出路。词的下片写雪堂小景:鸣响的暗泉,倾斜的北山,横流的小溪,孤秀的亭丘,一一写出,秀丽异常。而“斜川当日境”一句,则是前5句的总结。正因为雪堂类似斜川,作者才觉得可以在此学习陶潜,喊出了“吾老矣,寄余龄”的心声。该词在艺术风格上显然受了陶公的影响,感情淳朴真挚,意境清秀淡远。
又如《南歌子·带酒冲山雨》上片写梦,睡梦中词人摆脱了世俗的烦恼,变成了“栩然一身轻”的蝴蝶。这里,作者引“庄周梦蝶”的典故,表现其厌倦世俗、寻求超脱的心境。下片写归隐志向,“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两句,再次表明作者坚定的归隐志向,只想“求田问舍”,不想再思进取,哪怕英雄嘲笑也无所顾忌。作者只想避开尘世,过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
再如《浣溪沙·即事》(共五首),从不同的角度描叙“谢雨”途中的所见所闻。景物如池鱼、树鸟、麋鹿、猿猴、麻荷、古柳、莎草、沙路、蒿艾;人物如黄童、白叟、采桑姑、少女、使君、醉叟、络丝娘、牛衣卖瓜者;生活生产场面如聚睢盱、看使君、收麦社、赛神会、煮茧、缫丝、卖瓜、求荣等一幅幅农村风景画,意境冲淡、清新宜人。
此外,还有《蝶恋花·述怀》《行香子·述怀》等。这些词与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类,有一股闲雅清淡之气,接近于静安先生所谓的“无我之境”[7]。生命、万物、宇宙,如何有效地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心境的自适程度。持“留意于物”之态度,那“我”将困于“万物”之中而不得舒张,即“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反过来,若持“寓意于物”之态度,则“我”在“万物”之外而自由舒展,即“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除了冲淡,苏轼词中还有一些展露旷达之风的佳作。所谓“旷达”,即“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樽酒,日往烟梦。花复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6]92。可见,旷达就是人生苦短,忧愁且多,何不以酒为伴,踏歌而行,以平和的境界为足。东坡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属于这类风格。尽管雨打风吹,但词人握“竹杖”、穿“芒鞋”,且吟且啸,徐行归去。这与其在《过大庾岭》一诗中说的“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现了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和随遇而安的坦荡胸怀。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塑造了一位醉而复醒、醒而复醉但心如止水的词人,表达了作者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理想。这两句虽然流露出一种消极弃世的思想,但从词人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这不过是东坡在苦闷现实的折磨中喊出的心声。“报国未尝有门”,这是词人对社会的抗议。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里说:“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驾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起床,作者注)也。”[8]“小舟从此逝”,居然让郡守“惊且惧”,可见苏轼并不消极,而是词人追求自由生活,旷达以明志的表现罢了。此外,如《定风波·重阳》《十拍子·暮秋》等词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词人的旷达之风。
陈华昌以描写的物象及人物的不同在论证苏词旷达风格时说:“这类词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趋向于静态的美,是由人和自然的协调造成的。”[9]诚哉斯言!那“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的词人形象,那“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黄菊篱边无怅望,白云乡里有温柔”的安贫乐道,是一种静态美。旷达词则反之,尽管它与“冲淡”词一样,都表达了词人对摆脱世事功名羁绊的愿景,但其所塑造的不畏世道艰难、不避风雨击打的词人形象,则更鲜明地表达了词人对已选择的人生道路的坚定、执着。借酒浇愁,以酒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种由静趋动的美,是动态的美。
苏词中写得最好的,应该是其飘逸之词。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民,一洗绮罗之泽之态,摆脱绸缪转之变,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10]胡氏认为,苏轼往往运用虚实相间的独特幻觉,通过心境或物境、虚境或实境的杂糅和错层,来展示其人虽在红尘、心却在世外的奇妙感受。
在《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中,词人充分展开其波谲云诡的想象力和妙笔生花的创造力,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天上人间。词人以冷色调作词的底色,无论是“冷浸”“秋碧”,还是“玉宇”“琼楼”,无不给人以身处“清凉国”之感。在蓝色的月光之下,词人翩翩起舞,醉拍狂歌。望今月,想古人,因为“今月曾经照古人”,故而词人高喊“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他盼望与太白先生对谈,因为后者在三百年前同在月下喊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但词人也知道,风露毕竟短,欢情从来薄。于是,在怅惘之际,他再次调动想象力,将自己幻化成世外神仙,以乘风之势行归去之实,用一声横笛作为留在人间的绝响。
在这首词中,我们处处可见李白的身影。李白在上天入地之中暗藏自己对人生的悲观与无力,“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个“独”字显示了李白的寂寞。“月既不能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徒”字表明了无法摆脱的悲凉,“暂”字表达了无可奈何的孤寂。李诗素称“诵仙之诗”,但纵是他如此放荡不羁,却总摆脱不了尘世的烦恼。相反,同样“举杯邀月”的苏词却是那么意兴超然,真难以想象,词人当时正处于遭贬受谪、日益困匮、垦荒辟田、日炙墨面的坎坷境遇中。
清如美玉般的月色,碧波如洗的江面自然令人神往,但限于人力之所不及而无法亲临其境。那么,词人借现实比喻虚幻,制造了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感。
《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的题注写道:“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由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由此观之,词人所见之桥应是一座普通的小桥而已,但是,词人却化实为虚,仿佛小桥就是仙人渡,小河就是银河水,而一轮圆月就是一块美玉,他想醉卧芳草地,又怕碎了这珠圆玉润的月影。最后,他酣睡在绿杨桥之上,直至杜鹃报晓方才醒来。活脱脱一个刘伶醉和酒中仙。是饮酒未醒,还是内心陶醉呢?读至此,真难料到东坡当时是“只影自怜”,“憔悴非人”,“疾病连年,人皆以为已死”。
在《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一词中, 苏轼将飘逸之气发挥到了极致。他想乘风归去,一探天上宫阙之奥秘,但想到高处之寒,又心生退缩之意。天上人间,穿梭忘返,词中所展现的飘逸之风令人叹为观止。对于他的《卜算子》,其好友黄庭坚跋云:“语义高妙,格奇而语隽,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前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是!”
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极为赏识苏轼的飘逸词,他这样评价道:“昔人论词,要如娇女步春。余谓更当有以益之曰,如异军特起,如天际真人。”[11]所谓“娇女步春”意指婉约词,而“异军特起”则是豪放词。在刘氏看来,唯有“异军特起”者方可谓“天际真人”(意指遨游无穷宇宙的仙人,作者注)。由此观之,苏词,尤其是其飘逸词,已接近天际真人的高度,实乃词中之上品。
在344首苏词中,冲淡也好,旷达也罢,抑或是飘逸,无非都是一种“外相”,隐藏其后并贯穿其中的是词人的出世思想。只不过,旷达与冲淡是词人出世思想的动静不同的展露而已,至于飘逸,则是在前二者基础之上的一种飞跃。这三种风格虽各自不同,但他们均统一于苏轼的婉约与豪放词中。
三、苏词冲淡、旷达与飘逸之风成因
苏轼历来被认为是豪放派词人,其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大量的自然界的事物为物象塑造三国名将形象——周瑜,可谓豪放之至。但深究此文,可以发现作者是借周瑜表达一种旷达思想,即人生有限,岁月无情,功名利禄都无意义,只有自然才是永恒的。此外,如他的《水调歌头》也表现了类似的风格。
同样,在苏轼所写的婉约词,即“艳词”中,冲淡、旷达、飘逸之气仍充溢其中,如《贺新郎》《菩萨蛮》等。在这些词里,作者笔下的美人“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拜托绸缪宛转之度”。他们都成了词人高洁冷峻、孤傲自赏的品格的化身。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轼的豪放词或婉约词中,冲淡、旷达、飘逸的风格都始终存在,一以贯之,形成了苏轼特有的词风。
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形成,与他的学识修养、文学渊源和当时的文学氛围、创作时尚不无关系。同时,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阅历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也会有所作用。
对苏轼词风产生影响的原因有如下这些:
首先,陶潜、谢安等魏晋名士的影响。以陶潜、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继承东晋玄言诗任情适意、逍遥自在、快然自足的基本旨趣。同时,与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山水审美观照方式相联系,提出“心不役于外物为乐,适意知足为乐”[12]。苏轼对此极为推崇,在其《题渊明诗二首》《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超然台记》等作品中,我们均可看到苏轼对“适足”的赞美之词。正是这个原因,苏词中的冲淡、旷达、飘逸的风格才得以体现,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苏轼才超然自得地度过了坎坷不平的一生。
其次,佛家禅宗、老庄哲学、儒家学识对其词风的影响。苏轼受佛家、老庄思想的影响颇深,一方面,佛家清静无为、不为而为的主张,看穿忧患、因缘自适的观念,归真返璞、傲视权贵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苏轼的创作。苏轼善于把佛学家这些至理名言结合到自己的实际中,用以处理隐藏、出入、进退之节,因此就有了“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富贵本先定,世人自荣枯”“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等词句的出现。另一方面,老庄否定世俗官场、崇尚安贫乐道的思想在苏词中也有体现。“期于达”是苏轼潜于老庄所祈望的一种思想境界。所谓“达”就是识见通达而不滞阻,心胸豁达且能因缘自适,乃至履危犯难而泰然自若。其词旷达、飘逸之风正缘于此。作为一名文人学士,苏轼受正统儒学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执道而行,积极欲有所为,横逆来时不得不外圆内方一些,以坚持其初衷。这不正是儒家“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的积极入世的态度吗?
最后,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苏轼本是一个率真、爽朗甚至带有一丝童真的人,也是一个文采斐然、才情横溢的天才,还是一个为人正直、品行刚正的忠臣。但是,他却错误地卷入了朝廷的党争之中,以至于一生抱负未展、波折不断。新党对他不信任,旧党又与其政见相左,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请求外放为官,以避开权力的中枢。但又不时因文贾祸,最终到了“无人所居”之地。他试图自我调适:“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文人,他的神经是敏感的,他的感受是强烈的。谣诼不断,风雨交加,他怎能不为所动?所谓“已灰之木”“不系之舟”不过是一种自嘲罢了。可见,阴晴难辨、吉凶莫测的政治氛围是造成苏词冲淡、旷达和飘逸词风的外部原因。
综上所述,冲淡、旷达、飘逸的词风在苏轼词中虽各有侧重,但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它们长存于苏轼闪烁着艺术光辉、永垂文学史册的优秀词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