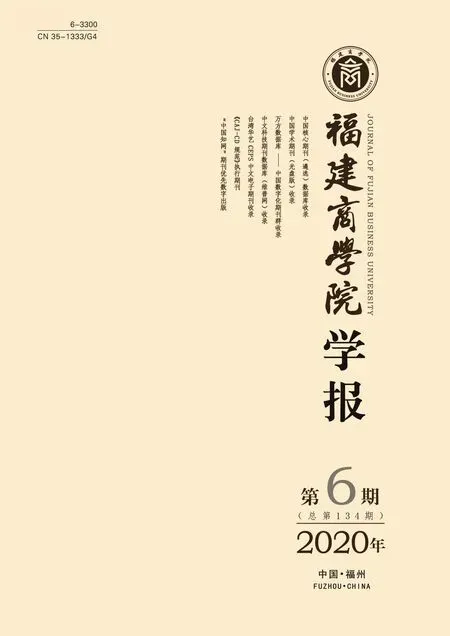语言规划理论视域下清末癸卯学制论析
史玄之
(闽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甲午战争的惨败敲醒了沉睡中的“天朝上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面临亡国的危机。1900年庚子事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财政、教育等方面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史称“清末新政”。新政改革并未解决清朝政治体制的痼疾,从改革成效上看没有实质性的突破,1911年清朝灭亡宣告改革终结。然而十年新政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特别是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而且建立了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加速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癸卯学制是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1903年,清政府命令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以日本近代学制为蓝本,制定全国学堂统一章程。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由于该年为旧历癸卯年,故《奏定学堂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并且推行的系统学制,包括《奏定学务纲要》《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等22个文件,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入学条件、教育年限、师资聘用、教育设施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虽然癸卯学制带有新政时期“急用先学”“照搬日本学制”的弊端,但其仍是中国近代教育普及化、系统化、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之后民国时期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癸卯学制的重要性,不少学者对其产生浓厚的学术兴趣。前人研究主要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癸卯学制的内容、制定过程和对清末社会变革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主题主要有以下四类:(一)癸卯学制与日本近代学制的对比研究[1];(二)癸卯学制对美术、体育等近代学科教育发展的影响[2-3];(三)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与癸卯学制的关系[4];(四)癸卯学制与西学知识普及的关系[5]。这些已有研究对癸卯学制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癸卯学制涉及的语言教育研究有所不足,缺少从语言学的视角对癸卯学制进行剖析。清末语言教育既包含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教育,又包含以本国语和外语为媒介进行的专业学科教育。从语言学视角剖析癸卯学制,对于研究清末新政时期语言与教育改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
本文以社会语言学分支之一的语言规划理论为研究视域,聚焦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近代教育制度——癸卯学制及其补充制度,从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教育规划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政府如何通过语言规划管理人们的语言行为,实现语言规划的目标。
一、语言规划理论阐析
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领域中较新的研究领域,早期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国家后殖民时期的语言问题,后发展为国家管理各领域语言生活的规划。德国语言学家Heinz Kloss[6]将语言规划分为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和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语言地位规划确定一定范围内各种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比如国语的选择,也包括语言功能规划(Language Function Planning),即确定各种语言变体的社会功能;语言本体规划在地位规划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不断规范、完善国语、民族共同语等有社会地位的语言,规划的内容包括文字的创制与改革,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规范等。随着语言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语言教育规划(Language Acquisition Planning)成为语言规划领域的新增部分,主要涉及母语教育、外语教育等问题。在语言规划领域,以色列语言政策研究专家Bernard Spolsky[7]提出的“语言政策三因素”理论模型最为著名。他认为语言政策包括三个要素:(1)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s),即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和目的;(2)语言信念/语言价值观(language ideologies),如语言的纯洁化、统一性等;(3)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即人们采用什么措施调整、影响语言行为。Spolsky 的“语言政策三因素”理论是语言规划三分法的进一步细化,特别是语言价值观,对语言的态度、语言选择与价值取向成为很多学者关心的问题。由于语言规划研究具有历时性、国别性、动态性的特点,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规划呈现各自特征,因此对语言规划的国别研究和历史研究有助于完善、丰富“语言政策三因素”理论体系,在未来建构新的语言政策理论模型。
二、癸卯学制中的语言地位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是一国语言规划的第一步,在语言规划中处于核心地位。清末新政时期,虽然清政府出台的癸卯学制未对汉语和外语的地位和功能做出明确规定,但可从其对各级各类学堂办学宗旨、学科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的要求归纳出清末新政时期具体的语言规划。
癸卯学制规定汉语和以汉语为传播媒介的中学知识(包括经学、伦理修身、中国历史、地理等)为学习之本。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1904年1月13日上奏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到:无论新式学堂性质和层次如何,其教育宗旨均“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8]5125-5126,只有中学底子扎实方可开始西学学习。中国经史学习以汉语学习为载体,《奏定学务纲要》明确阐释汉语对于经学学习的重要性,“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9]493。《奏定学务纲要》中提到的“中国文辞”和“文学”均指汉语文字,只有熟练掌握汉语文字才能读懂四书五经。汉语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癸卯学制对各级学堂汉语学科授课时长的要求上。无论是《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还是《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汉语课程和以汉语为载体的修身和经学课程都排在课程列表的最前列,每周授课时数高于其他课程。汉语学科的名称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的“中国文字科”变为《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的“中国文学科”,再到《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科类大学和宗教学专业设有的“汉学科”和“国文学科”。虽然学科名称一直在改变,但汉语学科的宗旨并没有大的改变,汉语教育的目标在于“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10]。
作为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一项重要语言政策,癸卯学制将汉语视为近代教育的基础,这体现了清末语言规划者“中学为体”的语言价值观。晚清著名教育家张之洞是癸卯学制主要的起草者,他在代表作《劝学篇》中具体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中体”指的是传统儒学知识谱系,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舆等方面的知识,而汉语是传承儒学知识的重要语言工具。在这一语言价值观的影响下,清政府通过癸卯学制管理人们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这体现了汉语在清末新式学堂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外语在清末语言规划中的地位虽不及汉语,但也被赋予了实用的工具性功能。《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11],而且在“各学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刻表”中,中学堂前三学年外语课每星期授课8小时,后两学年每星期授课6小时,授课时长仅次于“读经讲经”课,这充分彰显外语在中学堂课程列表中的重要地位。与《奏定中学堂章程》相似,《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要求外语课程每周授课时数须达到总课时数的一半,目的是为了“备将来进习专门学科之用”[12]。而所谓的“专门学科”是指西学学科,这揭示了掌握外语与学习西学知识之间的关系。癸卯学制对外语地位、功能的规划体现了“西学为用”的语言价值观。“西学”是晚清时期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近代知识,包括政治法律、科学技术等内容,而外语是传播西学的重要载体,也是新式学堂学生学习西学的语言工具。在“中体西用”语言价值观的影响下,癸卯学制对汉语与外语、中学与西学的学习次序做了以下规定:汉语和中学知识是清末蒙学堂、初、高等小学堂的基础,而在学生“固其(中学)根柢”后,从中学堂开始学习外语,进而“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8]5125-5126。
三、癸卯学制中的语言本体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对一国各种语言文字(及其变体)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和功能做出具体规定,可以看做是语言外部的规划,而语言规划理论体系中的另一部分——语言本体规划,则是面向语言内部的规划,即对语言的音系、词汇、文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提炼和升华。
清末新政时期的语言本体规划主要表现在汉语的不断规范、完善和统一上。语言规划者试图通过汉语语言文字内部改革,实现开启民智、国家认同的目的。《奏定学务纲要》特别提到官话统一的重要性,要求“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在师范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9]499。事实上,在《奏定学务纲要》颁布之前,晚清教育家在考察日本近代学制后,多次发文表示“官话统一”对中国发展近代教育的重要性。1902年2月13日,晚清著名教育家吴汝纶在与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函中阐释统一官话的意义,他提议以北京话作为官话的基础,“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外国民团体最要之义”[13]。统一官话不仅有助于解决各地居民因语言参差不通造成的沟通障碍,还是形成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路径。
统一官话的前提是创造一种便于广大人民识记、掌握的语言。晚清文字改革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民间士大夫学者发起并逐渐蔓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场语言文字运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卢戆章、沈学、王炳耀、何凤华、王璞等一批学者受到西方和日本教育的影响,提出切音字改革方案,希望通过给汉字标音来帮助下层人民掌握汉字和官话。从1892年到1911年,清末士大夫学者先后提出28种切音字方案,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14]。切音字运动的目的并非废除汉字,而是通过为汉字注音降低识记汉字的难度,进而在社会大众中普及教育,传播近代知识。1903年,士大夫何凤华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指出切音字运动是从普及大众教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语言文字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国)不患无上等教少数人之教育,所患者无教多数人之教育耳。何谓教少数人之教育?汉文、西文是也。何谓教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15]。
何凤华的观点代表相当一部分清末士大夫学者的观点,语言文字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在汉字之外再造一种文字,而是“欲以切音为学子识字之初桄”,甚至是“沟通西音之捷径”[16]。清末士大夫学者掀起的统一国语运动、切音字运动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对语言文字的改革方案,《奏定学务纲要》中提到“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9]499,拼音文字被视作小学堂汉语教学的一部分。癸卯学制颁布后,清政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创设简易识字学塾,制定提高识字率的具体目标。经过新政时期统一官话的推行,到1910年,在清朝十三行省中已有十省传习官话字母,官话字母已用来编印中小学堂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动植物等课本。一年之后,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统一国语运动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除了统一官话、切音字改革等语言本体规划外,清政府以“存国文”“端士风”为名开展汉语纯净化运动,排除外来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奏定学务纲要》明文规定,各级各类学堂“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除了关于西学知识的专业术语可借用国外名词外,其他“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搀杂”[9]494。汉语纯净化改革的背景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沿海地区青年人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这些崇洋媚外的青年人喜欢借用大量外国名词谚语。在清末语言规划者看来,如果中国语言文字掺杂外国语言的话,长久以来“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进而“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9]494。
切音字改革、统一官话、汉语纯净化改革等发生在语言文字内部的规划,体现了清末语言规划中“中体西用”和“保存国粹”两种语言价值观的交叉与融合。一方面,切音字改革、简化汉字等语言规划出于提高汉语实用性的目的,降低识记汉字的难度,为提高人民识字率进而阅览书籍、开启民智创造有利的语言条件;另一方面,清末汉语本体规划也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外来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侵袭,清末语言规划者试图通过统一官话、汉语纯净化改革逐渐形成“国语”概念,在“语言认同”的基础上促进国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四、癸卯学制中的语言教育规划
在对语言地位和本体进行规划后,语言规划者的下一任务是如何让规划的本国语言和外来语言更好地被人们接受,语言教育规划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语言教育规划涵盖了Spolsky“语言政策三因素”理论的三个重要方面,语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实践,而语言教育规划既能折射出语言规划者对某一言语社区不同语言所持有的态度,也能直接反映语言规划者对不同语言的管理行为。
清末语言教育规划主要在学校教育领域实施,包括对各级各类学堂语言学习起始年龄和教学语言选择的规定。《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第一章“立学总义”中提出“设初等小学堂,令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而第二章“学科程度及编制”中规定“中国文字”科(即汉语)从初等小学堂第一学年开设,总共开设五年,主要教学任务是帮助学生“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17],就此可以推测出七岁是学生汉语学习的起始年龄。关于外语学习,《奏定学务纲要》要求“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9]495,等到学生汉语通顺并考取中学堂以后,才允许兼习洋文。由此可见,在清末语言规划者看来,汉语学习须早于外语学习,这也是“中学为体”语言价值观在语言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奏定学务纲要》对外语学习的起始年龄并非一刀切,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在通商口岸高等小学堂就读的学生以及未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的贫寒子弟,可在课程之外学习外语,外语课程设置可根据“各处地方情形斟酌办理”[9]495。灵活的语言规划一方面体现了清末语言规划者对外语学习规律的认识并不充分,还处在犹豫徘徊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末语言规划“急用先学”的特点。为了在短时间内翻译西书、移植西学,清末语言规划模仿国外语言规划,在规划中“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但由于规划尚处草创之际,并未对中国语言环境进行充分论证,因此有诸多“于中国不相宜者”[8]5125,须根据实际情况对语言规划做出改变。
除了对汉语与外语学习起始年龄的规划外,癸卯学制还规定各学堂西学课程教学语言的选择。根据学生的学习层次和外语水平,癸卯学制对西学课程的教学语言提出不同要求:对于学过外语八年以上的大学堂学生来说,外语是西学课程的教学语言;而对于仕学馆、师范学堂和中学堂的学生而言,由于他们并没有达到一定的外语水平,学校须选择汉语作为西学课程的教学语言[18]。然而,由于考虑不周全,清末语言规划者在制定癸卯学制时并未对军事学堂等专业学堂的教学语言做出明确规定,导致之后出现同一类型学堂教学语言不同的问题。例如,江南陆师学堂和浙江武备学堂都属于军事学堂,然而前者的教学语言是德语,后者的教学语言是日语。如果两校学生今后进入高等军事学堂或者大学堂,之前学习阶段语种不同的问题会造成随后教学实践的混乱[19]。为了解决专业学堂教育实践中的混乱局面,晚清学部在1909年9月14日对专业学堂的外语语种和教学语言做统一规定,“农业应习英文;高等农学科者应习德文;工业应习英文;商业虽未经明定,要以肄习英文为宜……高等实业学堂应用西文直接听讲”[20]。癸卯学制对于专业学堂教学语言规划的不明晰,直接导致了这些学堂语言实践的混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教育规划与语言教育实践的内在联系,也体现了语言教育规划的复杂性、灵活性和动态性。与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相比,语言教育规划的覆盖面更广,它不仅涉及语言教育内容、语言教材选择、语言教育条件等静态规划,还须考虑受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语言教育规划者根据教育环境、教育主体和受教育对象的变化,对教育规划进行动态调整。清末学部针对专业学堂教学语言问题制定的补充政策,实则是语言教育规划动态性的具体表现。由于癸卯学制仅仅实施七年就因清朝覆灭而夭折,因此晚清学部无法从教育实践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进而对语言教育规划进行更多的调整。
五、结语
癸卯学制是清末新政时期最重要的语言教育改革措施。当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之时,语言文字承担着师夷长技、开启民智、国家认同的历史重任。在纷繁复杂、动态多变的社会语言环境下,清政府试图通过对汉语和外语进行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教育规划,达到转移国内矛盾、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清末语言规划中将汉语列为学习之本,并对汉语进行本体规划(包括切音字改革、统一官话和汉语纯洁化等规划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汉语学习的难度,推动汉语在中国广大中下层群众中的传播,在汉语普及的过程中开启民智,形成国家认同。外语在清末语言规划中的地位不及汉语重要,其被赋予了移植西学、富国强兵、对外交流的功能。无论在课程地位、授课时长,还是教学语言的选择上,外语课程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中的地位仅次于汉语和经学课程,成为向中国移植西学的重要媒介。
癸卯学制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而是根据社会语言环境、语言价值观的变化不断进行着变化,清末学部对于癸卯学制的多次修订正是互动循环变化的结果。清末新政仅仅持续了十年就宣告终结,因此无法以更宽广的时间范围验证语言规划的效力。然而,以癸卯学制为代表的清末语言规划对民国时期壬子癸丑学制等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发展的先声,也是中国近代语言教育规划的基石。除了对我国语言规划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外,癸卯学制的颁布也对清末新式学堂教育实践的开展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在语言规划部分,癸卯学制厘清了汉语和外语的地位和功能,将汉语教育与形成国家认同的爱国教育相结合,将外语教育与专业学科教育相结合,这为清末新式学堂制定教育目标、设置专业课程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在癸卯学制的影响下,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新式大学堂及其附属中学堂和小学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科技等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双语人才。在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清末新式学堂的不少毕业生在出国留学后,纷纷选择回国参与国家建设,推动了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国家近代化的进程。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清末及其他历史时期的语言规划进行系统梳理,对百年来中国语言规划展开历时分析和科学总结,这不仅有助于丰富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语言发展作出逻辑预判。
——核心素养与高师院校教学变革(DIA180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