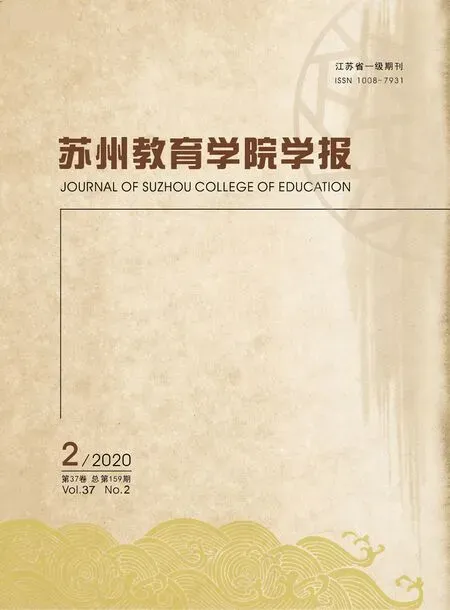《劳燕》:男性叙述下的女性故事
谢金娇
(桂林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劳燕》[1]是张翎的新作,也贯彻了她一直以来对女性成长故事和人性救赎的持续关注。《劳燕》在叙事上尝试创新,将鬼魂对话、书信来往、动物对话、新闻报道等形式杂糅在一起,既有的评论多从叙事创新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本文关注的是男性叙述视角下的女性故事书写。张翎以往的创作常以女性叙述视角讲述女性故事,并将女性的敏锐观察和敏感体验融入作品,塑造了一批坚韧的女性形象。而《劳燕》则把男性作为叙述者,以轮流言说的方式讲述了姚归燕的一生,刻画了历史风云中不断突围和成长的女性以及不断忏悔和寻求救赎的男性。正如有评论家所说:“从《金山》到《睡吧,芙洛,睡吧》,从《阵痛》到《流年物语》,张翎的长篇小说文本,真正可谓一部一个模样。”[2]
一、女作家的女性故事
“纵观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女性创作在这一文学领域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从20世纪60年代台湾旅美文群开始,女性书写更是北美华文小说世界里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3]从第一代移民北美的华文女作家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到第二代移民北美的女作家周励、查建英、严歌苓、张翎、陈谦等,她们在跨文化背景下书写了不同的故事,有去国离乡的故事,有风云变化的家族历史,有辛酸的移民史,也有女性婚恋故事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从女性故事中展现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如荒林所说:“北美华人新移民空间下的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现象,女作家人数不仅众多,而且代际相承,她们不是通过宣言,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文本,相互呼应,书写女性主体成长和超越的故事,共同呈现一种汉语文化生长崛起的独特风景。”[4]跨文化背景使北美华文女作家们对身份认同问题更加关注,而女性的细腻敏感为其书写女性故事带来更深刻的体验。在这些女性故事中,“隐藏于历史尘埃与现实生活之中的女性个体是一个个丰富而立体的生命元素,无论是气质、命运还是文化境遇都各不相同,但她们又以完整而丰满的形象织入北美华人小说的历史肌理,绘制出一幅独具特色的人物图谱”[3]。这些女性故事背景不同,叙事策略不一,塑造出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女性人物形象。
张翎从1990年代初开始创作,纵观她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擅长用女性灵敏的触角触摸女性生存的共同困境。无论是历史书写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张翎都把焦点放在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性生命创伤的书写,来揭示女性乃至人类成长的人生困境。与此同时,张翎也用她特有的温情许诺着人的幸福和人性的救赎。从《余震》的小灯、《向北方》的达娃、《金山》的六指、《睡吧,芙洛,睡吧》的芙洛、《阵痛》中的三代女性上官吟春、孙小桃、宋武生,到《劳燕》中的姚归燕,都显示了张翎对女性故事的偏爱和女性意识的一脉相承。在她笔下,这些女性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都会重新振作,重新认识自我,不断寻找生命的家园。正是对女性独特的个性化书写,使其创作形成了一个丰富的女性形象群——她们或遭遇亲情、爱情的创伤,或经历残忍的历史事件,看到过人性的复杂,却依然把爱化作生命的力量,扛起生命中所有的苦难。张翎把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无畏抗争、坚强勇敢等品质赋予那些为活着而努力的女性,且总能把女性故事延展到个体生命的人性思考中。
《劳燕》是张翎所擅长的女性故事的延续与创新。小说采用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方法,表层是三个男性鬼魂讲述的历史故事,里层是姚归燕的命运故事。张翎的小说常采用时空交错的非线性书写方式,使故事与故事之间具有某种跳跃性和补充性。《劳燕》也不例外,通过性别化叙事揭示出小说的主旨——女性是人类历史记忆和共同疼痛经历中最有韧性的代表,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形成自我意识,姚归燕的创伤记忆是她一生沉甸甸的包袱和无法言说的过往。张翎在创作谈中表示,原本计划第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写关于女兵的故事,在收集资料时一个叫阿红的普通女子给了她灵感,最后成了关于一个普通女性在战争中的位置和生存方式的故事,“其实,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女人走开。灾难不能,病痛不能,战争也不能,因为女人是住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活着,男人还有心,女人是永远无法真正离开的”[5]。正是这种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使她对女性故事情有独钟。
《劳燕》讲述了美国海军援华抗战时期,在温州一个抗战集中训练营里发生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张翎以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来搭建小说的主体框架,历史只是载体,女性的生命轨迹和顽强韧性才是主题。在张翎看来,在女性的故事里,历史只是时隐时现的背景。小说以战争为历史背景,以男女两性情感为线索,通过比利、刘兆虎、伊恩三个男性的回忆来讲述姚归燕的故事。姚归燕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失去父母,失去贞洁,失去青涩的爱情;身体创伤被治愈后,遭到村里人的羞辱、癞痢头的侵害,还有青梅竹马的刘兆虎的嫌弃;到月湖跟随牧师学医,身世却被传开,遭到鼻涕虫的侮辱与挑衅;战争结束后,伊恩离开中国,杳无音信,她一个人带着女儿回到四十一步村;在特殊历史时期,又多次为刘兆虎化解危机。姚归燕这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再一次为张翎对女性故事的偏爱作出注释。“在张翎的小说中,女性被赋予了特别的叙述权力,她们命运各异而又奇妙相连的关系,以及在历史劫毁中更加扑朔迷离的身份游走,恰恰成为连接不同时间、空间和文化的桥梁。”[6]
二、男性叙述下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体自我言说在张翎的女性故事中是主要的叙述方式,但偶尔也有创新和突破。中短篇小说《遭遇撒米娜》《沉茶》,以及长篇小说《劳燕》就与以往的女性主体叙述视角不同,是以男性为叙述视角来书写女性故事。对女性心理的洞若观火和对女性形象的真切塑造,得益于张翎细致入微的观察。《劳燕》中以比利、刘兆虎、伊恩三个男性鬼魂轮番言说的方式进行回忆,似乎是三个男性各自的故事,但其实核心人物还是女性。三个男性鬼魂担任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以自身有限的视角来叙述各自与姚归燕的故事。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是限知视角,或多或少受到时空的限制,不能全盘掌握每个人的心理。因此小说根据每个人出现在姚归燕生命的不同时间段来叙述故事,比利讲述了被日本兵糟蹋后的阿燕,刘兆虎主要讲述了童年时期和生下女儿后的阿燕,伊恩则讲述与阿燕的爱恋,三个男性交互叙述塑造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沉默的存在,她的内心只能通过男性的叙述声音展现。
阿燕的形象——失贞、独立、坚韧。姚归燕在刘兆虎的叙述中,首先是男性视域下的女性,然后才是社会中的人,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伤害。在传统东方文化中,贞洁是一种女性美德,它是女性生存立命于男性话语世界的凭证之一,如果女性失去贞洁,她将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从而生活再无尊严乃至被迫害致死。姚归燕因被日本士兵强奸而失贞后,遭遇了种种侮辱和伤害——刘兆虎的离弃、癞痢头的侵犯、鼻涕虫的羞辱。在刘兆虎的叙述中,姚归燕是值得同情却不能被接受的。失贞遭遇的种种创伤与困境,也使阿燕在不断挣扎中成长、独立,最后还成为了一个救赎者。13岁的阿燕在失去父亲后,自己剪去头发充当男孩,独立担当茶园的业务,还打破女性不能炒青、踩揉的规矩。战争结束后,姚归燕独自生下女儿回到了四十一步村生活,用粗浅的医疗技能为村民治病和接生,通过多种方式庇护刘兆虎。张翎用刘兆虎的独白概括了阿燕与其一生的恩怨和复杂情感:“她为了我能逃壮丁毫不犹豫地在那纸婚约上签上了她的一生;我为了她耽误了去延安的路程,从此生活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我为了她跳下那艘前程未卜的船,而身陷囹圄;她为藏匿我、营救我出狱费尽心机,不惜冒杀头之险;我为她和阿美掏出了我的心肝肺腑,她为我掏出了她的心肝肺腑……我不知道这些情感相加之后的结果是不是爱情,但我知道爱情在它面前黯然失色。”[1]369独白不仅道出了刘兆虎和阿燕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苦难命运以及情感纠葛,同时将阿燕独立、坚韧、善良的品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翎将刘兆虎设计在姚归燕的故事里,不仅是充当见证者,还是参与者,见证了她的创伤,也曾经造成了她的创伤,用刘兆虎艰难的一生,来反观女性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悲剧命运。
斯塔拉的形象——坚强勇敢。在中国传统男权话语中心被压制的女性,却有两个异族他者来拯救——一个是牧师比利,一个是美国大兵伊恩,这两个男性使姚归燕的身心都获得过救赎。牧师比利一出场就讲述他为姚归燕起的名字——斯塔拉(star,意为星星),他希望一直有星星照亮姚归燕未来的路。事实上,比利在见证了斯塔拉的遭遇与成长后,才明白这个女孩也是他的星星,不断照亮他的内心。张翎特意安排的这个男性牧师形象,秉承了她以往的创作风格。通过比利的视角用特写镜头描述了日本士兵强奸斯塔拉后的血腥场面,为斯塔拉后来要面对的种种遭遇埋下伏笔。比利在治疗斯塔拉的过程中看到了她的羞耻和疼痛,以及她被村民歧视、侮辱和欺凌时的孤立无援。比利对这个女子投去了更多的同情和怜悯,也正是他的这份博爱精神最终使斯塔拉打开心结,帮助她破茧成蝶。在协助比利救治伤者和在军营告发鼻涕虫时,斯塔拉才真正勇敢起来,在多次遭受欺凌和侮辱后,斯塔拉明白了要保住性命得靠自己。比利讲述下的斯塔拉是一个经历过身体和心灵创伤后慢慢成长的坚强女孩。张翎通过他者的视角完成了姚归燕成长中的关键转折,塑造了坚强的中国女性形象。
温德的形象——美丽轻柔。刘兆虎眼中的姚归燕不仅勇敢独立还有牺牲精神,是共同面对生活苦难的携手者。在牧师比利眼中,斯塔拉脆弱又勇敢,是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的星星,她懂得选择和拒绝,选择了伊恩的爱情,拒绝了他的含蓄表白。在伊恩眼中,姚归燕是温德,是像风一样的轻柔女子,拥有美好的青春。伊恩的出现是姚归燕故事的插曲,也是最生动的补充,同时完成了姚归燕的血缘传承。某种意义上,伊恩完成了姚归燕从女孩到母亲的转变。
第一人称男性视角叙述是张翎书写女性故事、刻画女性形象的一个策略,它促使被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某种隐秘的情感,即并不认可男性承认的伤害和歉意,同时引导读者重新建构女性的形象。张翎笔下的很多女性都具有“地母”精神,姚归燕就是其一。“阿燕面对苦难面对背叛,最后的还击是‘以德报怨’,以‘爱’的力量让所有的苦难都长出新生的花瓣。这个形象温柔又有力量,宽容又有原则,坚韧却又丰沛,宽恕但不遗忘,独立却又承担。作者也正是借由阿燕这样一个角色,展现了在苦难和命运的蹂躏下,我们民族的女性所展现出来的强韧的生命毅力和令人动容的情感动因。”[7]这也是张翎始终执著的主题,即人性在灾难面前不断裂变,不断完成自我和他者的救赎。
三、女性故事中的男性形象
女性形象是大部分女性作家擅长和喜欢刻画的形象,张翎的创作也是如此。男性一直是张翎觉得较难把握的,正如她说:“我书写女性人物的时候,有着比书写男性人物的天然便捷之处,因为我可以借助自身的生命体验,较为准确地揣测把握她们的内心活动和情感逻辑。而在书写男性人物时,我必须做跨性别的同理心揣测,这就增加了一道屏障。”[8]她在《阵痛》后记中也表示,书写男性缺乏信心,因为“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男人,却发觉男人只有一只手——男人的另外一只手正陷在世界的泥沼中。一只手的力量远远不够,女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经验中体会到了她们靠不上男人,她们只能依靠自己,于是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难时刻的常态”[9]。张翎笔下的男性一般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状态,甚少为主要人物。但《流年物语》《劳燕》却与以往小说有所不同,男性也成了故事的主人公。
刘兆虎——中国抗日士兵形象。张翎在小说中描写了多个抗日士兵,深入到那群被世人遗忘的抗战老兵内心,挖掘他们在历史风云变化中的复杂人性。尽管那些抗日士兵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当国家和战友遇到危险时却选择奋不顾身地相救。刘兆虎正是被贫穷和社会不公逼上革命道路的,他是被烙上时代印记的一代老兵代表,曾是充满激情的抗日青年,立志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但为了帮助阿燕,延迟了启程,终生都没有到达延安。为坚持革命,他曾到异乡宣传抗日;为了能上战场,他参加了月湖美军训练营。家仇国恨锻造了一个热血青年,但是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具有矛盾性。张翎把刘兆虎内心的挣扎和无奈悉数掰开:一方面他是进步的青年,面对国破家亡,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他又是传统守旧的男性,面对失去贞洁的姚归燕,愚昧懦弱,不敢面对和接受。张翎没有把刘兆虎写成一个高大传奇的抗日英雄,而是将其放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塑造成一个普通的青年男性。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刘兆虎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当姚归燕用身体为他换回牛奶的时候,他才明白“人变成动物的途径很多,最便捷的途径是不再知廉耻。我知道最后压垮我的意志的,不是那些掏空了身体的黑虫子,而是廉耻”[1]367。刘兆虎既是一个热血革命青年,又是被历史遗弃的抗战士兵,同时还是生活在女性庇护下的男性,他的形象是多面而立体的。
牧师比利——救赎者形象。张翎的创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牧师或者与牧师相近的人物,如《望月》的李方舟,《交错的彼岸》的安德鲁、陈约翰,《邮购新娘》的约翰、保罗祖孙,《雁过藻溪》的汉斯等。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小说中的宗教情节与人物形象是否有矛盾时,张翎回答:“我的主人公和我一起不断地在飞翔和落地中经历着撕扯和磨难。飞翔的时候思念着欲望丛生的大地,落地的时候又思念着明净高阔的天空。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所以伤痛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质之一。从这个意义来说,宗教里其实蕴藏着人性中最根源化的东西。”[10]《劳燕》中比利既是牧师也是医生,不仅救治人的身体疾病,同时也救赎人的心灵创伤。斯塔拉被拯救的过程,也是比利陷入爱恋的过程。对待爱情他始终小心翼翼,期望与斯塔拉日久生情;他既倾听所有人的秘密,也抱怨他的秘密无人倾听。在比利的形象塑造上,张翎运用人物心理刻画来展示他作为救赎者也是普通人的矛盾性,她将一个肩负所有人的救治与救赎却被众人忽略的形象置于读者面前,亲切而生动。
伊恩——美国大兵形象。军械师伊恩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比利、刘兆虎、幽灵、凯瑟琳·姚和一些家书来进行刻画。在比利眼中,伊恩是一个专业有素的军官,在感情上却是未定型的青年;在刘兆虎眼中,他是一名认真负责甚至有些固执的教官;在伊恩的行军日记里,他既深谙美国军队作战优势,同时也能认识到美军在因地制宜方面缺乏中国智慧;在家书中,他是个慢慢长大的青年,懂得体恤父母,会争取爱情,能支持妹妹;在幽灵眼中,他对爱情不够大胆;在女儿凯瑟琳·姚眼中,他既是曾抛下妻女离开中国的绝情父亲,也是懂得珍惜当下家庭幸福的温情男性。除了众多的侧面间接叙述,伊恩与温德的情感描写直接表现了伊恩的形象。比利、刘兆虎、伊恩对姚归燕的情感是截然不同的,刘兆虎纠结姚归燕的过去,比利操心斯塔拉的将来,伊恩更懂得温德当下的美好。正如伊恩所说:“而只有我,穿越了她的过去,无视了她的未来,直截了当截取了她的当时。我是我们三个人中间唯一一个懂得坐在当下,静静欣赏她正在绽放的青春,不允许过去和将来闯进来破坏那一刻美好的人。”[1]143可见,伊恩是一个懂得抓住当下幸福且具有浪漫气质的男性。
不管是比利、刘兆虎还是伊恩,在讲述各自故事的同时,张翎也让他们解剖自己的内心,自我忏悔,完成自我的救赎。“虽然时代的洪流太过汹涌,任何个人放置在如此波诡云谲的大变化中都难免显得苍白无力,但张翎却通过笔力将这些人物打捞起来,放大,让他们呈现出人性的光辉和力量。”[11]事实上,小说中的三个男性在历史风云和时空交错下,有着共同的创伤记忆。张翎通过男女情感关系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以及男性对女性主人公的深深忏悔来完成人性书写。他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在他们叙述姚归燕一生坎坷命运的同时,也是他们隐秘已久的心灵史的展现。
四、结语
华文作家跨界书写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拓宽了新视角。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是否能够站在不同的侧面去书写关于中国现在、过去乃至未来的故事,或是用独特的视角审视历史,反思过去,这应该是华文文学不懈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作为新移民的北美华文女作家张翎,一直结合着自己的生命体验,从女性的角度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她始终努力寻找着合适的距离,站在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异国时空交错的缝隙中,以女性为主体,通过其生命体验展现中国故事,塑造了一批具有坚韧和博爱精神的女性形象。当然,她不仅注重女性故事的书写、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小说《劳燕》中还刻画了三个不同的男性形象。小说在内容上涉及抗战老兵,是值得深挖的故事;在叙事上多种尝试,有创新。但对于抗战老兵的书写较粗糙急促,还不够深入细致。相对于女性形象,男性形象的刻画并不是张翎所擅长的,《劳燕》中的三个男性形象确实显得单薄,但较以往男性的缺席和半缺席已经有了明显的突破,且还利用男性叙述来展现女性命运,也是以往小说中不曾有的。《劳燕》以男性叙述视角展现了姚归燕和三个男性的情感故事,揭示了人物在面对灾难时人性的裂变和救赎,主题深刻,但是始终没有走出“遭遇灾难—再遇困境——站起来——宽恕救赎”的惯常模式。与以往小说的女性书写一样,遭遇相似,性格相似,差异性不大,很容易陷入人物类型化。此外,虽对时代、民族、社会等外在环境变化导致女性悲怆命运进行了深入描述,但缺少对女性独立个体本能、欲望的书写,这就使得女性形象不够立体和饱满。当然这些问题难以避免,唯有不断尝试才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