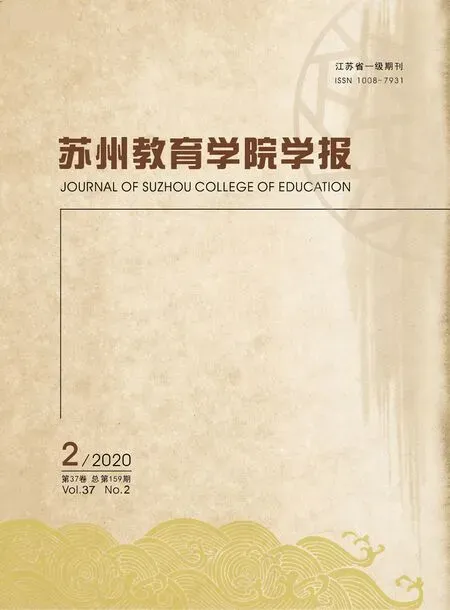严歌苓的“逗留者”创作心理与书写模式
——以小说集《少女小渔》为例
桑思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定居者”身份与“逗留者”心理
“逗留者”(sojourner)一词源自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原指区别于来自欧洲的北美移民(定居者/settler)的早期华裔北美移民:
从能指层面上讲,逗留者只在一个地方劳动、访问,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的短暂停留者,是匆匆过客。而从所指层面上讲,逗留者鲜有既来之则安之的长久打算。对于逗留者而言,客居异乡是人生岁月中的一个过程,一种短暂的生存状态或者生活手段,是实现短期目的的必然,而非最终的目的和目标。[1]
李贵苍从跨学科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华裔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意义,着重强调其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参考价值,并顺着这个视角把研究范围扩大,将在华语社会接受度和流传度更高、更广义范围的留学生文学和移民文学也纳入研究范畴,勾勒和还原出一幅更为细致生动的北美华人生存图景,从而体味和分析独特的异域体验给生存者造成的心理上的异变。创作心理的发展、形成与诸多因素有关,在这里主要归纳为童年环境、成长经历和知识背景,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创作者个体选择出国生活的时间点。基于上述梳理,文章进一步分析北美体验对于作家心灵的冲击和所导向的创作心理的异变。
严歌苓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祖父是留美博士,回国后从事翻译等相关工作,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文工团舞蹈演员。严歌苓切身经历了“文革”“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大事件,在女学生、文艺兵、战地记者等多重身份之间游移转换,父母和自己的第一段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彼此四散天涯,严歌苓曾说:“像别人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2]早期不稳定的经历和动荡的情感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使严歌苓自身带有强烈的漂泊色彩。1989年,赴美留学成为严歌苓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想法起源于两年前受美国新闻总署之邀参加作家访问计划。回国后,严歌苓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专业研究生,其间萌生了赴美留学的念头,于是中断国内学业,同年与已远赴澳洲的丈夫李克威离婚,正式赴美开启全新生活。这一选择为严歌苓带来了不同于早先的生活体验,极大地丰富和刺激了她的认知世界,长期处在不同于以往的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也使她的创作心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小说集《少女小渔》[3]所选篇目来划分,这一时期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自《女房东》(1991)开始,到《魔旦》(1999)收尾,总共历经十年,这也是严歌苓刚刚开始全方位接触北美异域文化的十年。无论现在的严歌苓在面对异域文化的包裹和冲击时显得多么游刃有余,一个长期生活在传统书香门第中,扎根在以军旅、战争、政治等关键词为背景中的中国人,在只身赴美的初期总会经历相似的煎熬与迷茫。
与漂泊经历对应的心理状态是不稳定、变革、冲突和强烈的矛盾感,如果放到个体生存的外在表征层面来看,长期持续的生活的陌生感会对人的心理层面造成极大的压力——在应对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来关照心理状态,与环境条件磨合,维持从内至外的稳定。而从更加私人的层面来讲,严歌苓在与丈夫的长期分居后终以离婚收场,离异独居与繁重的学业压力加重了身在异乡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导致她心理压力的骤然增加。刚到美国的严歌苓,面临语言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要一边兼顾学业一边打工挣钱,在成绩始终达不到理想要求的情况下,严歌苓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一个月内在三所不同的城市间辗转考试。初到美国,严歌苓在与这片新世界以及异域文化彼此磨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痛苦,长期处于迷茫和缺乏归属感的状态中,这种“逗留者”心态与“定居者”的身份显然是充满矛盾的。当这种心态和矛盾反映在文艺作品中,我们便能看到严歌苓本人和这一时期的创作对象——当代北美华人移民——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共鸣,作者的创作心理从多个维度投射在文本创作中。严歌苓在《〈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中描述自己刚出国的情景是“将生命连根拔起”,颇有“寄人篱下”之感,但是她也肯定了这段特殊经历对创作的促进作用:
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于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美国人常说美国是个大融化器(melting pot),它将各色人种、各种文化融为一体。等我被它融化了,或许部分融化了,我的敏感性也许会钝一些。而我多么希望我能永远保持我这新生儿般的敏感。[4]
从创作习惯上来讲,转型为职业作家后需要持续、高效地创作新作品,写作前多需要采风,严歌苓在采访中描述自己在创作《妈阁是座城》前,先找朋友了解赌场故事,后来觉得残酷到难以置信,所以又亲自跑到澳门对赌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采访,自己也亲身参与体验赌博的过程等。出国以后,严歌苓在孤独、矛盾的状态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美华人移民群体,创作了《少女小渔》等相关的短篇小说。一方面,严歌苓身为北美华人移民群体的一员,能准确把握当代移民身上存在的漂泊无定感;另一方面,在故事收集和前期采风的过程中,心理层面的孤独感不自觉地和华人社群一脉相承的思乡、聚集、民族等关键词产生共鸣。从严歌苓的小说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新一代移民居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茫,本身具有浓烈的汉文化意识却不得不面对北美文化居于不可动摇的主流地位的现实。作品中的人物都流露出浓烈的边缘人特质,这也正是由于严歌苓身处异域,浓烈的文化乡愁、早年生活所携带的漂泊感等特征所催生的漂泊无定、短暂逗留的创作心态决定的。
二、“群”与“个”:华人社区族群意识的体现与消解
在异域体验的刺激下,作者一方面反映了北美移民群体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又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潜意识支配深化和强调某种元素,这种作家意识不到的创作特点与创作心理是紧密联系的。而社区族群意识在北美生活状态下得到凸显,由于创作者的逗留心理,他们在异域环境中不自觉地还原了在母国的生存状态。
在《少女小渔》小说集中,严歌苓塑造了多组异国婚姻。如为了换取移民身份与意大利老头结婚的小渔,《红罗裙》中为了儿子前途与周姓老人结合的海云。二者对比下,小渔比海云过得更开心,恰恰是因为小渔即使结了婚仍然没有脱离自己本身的生活“圈子”——与带着她出国的江伟一起生活,而结婚对象意大利老头也有一个自己熟悉的陪伴者,所以这段看似畸形的婚姻实际上为参与者双方都保留了极大的自由空间,由于双方都没有脱离熟悉的社群团体,没有因为文化断绝而造成心灵上的畸变,小渔的故事在结局处反而透露出一丝温情。反观海云,婚后的她进入了一个完全白人化、美国化的社区,一直说英文的混血继子其实会讲中文,只不过丈夫为了营造自己的权威地位而禁止继子在海云面前使用中文,海云感到“讲英文原来只是在这房子里造成一股势力,一股优越的、排外的势力”[3]53。当继子对海云使用中文时,海云领悟到“现在只有他和她俩人,没什么可排外了”[3]53。夫权的压迫和婚姻生活中的冷漠,以及长时间几乎完全与过去的文化环境、社区族群的割裂造成了海云异国婚姻中的不幸,她开始变得病态而神经质。小说后半段,海云发现这位混血儿继子身上竟然也有着同样的孤独——父亲在生活上的缺失使中国文化因素在继子的生命中仅仅停留在基因阶段,母亲的过早离世使西方文化因素在继子的骨子中也没有刻上深刻的印记,于是海云和继子的不伦结合更像是两个被社区族群文化所抛弃的流浪儿,在异域文化避无可避的冲击下,依偎着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小渔虽多次遭受身体上的摧残,但纯洁高尚的心灵以及与母国文化紧密的联系使她在美国乐观地生活着。海云虽还处在春华犹在的年纪,但心灵却早已让两次畸形的婚姻折磨成一潭死水,异域环境下文化冲突带来的高压无法通过社区和族群纽带进行排解,最终导致她一步步走向畸变。严歌苓通过对两个移民女性形象的对比性塑造,展现了族群文化在北美华人移民身上打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这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扶桑》中也有所体现。扶桑虽深爱美国少年,但最终没有接受他“救赎式”的爱,而是选择了并不相爱的大勇:一方面这和对异域文化居高临下的拯救进行解构和反抗有关,另一方面,严歌苓是这样解释的:“她并不爱大勇,但是大勇对她来说是家乡、祖国所有东西的象征,她在大勇身边有很多的归属感,有依靠的感觉。”[5]可见受“逗留者”创作心态影响,在严歌苓笔下,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异域拼搏与奋斗,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移民者内心深处“非定居”的生存状态,社区族群与文化源头仍然是移民群体对于母体文化的想象和寄托,也是其生存下去的精神源头。
此外,严歌苓对于新一代移民,特别是女性移民的最终目的进行了明晰的揭示,在《红罗裙》《约会》《冤家》中,严歌苓塑造了抛弃亲人朋友、和过去的身份环境完全隔离、只身来到美国结婚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红罗裙》中的海云、《约会》中的五娟,还是《冤家》中的南丝,都亲口承认移民就是“为了孩子”,就算牺牲掉以爱情和相互扶持为基础的正常婚姻关系,在出国等于为孩子争取到光明的前途这种考虑面前也完全算不了什么。母性成了支撑这些女性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唯一支柱,因此她们或多或少都显得有些病态,对孩子的控制欲也极强,作者甚至这样描述南丝和自己女儿见面时的场景:
细长的摩尔烟卷架在她向后弯翘的两根手指之间,精心育植的两支尖细指甲与香烟取成一个准星,使女儿和她心目中十四年来的一个瞄准无误地重叠。璐被她严格地栽培修剪得这样姣好……如她所期的重版了她的青春。南丝在烟卷冒出的最原汁原味的第一线烟中,看着女儿从校门走出来。连走路的姿态也是南丝自己的。[3]109
这样的文字多少能让读者体会到母女之间不同寻常的冷酷,仿佛南丝不是在培养女儿,而是为了报复孩子的父亲,将他所给予的因素全都抹杀掉。在《约会》和《红罗裙》中,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则呈现出另一种畸形,血缘关系中混杂进了偏执的爱欲和占有欲,甚至导致其继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嫉妒和反感。在这些畸形的母子关系中,严歌苓想要展示新移民一代的部分人为了孩子的前途而义无反顾地和自己的地缘、文化血脉割裂,最终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扭曲。造成这些女性不幸生活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远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自身目的,“为了孩子”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远离故土的行程终将是一段没有归期的旅程,缺乏以工作为纽带而得到承认的社会身份,她们与异域社会文化的彼此认同感都处在极低的状态,是更加纯粹意义上的“逗留者”和“漂泊者”,虽然当前国际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美社会对移民与身份转换也显得更加宽容,但在严歌苓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悲观者的心态,更多的应该是对自身价值的错误认知和愿景与现实的错位所致。
三、“个”与“群”:异域环境中个体的彷徨与选择
对严歌苓来说,身份与心灵是长时间错位的——虽身在美国,文化背景却是中国式的;虽认同中国文化背景但饱受困扰,如在国内时遭受了“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出国后试图融入美国环境的过程中又饱受母语造成的隔阂的困扰,种种矛盾注定了严歌苓长时间处于中间层与夹缝状态,漂泊多地也始终难以找到内心真正认同的精神家园。严歌苓在采访中表示:“我觉得我永远是个边缘化的人,不仅在美国是边缘化的,在中国也是边缘化的。”[5]因此,与“留学生文学”关注的痛苦焦灼中的异域生活不同,当漂泊与逗留已经不是短暂的状态时,在严歌苓的创作中能明显感觉到“逗留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一种生存状态,她试图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探讨更深层次的人性问题,通过创作心理的支配,切实影响到作家创作中的选材、关注点和故事走向,并通过多种要素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
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严歌苓在描写文化冲突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对移民造成的痛苦和迷惘,而是试图挖掘在北美文化占优并具有强烈压迫性的表象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中国移民潜在的反击,这一点在分析扶桑的性格问题时严歌苓曾经谈到:“那个年代,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境遇非常悲惨,一个白人救了她,以非常高的姿态像救牺牲品似的……救她的人有一种君临的态度,像基督的态度,我比你高一等,我赏给你自由,这是扶桑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扶桑特别能代表中国很广大的草根女人,她随遇而安,在自己没有办法来反抗的情况下,她内心的自由使她非常强大。”[5]以爱情描写为例,严歌苓在移民题材小说中时常讨论在西方的背景下,白人对东方不自觉的鄙夷和宗教习惯式的拯救心态。其笔下经常出现这样的经典场景——当跨种族恋爱中出现包含政治、种族、宗教、文化相关的拯救意识,或当白人一方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优越感时,即使是善意的,东方女性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掉头离开。在《栗色头发》中,“栗色头发”被“我”的东方古典气质深深吸引,但在“我”面前傲慢地学中国人吐痰,在谈及中国人时使用轻蔑的口吻,最后我放弃了与“栗色头发”的相恋。
而在《少女小渔》小说集中,严歌苓也将视线集中在裹挟于北美主流文化大潮中的边缘人物,并着力展现这些人物身上神秘顽强的东方色彩。不同的是,严歌苓在这里有意选择了多个男性角色,展现受到文化压迫冲击的并不仅仅只有女性,这是整个移民群体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和考验。相较于温婉、内敛的女性角色,面对多重文化带来的冲击,男性角色们或出于本心,或由于与母国文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激发,选择了更为直接和积极的反抗方式,《魔旦》的主角阿玫和前辈阿三,以及《橙血》中的阿贤便是这样的人物。
阿玫、阿三和阿贤的共同特征是带有典型东方色彩的阴柔美:苍白的皮肤、纤细的手指,都在戏曲行业中从事扮演女性的工作,阿贤甚至保留着那根从清末留下来的辫子。从外貌上来看,三人都是西方人印象里典型的带有东方特色的男性,无骨般的柔美、性别的模糊使他们又多了一丝顺从的特征。但塑造这样脸谱化的东方形象显然不是严歌苓的最终目的,小说中的许多细节能使我们感受到三者与表面上的柔弱截然相反。阿三在美国同性恋流氓们逼迫他脱下裤子以证实性别的时候,选择了一种非常戏剧化的野孩子的方式——站在树上朝他们撒了泡尿来证明自己的性别;阿玫的性格更加柔软,更加精巧细致,他的心更像女孩子一些,所以如果和阿三遭遇相同的状况,阿玫可能选择直接被烧死而不会脱下裤子以维护尊严,但正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温吞的少年,在被误认为女扮男装从而被要求脱衣检查时,却始终没有让三个高头大个的洋夫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这是严歌苓在他性格中埋下的一处伏笔。
关于阿玫的阴柔气质,严歌苓甚至在性取向上也赋予了他可以供人揉捏把玩的错觉,在故事中阿玫有两条感情线分支,和奥古斯特的纠缠带有更多西方对东方的原始意味的侵略、占有和赏玩,和芬芳的交往看起来则有更多注定的意味——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身处异域文化的两人拥有对彼此致命的吸引力。三人同时出现时,阿玫和芬芳用中国话交谈,使奥古斯特感到不适,两人分别为戏子和情妇的身份,也使得他们基于共同的无尊严经历而更多相互理解。严歌苓并没有直接描写芬芳和阿玫的心理活动,因为她试图带给读者的切入视角是由西向东的,西方背景下对东方元素的关注不需要看透和理解,它们需要的只是隔着一层纱般赏玩的神秘感,由于阿玫和芬芳的感情是一种只有相同文化背景、相同思维体系的人才能理解的惺惺相惜,所以作者也故意采用这种朦胧晦涩的写作手法,试图给读者创造相似的阅读体验。
阿玫利用奥古斯特成功洗清了自己身上的嫌疑,同时也摆脱了他的纠缠和控制,自己“从会计学校毕业,真的就混入了穿西服打领带的金融区人群”[3]84,他带着芬芳在高档社区租了房子并且生儿育女,到小说的最后,读者终于知道前文博物馆里一直引导读者的温姓老爷爷极有可能是阿玫本人。通过为故事发展设置一个合理的引导人,提升故事的代入感,同时悬念的设置可以更加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最重要的是,采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可以将爷爷和阿玫的形象截然分开,两种截然反差的人生组成了两段看似互不相干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在创作上对西方视角下东方固有形象的一种反思,阿玫带有复仇意义的故事和前后段人生的割裂性,实际上是东方文化对一直处于被冲击和压迫的劣势地位的有力回击。
相类似的角色还出现在《橙血》中。玛丽是一个守着自己水果园的古怪女人,阿贤是她“圈养”起来的中国少年,对于老态龙钟、性格孤僻古怪的玛丽来说,美丽病弱的东方少年阿贤更像是一块收藏的古董——古老温和而谦逊,玛丽对他的欣赏和《魔旦》中奥古斯特对阿玫的欣赏很相似,都是模糊了带有东方柔韧美的少年的性别后对其进行把玩和鉴赏。玛丽拒绝卖树种给中国女人,原因是“不卖给中国人树胚,是因为任何东西在中国人那里都会得到淹没般的繁衍”[3]183。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视角,充满对中国传说的恐惧,但事实上也体现了生活在异域的移民群体在早期确实曾以这样的方式对抗扑面而来的社会、文化上的冲击和压力。建立族群和社区,重构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恢复自身血脉中留存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行为在西方视角中被夸大扭曲,成为恐惧的来源。阿贤在遇见中国女人后开始反抗和叛逃,最后剪去具有象征意义的辫子,在沟通无果后执意逃离果园并最终死在枪下,他用自己的死亡诠释了东方民族隐藏在温柔性格里的倔强。
严歌苓在小说中用强烈的东西方对比,体现了她所观察到的西方对东方的病态理解,小说中人物皆因为遇到同根同源的另一位中国角色,而被激发起潜藏在骨子中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对回归中华族群的向往,由此发起了对命运的反抗,这也可以理解为异域背景下东方文化对一直以来受到的冲击与压迫的反抗与叛逃。小说主人公的命运由遭遇到启发其文化认同感的人物伊始,前后形成鲜明对比,其结局虽然有幸与不幸,但从人物精神面貌上来讲,主人公在经历过对异域文化冲击和压迫的反抗,追求过与母体文化的紧密联系后,无一不显得更加鲜明可爱,而不仅仅只是小说开头塑造的一个模糊且面具化的空洞形象。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移民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无处躲藏,严歌苓或选择如《扶桑》中的东方妓女和《少女小渔》中小渔的包容、弱者的姿态,或选择《魔旦》和《橙血》中的中国少年,由善良、逆来顺受的弱者形象逐步向更为激进的方向转变,反抗西方文化全方位的碾压与侵略,这个现象背后是严歌苓在体验异域、转变生活环境时所产生的“逗留者”心态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这与《少女小渔》中描写的当代移民的心态遥相呼应,成为“非定居”意识和“逗留者”创作心态贯穿整本小说集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