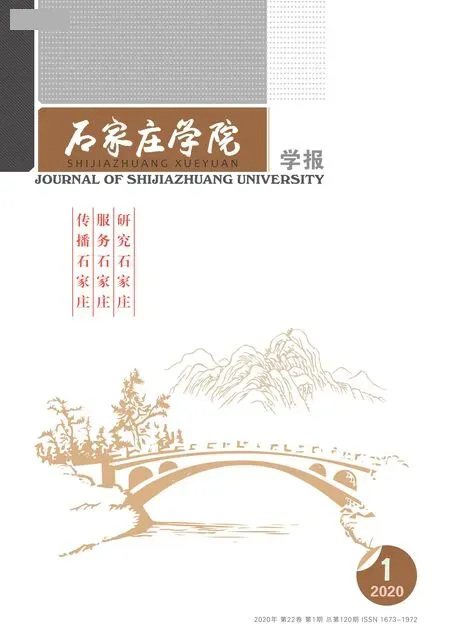雅化还是俗化:语言规范过程中的矛盾与平衡
纪凌云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上学时大家都做过查找并修改句子语病的练习。《咬文嚼字》杂志从2006年便开始搜集并发布年度“十大语文差错”,旨在提示人们日常语言使用中存在的一些习焉不察的错误,以期对语言的规范使用起到一定的助力。其中,2017年“十大语文差错”中的第8条为“敬请期待”,具体分析如下:
社会礼貌用语中,“敬请期待”呈流行趋势。商店即将开张,商家总会挂出横幅:“开业在即,敬请期待。”
电视剧即将播出,电视台也会推出预告:“开播在即,敬请期待。”
谦恭的“敬请”和自负的“期待”,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组合。
所谓“期待”,是充满期望的等待,这是一种主观感情的显示;强行要别人“期待”,至少是有悖于传统礼仪的。正确的用法是“敬请赐候”。
今年年初,一篇题为《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其实是2016年完成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中对部分字词读音所作的修改。该审音表由教育部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参与研究制定,具有语音规范性质。不过新版的审音表尚处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并未最终颁布。其中提到的一些字词读音的改变引发了公众热议,比如:
“一骑红尘妃子笑”中“骑”的读音从jì改成qí
“乡音无改鬓毛衰”中“衰”的读音从cuī改成shuāi
“呆板”的“呆”从ái改成dāi
“粳米”的“粳”从jīng改成gěng
以上两个案例都与语言规范紧密相关。
一、语言规范
作为兼类词的“规范”,有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三种词性。与此相对应,“语言规范”也有三种含义:“规范”为名词,“语言规范”指语言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标准和典范[1];“规范”为形容词,“语言规范”指语言合乎规范;“规范”为动词,指使语言合乎规范。这便决定了“语言规范”同时隶属学术与实践两个领域。[2]它通过制定和颁布具有规范性的语言文字标准,使得语言使用合乎规范。语言规范可以视为语言规划的下位概念,基本上属于语言本体规划的范畴。[3]
语言规范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概念,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语言规范工作开展得最早的国家之一。《礼记·祭法》记载:“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这种对名实关系的辨证实际上便是一种语言规范行为。事实上,历朝历代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体现其统治力和实现长治久安,都会制定语言规范政策,加强语言规范工作。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的语言规范工作更多地集中在文字和语音两个方面。
据记载,黄帝派了史官仓颉“作书”。虽然仓颉不见得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创造文字,但这种提法至少体现出原始先民对于文字所作的整理和规范工作。这可以看作是我国语言规范的滥觞。《周礼·春官·外史》有:“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根据郑玄的理解,“正名”即“正字”。孙诒让疏曰:“谓以书名之形声,达之四方,使通其音义,即后世字书之权舆也”。这反映出当时对文字进行统一规划的现实。周宣王时,太史籀编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实际上也是对汉字的整理和规范。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的“书同文”政策,是中国正史记载的最早的、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语言地位规划和文字规范活动。之后,历代的字书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具有文字规范的作用。秦代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汉代有史游的《急就篇》,而许慎的《说文解字》正是为匡正当时的经学家谬解篆字的情况而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打破了秦以来文字一统的局面,篆体谬误,隶体失真,异体字繁多,因此六朝时编写了大量字书,对当时的汉字字形进行规范,如魏初张揖的《古今字诂》、晋代吕忱的《字林》、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北魏阳承庆的《字统》、南朝梁阮孝绪的《文字集略》、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等。隋唐以后,各朝政府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都很重视。唐初出现了大量整理异体、辨别俗讹、订正经典的字书,如颜师古的《匡谬正俗》《颜氏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等;宋代的字书有张有的《复古篇》、旧题司马光撰的《类篇》、李从周的《字通》、僧人行均的《龙龛手鉴》、娄机的《班马字类》;元代有李文仲的《字鉴》;明代有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有《康熙字典》等。
除了汉字以外,语音也是历代政府对语言进行规范的重要方面。这种规范主要体现在对雅言和普通话的倡导和推行上。雅言的形成体现了早期对于标准语语音的规范。“雅”就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确规范的语言。清代的刘台拱在《论语骈枝》中提出,“‘雅’‘夏’古字通”,“雅,之为言夏也”,西周王都一带为夏地,“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据此可知,雅言指的是西周王畿一带具有较高威望的方言。讲雅言的人,除了周王室的贵族外,还有各路诸侯、卿大夫以及士大夫文人。通过相关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到,周王朝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对雅言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广。《周礼·秋官·大行人》中有:“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①属:聚集。象胥:进行翻译工作的官员。史:指掌管文字、文献资料和记言、记行的官员。孙诒让正义:“此谓行人召侯国之象胥、瞽史来至王国,则于王宫内为次舍,聚而教习言语、辞命、书名、声音之等也。”文人们是自觉地遵守通语的语音规范。《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读书执礼的时候都使用雅言。这段话也反映出早在孔子的时代便存在“文白异读”的情况。王力先生曾对《楚辞》的音韵系统进行过研究,他在《楚辞韵读》中将《楚辞》中的韵部分为三十部,只比《诗经》韵部多了一个东部。这有力地证明了尽管当时实际口语中存在着南音与北音的差异,但文人们在写作时都自觉地使用雅言。六朝开始,历代的韵书和许多字书都具有语音规范的功能,如:隋唐的《切韵》,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集韵》,金人王文郁的《平水新刊韵略》、张天锡的《草书韵会》,宋末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吕坤的《交泰韵》等,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张玉书等奉敕编撰的《佩文韵府》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院”②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八年内在福建、广东推行官话,八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来推行官话,此项正音举措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近现代和当代的语言规范工作学者们对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多有论述,相关介绍可以参看吕冀平主编的《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一书,这里不再赘述。这一时期的语言规范工作更加全面、系统,除了文字和语音外,又增加了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内容。
二、语言规范过程中的雅化与俗化
“语言不是静止的,语言在运用中不断产生变化。”[4]44语言规范实际上体现了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语言规范的制定既要符合语言常识,也要考虑社会惯例,由此形成了语言规范过程中的雅化和俗化两种力量。
(一)雅化
语言规范的雅化是指语言规范过程中使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标准合乎学术化的规范,即传统语言规范观念中所说的“匡谬正俗”。吕冀平将其称为“理性原则”。语言规范的雅化主要是使语言的各个方面合乎语言结构系统的发展规律。语言教科书中的发音矫正、词语辨析和病句修改,报纸、杂志上的咬文嚼字以及关于“语言美”、语言文明的提倡,都是依照语言规范进行的语言雅化工作。
(二)俗化
语言规范的俗化是指在语言规范过程中选择民众普遍使用的与雅化标准不相一致的用法,即通常我们所说的“约定俗成”。这种用法根据雅化的标准来看,一般都是不规范的,甚至是错误的。吕冀平将其称为“习性原则”,如:《汉书》中的“谈/何容/易”,如今变成了“谈何/容易”;先秦时的“每下愈况”,最迟到南宋时已变为“每况愈下”。这样的例子生活中随处可见。如“纪”在姓氏用法时,词典中标注的读音为“jǐ”,但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读去声“jì”。再比如成语“万人空巷”的意思是人们都跑到大街上,家家户户空无一人,其中“巷”泛指住处,后来随着“巷”字街巷意义的普遍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将“万人空巷”理解为人们都待在家里,街上空无一人,与其本来的意义刚好相反。再比如“无时无刻”一词,由并列结构“无……无……”构成,“时”“刻”为近义词,该词与否定词“不”一起使用构成“无时无刻不……”结构,表示“时时刻刻都……”的意思,然而在生活中甚至主流媒体中却经常能见到或听到这样的句子:
聪明人一般都比较懒,因为他们无时无刻在思考怎么偷懒。
朋友无时无刻都在对你传递负能量,怎么办?
无时无刻都有饥饿感。
(三)雅化和俗化的相对性
雅化和俗化是相对的,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种俗化的语言现象一旦被官方承认并给予规范的地位,它便转化为雅化的标准,成为衡量语言使用是否符合规范的尺度,与之不符却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则成为俗化现象。如隶书在取代小篆成为官方正体之前,相对于正体的小篆便是文字的俗体。但是因为隶书便于书写,满足了人们追求书写速度的需求,因此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到了汉代,隶书被确认为官方字体以后,便华丽转身,成为衡量汉字使用是否符合规范的雅化标准。
雅化和俗化之间的变化体现的是语言的发展演变。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篇引起公众热议的帖子,人们争议的最大焦点在于对一些古诗词读音的调整,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斜”,不再读xiá,而改读xié;“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野”,不再读yǎ,而改读yě。大家觉得这些字的读音一旦改了,古诗词就不押韵了,诗歌的韵味就被破坏了,实际上它们本就不该有这样的读音。我们知道,语言是发展演变的。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先秦的《诗经》到了宋代,很多地方用当时的语音读已经不押韵了,朱熹不理解语音的变化,便以“叶音”来改读《诗经》,这种做法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斜”读xiá、“野”读yǎ便属于“叶音”的做法。唐宋的诗词到了现代,很多也已经不押韵了,尤其是北方方言,声韵和音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导致许多古诗词用普通话读起来都不押韵。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迁就个别诗词的押韵而给现代汉语的某些字词加上特殊的读音,这样反而会造成混乱,同时也会掩盖语音演变的事实。
三、语言规范标准的雅俗之争
语言始终处在发展中,语言生活也时刻在发生着变化,因此语言规范要根据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生活的变化不时进行调整。语言规范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规范和不规范、雅化和俗化的矛盾与平衡过程。汉字的正体与俗体之争、语音的文读与俗读之辩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一)汉字规范的雅俗之争
汉字的正体和俗体之争历代都有。通常是官方规定正体,民间却使用俗体。曾经作为俗体存在的隶书取代小篆、楷书取代隶书,都是俗体对正体的胜利。上述这两种字体更替是作为字体演变的大趋势发生的,在这种大趋势之外,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有俗体字形被吸收到正体当中的情况。人们出于追求书写的速度或其他原因,同一个汉字可能会有一个或多个不同的俗体书写形式。这些俗体书写形式,在文字规范过程中,有的被正体规范掉了,有的则被吸收到规范字体中取代了原有的正体字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便是一次传统正体文字与俗体文字的大交锋。195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1 055个异体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 236个简化字,简化了264个繁体字。这些规范后的异体字和简化字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前代已有的俗字。
《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中严肃地指出,词汇、结构等方面存在的“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199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提出,“提倡在手写招牌和题词中使用简化字”。“提倡”一词表明,对于规范简化字在招牌和题词中的使用已经不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政府相关部门第一次在重要文件中修改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以来的提法。这一改变,可以说是民间习惯对官方规定的一次胜利。
(二)语音规范的雅俗之争
语音的雅和俗,一方面体现为通语或普通话语音的统一化和方言语音的多样化,一方面体现为通语中同一个字的文读音和俗读音。历朝历代对通语或普通话的推广都可以视作是雅化对俗化的胜利。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历次新语音规范的制定中,总是有俗读音取代原有的文读音成为新的语音规范。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古音的实际面貌如何,但是通过一些典籍的相关记载,仍然可以窥见语音规范制定中雅俗之争的概貌。建国后发生了多次字词的文读音和俗读音之争,《现代汉语词典》历次修订过程中对个别字词读音的调整正是其体现。
《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其编写宗旨是推广普通话和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至今已发行到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一般依照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审定。从第三版开始,参照国家语委、国家教委(今国家教育部)和广电部1985年2月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进行了注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审音表》审定的某些读音与实际应用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于是在对《现代汉语词典》进行修订时,一些口语音成为正读。如第六版中对一些姓氏用字的注音处理,常标注为“近年也有读X/今多读X”,像前文提到的“纪”,相同情况的还有“华”。它们的常见读音为“jì”和“huá”,姓氏里则读为“Jǐ”和“Huà”。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们在作姓氏时有特殊的读音,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们读为“Jì”和“Huá”。久而久之,这种错误的读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终使得正确的读音“从俗”而让位给错误读音。
事实上,对于语音进行调整很多时候并不是简单地从雅或是从俗就可以,常常需要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ABB式形容词的注音为例,《现代汉语词典》一到四版中均按实际读音标调,如“沉甸甸”注为“chéndiāndiān”。而从第五版开始,则按ABB式的口语和书面语性质,分情况作了三种处理:一是对只出现在口语中的,BB就注作一声,如“绿油油”注作“lǜyōuyōu”;二是对只出现在书面语中的,BB注为本调,如“金灿灿”注作“jīncàncàn”;三是对既可以用在口语中也可以用在书面语中的,则在注本调之后,加括号注明“口语也读X”,如“【沉甸甸】chéndiàndiàn(口语中也读chéndiāndiān)”。[5]据李丽云统计,第六版中标注“口语中也读X/口语中多读X/口语中(常)说X/X的口语音”的情况共有71个。[6]如:
指甲zhǐ·jia(口语中多读zhī·jia)
作料zuò·liao(口语中多读zuó·liao)
绿油油lǜyóuyóu(口语中也读lǜyōuyōu)
这zhè(口语中也读zhèi)
早早zǎozǎo(口语中多儿化,读zǎozāor)
李宇明曾提出:“语言在不同人、不同地区的使用中,在不同媒介物的负载、传递中,会产生各种变异,会出现各种分歧。”[3]他将这些变异、分歧统称为“语言变项”。语言变项实际上体现的是语言使用中的俗化倾向。语言规范行为,本质上正是对各种语言变项的选择与规范。这种选择与规范的过程正是雅化和俗化两种力量的角逐与平衡过程。
四、结语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当代的许多语言规范实际上都是通过对语言本体的规划来指导人们的语言使用。当然语言规范并不限于此,它还包括其他方面,但这些对语言本体的规范是与每个语言使用者最息息相关的。正如李宇明所说:“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3]因此,当政府在学术团体和学者的参与下制定语言规范,使得语言雅化的同时,决不能忽视语言使用者的感受和影响,即语言使用中的俗化倾向。基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咬文嚼字》对于“敬请期待”的匡谬,虽然符合语言雅化的规范,但绝不会成为日后的语言标准,因为它有悖于语言俗化的倾向。而对于语音的规划,我们在从俗的同时,也不能不顾语音的系统性和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由此可见,在制定语言规范时是从雅还是从俗绝不是一刀切,也决不能一刀切,必须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正是语言规范工作复杂性的体现。
在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语言规范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操各种语言和各地方言的人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不同语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各地方言之间的影响和交融在加剧。自媒体的兴起使得每个人都成为风格的创造者,不合规范的语言现象在网络上大量出现。它们被视为风格和个性的表现,受到网友的追捧并迅速传播。可以说,网络时代语言变异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快。在这样的形势下,语言俗化的力量势必会在语言规范中得到加强。面对新形势,语言规划如何把握好语言雅化的大方向,确保语言有序、健康地发展,是每个语言工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