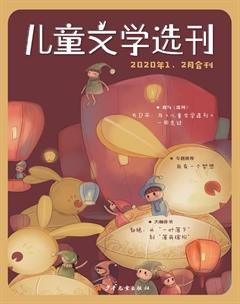银项圈

女孩佩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上。平常,她一定是连蹦带跳的,这一次,她的步子分外稳妥,甚至有点儿谨慎,因为她的手里提着一个长柄的食盒。
走着走着,佩双觉得身后有咻咻的鼻息声。一回头,哎呀,跟着的是一条大狗呢。那大狗一身黑,在阳光下黑得发亮,像一匹流光闪烁的黑缎。它紧紧地嗅着食盒,还时不时地撩过红色的舌头。看呀,它的口水也滴滴答答地掉下来了。那样子使得大狗看上去像极了一匹凶恶的狼。佩双心里陡然一凛,忙把提盒换到另一只手,口里叫着:“去去去!”那狗自然舍不得轻易离开,反而灵活地挪腾到另一边了。佩双没办法,把食盒举起,护在胸前,加紧了步伐。可是那狗左蹦右跳的,似乎想跃起身来够那食盒呢。终于,佩双吓得闭上眼睛,哇一声哭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佩双听到一声“嗬去”,睁开眼一看,前面站着一个男孩子,看样子比她大不了几岁。那男孩的手里牢牢抓着一把芦花帚。佩双环顾一下,发觉那狗远远地去了。佩双心内还有些惊魂未定,一时也就忘了跟那个男孩道谢。
倒是男孩先说话了:“你没事吧?”佩双摇摇头。男孩又说:“以后遇到狗了不要害怕,你慢慢蹲下来,假装捡石头,狗就会吓跑的。”佩双这才想起来什么,说了一句:“谢谢你。”男孩挠着脑袋笑了:“这没什么。”又好奇地问,“对了,你拎的是什么,怎么那狗老跟着你?”
“是一碗肉末蒸蛋。”佩双答他。男孩笑道:“难怪!”末了又关切地问一句,“你去哪里?”佩双告诉他:“我去柳枝巷外婆家。”男孩说:“柳枝巷还有点儿远的,你路上小心,小心再遇着狗。”佩双慧黠地笑:“没关系,再遇见狗,我就照你说的,假装捡石头。”
佩双与男孩道了别,却没有马上抬脚离开,而是目送男孩走远了。那男孩进了一家银匠店。佩双想起男孩刚才拿着的芦花帚,猜测着他应该是这个店里的人。这么一想,佩双忽然对银匠店多了几分亲切。
隔了几天,佩双又去看外婆,不提防下起了雨。春天的雨下得不算大,可是淅淅沥沥,落在身上潮乎乎、湿答答的,叫人不好受。佩雙只管挑了人家的屋檐下走。屋檐下,有的架着一竿衣服,还没来得及收进去;有的坐着一只茶水炉子,水已经快开了,茶壶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不知谁家的屋檐下挂着一只鸟笼,那笼子里的黄鸟也许是因为下雨,倒显得很兴奋,扑棱着翅膀跳来跳去的……佩双一路小心地避着雨,忽然传来一声:“喂!”声音不大,佩双虽不至于唬一跳,还是稍稍有些吃惊,循着声音一看,不见说话人,看看店铺,噢,是那家银匠店。佩双也就知道是谁在跟她打招呼了。
果然,店铺后面探出一个身影来:“我在这儿呢。”男孩说话之间有种得意的神气,好像他们在玩捉迷藏,她没有发现他。佩双见他笑嘻嘻的,也就笑着问:“你怎么看到我的?”男孩说:“下雨了,街上冷清清的没什么人,我难得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不经意瞧瞧,原来是你。”男孩说了一气,又问,“你又去你外婆家?”佩双点点头:“你呢,在干什么?”男孩说:“看守铺子呀。”佩双哦了一声,看看细细密密的雨幕,说:“我得去外婆家了,雨落大了可不好。”
“等等。”男孩叫住她,在店铺的排门后找出一柄湖绿色的油纸伞,“刚好这儿有一把呢,给你。”佩双接过了,笑着道:“每次都是你帮助我。”男孩依旧挠挠头:“这没什么啦。”
佩双到了外婆家,和外婆一起用了午饭。返回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经过银匠店的时候,佩双自然就记着把伞还给那个男孩。
佩双去还伞的时候,一开始叫不应,也就不由得跨进店铺,先把伞放下,等等再说。佩双第一次进银匠店,眼前一片银晃晃的。正待定睛看个仔细,那个男孩出来了:“来了,我刚才在后厢,早听见你‘喂喂地叫我了。”佩双不由得觉得好笑:“你叫我不也是‘喂呀‘喂的?”男孩自觉理短,就成了锯了嘴的葫芦。佩双嘻嘻一笑,大大方方地告诉他:“我叫佩双。‘佩就是‘玉佩的‘佩,‘双就是两个‘又。”男孩听了拍手说:“哎呀,你的名字真有趣,就是佩了两块玉。”说罢也告诉对方,“我的名字叫卯生,‘卯就是兔子的意思,因为我生在兔年。平常我师父叫我‘阿卯。”
“你属兔子的?”佩双惊奇地问。阿卯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佩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物什,原来是只陶做的小兔子造型的口哨,“人家送我的,听说是从惠山带来的。既然你属兔,就送你。”阿卯摇摇手:“不好,人家送你的,你还是自己留着玩吧。”佩双把陶兔放在柜台上:“给你——不然我以后不跟你说话了。”阿卯只好谢着收下了。
阿卯叫佩双在铺子里玩一会儿:“反正我也是一个人。”佩双问:“你家大人呢?”阿卯说:“我师父师娘最近去上海了,留我一人看守铺子。”佩双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他是银匠店的小学徒了。说话间,有女客进来了,阿卯起身询问。原来那人是想把旧的银器新打首饰,阿卯在本子上把客人的要求细致地记下了,又告诉她做好大概要多少时间。
待那人走了,佩双服膺地说:“你真厉害。”说得男孩有些不好意思:“我其实什么也不会,帮师父打打杂而已。要论厉害,我师父才称得上呢。你看,这些首饰都是我师父打的。”佩双在男孩的邀请下,隔了玻璃看柜台下的银首饰。陈设着的首饰有大的小的,圆的扁的,挂的戴的,各式的造型,各式的纹样。阿卯一一地指与她:“你看,这些都是女饰,这是戴在头上的簪子;这是耳环,这个又有点儿不一样,是耳坠;这个是一串银项链,这些都是项链的坠子:花瓣形、鸡心形……”佩双看得频频感叹:“真好看,真想知道它们是怎么打出来的。”阿卯又示意佩双看另一边:“这些是童饰,这是锁片,这是麒麟送子牌,这是手镯,这个有铃铛的是脚镯。”佩双打断他的话问:“脚镯是不是戴在婴儿脚上的?”阿卯说:“对,一般都是满月了戴的。”佩双见那铃铛圆灿灿的精致可爱,情不自禁地喃喃道:“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件银饰就好了。”阿卯笑起来:“你才刚问了,这是婴儿戴的。”佩双知道阿卯误会了,认真地解释:“我是想着送给小弟弟的,我娘快生了。”阿卯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想想又觉得奇怪:“你娘还没生下来呢,你怎么知道是个小弟弟?”佩双叹了口气说:“其实我想有个小妹妹。我爹不让我这样说,他说娘这回生的肯定是个小弟弟。”阿卯像个小大人似的眨眨眼总结说:“其实你爹是想要个男孩呢。”佩双听了,又笑了:“没关系,我娘悄悄说了,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我都快当姐姐了。”
“哦——”阿卯又回过神来,“怪不得你老是跑外婆家。原来是你娘不方便出门了,你代你娘看外婆。”佩双点点头:“我外婆身体不好。我娘常常惦记着,做了好吃的让我给外婆送去。”阿卯建议说:“可以把你外婆接到你家呀。”佩双轻轻摇头:“我外婆不肯上我家呢,说我娘自己都照应不过来,她来了还要照应她。”佩双说完,就呀的一声叫起来:“说了半天,我该回家了。回得晚,我娘肯定要担心了。”
临别的时候,阿卯和佩双约定好,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到铺子里来找他玩。佩双爽快地答应了。“不过——”阿卯想到什么,又说:“我师父师娘应该快回来了,要是你经过的时候看到我师父在,不要进来。我师父不喜欢小孩子来店里看野眼,除非是大人带着的。”佩双清脆地应了一声:“我知道了。”
佩双有好几天没去外婆家了,因为佩双外婆来佩双家了。外婆本来是送催生的小黄衣服的。佩双娘见佩双外婆来了,挽留她住几天。佩双也劝:“外婆,您就住下吧,您不住我家,我娘也一样要给您做菜呀。您住下来,还省得我跑腿。”佩双外婆就向佩双娘笑:“這鬼丫头,原来净给自己考虑呢。”
佩双外婆住了下来,佩双时常地给外婆说笑解闷,或者给外婆梳梳头、捶捶背。乐得佩双外婆说:“佩双待外婆这么好,外婆就不想回家去了。”佩双就说:“好呀,外婆和我们住一起,多热闹。”更多的时候,佩双是在院子里洗衣服。除了洗爹娘的衣服、她自己的衣服,现在还多了外婆的衣服。
佩双家的院子里有一口井。这天天气晴好,佩双提了吊桶,打了水,又把水倒进一个大木盆里。佩双很喜欢水倾泻下来的样子,哗哗哗,像个小小的瀑布。水珠溅起来,也那么美,如珠如玉。
哗哗的水声中夹着口瞿口瞿的声音,像蟋蟀在月光下的清响。佩双愣了一下,放下吊桶,开了院门,凝神谛听了一会儿,果然看到那边一个身影在巷口一晃,就要过去了。佩双跑出一段路,叫住他:“阿卯——”
只见阿卯诧异地转身:“佩双?你怎么在这里?”
“我家在这条巷子呀。”佩双说时手一指。
“你去哪里?”阿卯问。
佩双笑起来:“咦,怎么抢了我的话?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准备洗衣服呢。”
阿卯也笑:“我给人家送货呢。”又疑惑着问,“你既然在家里,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佩双一指阿卯脖子上挂着的那只陶兔口哨:“呶,是它告诉我的呀。我一听哨子声,就觉得这声音很熟悉。”
阿卯和佩双说了几句,因要去一户人家送打好的首饰,就和佩双先别过。刚走出几步,就又折回来:“佩双,你想看怎么打银饰吗?”佩双不假思索地说:“想。”“明天你来。”阿卯说完又小声地在佩双耳边叮嘱了几句。
第二天,佩双如约到银匠店。侯银匠在店里。佩双也不胆怯,落落大方地叫了一声:“银匠师傅。”侯银匠见佩双恭恭敬敬地叫自己,自然也就不能不搭理:“小姑娘,你来这里做什么?”佩双说:“我来看看我表姐的首饰打好了没,表姐说,她的戒指是要桃心梅花式样的。”
侯银匠叫阿卯把登记簿找来,查看了一下,说:“你表姐姓什么……哦,姓方……对,有个方慧琴,花草纹银镯一对,桃心梅花银戒指一个。小姑娘,你放心,这儿记得清清楚楚的。”佩双又问:“什么时候能打好呢?”侯银匠说:“快的,明日就可以拿。”
佩双听到这里,不知该怎么办,走还是留,进退两难。阿卯也有些着急。刚才的这出“戏份”是阿卯跟佩双说好了的,假装佩双是其中一个顾客的熟人来店里探问。正在为难之际,只听侯银匠说:“小姑娘,你不放心,我现在就把戒指打起来给你看看。”
佩双悄悄朝阿卯看了一下,着实有些喜出望外。
侯银匠拿出一套工具:各种锤子、锉子、钳子、模子,看得佩双眼花缭乱。侯银匠又拿出一盏酒精灯,点亮,那透明的玻璃瓶上便似开了一朵蓝莹莹的莲花。侯银匠取过一支带有弯头的吹管,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那蓝色的火焰便被吹成了一道细线。火焰的那头,正对着一方银块。那银块在火焰中融软如泥。侯银匠不慌不忙把变软的银块放进一个铜模子里,气定神闲地拿了一把小锤子叮叮当当敲一敲,哎呀,那一块渐渐延展开来,一会儿有了一个圆环的造型了!侯银匠又锤一锤,锉一锉,动作如行云流水,丝毫不乱。佩双还没看够呢,叮叮当当的声音也还没听够呢,侯银匠又变戏法似的把它放进水中,嗤啦一声,眼前就是一枚闪闪发亮的银戒指了。更令人叫绝的是中间是一个优美的桃形,一朵梅花在桃形中冉冉开放,梅蕊也清晰可见。佩双看得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侯银匠朝佩双笑道:“小姑娘,看清楚了哦,桃心梅花,不错的。”佩双回过神来,连连说:“真好看,银匠师傅您真是太厉害了。”侯银匠哈哈一笑,大概受了夸赞,兼之熟能生巧,另外两只镯子也一会儿就打好了。侯银匠问佩双:“你表姐有说让你把东西带去吗?”佩双干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接口了。还是阿卯反应快:“师父,还是我送去吧,万一有个闪失。”侯银匠赞许地点点头:“对,还是你送。”
两人出了银匠店,走出一段路。阿卯叹了一声:“好险!”又问佩双,“你怎么看得忘记走了呢?”原本计划着的,让佩双看完一件银器的制作就离开店铺,逗留时间久了,怕被师父觉察出什么。佩双有些歉疚地说:“真不好意思,我看得不觉忘了——好在你机灵。”阿卯听佩双这么说,淘气地吐吐舌头。
自从在银匠店看银匠打银,此后一段时间,佩双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店铺。既然阿卯的师父回来了,佩双也就不好去银匠店找阿卯说话了。
当然,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佩双娘生了。佩双得在家里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娘,帮娘端茶送饭。娘休息的时候,佩双还要帮娘洗新生儿的尿布。佩双家院子里现在到处晾晒着旧床单做成的尿布,在五月的熏风中飘飘拂拂,像一面面暗淡的旗帜。
佩双正在晒着尿布的竹竿下穿梭着,忽然听到院门有剥啄声。轻轻打开,咦,门口站着阿卯呢。
佩双连忙让阿卯进院子。阿卯摇摇头:“不了,我跟你说句告别的话就走。”佩双发觉阿卯今天有些异样,猜着阿卯肯定遇到了什么事,执意让他先进来坐会儿。阿卯也就不推辞了。
一路,佩双用手抚着被风吹起来的尿布,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娘生了。”
“生了?”阿卯反问。
“嗯,是个弟弟。”
“不是妹妹呀?”阿卯好像为佩双有些惋惜。
佩双却由衷地说:“弟弟也好,我也喜欢。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可爱呢,胖嘟嘟的。”
刚才阿卯和佩双说话的时候,佩双看到他的眼睛有些红红的,佩双咦了一声:“阿卯,你今天真变成一只兔子了。”佩双说的是句玩笑话,换在平常,阿卯早就笑了,在今天却还是闷闷不乐的。
佩双问:“你怎么了,到底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阿卯就把事情简要地向佩双道来。原来今天阿卯被师娘骂了。师娘发现她的一条金项链不见了,找遍了未果,就问阿卯有没有看见过。阿卯明白师娘是在怀疑自己,心里很气愤。一向熟谙自己的师父过来帮阿卯说了句好话:“他要拿,这满柜子的银的早就拿了。”师娘轻轻哼了一声:“他傻呀,当然知道金的比银的值錢了。”阿卯心性高,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话,一面大声地说:“我没拿,没拿!”一面就跑出来了……
佩双听到这里,问:“阿卯,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还回去吗?”
阿卯摇摇头:“不想回去了,师娘怀疑我偷了她的东西,我回去了,就一直得背着一个偷窃的骂名。”
佩双叹了口气:“那你以后去哪里?”
阿卯垂下了头,半日没吭声。
佩双问:“你家在哪里?”
阿卯声音一低:“我没有家了。”
佩双吃一惊,斟酌了下,又问:“你爹你娘呢?”
阿卯声音更低沉:“也没了。”
佩双不知如何安慰阿卯,只是陪着他坐着。良久,阿卯自己开口了:“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人世了。我是我奶奶拉扯大的。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奶奶生了病,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了族里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现在的师父。”
佩双听了说:“这么说,后来是你师父把你养大的?”
阿卯点点头:“对,师父还教我制银的手艺。”
“那你原来的家呢?”
“卖了。卖了的钱给我奶奶下了葬。”
佩双听了,不觉把膝盖抱紧,把下巴搁在膝盖上:“阿卯,那你以后去哪儿呢?”
“暂时还没想好……”
“要不——”佩双抬起来,眼睛真挚地看着阿卯,“你先来我家住几天吧,以后你慢慢找去处。”
阿卯听佩双这样说,有些惊讶,他马上摇摇头:“不行的……”正待说几句,耳边传来婴儿又尖又细的哭声。佩双站起来:“我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又对阿卯说,“你先坐会儿。”
过会儿佩双出来一看,阿卯早离开了。
佩双回想着阿卯刚才和自己的对话,不知阿卯现在去了哪里。她心里有些隐隐的担忧和忧愁。
佩双想着,如果自己就是阿卯,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去哪里呢?佩双想了一个晚上,也想不出能去哪里。第二天,佩双寻了个空,决定先到银匠店看看,但是看到店铺上了排门。
一连两天,佩双都吃了闭门羹。
第三次,佩双来到银匠店,才看到银匠店像以前那样开张着。尽管如此,佩双还是悬着一颗心。
银匠店静悄悄的,该是没什么人吧?佩双正把身子隐蔽在外面,朝里看望的时候,不期却看到了阿卯。
“你在了?”
“你来了?”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两人的声音也一样地充满了惊喜。
阿卯面上有些讪讪的:“进来告诉你。”
“你师父师娘呢?”佩双有些顾忌。
“都出去了。”
佩双这才进来了。阿卯告诉她,自己本来不想回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就在外面过的夜。第二天,他想去哪里找份事做,不料却饿昏在地。有人认识他,就把他送到了这里来……
“你以后不会走了吧?”佩双问。
“毕竟师父还是对我好的。”阿卯委婉地答。阿卯还告诉佩双,为了这件事,师父还狠狠地把师娘数落了一通。
“那条金项链呢?”佩双插话问。
“找到了。”阿卯不等佩双细问,解释说,“第二天就发现了。那条金项链,就在师娘的房里,师娘自己找到的。”
说到这里,阿卯叫佩双等等,转身跑进里厢去了。
佩双不明白阿卯有什么事,阿卯旋即就出来了,手里拿了一样东西。定睛一看,是只银项圈。
“给你——不,给你小弟弟。等他满月的时候可以戴。”
佩双摆摆双手:“不要不要,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这银项圈是我师父给我的。本来也是人家订做的满月礼,我师父酒后糊涂——恕我这么说一回我师父,我师父没有别的爱好,闲来就爱上酒馆喝酒——就多打了一只。师父见打出来的项圈精巧可爱,也不忍把它毁了,就送给了我。”
佩双说:“你师父送你的,你就自己留着吧。”
“听着,”阿卯像是命令地说,“这项圈对我来说,其实从来就用不上,太小了。就算大小正合适,我也不能戴在身上——我师娘见了肯定要多话。我就一直把它藏在我的床底下。送给你,也省得我提心吊胆的……”
“祝你的弟弟健康平安。”阿卯把银项圈递到佩双面前。
佩双终于接过来:那银项圈锃亮、圆圆的,像极了一轮满月的月环。
选自《十月少年文学》2019年第9期
吴新星,浙江宁波人,儿童文学作家。文章见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读友》《童话世界》《十月少年文学》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种版本的年度儿童文学,著有小说集《玉簟寒》《苏三不要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