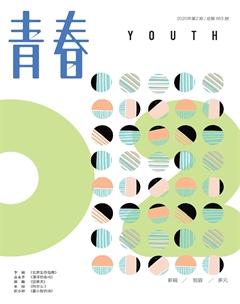麻雀
王鹏辉
教师点评
青春是一团莫名其妙的情绪,总是充满悖论和疑问。青春小说家难能可贵的是将自己知道的省略掉,将自己不知道的写出来,在寻求疑问答案的同时,呈现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出能供人深思的新困惑。米兰·昆德拉也曾说过:“小说家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在我看来,本文的魅力正在于作者比较充分地展示了青春期的莫名躁动和无法言说的生命之河。少年时,由于自己烦躁不安,打死了一只麻雀,内心滋生了无尽的愧疚,然而到了当下,儿子却又在自己深陷于过往的愧疚时,失手打伤了羊羔的眼睛,生命之殇在不同代际之间流转,令人唏嘘不已。当然,此文的缺点在于作者对意绪的铺排和细节的刻画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在祭奠麻雀的时候,描写显得过于简单。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陈晓辉
“要玩出去玩!”我朝在书房里乱跑的小叶子喊道。
小叶子已经八岁了,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我和他妈管不住,任由其胡来。虽然生活被搞得一团糟,但我们还是相信天性的力量,我们只是悄悄地画了一个他看不见的笼子。
“爸,别写作业了,快来陪我玩。”小叶子趴在床边嘟囔着,我转过头去发现他背对着我并且手里正在玩着什么。
“小叶子,快出去玩,爸爸要工作。”我将声音提高了一点,我知道这话小叶子肯定听不进去,他有自己的世界。我又说了一句:“快去跟院子里的小羊玩。”
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因为我知道小孩对这些新奇的动物感兴趣。这只小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进我家院子的,那天早上就是被这稚嫩的羊叫声吵醒的。这只小羊满院子乱窜,虽是小小的一个,却跳得极高,一般人根本抓不住。当时小叶子就在院子里追着它跑,看两个活泼的生命在院子里追逐也别有一番情致。
小羊羔一直没有人来认领,它也就习惯了在我们家的生活。早上依旧是满院子狂跳,下午跳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睡大觉。
今天的小叶子却无动于衷,他依旧趴在床边玩着自己的玩具,看来他对小羊羔失去了兴趣。小孩子喜新厌旧的快,满屋子的玩具就是证据,看来手里玩的东西正是他的新战利品。这样也好,我能安静地工作了。可是不一会儿,他又开始在我身后大叫:“爸爸!”我转过头去,脸上挨了一颗塑料子弹,虽说软绵绵的不怎么疼,但我心里开始冒火了。小叶子却哈哈大笑起来,紧接着就开始在书房乱跑。我气得大叫:“谁给他买的弹弓!”但他一点都不怕我,笑声传满整个书房。我决定给他一些教训,我站了起来,他嘻嘻哈哈地跑到了门边,拉开弹弓,做攻击的姿势:“不许动,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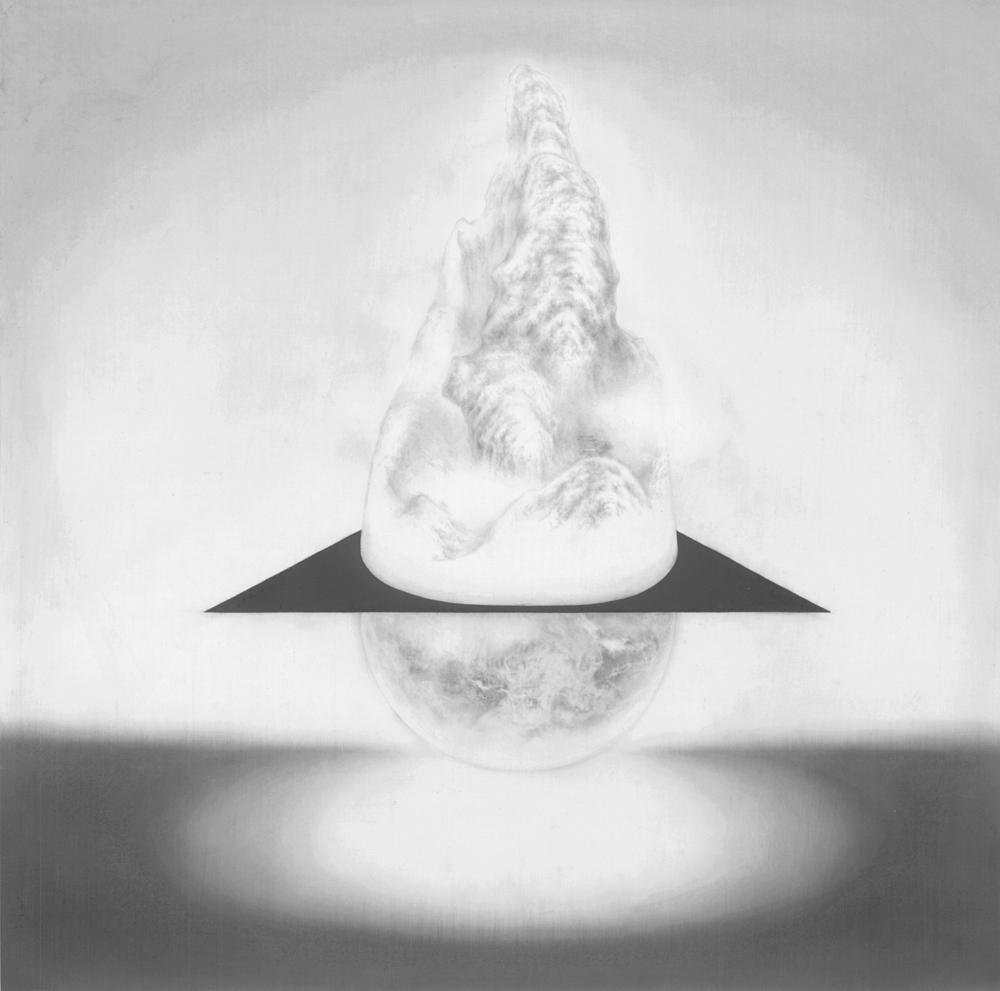
我尝试着朝他前进了一步,没想到这臭小子竟然将子弹射了出来,我下意识地抱了一下头。其实小叶子打偏了,子弹从我旁边飞过,击中了阳台上的镜子。虽说是塑料子弹,但镜子还是哐啷一下出现了裂纹,镜子被分割成了好几个部分。我的脸沉了下来,镜子里出现的好几个小叶子,都是一脸惊恐的表情。我假装不看他,他也深知自己做错了事情,趁我还没有转过脸来,就悄悄出去了。
虽说损失了一面镜子,但我的世界总算清净了。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一时半会还难以适应。我点了一根烟,转过身,通过阳台上已经四分五裂的镜子,看到八九个小羊静静地卧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小叶子已经跑到院子里,他在草丛里乱跑一气,麻雀被他赶得叽叽喳喳乱飞。一只无意中竟落到了小羊的头上,小羊并没有排斥,还在呼呼大睡,于是镜子中又出现了八九个麻雀的身影,它们整齐地跳跃着。
这一刻时间概念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了,我对我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了多年前的一幕,这一幕在我的身体里埋藏得很深,而镜面里的麻雀将它提出了水面。过往的事情像一组连环画,画面中带着夏天的燥热与不安。我望着那镜子里的小羊和麻雀出了神。它们的形象充斥在裂缝的周围,有的填满了小块的镜子,有的被裂缝切成了好几瓣,不停地动着,声音却从远处传来。我摸了一下额头,挪动了一下凳子的位置,重新看向那面镜子。倒三角的尖喙中装着红色尖舌、黑色的眼珠埋在褐色羽毛里。我盯着它们看,那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大,向我袭来,吓得我转过身去。但记忆的洪水还是包围了我。
我闭上了眼睛。
蝉叫声出现了,是那天的蝉叫声,密集而强烈,甚至盖过了间断的麻雀叫声。
当时满天灰白色的云朵挡住了太阳,密压压的,很有层次。
我正蹲在粪堆旁屙屎,一边用手不停地驱赶着我屁股上的蚊虫,一边瞅着天空。云朵堆积起来像一面挂在天空的镜子,就像我现在看到的镜子一样,云缝是天空的裂痕。我盯着一个地方使劲看,不一会儿,天空中的云动了起来,它们整齐地从一个方向游动到另一个方向,但当我的目光随着云移动的时候,那些云又停了下来,我回过头来找目光的起点,却已经找不到了。
不一会儿,我弟也将裤子褪到脚踝,蹲在了我旁边。我嫌他臭,半蹲着移了几步,蹲在了桐树的正下方。那棵巨大的空心树就在我的正前方,蝉鸣和麻雀叫就从树叶最密集的地方传来。偶尔我能看見麻雀的影子闪过,却找不到任何蝉的影子,只能在不经意间看到褐色的蝉蜕。
云压得更低了,像极了土地的被子。燥热感更加强烈,我裸露在外面的屁股仿佛蒙上了一层雾。蝉叫得更凶了,那些麻雀在密集的树叶里窜来窜去,树叶子偶尔掉在我头上。那些桐树叶只有空心的杆子,树叶子已经发黄卷缩。我稍稍将屁股抬高了一些,伸手去捡旁边的树叶子。我将它们拿在手中,使劲吹了一口气,顶部干瘪的树叶子就掉落了。我还不满足,将剩下的树叶子捏在手中,使劲地揉搓了起来。手汗混着空气中的热气一起被揉进了树叶子里,它变成了许多小片,从我手心中掉落。在掉落的过程中仿佛沾上了空气中的水汽,落在地上变得又细又碎,黏成了一团。
我记得当时有点风,但丝毫吹不动地上的细屑。我将手盖在这堆东西上,手心湿湿的,死掉的树叶子虽然细碎,但还是扎手。我开始使劲压,我感觉黄土逐渐淹没了它。雀麻叫、云朵、蝉鸣仿佛也被我压在了手下。彷徨、高兴、悲伤都不重要了,只是心底还在隐隐作痛。这是时间带来的,也是时间所揭示的。
想到这里,书房中我的手也变得湿湿的,我用手心摩挲着凳子,就像当时手底下压着的树叶一样。
“爸,看我!”小叶子的声音传了进来,我惊醒了。“咣”的一声,弹弓的子弹打在了书房的玻璃上。我没有管他,只解开了上衣,摸了摸湿热的胸膛。碎片中的小羊又跳了起来,它额上的麻雀已经飞走了。我向镜子靠近一些。
一个老头拉着一只大羊从里面出现了,还带着三只小羊羔。
那只羊在哺育期。三只小羊羔跟在大羊的后面。老头的行动很缓慢,他将羊拉到草最茂盛的地方,慢慢地弯下腰,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羊橛上,可羊橛在土里只扎了一小半。他又慢悠悠地捡起旁边的砖头砸了几下,金属声穿透了其它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我那声音一下又一下,很有规律。他直起腰用脚踢了几下,羊橛没有怎么动弹,他才放心地抽烟。
三只羊羔一直想找机会吮吸奶,大羊却只顾着吃草。小羊稍微一靠近,大羊就会立马走开。老头看见了我们,朝我们笑笑。
我又重新挪回空心桐树的正面。我弟朝我挪动了一步,并扔过来一个土块。我嫌那东西扎屁股,就扯了几片桐樹叶擦擦,就跑回家了。我弟用土块擦了几下也跑回了家。他就在我身后,我扒在门框上朝外看——那老头还在看着我们,就像我现在看着这面被打碎的镜子一样。
蝉声更加稠密了,麻雀好像从树叶最稠密的地方分散了。它们在我前面的任何地方,我看不见它们,它们却包围住我。
我更加烦躁了,碎镜子竟然引起这么多回忆。我靠在阳台的墙上,那些碎片也映出了我的脸。在挠刚被裤子遮住的屁股时,我大叫一声,试图盖过身边可恶的叫声。等我的声音消失后,大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重新埋下头。
我弟追在后面问我叫什么。我没有说话,又挠了挠屁股。
三只小羊羔里有两个比较壮实的。它们在大羊的腿间跑来跑去,大羊一边吃草,一边躲小羊。第一只小羊被大羊一脚蹬开了,第二只小羊趁着大羊抬腿之际,迅速噙住了大羊的一个奶头。大羊使劲地蹬着后腿“咩咩”叫着,可这小羊就是噙住不放,大羊叫了几声后便妥协了。
麻雀还在使劲地叫着。一辆拉着沙子的拖拉机从公路上驶过,挡住了老头和他的羊。
我跑出去捡了一块土,向左侧扔去。那里堆满了柴火。扑棱棱,许多灰色的麻雀从干枯的树枝中飞了出来,飞得很低很快。不久它们又消失在新的树枝中。我弟跟在我后面向刚才的地方也扔了土块。他力气小,土块落在了干柴旁边,并缓缓地滚进了干柴里,可惜麻雀已经飞光了。
我又捡起一个土块,向着空心桐树的高处扔去。土块穿过了树叶,一群麻雀又飞了起来。土块落到了对面的草丛里,大羊警惕地抬起了头,停止了咀嚼。小羊半卧在大羊的身体下,不停地吮着大羊的奶头,偶尔用头撞一下。那两只强壮的小羊嘴里泛着白沫,比较弱小的那一只没有抢到奶头,着急地在另外两只的身上踩来踩去。大羊厌烦了,往旁边移了一下,它便滚落下来。
我又捡起一块土,向空心桐树的高处扔去。又有一些麻雀飞了起来,我心里想着一定要赶走这聒噪的声音。这次土块落到了老头的旁边,老头吐了口痰,把烟袋在鞋底敲了几下:“娃,你这样是打不着的。”他说。“我肯定能打着,一会儿我给你打一个看看。”
我捡起土块又扔了几次,麻雀总是从这里又飞到那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并没有减弱。我弟给我拿来了一把弹弓,那是我们用铁丝和皮筋做的。我往兜里装了一把小土块,再往弹弓里装了一个。我朝桐树叶密集处打去。弹弓的威力果然大得多,土块穿过树叶,打在了树干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当我听到这响声时,我挠了挠屁股,感觉清爽了些。我又打了几发,但都没有打中。
“爸!”小叶子又在喊我,我重新回到书桌前。我摸了摸自己,那种潮热感又加重了。镜子里小羊和麻雀已经消失了,只留下被切割的草地。小叶子还在院子喊叫,我听见他在追逐跳跃的小羊。小孩子的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他打到我的事情或许已经忘记了,我也快忘记了,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就像小叶子一样。看到他就像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那一年小叶子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我想为他造一座高塔,又想在这高塔之外立一个牢笼。希望他体验到做人的快乐,又不至于偏离人的轨道。
我调整了一下姿势,躺在了椅子中,望着蓝色的灯光,那是我工作时必须要开的蓝光。透过蓝光,我目眩了起来。蓝色的天花板变成了灰白的天空,我看到那时的云向我袭来,很低很低,并且远处传来一阵轰隆声。
大羊的两只奶头干瘪了下去。那两只半卧的小羊肚子圆滚起来。瘦弱的小羊依旧在大羊的身下挤着,怎么也噙不到奶头。
左侧的柴火堆里落了一只麻雀,黑色的身影晃动着。我往弹弓中装了一个土块,拉满了皮筋。“嗖”的一下,击中了麻雀站立的柴火堆,麻雀飞走了。麻雀的叫声弱了一下,又恢复了。蝉也一直在叫。
记得当时我的屁股又变化了,它贴上了一层雾。就像对面老头身前的烟雾。大羊依旧埋头吃草。两只小羊已经在一旁玩耍起来,那只弱点的小羊发疯地噙住干瘪的奶头,但它的嘴角没有渗出白沫。
我重新抓起一把土,向树叶深处扔去。一群麻雀飞了出来,在左侧的柴堆上又站了一些麻雀,一个蹦跳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刚才的地方。我再次拉满了皮筋,瞄了一下便放了手。那个身影叫了一声,便掉落下来。像一滴黑色的雨。
我打死了那只麻雀,我想。
“打中了!”我弟说。
我隐约听到了老头又在敲烟袋,我记得我当时又摸了一下屁股,冰凉的,并且心情平静了下来,没有了兴奋的感觉。
我对麻雀死后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弟跑了过去,捡起树枝戳了戳落在地上的麻雀,那麻雀的尸体在我弟的拨弄下左右翻转着。我听不见蝉声和麻雀叫声了,雷声却越来越近。
麻雀的爪子蹬得直直的。我捡起它放在手心,羽毛软软的,还有温度。土块打中了它的头部,眼睛凹陷下去,尖尖的舌头露在外面,血从眼珠的位置和嘴角渗了出来。我用手动了动它,除了肚子上的绒毛被风微微地吹动,它的其它部位已经僵硬了。
土块已经被打散了。我看着这细小的颗粒,仿佛看见它从皮筋中射出的场景。我是土块么?我当时就在想着,应该是吧,土块带走了我全部的感觉。
当时的这种感觉在这书房中又被重新找回来。我又脱了一件衣服,那种黏稠的潮湿感席卷了全身。我站起身,打开阳台窗户,外面吹来的风并没有起缓解作用。小叶子和小羊跑累了便坐在树下休息,他用弹弓在打着什么。一颗子弹越过窗户击中了镜子。一块碎片被打掉了,剩下大的碎片被击成了更小的。院子里的小羊又出现在镜子中,这次它的身影更多。
我已经没了火气,我的心思全在那只麻雀身上,我不停地回味,甚至在某个时刻感觉自己就是那只麻雀。小叶子又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转过身去背靠着墙,看着更加破碎的镜子。
我听见大羊叫了一声,踢走了那只瘦弱的小羊。两只干瘪的奶头在它身下晃动着。瘦弱的小羊羔滚了几下重新站了起来,它的嘴角没有渗出白色的乳汁。而另外两只斗得更凶了,头骨碰撞的声音我仿佛都能听见,白色烟雾又遮住了老头的脸。
蝉声又在我耳朵里出現了,盖过了麻雀叫。我已经分不清是当时的耳朵还是现在的耳朵。
我记得我那时坐在门口,我弟坐在我旁边。我看着天上的云,密压压的。
那尖尖的舌头不停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凹陷的眼窝。我闭上眼睛,这两样东西在我的脑海里转了起来,它尖尖的舌头伸了出来,变得很长很长……
老头的声音还在不停地回响:“娃你这样是打不着的!”我本来不想打死它的,只想击中它,它太吵了,可是我终究还是打死了它。我睁开眼睛,看了看老头,他的脸依旧在烟雾里。两只吃饱的羊羔撞得更凶了,一下又一下……那只弱小的羊羔开始叫起来,每一下叫声都很长。大羊还在吃着草,偶尔抬起头来。它嘴角渗出的绿色汁液,渐渐地染绿了它的白胡须。
雷声又响了几下后,麻雀叫和蝉声重新回到我耳朵里。
记得我当时站起身来捡起死掉的麻雀,拉着我弟朝那棵空心树走去。我坐在树旁,像极了那三只吃奶的小羊羔。我将麻雀放在树根处,找了很多树叶堆在它身上。
回家想取个打火机来点着它,忽然对面老头点烟的样子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反复想着他点烟的动作。他掏出火柴来,轻轻一擦,火苗便窜了出来。小小的烟草只需要一根火柴所产生的火苗,那火苗的形状也就越来越大。这只死去的麻雀需要更大的火苗,对!更旺的火焰。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跑回家拿了一盒火柴,一个打火机。我将整盒火柴都掏出来,攒成了一把,用绳子绕了几圈然后扎起来。打火机一点,火柴发出“嘶——”的声音,白烟升了起来,巨大的味道直往我鼻子里窜。
我坐在椅子上摸了摸我的鼻子,是刺鼻的味道。接着我将火柴扔到了那堆东西上。树叶燃了起来,升起的白烟穿过了空心桐树茂密的树叶。一阵鸟叫声又响了起来。
我揉了揉耳朵,坐得端正了一些。
我听见小叶子又在外面的草丛里胡闹了,麻雀叽叽喳喳地乱飞。书房里暗了下来。那红蓝色的火苗从那些碎裂的镜子中溢出来,烧麻雀尸体的情景重新显现出来。我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那火依旧在镜子中燃烧着,我已经听不见小叶子玩耍的声音了,我自己的行为逐渐在镜子里显现。我朝着那堆东西磕了一个头。我不知道当时磕头的对象是火焰,还是火焰下面的死麻雀。我弟就站在旁边,他呆呆地看着那升腾起来的火苗,窜起的白烟冲起了些许羽毛和灰尘。我说快,你也磕一个。他无动于衷,他说不就是死了一个麻雀吗?我说那是我打死的。我磕,你也必须磕。我拉着我弟让他也磕了一个,他脖子梗得直直的。升起的烟灰落在了他的头发上,像一片片被污染过的雪花。
雷响了几声,雨落了下来。我又摸了摸屁股,好像重新蒙上了一层雾。对面的老头站了起来,敲了敲烟袋拉着他的羊回家了。那只弱小的羊羔依旧在叫。
我和我弟站在门道里,蝉声和麻雀叫声逐渐被雨声覆盖了。
坐在此时的椅子中想着当时的感觉,有了时间的隔阂仿佛看得更清楚了。那只是一种原始的冲动,不知怎么来的,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想做这件事,无关对与错。那股潜藏在身体里的力量折磨着你,让你不断动着身体,就跟今天的小叶子一样,只按自己是否快乐来进行。当时我可能有一点点理智,可这唯一的一点在冲动的漩涡中很快就被湮没了。我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那股力量被释放之后,我的理智、我的恐惧又恢复了。尤其是现在,当我看到破碎的镜子,镜子中的麻雀,我的恐惧感又出现了。时间只能在我心里的创口上盖上一层膜,可回忆会在某一时刻戳破它。带着狂躁与理智戳破它,那个伤口会更深,血流的会更多。那是以前罪责的堆积在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效果。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决定看看那鲜活的生命,以便让自己的伤口愈合。
“爸爸!”小叶子在下面喊我了。我向下看去,小羊躺在树下,四条腿不停地蹬着。小叶子正按着它的脖颈,四只小小的蹄子在地上划出很多痕迹。“爸爸!”他叫道。小羊的眼睛流出了红色的血,弹弓的子弹应该击中了它的左眼球。血顺着眼角向下流着,但没有浸染白色的羊毛,像一滴滴露水划过荷叶。
“小叶子!”我大喊了一声便转过头去。
只听见小叶子在底下“爸爸”“爸爸”的叫着,我没有再看他。我点燃一根烟,我看见了那些碎片中被烟雾遮盖住的自己。当这股烟雾消失之后,背后出现了喊叫着的小叶子,和颤颤巍巍要站起来的小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