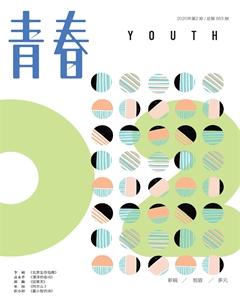阿尔山
巫昂
年二十九,也就是次日大年三十的那天,索伦高娃约我一起吃饭,那天的气温大概零下七度,我犹豫是该打车去还是骑车,或者走路,高德导航显示,从我的住处到我们吃饭的四川办事处餐厅只有一点五公里。在犹豫的过程中,试了试滴滴,已经没什么司机接单了,走路又太冷,我只好骑上摩拜。
贡院东街,从一道一米不到的门穿过去,就是“川办”的餐厅,门前挂着红灯笼,一个保安在寒风中缩着脖子,瑟瑟发抖。索伦高娃比我早到约莫十分钟,她坐的直达公交车。她个子很高,穿着一件粗线长毛衣,边上的椅背上搭着黑色长款羽绒服、围巾、帽子,确实是内蒙古人,有足够御寒的衣服、靴子都是半高的,像羔羊的一截身体被嫁接到她身上。
“川办”还是我四五年前来的样子,在那之前彻底装修过。更早之前,像驻京办事处的食堂,虽然面积不小,但是陈设极其简陋,员工还穿着前襟尽是油垢的白色工作服。一个胖服务员站在我们身侧,我凭着记忆点了:重庆辣子鸡、夫妻肺片、麻婆豆腐,索伦高娃要了炒豆苗,我另外要了一碗担担面。两个人的晚饭,这不算简单了,挨着窗户,我细看,才发现那是假窗户,外边就是一面紧贴着的墙,窗外并没有任何风景。窗户就像一张刚刚使劲张开的嘴,被一股寒风堵住。
索伦高娃和我认识的时间不长不短,她有一种高大而神秘的美感,五官排列像是时刻处于不明不暗的光照之中,眼睛是深栗色的,头发微卷,皮肤呈现出日光下瓷器的白。她小我十二岁,非常合适坐在一起,我留意到她手上多了一些纹身,手背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左手每个应该戴戒指的地方都被纹身填满了。而后,我留意到她的手型,骨节突出而饱满。
她家就是阿尔山的,我们相约七月份一起去阿尔山,住在她表哥家,去山里转转。她正在帮出版社翻译一本书,从蒙语翻成汉语,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呢,也接了一本书的翻译活儿,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说是长篇小说,不如说是他的博客日志。如果要在蒙语、汉语和英语之间铺设一条铁轨,那会是从悬崖之上先落到灰尘弥漫的泥地上,而后被从天而降的雨淋湿,淋得到处烂糊糊的。
等菜上桌的时候,我让她说句蒙语给我听听,她问我想听什么。
“你真是挺吸引人的,怎么说?”
她认认真真地说了一遍,我什么也没记住,只觉得她的下巴的线条很特别,像是一只羚羊走在陡峭的岩石上,岩石又被细小的砂砾覆盖。
“为什么你想学这句话?”她问。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深交的内蒙古人。”
确实如此,索伦高娃是朋友带来我家玩的,她一走进屋里,我就觉得竟有那么说不清道不明让人深感吸引的人存在。她坐在沙发上,手肘附身在膝盖上,就那么和我们聊天,聊了很长时间,这个姿势都没变化过。这是个雕塑般的姿势,她做起来非常自然,她像是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神奇物种,那天我们聊得很尽兴,还喝了一瓶酒。她说起了她认识的一个大萨满,丰神威仪,大萨满想让她也去当萨满,伺奉神,她觉得这是个太大的决定了,无法贸然接受。
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任何联系,再见到她的时候,是我的一次新书活动上,她给我带来了两个会弹马头琴的男孩儿,我们坐成一排,聊一会儿,听他们弹一会儿马头琴。她始终坐在第一排的最右边,什么话也不说,像是在放空,即便如此,她脸上还是带着度母般似有若无的微笑,神秘到让人不知所措。活动结束后,我提议大家一起吃饭,她说自己还有事,得先走了。而弹马头琴的男孩们也没有留下来,他们三人好像突然要组成战队奔赴草原,旋风般,而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说真的,我对她有点儿念念不忘,她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是以金属铁笼里安静的怪兽这种心理形象存在,直到有一天她主动跟我联系。
“我爸爸突然去世了,我来北京办后事,然后得留下来照顾妈妈,医生说她老年痴呆,身边不能没有人。”她在微信上告诉我。
“那你在呼和浩特的工作什么的呢?”
“我在呼和浩特没有工作,本来打算去结婚的,没结成,耗了一年多,把租来的一大套房子装修完了,本来想用那套房子和未婚夫一起做个民宿,搬进去没几天,离民宿正式开张还有半个月,我们就开战了。结果客人住进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战场,从客厅到厨房到卫生间,一塌糊涂,我专挑玻璃类、瓷器类的东西摔,客人怕扎到脚,疯了似地就躲到屋里去了。结果屋里地上也有,脚是没扎到。因为我们压根就没雇帮忙的人,我们两个干仗,来不及收拾,只能一边开张,一边打仗。”
“和谁结?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
于是她改用微信语音把她本来打算结婚的对象简单讲了一遍,概括起来变成如下几点:他很帅;他会做饭;他很讨女人喜欢;他背信弃义,喜欢上了其他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她也认识;她知道是这个女人之后,有一天在街上碰到那女的,她走上前去,狠狠地扇了一下那女的耳光。
我想象不出这样一个女人也需要婚姻,总有人应该跳出三界之外,另外建造一种虽然经不起风雨但至少可以躲避一下阳光的窝棚。最激烈的时候,她曾经和未婚夫拔刀相向,刀是蒙古刀,一尺长,开过刃的,本来是用来切割白水煮的羊肉的。持刀的人是她,个子高大持刀才有气势,刀刃在她身侧闪着不锈钢幽冷的寒光,她站在客厅面对着他,无所畏惧,而且打算那天就一刀捅死他,把这段痛苦彻底了结。
“他身高一米八五你知道吧,当时就怂了,嗖地吓得光着脚就跑了出去,好几天都没敢回来,当然我也就接到我爸爸病危的消息,只好回北京了。”
就这样,索伦高娃没能结婚,她回到北京,住在南城一个老小区里,和母亲住在一起。过去妈妈早上起床,都要念一会儿经,再做早饭,现在她四五点钟醒来,开始哇哇叫,让索伦高娃走過去,走到她房间里,索伦高娃昏昏沉沉地去往她的房间,呆呆地站在她床前。母亲还是哇哇叫,索伦高娃得过去坐下,拉起她的手,轻轻地抚摸好长时间,她才能平静下来,在天彻底亮之前再睡个回笼觉,索伦高娃就趴在她床边又眯了一小会儿。等到八点钟不到,索伦高娃得去做早饭,煮小米粥,蒸两个馒头一人一个,再烫个青菜,然后喂给她吃。
从呼和浩特回北京之后,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不知道什么邪恶力量控制了,坐在那里,感觉肋下的一小块肌肉开始轻轻跳动,慢慢地,跳动的节奏越来越快,可以说,是加速度了,然后那块肌肉深处开始感到疼痛。而后,这种疼痛开始蔓延开,像烟一样,从那块肌肉向上蔓延到胸口,到喉咙。它像长很多脚的八爪鱼,从那一个痛点伸展开,缠绕了她的背部和臀部。她疼得一动都不敢动,只能坐在那里,扶住桌子的边沿,疼痛蔓延到了臀部、大腿和小腿,击打着脚踝上的皮肤,使劲地向脚底板袭去,脚底板有如一百根针在扎。太阳穴也有如一百根针在扎,天灵盖亦然。全身上下有成千上万根针,细密而频繁地扎着她身体的每一处。她的汗开始滴落下来,从鼻子渗出大颗大颗的汗,她感到一阵昏厥,又不敢站起来,只能张大嘴使劲呼吸。
“我要疯了,我想出门!”她跟我说。
我们商议了一下让她出门的计划,要和她见面只能是晚上九点以后,她妈妈入睡后,而且不能走太远。我到她家小区边上的一家便利店等她,然后就坐在便利店一角聊会儿天,我们分别从冰柜里拿出酸奶,膝盖挨着膝盖坐着,也是第一次,我发现她眼窝深陷,眼神中燃烧的火有些暗淡。她说自己最近因疼痛近乎昏厥了三次,她甚至动念要切开自己的皮肤看看疼痛是什么形状和颜色的,但疼痛进展的速度往往超过她定位的。
“你去医院看看?”
“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血常规、胸片、心电图、内脏b超,都做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不开心?晚上睡不着,早上不想起来?”我贴着抑郁症的症状问她。
“不,我十分嗜睡,躺下就着,早上恨不得睡不醒。但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很容易突然难过起来,一定要大哭一通才能缓解。”
我不是医生,口舌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又着急,只好岔开话题。我跟她说最近我在学画画,很想找个地方练习人物写生,可是裸体模特儿去哪儿找。吴冠中说他在巴黎留学学画的时候,会聚集到一个叫做树屋的地方,上上下下好几层人都在画裸体模特儿,那个模特儿很专业,每十五分钟换一个姿势,无需任何人指点和提醒。
“真希望有这么个‘树屋。”我说。
“你要真想画裸体模特儿,我可以给你当。”
我画了她两次,在她家,她的卧室里,她妈妈晚上九点睡着之后,她就坐在床上,或者躺着,给我画,我还不会画光线,只是把她大概的样子画了出来。她的身材高大,骨架也像一匹马一样,因为高大,所有的骨骼和肌肉都比常人长。
她喜欢喝酒,我让她躺在那里的时候,可以顺道喝喝酒。我带了一瓶新买的百龄坛,她一个人喝了三分之一,然后歪着脑袋扎到枕头里睡着了,于是我画了她的背部,还有臀和腿的线条。她的肤色在白里面掺了一点银灰,这让她在有阴影的地方也发出微弱的光,我走过去,俯身观察她,感觉她睡熟了,而后,把她的一缕头发从脖子的地方放到脑后。画完后,我给她盖好被子,也去她妈妈的房间看了一眼老太太睡熟的样子,那可真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像索伦高娃一样高大俊美的美人儿。她睡得很沉,很香,微微张着嘴。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别人的妈妈,心里涌现了无限的温情,我觉得我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来帮着照顾照顾她妈妈。她家的门是撞上就关了的老式防盗门,我离开的时候,倒是忘了关她房间里的灯,到了楼下才想起来,仰头找那个窗户,它就像是夜幕中唯一的发光体,我怀疑是她的身体发散出来的。
我第二次画她,感觉比第一次略强一点,还观察了明暗关系,把一些关键的地方深入地画了出来,比如肩膀、脖子和腰臀。我带来了第二瓶百龄坛,淘宝买一送一,一百五十六买两瓶,感觉很合算了。这回,她一个人喝了半瓶,然后跟我说上次剩下的三分之二还原封不动呢,真不该开了这瓶新的。她从冰箱里挖出几颗冰块,在酒里加几块冰让它的温度下降,会有一种清冽的感觉。她还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找出来一袋过期的牛肉干,给了我一块拿在手里,一边画画一边撕咬着,她很自然地脱光了衣服,摆了一个和上次不一样的姿势。
我们这样相对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和谐,不是敌对的、尴尬的,而是顺畅的、简单的。我仔细观察着她身体的特质,不带任何情欲的判断,但我也担心她会突然感到疼痛,从肋下或者什么地方,我一直问她要不要歇会儿,反正画画这件事对我来说,纯属业余爱好,没必要那么郑重其事。
她把手撑在脖子底下,就那么歪着脑袋,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慢慢又喝多了,把脑袋扎到枕头和被子里团成一大堆地喊骂着。
面对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我还没有什么处理的经验,只好到客厅给她倒了一杯水,又去把她妈妈卧室的门掩上,留一个很小的缝隙,让客厅里的灯光能透进去。
我坐在索伦高娃床边,她在我出去倒水的这点时间,居然又睡着了,她真是入睡奇快的体质,睡着了之后,像带孔的珠子,被一根线穿起来了,睡眠成了她的主旋律。我再次帮她盖好被子,实际上,我意识到,如果想画好一个人,得用手触碰她,了解她起伏的身体和转折点,肌肉底下的骨头,要对她的皮肤和毛发有触感,这才行。所幸我并不是拿画画当作本位的人,我只是对人体有无穷无尽的困惑,是什么支持我们的心跳,还有活动,以及爱恨情仇。喝多了之后的索伦高娃和她不喝多的时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始终有一种异族的气质,和我们这些所谓的汉人有色差,在青绿的我们身边,她是浓郁的青金蓝和鲜艳的拿波里黄。
第二次离开她家,坐在那座破破烂烂的塔楼电梯里,我一直在想走的时候关灯了没有,下楼回头张望,才知道又忘了关了。
从那以后,我们好几个月没碰过面,直到这次她约我到“川办”吃饭。
“我好想談恋爱,我觉得我应该有个男人。”她坐下没多久后就跟我说。
“有看上什么合适的人没有?”
“有一个在暧昧期,每天都会聊会儿,但也没聊什么别的,还给我用微信语音读诗。”
“读谁的诗?”
“他在一个公众号找出来的诗,说临睡前读诗,有助于睡眠。”
“这已经算是开始恋爱了。”
“他小我十岁,他好像没这个胆子。”
“对小姐姐又爱又怕。”
“那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昨天约会了。去簋街吃重庆火锅,给我辣的,我就想开始约会了,至少可以拉拉小手吧,我就去拉人家的手,把小男孩吓坏了,一把给我甩开。”
“你太奔放了。”
“我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奔放,他给我读情诗,说晚安,好好睡觉,做个美梦,却不许我拉拉他的手。”
“我们汉人的汉子都是又面又怂的,大叔这样,小男孩也这样,无一例外。”
“真是没劲,最后火锅还是我买的单。”
菜上来了后,我们忘了这个大怂包,开始吃起来。
“你知道我现在是个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人吗?”吃完大部分的辣子鸡,她又跟我说。
“我们好像从来也没聊过你的经济状况。”
“一个字,穷。自从结婚的计划破产后,我就再也没工作过,我有两个姐姐,她们说我既然不上班,又不成家,那就干脆让我照顾妈妈。照顾妈妈我没意见,可是我没收入啊,翻译这本书你猜出版社给我多少钱?”
“小语种不至于太少吧。”
她摇摇头,“人家最后就打算印五千本,这要不是列入国家扶持计划,可能连翻译的钱都给不了,千字六十,十八万字,我可以拿到一万零八百。房子是大姐的,我们住在里面不需要付租金,她每周给我们买点菜和主食来,就这样,我和妈妈就跟坐牢一样呆在家里。”
“哦。”
“我没有现金,哪儿都去不了,不过今天我请客,是我们事先说好的,你别跟我抢。”
我也差不多很久没有挣钱了,一年出头,除了翻译凯鲁亚克那本书预付的一點儿稿费,但我不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阶层,我的妈妈有退休金,我们的日常生活靠她支付,我还有一个做工程师的弟弟,他会帮我们买那些比较贵的东西。比如一件家电,或者窗户坏了,找人来修一修,除此之外,我可支配的钱也不多了。
我坐到她身边,画过她两次之后,我感觉我对她并非一无所知,她的身体、骨骼还有体温,好像火车行进中的隧道,没有进入过隧道的人不算坐过火车。
她突然挨近我,近乎接吻的距离,但我们并没有,她只是贴了贴我的脸。我穿着一件黑色西服,皱巴巴的,头发也乱蓬蓬的,好几天没出门的结果。我们当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这太奇怪了,何况刚吃完辣子鸡,嘴巴里又辣又油乎乎。我相信如果可以深入地去了解一下她,会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如果可以深入她体内,探听一下那里的虚实,并在里面埋一些雷,来年开春说不定有些惊喜。
“我本科学的俄语,研究生在圣彼得堡留学,我本来可以留在那里往国内倒卖倒卖皮草和日用品,结果鬼迷心窍回国了。本来在北京的一家4A级广告公司干得好好的,工作体面加班又多,挺不错的,又被这个未婚夫诱惑回呼和浩特去结婚。我们租了一栋呼和浩特卖不出去的那种独栋楼,自己花钱装修,花了几十万,两人的积蓄都花光了。然后就是我这两个奇葩姐姐,一个比一个抠门儿,我二姐有五套房,我前两天鼓足勇气跟她说,你有五套房,我一套也没有,你给我一套,她吓坏了。”
“送自己的妹妹一套房子,而且是北京的,这对于任何中产阶级都是天打五雷轰的大事儿。”我说。
“不全是北京的,我想要的那套是阿尔山的,我爸爸生前买的集资房,村产权,跟村支书签的购房合同,面对着群山,我早就看上它有个不小的阳台,早上起床后站在那里,用力吸一口新鲜空气,多好啊。我二姐可能那天突然良心发现,居然答应了。我大姐就说,你要答应了,就赶紧把手续办了,写个过户声明,找地方公证一下。”
我想象了一下弥漫在雾霭之中的阿尔山山景,松树上跳来跳去的尾巴蓬松的松鼠,还有隆冬时节,树枝上的冰凌。在冰天雪地当中,穿不多的衣服,站在阳台上,用力吸一口零下三十八度的新鲜空气,恐怕鼻腔会瞬间变成太平间里装尸体的匣子。从阳台上往下看,赤裸的索伦高娃躺在冰天雪地里,她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鱼,鱼鳞闪闪发光,通体透明,现出鱼刺的形状。
“等我们夏天去阿尔山的时候,我带你去看看那套房子,将来你要是想去那儿住一住,翻译你的书,也没问题。你一个人去的话,我把钥匙给你,你可以在那儿写东西,看看风景,买当地偷偷摸摸打猎的人打来的兔子烤着吃,我最喜欢吃烤兔子了。”
汉人的血统让我像长年用三十六度的温水浸泡着一只壮实、剥了皮的公兔子,这就是我个人悲剧的源泉,我的血永远不能像岩浆一样沸腾,也不能像烧开的油一样,能炸熟油条和酥肉。刚才说,我斗胆坐到她身边,也不过是我幻想中的情景,我依然钉子一样钉在她对面,一动不动。文明的世界当中,你要让一个人脱光了,得用你想画她写生的冠冕堂皇的名义,你面对她酒后的赤身裸体无计可施,只能灰溜溜地离去。
“你今天怎么能吃饭的点出来?”我问她。
“明后天,我大姐全家要去海南,二姐一家要去西班牙,她们整个春节期间都不回来。所以,我和她们谈了条件,让她们今天来替我值班一整天,我有二十四小时人身是自由的,直到明天中午。时间非常宝贵,我简直不知道该干嘛才对得起自己。”
“那我们去东四四条的吾肆喝一顿吧,那里威士忌品类丰富,我已经喝到第八种还是第九种了。”
“你请客吗?我今天已经超预算了。”
“当然,我还有点儿钱,我把钱存在弟弟那里,每个月他发工资一样发给我三千块。我还有花呗信用额三千块,加起来六千块,我一个月喝几次酒也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走路去了吾肆,从贡院东街到东四四条,只需要经过东总布胡同和朝阳门南小街,这段路在高德步行导航中显示的是二点九公里,需要走四十分钟。气温在我们吃一顿饭的工夫,又下降了两三度,我们行进的速度不紧不慢,街道上几乎没什么人了。我和索伦高娃穿过东总布胡同的时候,一只狗不紧不慢地跟着我,跟了整条胡同。东总布胡同不窄,两辆车会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条狗就蹊跷了,它是条黑狗。
我们从一个个黑漆漆的门洞走过,朝阳门南小街比东总布胡同要宽一倍,四辆车并着开没问题。但我已经在空气中闻到碎成碎块的卤汤,还有油炸食品的气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出来。每个院子的入口处总是停满了自行车,没有自行车也有堆放多年的杂物。
“有一年,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租住了这样一个院子一角的一个房间,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冬天的时候,暖气管冻裂了,我们狼狈不堪地睡在电热毯上,白天也披着被子,戴着帽子。”我告诉索伦高娃。
“哪一年?”
“2000年?差不多。就这样熬过了冬天,结果夏天一来,一场雨就把屋顶给下漏了,我们拿出所有的臉盆、塑料桶还有空储物箱来接雨水。但是墙也开始渗水了,地上的水排不出去,我们只好搬走了。”
“你北漂得真早。”
“是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的嗓子一到冬天还是干得疼,半夜都会咳醒,估计你没问题,内蒙古又冷又干。”
“我也不行。”
吾肆一个客人也没有,所幸开着门,微胖的酒保在吧台坐着,看到我来了,也没有露出熟人般的微笑,他是一个面无表情的人。这个酒吧在一个小院子里,主要的房间里放了三张小桌子,院子里天热的时候能坐。另外还有一间院子中央的房间,放着一套皮沙发,还可以看碟,那里拉上百叶窗叶片,就是独立空间,但我一次也没进去过。
我们坐在靠右边的小桌子上,背对着一副两个裸女,一个从背后抱住另外一个的画儿。也就是这个时间,雪从窗外悠哉地落下来了,每落下一朵雪花,都为天堂减轻负担,这恐怕是死者的回访。
“不要客气,我们一醉方休。”我把酒单从吧台自行取下来,递给索伦高娃,她说,“那我闭着眼睛,指到哪个就是哪个,怎么样?”
我求之不得,我希望她尽兴,盲点是个好方法。她果然闭上了眼睛,微笑着伸出一根指头,指着酒单中间,再重重地往下一划,停在酒单那面接近结束的地方。
“不管是什么,就要这个。”她笑出声来,她的笑声充满了浮力,似乎可以躺在那一串的笑声上仰望天空。
我们就着外边的雪景喝酒,喝酒的过程变得异常放松、漫长。
“我已经想好了,哪天我妈妈不在了,我要回阿尔山,承包一个山头,做一个小农场,我要在阿尔山度过余生。”索伦高娃说。她是个不易察觉喉结的女人,这么说话的时候,喉结的部位就跟机关枪的枪栓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去触碰一下。她的脖子像米开朗基罗那个五米高的大卫的脖子,脖子上覆盖着一层灰白的绒毛,这些绒毛也跟喉结一起起伏不定,我的眼神一直紧跟着这个起伏,又沮丧,又迷醉。
“你知道怎么运营管理一个小农场吗?”
“大概了解一些,我想养马、养牛、养鸡,光是这些就够忙的了。自己做果酒,还可以养蜜蜂,这些我都可以在网上卖,最好能雇几个帮工,帮我干活儿。”
“那等你农忙的时候,我可以过去帮忙。”想到能天天看到索伦高娃并且在一起吃饭干活儿,还是挺让人高兴的。
“你能干啥?”
“我泡过果酒,我会做荔枝酒、青梅酒、樱桃酒……”
“养过鸡吗?”
“小时候外婆养过好多鸡,知道怎么做鸡食,捡鸡蛋,打扫鸡窝。”
“这就足够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把未来农场的规划,一项项聊了一遍,聊得越来越起劲。她说如果我也去,她就有伴儿了,可以在山里盖个小房子,房子周边是鸡舍、羊圈和牛棚。还可以自己种蔬菜和果树,自己买台豆浆机磨豆浆做豆腐。吃不完的豆腐冬天放在室外做冻豆腐,晒干了就是干的冻豆腐,下火锅很好吃,自己做一些酸菜、奶皮子、奶酪。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到冬天就把屋子烧得暖暖和和,躲在家里看窗外下雪,清晨起来大雪封住了门,等爬出去。“雪地里,一定要在雪地里,你才能感到全身都在燃烧,那种从内到外的热,零下二十八度,三十八度,你想想。”
我拉住她的手,借着酒劲儿,使劲握紧,让她的手骨和肉,在我手掌的重压下扭在一起。她也没有挣脱,我们正在嘻嘻哈哈的状态当中,酒精给了我拉她的手绝妙的借口。然而,除此之外,我并不想进一步地做点儿什么。她是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女人,她就像一台拖拉机,“突突突突”从田野上开过来,看也不看我一眼,开了过去。
“干脆,我们今晚就去阿尔山?”我说。
“没问题啊。”
“真行吗?立刻、马上动身,而且可能再也不回来了,你今晚说的这些计划都很好,我们去阿尔山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再也不要在北京这个地方混吃等死了。”
“我觉得也是,北京太没意思了,在这里每天我都感觉自己在慢性自杀。”
按照凯鲁亚克的逻辑和行事风格,我们应该立刻回家拿上厚点的衣服,奔赴火车站。然而,我们哪儿都没去,我陪着喝得醉醺醺的她,在铁岭之家酒店开了个房,住了一晚上。当夜她又吐又哭,我一边帮她拍着背,一边忍不住恶心。我们分头洗了澡,躺在各自的小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一大早,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在微信上给我留了一句话:“我得回家照看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