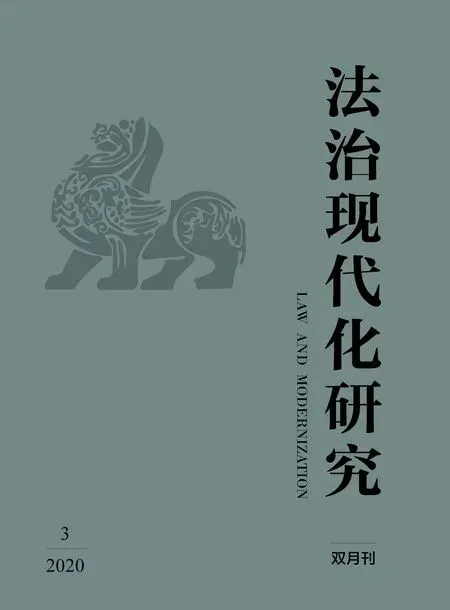“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法理之辨及其实践样态
——以裁判效力为中心的考察
树德
一、 引 言
在中国司法语境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乃耳熟能详的司法原则或者司法政策,但是,该原则或者政策在裁判文书特别是裁判说理中的具体化或者实践化仍衍生出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争论性问题。例如,本文要论及的“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两个范畴的内涵如何界定,二者究竟是何种关系,是种属关系、并列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宪法条款和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的效力究竟如何定位,是只能作为裁判理由还是亦可以作为裁判依据?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2009年11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以下简称《规定》)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第6条规定:“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2018年6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以下简称《意见》)第13条规定:“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下列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司法解释类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公理、情理、经验法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立法说明等立法材料;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与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规定》提出了“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的依据”范畴,《意见》提出了“论证裁判理由的论据”(1)英国学者拉兹关于“运作性依据”(即指那些抽象的、指示了行动类型的依据,这些一句内含了“应当/不应当”的规范性要求)和“辅助性依据”(即对特定的抽象行为依据进行具体化的依据,其任务是在运作性依据所指示的一些行动类型中,确定哪个具体的行动是妥当的)的区分及裁判地位的分析,值得借鉴。参见陈林林:《法律方法比较研究——以法律解释为基点的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范畴。“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这些司法文件所提出的上述范畴是有其法理依据还是存有随意使用之嫌疑,进而有无必要从“实践中的法理学”(3)所谓“实践中的法理学”是相对于“书本中的法理学”而言的,是指“法理学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是以立法、用法、执法、司法等载体存在的法理学”。参见张文显:《书本中的法理学与实践中的法理学》,载钱弘道主编:《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视域进行辨析,并为裁判文书中宪法条款和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即裁判理由抑或裁判依据的争论提供统一的话语基础,可以说就是本文所要论及的问题之所在。
二、 “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法理之辨
(一) 什么是裁判依据
2007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27条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4)1997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法发〔1997〕15号)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2009年11月4日施行的《规定》将“裁判依据”(第1条)和“裁判说理的依据”(第6条)并列;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6条规定:“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裁判依据,阐释裁判理由,反映控辩双方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则将“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并列。但是,上述司法解释或者非司法解释类规范性文件既未对裁判依据及其相关范畴(5)与“裁判依据”类似的表述还有“判决依据”“审判依据”“裁决依据”“规范依据”“论证依据”“理论依据”等,运用例证如,“判决依据是在后来案件中也要适用的原则,它宣示了对所有当事人有拘束力的法律”。参见前引①,陈林林书,第41页。“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在个案中的冲突,主要集中表现为个案审判依据即司法标准的选择”,以及“政策或者政治主张可以指导立法但不能取代立法,可以作为适用法律的参照以补充法律遗漏,但不能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参见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中国法的两仪相对关系》,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222、316页。“陪审团的裁决依据经常是一些不为法律所承认的实质性理由”,以及“司法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成了人民法院裁判案件时必须优先考虑和适用的规范依据”。参见前引①,陈林林书,第71、211页。“对法官裁判依据的证成不能只局限于法律原则,比如情理在必要时可以作为论证依据”。参见胡君:《原则裁判论——基于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理论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审判规范是针对具体案件的个别规范”“是法律解释的一种结果,是个案判决的理论依据”。参见陈金钊:《论审判规范》,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做进一步的细化与明确,也未对这些范畴的关系予以澄清。其实,无论是这些范畴的内涵界定,还是其关系辨析,均存有细究的必要。
就“裁判依据”而言,近期有学者认为,裁判依据是司法裁判推理论证最终作出决定的规范基础。根据最高法院发布的一系列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相关规定,裁判依据在判决书中应以“依照……之规定,判决如下”的格式出现,且所援用条文一般须源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6)参见余军等:《中国宪法司法适用之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有学者认为,“裁判依据”是有效裁判得以作出的规范基础,是“依法裁判”之“法”的载体,通常情况下,法官只需在裁判文书中指明裁判所依据之法律规范的出处,即相关的制定法名称及其条款号即可。(7)参见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年第1期。类似的观点如“法官解释法律的首要目的在于寻找裁判依据,也就是说,通过解释法律而确定解决纠纷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有学者认为,“裁判依据”首先指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规范和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及相应的真实性的证据,再延伸到包括指导性案例、学界的通说或主流学说、商业惯例等等。(8)此系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教授通过微信(2018年11月13日18:52)对我提出的“‘裁判依据’定义如何下?如何与‘裁判理由’区分?”的回复。他同时认为,裁判理由是运用这些依据进行论证说理,是对法官推论的结构层次和逻辑的表述。有学者认为,“裁判依据”既包括事实依据,也包括法律规则依据。(9)此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宋显忠教授通过微信(2018年11月13日21:34)对我提出的“‘裁判依据’定义如何下?如何与‘裁判理由’区分?”的回复。他同时认为,裁判理由则是裁判推理的根据,除了事实和法律依据之外,还包括法官意见(即法官对证据和规则的选择、解释与判断)和法官的推理过程。裁判理由要比裁判依据范围大且宽泛,可以说裁判理由是对裁判依据的补充。上述观点至少可以引发如下几点思考:一是裁判依据是仅限于规范依据,还是同时包括事实依据和规则依据;二是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基础”相对于裁判结论而言,是限于最终论证环节,还是同时包括整个论证过程;三是从论证层次而言,裁判依据是限于第一层次,还是同时延伸到第一层次以下的其他层次;四是裁判依据的外延宽于还是窄于裁判理由;五是裁判理由是仅指静态的推理理由,还是同时包括静态的推理理由和动态的推理过程。
综上,“裁判依据”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界定,实乃正常。此处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就审判/诉讼原则而言,“裁判依据”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
就裁判文书样式而言,“裁判依据”是限于裁判结论所依据的最终的规范基础,即目前裁判文书样式中“依照……(参照……),作出如下判决”中的省略号所指的内容。(10)2009年11月4日施行的《规定》第3条、第4条、第5条分别对刑事裁判文书、民事裁判文书、行政裁判文书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进行了明确规定。即第3条规定:“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适用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第4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第5条规定:“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民事、行政、刑事裁判的“最终的规范基础”是有所区别的。(11)法理学界哈特和德沃金的著名论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疑难案件的最终裁判依据问题,德沃金反对哈特的实证主义规则模式论,主张“规则—政策—原则模式论”,即在疑难案件审判中不仅依照规则,而且依照原则(即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和政策(即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改善),参见Ronald.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Seventeenth printing 1999),pp.22-23。201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2018年6月13日施行的《意见》第7条规定:“民事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法官应当首先寻找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判;如果没有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可以依据习惯、法律原则、立法目的等作出裁判,并合理运用法律方法对裁判依据进行充分论证和说理。”受“依法行政”的影响,行政裁判的“最终规范基础”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裁判的“最终规范基础”,《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若行政诉讼个案没有这些规范性文件作为“最终规范基础”时,法院完全可以参照前述民事裁判的做法。而刑事裁判则受“罪刑法定原则”和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约束,“最终的规范基础”只能是现行有效的刑法规范(就定罪而言,必须存在刑法分则性规范)。(12)河北省固安县某法庭1991年审理民事案件时,适用外国关于“藐视法庭罪”在程序上不同于一般刑事诉讼的法律原则,追究孟祥光等人刑事责任。参见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9年第3辑),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就裁判文书说理而言,“裁判依据”存有多层次的划分。裁判文书说理是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在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围绕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争议焦点、裁判论点和推理过程,论证裁判主文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活动。(13)2018年6月13日施行的《意见》第1条规定,“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间接地涉及了“裁判文书说理”的部分内涵。此定义具体概括为以下方面:(1) 裁判文书主要立足四个方面或者环节进行说理,即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行使自由裁量权;(2) 裁判文书重点聚焦两个中心进行说理,即争议焦点和裁判论点;(3) 裁判文书着重围绕两个方面内容进行说理,即推理过程和合法性、正当性的理由。“裁判文书说理”既不同于“裁判说理”“庭审说理”“判后说理”,也不同于“裁判论证”“裁判解释”,更不同于“裁判理由”和“裁判文书说理部分”。“裁判文书说理”具体包括“审查证据判断说理”“认定案件事实说理”“法律适用说理”“自由裁量权说理”四种类型或者四个方面内容。(14)此处“认定案件事实说理”与“法律适用说理”的划分仅具有相对的意义,理由是,正如中外学者所言,“认定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是不可切分的“往返”和“互动”过程。德国学者指出,法的适用是一个将事实与规范类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相互诠释,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得出一个具体化了的“犯罪构成”,通过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案件事实接近类型事实;比较的对象是“意义”(法的意义),在此意义中,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相互“适应”,法律规范才能被适用。参见[德]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德]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我国学者也认为,“案件事实的确认和法律规范的解释是交互进行的,即以事实为依据确定规范的意义,以规范为依据认定和筛选案件事实”“事实归类与寻找、解释法律规范这两个步骤不是各自独立且严格二分的两个行为,而是一个互相关联、不断比对的互动过程”“判断主体的目光不断流连往返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以规范为依据去筛选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去诠释或解释规范,以期能够使规范与事实相匹配”。参见任彦君:《刑事疑案适用法律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0、6、109页。从裁判文书说理论证的层次来说,裁判文书最终的结论证成是奠基于系列不同层次论证的结果(论据、论证、论点或结论)之上的,即初端的论证服务于中端的论证,最后共同服务于终端的论证。此种论证贯穿于“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三个环节,例如,当事人提出某个关键或者争议证据,法官经过审查判断后得出是否采纳的结论,其中证据规则属于“论据”的范畴,审查判断过程属于“论证”,关于证据是否采纳的结论属于“论点”;法官运用证据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中,采信的证据属于“论据”,遵循案件事实的规则与方法来认定事实的过程属于“论证”,关于事实是否认定的结论属于“论点”;法官针对已认定的事实来适用法律中,已认定的事实和找到的法律规范属于“论据”,不断拉近和“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过程属于“论证”,得出的裁判结果属于“论点”。既然裁判文书说理是一个(就简单案件而言)或者多个层次(就疑难案件而言)论证裁判主文的过程,那么,在裁判文书的得出奠基于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有时还有更多层次)的裁判论点之际,“裁判依据”也同样存在多个层次的划分,显然不能限定于“最终的规范基础”。
(二) 什么是裁判理由
裁判文书说理即裁判文书阐明“裁判理由”,(15)与“裁判理由”类似的表述还有“判决理由”和“法律理由”,例如,“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作出裁判时必须阐明判决理由”。参见前引①,陈林林书,第213页。法律格言“法律的理由是其灵魂所在”(Tatio legis est anima legis)、“法律理由消失,法律本身也不存在”(Cessante ratione legis cessat et ipsa lex);再如,有学者认为,规范性法律文件开头部分“为了……根据……制定本法”的表述部分就是“法律理由”,具体分为法律性理由(是指表明该规定的合法性的理由,即该规定在效力上的基础)和事实性理由(是指表明该规定的合理性的理由,即该规定在道德上的基础);“法律理由”是法律的弹性要素,有别于法律规范、法律注解等刚性要素。参见前引⑤,孙笑侠书,第16、18页。是经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据说在西欧,法官必须在判决书上写明理由的义务只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在17、18世纪,法国和日耳曼国家的法院都不写明判决理由,其理论根据是:(1) 他们是经君主授权从事审判的;(2) 直到18世纪中叶,日耳曼法律援引罗马法的传统,拒绝把判决理由告诉当事人。18世纪时法国人约斯(Jousse)甚至劝告法官不要说明理由,以免败诉当事人的挑剔导致讼争的重启,所以当时的判决只有主文(dictum)。理由空洞到了只有一句话——“考虑了应考虑的各点之后”。(16)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时代后,裁判文书说理乃是普遍性(17)当然,如今也存有这样的法律谑语,即“我愿给法官一个建议:在判决书里绝不要附理由。因为你的判决可能正确,但理由一定会弄错”。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页。这也多少表明裁判文书说理的不易。的司法样态,只是各国司法说理要求、说理方式等有所不同而已。
裁判文书说理是现代司法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司法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例如调解、仲裁、决斗、抓阄等而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法院/法官遵循诉讼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居中作出裁判。“正当程序要求在强制方式下形成的结论,必须说明理由——即说服决定者主观思想的东西以及说服其他人的那些东西”。(18)前引⑤,孙笑侠书,第144页。“司法‘定分止争’功能的发挥,离不开相应的司法机制,包括程序的感染力、判词的说理论证”。(19)前引⑤,孙笑侠书,第255页。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20)在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同样也需要说明理由,只是说理要求、说理内容、说理方式等方面会表现出差异,行政官僚色彩最浓、程序传统最淡薄的法国,1979年汲取行政程序法之精髓——说明理由的行政程序,制定了《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改善行政机关和公民关系法》,该法规定,对当事人不利和对一般原则作出例外规定的具体行政处理必须说明理由。而言,是一种判断权,但司法又并非一种纯粹的判断,按照伊芙林·菲特丽丝(Eveline Feteris)的观点,“任何提出法律命题的人都被期待提出论据去支持它”,(21)前引⑦,雷磊文。因而,司法裁判是一种举出理由支持某种主张或判断的活动,(22)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是一种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或法律论证(legal argumentation)的过程。可以说,作为“依(据)法裁判”(23)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2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庞德使用了“权威性资料体系”的表述。的司法裁判也是一种依(据)法裁判的论证活动。(24)参见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我国学者同样认为,作为追求个案正义的司法裁判大体上具备以下三大要素:一是要具备规范基础,即法官的论证绝不能只是纯粹的道德论证或者价值诉求,而必须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寻找规范基础(如一般法律原则)作为这种价值的支撑;二是要运用法学方法,即通过运用法律人共同体所普遍承认的法学方法,保证裁判结论与主流价值或道德保持一致;三是要承担论证负担,即法官在超越依法裁判的层次去追求个案正义时,负有义务来证立其所采取的价值判断(25)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法律适用不再是田园诗般的静态的逻辑推演,而必须加入多样化的社会价值的考量”。参见孔祥俊:《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项基本司法政策的法理分析》,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期。此种“加入多元化的社会价值的考量”无疑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政策“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本质要求,只是随之裁判论证负担会加重。具备规范基础,此种证立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展开,从而使价值判断符合宪法和社会主流价值且可以适用于个案。(26)参见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75页。
就当下立法而言,一些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和诉讼法专门对裁判说理进行了详略不一的规定。例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141条规定:“所有法院判决一律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附理由说明”。《比利时联邦宪法》第149条规定:“所有判决均须说明理由”。《荷兰王国宪法》第121条规定:“除议会法令规定的情形外,审判应公开进行,判决应说明其所依据的理由并向社会公布”。《西班牙王国宪法》第120条规定:“判决必须包含判决理由,并公开宣判”。《希腊宪法》第93条规定:“每一法院判决必须详细地和完整地说明理由并且必须公开宣判”。《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第93条规定:“司法机构的判决均应公开进行,所有判决必须理由充分,否则无效”。《苏里南共和国宪法》第136条规定:“所有判决都应陈述其所依据的理由,刑事案件的判决还应写明作出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13条规定:“1. 判决书应记载:……(4) 判决主文;(5) 事实;(6) 裁判理由。……3. 裁判理由项下,应简略地、扼要地记载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作出裁判所依据的论据”。(27)据我国学者介绍,德国的判决书分为前文、主文、事实说明、判决理由、法官的签名,其中,“事实说明”要简单地叙述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事实、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以及法院调查到的证据提要,“判决理由”包括法院评论证据的价值,指出判决所依据的法律理由。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6页。《日本民事诉讼法》(28)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总第6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页。第253条规定:“判决书应记载下列事项:主文、事实、理由、口头辩论的终结日期、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法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裁判,应当附具理由”。(29)《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1. 判决书应记载下列事项:……(2) 主文;(3) 请求的主旨及上诉的主旨;(4) 理由;…… 2. 判决书的理由应记载对当事人的主张以及其他攻击、防御方法作出的判断,以致可以将主文认定为正当的程度……”。《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裁判应明示理由。但是,不允许上诉的决定或者命令除外”;第323条规定:“1. 宣告刑罚的,应在判决理由记载构成犯罪的事实、证据的要旨及法律的适用。”《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30)《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第297条规定:“1. 刑事判决应该是合法的、根据充分的和公正的。2. 刑事判决的做出如果依照本法典的要求并正确适用刑事法律,刑事判决被认为是合法的、根据充分的和公正的”。与之对应的是,修改之前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01条规定:“法院的刑事判决必须是合法的和有根据的。法院必须将刑事判决建立在审判庭已经审查过的证据的基础之上。法院的刑事判决必须是说明理由的”。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苏方遒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条规定:“1. ……刑事判决用法庭审理时使用的语言制作,由开始部分、叙事和理由部分及结论部分组成”;第305条规定:“1. 无罪判决书的叙事和理由部分应该叙述以下内容:(1) 所提出指控的实质;(2) 法庭所确认的刑事案件情节;(3) 宣告受审人无罪的根据和证明这些根据的证据;(4) 法院推翻指控方所提交的证据的理由;(5)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的理由……”;第307条规定:“有罪判决书的叙事和理由部分应该包括:(1) 描述法庭认为得到证明的犯罪行为,并指出实施犯罪的地点、时间和方式,罪过的形式,犯罪的动机、目的和后果;(2) 法庭据以对受审人做出结论的证据,以及法庭推翻其他证据的理由;(3) 指出减轻和加重刑罚的情节,而如果认为某一部分的指控证据不足或者确认定罪不正确,则还要说明变更指控的根据和理由;(4) 解决所有与判处刑罚、免除刑罚或免于服刑、适用其他感化措施有关的问题的理由;(5) 说明解决本法典第299条所列其他问题的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1. 判决,应制作判决书,记载下列各款事项:……(4) 主文;(5) 事实;(6) 理由……3. 理由项下,应记载关于攻击或防御方法之意见及法律之意见。4. 一造辩论判决及基于当事人就事实之全部自认所为之判决,其事实及理由得简略记载之”;“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判决,应叙述理由,得为抗告或驳回声明之裁定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一) 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 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三) 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四) 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第154条规定:“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
结合上述各国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裁判理由可作不同的分类。一是按照裁判理由的说服受众来分,即德国法学家埃塞尔(Esser)的观点,判决的理由这一术语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判决所根据的理由(begründung),另一种是指判决的心理动机(motivation)。比利时学者班来门认为,两者是不能等同的,前者是客观的,指怎样说服其他人,后者是主观的,指什么东西说服了法官。(31)参见前引,沈达明书,第245页。二是按照裁判理由的属性来分,裁判理由包括裁判事实性理由和裁判规范性理由。“司法裁判的结论建立在恰当的法律规范和被正确陈述的案件事实(亦即证据事实)的基础之上”,(32)前引⑦,雷磊文。因此,裁判事实性理由就是裁判依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裁判规范性理由既包括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包括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例如类推适用所依据的法律理由或立法理由、学界围绕相关条款的适用所提出的法教义学观点,尤其是通说),等等。三是按照裁判理由在裁判论证中的位阶层次来分,(33)奥地利学者认为,“裁判理由(ratio decidendi)”是“支撑(促使产生)裁判的论证的总结”。参见[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包括最终结论的裁判理由和论证最终裁判理由的理由。以裁判规范性理由为例,从法律规范的证立而言,具体可分为“权威理由”和“实质理由”两类,前者是指因其他条件而非其内容来支持某个法律命题的理由(例如,法律渊源是最重要的权威理由),目的是为法律命题及依据法律命题得出的裁判结论提供权威性和合法性,后者是一种通过其内容来支持某个法律命题的理由,目的是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和裁判结论的正当性。(34)参见前引⑦,雷磊文。显然,此处的“权威理由”有的是“最终结论的裁判规范性理由”(裁判文书样式中“依照……,作出如下判决”的省略号表述的内容,亦即作为“最终的裁判规范性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有的是“论证最终裁判理由的理由”(亦即裁判说理部分所援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实质理由”往往就是“论证最终裁判理由的理由”。此种二分法,不仅与法律论证的内部证成(按照司法三段论,经由大前提、小前提推理出结论)和外部证成(证明大、小前提的成立)相契合,更是与当下司法哲学从严格规则主义向司法能动主义(或者自由裁量主义)、(35)参见前引⑤,孙笑侠书,第212页以下。从形式公正向实质公正、(36)美国学者昂格尔分析当代“后自由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和“合作国家”的发展对法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趋势:一是在立法、行政、审判中,迅速地扩张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条款;二是从形式主义向目的性或政策导向的法律推理的转变,从关注形式公正向关心程序公正或实质公正转变;三是私法与公法界限的消除,出现了社会法。参见[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从形式理性向实质理性转变相呼应。(37)其实,这也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合理’与‘合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合法’必须以‘合理’为前提条件,‘合理’则是‘合法’的内在根据;‘合理’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而‘合法’则体现了法律对合理性事物的保障。换言之,只有合理的法律(权利已变成法律),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参见公丕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三) 二者的关系框定
综上,“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的关系,应在同一语境中来加以框定,否则会得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结论。2009年7月13日《规定》第1条和第6条分别使用了“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依据”(38)此种划分可以从德国学者将法律渊源划分为法律认知的渊源和法律创设的渊源受到启发。参见[德]马蒂亚斯·耶施泰特:《法理论有什么用?》,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的表述,只有从裁判结论的“最终的规范基础”(最终的裁判规范性理由)及“最终的裁判理由的理由”的区分角度而言有一定的合理性,若不作此种限定而广义地理解,就会显示出不妥之处,理由是,无论是“裁判依据”还是“裁判说理的依据”相对于“裁判结论”而言应该都是“裁判理由”(“裁判结论的论据”或者“裁判结论的说理依据”)。(39)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参见前引②,博登海默书,第488-489页。“裁判依据”与“裁判说理的依据”两个范畴显然不属于并列关系。
此外,就裁判文书中“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的关系框定而言,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区分事实性依据/理由和规范性依据/理由;二是要注意不同论证层次(40)例如,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的“一阶—二阶证成”模型(即一阶证成是指法官如何依据某条法律来证明判决结论的正确性,这往往是一个形式推理的过程;二阶证成是指在判决依据的选择上,法官如何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参见前引①,陈林林书,第207页。的裁判依据/理由,具体分为最终的裁判理由和强化或者补强最终裁判理由的理由。(41)有学者“将作为判决结果的依据称为判决理由中的第一性依据,将作为援引、选择这些依据的依据称为判决理由的第二性依据”。参见前引①,陈林林书,第9、69页。据此,裁判文书样式中“依照……作出如下判决”(42)此处“依照……”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的“依照法律”。按照宪法学者的观点,此处“依照法律”是“狭义的,具体是指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它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依法取得,并依法获得保障;二是要对独立审判权作出限制或干涉,也应有法律的规定”。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也就是说,此处“依照法律”指的是法院审判权的来源为法律授权,而不是法院依据法律、法规作出个案裁判。参见前引⑥,余军等书,第119页。中省略号表述的内容仅限于“最终的规范性理由”,即得出裁判结论的最终的规范基础。
三、 宪法条款的效力定位:裁判理由抑或裁判依据
就宪法审查制度而言,域外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以普通法院为审查机关的美国式分散审查模式;二是以宪法法院为审查机关的欧陆式集中审查模式。(43)此处拟不对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宪法文本在裁判个案的具体运用模式、援引方式、效力定位等进行法理层面的比较研究,仅立足我国现行宪法体制和宪法惯例下的人民法院在司法个案中实施宪法进行分析。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别提出的改革部署即“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但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当下宪法实施仍是“政治实施主导,法律实施并存”的“双轨制”。就宪法在个案裁判中的具体适用而言,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两个维度考察。
(一) 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
最高人民法院总体上坚持个案裁判不得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立场,这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现在几个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之中,即: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示作出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
1986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指出,“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凡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可在办案时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贯彻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此《批复》回避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包括宪法以及宪法能否被引用作为裁判依据的问题。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规定,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工伤概不负责”的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此《批复》意味着法院可以引用宪法作为说理依据。
2009年11月4日施行的《规定》第1条,“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同样未对作为裁判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包括宪法作出明确界定。
2016年8月1日施行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裁判依据”部分则明确提出,“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二) 地方各级法院的实践
地方各级法院在部分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1.将宪法作为裁判理由援引
这种情形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非解释性适用”,即在裁判理由中援引宪法,但未对相关的宪法规定进行任何解释或阐释或者无法识别出其所具体援引的宪法条款,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方式:其一,直接列明所援引的宪法条款。例如,“潘某某、李某某非法拘禁案”,其裁判文书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之规定后表述,“具体到本案,虽然被告人闫某某是为了索要其合法债务而对被害人采取的非法拘禁行为,不同于一般纯粹的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为目的的非法拘禁,但即使被害人作为担保人未履行担保还款义务,被告人也不应采取上述犯罪行为,而应当用合法的手段和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其二,单单出现“宪法”一词,且能合理推知其所援引的宪法条款。例如,“博兴县锦秋街道菜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盖玉璇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案”的裁判文书表述,“不应对村集体成员给予差别待遇,故盖玉璇基于其村集体成员资格请求村委会给予其无差别的福利待遇的请求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和宪法的人权原则,本院予以支持”。“蔡攀峰诉常明军等五人名誉权纠纷案”的裁判文书表述,“被告常明军、宋海军、吕改红、常建林、李天锁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由,通过向县纪委、县检察院递交控告书的形式反映问题,其行为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属于合法范畴”;“范有秀诉樊城区人民政府拆迁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案”的裁判文书表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上诉人范有秀位于襄阳市樊城区兴武街6组前街276—10号的房屋依法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其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其三,单单出现“宪法”一词,且无法识别出其所具体援引的宪法条款。例如,“邵廷贤与苏文科等财产损害赔偿案”的裁判文书表述,“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我国宪法、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他人人身、身体或其他权益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对损害后果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解释性适用”,即在裁判理由中援引宪法规定,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者阐释(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其一,裁判文书作了简略的文义解释。例如“顾建兵、吴陈新等与南通市商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的裁判文书表述,“本院认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公民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等权利。举报权利是对检举权、控告权的进一步发展,是公民依法向有关专门机关检举揭发违纪、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权利。检举、举报人的权利包括选择受理机关的权利、决定是否实名举报的权利、获得保护的权利、查询结果和申请复议的权利,等等。因此,检举、举报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监督权利……并非一种实体法意义上的权利。”其二,裁判文书作了适当的体系解释。例如,“曹某某与颜某某赡养纠纷案”的裁判文书表述,“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中国是礼仪之邦,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时候,赡养老人不仅是道德规范的要求,更是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我国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多个法律规定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且法律规定的完整的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供养,还包括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子女应当妥善安排好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更不得让老年人流离失所。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给予父母扶持、照顾。赡养父母是一项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其三,裁判文书作了详细的目的解释。例如,“吉林科龙优质种(肉)牛繁育有限公司与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杨家岗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的裁判文书表述,“法院认为:一、我国征地制度分为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2004年,全国人大对宪法相关内容修改前,国家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无论是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还是短期使用,一直都统称为征用。2004年3月,全国人大对宪法作了修改,将宪法原第10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同年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兆国副委员长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第10条修改说明为,‘这样修改,主要的考虑是:征收和征用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宪法第10条第3款关于土地征用的规定,以及根据这一规定的土地管理法,没有区分上述两种情形,统称‘征用’。从实际内容看,土地管理法既规定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收;又规定了临时用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用。为了理顺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征收、征用而发生的不同的财产关系,区分征收和征用两种不同情形是必要的’。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本案发生在该法实施之前)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该法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二、对‘公共利益需要’之界定。土地征收和征用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但目前法律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定义性规定。2011年1月21日公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对哪些情形属于‘公共利益需要’作了列举式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一) 国防和外交需要;(二)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 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害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上述规定所适用的对象只是针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的行政行为,但该立法精神可以在处理农村土地征收和征用纠纷时予以参考”。
2.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援引
“援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对当事人所形成之客观拘束力自然强于在裁判说理部分中援引宪法的效力”。从实践个案来看,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形具体包括:(1) 单独援引宪法条款作为裁判依据,例如,“黄福高诉李兵财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单独以宪法第10条为依据认定系争合同无效。(2) 同时援引宪法条款和非法律规范(如党的政策)作为裁判依据,例如,“怀安县左卫镇冀家庄村民委员会与李守功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法院援引宪法第10条,同时“参照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作出驳回原告解除承包户同的诉讼请求的判决。(3) 同时援引宪法条款和其他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例如“陈结华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荷村村资产管理办公室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法院援引宪法第13条和民法通则相关条款,认定任何人不得违法侵犯原告在股份社的股份分红和量化分红的合法财产,作出相应判决。
3.将宪法作为诉求与回应的载体
即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主动援引宪法作为诉讼主张的理由,法院在裁判说理部分对其作出相应的回应。从实践个案来看,既有当事人一方援引的,也有当事人双方援引的,还有当事人三方(包括诉讼第三人)援引的;从法院对此的回应来看,具体分为“予以回应”和“未予回应”两种情形。其中,“未予回应”暂不讨论,“予以回应”的情形又具体包括几种形式。其一,“直接回应型”,即直接围绕当事人之涉宪诉求作出符合逻辑的论证和结论。例如“魏有德、魏九龙与魏锦华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锦华辩称,“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本案诉争土地属于农村土地,应当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转让”,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因此,魏有德、魏九龙认为本案诉争土地是先辈遗留下来的宅基地、滩涂及沙洲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调整对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间接回应型”,即通过回避或者径行确认受质疑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抑或简单、粗略地认定其不属于案件受诉范围或审理范围,从而模糊地回应当事人。例如,“孙文麟、胡明亮与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不履行婚姻登记法定职责案”,二审法院认为,“根据起诉状,本案孙文麟、胡明亮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结婚登记。根据婚姻法第2条、第5条、第8条等相关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必须是男女双方。两上诉人均为男性,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办理结婚登记的条件,其要求判令被上诉人为其办理结婚登记,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提出刑法中聚众淫乱罪的处罚对象包括同性,婚姻登记也应该涵盖同性,婚姻法中的‘男女平等’应当解释为男女可以平等地和男方结婚,也可以平等地和女方结婚等,其理解明显超出婚姻法相关规定中‘男女’的文义范围,属于曲解法律,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根据宪法等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婚姻登记排除同性是歧视,对同性申请婚姻登记应予办理,该主张系否认法律的效力,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正如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认为,司法个案裁判文书援引宪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法院对宪法的适用、援引在形式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非解释性”“简约化”现象;二是宪法文本中基本国策条款、基本权利条款、社会权条款、宪法义务条款在解释适用过程中未能区别对待;三是基本权利条款“私法化”适用,即法官大多并不区分宪法基本权利(公法上的权利)和民法权利(私法上的权利)所能适用的法律关系与拘束对象的不同;四是法院在民事案件中以宪法为依据或者以宪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为共同依据作出“违宪”判断,导致“违宪”主体的泛化。(44)参见前引⑥,余军等书,第206页。基于此种“两极”现象(即最高人民法院的“谨慎立场”和地方法院的“积极引用”)的存在,再加上具体个案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条款作为裁判理由有无必要(是否存在戴宪法“高帽”和逃逸高位阶条款的嫌疑)、援引宪法特定条款作为裁判依据(往往伴有低位阶的法律规范)是否合适的争论,(45)参见前引⑥,余军等书,第127页。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确有必要立足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加强合宪性审查”的改革战略部署,积极稳妥地承担起司法环节“保障宪法实施”的使命,(4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及时出台规范性文件,一方面从正面统一规范和指引各级法院援引宪法作为裁判说理依据(即论证裁判结论最终理由的理由),包括援引宪法的表述方式、解释宪法的方法,等等,另一方面从反面规定不得无必要地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即裁判结论的最终规范基础)。
四、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裁判理由抑或裁判依据
2015年5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2016年8月1日施行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裁判依据”部分仍然强调,“指导性案例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47)此种定位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参照的含义首先意味着其(即指导性案例——引者注)不是法律渊源,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参照的含义还表现在,法官可以在说理部分直接援引指导性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导性案例可以成为说理的理由”。参见前引⑦,王利明书,第753页。这两个司法文件同样提出了“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的范畴,并对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的效力与功能作了官方表达。(48)以下拟不对英美法系判例法和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判例制度进行法理层面的比较研究,仅立足于当下我国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运行展开分析。
近期,实务界代表人士对此有了认识上的变化,即曾经认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可以作为裁判说理依据引用,不宜作为裁判依据引用,理由是,如果说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引用,容易产生把指导性案例当作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判例的误解;现在则认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既可以作为说理的依据引用,也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引用,理由是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的,其裁判要点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总结出来的审判经验和裁判规则,可以视为与司法解释具有相似的效力。同时主张,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像司法解释一样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引用的顺序可以放在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之后。比如,某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其裁判文书在引用刑法和司法解释相关条文后,认为有必要参照指导性案例3的,就可以这样表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3号指导性案例,判决如下:……”。(49)参见胡云腾:《关于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1日。
在笔者看来,上述认识的变化仍值得从“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的关系框定角度加以申论。(50)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先例之所以值得适用,主要是因为先例的说理论证能力而非形式拘束力”。参见前引①,陈林林书,第180页。因此,此种延伸思考只有立足于我国当下立法权与审判权的宪法定位及各种国家权力具体运行的现实语境,方有其意义。一方面,“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的区分必须严格限定在同一语境中,不宜笼统地、大而化之地宣称指导性案例只可作为裁判说理依据(裁判理由),不宜作为裁判依据。理由是,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在此语境中,“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均是裁判结论的“裁判理由”,而在彼语境中,“裁判依据”仅是指裁判结论的“最终的规范性理由”,而“裁判理由”同时包括裁判结论的最终的理由以及“最终理由”的证成理由。
另一方面,要“类型化”地看待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功能。从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来看,“裁判要点”具体包括三种:其一,“裁判规则型”。例如,“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的“裁判要点”,即“‘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是指违反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擅自购买或者出售毒害性物质的行为,并不需要兼有买进和卖出的行为”;“杨延虎等贪污案”的“裁判要点”,即“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等等。其二,“裁判理念型”。例如,“李飞故意杀人案”的“裁判要点”,“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且系累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亲属主动协助公安机关将其抓捕归案,并积极赔偿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节,从尽量化解社会矛盾角度考虑,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王志才故意杀人案”的“裁判要点”,即“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董某某、宋某某抢劫案”的“裁判要点”,即“对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根据其犯罪的具体情况以及禁止事项与所犯罪行的关联程度,对其适用‘禁止令’。对于未成年人因上网诱发犯罪的,可以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进入网吧等特定场所”,等等。其三,“裁判方法型”。例如,“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裁判要点”,即“……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等等。
正如胡云腾大法官所指出的,“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本质上属于对法律法规条文或者法律规范的一种解释(即“裁判规则型”——引者注),通常是对法律法规进行一定程度的细化、明确或补充,而不是修改或新立,故一般不能独立作为司法裁判的规则或者准据”,(51)前引,胡云腾文。即使属于“裁判规则型”的“裁判要点”,“一般”不能作为裁判结论的“最终的规范性理由”,但若其“例外”地属于“造法性解释”或者“法律漏洞填补”(民事、行政审判领域),(52)就刑事审判领域而言,在1997年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之前的“类推时代”,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两宗以制造、贩卖有毒酒的危险方法致人伤亡的案例,克服了1979年刑法中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制造、贩卖有毒食品致人伤亡行为无明文规定的不利因素,用判例的形式创制了“以制造、贩卖有毒酒的危险方法致人伤亡罪”的新罪名与量刑标准。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3期。则完全可以作为裁判结论的“最终的规范性理由”(当然,大多情形要依附于具体的蕴含法律后果的法渊源或法规范)。例如,“贾国宇诉春海餐厅人身伤害纠纷案”,(53)案情及判决情况:1995年3月8日19时许,原告贾国宇和家人及邻居在被告春海餐厅聚餐,在就餐期间,春海餐厅使用的石油气气罐发生爆炸,致贾国宇面部、双手烧伤。贾国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气罐的生产者气雾剂公司和厨房用具厂以及春海餐厅承担赔偿责任。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事故发生时,贾国宇尚未成年,但身心发育正常。烧伤造成的片状疤痕对其容貌产生了明显影响,并使之劳动能力部分受限,严重地妨碍了她的学习、生活和健康。除肉体痛苦外,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终身悔憾与痛苦,甚至可能导致其心理情感、思想行为的变异,其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2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海淀区人民法院采用填补法律漏洞(54)法律漏洞的填补又称法律补充或法律续造,是指在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由法官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针对特定的待决案件,寻找妥当的法律规则,并据此进行相关的案件裁判。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基于习惯法的填补漏洞、基于比较法的填补漏洞、基于法律原则的填补漏洞。参见前引⑦,王利明书,第563-566页。的方法,弥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健康权)并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形成了“侵害健康权的,可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规则,此先例就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在立法没有作出补充完善之际)共同成为判决此类案件的裁判依据。(55)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通过判例,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确认一些新的民事权利,以补充民法典等之漏洞,例如,德国的“一般人格权”就是通过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发展起来的。参见徐国建:《德国民法总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再如“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56)参见《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3期。法院判决理由适用正当程序原则来弥合法律漏洞,为具体行政管理领域树立起法律的界碑,(57)参见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即“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号“深圳市斯瑞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坑梓自来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泰蓝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发明专利纠纷案”,采用类推和目的性扩张方法(58)参见孙光宁:《漏洞补充的实践运作及其限度——以指导性案例20号为分析对象》,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另见孙光宁:《中国司法的经验与智慧——指导性案例中法律方法的运用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314页。弥补了专利法存有的专利临时保护期内的实施行为及其后续行为的法律定性方面的“开放的法律漏洞”,(59)所谓“开放的法律漏洞”是相对于“隐藏的法律漏洞”而言的,前者是指“针对某一特定案件事实,依据法律的目的应当运用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调整,而此时法律规范未作规定的情形”,后者是指“针对某一特定事件,虽然已经有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和规制,但此种规制对评价和裁判该事件并不合适的情形”。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4-255页。明确主张“专利权人无权禁止他人对专利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专利侵权产品的后续使用、许诺销售、销售”。(6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11月23日。
五、 结 论
综上,无论是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及非司法解释类规范性文件,还是学界针对宪法条款和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的实践效力的讨论,均存在对“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的混淆理解和泛化使用,进而导致实务界、理论界以及实务界与理论界之间存有“无谓争论”或“片面正确”。可以说,此种因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或者语境各自提出“新论断”“新观点”“新命题”,随之基于相互之间的非同一语境或者视角进行“商榷”或者“争鸣”,造成一番学术热闹景象,绝非此一例,例如,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61)参见刘树德:《司法改革热问题与冷思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以下。法理学界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62)参见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和“法治反对解释”与“法治不反对解释”之争,(63)参见范进学:《“法治反对解释”吗?——与陈金钊教授商榷》,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陈金钊:《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诠释——答范进学教授的质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诉讼法学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64)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导论。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争,(65)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等等,均多少存在非同一语境的争论。显然,此实乃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来避免的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