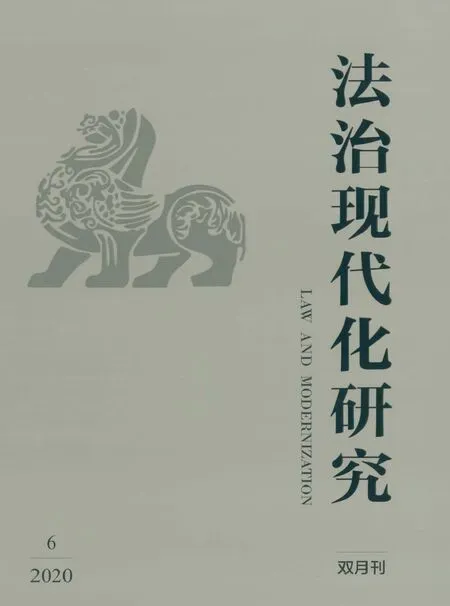晚近20年英美法理学发展评析
——以夏皮罗等人的实践差异命题、法律规划理论为中心
何勤华 吴 怡
一、 引 言
美国法律实证主义学者斯科特·夏皮罗(Scott J. Shapiro)在其著作《合法性》(Legality)(1)本文所参考《合法性》的英文版本为:Scott J. Shapiro, Legal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版本为:[美]斯科特·夏皮罗:《合法性》,郑玉双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在中文译本不存在理解困难的情况下以参阅中文版为主,而关键字词的书写与理解以夏皮罗原书为准。中所提出的“法律规划理论”处于目前英美法理学研究中较为前沿的位置。夏皮罗在《合法性》一书中所传达的“法律是一个自我证明的强制性规划组织”的“法律规划理论”(Legal Planning Theory),与其包含的“法律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弥补合法性环境中道德缺陷”的“道德目标命题”(Moral Aim Thesis),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尽管夏皮罗一直以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忠实维护者自居,但亚利桑那大学的康妮·罗萨蒂教授(Connie S. Rosati)则认为,夏皮罗以其道德目标命题一跃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家中的异类。(2)罗萨蒂教授尖锐地指出,夏皮罗同其他法律实证主义学者之间的距离,要比他自身所设想的远得多。参见Connie S. Rosati, “Normativity and the Planning Theory of Law”, Jurisprudence, 7, Issue 2(2016), pp. 307-324.德国法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教授(Robert Alexy)也指出,夏皮罗的法律规划理论在关键部分上是非实证主义的,在其他部分中则是实证主义的,并总体上也正在向一种非实证主义过渡,故他称夏皮罗是一位“超包容非实证主义者”(Super-inclusive non-positivism)。(3)阿列克西教授长期同夏皮罗所属(至少在《合法性》出版前所属)的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阵营有着多角度的论战,尤其是同实证主义理论家中最为“激进”的约瑟夫·拉兹教授(Joseph Raz),是故阿列克西对夏皮罗的评价极具参考价值。参见Robert Alexy, “Scott J. Shapiro between Positivism and Non-Positivism”, Jurisprudence, 7, Issue 2(2016), pp. 299-306.而我国学者沈宏彬博士在《成规、规划与法律的规范性》一文中,则从规划理论对于哈特的规则理论之不足的修补上,称其为最好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又从其对于道德目标的依赖和强调中,指出该理论正在趋向演变成一种自然法,故它又是最后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4)参见沈宏彬:《成规、规划与法律的规范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沈宏彬博士在《社会事实、价值与法律的规范性》中提到,唯德沃金可称为哈特的“传承人”,这一极具创见的观点也可以作为分析夏皮罗法学理论的一个侧面。通过以上学者的评价可以发现,夏皮罗的法律规划理论存在着某种由内部不调和而产生的“界定困难”,这位言必称“社会事实”并以构建一种最具说服力的实证理论为目标的法理学者似乎陷入了“身在曹营,而心在汉”的窘境之中。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大多没有重点关注的是:如果对夏皮罗的法理学理论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会发现其法律规划理论中的道德目标命题与他之前所提出的“实践差异命题”(Practical Difference Thesis)存在极大的不融洽之处。这集中体现为前者主张以弥补道德缺陷作为法律活动的重要目标,而后者则断然拒绝在法律论证中容纳任何形式的道德判断。是故,道德内容究竟于法律运作中扮演何种地位,在夏皮罗前后两个命题中存在极大的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按照英美法理学界的一般评价,即如果说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二战后经历了由法律实证主义向自然法理论转换的话,那么,在夏皮罗的身上是否也发生了这样的“大马士革之行”呢?(5)值得说明的是,拉德布鲁赫的转换只是英美法理学界的“一面之词”,德国学界一般认为拉德布鲁赫自始至终即秉承新康德学派,而未有理论转向。此处仅在拉德布鲁赫与夏皮罗之中构建一种可能并不对应的联系。从实践差异命题到道德目标命题,其中的法律理论发展是逻辑上的继续,还是存在着矛盾?如果确实存在矛盾,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发生?又能从这种矛盾中得出对于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演进的什么认识呢?
本文认为,如果想要对夏皮罗的法律理论进行准确地把握,首先,需要从目的论的角度上理解他旨在克服先前法律实证主义诸理论的缺陷,尤其是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其次,还需要建立夏皮罗论证逻辑同实证主义基本前提的动态联系,由此可以一举两得地明确其讨论起点与理论性质的界定。以此为路径,本文的论证结构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哈特承认规则的缺陷出发,回顾夏皮罗实践差异命题的提出及其所遭受的批判。第二部分从这些批判出发,分析夏皮罗是如何从中产生与提出更宏大、完善与具备证明力的法律规划理论及道德目标命题的。第三部分以实践差异命题与道德目标命题的关联性与逻辑差异性为对比,在法律实证主义的语境中,分析该法学理论是否处于,又是如何处于困境之中的。
经由这些分析,本文试图证明:夏皮罗的实践差异命题可以部分为法律规划理论吸收,成为其证明过程中的一环,但是该命题原本指向的法律理论同道德目标命题所构建的理论并不能兼容,两者存在深层次的本体论角度上的不融洽。这种前后不一致情况的发生,是法律实证主义自身前提与其所要回答之问题间的张力导致的,法律实证主义自始就处在一种“困境”中。
二、 实践差异命题:论证与批判
关于“法律是什么?”的争论贯穿了整个法律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诸多命题相继提出又被驳倒,在去芜存精中,争论的主题日渐明确。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在他的名著《法律的概念》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法律义务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有怎样的区别和关联?第二,分享着同一套权利和义务词汇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有什么不同与关联?第三,什么是规则?一项规则存在意指什么?法院真的在适用法律吗?或仅仅是在假装这样做?(6)实证主义法学的旨趣在于构建法律在事实性和规范性之间的桥梁。哈特的问题建立在对其前辈约翰·奥斯丁提出的“法律命令说”与汉斯·凯尔森的“规范法学”的反思之上,哈特认为他们各自只执了实证主义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一端。拘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奥斯丁与凯尔森的理论进行深入介绍与论证回顾,他们的理论,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相关论述,参见陈景辉:《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哈特的问题,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哈特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对“法律是什么?”这一争论进行了多角度呈现:从本体论的角度上看,法律实质上是什么?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什么?从实践理论的角度上看,法律又是如何被运用于裁判之中的?
(一) “承认规则”理论的不足
实证主义法学的旨趣在于构建法律在事实性和规范性之间的桥梁。哈特在区分规则指引与习惯性行为的基础上否定了奥斯丁的“服从习惯”理论,赋予了法律以规则实践的属性。同时又将作为法律效力的终极标准的承认规则定义为:“法院、政府官员和一般人民,在援引其所含判准以鉴别法律时,所为之复杂但通常是一致的实践活动本身。”(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哈特通过将承认规则产生于聚合实践,而聚合实践又是由某种规则指引的方式,将规则传导至法律本身,(8)规则的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属性使承认规则具备规则的属性,继而根据承认规则赋予法律以效力。但是法律并不必然具有规则的属性。参见前引⑥,陈景辉书,第241页。并就此阐发出法律的功能在于指引行为的论点。在同德沃金的论战中,“原则理论”的猛烈炮火使得哈特的理论模型出现了多道裂缝,(9)哈特与德沃金的论战是20世纪英美法理学最重要的论战。德沃金借由哈特的承认规则不能顺利推出法律原则这一观点,对哈特的规则理论展开了全面批判,使得规则理论全面退却至惯习(convention)领域,实证主义法学内部发生分裂。德沃金之后又提出了“整体法”理论。关于论战的具体经过,参见熊毅军:《论现代西方法理学的三大论战:基于古今之争立场的审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德沃金对哈特的批判以及“整体法”理论,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其中最为重要的争论点在于:承认规则是否可以安置道德论证?实证主义内部对于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发生了分裂,按照瓦卢乔(W. J. Waluchow)的划分,对于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的派别被称为“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Exclusive Legal Positivism),他们认为承认规则只包括形式化的承认规则;持肯定态度的则被称作“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m),他们认为承认规则不单单包括形式化的承认规则,还至少包括了道德实质化的承认规则。(10)一般而言,形式化承认规则指制定法与习惯法等法律渊源,实质化承认规则包含直接将道德原则赋予法律效力的内容。参见W. J. Waluchow, 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m, Oxford: Clarendon, 1994.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主张在承认规则许可的前提下,某些法律可以在其内容合乎道德判断时获得效力,这就是所谓“道德安置命题”(Moral Incorporation Thesis)。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则认为如此行事会损害分离命题的和谐性,并最终影响到实证观念的有效性。为了反驳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的主张,夏皮罗回到“承认规则”本身,指出哈特的理论框架在承认规则属性的认定上存在重大的缺陷,正是这一缺陷给了德沃金与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者们将道德论证嵌入法律论证的空隙。
(二) “实践差异命题”的提出
对于哈特的分析路径,夏皮罗指出,包括聚合实践在内的社会活动并不一定仅仅受到规则的指引,还可能受到一般性规范判断(general normative judgement)的引导。为了更好地区分两者,夏皮罗使用这样一个例子进行说明:吉姆非常厌恶喝酒,而约翰嗜酒如命;如果有一天颁布一条禁酒令,那么从表面上看他们二人都会选择不再饮酒,但实际上吉姆本就不饮酒,约翰则不得不放弃饮酒。故此,夏皮罗指出,吉姆所作的选择是受一般性规范判断所引导的,即“我不喜欢饮酒”这样一个判断,是故禁酒令的规则实际上并没有对吉姆产生作用;而约翰则确实受到了规则的指引而放弃了饮酒。夏皮罗借此说明,只有规则对行为结果产生了实际影响,才可以说规则发挥了指引作用,(11)参见Scott J. Shapiro, “The Difference That Rules Make”, in Analyzing Law: New Assays in Legal Theory, Brian Bix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33.换言之,规则指引功能的存在以实践差异的存在为必要。
为了更透彻地分析哈特理论框架下的承认规则的缺陷,夏皮罗将前者“承认规则”框架下的规则模式称为“决定模式”(Decision’s Model)。在该模式之下,行为人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指引进行了一个判断,只有遵循规则的行为较之于不遵循更具有优先性(Preference)时,行为人才会决定遵循规则。同时,在这一判断过程中,行为人亦始终有能力不遵守规则。(12)夏皮罗同时提出了“优先性命题”,指出在这一规则模式下,行为人对于规则的遵循完全处于遵循是一个更优先的理由。易言之,并不是因为形式上的规则而是由于实质上的内容。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 38.可见在决定模式之下,行为人对于规则的遵循并不必然受其指引,例如前述吉姆拒绝饮酒的例子就无法必然得出他是出于“禁止饮酒”的规则还是“我不喜欢饮酒”的一般规范性判断,后者很大程度上可能借助着同前者的实质符合而“狐假虎威”,充当着具有效力的规则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决定模式下,规则无法产生实践上的差异,因为无论规则是否存在,当行为人所持有的一般规范性判断与其符合时,行为人还是会依据没有规则存在时的行为模式行事。是故在决定模式下,要么产生规则与一般规范性判断并行的结论,要么产生规则不具有指引性的结论,而这是不可接受的,从而决定模式并不可行。
作为对比,夏皮罗紧接着提出了“限制模式”(Constraint’s Model),(13)作为对比,夏皮罗还给出了“可行性命题”,这一命题的要旨在于,当规则存在时,行为人需表现为除了遵循规则之外别无他法。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 47.在该模式下,行为人自主选择与判断的机会被剥夺,易言之,他并没有去评价遵循或不遵循孰为优先的空间,而只能选择遵循规则。实践差异便在这种限制性的情境下产生,任何人都须按照规则的要求行事,此处并不讨论一般规范性判断的情况,因为这种分析已经被跳过了。质言之,无论行为人原本持有什么样的判断都不会被纳入考虑,而只需要依照规则的要求即可。同时在限制模式下,人们依照规则行事的理由是规则本身。换言之,如果规则不存在,人们就不会如此行事。
通过上述两个规则模式,夏皮罗揭示了规则与一般规范性判断的差异,即前者会产生实践差异而后者更多地参与优先性判断,前者指引功能的发挥以实践差异的存在为必要,而后者单纯为行为提供可依据的理由。
(三) 指引功能与实践差异的产生
将这种差异移至法律上,则显而易见的是:法律如果想要具备指引功能,就必须能够产生实践差异,就必须首先作为一种规则存在。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法律作为一种一般性规范判断存在,那么它将不再具有指引属性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可供遵循的行为理由,这自然是荒谬的。同样地,法律如果需要为其权威性进行论证,就必须坚持其能产生实践差异的规则属性。回到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与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争论的主题,如果将道德论证引入承认规则之中,是否会使得法律丧失实践差异,继而失去指引功能呢?夏皮罗接下来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理所当然的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安置道德的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将无法立足;如若不然,则夏皮罗借由实践差异命题展开的攻击便会无效。
哈特将法律的指引作用视为其首要功能,其谓“在把法律看作为人之行为提供指引和批判标准之外,寻找法律的其他目的的做法是徒劳的”。(14)前引⑥,陈景辉书,第251页。但是哈特并没有明确这种对于行为的指引具有何种意义,在哈特理论模型下的指引功能以次级规则(主要是承认规则)的形式在法律官员那里产生出初级规则,随后初级规则就具体事项在民众中产生指导作用。但是夏皮罗认为,法律指引作用的发挥其实具备两种形式,即动机性的指引(motivational guidance)与认识上的指引(epistemic guidance)。所谓动机性的指引,意为当行为人遵循法律的指引时,是因为“对于法律规则本身的确信”(conform to a legal rule by the rule itself)而选择遵循。所谓认识上的指引表明的则是,行为人对于法律规则的遵循是出于对其法律义务和内容的了解。换言之,并不是因为作为“规则”的规则本身而遵循,行为人的遵循可能出于对法律规定的内容的认可,也可能单纯出于对违反法律而遭受惩罚的恐惧。(15)参见Scott J. Shapiro, “On Hart’s Way Out”, Legal Theory, 4, Issue 4(1998), pp.469-508.综合地看,动机性的指引产生的是对于法律规则的形式遵循(要求产生内在观点),认识上的指引产生出对于法律规则的实质遵循(不要求产生内在观点)。
这两种指引功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首先,经由承认规则,某一个本来属于法律之外的规则被法律官员接受为法律规则,赋予其权威性,此时动机性的指引发挥作用,法律官员不需要对该规则进行任何价值上的判断,只需要依据对规则本身的确信即可。例如议会颁布一条规则“市区内车速不得超过60千米每小时”,则法律官员只需要将其法律规则化即可。其次,法律规则并非以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而由法律官员传达给普通民众。因此,法律规则以作为法律官员与民众之间中介的方式指引后者的行为。(16)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p. 469-508.最后,普通民众依照具有“权威标识”(marks of authority)的法律规则行事,如不在市区内超速行驶,此时法律认识上的指引功能发挥了作用。
经由这样一个指引功能运行规则,夏皮罗将“承认规则中能否包含道德论证”这一问题转化为考察承认规则能否满足规则指引的两类指引形式,并且能否产生实践差异的检验。
就两种法律实证主义都包含的形式化承认规则而言:以议会颁布“市区内车速不得超过60千米每小时”这一条形式化规则为例。首先,这条规则本身就构成了依据其行为的依据,法律官员不需要对其进行任何价值上的判断,无须考察其是否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动机性的指引产生;其次,该规则明确了普通民众应当承担何种法律义务,也认识到如果违反这条规则会面临的惩罚,认识上的指引产生;最后,这条规则颁布前人们不会遵循“市区内车速不得超过60千米每小时”的规则(至少这样的聚合实践不可能产生),如果这条规则被废止,那么人们也不会再照此行事,由此实践差异也存在。综合上述分析,形式化承认规则能够保障法律指引功能的实现。(17)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p. 469-508.
与此同时,就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支持而其论战对手否定的实质化承认规则而言:以“出现疑难案件时,应当依据道德准则行事”这一条最具普遍性的实质化规则为例:首先,夏皮罗认为这条规则无法使法律官员透过其了解应该延伸出的初级规则,换言之,该规则要求法律官员进行价值上的判断,以评价哪种行为更具有优先性而应被认可,故此动机性的指引随之失去;其次,鉴于道德标准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法律官员依据他们的价值判断得出的法律标准的方式并不能使这一法律规则获得“权威性标识”,因为普通民众也可以作出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由此认识上的指引也相应失去。最后,规则与一般规范性判断在此处混淆,法律官员依据的道德判断本身是一种一般规范性判断的存在。换言之,如果法律官员不作出规则性定义,此处也本就存在某种一般性的规范,无论法律官员是否颁布规则都不会产生什么区别,所以夏皮罗指出,于此实践差异并不存在。(18)一般性的普遍判断,法律官员依据这样的判断制定出的规则,其存在与否并不会产生实践上的差异。例如假设社会存在一种关于恰当工资的判断,其默认每小时工资低于20元是不正义的,那么法律官员制定的规则如果合乎了这种判断则并不会产生实践差异,因为没有这条规则时社会本就是如此行事的。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p.469-508.综上,实质化承认规则不能够保障法律指引功能的实现。
通过法律指引功能与实践差异相结合,夏皮罗认为规则的特性在于其能够产生实践差异,进一步说,法律规则如果想要产生指引功能,也必须要具备实践差异。而包含道德论证的实质化承认规则无法产生实践差异,也无法产生指引功能,所以无法成为特定法律规则,此即“实践差异命题”。该命题内部逻辑圆融,且从功能主义与规则的基本性质出发,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尤其是关于如果不能满足法律指引功能的要求,即不能构成有效力的法律理论的论证,使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濒临破产”,迫使该学派之后的论证必须以反驳或使实践差异命题无效化为前提,否则就将宣告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的最终胜利。那么他们的反击将会如何展开呢?
(四) 对实践差异命题的批判
瓦卢乔认为,诚然道德论证有其本就包含行为规范的成分,(19)事实上,关于道德是法律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在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内部又产生了两个分支,本文介绍的瓦卢乔属于“必要条件”派,海默属于“充分条件”派。参见Kenneth Einar Himma, “H. L. A. Hart and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Thesis”, Legal Theory, 6, Issue 1(2000), pp.1-44.但这并不是全部。他用一个支付薪酬的例子进行说明,假设社会上存在一个“每小时应支付不低于6美元作为薪酬”的规范,那么法律官员会依据这一规范制定相应规则,这时是存在一种认识上的指引的,而当“每小时应支付不低于6美元作为薪酬”这条法律规则出台时,对民众就会产生动机性的指引,普通民众会对这样一个规则产生内在观念,而在这之前是不会出现的。所以瓦卢乔认为,光凭道德是难以产生实践差异的,唯有当法律以道德为必要条件并由此产生出法律规则时,实践差异才会产生。瓦卢乔将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作用称为“此外的理由”(one has to know more than that law conforms with moral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at to do),正是这一此外的理由的介入,才赋予了该法律规则以指引功能与实践差异。(20)参见W.J. Waluchow, “Authority and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Thesis: A Defense of Inclusive Legal Positivism”, Legal Theory, 6, Issue 1(2000), pp.45-82.
与此同时,海默(Kenneth Einar Himma)提出,夏皮罗对于“道德”概念的定义存在片面化倾向,在夏皮罗的实践差异命题中,道德是静态(static)的,所谓静态是指一种对于道德原则必然为真的预设,因为某一道德原则为真,所以它必然引起确定的价值判断,当某一条法律依据道德内容的正确性而获得效力后,该法律也会延续道德原则的正确性。(21)参见Kenneth Einar Himma, “Waluchow’s Defense of Inclusive Positivism”, Legal Theory, 5, Issue 1(1999), pp.101-116.这就使得法律效力与道德正确性重叠而失去实践差异,毕竟如果社会上存在一个确定的且必然为真的道德原则时,例如“不得杀人”,法律官员并不会在不存在“不得杀人”这一初级规则的前提下给出不同的规则。(22)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是哈特的实证主义还是拉兹、夏皮罗的排他性实证主义都接受一些“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任何承认规则也都必须符合这些条件的要求,否则法律体系将不再可能。参见note , Kenneth Einar Himma, pp.1-44.而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原则及其论证并不必然为真,正如海默采用伦理主观主义的观点说明道德原则同民众生活中的多种规范并存一样,其产生出的有效性只是单纯的偶然性事件,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应的行为展开,唯有经由承认规则赋予某种道德原则以法律权威后,才会对其所指向的民众产生义务性约束,也就此符合实践差异的要求。是故夏皮罗并不能当然得出道德论证无法产生指引功能的结论。
朱尔斯·科尔曼(Jules Leslie Coleman)则认为瓦卢乔与海默的反驳纯属困兽犹斗。在他看来,一旦承认了法律指引功能及实践差异命题的有效性,那么接受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为实证主义法学内部主流只是理论推导上的时间问题,“目前我尚未被我所见到的任何回应说服,我也不赞成这种防卫策略,这种策略由于让步过多而受到不适当地促动,以至于产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结果”。(23)[美]朱尔斯·科尔曼:《原则的实践——为法律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辩护》,丁海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所以科尔曼意识到,必须证伪该命题的前提,即指引功能是法律的唯一功能,方能扭转此种被动局面。
同夏皮罗一样,科尔曼选择从哈特的理论出发,他指出哈特对于法律功能的看法并不仅仅局限于指引功能,而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法律服务于人类各种各样的重要而正当的利益;其次,为了达成此目的,法律指引人们的行为。夏皮罗对此采取了功能主义的解读,得出结论“法律的功能在于指引行为”,而事实上哈特旨在提供一个“社会科学式的解释假说”,以此说明法律为什么产生与为什么持续存在;前者的解读只是这一假说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故此,科尔曼认为以功能主义的方式理解法律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指引功能仅仅适用于具体法(a law),而并不是对于法(the law)概念的要求。这样的论证还可以推及实践差异之上,科尔曼承认法律总体上具备的指引功能与实践差异,但它们并非法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在承认规则中接纳道德论证,虽然可能抵触实践差异命题,但并不影响其在法概念中的成立。同时科尔曼还认为,在实质性承认规则之下,法律可以承担体现道德判断并使其简明化的角色。易言之,它并不需要指引行为,只需要让道德原则变得更为具体,就也成为一种法律。(24)参见前引,科尔曼书,第186-187页。
是故科尔曼通过解读哈特对于法律功能的定义,扩大了其范围,提出了“法律为人类正当利益”服务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法”与“具体法”。一方面使得实践差异命题的前提无效化,另一方面在不直接否认该命题本身论证的情况下抵御住了其对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的瓦解。
(五) 批判的总结与分析
瓦卢乔与科尔曼等人对实践差异命题的批判可以被理解为实践论、认识论与本体论三个层次。
首先,实践论层次下争论的核心在于“承认规则是否可以安置道德论证”。实践差异命题经由功能主义解读哈特的法律理论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而瓦卢乔与海默通过细分道德概念进行了回击。关于这一差异或许可以通过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 v. Palmer)进行观察,该案的判决理由“任何人不得因其非法行为获利”并非出自立法、判例或者习惯法,而是来自“出处不明”的法律原则,其实际上是一种因其道德正当性而获得法效力的实质承认规则的适用。如果对其进行分析的话,那么“任何人不得因其非法行为获利”因其内容不可非议的正当性而取得对法律官员的动机性的指引,同时也符合普通民众对于“不可因非法行为获利”的价值判断,因而获得认识上的指引。最后,如果没有这一规则,那么帕尔默本应依照纽约州遗产规则获得继承权,而这一规则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实践差异产生。
实质承认规则具备合理性的重要原因在于,承认规则本身就具备规则的属性。该案的裁判是基于“出现疑难案件时,法官应当援引相关的道德原则作为判决的基础”之规则,该规则在保障法律与道德界限的同时,如瓦卢乔所说的那样,以“此外的理由”赋予道德规则以法律效力。诚如我国台湾学者庄世同所指出的那样:“宪法与部门法中的一系列原则都将一系列政治道德的要求纳入自身的内容之中。”(25)前引⑥,陈景辉书,第313页。哈特在他的实证主义法学体系中容纳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存在,这实则表明,即便是形式化的承认规则也包含着道德判断的成分在内,无非其为立法、判例与习惯法的外壳所遮盖;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化的承认规则多少呈现出被实质化承认规则包含的态势。
其次,认识论层次下的主题表现为容纳道德论证的承认规则,是否还合乎分离命题的要求呢?实践差异命题试图通过道德与法律重叠的正当性来否定前者,这是因为当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的正当性之上时,法律的存在就将变成多余的了,法律就会成为道德伦理的附属物。经由海默的伦理主观主义解释,可以发现,承认规则对于道德论证的包含,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再现,概因其并不是一种必然的情况而只是偶然地展现。以“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为例,纽约州法官放弃适用纽约州继承规则而援引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实质是道德原则)进行判决,对于该原则的援引会成为日后类似案件适用“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原则所依据的实践。同时该种援引行为,也会成为之后的司法裁判中法官认为实在法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时,援引法律(道德)原则审判的有效性实践先例,而并非限制法官只能一事一议地适用特定的法律(道德)原则。
或许可以这样进行评价,以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必然”,以拉兹、夏皮罗为代表的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两者间的关系是“无”,而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两者间的关系是“偶然”。在这一偶然中,其实包含了“有”与“无”的两种情况,或许有但不必然有,就此分离命题得到维护,也同时容纳了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者的观点。
在前两场争论中,隐约可以看到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对于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在论证上的包容关系,而在本场争论中,科尔曼首先表明他对其他包容性实证主义者驳论的鄙夷,其谓“目前我尚未被我所见到的任何回应说服,我也不赞成这种防卫策略,这种策略由于让步过多而受到不适当地促动,以至于产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结果”。(26)前引,科尔曼书,第179页。但事实上,通过科尔曼对于法律功能的扩充与法律概念的扩充可以看出,他在“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采取了包容策略,那么,他的策略具备证明力吗?科尔曼认为在“关于法律,什么必定为真”与“关于每个法律,什么必定为真”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鸿沟;迄今为止,似乎没有概念上的论证来弥补此鸿沟。是故,他可以大方地承认实践差异命题与法律必须具备指引功能的正确性,而不去担心它们会对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产生实质上的冲击,因为即便具体法必须合乎上述两个要求,也不能说明法概念需要做同样的事,他指出:“即使它们是在一项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与该制度也并不相连,例如,存在许多由一个游戏规则所创设的权利和义务。”(27)前引,科尔曼书,第185-186页。
然而,科尔曼所作的这种区分,还处在“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框架之下吗?对此,或许可以援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举的一个例子,“我曾经把他比作一个患病的学究,医生劝他吃水果,于是有人把樱桃或杏子或葡萄放在他前面,但他由于抽象理智的学究气,却不伸手去拿,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樱桃、杏子或葡萄,而不是水果”。(2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如若科尔曼旨在通过法概念与具体法的区分容纳实践差异命题的话,那么他无疑陷入了唯名论的陷阱,以科尔曼的反驳逻辑继续推导的话,那么现存任何一种法律流派均不具有证明力,因为他们均是对于“每个法律”的理论。
总结以上三者,可以发现夏皮罗的实践差异命题并没有彻底瓦解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的有效性,相反他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后者所包含。但在关于“法律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的解答上,该理论从功能主义层面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也正是以此为起点,夏皮罗从本体论的层面开始,对哈特以来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颠覆和突破,这便是“法律规划理论”的提出。
三、 道德目标命题:提出与论证
经由前述分析,可以发现夏皮罗的实践差异命题并没有能够达到他所旨在实现了瓦解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有效性的目的。哈特规则理论的固有不足与实践差异命题仅从局部入手修补前者的证明力缺乏,使得夏皮罗开始了一种理论上的转变。在《规则产生的差异》(The Difference That Rules Make)一文发表四年之后,夏皮罗在题为《法律、规划与实践理由》(Law, Plans, and Practical Reason)(29)参见Scott J. Shapiro, “Law, Plans, and Practical Reason”, Legal Theory, 8, No. 4(2002), pp. 387-442.值得一提的是,夏皮罗在该文中的诸多论述与例证基本都还原到了他的著作《合法性》之中。的论文中首次将法律理论与哲学家迈克尔·布莱特曼(Michael Bratman)的规划理论结合,试图在崭新的规划领域中寻求法律理论的突破。2011年,夏皮罗出版《合法性》一书,标志着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最新版本,即法律规划理论的正式提出。该理论的要旨是:法律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规划,法律通过告诉社群中的成员何者可为与何者不可为,确定由谁决定可为与不可为之事来形成规划,法律规则是普遍化了的规划或类似于规划的规范。而法律运行的过程则是将这种规划(或规范)运用到其指向的人之上,并由这种方式,法律规划并组织了社群的行动,并将道德善引入其中。(30)参见note ①, Scott J. Shapiro, p.155.然而,就如同夏皮罗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在法律理论思辨的领域中,“答案通常会引发更多的问题”。(31)前引①,夏皮罗书,第105页。法律规划理论引发的问题与争论也并不比它所带来的答案要少:法律规划理论对于哈特的批判是否妥当?该理论的构建环节是否严密?由“引入道德善”推论出的道德目标命题是否还是一种实证主义理论等问题接踵而至。为了就这些问题对法律规划理论进行考察,有必要从实证主义法律理论的基本理论起点出发,即可能性难题(Possibility Puzzle)与休谟准则(Hume’s Law),分析哈特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的,并考察夏皮罗是如何从哈特规则理论的不足中提出其规划理论的。
(一) 法律规则理论的不足
可能性难题思考的是法律规范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方面,立法者依照何种规范获得制定法律的权力?另一方面,授予立法者该权力的规范又是由谁制定的?如果单纯主张其中任何一者在先,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限逻辑倒退之中。(32)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p.469-508.同时对于实证主义理论而言,对这一难题进行破解,还必须考虑到休谟准则的约束,即关于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判断不能从关于社会实践的纯粹描述性判断中衍生出来的观点。
哈特规则理论的功能便是停止这种倒退。哈特认为法律由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构成,在规则的背后存在着确认规则规范性的帝王规则,即“承认规则”。承认规则判定在法律体系中何种权威主张具有规范性并使之成为规则,而规则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承认规则并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由法官的一致遵循和对其采取的反思批判态度所产生的,故此承认规则不需要考虑谁制定的问题,因为它借由法官的实践而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然而,夏皮罗认为,经由实践产生的承认规则做出的法律规则、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有效性判断,并不能符合休谟准则,是一种从纯粹描述性判断中推论出规范性判断。(33)参见前引①,夏皮罗书,第129页。但是夏皮罗同样指出,哈特应当意识到了休谟准则的威胁,所以夏皮罗认为,规则理论实际上对规范性判断的客体进行了延展,具言之,哈特排斥了“规范性事实”的存在,认为人们对于某种事物的否定性判断并不是一种“事实”,而只是一种表达了避免接触该事物的实践承诺。所以,描述性事实不但是描述性判断的客体而且也是规范性判断的客体。由此,哈特在反驳了休谟准则的同时,也回答了可能性难题。
但是,夏皮罗紧跟着指出,哈特的规则理论存在一个范畴错误,将社会规则化约为社会实践的方式是错的,因为规则和实践属于不同的形而上学范畴。规则是抽象的客体,实践是具体的事件,规则和实践是不同种类的事物,一种不能化约为另一种,就好像7个苹果不能同数字7化约一样。(34)参见前引①,夏皮罗书,第134-135页。而这一错误所导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其与法律实践还有严重的不匹配之处:按照哈特的观点,确定的社会实践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规则,法律官员间认可的社会实践会产生相应的法律体系的规则。对此,夏皮罗指出,一方面很多情况下社会实践都没有能够产生社会规则,另一方面假设对于行为的一致遵循和内在观点的采取就能产生规则的话,那么只要对于另一种行为也采取类似的作法,先前的规则就将骤然不复存在,规则的生命——规范性,对此也将束手无策。结合之前所提到的实践差异命题,可以发现,在哈特的规则理论之中,实践差异所依赖的基础,即规则本身是松动的。哈特并没有赋予法律一个真正明确与稳固的基础,当一致遵循的实践改变时,规则并不能对这种偏离进行规制,相反其会自动消解并产生适应新的实践的规则,而这与实际上的法律活动是不相符的。(35)参见Scott J. Shapiro, “Law, Morality, and the Guidance of Conduct”, Legal Theory, 6, Issue 2(2000), pp.127-170.是故,夏皮罗需要为法律寻找到一个更加稳固的理论解释基础,使其能够断然地完成指引与评价行为的功能,而不会喧宾夺主地为实践取消其规范性,这便是法律规划理论的建立在实践差异基础上的功能主义面向。
与此同时,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仍旧有待解决。夏皮罗认为,哈特的规则理论有模糊法律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危险性,例如,“义务”在法律语境和道德语境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某人对另外一人具有法律义务的同时并不能说明其人在道德上也负有义务,哈特的规则理论的推论是:规范性的法律术语可以融贯地解释一个人如何始终一致判断某人只负有法律义务而非道德义务,但这样的推论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法律的功能上也是不能从描述性事实那个推论出来的,原因在于法律的术语旨在描述行为、提出义务性要求并且评估行为与提供理由,它们并不是在说明“是”的问题,而是在阐述“应当”的情况。(36)参见Joseph Raz, Incorporation by Law,in Legal Theory, 10, Issue 1(2004), pp. 1-18.为了给予法律的“道德合法性”,道德目标命题也将被论证于规划理论之中。
(二) 法律规划理论的论证
规划理论的基本逻辑起点是将哈特理论中的规则置换为规划。规划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夏皮罗在其中发现了实证主义法学的两个基本要求:首先,规划有着纯粹的社会来源。规划之所以会被制定出来,单纯是因为人是会作规划的动物,我们有着通过自己的意图,在有限的条件下,制定一个追求复杂目标的行为方式的能力。(37)参见Michael E. Bratman, Intention, Plans, and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4.这一能力的获得不存在任何规范性判准,正义之士会制定规划,恐怖主义团伙也会。规划的存在与生效条件是一个描述性事实,其被制定并以特定方式执行即可被视作存在。其次,规划具有规范性,并能产生夏皮罗所描述的实践差异。当规划存在时,其要求、允许或授权行动者在特定条件下以特定方式行动或不行动,作为规划参与者的行动者会因为规划的存在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鉴于规划能力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理性能力,夏皮罗认为,无论是国家的治理还是社会的运作,都离不开规划;而法律则自然而然地是一种社会规划的形式。这一主张并不仅仅是由规划向法律的类比,夏皮罗借此对于法律的本体论作出了主张,法律能产生权威性的理由并非其他,而是人们对于这种社会规划的接受,并由此产生出拘束力。
关于规划可以从制定、结构与运行三方面进行解说。规划的产生具备工具理性,即规划旨在明确为了解决什么问题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行为。出于问题往往由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问题群组成,相应的解决方法要求规划具备由总体规划与部分规划组成的嵌套结构。而在按照规划执行的过程中,关于规划优缺点及存在意义的讨论应当被阻止,其断然性地要求参与者将问题解决本身同规划绑定,理性人将不会自我推翻与主张不达成问题的解决。同时,规划并不仅仅局限在个人行为上,相反,夏皮罗指出,如果没有规划,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行为将不再可能。(38)参见前引①,夏皮罗书,第170页。规划可以结合群体、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成员间的差异与认知不足,形成层级以更有效地分配和执行。更重要地是,规划使群体行为具备了可预测性,使单个人的行为不再是“前规划时期”的无规律依据与对他人漠不关心和一无所知。
类比“前规范性环境”与“规范性环境”,夏皮罗将规划存在环境过渡至法律之上,提出“合法性环境”(circumstances of legality)的观点。夏皮罗认为,一个法律体系的权威证明不需要主张道德的合法性,并由此来强制履行法律义务和赋予权利,只需要具备规划能力即可。(39)参见Thomas Bustamante, “Interpreting Plans: A Critical View of Scott Shapiro’s Planning Theory of Law”,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 37, (2012), pp. 219-250.法律因此是一个在总体规划的要求下以普遍的手段协调社会行动方向的手段。所谓总体规划,是作为“规划的规划”存在的,并与规则理论中作为“规则的规则”的承认规则相对应。但是总体规划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同承认规则一样,仍需要面对可能性难题的检验。
夏皮罗认为,在承认每个人都具有制定规划能力的前提下,总体规划来自官员们的共享合作规划。与哈特的规则理论相类似的是,规划理论将其法律规则与制定法律规划存在的前提建立在官员们的接受之上。在哈特的理论中,官员们以“内在观点”的态度接受法律,但是在夏皮罗这里,总体规划来源于官员们的共享合作规划,在前者由后者的集合产生的过程中,官员们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内在合理性”(inner rationality)观点接受规划。(40)按照夏皮罗在该处注释中的说法,“内在合理性”一词源于朗·富勒(Lon L. Fuller)的“法律的内在道德”观点。参见note ①, Scott J. Shapiro, p. 182.他们采纳总体规划,并承诺在该规划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也要求(许可)其他人依照规划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因为官员们接受他们的职责,就是在接受规划的一个部分,同时参与规划活动的独特的理性规范必然会发挥作用。因此,如果一个官员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不服从上级,或没有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完成上级的命令,或采取与总体规划所涵盖的不一致的规划,甚至重新考虑规划的存在意义,其人就会受到内在合理性的批评。(41)参见note ②, Connie S. Rosati, pp. 307-324.总结夏皮罗的观点则是,法律之所以能够被我们所创造是因为我们是能够进行规划的群体性动物,而法律只是社会规划的一种。某一主体被授权制定规划,是由我们所制定的共享合作规划所产生的。故此,规划理论能够回答法律规则的权威性问题,而没有陷入逻辑倒退之中。(42)参见前引①,夏皮罗书,第234页。
到此为止,规划理论还需要经过休谟准则的检验才可算在逻辑上完全成立,对此夏皮罗区分了法律权威考察中的“形容性”解释与“视角性”解释,前者主张法律权威包含着道德权威的获取,后者则在两种权威中进行分离。夏皮罗主张排除形容性解释的方法,因为按照前者的逻辑,没有道德权威的法律体系将不可能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并非如此。而视角性解释以其对于道德权威的限定使得可以将该种法律体系也认为是法律,但同时夏皮罗也认为,视角性地理解法律并不意味着抹杀道德权威的存在的意义,而仅仅是承认任何人在道德层面上没有遵循法律的义务与因不遵守法律而受到道德谴责的理由,视角性的解释仅仅是在声明:“不服从法律是具备受指责可能性的。”是故,在休谟准则的评价中:视角性解释中的法律对权威、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判断是一种描述性判断,因为当一个主体在系统中具有合法的权威,是因为它在法律上具有道德权威;在法律上具有道德权威,因为它在系统规划中被授权。而由于授权机构的规划是该系统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因此,由于总体计划授权该机构,所以该机构在系统中具有法律权威。如我们所见,总体规划的存在与道德事实无关,而仅仅是从规划到规划的推导。继而,经由法律产生的判决,就可以理解为在系统的规划中,某人根据某一规划而对另一人享有权威,其是从规划的描述性事实中得出了合乎规划内容的描述性判断,符合休谟准则。(43)参见Emily Sherwin,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A Comment on Scott Shapiro’s”, Legal Theory, 19, 4(2013), p.403; note ①, Scott J. Shapiro, pp.187-188.
然而,法律规划理论的关键要素“意图”仍旧迷雾重重,夏皮罗需要进一步解释道德在他的法律理论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某一具体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上可质疑的属性,具备道德缺陷的法律是否会影响其作为法律的资格,并从目的论的视角说明规划的制定者究竟旨在通过法律达成何种目标。
(三) 道德目标命题的矛盾
承担上述问题回答任务的即道德目标命题。夏皮罗认为,在“前规划时代”,在社会中持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分歧,如果不依赖作为社会规划的法律,那么解决方式就将是暴力的、复杂的且有争议的,也毫无疑问是低效率与高成本的。规划的工具理性特点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的首要目的就在于区别于其他形式地弥补社会中存在的道德分歧与缺陷,此即道德目标命题。
具体地说,该命题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解决人类协作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道德分歧,其通过提供权威性的方式降低协商成本、补偿认知能力的区别并使行为一致化。经由法律旨在解决道德争端,并试图确立其规范的道德权威属性的路径。夏皮罗指出,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何种道德上的要求,而是因为它具备一个道德要求。人们可以依据这一要求对社会的纠纷进行判断与处理,而这种依据并不需要人们对于法律提供的解决办法在内在理性中采取赞同的态度。(44)参见David Dyzenhaus, “Legality without the Rule of Law: Scott Shapiro and Wicked Legal Systems”,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 Jurisprudence, 25, 1(2012), pp. 183-200.夏皮罗进一步认为,法律本身对于道德也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法律不知道或不关心这些规范性判断是否正确——法律只是在产生这种判断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罗尔斯无知之幕的“黑盒理论”,道德的要求是什么并不重要,值得被考察的唯有法律的观点。
规划理论看似经由道德目标的论证夯实了其建立在分离命题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性质,但是问题随即产生。仅就道德目标命题内部而言,道德目标在法律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之重要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按照夏皮罗对于该命题讨论的延展,一套规划如果想要成为法律,其必须具有道德目标,“如果我们想解释是什么使法律成为法律,我们必须看到它必然具有一个道德目标,一个犯罪组织不一定拥有的目标”(45)参见note ①, Scott J. Shapiro, p.215.。然而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承认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如何理解邪恶法律体系(evil legal systems)问题?对此,夏皮罗认为:首先,法律尽管需要解决道德难题,但是它在原则上对道德持不可知论的态度,换言之,它不应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性追求。其次,在这一目标的要求下,法律制度本身是可以被评价的,一个不能有效解决道德难题的法律制度是应受到批评的。那么是不是说一个规划组织符合上述要求,就是法律呢?例如一个黑社会组织,它有规划、有目的、有官职、有强制性的管理,甚至它和我们所熟悉的法律一样发布一些不需要对象人许可的命令,这个黑社会组织是法律制度吗?夏皮罗认为,此时还需要添加一个目的上的限缩。法律必须要有目的,而犯罪组织并不必须;法律毫无疑问要比犯罪组织有更优良的道德目标,而且重点在于,法律必须要有。(46)参见Triantafyllos Gkouvas, “Planning from a Legal Point of View”, Jurisprudence, 7, 2(2016), pp.341-354.我们会说一个法律是不正义的,故此它在道德上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不会说某位黑社会成员是不正义的,这并非表明对其认可,而是关于正义的评判在缺乏道德目标的情况,不适用于评判后者。道德目标命题所能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法律应该解决道德难题,还包括对于奥斯丁的疑问,即“如果正义不复存在,除了是一帮强盗,王国还能是其他什么吗?”的回答,因为存在道德目标的设定,法律必须在“合法性环境”下解决问题,所以黑社会组织、强盗并不能产生法律,因为道德目标的缺失产生不了“合法性环境”。但是我们的疑问还没有结束。是否一个有规划、有正当的(解决道德难题)目的、有官职也有强制性管理的组织,就是法律呢?例如公寓管理委员会是不是法律组织呢?对此,夏皮罗提出“自我证明”这一要素予以回应,所谓自我证明是指,每当一个规划组织可以无需向其上级(如果存在的话)证明它的规则是有效的就能自由地执行它的规则。当公寓内发生犯罪时,公寓管理委员会显然不具备司法权力,但是警察局与法院显然并不需要向立法者申请才能展开行动,因为他们是“自我证明”的。(47)参见前引①,夏皮罗书,第279-282页。
相较于此,道德目标命题同实践差异命题的矛盾更为“深重”。(48)应当说,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即便是同一位学者出现理论的变化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文认为,夏皮罗的两个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互相冲突的,这一点并不多见。从本体论的角度上讲,纵然前者基于崭新的规划命题而后者则处在规则理论的框架内试图修复被原则理论破坏的承认规则。但是在规则理论的框架内,法律的本质属性不依赖“目标”,更不依赖对道德目标的追寻。按照夏皮罗曾经的说法,道德是否充当了法律存在的必要理由都充满不确定性,而在道德目标命题中,这一个不确定性走向了其反面。从实践理论的角度上看,诚然规划理论吸收了实践差异命题的重要结论,借由规划发挥出指引行为的功能,两者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但是细究其内核则实际上是两种结果相同但过程相异的推理。就实践差异命题所构建法律论证理论而言,道德在这一过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与其说不对论证产生影响,毋宁说这是一个道德完全“真空”的领域,法律不关心道德规范的要求,而只是单纯进行一个行为指示,法律所指向的人按照其要求行事即可。(49)参见note , Scott J. Shapiro, p.36.这是实践差异命题的核心所在,即当法律存在时,其成为决定性与断然性的实践理由。规划理论下,法律似乎也具有这样的功能,但其产生的路径充满了被实践差异命题所不断排斥的“选择”。从理论完整性的角度来为夏皮罗辩护的话,他或许可以主张道德目标命题理论并没有在法律论证过程中进行选择,而只是合乎规划要求地作出判断。但事实上,摆在规划法律理论面前的是一系列道德选项,总体规划要求其作出选择,而作为嵌套结构的部分规划要么根据前者的要求进行选择,由此违背实践差异命题的要求;要么不遵循总体规划的要求,继而导致破坏规划理论的结果。
四、 法律实证主义的困境:以法律规划理论为视角
前述经由对法律规划理论以及道德目标命题的分析,阐述了该理论内部的逻辑不融贯与外部的同夏皮罗曾经提出的实践差异命题的矛盾之处。从理性思维的角度,夏皮罗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矛盾,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实证主义自身的缺陷。
(一) 法律道德界分的困境
对道德目标命题进行批判的常见理由是前述言及的邪恶法律体系问题。在法律实证主义的一般观点中,邪恶法律体系不仅是可以存在而且是已经存在的。那么按照道德目标命题,这种法律体系也一定有其道德目标。如果这样认识的话,实际上道德目标就具有了双重的含义,一个“邪恶”的道德目标与一个应用合理的道德目标的法律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似乎就像一个为了杀死某人而故意碾压某人的人和一个为了帮助事故受害者却误杀了他的人之间的区别。(50)参见note ②, Connie S. Rosati, pp. 307-324.夏皮罗可以通过将道德目标命题退却至“表面的”目标与“最高层次”目标的二分之中来寻求解释,即邪恶法律体系之中的不法是发生在“道德善的伪装”之下的,构成行为的目的本身是善好的,只是其代理人是“邪恶”的。法律体系的道德目标并没有出现扭曲而只是被误解或者误导了。然而,这样一种解释进路无异于承认,纳粹的法律制度并不是错误而仅仅是失误而已。即使该种回应能够奏效,在更深层次的论证路径上,夏皮罗也存在被指责有逻辑循环的危险,当描述的对象已经被确定为“纳粹德国”与“黑社会”组织时,如何从这种已经被标明的规范性评价中再论证其评价?夏皮罗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无异于在告诉我们,黑社会组织为什么产生不了法律,因为他们是邪恶的黑社会而已。(51)参见前引①,夏皮罗书,第279-280页。
同样的基于规范性评价论证的思路,事实上还可以从整个法律规划理论的逻辑前提进行分析。前已言及,夏皮罗借鉴了布莱特曼的规划理论,他们共同指出人具有面对复杂问题时制定规划的能力,而这一个前提,恰恰是有着自然法的理性主义内核的。诚然,夏皮罗在他的论证过程中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是故他着重强调规划的工具理性意义,并将其限定在纯粹形式价值之上。但正如他自己提到的那样,制定规划一定有着特定的“意愿”,并且规划也必须具备明确的“目的”,无论如何淡化规划意愿对于价值的态度,也不可能否认规划的制定包含着对于什么值得追求与说明应当避免的认识。毕竟如果否定了后者,规划自身将是难以成立与不可能被理解的。(52)参见note ③, Robert Alexy, pp. 299-306.同样地,当社会规划具体为法律规划,一般意愿具体为法律旨在完成的道德目标时,隐藏在复杂、混乱与断然的各种道德理由背后的选择,并不会是价值中立的,否则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在法律规范的层面是不可能的。这样来看,就如同夏皮罗在描述可能性难题时选用的节标题“选择你的毒药”一样,规划理论以及其中的道德目标命题也为夏皮罗自己提供了两瓶毒药:要么承认价值中立的工具规划难以解释法律的本质属性,要么放弃规划理论的实证主义属性转而承认其在理论起点上是一种自然法理论。
(二) 基础哲学理论的困境
夏皮罗在法律与道德的界分中陷入的困境,其实是由法律实证主义旨在解决的问题与其解决的方式决定的。规划理论产生于规则理论的不完善之中,夏皮罗认为这种不完善是由于哈特在确定法律性质的过程中出现的范畴错误。然而这一点是不能完全成立的。首先,哈特的承认规则并不仅仅是描述性事实,(53)张文显等主编:《法理学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其在由法官的聚合实践产生并推导出初级规则的过程中具有着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双重特质。所以,承认规则并没有单纯地借由规则产生实践,范畴错误的说法严格地讲并不成立。更为重要的是,夏皮罗范畴错误的反驳路径证明力是不强的,哈特的规则理论在由描述性事实向规范性判断的推导中突破了休谟准则,否定了作为规范性判断前提的规范性事实的存在。夏皮罗所谓范畴错误的内核,其实是一种异化了的休谟准则的适用,其无非在说明哈特的规则理论不符合休谟准则而已。但是同样的可能性难题也可以抛给休谟准则,那就是该准则如何具有规范性呢?缘何可以通过一种规范性判断否定一种描述性事实的存在呢?显然,在法律理论的推导中,是事实而非逻辑,要求着正确性的合乎。
在目前的英美法理学讨论中亦确有提及的是,关于“法律的本质”是否能够进行研究的问题,“法律的本质”是一个可以研究或者说可以得出准确答案的问题吗?托马斯·巴斯塔曼特(Thomas Bustamante)教授认为,法律同物理现象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前者并不外于我们而存在,法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我们如何参与、实践并对其持有什么态度的“动态现象”,关于法律性质的判断“较之于海岸线更加起伏不定”,但夏皮罗等法律理论家在他们的书中屡屡提及“法律的哲学真理”与“法律的本质属性”时,他们的研究方法可能在一开始就是有所偏颇的。(54)参见note , Thomas Bustamante, pp. 219-250.
五、 结 语
自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提出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旷日持久的论辩至今战火仍然未熄。在法律规则之概念的提出,继而拆开与细分,最后再定义与推翻的过程中,在“实证主义真的胜利了吗?”的提问,到逐渐演变为“实证主义是否还存在”的质疑过程中,英美法律理论界一般法理学的统一叙事的碎片化之“无王期”似乎已经降临。(55)参见蔡琳:《实证主义真的胜利了吗?——以哈特、德沃金之争为中心》,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在这一现象产生的背后,是否存在语言哲学引导下对概念过度解读的陷阱呢?至少在对于实践差异命题的观察中,不同学派的概念用法存在着重合与混淆的情况,这是理论界百花齐放的幸运,还是之后研究者需要面对盘根错节的不幸呢?夏皮罗的法律规划理论在佩戴着法律实证主义最新与最具证明力的新版本光环的同时,其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并不比提出的观点更少。那么,谁是最好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规划理论是不是最后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等问题,在今日的英美法理学界亦没有明确的回答。当然,在各个学派的诘问反驳之中,或许并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失败与无效的,也或许法理学理论的多元化与差异化,是英美法理学界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趋势,但反思、质疑、辩解应该是法理学学术研究的最为珍贵的内涵,因为最终胜利的只有真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