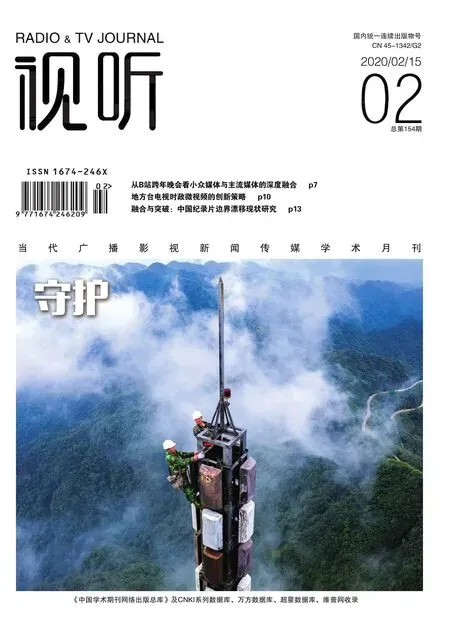镜式情景中的“隐秘他者”
——赛博格式科幻电影下的恐惧心理探究
□ 庄紫涵
作为人类,总是致力于探究和改变生存现状,试图利用科技推进人类发展进程,但是科技发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类不可预测的负面性影响,因此人面对种种新事物的产生总是隐约带着一种具有原生性的恐惧心理。科幻电影给了人类一个假想的窗口,人们坐在影院里安全地观看和体验未来世界,达到宣泄现实世界里对科技产生的恐惧心理之目的。但与大部分科幻片不同的是,以表现类人型机械人参与人类社会工作为主要情节的赛博格式科幻片,将传统科幻片中的显性他者——例如外星生物、变异人等——转变为类人型甚至真人型机械人这样一种隐性他者,一种极其近似于“我”但又高于“我”的新物种成为了被展示的客体元素,不再仅仅是依托于想象之上的形象,而更像是真实人类的镜像。赛博格式科幻电影中所产生的观众与类人型机械人这种诡谲的镜式情境,印证了该子类型影片的特殊性。笔者结合具体影片分析由其带来的特殊恐惧心理的原因。
一、镜式情境下他者形象的隐秘性
在“银翼杀手”系列影片中,所表现的主体是复制人,整部电影在叙事过程中展现了他们生活工作的一切细节,但是唯一隐去的是复制人的生产过程,当复制人出现就已经是与人高度相似的形态。《银翼杀手2049》中的男主角K 由当下比较热门的男演员瑞恩·高斯林扮演,影片中关于复制人的带有幻想性质的产生片段被抹去,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作为观众在影片开始对影片中的人物进行建构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任何能够将警官K 指认为他者的线索,这就让观众在影片初期解读之时模糊了人与复制人的界限,模糊了“我”与复制人之间的界限。
根据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在1906年提出的“恐怖谷”理论,当机器人与人类相像超过95%或直至到了一个特定程度,他们的反应便会突然变得极其反感。类人型机器人或者复制人式的科幻电影在其表现主体的形态上显现出与人类高度的相似性,观众在观影的初期认出了他们,将其误认为人类,给予其中的角色一种肯定的情绪,形成了一种“镜式情境”,但是随着影片的进行,复制人的“非人性”越来越暴露出来。例如在《银翼杀手2049》中,警官K 受伤时选择用胶水粘合伤口,这样的小细节在影片中数不胜数,在高仿真形态下真假的不确定性让观众对复制人的观感时刻游离在“同类”和“他者”之间,从而产生一种焦虑感和恐惧感,这种焦虑感与恐惧感往往又在影片的反派角色与人类角色的对抗上得到彻底的印证。《银翼杀手2049》中的复制人露芙逼问乔西警官K 的下落,露芙的回答是:“你这弱小的人类,遇到新事物,你就一心想要扼杀他,害怕巨变?螳臂当车是没有用的。”然后轻而易举地将人类角色杀害了。观众在此时彻底认知到在观影过程中所建立的镜式情境的“同类”实际上是带有危险性的隐秘他者。
从初步形象上的认同到不确定的游离最后到确认他者感到恐惧的这一过程中,观众打破原本对于类人型机械人的认同,意识到了自身与一个极其相似“我”却又高于“我”的机械人产生了镜式情境,而这个对象本身是不可信任的并且具有极强的他者性质的,会给“我”带来强烈驱逐感的形象,因此在观影过程中,从他者形象上而言,产生了比传统科幻片更为复杂的恐惧心理。
二、类人型机械人所带来的人类主体性危机
假设类人型机械人,仅仅是停留在外表长相与人体近乎相似却没有自我意识的状态下,观众还能够在认知范围内区分其是“他者”还是“同类”,如果一旦机械人拥有了自我意识或者自我认知之后,观众对于其的恐惧感将会从纯粹因为形象上的高度相似转变为人类主体性危机之上。
在赛博格式科幻电影中,类人型机械人被创造出来往往是带有完成人类不能完成之事或者替人类解决低能性质的生存工作之使命,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人类欲望的投射对象,但因为类人型机械人在创造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工具性质,在与人类角色的关系之中,由人类角色对其进行操控和赋予权利,占据主体位置的仍然是人类,此时二者的关系还停留在造物主与造物之间,但是在赛博格式的科幻电影中几乎都会出现一个相似叙事,就是类人型机械人在经历过一番事件之后,开始寻求脱离人类的操控,试图建立属于机械人自身的社会秩序,开始对于自我的生存价值进行思考,并且产生人类独有的情感。而观众在这样的文本里意识到了类人型机械人开始产生了欲望,并且在追寻欲望的过程中,将欲望反投射到人类身上,打破了原本造物对于造物主“为我所用”的状态。根据精神分析学说中对于主体性的论述,欲望的产生和投射正是主体性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意味着类人型机械人产生了自我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了强烈的威胁,于是观众在这一诡谲的自我镜像中再一次发现了不同于“我”的隐秘他者,并且这个他者,或者说异类,在生存能力上更是高于“我”的,人类被自己所创造的异类拉下造物主的神坛,主体性岌岌可危。
三、同类认同焦虑
观众此时已经在之前的镜式情境中认出了类人型机械人这类他者,为了消解被反噬的焦虑感,观众与片中的人类角色建立了新的镜式情境,将驱逐他者保全主体性的欲望投射至人类角色身上,希望其能替代“我”解决,对人类角色观众基本处于认同状态之下。但在这样的情节之后,由于赛博格式科幻电影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反乌托邦”性质,人类角色在追捕驱逐的过程中“必须”展露出越来越多人性的负面,例如残暴、凶狠、懦弱等以及更多人类的原生弱点,但是反观类人型机械人,他们所展露出的更多是越来越人性的一面。在《银翼杀手》中,因为不满被限定的生命复制人部队发动了叛变,之后他们被人类宣布为违法物必须处以死刑,被称为“银翼杀手”的特种警察部队奉命侦查所有的复制人。电影的最后,在这场为了生存权利的战斗之中,在最后的生死关头,却是复制人对人类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他们必须接受被驱逐报废的宿命,但很难说明到底谁才是这场战争里百分之百的胜利者。
观众将解决生存焦虑的欲望投射至影片中的人类角色身上,却在赛博格式科幻片特有的叙事文本属性之中又陷入了一种同类认同疑问焦虑的尴尬境地。在这样两种镜式情境下,观众都无法将焦虑与恐惧释放而得到欲望的满足,反之产生的是具有强烈虚无感和孤独感的自我疑问,这样的认同焦虑使得观众再次产生更为深层次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恐惧心理。
四、结语
赛博格式的科幻电影对于人的自主性思考使其成为了科幻片类型中较为独特的一个分支,更具有哲思与艺术感。在观看复制人这种在视觉上与人几乎无差别的奇观时,观众在银幕上有了错认的可能,进入到第一层诡谲的镜式情境之中,又因为逐渐在影片中发现其与人类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认知到了这类“隐秘他者”的存在,在其存在背后接收到了他者欲望的反投射,试图摆脱自带的工具性质,人类独有的自主性受到威胁,于是观众开始脱离镜式情境,转而试图认同片中的人类角色。然而,由于该类科幻片文本性质的特殊性,在同类认同的镜式情境之上,观众无法获得百分之百的满足感,最终产生认同焦虑以及生存恐惧。该类型的影片以一种伤痛式的观影体验为沉浸于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中的我们画了一个问号,人类应该如何存在、面对科技人类应该如何自处等疑问全部包含其中。通过科幻电影所呈现出的这些与人相当的赛博格去认知人类自身的人性特点,似乎也不失为一条有趣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