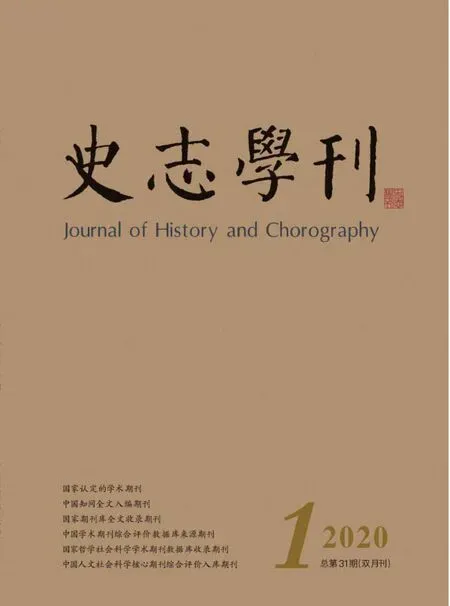《征士法高卿碑》性质考辨
张寅潇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西安 710065)
一、问题的提出
《艺文类聚》卷37《人部·隐逸下》载有后汉胡广《征士法高卿碑》,其曰:
“言满天下,发成篇章,行充宇宙,动为仪表。四海英儒,履义君子,企望来臻者,不可胜纪也。翻然凤举,匿耀远遁,名不可得而闻,身难可得而睹。为尧、舜所知,不饮洗耳之水,超越青云之上,德逾巢、许之右。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声而声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轻宠傲俗,乃百世之师也。其辞曰:‘邈玄德,膺懿资,弘圣典,研道机。彪童蒙,作世师,辞皇命,确不移。亚鸿崖,超由、夷,垂英声,扬景晖。’”[1](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57.《全后汉文》卷56《征士法高卿碑》与之基本一致,只“鸿崖”作“洪崖”(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第783页下栏.该碑已不存,只保留了部分碑文。
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东汉南郡太守法雄之子,蜀汉尚书令、蜀郡太守法正祖父,《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了法真的生平,其曰:
“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惧然,不敢复言。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2]田弱.(西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下).法真.作“田羽”.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第 46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21页下;全后汉文(卷 63).荐法真.亦作“田羽”.(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817 页上栏;(汉)赵岐撰.(晋)挚虞注.(清)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决录(卷1)所引《高士传》作“田翼”.三辅决录.三秦出版社,17;(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52)汉纪.44“顺帝永和二年”.亦作“扶风田弱”.中华书局,1956.1680;(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 884).总录部·荐举》曰:“田弱,弱一作羽。”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10473页下栏.按:综合以上史料来看,笔者认为,“田羽”的可能性较大,《高士传》的成书最早(《三辅决录》虽成书更早,但因早已失传,现今见到的版本实为后世所辑,故可靠性稍显不足),“田弱”或“田翼”可能都是传抄中出现讹误所致。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衮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征。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1]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中华书局,1965.《高士传》所载与《逸民传》略同.(P2774)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注引《三辅决录注》的记载与之类似,其曰:
“(法)真字高卿,少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前后征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2]三国志(卷 37).蜀书·法正传.注引《三辅决录注》.中华书局,1982.(P957)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了解到法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关西大儒,前往求学者达数百人,州郡、公府多次征辟,甚至皇帝亲自征召,法真均不为所动,坚持隐居,友人郭正便与一些朋友共同刻石立碑赞颂法真这种高洁超然的品格。汉灵帝中平五年(188),89岁高龄的法真与世长辞。与《逸民传》不同的是,《三辅决录注》中并未言明“刊石”,只是说“美之”,但据碑文可知,应该是有刻石立碑的行为,不然也不会有碑文一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三辅决录注》本身比较简略,其次就是裴松之在作注时有所节略,这种转引古书不直接引述原文的现象在古代非常普遍。
从文献记载的顺序来看,众人刊石在前,法真去世在后,那么这块碑似乎应该是法真在世之时所刻,可是在当时为活人立碑的现象本就少见,而且即便有,碑主也往往是当今帝王(如秦始皇东巡刻石)或者理政清明的地方官吏(如《张迁碑》《曹全碑》等),这样的碑被称之为功德碑,而为一位从未出仕过、尚在人世的隐士立碑在当时似乎没有这样的先例。难道说法真去世在前,众人立碑在后?文献记载有问题?那么《征士法高卿碑》的作者——后汉胡广又是何时去世的呢?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胡广卒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而法真是在16年后的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方才去世,这就让人很匪夷所思,明明胡广先于法真去世,那么他又是如何为法真撰写碑文的呢?另外,从古至今,不少学者都将“玄德先生”作为法真的谥号,但如若此碑确为法真生前所立,而谥号须人死后才会确立,那么就不应当将其当作谥号来看待。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拟从胡广与法真的关系、东汉碑刻的特点与种类等方面对《征士法高卿碑》的性质进行初步探究,并对“玄德先生”是否为法真谥号的问题作出分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二、《征士法高卿碑》确为胡广所作
对于《征士法高卿碑》撰者胡广先于碑主法真去世的问题,陈君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在《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一书中写道:“胡广卒年在法真前,不及为法真撰碑。此碑盖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3]陈君.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P388)陈君的解释看似有一定道理,然而,无论是《艺文类聚》还是《全后汉文》却均将《征士法高卿碑》的作者定为后汉胡广,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我们认为不宜轻易否定传世典籍的记载。
下面我们先从胡广与碑主法真的关系入手,来分析胡广作碑文的可能性。《后汉书·胡广传》载: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助求其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1]后汉书(卷 44).胡广传.中华书局,1962.(P1504-1505)
关于法真推举胡广一事,《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注引《三辅决录注》的记载更为详尽,其曰:
“初,(法)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观朝吏会。会者数百人,真于窗中窥其与父语。毕,问真‘孰贤?’真曰:‘曹掾胡广有公卿之量。’其后广果历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2]三国志(卷 37).蜀书·法正传.注引《三辅决录注》.中华书局,1982.(P957)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我们得知胡广当时只是郡属散吏,而法真的父亲法雄是南郡太守,法真则是一名尚未加冠的孩童。在一次前往探望父亲的偶然机会中,法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父亲推荐了胡广,法雄也同意了法真的看法,举胡广为孝廉,推举他去京师试考。胡广到京师后,受到汉安帝的特别重视,“以广为天下第一”,很短的时间内便官居要职,之后更是青云直上,做到了大司农、司徒、太尉、太常和太傅,“果历九卿三公之位”,世人皆叹服法真能够识人。
当然,客观来讲,一位尚未加冠、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本身是很难挑选出合适的人才的,这段记载未免有夸张之嫌,但胡广的发迹与法雄等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应属事实。如果不是法雄的推举,胡广的仕途未必能够如此顺畅,所以胡广对自己的举主法雄以及其子法真的确是怀有感激之情的,为法真作碑文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另外,朝廷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征召法真,固然是因其深厚的才学和高名,但已经居庙堂之高的公卿胡广很可能也曾向朝廷推举过他,所以从二人关系来看,胡广为法真撰写碑文、称颂其名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我们再从年龄上推算胡广作碑文的可能性以及二人卒年记载的可靠性。据《后汉书》记载,胡广生于公元91年,卒于公元172年,享年82岁;法真生于公元100年,卒于公元188年,享年89岁。从年龄上来推断,二者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胡广比法真稍大,存在作碑文的可能性。再根据《后汉书·法雄传》的记载,我们得知法雄任南郡太守的时间大约在汉安帝元初元年(114)至元初中(117)[3]后汉书(卷 38).法雄传.中华书局,1962.(P1276-1278),其时法真15至18岁间,男子二十弱冠,符合“年未弱冠”的记载,而此时胡广为24至28岁间,也与“为郡吏”相合,说明《后汉书》关于二人卒年的记载也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东汉胡广与《征士法高卿碑》的碑主法真不仅有过交集,而且,胡广的脱颖而出与法雄的极力推举、法真的慧眼识才又有着重要的关联,史书上关于二人年龄的记载也基本符合情理。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征士法高卿碑》应该就是东汉曾任太傅的胡广所作,碑文所作时间亦不会迟于公元172年,此碑应为法真在世时所立,而非墓碑,陈君“盖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的说法没有史料依据,可信度不高。
三、《征士法高卿碑》应属颂德碑
既然《征士法高卿碑》不属于墓碑,那么我们再来从东汉碑刻的特点来看该碑的性质。根据张晓旭《秦汉碑刻研究(下篇)》的考证,东汉碑刻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东汉是中国古代碑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桓、灵年间和熹平、光和年间为东汉碑刻的最盛期。
(二)东汉碑刻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数量众多,……主要有纪功碑刻、墓葬碑刻(含地下和地面)、儒学碑刻、交通碑刻、寺庙碑刻、官约民类碑刻等六大类。……
(四)碑文书写格式固定,特别是墓碑碑文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一段散文体文辞,开头交代‘君讳……’然后再介绍碑主生年、籍贯及其生平事迹。结束后为四字韵语(后一部分),其开头由‘其词曰’或‘其辞曰’‘其铭曰’‘乱曰’‘颂曰’连接,然后用韵语形式高度概括前面散文体文辞所述内容。……”[1]张晓旭.秦汉碑刻研究(下篇).南方文物,2000,(2).(P94)
汉桓帝和汉灵帝在位期间大约为公元146年至公元189年,根据《逸民传》的记载,我们得知郭正等人为法真立碑的时间是在汉顺帝西巡,四征法真不到之后,而汉顺帝的在位时间即在公元125至144年间,所以《征士法高卿碑》的刊立时间基本与东汉碑刻高峰期相重合。
而从立碑的目的来看,就是为了“颂之”,颂扬法真这种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高洁精神,从碑刻分类的角度来看,它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的功德碑。历史上比较典型的功德碑都是为了宣扬碑主的功绩,像著名的秦始皇东巡石刻、封燕然山铭、张迁碑、曹全碑等,这些碑的碑主或是古代帝王,或是地方官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功绩,但像法真这种从未做过官的隐士似乎还真没有生前立碑的先例。
虽然为在世隐士立碑的现象并不多见,但当时还是有一些为了宣扬某种精神或风尚而为活人立碑的例子,像《都乡孝子严举碑》是为了彰显孝义,《赵娥碑》是为了表称节义。《隶续》卷11收录了《严举碑》的碑文,其曰:
“都乡都里孝子严君,父讳□,字子顺。结发治身,非礼不行。□郡入州,居□□孝,位至蕃车,产生三女,绝嗣,无男,愤然。□恐□户孤寒,宗族□□,收集孤□□以作后。礼,为人后则为人子,举□□□□□□□□□□,尤勤和颜□以□终制□行□,忉怛愤泣,憔悴消躬。□乱不□,不□□□□□□母老□□□请,然后为稽,然后行□□□□□□□□□□□孝顺行则闺门□积行慎心。德刑州里,莫不称□,歌□□慈,仁其□□。前世官贤有秩,长思褒大其义,造□□□□□□□,□善慕类君子之伦,共立碑表,勒石述叹,以章其芬。颂曰:‘□□□□,炎翟(曜)隆恭。徂德配神,广彼明察。化及黔首,施流润□,……。’延熹七年五月辛未朔十一日辛巳,临江长恺丞杜谓都□言:‘孝子严举,为父行丧,服制逾礼,追思慕义。□表门闾,有书贤明。宰卿□应,风生是以。天□仁人,孝弟之至,通洞神祗,盖淑□赏则庶民劝。今□书到,□□勉加劳来,以究言如诏书。’”[2](宋)洪适.隶续(卷11).都乡孝子严举碑.隶释·隶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P394)
从这些断断续续的碑文中,我们大概得知,严举是过继给别人为后的,但他对待自己的养父母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恭顺,“和颜奉亲,送终尽孝,母氏年老,事继若真,德刑州里。”[2](P394)为了宣扬表彰严举这种孝义的行为,“褒大其义”,县乡官员特意上书,为其刊石立碑,显其门闾,“以章其芬”。值得注意的是,该碑刊刻的时间是汉桓帝延熹七年,即公元164年,亦在东汉立碑高峰期,与《征士法高卿碑》刊立时间相当接近。
《三国志》卷18《庞淯传》记载了赵娥舍身为父报仇的义举,其曰:
“初,(庞)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帷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会赦得免,州郡叹贵,刊石表闾。”[3]三国志(卷 16).庞淯传.中华书局,1982.(P548)注引皇甫谧《列女传》曰:“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追述娥亲,为其作《传》。”[1]三国志(卷16).庞淯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中华书局,1982.(P549)
无论《严举碑》或者《赵娥碑》,都是人们为了彰显某种节义的精神和品格而在碑主在世时所刻,这点与我们讨论的《征士法高卿碑》是一致的,虽然这些碑主未曾出仕,没有什么伟大的功绩,但他们身上这种精神都是值得世人学习的,所以人们才会在生前为其立碑,“褒大其义”,这种颂扬生者品德精神的石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颂德碑”。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将这些表彰孝子、节妇、烈士等封建道德典范的石碑也归入功德碑[2]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中华书局,2019.(P141-142)。
通过对比,我们还发现,现存的《征士法高卿碑》首尾可能存在残缺的情况,按照碑刻的体例,一般都在开头介绍碑主姓名、籍贯等,末尾注明刊立的时间、人物等一系列信息。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碑文这些都没有,只保留了中间一部分正文。不过颂德碑与墓碑的一大区别便是前者重在突出碑主某些需要突出的事迹,而后者则会详细记载碑主的生平、历任官职等详细信息,大部分还会刻上卒年日期等,这些都是区别于颂德碑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征士法高卿碑》为墓碑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碑文撰者胡广和碑主法真的关系考虑,还是从东汉碑刻的特点和立碑的目的来看,《征士法高卿碑》应该是法真友人郭正等人于法真在世时为其刊立,碑文由胡广撰写,立碑目的在于颂扬法真淡泊名利、高洁脱俗的精神,该碑与《都乡孝子严举碑》《赵娥碑》等应同属颂德碑,而非墓碑。
四、“玄德先生”非谥号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玄德先生”是否为法真谥号的问题。古今不少学者都认为“玄德先生”就是法真的谥号,如南宋著名金石学家洪适云:“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词,谥之(指娄寿)曰元儒先生,犹陈寔之文范,法真之元(本为‘玄’,因避讳改为‘元’)德也。《隶释》又有《忠惠父鲁峻碑》,亦非谥于朝者。群下私相谥,非古也。未(末)流之弊,故更相标榜,‘三君’‘八顾’之目,纷然而奇祸作矣。”[3](宋)洪适撰.隶释(卷9).玄儒先生娄寿碑.隶释·隶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P103)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于张璠《后汉纪·桓帝纪》处注曰:“东汉中期起,门阀世族开始形成。由于名节道德观的确立,以及荣辱与共的政治利害关系,门生故吏对举主座师,莫不竭诚相报,虽死不辞。其形式繁杂,私谥即其一。据文献及汉碑所载,此风盛行于东汉,有案可查者计十六人:……法真谥玄德先生,见《蜀志·法正传》注引《三辅决录》。以上诸人之谥,《水经注》《艺文类聚》亦有所载。当时荀爽亦有所讥,而此风愈炽。”[4]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701-702)
沈刚《东汉的私谥问题》对东汉的私谥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同样也将“玄德先生”视为法真谥号[5]沈刚.东汉的私谥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P93-101)。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征士法高卿碑》是在法真生前所立的颂德碑,那么紧接着“刊石颂之”的“号曰‘玄德先生’”应该也是在当时为之,而非死后再行议定。以上多位士人虽然都是死后被后人谥为某某先生,史籍中“号曰某某先生”也多发生在士人去世之后,但由于有《张迁碑》《曹全碑》《赵娥碑》等生前碑的存在,且《征士法高卿碑》的确也是在法真生前所立,“号为玄德先生”一句又在“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之前,故“玄德先生”为法真生前尊称的可能性非常大。
方北辰先生也认为“玄德先生”不是谥号,而是尊称,他在《〈三国志·先主传〉注译札记》一文中写道:“法真品德高尚,不慕名利,终身隐居不仕,在老年时,被仰慕者尊称为‘玄德先生’。”[1]方北辰《三国志·先主传》注译札记.载于《一个成都学者的精彩三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P123)许嘉璐先生主编的《后汉书全译》同样将“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一句译为:“于是一同刻石歌颂他,称他为玄德先生。”[2]许嘉璐主编.后汉书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P1676)
这种在当世之时就被称为某某先生的也大有人在。《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云:“太守谒焕,先为诸生,从(廖)扶学,后临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年八十,终于家。”[3]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P2720)《魏书》卷84《儒林列传》曰:“(常)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4]魏书(卷 84).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74.(P1849)《南史》卷76《隐逸列传》云:“(沈麟)居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5]南史(卷 76).隐逸列传.中华书局,1975.(P1890)
既然《征士法高卿碑》非为墓碑,“号为玄德先生”一句又在“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之前,典籍史料中也有生前尊称某人为先生的事例,那么,我们认为,据此应该可以认定“玄德先生”并非法真谥号,而是时人对他的尊称。
五、结语
东汉时期尤其是桓帝、灵帝在位期间是中国古代碑刻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当时的社会,立碑刻石成风,不仅为死者,亦为生者刻碑。虽然绝大多数为生者立碑者皆为功德碑,但也有为颂扬节操的颂德碑,如《都乡孝子严举碑》《征士法高卿碑》等。《征士法高卿碑》的碑主法真博学多才,教授子弟,淡泊名利,不事功名,友人郭正等有感于他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超凡脱俗的精神,便于生前为其刻石立碑,高大其义。曾受法雄、法真父子推举、位居公卿的胡广亲自为其撰写碑文。立碑之后若干年,法真才终老于家,比胡广去世晚了16年,这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征士法高卿碑》并非墓碑,而应属颂德碑,“玄德先生”亦非法真谥号,而是当时人们对他的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