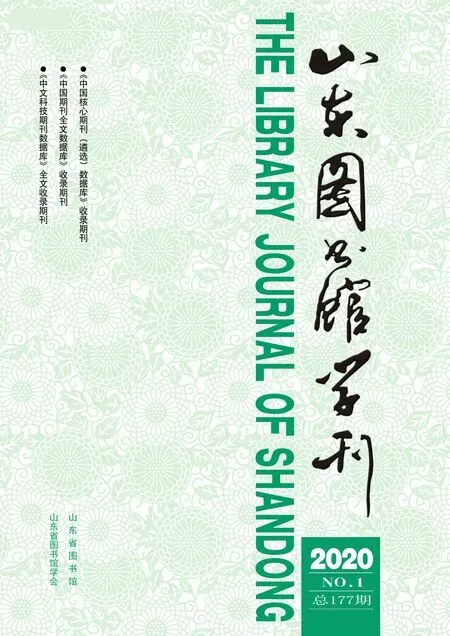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评介
钱 昆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32)
2016年8月,吴则虞先生的《续藏书纪事诗》(全二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至此,由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始,历经近110余年的时间,“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类的完整著述全部付梓,在研究古今私家藏书的发展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中有为伦明做诗传,其中诗言:
此才晚出惜沉沦,赤脚拖鞋垫角巾。
我亦有诗三百首,青萍无处觅斯人。”[1]
1 伦明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1.1 伦明其人
伦明(1878-1943),字哲如,亦作哲儒、喆儒、节予,广东东莞人,出身重视文化教育的伦氏家族。少年时期即好藏书,及至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已经逐渐积累起丰富的书藏经验,在京亦开设“通学斋”促进书藏,于藏书研究、藏书实践等方面皆有所得。伦明以“续书楼”主人自居,其藏书不仅能供其读书治学以自用,同时还能惠及友人并泽被后世(伦明去世后,其大部分藏书归公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伦明丰富的藏书经验也为其日后撰写《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等相关学术工作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其以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古旧书业经营家等身份被后人所知。
1.2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由来
“藏书纪事诗”这种文体肇始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后继者有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和宋路霞合著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在五部续藏书纪事诗的著作中,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伦明作《辛亥以来藏纪事诗》,原因有三:(一)清代藏书家人数在叶诗中辑录不足:伦明读叶诗,认为清代藏书家只纪329人明显不够,于是增益数十人,“辑录粗就,尚待润色,依例叶书。大抵据志乘说部,别集信而有征者”[2];(二)为近人立传传世:伦明认为晚清以来近人远不一世,耳目接触其人其事,因近在当前而不烦摭拾,但及今不述则久而忘之;(三)社会巨变下的文化传承:伦明认为20余年(指辛亥革命前后)来社会变化甚剧,天灾、时势、人祸皆可使藏家藏书散佚。随着新式学校与图书馆的建立,需旧书者少而新书者多,伦明认为“以浅俗白话,代粹美之文学;用新式符号,读深奥之古书。斯则学术之患、世道之忧。所系尤巨。知而不述,人且忽之。”[2]可见伦明主要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也是为了自己续修《四库全书》的宏愿,编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2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内容总揽
伦明《辛诗》所纪,除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通行本之外,还要参考未刊的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纪事诗手稿,合二为一,才能说是足本,或者说是接近足本的伦明《辛诗》。经笔者统计整理后,得出结果如下:
(1)已刊:共155篇,涉及藏书家154篇178人(正传150人,附传28人),藏书机构1家即涵芬楼;
(2)未刊:共44篇,涉及藏书家13篇19人,藏书机构10篇13家,藏书事件等11篇,其中有诗无传者10篇(没有题名,不知何人或何事)。
可见,伦明《辛诗》的足本如果以藏书家和藏书机构算的话,应该是藏书家167篇191人,藏书机构11篇14家(藏书事件11篇和有诗无传者10篇暂不计算在内)。纵观伦明《辛诗》所纪藏家内容,主要从以下九个方面有所体现,为后世研究私家藏书保留了珍贵资料。
2.1 藏家的传记资料
伦明《辛诗》中通过藏家姓名(没有字号)、诗、传三个部分为我们保留了一些近代藏书家的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后世增补藏书家传记资料的主要来源。如伦明开篇即纪叶昌炽,表达了对叶氏的尊敬和褒扬之情:
叶昌炽
买书难遇盲书贾,管教仍然老教官。
芸香浓处多吾辈,广觅同心叙古观。
叶鞠裳学政昌炽,精目录金石之学,所著《藏书纪事诗》《语石》《邠州石室录》《诗文集》,俱梓行。近始见《缘督庐日记抄》,凡平生所得及所见之书及金石,俱详载其中,晚岁居上海,所见古书尤博。……(此处省略“盲书贾”和“老教官”的典故说明)。余尝补君《纪事诗》数十人,今又拟《辛亥以来纪事诗》若干人,识陋才拙,狗尾之续,渐恧而矣。[2]
以上是伦明所写关于叶昌炽的诗传部分,虽然字数不多,但包含的信息量不少,对于叶氏的字号、官职、著述、治学特色、访书情形等方面都做了论述。其他藏家亦按此体例撰著。
2.2 凡属于书者无所不纪
在揭示藏书处所方面,因伦明并非“但纪私家”,而是“凡属于书者无所不纪”[2]。《辛诗》中所纪藏书家并非每一位都有藏书楼,伦明重在论述“书之聚散”,因此对于藏书处所并未刻意查考并全部揭示,如上例叶昌炽条即没有说明叶氏的藏书处所,当然也有部分藏家的藏书处所经由伦明在传的部分予以说明,如条目二范氏天一阁、条目六杨以增海源阁、条目七瞿镛铁琴铜剑楼、条目八丁丙八千卷楼、条目一○丁日昌持静斋,等等。这些条目都是伦明在传的部分直接写出标明,但有些条目则需要通过传中对所纪藏家所编书目的名称,推敲后才能得知,如条目四三沈曾植,其传的部分“……有《海日楼》藏书目……”,据此推测沈氏的藏书处所为“海日楼”[2],类似的条目还有六○刘承幹所刻《嘉业堂》、七六梁启超编有《饮冰室书目》,等等。另外有些条目则是没有提及藏书处所问题,如条目一六孙诒让、一七萧穆、一八谭献、一九平步青、五九刘体智、一○九张次溪、一一○陈融、一一五桂浩亭等,这种情况要么是资料难得故不得而知,要么是这些藏家本身就没有藏书楼,抑或本身就没有给自己的藏书室起个雅号。这也反映了近代藏书风气的变迁,随着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私人藏书家为自己构楼贮书的做法已大为改变。
2.3 藏书治学特色
中国古代藏书家历来有“读书治学以自用”的传统,因此私家藏书基本与自己的读书治学志趣相契合,伦明在《辛诗》里对所纪藏家的藏书、治学特色亦有表述。其中有定性描述直接总结的,如条目一叶昌炽“精目录金石之学……凡平生所得及所见之书及金石,俱详载其中……”[2],条目二四李文田“……素究《元史》地理,好搜明季野史。其未刊稿,以《元史地名考》最巨……”[2],条目四一缪荃孙“……为近代大目录学家……”[2],条目五二夏孙桐“……亦谙目录之学,精于医……”[2],条目八○王国维“十余年来,故都言国学者,靡不曰王静安……君读书最精细,凡过目者,多精密校本,所纠讹文阐新义,多谛当。……”[2],等等。
亦有定量列举藏家著述及收藏,以体现其藏书、治学特色的,如条目一○九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书多罕见。要目有:……《燕兰小谱》五卷……《日下看花记》……《片羽集》……(此处省略三十余种)”[2],条目一一五桂浩亭“……兼治群经,所著《易大义补》《禹贡川泽考》《毛诗释地》……《周礼今释》……《孝经集解》……俱已梓行。其有目无书者,……见《国氏儒林传》者,……此外不涉于经学者又有八种。”[2]条目一四○冼玉清“……现教授岭南大学……收粤人著作甚备。撰有《粤人著述过眼录》……又撰《管仲姬书画考》,谓仲姬画,十之九出伪作,其愈工者愈伪……又好游,尝居故都一年……撰有《万里孤征记》”[2],等等。
2.4 藏书管理
2.4.1 世代递守被盗
明代范钦的天一阁藏书因其保管严格、秘不示人而世代递守,至今逾400年,成为我国私人藏书历史上最为悠久的藏书楼,期间只有十余位学者曾登阁阅书,如黄宗羲、赵万里等。伦明在《辛诗》条目二中并未着墨阐述天一阁之所以能递守的原因,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是阐述黄宗羲登楼后所抄的书目,凡书四千零九十四种,此为当时关于天一阁藏书最多的记载,其后列举他人所抄、所编书目皆是于所藏越来越少,伦明因而在小传中记载了天一阁藏书被盗的事实,被盗后有贩卖现象,伦明转缪筱珊语“忽闻阁书大批出售……意其子孙居然肯卖”[2]之语,体现了其他藏家对于天一阁藏书居然在市面上能够出售的惊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一阁藏书历经数代管理严格的传统。只可惜事易时移,时局人祸所致,天一阁藏书被盗亦是事实,伦明在此也为我们补充了天一阁藏书的史料,弥足珍贵。
2.4.2 藏书公开被盗
古代藏书家虽然大多“读书治学以自用”,但也有少数藏书家对自己所藏予以公开,如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伦明在《辛诗》条目七瞿镛传中转引瞿氏宗人瞿冕垓的言论,大意是瞿镛开放书藏供众阅览,而且还供造访者膳食,结果藏书渐失,推测被不肖者盗走,而典守者亦不自觉。于是关闭书楼,此后再无览书者[2]。
2.4.3 子孙无志于书藏
晚清民国时期时局骤变,天灾、时事、人祸皆可使藏家书藏受损,或多或少的发生散佚,即使如范氏、席氏诸人能世代递守者亦不例外。亦有子孙不能递守者,伦明《辛诗》条目四谭莹之孙谭祖任,擅长填词、喜书画、善鉴别,但是对于家中藏书无心管理,或置于旧宅,或弃于上任途中,或请书店代为整理,最后因其无后,遂弃于破屋中,被某书店以百金购得,转手即卖千金,可悲可叹!唯其在北京设酒肆所创“谭家菜”闻名一时,冠绝北京[2]。
2.4.4 近代藏书家应吸取之先进经验
伦明在《辛诗》条目一三三袁同礼传的部分阐述了袁氏藏书管理的先进经验,认为“此三事,藏书家皆当遵用者”[2],一是编目不以经史子集分,而以笔画多少分,诸要书各附索引,亦有合若干种书,共作一索引者,于检甚便;二是记书目于散片上,可以随时更调增损;三是书帙包上下四周,不似旧式之空其上下,书本大小长短不同,而帙则同,插架有整齐划一之观。袁同礼从欧洲传图书馆学回国,于藏书管理自有其一套理论,他的藏书管理经验被伦明所推崇,认为其他藏家亦应学习使用。
以上仅举伦明《辛诗》数例说明近代藏家藏书管理之状况,即使当时部分藏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但也抵挡不住因天灾、时事、人祸等原因所造成的散佚命运。藏书或辗转流传不知所踪,或归于某位私家之手,最好的归宿莫过归公于图书馆泽被后世,这也是很多近代藏书家的夙愿。
2.5 书籍散佚情况
伦明《辛诗》所纪大部分藏书家皆晚清民国时期人物,且多与伦明为同时之人,因此伦明在1935年连载发表《辛诗》时,有些藏家的藏书已开始散出或已散尽,如条目五三陈毅、七三麟庆、九三王鸿甫、一○三章士钊、一一一盛景睿、一一七辛仿苏、一四四谭笃生等,此种情形伦明或于散书时偶有所得,或见于他处少数几种,整体来看皆难于寻其最后踪迹;此外还有藏家去世后书始散,伦明所闻或卖给私家或公家,或抵押给书店,但最后是否成行皆未可知,如条目五四李盛铎、七○吴怀清等;还有毁于战火者,如一四一涵芬楼(1)关于涵芬楼藏书归宿,伦明发表《辛诗》之时,认为涵芬楼的藏书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被日军炸毁于东方图书馆中,确实有一部分涵芬楼的方志之书与东方图书馆藏书一起毁掉了,但是还有部分涵芬楼的藏书此前被保存在银行里,没有遭受战火波及,幸存下来的书籍被编成《涵芬楼烬余书录》,这批书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还有藏书散出之时为另一私家购藏整体或部分,但另一私家之藏书后也发生散佚,辗转流传,大多不知所终。笔者曾对伦明《辛诗》中查有可考的37条目涉及42位藏家书藏归宿进行统计,限篇幅所限,仅举几例说明,如觐县范氏天一阁藏书,即浙江宁波天一阁;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归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李盛铎的古欣阁、蜚英馆、凡将阁诸处藏书,多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购藏,另一部分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掠去;刘承幹的嘉业堂藏书,因抗战时期家道中落而售与各公共图书馆,余存之书捐给浙江省图书馆;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归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邓之诚的五石斋藏书,卒后捐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等。
通过伦明《辛诗》,既可以了解辛亥前后尤其是辛亥以来私家藏书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了解重要典籍的辗转流传及最终归宿,使后人研究治学有的放矢,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史料。
2.6 藏书史实的辩证
2.6.1 《玉台新咏考异本》的作者实为纪昀
伦明《辛诗》条目三纪昀,传中言伦明得《河间纪氏家集》原写本两册、文达(纪昀谥号)《玉台新咏考异本》手稿本及其父容舒《杜律详解》传录本,在《四库》中《玉台》著录容舒名,但是伦明所得手稿本则是文达自著。伦明“证之后序,刻本题纪容舒序,稿本题纪昀序。刻本‘余自姚安归来’句,稿本姚安作栾阳二字外,文全同。因思是书所引诸异本,非容舒所能见,文达兹举,殆善则归亲之意耶?”[2]可见伦明通过证书之后序和书中内容所引异本在时间上并非容舒所能见的依据,推测《玉台》实为纪昀所作,刻本在《四库》中之所以冠其父容舒名,有可能是纪昀善意之归誉。
2.6.2 丁日昌强取豪夺之事为伪
伦明《辛诗》条目九丁日昌,传中记载“江南乱后,故家书尽出,中丞留意收拾,遂成巨观。相传有豪夺之事,盖陆存斋诬之。存斋欲据郁氏宜稼堂书,及自闽归,其精椠已为中丞所得,大嗛之,因造无稽之言。蒋香生、俞荫甫俱有辨,不赘述”[2]。另王謇《续补诗》、徐信符《广东诗》皆有争辩且持伦论,且因伦明与丁日昌子惠康有所交游,关于丁日昌强取豪夺之事为伪的结论应该可信。
2.6.3 辨疑《书目答问》作者
伦明《辛诗》条目四一缪荃孙,伦明提出张之洞《书目答问》乃缪荃孙代作的观点,但不是特别肯定,尚存疑虑。伦明据年谱得出缪荃孙如作此书,当年其应为二十四岁之时,且缪氏早年从宦川滇,地域偏僻又乏师承,学识积累不能渊博至此,伦明因此疑之。后又引陈慈首云:“是书盖江阴一老贡生所作。先生得其稿,又与张之洞共参酌成者。”[2]伦明认为陈氏曾令江阴,所言或有据。因此伦明提出此说,有待后人证也。
2.7 近代藏书风气的变迁
中国古代尤其是晚清以前,藏书家基本上都是贵远贱今,以搜集、珍藏、鉴赏和利用为主要特征,到了近代藏书风气有所改变,多表现为悉心收集、建立专藏,为学术研究服务,如山经地志、俗文曲部、谱牒笔记等以前藏家不太重视的子、史、集部僻书,近代藏家多有收藏。伦明本人亦重视清人文集的收藏,《辛诗》条目四五王绶珊,伦明在传中言未识王氏其人,但有杜国盛者曾撰《九峰旧庐藏书记略》,言王氏有宋本百余种、明本千余种、方志两千八百零一部,占全国方志总数的90%。《辛诗》条目一○九张次溪专收梨园史料,条目一一○陈融广收近代诗集至千数百家,条目一二八马叙伦多收近代人词集至数百册,条目一四○冼玉清收粤人著作甚备,等等。
2.8 为书贾立传
中国古代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同时也有“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理念,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书贾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更是不被人重视,即使有些书贾不乏书业经验与广博学识。因此叶昌炽曾在《藏书纪事诗》中为书贾立传,伦明在《辛诗》中继之,“余交游中,书贾居半,纪不胜纪,则摘其可称者数人著之”[2]。伦明虽说著录数人,但其实只有5位而已,包括谭笃生、何厚甫、孙耀卿、王晋卿、席玉照(席氏扫叶山房),这五位中既有跨越明清两朝、世代刻书、近世因机械印刷的传入而衰落的席氏扫叶山房,也有与伦明交游甚密且有着丰富书业经验和版本目录学识的何厚甫、孙耀卿、王晋卿三人,更有书业虽大且熟识版本却好以赝本欺人兼盗内府书的不良书贾谭笃生。在这5位书贾中,伦明对孙耀卿和王晋卿二人尤为推崇。
2.9 其他
伦明《辛诗》所纪藏家身份众多,其中属于官宦之家的不少,这也是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这些世家子弟大部分自己也能考取功名并有自己的藏书治学志趣,但也有少数出生官宦之家但自己却不能考取功名,最后只能卖文自给,如沈宗畸,其所藏书多清代笔记及野史资料,逝后藏书尽散[2];还有袁世凯之次子袁克文,所藏书皆钤有“皇二子”印章,多为内府物,以巨资购书画、金石、古钱币,所藏宋版书达200种。袁世凯死后,袁克文藏书星散大半,所谓聚之也快散之也快[2];还有富商之子辛仿苏,因所得遗产甚富,遂事收藏,曾携十数万金游京师,恣意挥霍,旁及字画古书,使得京师书业价格大涨,民国后居北京,因组建戏班不幸破产,藏书散尽,辛氏抑郁而终,可悲可叹[2]。还有一些身份敏感的藏家,如梁鸿志、王叔鲁、张岱杉、李赞侯诸人,因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扶持的各种伪政府中任要职而被后世定为“汉奸”,王叔鲁在抗战胜利后被捕并于狱中畏罪自杀,梁鸿志于1946年被枪决,张岱杉1937年病逝,李赞侯1968年卒于上海(或因只担任文职,即汪伪政府上海《新闻报》社长)。此处所列四人虽藏书各有志趣,但因政治问题,不仅书藏不知何处寻踪,自身也大多未得善果。
3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评价
3.1 承前启后之功
“纪事诗体藏书家传”[3]这种文体肇始于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属于“发凡起例”[4]之作,该书纪录了五代以后直至清末739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史实。伦明在此基础上作《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纪录范围以辛亥以来藏家的藏书史实为主,据该书足本统计共211家(197位私人藏书家,14个藏书机构),与叶《诗》少有重复,可以说是对叶《诗》在纪录藏家内容上的补充和延续。伦明《辛诗》继承叶《诗》“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著述体例,先诗后传,开篇首例即是叶昌炽诗传,体现出对叶氏的敬重。在传的写作手法上采用了“笔记体”而非叶氏“辑录体”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叶氏广引资料时偶有错误的问题。又因伦明与所纪之人大部分是同时代之人,且多交游,因此在各位藏家小传的部分,其写作笔法显得简明扼要、生动,可读性较强。叶《诗》对后世影响深远,伦明在其影响下作《辛诗》即是有力证明,而伦《辛诗》在诸续补之作中亦有启示参考之重要作用,因此“倘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为书林《史记》,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为书林之《汉书》。叶著为书林通史,而伦著则为断代之史。”[5]
伦《辛诗》虽然继承了叶《诗》“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著述体例,但在藏家小传的具体写法上采用了“笔记体”而非叶氏的“辑录体”,这种“笔记体”的写法对徐信符、王謇、周退密(宋路霞)三家有所启示,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和周、宋二人合著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皆与伦明一样采用“笔记体”的形式。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言“拙诗之作,盖由先生启之也。”[6]此处的“先生”,即指伦明。另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亦于诗下附传,沿袭叶著、伦著之体例,然其传记不列史料出处,且如曾钊、潘仕成等人各记诗两首,广雅书局则有三首,似更近伦著。”[7]
在五种续补《藏书纪事诗》著作中,只有吴则虞的《续藏书纪事诗》于藏家小传部分,仍然采用叶氏“辑录体”的形式,是后世续补之作中最“像”叶《诗》的,但也正因为其出版时间较晚,同时小传部分又是“辑录”的形式,所以前边几家,尤其是伦明的《辛诗》,成为其广泛征引的来源之一。据笔者粗略统计,吴《续诗》中大概有80余处援引伦《辛诗》,标为“伦明《诗》注:……”。可见伦明《辛诗》既对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有所继承与发展,同时也对其他后续四家有启示作用,这种承前其后的意义尤为巨大,因此才有以叶《诗》比《史记》,以伦《诗》比《汉书》之论[5]。
3.2 “笔记体”的局限性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采用“辑录体”的形式来写藏家的传记,而伦明《辛诗》采用“笔记体”的形式写藏家传记,二者各有特色,前者于辑录资料方面旁征博引,便于后人查考;后者则篇幅较短、语言简练、随笔而记,有真实之感。但同时这两种写法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叶《诗》援引资料众多,除了偶有引用错误之外,也“缺乏融会贯通的气魄”[8],这就好比翻看蝴蝶装,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时间长了难免使读者心生厌烦,总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能通透之感;伦明的“笔记体”则犹如包背装,虽然阅读容易一目了然,但也正是因为其简明扼要,有些信息使后世读者难免惑于寻根觅源之难。
因伦明“胸中之目录,十倍于眼中之目录”[1],又多年经营通学斋书店,故而熟识版本,因此在传的部分言简意赅,或许认为他人皆有同感。但版本目录之学并非每人都有其造诣,其他续补四家估计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传的部分都有所扩充,进一步丰富了藏家史料。
“笔记体”的局限性还体现在伦明的某些研究结论中,即伦明在藏家小传部分偶有语焉不详或稍显武断之结论,如伦明《辛诗》条目六五卢靖,伦明在传中言卢氏自印《湖北丛书》,经笔者查考,该书实为清赵尚辅辑,据杨琥增补资料,卢靖曾先后辑刊有《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湖北先正遗书》等,因此伦明所言《湖北丛书》,其实应为《湖北先正遗书》。除此之外关于《书目答问》的著者是缪荃孙的言论,似乎也有些武断,有待后来者进一步考证。
3.3 客观对待批判之语
伦明《辛诗》在一系列续补之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地位与影响。但在某些方面也有人持批判的态度,如雷梦水在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时曾说“作者由于受历史局限,所录人物,亦有汉奸等辈厕杂其间”[9],这里说的“汉奸等辈”,包括反对戊戌变法、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湖南土豪叶德辉,复辟帝制的军阀张勋,还有参与日本扶持的各级伪政府的人员如梁鸿志、王叔鲁、张岱杉、李赞侯诸人。其次,由于伦明《辛诗》中所纪粤人藏书家占有最大的比重,因此曾召来“不无阿附乡曲之见”[10]的责备。最后,《辛诗》中所纪藏家叶恭绰也曾有批评之语:“此册所纪不少遗闻轶事,然有传闻失实者,又时杂以恩怨,未尽足据……特乡邦文献得此著录,固亦佳事”[11]。
对此,笔者认为应该持有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伦明所纪之人,如伦明纪广东藏家最多,是因为伦明本身抱有乡邦之情,同时又受其自身居游关系的影响,所纪粤人最多无可厚非。另外从伦明所纪粤人藏书家的内容上,言其“阿附”未免也有些失实,见《辛诗》四八条王存善,伦明在其诗传中分析了粤人藏书风气的兴起乃源于粤吏多好收藏,并列举了一批粤吏藏家,最后表明“勿问其政声何似,而雅尚殊足嘉也”[2],可见伦明纪录这些藏家是抛开政治影响,只谈藏书事迹的。另七六梁启超一条,伦明虽然尊重梁启超并敬佩他的学识,但在这一条的传中亦纪录了他与梁启超就《古文尚书》内容进行辩论的事情,最后梁“瞠目不能答”[2],可见伦明对于梁氏都未有“阿附”之意,何况他人呢?
伦明《辛诗》“凡属于书者无所不纪”且重“书之聚散”,因此除了上述涉及粤吏藏家不论政绩只谈藏书外,也收录了如雷梦水所言的“汉奸等辈”。笔者认为这并非如雷氏所言,是由于著者本身受历史局限性的问题,而是伦明本身著述《辛诗》的出发点或目的性就很明确,即“凡属于书者无所不纪”“勿问其政声何似,而雅尚殊足嘉也”。另叶恭绰所评或有其依据,因其与伦明为同时之人且晚于伦明去世,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于五部续补诗中重复著录之人。如叶氏的批评属实,那么笔者推测,叶氏所言很有可能源于伦明采取的“笔记体”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简明扼要、生动易读、随记随写,故可能有传闻失实之处。叶氏于此既未细说,则有待后人查也。
4 结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12月由东莞图书馆整理的《伦明全集》(一至五册)成功付梓,成为研究东莞地方乡贤文献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由此进一步带动了研究伦明及其学术思想的热潮。在研究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领域,近两年亦有新作问世,如黄诚祯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研究》[12]、刘平的《记事存藏书史,抒情明读书志——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研究》[13]、孙雪峰的《伦明及其〈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述评》[14]诸文。这些文章从书籍内容、文艺评论、述评等多个角度对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进行了研究,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这些前人研究的成果中都未对新出的资料,即2016年8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全二册)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难免缺乏融会贯通的研究视野,从而影响对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客观评价。基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资料,融会贯通“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类的所有资料,进一步深入分析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通过横向比较,肯定其承前启后之功,同时也指出其“笔记体”的局限性,最后给予客观评价。